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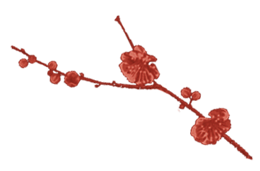
从柳凝丝到柳绣坊,既没有直达的公交,更没有地铁。这个地段出租车也很少。就算有出租车,柳凝丝也不会去打。离开林家的时候,林昱的妈妈倒是硬朝她口袋里塞了几百块钱,但是她舍不得花,别说是在外面打车了,连吃一碗几块钱的面条她也舍不得。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她从小跟着爸爸过惯了清贫的日子,养成了节约的习惯。如果她是爱虚荣、爱花钱的孩子的话,她早就花钱如流水了,她并不是没有机会得到金钱,从小到大,妈妈动不动就塞给她大把大把的金钱,但她从来没有正眼瞧过,因为爸爸从小告诉她,为人要有骨气,不是自己挣来的钱,一分都不该去动。她会把妈妈塞给她的钱,整整齐齐地放入妈妈留在家里的包里,那些包妈妈基本上不用了,妈妈有无数个包,每只包都有着显赫的品牌和昂贵的身价。直到有一天妈妈偶尔整理那些包,发现了那些已经发霉却依然码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气得破口大骂,以后再也不塞给她钱了。第二个原因,她口袋里的这几百块钱,并不是她自己的,是林昱的妈妈给的,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奢侈,尽管吃碗面条、打个车,根本算不上是奢侈。
整整步行了四十分钟,柳凝丝终于到了镜溪老街。还没有到达柳绣坊门前,她就站住了,那一路上因为想着柳绣坊而热乎起来的心凉了半截,因为她看见,那卷闸门的缝隙里,渗出一些灯光来,犹如泼洒的水银,泛在卷闸门的外面。
买主终于来接管房子了,柳绣坊,这座她和爸爸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屋,再也不属于柳家了!柳凝丝紧紧地咬着嘴唇,她在竭力控制着自己,控制自己不发抖,控制自己不哭,控制自己不慌张……她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哭叫、害怕是没有用的,今后一切都得靠她自己了。她很庆幸,离开柳绣坊的时候,把爸爸的骨灰带了出来。她贪婪地看着卷闸门下的灯光,仿佛想把这道灯光装进自己的心里去,她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最后一次看柳绣坊的灯光了,这相伴了她二十多年的灯光!
但是,她没有让这种眷恋在自己心里停留多久,眼下她要想办法去解决吃饭和睡觉问题。她刚挪出一步,就停住了,她看一个熟悉的东西——一辆汽车,一辆半新旧的国产两厢车,它就静静地停在柳绣坊门前。从卷闸门的缝隙泛出的灯光,也折射出一片映照在车门上,在那暗黄色的车体上映出一片同样泛黄的光来,好似一抹夕斜阳铺展在那儿。柳凝丝顿时感到一阵温暖,甚至有点激动,这种感觉以前可从来没有过。哎呀,刚才自己只顾着看卷闸门,门口停着这么大一辆汽车,竟然没有注意到。在门里的难道是……她低叫一声,一路小跑着奔向卷闸门。她举起手,刚想拍响门,却又猛然停住,她心想,不会敲错门吧?里面真的是翰林吗?她缓缓放下手,透过卷闸门的一处缝隙,朝里面看去,只见屋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打扫得纤尘不染,所有的物品都被摆放得整整齐齐。一个瘦小的年轻男性正站在凳子上,整理着装饰在刺绣壁挂上的绿萝。他的表情是那么专注,那近视镜片后的眼神是那样虔诚。那绿萝的摆放位置,本来已经很妥当了,可是他仍然在细心地搬弄着,仿佛要让每一片绿叶,都为刺绣壁挂烘托出最佳的效果来,仿佛这墙上的刺绣根本不是什么刺绣,而是一尊尊圣母挂像似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柳凝丝忽然失去了开门的勇气,刚才填满胸膛的喜悦感,也在慢慢散去,随之悄悄潜入的,是一股酸楚。她知道鲍翰林为什么会来,她知道鲍翰林为什么会这么细心地整理这间屋子,包括墙上的这些绿萝。可是,翰林,你这又是何苦!她背靠在卷闸门上,倚着那冰凉的门体,慢慢地滑坐到地上。
从下飞机到现在,鲍翰林连水都没喝过一口,他不觉得渴,不觉得累,不觉得饿,他只想把这个地方收拾得比什么地方都要好,因为这是他的心上人住的地方,实际上也是这么多年来,他的心灵的归宿。但不管什么样的情绪,也不能取代正常的感觉。当很多人早早地吃过晚饭上床休息了,那又渴又累又饿的感觉,还是不可避免地袭上了鲍翰林的身体,而且越往下等,这种感觉越强烈。他想起外面汽车里还有半袋子面包,那是他平常在外面干园艺活时,饿了填肚子的,以前为了省钱,他经常这样用几片面包对付一顿午餐。
他爬下凳子时,才发现因为在凳子上站立的时间太久了,腿都麻了。他拖着两条僵硬的腿,一步一步挨到卷闸门边,弯下身子,向上提起卷闸门,却不防一个人从外面向里倾倒进来。他吓了一跳,定睛一瞧,这个人不正是他做梦都想见到的凝丝吗?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下意识地上前一把抱住柳凝丝:
“凝丝,你,你怎么在这儿呀?可把我急死了……”他的嗓子哽咽了,再也说不出话来。
柳凝丝凝望着鲍翰林,心里一阵阵难过。翰林,你不该到这儿来的。
从小到大,鲍翰林还从来没有和哪个异性有过如此亲密的举止呢,包括柳凝丝。他意识到什么,赶紧放开柳凝丝,嗫嚅着说:
“对不起……”
“你是来带我走的吗?”
鲍翰林点点头。
“是我妈妈叫你来的吗?”
“是的,你妈妈还给了我柳绣坊的钥匙。但是,我要带你去的地方,跟你妈妈指定的地方不一样,那是我自己寻找的。我要带你去印尼,跟他们不在同一个国家。将来,我会靠自己的力量,买一座大花园,我要把这座花园送给你,我们一起生活在里面,生儿育女,没有任何人来打扰。那里没有谁认识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家庭背景,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
柳凝丝别过脸去:“翰林,你不该来的,我不会跟你走的,我永远不会离开这里。”
鲍翰林说:“凝丝,我知道,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一定以为,我跟他们是一伙的。我不是,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参与他们的任何事情。他们想盗挖若萱陵,我也是才知道的,我很讨厌他们做这种事,我一直从心底里厌恶,这你是知道。没错,你妈妈急着让你这个时候离开,是因为他们盗挖若萱陵以后,就会逃到国外去,再也不回来了,怕永远也见不着你,所以逼着你也出国。也许你会想,为什么我也会选在这个时候带你离开,那是因为,他们盗挖若萱陵,势必会引起巨大的轰动,那,用异样的目光看我的人就更多了,这样的目光我受了多少年,我再也受不了啦。我也不愿意别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你,不愿意别人在你背后指指戳戳,因为参与盗陵的,也有你的妈妈。所以,我才一心想着带你一起离开。我们的确是因为他们而离开,但绝不是去分享他们盗墓得来的财富,我们想去的地方,跟他们不在同一个国家,我们会离他们很远很远,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永远不见他们,他们也永远别想找到我们。”
听着鲍翰林的述说,柳凝丝不由得抬起头来,定定地看着鲍翰林。片刻,她痛苦地扭过脸去:
“翰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心的人,就冲这个,我也得对你说声谢谢。但是,真的很抱歉,我现在不能跟你走,因为我的事情没有完成,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若萱陵被盗挖。我柳凝丝虽然是个女流,但我毕竟是若萱的后人,是若萱先祖在这世界上仅存的后人。别人都在为保护若萱陵而努力,我身为若萱后人,能够袖手旁观吗?我的父亲就是为此而死的,如果我就这样离开的话,我的父亲会死不瞑目。”
柳凝丝的话仿佛一点也不出乎鲍翰林的意料。他点点头,说:“凝丝,别担心。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和你一起扛。”
柳凝丝有点不解:“你是什么意思?”
鲍翰林说:“我不会看着他们盗挖若萱陵。”
柳凝丝瞪大眼睛:“你——你和我一起去阻止他们?”
鲍翰林深深地点着头:“其实,在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不是刚刚才下定这个决心的。我不知道别人对盗墓这种事情怎么看,每当我看到有些人对盗墓小说那么感兴趣,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恨。我敢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厌恶盗墓的人,就是我鲍翰林,我这么说可能谁也不会相信,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盗墓贼的儿子,我的身上已经深深打上了盗墓贼儿子的烙印,别人看我的那种眼光,仿佛我就是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我爸爸可能不会想到,他这辈子挖了那么多墓,可是我周围的人却用异样的目光堆起了一座墓,被埋进墓中的人,正是他那唯一的、心爱的儿子!这么多年来,别人看我总是乐呵呵的,每天还与美丽的花草为伴,似乎总是那么快乐。可是谁又知道,我被深埋在那座谁也看不见的坟墓里,已经被埋了那么多年了,再不出来透透气的话,我真的要窒息死亡了!”
鲍翰林一时说不下去了,他别过脸去,他不想让眼中那闪烁的泪光被心上人看到。柳凝丝被鲍翰林的话震住了,不由得轻轻抓住他的手臂,叫了一声:
“翰林……”
平静了一下,翰林继续说:“我知道,要阻止他们挖若萱陵很难很难,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到。因为那个人从来不会听我的。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阻止他盗墓,可是他哪一次听我的呢?这一次,他同样不会听我的。但是再难,我也会去做,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帮你,谁来帮你呢?”
柳凝丝凝望着鲍翰林,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鲍翰林的目光重新转向柳凝丝,眼底凝结着一层无言的痛苦:“凝丝,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爱过我吗?我指的是像恋人间的那种感情,而不是兄弟姐妹间的亲情。”
柳凝丝静静地回望着鲍翰林,没有说话,她的眼神中闪烁着一种不忍,但她的眼神又明明白白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她不能说假话。
鲍翰林点点头:“我明白了。他说得对,我们之间的青梅竹马,是畸形的,这样的青梅竹马,怎么可能产生真正的爱情呢?”
柳凝丝一时绕不过弯来:“你说什么?谁这样说的?”
鲍翰林却答非所问:“就算真是这样,我也帮你,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柳凝丝隐隐猜到些什么:“我明白了。你去见了一个人,是那个人对你说了刚才这些话,对不对?”
鲍翰林没有否认:“虽然这些话刚听上去时很令人难受,但是事后想想,他的话是对的。我们不该相识,我们之间的青梅竹马的确是畸形的。可是谁叫我们相识了呢?我恨命运之神,他安排我走错了门,我不知道这是命运之神的故意捉弄,还是他的一时失误,或者,我前世欠了谁的情债,所以他故意在今世安排了这段错误的青梅竹马,来折磨我,我是还债来了。”
柳凝丝痛苦喊了一声:“翰林!”她摇了摇他的手臂,过了片刻才说道,“翰林,我不知道此刻该对你说些什么。是的,我承认我对你并没有产生恋人那样的感情,但我想告诉你,那个千年缘,其实我并不相信,它只是个传说,我不爱他。”
鲍翰林深深地点着头,似乎松了口气:“如果我帮你实现了愿望,你愿意跟我走吗?”
鲍翰林乞求地望着柳凝丝。良久,柳凝丝终于点了点头。
柳凝丝从碗柜里找出半个挂面,权当两个人的晚餐。当两个身心俱疲的年轻人端起碗来的时候,鲍翰林终于发现了柳凝丝颈部和手臂上的抓挠痕迹,他心疼极了。
“凝丝,这是怎么回事?谁干的?”
“没事。”柳凝丝掩饰着,她不愿意把所受的委屈说出来,这么多年来,她早已养成了自己的伤口自己舔的习惯。她只草草地说,去找妈妈,被人家当成了小偷,抓了一下。倒是有一点,她一想起来就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人一听说我是孙红菊的女儿,就吓坏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妈妈的名声原来那么大,那些人那么怕她。那些人究竟怕她什么呀?”
鲍翰林摇摇头:“我也不清楚。我和你一样,都讨厌这些事情,对这些总是离得远远。我爸爸从小也不许我关心这些事情。”
“你知道你爸爸在哪里吗?你对他了解多少?”
鲍翰林又摇摇头:“不知道,也不了解。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他了。”
“那,咱们到哪儿去找玉蟾,又怎么去阻止他去挖陵呢?”
鲍翰林说:“很多年,爸爸给过我一部手机,里面只存着一个号码。爸爸说,如果有紧急的事情,可以打这个电话,由接电话的人带我去找他。那部电话,我放在康平路的一栋房子里,那是我爸爸给我买的一栋房。今天太晚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去找那部手机,你说好不好?”
柳凝丝里升腾起一丝希望,好似一个漂泊在茫茫大海上的人,终于望见了一线陆地一般。
“他为什么不让你直接联系他,而要让中间人联系呢?”
“我记得我爸把那部手机交给我的时候,对我说,他是怕警察根据手机信号,测定他的方位。所以,他才会让中间人跟他联系。事实上,我随身的手机里还存有他的另外一个手机号码,但是我一次也没打过。刚才你回来之前,我试着拨了拨,没有能够打通,他不想让我直接联系他。也许我爸爸认为,他是盗墓的,警察会连他的家人一起监控。干这一行的人大概都是这样,疑神疑鬼,总觉得多绕些弯子,别人就不容易找到。”
柳凝丝难受地叹了口气:“可不是吗,我打我妈妈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
鲍翰林自嘲地笑了一下:“你妈妈一定以为,我已经把你接走了。他们盗起墓来,就更加没有后顾之忧了。可是,我们还在这里。”
柳凝丝瞪大眼睛:“你后悔了吗?”
鲍翰林收起笑容,一字一句地说:“为什么要后悔?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永远不后悔。”
当晚,鲍翰林就在柳绣坊里住了下来。鲍翰林还是第一次在柳绣坊过夜,他睡在柳烟尘的房间里。对于柳凝丝来说,也是第一次有一位除父亲以外的成年异性在自家过夜。不过,两个人都没有觉得别扭,反倒觉得这样住在一起,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半夜时分,柳凝丝突然惊醒过来,因为她在梦中觉得,有一双眼睛不声不响地注视着自己。睁开眼睛,竟然发现真的有一个人正蹲在床头,静静地、仔细地看着她的面孔。她吓得浑身一哆嗦,立刻认出,这个人是鲍翰林。她轻轻地叫了一声:
“翰林,你想干什么?”
“凝丝,我想知道,如果我没有承诺帮你一起去阻止我爸爸,你肯定不会跟我走,对吗?”
柳凝丝没有回答。鲍翰林趴在床边,无声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