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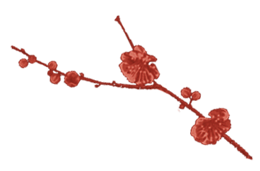
柳凝丝回到城里的时候,正赶上下班晚高峰。马路上都是密密麻麻的汽车,看上去令人生畏。柳凝丝歪靠在车窗上,望着窗外,目光呆滞。她觉得,自己就是漂在这车河上的一片树叶,漂快漂慢,漂向哪里,完全轮不到自己作主。
她没有回柳绣坊,而是直接去了古玩一条街。在这条街上,有一片名叫“通四海”的文物店,那是妈妈刚刚涉足文物生意时开的。小时候,她倒常跟着妈妈来这里,那时候经常一起来的,还有鲍翰林。但是,自从她懂事以后,就再也不来了。如果在林家洼时,她打通了妈妈的电话,那么这次她也不会到这儿来。可当时在电话听到的都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在她的印象中,能找到妈妈的地方,似乎只有这里。
通四海文物店门面只有几平方大小,后面还有一小间,这条街上的文物店一般都是这样的格局。柳凝丝看到,店门开着,这让她心里暗暗透了口气。刚才她一路都在担心,会不会一到这里,就见到铁将军把门,毕竟这几年来,妈妈直是大忙人。
走到门口,才发现店内的布局与印象中相比大不一样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上次到这里来时,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十几年中,一家商店更换货柜、改变货物摆放,是很正常的事情。没看见街上的商场几年就会装修一次吗?那是为了以新意吸引客户。
一声“妈妈”到了嗓子口,却没能喊出来。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喊妈妈了,自从小时候撞见妈妈与老锹的那一幕后,“妈妈”就成了一个令她一想起内心就隐隐作痛的词,她不愿意想这个词,也不愿意看到、说到这个词。不,这绝不代表着她讨厌这个词,实际上一看到别人的妈妈,她就油然而生起一股亲近的情感,油然想喊上一声“妈妈!”可是越不愿意想起这个词,就越是难以忘记。是啊,只要是动物,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词,因为从生命孕育的那一刻起,这个词就融进生命里了。
店里没有人,也没有开灯。或许妈妈是在后屋吧?柳凝丝悄悄穿过前店,直接进了后屋。她不想在前屋停留,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来过这里,就像自从她懂事后,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是孙红菊的女儿一样。后屋也没有人,或许妈妈是临时出门办个什么事儿去了。她悄悄地找了一个昏暗的角落,静静地站在那儿。她想静静地在这里等,等妈妈回来,她回来了,会看见她的。
柳凝丝可不知道,她一进店,就被一双眼睛盯上了。这双眼睛就藏在柜台后。不,说藏不合适,它原本就在那儿,眼睛的主人猫着腰,在那儿整理着柜台里的物件。如果柳凝丝进店时细心点,便会发现柜台后有一样东西反着光,那是一个肥肥的秃脑袋,店主人的脑袋。秃脑袋瞪着那双同样肥肥的眼睛,警惕地观察着柳凝丝的一举一动。当柳凝丝顺手拿起一件青花瓷瓶观看的时候,秃脑袋蹑手蹑脚地从柜台里走出来,一个虎扑,便扑到了柳凝丝的身后,呼地一下,胳膊便勒上了柳凝丝的脖子,嘴里嚎着:
“嘿嘿,小偷,这回看你往哪里逃!”
秃脑袋的那支胳膊比象腿细不了多少,柳凝丝那细嫩的脖子如何受得了?她顿时被勒得喘不过气来。一失手,青花瓷瓶便啪地掉到地上,砸得粉碎。这下秃脑袋更加来劲:
“啊?还敢砸我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一边紧紧勒住柳凝丝的脖子,一边扯过一条绳子,企图将柳凝丝捆绑起来。突如其来的袭击,把柳凝丝吓坏,片刻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本能地用力挣扎起来,边挣扎边喊叫:
“我不是小偷,我找人!”
但柳凝丝的喊叫根本不起作用,那支肥胳膊勒得更紧:
“还狡辩!不是小偷,你鬼头鬼脑到我店里来干什么?一个星期,我这店里就连丢了三回东西,这回总算逮着你了!”
柳凝丝拼尽全身力气一挣,好不容易喊出一句话:
“我真的不是小偷,我来找我妈妈,我妈妈是孙红菊!”
这句话起了神奇的作用,秃脑袋一下松开了胳膊,绕到柳凝丝的前面,怔怔地看了柳凝丝一阵,吃吃地说:
“你,你找孙红菊?你是孙红菊的女儿?”
“是……”
柳凝丝捂着胸口,喘着气,边说边恐惧地往后退着,准备向门口逃。却见秃脑袋突然扬起那只肥肥的咸猪手,啪!啪!狠狠地在自己那张肥得跟面盆似的脸上揍了两下:
“瞧我,怎么敢冒犯孙二娘的千金!对不起啊对不起,是我瞎了眼,姑娘,你可千万别告诉你妈妈,千万千万,拜托了!”
这样一来,柳凝丝倒暂时停止了后退,只是小心地与秃脑袋保持着距离:
“我妈妈呢?”
“你妈妈……”秃脑袋心中疑窦忽生,“怎么,你连她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你究竟是不是孙二娘的女儿?”
柳凝丝赶紧连连点头:“我妈妈就是孙红菊,这间店原来是我妈妈开的呀,我为什么要冒充?小时候我经常来这儿?”
“哦。”秃脑袋眼中怀疑的火光黯淡了许多,“她上个星期把店转给我了。”
“那,她去哪里了?您能联系上她吗?”
“这我可不知道,她没留电话。她好像急着要把这间店转出去,说实话,给我的价很低。我也奇怪,我们这行当里谁不知道孙二娘的身价?她哪会缺钱哪?”
秃脑袋絮絮叨叨地说着。柳凝丝不敢再停留,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才想起那被摔碎的东西:
“那只花瓶——”
秃脑袋赶紧摇摇手:“算了算了,我能跟孙二娘的千金计较这个吗?我瞒谁也不能瞒您,这也不是真品!”
柳凝丝半秒钟也不想停留了,向街上逃去。她沿着街道一直往前跑着,直至跑到一处河边,才停了下来。这时她才感觉到双腿发酸发软,再也迈不动了,心跳得仿佛欲从嗓子口蹿出来,而夜色不知不觉间已经掩盖了一切。
她不知在河边的条凳上坐了多久,夜色把她的身体浸得冰凉,连心也是凉的。可是脖子部位和胳膊、手腕上那火辣辣的疼痛,却一点没有减轻,这都是那个男人干的。从小长到这么大,她还从来没有被一个男人这样粗鲁地对待过呢。一想到这个,她便无声地哭了。但只呜咽了两声,她就停住了。不,我没有资格哭,她在心里说,爸爸死了,妈妈跟我不是一条心,现在只剩下我自己了。为了爸爸,为了祖陵,我不能哭。她狠狠地擦了一把眼泪,环视了一下四周。不知不觉间,四周的人已经开始稀少,夜已渐深。她感到肚子饿得厉害。我得填饱肚子,找个地方休息,养足精力,才能继续跟他们斗,她想。
柳绣坊与这里隔着三条街。柳凝丝犹豫了一下,拔腿朝柳绣坊走去。妈妈曾说,已经将柳绣坊卖掉了,她为什么那么急着卖呢?就跟卖她的四海通店面一样。不知道买主接管柳绣坊没有?先去那里看看,只要买主一天没来,我就住在柳绣坊住一天,那里是我跟爸爸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地方,到处都留有爸爸的气息,别的地方再也没有这种气息了。一想到这些,柳凝丝的眼睛便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