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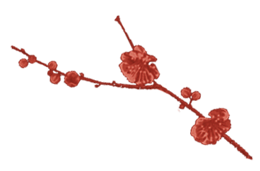
或许是因为有心事,也或许是因为第一次在这陌生而又熟悉的林家小院吃饭,这顿饭柳凝丝吃得很矜持,只小口小口地扒拉着饭粒,把热情劝饭的赵瑞芳弄得很是着急:
“孩子,你吃这么点怎么成呢?你看你,跟个大小姐似的,只吃这么一点点,那哪能饱呀?人家米妮吃起饭来……”
赵瑞芳的话没说完,就被丈夫在桌底下踩了一脚。她这才意识到说漏了嘴,赶紧住了口。林诗达放下手中的酒碗,对柳凝丝说:
“孩子,我们知道你有心事。你跟我们千万不要客气。如果觉得我们能帮你做点什么,你尽管开口。”
柳凝丝正在埋头扒拉饭粒的动作突然停住了。过了片刻,她抬起头来,目光缓缓扫过林家三口人,说:
“林叔叔,林阿姨,林昱,你们一家人对我这么好,完全把我当成了自家人。我爸爸,还有我,给你们添了那么多麻烦。林家和柳家又有着那么长那么深的缘分。所以,我们家的事情不应该再瞒着你们了。但是,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实际上,实际上都跟我的母亲有关,那,那实际上是我们家的家丑。”
柳凝丝说不下去了,重新把头埋下去。当她再次抬起脸上,面颊上已经泛起一股绯红,与对面喝了几口酒的林诗达的脸色一样红。但和林诗达不一样的是,林诗达脸上的红带着一股酒意的舒适,而柳凝丝的脸红则是因为羞愤,旁观者谁都看得出来。林家的三个人几乎都不敢看柳凝丝的眼睛,因为怕看见她眼中的泪光。林昱知道,父亲所问的事情,必定触及到她心中的最耻辱处,如果让她开口讲出这些事情,等于是由她在亲手揭开自己心中的疮疤。林昱心中不禁一阵阵发疼,真不希望她继续讲下去,可是好奇心又驱使他支起耳朵,想弄明白柳家究竟发生了,弄明白她家里发生了什么,才能够有的放矢地去帮助她呀。林昱想起前天上午召开的案情分析会,忍不住问道:
“是不是也跟一个名叫老锹的人有关?”
柳凝丝一下子瞪大了眼睛。林昱从这双泉水般清澈的眼睛里看到一种东西,它犹如冬日的寒雾一样在眼底若隐若现,林昱的心仿佛被一双手揪了一把,他一下子看明白了那种东西是什么,那是一种恐惧,一种包含了羞惭与戒备的恐惧。林昱真后悔问了刚才的话。他朝父母使了个眼色,装作一心一意吃饭的样子,埋下头扒拉起饭粒来。
晚上,月光如同水银一样洒满林家小院。在这个流淌着甘醇酒香的小院里,响起了古琴的弹奏声。林诗达的琴平常就放在院中的桂花树下。但今晚奏响这架古琴的,并非林诗达,林诗达的琴声古朴而逸致,琴音里自有一种隐者超然物外的情怀。而今晚的琴声里却蕴含着清冷、孤独与一股深深的落寞。琴声传到林氏夫妇的房中,正披着衣服练字的林诗达不由得停下手中笔,对赵瑞芳赞道:
“唉,这才是若萱娘娘的后人啊,琴弹得这么好。”
林昱早已循声跨出卧室,站在屋檐下静静地聆听着,咀嚼这与以往院中飘出的截然不同的琴音。清泠的琴声忽然停住了。柳凝丝望着屋檐阴影下的林昱,幽幽地说:
“我爸爸教我的,他弹得比我好。我爸爸还会刺绣,绣得也比我好,柳绣坊就是他开的,在镜溪老街开了很多年了,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可惜生意一直不好。我爸爸是个很好的人,可他不适合做生意,他适合去当老师,到大学里教教古典诗词,可是他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连一般的工作也找不着,生存都成问题,他这一生过得很窘迫,很无奈。”她说着停了下来,咬着嘴唇,仿佛下决心似的重新抬起头,说,“你猜得没错,我们家的事情,的确和老锹有关。”
林昱心想,果然是这样。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老锹的?”
“我第一次见到老锹,是在5岁那年。”顿了一下,她又说,“认识老锹,是从认识他的儿子鲍翰林开始的。”
林昱脑中闪过那天在柳绣坊见过的那个挂绿萝的男孩子的情景:
“鲍翰林,就是我第一次去柳绣坊,见过的那个挂绿萝的男孩子吗?”
柳凝丝眼波闪了一下,点了点头。林昱有点纳闷,老锹的儿子不是叫鲍掘吗?但他忍住了,暂时没有提出疑问。
柳凝丝说,那个时候,她在离镜溪老街挺远的实验幼儿园上学。
其实离柳绣坊不远处,就有两所挺好的幼儿园。之所以到那么远的地方读幼儿园,是父亲柳烟尘提出来的。柳烟尘觉得,柳家是诗书世家,柳家的孩子上学堂,当然得找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老师,从凝丝诞生的那天起,这个心愿便在柳烟尘的心里扎下了根。
实验幼儿园是当时杭州城内最好的幼儿园之一。进入这样的幼儿园就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能够进入实验幼儿园的,除去施教区的孩子外,要么就是官员的子弟,要么就是花上大笔赞助费买进来的。柳烟尘既非官员,又非有钱人,柳凝丝也不在这所幼儿园的施教区范围之内。可是柳烟尘自幼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气节的濡染,又时刻不忘自己是若萱娘娘的后人,生在传承千年的贵族兼诗书世家,骨子里自有一股傲气,觉得自己比周遭的人高上一等,既不屑去拉关系,也不屑与权贵铜臭为伍。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书呆子,又觉得自己是个看透一切的智者,有点类似于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著名的孔乙己。
可想而知,柳烟尘带着柳凝丝去实验幼儿园报名,当然是碰了壁。柳凝丝的妈妈孙红菊气不打一处来,积蓄了多年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直骂柳烟尘“看上去儒雅有学问,其实假清高,死没用,想吃天鹅肉,实际上自己是只癞蛤蟆,偏偏还以为自己是只金蛤蟆呢,嫁给了你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买不起,还不如嫁一个叫化子”,骂得柳烟尘羞愧交加,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只能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是真的满心内疚,觉得既对不起老婆孙红菊,也对不起女儿柳凝丝。孙红菊自从嫁入柳家以后,他还真的没给孙红菊添过一件漂亮衣裳,更别说什么金银首饰了。他并不是不想买,而是没有钱啊。守着这个生意萧条的柳绣坊,能让一家人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现在女儿想上所好学校却上不了,还不是因为无钱无权无势?孙红菊大哭一场,甩门而去,临出门时甩下一句话:
“这学,别上了!你们柳家不是诗书世家吗?你柳烟尘自己留在家里教好了!”
然而,孙红菊出门后不久,又重新返了回来,一把抱起蜷缩在屋角的小凝丝,说:
“走,凝丝,妈妈带你报名去!”
小凝丝怯生生地说:“妈妈,我不上学了,您别再骂爸爸了。”
孙红菊口袋里抽出一大叠钞票,笑着对小凝丝说:“妈妈有钱,妈妈带你去上学,上最好的学校。”
柳烟尘惊呆了:“红菊,你哪来的钱?”
孙红菊轻蔑在瞥了他一眼:“跟生意上的朋友借的。有本事你也去借呀。”
柳烟尘无言以对。他知道,孙红菊因为嫌弃柳绣坊生意不好,几个月前已经开始学着做一些古董生意。
上学的第一天,孙红菊牵着小凝丝的手,把她带到一个瘦小的男孩子面前,说:“凝丝,认识一下,他叫鲍翰林。妈妈特地跟老师打了招呼,让你们俩坐在一块儿,今后他就是你的同桌了。你以后可要对翰林好,就是他爸爸借钱给你报上名的。”
小凝丝拼命地点着头,心里对这个怯生生的小男孩感激极了,仿佛他是自己的救星似的。在家里的时候,她曾对妈妈说不想上学了,其实那都是假的,她是怕爸爸继续挨骂,实际上她心里对这所漂亮的学校喜欢极了。
下课的时候,小翰林悄悄告诉小凝丝一个秘密,他没有妈妈,他的妈妈被土砸死了,他真想把小凝丝的妈妈当成自己的妈妈。小凝丝慷慨地说,她同意小翰林喊孙红菊妈妈,只要让她妈妈天天晚上回家陪她睡觉就行。就在那天,孙红菊用自行车载着小凝丝和小翰林二人,去了一座漂亮的大房子。小凝丝和小翰林互相勾着肩进入了一间大屋,在那里,小凝丝见到一个跟爸爸年纪差不多的人,这个人比爸爸身材瘦小多了,看上去却比爸爸精干多了。一见到这个人,小凝丝就想起在家中房梁上蹿来蹿去的老鼠。可惜的是,那人瘸了一条腿。小凝丝悄悄问妈妈,这个人是不是老鼠变的?因为他的眼睛就像老鼠的一样亮。妈妈却轻轻打了她一下,告诉她,他就是鲍翰林的爸爸,就是他出钱让她上的学。在小凝丝眼中,这个老鼠一样的男人顿时像山一样高大起来,可是她心底对这个男人却有些害怕,因为他总是阴着脸。他只看了小凝丝一眼,就把目光游移到别处,阴着脸说了一句话,也不知到底是说给小凝丝听的,还是说给孙红菊听的:
“没事,好好学吧,以后我供你读博士。”然后又加了一句,“这孩子水灵,以后给我当儿媳妇吧。”
孙红菊乜斜着眼睛瞅着鲍翰林的爸爸,声音说不尽的妩媚:
“老锹,你索性连我也一块儿娶了吧。”
老锹无声地笑了,老鼠眼中迸射出的亮光,仿佛银光闪闪的钩子一样钩住了孙红菊。
这一天,小凝丝回家特别高兴。一回到家里,她就高兴地告诉爸爸,自己上学了。爸爸没有说话,只是把她久久地搂在怀里。她奇怪地问:
“爸爸,您不高兴吗?”
爸爸一遍一遍地轻抚着她的背,笑着说:“高兴,高兴。”
小凝丝却发现,爸爸的笑容是那么勉强,那么坚硬,带着一股寒意,就像有一年冬天她家屋后的镜溪里的结的那层薄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