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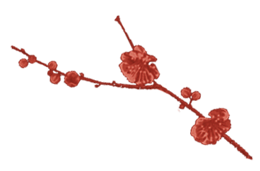
林昱直接去了局里。被雨一淋,他的脑袋冷静下来了,想起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雨伞忘在了镜溪茶缘,但他说什么也不敢回去拿了。米妮可就在那一带赏梨花呢,万一真的撞上这小母夜叉,那可怎么收场?第二件事是,刚才真不该对老宫那样发火。他是自己的领导不说,人家可都是为了什么呀?人家一心想保护文物,何况眼下要保护的对象,与他们林家还着不解之缘,从某程度上来说,大家是在帮他林昱的忙。
到了局里,他的身上已经淋得半湿了。他看到一辆警车停在院中,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往会议室里搬着投影设备,想必案情碰头会就要开始了。他是喷嚏连天地走进会议室的。邢警队安队长、文物局稽查大队长老宫他们果然也都在。老宫一见林昱的狼狈样,连忙丢过一包纸巾:
“快擦擦。怎么搞的?怎么没带把雨伞?为了工作也不能不顾身体。”
林昱只好顺着老宫的话说:“没什么,一点小雨算得了什么?革命前辈为了人民幸福,刀山火海也照样闯,和他们比,我差远了。宫队,刚才我在电话里态度不好,不该向您……”
老宫不耐烦地摆摆手:“说这些干什么?别跟个老娘们似的。好啦,就等你一个人呢,你到了,人就齐了。老安,咱们这就开会吧?”
安队点点头:“好,同志们,咱们抓紧时间开会。今天这个会呢,主要是汇总一下案情,捋一捋思路,更顺利地推进案件侦破工作。”他把目光投向林昱,“怎么样,小林,今天去了柳绣坊吧?刚才我们还在说你呢。”
林昱把刚才跟那个女孩在镜溪茶缘见面的情况,作了大概汇报。当然,他隐去了两点,一点是他对那梨花一样的女孩怦然心动的感觉,那种感觉没法儿在这种场合言说,说了别人也不一定能理解。还有一点,就是女孩托付给他的柳烟尘的诗稿,这与案情没什么关系。
安队一边听,一边不时点着头,还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安队听完,和宫队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那只玉蟾上果然有文章,和我们分析得一模一样。”
老宫摸着脑袋,对林昱说:“这个女孩子是什么意思呀?前面老是提醒你,别让盗墓分子偷走玉蟾,这会儿又让咱们甩手别管了,任由别人挖若萱陵去。她到底想干什么?”
安队看着林昱,沉吟着说:“玉蟾没能守住,这个女孩子是对你们林家失去信心了。再加上你的母亲又曾经被那帮家伙绑架过,她担心你的家再受到牵累,就索性听天由命了。这个女孩很善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夺走玉蟾的那帮盗墓分子不是一般的人物,很难斗,女孩子心底对他们也很害怕。”
林昱听得连连点头,安队的确分析得有道理。
老宫又把目光投向林昱:“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
林昱摇摇头:“不知道。”
老宫不满地说:“接触了几次,连个名字都没弄清楚,瞧你这个侦察员当的!这样,你下午不要歇着,我和你一起,赶紧再去找那女孩子,告诉她,咱们为保护若萱陵,已经成立了专案组,不是一般的专案组,是由区公安局副局长亲任组长的专案组,什么样的罪犯也翻不了天,要给人家以信心,她才肯与咱们合作,明白不?”
林昱一个劲儿地点头,满脸通红,诚惶诚恐。安队却微笑着说:
“不能要求太高,新兵嘛,又没学过刑侦,瞧身上都淋湿了,能这样跟着吃苦已经不错啦。我们这边也有了些收获。半个月前,阳山市公安局抓获了几名盗墓分子,其中一人名叫彭四郎,绰号钻地鼠,从小和老锹一块儿长大,这两个人刚出道时,曾经搭裆一块儿盗墓。”
随着安队的讲述,悬挂在会议室正前方的一块幕布亮了,上面出现了一个约摸五十岁的男子,穿着黄色的号服,坐在铁窗内。这个人物一出现,会场上就发出轻微的笑声。把这个家伙称作“钻地鼠”,还真没有冤枉他。瞧他那獐头鼠目的样子,不就像只老鼠似的吗?那两只眼睛还贼亮贼亮的,骨碌碌乱转着,仿佛在寻找哪里有个洞可以钻进去。跟彭四郎隔窗而坐的,正是穿着警服的安队和专案组成员王雷。安队问着什么,王雷专心记录着。
安队说:“昨天下午,我和小王去了趟阳山,突击审讯了彭四郎。我们的运气不错,彭四郎把他所知的有关老锹的一切,全都倒给了我们,许多情况是我们没有掌握的,包括老锹过去的经历等等。”说着,安队自己忍不住嘿嘿笑起来,“并不是我们的审讯技术有多么高明,而是这只钻地鼠与老锹有着生死之仇,他差点死在老锹手里,他恨死了老锹,巴不得老锹也被我们逮起来哩。”
幕布上,彭四郎那戴着手铐的双手挥舞着,面红耳赤,很激动的样子。
接着,幕布上又投映出一个新的形象。这个形象刚一出现,林昱的嘴巴就一下子张得老大,差点叫出声来。幕布上的这个男子,分明就是第一次去柳绣坊时,见到的那个挂绿萝的瘦小男子。但随即,林昱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幕布上的这个人明显要黑一些,皮肤也比柳绣坊的那个男子粗糙,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为什么那么神似呢?
安队的话继续响着:“这就是老锹,真实名字鲍秋生。这家伙是阳原县前山村人。他不仅善于挖掘,为了准确地找到墓地,还刻苦学习风水知识,往往能够一下子找准墓葬所在地,盗起墓来又快又准,所以江湖上送他绰号‘老锹’。在一次和其他盗墓贼的拼斗中,他被打断了一条腿,所以江湖上也称他为老瘸。但令同行叹服的是,这位老瘸安上假肢后照样行走如飞,或许也正是身体残疾而影响到其心理,他行事比一般的盗墓贼更加狠辣,敢打敢杀,很多同行都吃过他的苦头,没有一个不怕他。”
林昱突然想到一点,这两个人会不会是父子关系呢?柳绣坊里的那个瘦小男子,会不会是幕布上这个老锹的儿子!
一想通了这一点,林昱的脑袋不由得“嗡”地响了一下。老锹的儿子为什么会出现在柳绣坊里呢?他还自称是柳烟尘女儿的男朋友,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吧?他参与父亲的盗墓行动了吗?柳烟尘的女儿知道自己男朋友的家庭背景吗?她有没有陷入到里面去?这么一想,林昱背上的冷汗汩汩直下。他想对着老宫老安他们说出自己此刻心中的真实想法,可是脖子却像是被谁掐住似的,发不出一点声音,连身子也麻木了,只能像根木头似的呆坐在那儿。他听到心中另外有个声音不断地对自己说,不不,不能说出真相,万一那个女孩真陷进去了,这一揭发不就把她送进监牢里去了吗?
稽查队员刘昊天说:“传说这老锹也是穷苦出身,许多人正是家里穷,才走上了盗墓这条路。”
老宫白了这位下属一眼,说:“那不一定。我小时候家里也穷,我也挖洞,但我挖的不是盗墓的盗洞,而是螃蟹洞,黄鳝洞,逮点螃蟹、黄鳝啥的换点零花钱。”
安队继续说:“没错,老锹小时候家里确实很穷,他的父亲在他五岁那年就去世了。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拉着家里同样穷困的彭四郎走上了盗墓这条路。但是,二人的合作并不长久。”
多数听者都等着听安队的下文。却听老宫说:
“是因为二人并非血亲关系?”
安队赞许地点点头:“没错,到底不愧是老文物,了解盗墓行业特点。”
老宫扭过头来,对着大家说:“专业盗墓贼往往是两个人合伙,原因很简单,人多的话分赃的也多,而且人多容易暴露目标,一个人单独干的也很少,一个人顾不过来。而两个人可算得上是黄金组合,挖盗洞时,可以一个人负责挖掘,另一个人清土,兼带望风。挖进墓室后,另一个人在上面接取坑土和随葬品。这对搭裆为什么要选有血缘的亲戚呢?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谋财害命。一个盗洞往往有四、五米深,又陡又滑,通常只靠绳子上下。想想看,如果下面的人把挖出的宝贝递上去,上面的人拿了宝贝以后,却不拉下面的人上去了,或者当下面的人快到洞口时,猛地一松绳子,再把挖出的坑土往下一填,那下面的还能活命吗?就算喊救命也没用,因为陵墓往往地处偏僻,人迹罕至。下面的那个人可就直接殉葬了。所以,盗墓贼们对于搭裆之间是否是血亲十分看重,有了血缘关系,互相之间就难以忍心下手了,安全性就高多了。”
安队长竖起大拇指:“老宫,您要是出个《盗墓指南》之类的册子,一定能够成为盗墓行业的指导用书。”
安队的玩笑,引得大家轻笑起来。老宫得意地晃着脑袋,毫不谦虚地说:
“就是,你们多学着点,当然不是叫你们学着去盗墓,多懂点,将来对付盗墓时用得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安队呷了口水,说:“彭四郎说,每次盗墓,老锹都借口自己腿脚不好,让彭四郎钻盗洞,实际上他是多了一个心眼儿,防着别人对自己下黑手,可他自己就存了这样的心思。有一次在河南盗挖一处古墓时,彭四郎在递上墓葬品后,拽着绳子往上爬。爬到一大半时,老锹却松开绳子,彭四郎差点没摔死。老锹正准备把坑土往盗洞回填,企图活埋彭四郎时,幸好有人路过,彭四郎捡回一条命。彭四郎爬出盗洞后,从此跟老锹分道扬镳。不过那仇恨可就埋在彭四郎心里了。他暗中注意老锹的行踪。在一次老锹出售盗来的文物时,他向警方举报,老锹被逮个正着。现在幕布上出现的这张老锹的照片,正是被捕时拍下的,离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可惜的是,除此以外,目前再也没有老锹的其他照片。他的照片之所以这样少,实际还是在防范公安人员,相对来说,他的个人资料外泄得越少,他就越安全,他的反侦查意识由此可见一斑。江湖上传言,这次潜回国内之前,为了躲避警方打击和仇家报复,老锹特意整了容,已经完全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谁也认出不他了。”
老宫咂了咂嘴巴,说:“这么说,你提供的这张照片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林昱的脑海里又一次闪现出柳烟尘女儿的形象,心里说,但愿她的男朋友跟老锹完全没有瓜葛。
安队也咂了咂嘴巴,仿佛在跟老宫一起品尝着什么美食似的,遗憾地说:“是啊,目前看来是这样,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还很有限。”
稽查队员李丁问:“后来老锹继续盗墓了吗?”
“当然。”安队说,“这是他的老本行,他不会轻易放弃的。从那以后,可没人敢跟老锹合作了,都怕心狠手辣的老锹下黑手。据说老锹找不到其他搭裆,只好拉上自己的老婆巩翠芬。他的老婆可不走运,第一次出活,就遇上塌方,被活埋在陵墓里。他跟巩翠芬感情很深,属于那种患难夫妻。年轻时老锹因为家穷,腿瘸,又有盗墓贼的坏名声,没哪个姑娘愿意嫁给她,但巩翠芬没有嫌弃她,跟老锹做了夫妻。老婆死后,老锹悲痛欲绝,差点也去陪葬。老婆过世以后,老锹就带着儿子离开了老家,住进了杭州。在杭州,他重新找了个女人,这个女人是早年间做点文物小生意时傍上老锹的。”
随着宫队的话语,幕布上打出了一个中年妇女的形象。这个女人浓妆艳抹,倒也有几分姿色,却是面带横肉,目露凶光,一看就是个很厉害的女人。只听宫队继续说道:
“这个女人,就是已经过世的柳烟尘的妻子,名叫孙红菊。”
安队的话,令林昱大吃一惊,禁不住“啊”地叫出声。这样一来,安队的叙述便被打断了。他把目光投向林昱:
“怎么了,小林,有什么不对吗?”
这样一来,林昱倒不好沉默了,他红着脸说道:
“她真是柳烟尘的妻子?柳烟尘的妻子,居然是老锹的姘头?她既然是柳烟尘的妻子,那么她就是柳绣坊里那个女孩的母亲了?那个像……像宋词一样宛约的女孩子,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母亲呢?”
林昱的忸怩,引得大家发出一串善意的笑声。宫队不屑地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到监狱里去看看,有多少犯罪分子没有妻子、没有丈夫、没有儿女?他们的妻子、丈夫、儿女,不也个个跟柳烟尘父女一样,都是无辜的?可他们都背负了沉重的压力啊。”
老安继续说:“老锹用盗墓发的财在杭州城里买了房,重新安了家。孙红菊不但成了他实际上的夫人,而且还是他的得力助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帮助老锹控制着手下,成了江南盗墓圈内赫赫有名的‘孙二娘’,在整个文物一条街也是说一不二,是不折不扣的母老虎、大姐大,文物一条街上有句歌谣‘想玩古玩,先拜二娘’,这个二娘,就是指孙红菊。不少商户因为冒犯她而吃过她的苦头。为此她也曾经受过公安机关的打击,被判过刑。但她出来后反而变本加厉,但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引出老锹这条大鱼来,我们暂时还不能动她。”
老宫突然一拍大腿:“咳,我说,我们可真笨!那女孩既然是柳家的人,肯定知道自家的祖坟在哪里。老锹不是一心想着掏若萱陵吗?咱们问清楚若萱陵在哪里,去若萱陵蹲着,来个守株街兔,不就得了?”
老宫的话,引得屋中其他人纷纷赞同。安队却摇摇头,说:
“我看未必那么容易,可以试一试。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柳烟尘的老婆孙红菊是老锹多年的姘妇,两个人是一丘之貉。按照老宫的逻辑,孙红菊也应该知道若萱陵的位置。如果这背后的盗墓分子真是老锹的话,孙红菊难道不会把萱陵的方位告知老锹,还用得着在玉蟾身上费劲吗?”
安队的分析,又引得大家不住点头。
老宫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背后的人物未必是老锹?”
安队说:“现在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也许这个女孩和孙红菊都不知道若萱陵的位置。但是,我个人觉得,背后的大盗墓贼是老锹的可能性更大。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才千方百计去查找有关老锹的信息,以及他与若萱陵之间的一切联系。”
老宫说:“那老锹到底在哪儿呢?”
安队说:“目前还不知道他的确切下落。各种各样的传言很多,最可靠的说法是,他在马来西亚买了一个很大的农场,从此金盆洗手,怡养天年。前天我们通过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协查请求,请他们查一查近二十年来华人在马来西亚购买大型农场的情况,国际刑警组织效率非常高,很快就发来了协查结果,这得感谢现代化互联网信息系统,无论查什么,摁上几个键,结果都出来了。”
老宫问:“那查到老锹的信息了吗?”
安队说:“没有。但是我们注意到,有一位名叫包凡的华人曾在十年前买下了马来的一处大型农场。我们怀疑,这个包凡是不是老锹的化名。”
老宫说:“化名?怎么化名?”
安队说:“你想想看,老锹名叫鲍秋生,而他的亡妻名叫巩翠芬,他会不会在自己与亡妻的姓字中各取一半,组成新的名字?”
李丁说:“鲍取一半是鱼……”
刘昊天反对说:“鲍取一半是鱼,那剩下的一半不就是包吗?”
老宫思索着:“‘鲍’中含有一个‘包’字;‘巩’中含有一个‘凡’字。组成新的名字正好是包凡。”他突然拍了一下桌子,把别人都吓了一跳,“肯定是老锹!取包凡这个名字,即遮人耳目,又纪念了他的亡妻。唉,这个盗墓贼虽然对别人心狠手辣,对自己的亡妻可算是有情有义了。”
安队却摆摆手,说:“不,光凭名字,我们还不敢作出这样的推断。据马来警方提供的情报,有几次,邻居看到这家农场的主人撑着拐杖在行走,而老锹也瘸了一条腿……”
老宫一拍大腿:“那不就是他吗?他人呢?”
安队说:“不见了。”
“不见了?”
“对。大约五年前,这家农场换了主人。”
“什么情况?”
“据马来警方反映,农场主人包凡好赌,不仅把好好的一座农场赔掉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不得已卖掉了农场,为了躲避债主,包凡也失踪了。”
“那他可能去了哪里呢?”
安队说:“老锹好赌,我们在提审彭四郎时,也得到了证实。我私下里作了这样一个推断:老锹输掉了苦心购置的农场,没有了退路。又欠了一屁股债,遭到当地黑帮的追债。他在马来混不下去了,不得已离开了马来。可他又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一心想东山再起,于是,潜回国内,重操盗墓旧业,这是他的特长,他也只能干这个。他急于发个大财,以打个翻身仗,所以一开始就把目光盯上若萱陵。于是,我们的斗争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私人角度讲,我安某要感谢这个即将到来的新阶段,因为这为我提供了抓捕老锹的机会,否则,就算到了另一个世界,我脸上的这道疤也将一直成为我从警生涯的奇耻大辱!”
安队的一席话,说得大家血流加快,心里升腾起一股似悲愤又似兴奋的情感。
安队环顾了一下大家,说:“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所得到的情报。今天开的,算是个务虚会。希望今天提供的这些情报,能对大家接下去的侦查提供一些帮助。现在的关键,是尽快找到若萱陵,决不能等到我们发现若萱陵的时候,里面已经被盗空了,那我们就成历史的罪人了。对了,在宫队长的亲自布置下,我们的疑兵计开始起作用了,现在文物贩子中到处在传我们已经找到若萱陵的消息。”
老宫呵呵笑着说:“计策是你安队长出的,你才是诸葛亮啊,我只是照你的计策行事而已啊。”
安队也笑了笑,继续说:“宫队还安排了人,在一些有可能出现若萱陵的地方加强了巡防,估计老锹见了这样的声势,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若萱陵暂时还是安全的,这为我们的侦破工作争取了时间。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安全,老锹是什么人?几十年的大盗了!他很快就会识破我们的计策。一旦他发现我们是在虚张声势,会立刻动手掘陵。所以,同志们,我们必须跟时间赛跑啊,要做到两确保,既要确保若萱陵万无一失,又确保将老锹一伙一网打尽!”
安队说着摆摆手,示意散会。林昱募地想起上次母亲被绑架时,自己没有及时报警一事,再也忍不住了,霍地站起来,说道:
“安队,我有情况汇报。我,我见过一个人,跟刚才照片上的老锹非常相似。”
安队问:“谁?”
林昱又有点犹豫起来:“我不知道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准确,但我怕漏掉情报信息,上次玉蟾的事情我没有及时报警,已经造成工作上的被动了……”
安队说:“不要紧,有什么情况及时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分析么。”
林昱说:“我怀疑,那个人是不是老锹的儿子。”
大家立刻来了精神。安队面对着林昱,身休前倾:
“嗯,说下去。”
“我是在第一次去柳绣坊时见到他的,只见了一次,以后再也没见着。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幕布的这个人明显要黑一些,皮肤也比柳绣坊的那个男子粗糙,但是,他们的眉眼间真的很相似。”
老宫说:“有这样的事情?如果那个人真是老锹的儿子,他为什么出入柳绣坊呢?他跟柳家又是什么关系呢?”老宫说着说着兴奋起来,一拍大腿,“这是不是更加说明,老锹一伙和玉蟾的丢失有关系,他的这个儿子说不定就是帮手!”
安队说:“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么角色。”他赞许地看着林昱,“但,这是个重要情报,我们会往加紧排查。小林,你越来越会观察了,有进步!”
老宫也很高兴,表扬了他手下的兵,不就跟表扬了他差不多么?他冲小林竖了竖大拇指,说:“小林,下午接着去柳绣坊,看有没有新的情况。只要一天不挖出盗墓团伙,我们就一天不能松懈。下午早点儿,我在局里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