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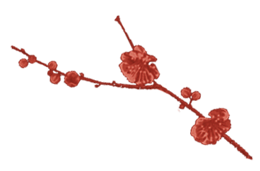
白云庵离得并不算远,在林逋家和信王府之间。林逋和梅香乘着翠兰来时所坐的马车,一路向着白云庵风驰电掣地疾驰。车上的林逋已经换上了一身新行头,若是在平时,梅香和翠兰见了林逋的这身打扮,非得笑喷出来不可。林逋现在完全成了一个俊俏大姑娘的模样,一袭素色的衣裙,穿在他那本来就挺拔消瘦的身体上倒也十分合身。翠兰还带了一只化妆盒,为他脸上抹上胭脂,涂上口红,直把林逋收拾得楚楚动人,就算是林逋的亲爹亲妈来到林逋眼前,也未必能认出亲儿子来。梅香在一旁简直看傻了眼,叹了口气,幽幽地道:
“林相公,怪不得咱们若萱小姐那么迷恋您,我以前一直以为,小姐只是迷上你的才学。您瞧,翠兰姑娘给您这么一收拾,您简直比我们小姐还俊。”
翠兰伤感而又无奈地说:“是我们小姐特地吩咐我这么做的,希望相公不要怪罪。信王府耳目众多,要是让王爷知道若萱小姐在府外私会相公,那后果想都不敢想。”
虽然只花了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白云庵,但林逋仍然觉得这段路程太长了。由翠兰引着,一行人没费什么周折就进了若萱娘娘所在的院落。到了若萱的卧室外,翠兰先让林逋停下来,进去通禀了一声,然后让侍候的丫环婆子们统统离开卧室,这才出来对林逋说了声:
“林……林姑娘,我们娘娘请您进去。”
林逋早就在等着这句话了。翠兰的话音还未落,他就迫不及待地朝卧室里跨去。却由于意乱神迷,不小心在门槛上磕绊了一下,差点摔倒。翠兰赶紧扶了林逋一把:
“林姑娘小心。”
等林逋一进屋,翠兰便在身后把门带上,和梅香一起,小心地守在门口。
一进屋,林逋的心便怦怦狂跳起来,心中竟然泛起一股异样的情感,连呼吸都有些不自然了。其实虽然和若萱青梅竹马相伴那么多年,林逋还从来没有进过若萱的闺房呢,更别说是进王妃娘娘的这间卧房了。即便是在寺院中,但信王爷仍然让人按照若萱在王府内的卧室格局,把这间原本简朴的屋子布置得奢华无匹,为的是让若萱不至于有“离开家”的感觉。无处不在的华贵装饰,无处不在的沁人幽香,弄得林逋脑袋有点晕,加上光线昏暗,林逋一时都弄不清东西南北了。昏暗中,他听到一声呼唤:
“林相公。”
这个声音不高,而且是那么虚弱,可是在林逋听来,却不啻一声惊雷。这是他以前在韩家私塾里读书时,日日听到过的声音,那么熟悉,就算是在一万个人当中,只要这个声音响起一丝半息,他也能辨出是谁发出来的。他已经差不多有一年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一时间,他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那个令他内心如沸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林相公,请到这边来。”
林逋心里升腾起一股怨气,哼,你想离开我便离开我,这会儿又要我过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当我林逋真是那么没骨气吗?但是,这股怨气只在林逋心中盘旋了半圈,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随着眼睛渐渐适应了里面的光线,他看清,若萱躺在卧榻上,面白如纸。他紧走几步,来到病榻跟前,斜着身子在床沿坐下。林逋只觉得仿佛有一双手扼住了他的喉咙一般,令他透不过气来。因为他看到,病榻上的若萱骨瘦如柴,瘦得那额上的青筋根根突起,仿佛都能看见血管里那所剩不多的的血液在若有若无地流淌。唯一不变的是,若萱的容颜仍是那般清秀,眼睛仍是那般清澈。林逋忍住泪,握住若萱露在被单外侧的一只同样骨瘦如柴的手。两个人四目相对,目光绞在了一起,两只手也绞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良久,若萱那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对不起啦,相公,今日让你看到的是一个如同鬼魅的若萱。以前若萱的手滑润细腻时,没能让你握。今天你第一次握我的手,就握到这只干柴般的手。”
林逋的手颤抖着,使劲儿捏着若萱的手,仿佛要以此来验证自己究竟是不是在梦中。他的声音也在颤抖:
“若萱,你怎么,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还以为,你在王府里锦衣玉食,没想到,没想到……”
若萱贪婪地回握着林逋的手,握得那么无力:“林郎,今天咱们说好,谁都不许哭。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是趁着若萱还有一口气,最后见你一面,告诉你一件事。本来我打算把身体养养好,将来找机会与你相见。可是看这样子,我是再也起不了床啦。所以,只好把你约到这里来,劳烦你的大驾啦。”
林逋强忍悲伤:“若萱,别胡说,你会好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若萱吃力地摇摇头:“林郎,不要安慰我了,我自己的身子骨,自己有数。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吧,王爷他这几天总往我这边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过来了。我知道,有件事情一直搁在你的心里,你一定非常怨恨,怨恨若萱为什么会突然离开你。”
没错,今天林逋过来,也想当面问一问这个问题。他的两眼一眨不眨地紧盯着若萱。若萱喘了一几口气,继续说:
“把我嫁进信王府,我爹也是万般无奈。否则,我们韩家便有可能遭到灭门之祸。”
林逋失声叫道:“灭门之祸?”
若萱说:“对。你知道这几年我爹的生意为什么能做到那么大吗?是因为他跟北方的金人有生意来往,他把金人的药材贩运到南方,又把南方的瓷器、绸缎、铁器、漆器贩运到北方。实际上,他现是金人最大的生意伙伴。凭着这一点,他原来的生意对手,一个个都被他打败了。那些对手们个个痛恨我爹,于是,那些人就联合起来,诬告我爹勾结金人,借着做生意的幌子,为金人搜集大宋军情,为金人将来南下作准备。林郎,你知道,这几年北方边患不断,金人屡屡南犯,已成朝廷心头大患,勾结金人,一旦查实,那必定是祸灭九族。”
林逋倒吸一口冷气,原来韩家遭受到那么大的麻烦:“那,那后来,后来,官府有没有查实呢?”
若萱说:“我爹爹常年与金人做生意,难免和金人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金国的一些大臣、金兵的将领有交往,也难免会有一些书信往来,要从这上面寻找一些麻烦,这又有何难?何况爹爹的生意对手那么多,大家异口同声,诬陷爹爹。三人尚且成虎,何况那么多人?这些生意对手买通了杭州安抚使蔡驰蔡大人。蔡驰的贪名路人皆知,正愁找不到借口查抄大户,好大发横财呢。当下,他便准备查抄我们家。我爹爹得到消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正当我爹爹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为爹爹指点了一条路。”
“把你嫁入信王府?”
“对。信王是当今圣上的亲叔叔,在朝中很有威望。如果能傍上这棵大树,那么,任凭蔡驰再贪再横,也没有胆量动我爹爹一根寒毛。当时信王爷刚好身染重病,性命堪忧,需要找一个人来冲喜。于是,爹爹便趁着这个机会,把我嫁入信王府。靠着信王爷,韩家总算逃过一场塌天大祸。”
林逋听得脊背一阵阵发凉,心头一阵阵刺痛。他一遍一遍摩挲着若萱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不停地重复着:
“若萱,你受苦了。若萱,你受苦了……”
若萱说:“不,相公,我自己倒没什么。我是韩家骨肉,韩家危难之际,我出来拯救,那是责无旁贷。我唯一觉得对不得住的,就是你,我的林郎!”本来说好不哭,可是说到此处,若萱还是忍不住呜咽了一下。她镇定了一下,努力挣扎出一丝笑容,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本来说好不哭的,瞧我……这些事情,爹爹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能讲给别人听,连韩家下人也不让知道,因为这事关信王爷与蔡大人的面子。况且,信王爷在朝中也并非没有对头,有些对头的势力并不在信王爷之下,万一有人在圣上面前告刁状,说信王爷包庇韩家,那么韩家还是少不了麻烦。但是,林郎,我必须把这些告诉你。如果不将这些真相告知你,我将死不瞑目,我在阴间也无法安宁,因为我愧对于你,我不能让你带着这块心结过上一辈子。”
林逋捂住若萱的嘴巴:“若萱,不许你胡说,你不会死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
这时,房门被敲响,翠兰和梅香推门进来:“娘娘,王爷来看你了,已经往这边来了。林相公,你快走,被王爷知道了,可就不得了啦!”
林逋和若萱都怔了一下,不约而同互相松开手。但顷刻间,两个人又互相伸出手去,死死地握在一起,四道目光重新绞在一块儿,那目光绝非仅瞧在表面,而是直射进对方体内,射进对方的生命最深处。林逋的热泪夺眶而出,啜泣得几乎语不成句:
“若萱,若萱,我们经历了丰谷镇茶馆的生离,今天在这白云庵里,难道是我们的死别吗?!”
若萱也早已泣不成声。她颤抖着,用另一只手拔下头上的玉簪,塞进林逋的手中。
“林郎,林郎,若萱对不起你,对不起你……这只玉簪早该是你的了,今天我把它正式给你,给你……”
翠兰急了,用力掰开林逋和若萱相互扣着的手,硬拉着林逋往外走:
“相公,快走吧。要是被王爷发现了什么,那连韩家也得跟着倒霉啦!”
林逋被扯着,踉踉跄跄地走到门口,忽然听到若萱在床上大叫一声:
“林郎——”
林逋猛然回首,只见若萱在床上支起半个身子,死盯着林逋,一字一句地说:
“林郎,佛云,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们经历过生离,又经历了死别。我若萱不怨天,不怨地,我只相信这是命,是上天故意要这么安排。上天说,我们只修行了百年,还不够格成为夫妻。那,我们继续修行,我们就按照佛祖的规矩,修行一千年,来生再做夫妻。林郎,你愿意吗?”
林逋狠狠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举起那支玉簪,大声说:“好,若萱,我们一定会有来生,我们接着修行,我们约好,一千年后,我们必定做成夫妻!到那时,我就带着这支玉簪来找你,如果你认不出我了,见到这支玉簪,就知道我是谁了!”
若萱那苍白如纸的脸上挂满满足的笑容,开心地说:
“好,林郎,林郎,我们约好,一千年后,我等你,等你来和我白头偕老……”
若萱说着,噗地一下,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如同绚丽的朝霞一样,染红了床幔。她那支撑起身子的手臂一松,身体软了下去。林逋、翠兰还有梅香魂飞魄散,一齐失声叫道:
“若萱,若萱……”
“娘娘,娘娘……”
“小姐,小姐……”
梅香突然清醒过来,一把捂住林逋的嘴巴:
“快走,来不及啦!”
两个丫环一起,把早已六神无主的林逋拽出门去。刚转入一堵山墙后,便见到信王爷坐着软轿,从长廊那儿过来了。而在长廊的另一边,一名内宫丫环托着一碗刚煎制好的药汤,已经快走到若萱卧房门口了。三个人躲在山墙后,大气都不敢喘。不大功夫,王爷的轿子行近了。只听王爷发话道:
“若萱娘娘现在怎么样了?”
随行的人还没来得及发话,猛然从若萱房中传来内宫丫环惊恐的哭喊声:
“不好啦,若萱娘娘她,她,归天啦!”
信王爷犹如被铁锥戳了一下,肥胖的身子一挺,从轿子上滚落下来,把轿子都带翻了,鞋都掉了一只,就这样只穿着一只鞋,踉踉跄跄边朝前跑边声嘶力竭地喊道:
“若萱,若萱,我的若萱哪!”
后面的随从慌不迭地追上去搀扶他:
“王爷,王爷,您小心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