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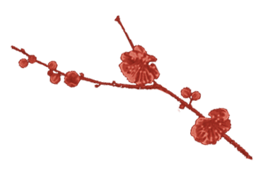
不知道托了多少回底,终于到了路的尽头——一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正对着砂石路。到了大铁门边,汽车照常朝前行驶着,似乎就在汽车撞上大铁门的一刹那,门被从里面拉开了,那门显然不经常开动,嘎吱嘎吱的响声,让人直起鸡皮疙瘩。汽车驶进去以后,门又在身后嘎吱嘎吱关上了。
到了里面才发现,里面挺宽敞,原来这里是一处废弃的采石场。车子在一座破旧的大房子前停下来,一群人汉子早就候在门前,没等车停稳,就将车团团围住。紧接着,两侧的车门被打开,鲍翰林觉得自己被一双粗暴的手地扯了下来,胳膊被抓得生疼。而柳凝丝也已经被从后备厢里抬了下来,犹如扒皮一样扒去了套在身上的口袋。鲍翰林也被摘去头套,因为在黑暗中呆了半天,外面明亮的光线刺激得两个人一时睁不开眼。一个人在后面推了柳凝丝一把。她全身被布条缚得紧紧的,哪里迈得开步?立刻一个趔趄,摔倒在地。鲍翰林本能地打算绕过车头,去保护凝丝:
“你们干什么?不许碰她!”
他话音未落,一个壮汉便上来啪啪扇了他几个嘴巴。壮汉阴森森地道:
“老实点,要不然,我当着你的面,把你的女朋友开了,你信不信?”
鲍翰林顿时吓得不敢动弹了。有人拿来两根绳子,转眼间,便把他捆得结结实实。鲍翰林看到老花头坐在屋前的一块石头上抽烟,喊道:
“师父,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花头深深吸了口烟,掸了掸烟灰,走到鲍翰林面前,说:
“孩子,河北的鬼手梁听说过吗?”
鲍翰林问:“鬼手梁?”
“也是玩搬山的。早年你爸在河北找墓时,曾经和鬼手梁他们结下了梁子。”
鲍翰林问:“他们,他们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手呢?”转念一想,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明白了,他想绑架我们,逼迫我爸把若萱陵交给他们。而您,当了他的帮凶。我原本一心指望着跟您能把我跟凝丝弄出去,没想到,没想到……”
鲍翰林心潮起伏,说不下去了。
老花头点点头:“孩子,别怪师父心狠。你爸爸想发财,其他人也想。干这行的都知道,掏墓容易找墓难。找不着墓,人家只好打你的主意,早就盯上你啦。我如果不听他们的,他们就不会放过我。再说,我也是个人,我也会享受,我伺候了你爸这几十年,早够意思啦,我也不能一辈子当你爸爸的奴隶,我也该发点小财,是不是?唉,实不相瞒,本来这事儿我还在犹豫,毕竟咱们相处了这么多年,有感情啊。原先呢,我们只想绑你一个人,打算过几天就动手,谁叫你绑了柳凝丝呢?这事儿要是被邻居知道了,报了警,警察把你们都带走的话,我们可就两手空空啦。所以事不宜迟,我们只好顺水推舟,提前下手,把你们两个都带来了。”
一个满脸阴气的长脸汉子从屋子里慢步踱了出来,那些本来围在鲍翰林和柳凝丝身边的人立刻散开,静静地望着长脸汉子,等候他的发话。两个被绑者虽然不知道这个汉子是谁,但从身边人的反应也能猜到,这个人身份不一般,说不定是这伙人里面的头儿。
长脸汉子踱到鲍翰林身边,伸出一只巴掌,贴在鲍翰林的脸上:
“凉吗?”
“凉。”
“知道我是谁了吗?”
鲍翰林不安地说:“知道,鬼手梁。”
“凭什么?”
“你的手很凉。”
鬼手梁阴冷地笑了笑,回头冲老花头说:“老花头,给老锹发短信,就用这小子的手机发,告诉老锹,他的儿子跟儿媳在我们手里,叫他拿若萱陵来换。我们等他两天,他要是不愿意,那他就永远见不到他的儿子跟儿媳了。”他又朝着鲍翰林说,“小子,我也不瞒你,瞒也瞒不住,发丘圈子就这么大,你爹的脑瓜子可比谁都灵,他不用打听就能猜到,把你们请到这儿来的人,是我鬼手梁。”
柳凝丝呜呜叫唤了几声——她的嘴巴仍被堵着。也许别人听不懂她这呜呜声的含意,鲍翰林却听得明明白白,那是她在抗议,抗议这些打柳家祖陵的强盗们。鲍翰林生怕她的声音激怒鬼手梁,不知不觉地往她身边挪了挪,准备随时保护她。幸好鬼手梁瞧也没有瞧柳凝丝一眼,而是继续朝着鲍翰林说道:
“小子,地下的墓,其实是我们大伙儿的,你爹他不该太贪心,不该吃独食。你爹要还债,我鬼手梁也体谅他的难处。我们的要求不高,你爹从若萱陵得来的东西,我们只想得一半。拿到我们的那份,我们立刻放人。或者,告诉我们若萱陵在哪儿,让我们自己去挖也成。如果他在挖陵的过程中遇到难处,我们这些人也可以打打下手。别以为他老锹总是高人一等,他出去这么多年,国内的发丘圈子已经不是从前了。小子,你自己瞧瞧,在场的人里,是不是有几个熟人?这些人,以前可都是跟着你爹的,现在他们投奔我啦。所以,你要好好劝劝你爹,识时务者为俊杰。”
鲍翰林扭头瞧去,人群中果然有好几张熟脸,这几位以前是柳凝丝的妈妈孙红菊的跟班,他们跟着孙红菊回柳绣坊时见过几次。鲍翰林心里不禁一阵难过,一来是为自己与柳凝丝的处境,二来是为父亲与孙红菊。唉,父亲与孙红菊此时已经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了。
鬼手梁挥了挥手:“短信也给孙二娘发一个,发完卸掉电池板。”
说着,他转身回到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