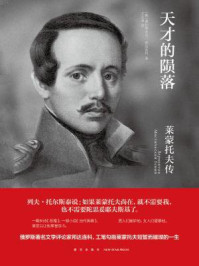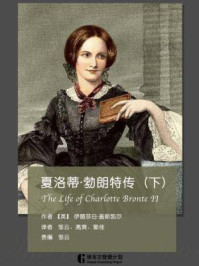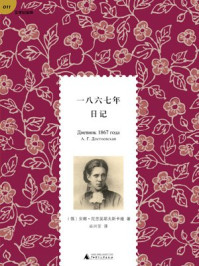现世终究难以安稳
现世终究难以安稳

回到上海时,张爱玲已经八岁了。望着千种繁华的大上海,张爱玲莫名地兴奋起来,或许她本来就属于这里。
不久,黄逸梵回国了。在出洋的四年里,她学习了音乐、绘画以及戏剧等。可能这些并不是系统学习的,却扩大了她的眼界,增长了她的见识。而经历的漂泊之苦,对于初出家门的新女性来说,也只有她本人深刻体会了。接到丈夫的信,黄逸梵或许是找到了一个台阶,或许是淡忘了之前的家庭争吵,又或许是放不下一对儿女,总之她回来了。
母亲回来那天,张爱玲吵着让女佣给她穿上小红袄,这是她自认为最漂亮的衣服。看来对于这个见面,她还是很重视的。可是黄逸梵一见到她,第一句话就是:“怎么给她穿这么小的衣服?”一下子使得张爱玲很郁闷。然而不久,母亲就为她添置了新衣,把她打扮得漂亮极了。这时,父亲确实也想改好,他到医院接受治疗,戒除毒瘾。
张爱玲一家人又搬到了宝隆花园的一所欧式洋房里去住,那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客厅里铺着玫瑰红的地毯,椅子上覆盖着蓝色的椅套。母亲还吩咐人给张爱玲姐弟俩重新装饰了房间,姐姐房间的墙壁是橙红色的,成年后的张爱玲仍记得这一细节,因为她觉得这种颜色温暖而又亲近。或许这种感觉是童年的她最需要的。总之,她对当时的一切都非常满意,她希望过一种安稳的生活,从小就希望。但生活对这个临水照花的女人显然并不眷顾,这也许就是一种令人扼腕神伤的宿命。
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欢愉起来,欢愉得有点不真实。妈妈、姑姑还有一个胖的伯母经常在一起谈笑,她们喜欢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情景。这时,张爱玲就在旁边看着,时常大笑起来,兴奋地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这一段光阴是张爱玲童年时期最开心的日子。后来,弟弟张子静撰文回忆:“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着,对我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每读至此,都让人不胜唏嘘,这个天使仅仅就要求这些。
这种快乐,张爱玲是要与人分享的。她兴冲冲地给天津的一个玩伴写信,描述新房子、新生活,足足写了三页信纸,而且还配了图。之后,她没有收到回信。成年后,张爱玲推测,那应该是粗俗的夸耀让人生厌了。
姑姑张茂渊的钢琴弹得很动听,她每天都坚持练习钢琴。那种画面在张爱玲脑海中永远定格了:姑姑穿着泛着银光的大红毛衣,扎着漂亮花绒的衣袖,伸出纤细的手指弹奏着,琴上的玻璃瓶内插着花,旁边就是明净精致的窗子,妈妈则站在旁边伴唱。
妈妈很喜欢新小说,自己也订阅了《小说月刊》。那时《小说月刊》上正刊载老舍的《二马》,妈妈很喜欢,一边坐在抽水马桶上,一边阅读,常常笑出声来。看到这种景象,张爱玲也靠在门框边上傻笑。此后,张爱玲也很喜欢老舍的小说,显然与妈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接受诸多艺术熏陶的张爱玲也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充满着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一朵花,听妈妈说花的历史,她竟然掉下泪来。妈妈见了,就对弟弟说:“你看姐姐不是因为吃不到糖而哭哟!”一被夸奖,张爱玲高兴起来,眼泪也没了,觉得很不好意思。


然而现世终究难以安稳,这也是张爱玲所不能得的。
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父母的关系又变僵了。起因是父亲禁不起诱惑,又抽起了鸦片。不仅如此,父亲似乎变得聪明起来。他不愿意出全家的生活费,要妻子将自己的钱拿出来,为的是把妻子的钱逼光,到那时她想走也走不掉了。受过西式教育的黄逸梵怎么会吃他这一套,据理力争,丝毫不向好吃懒做的丈夫示弱。
于是父母间激烈的争吵又开始了。仆人们也吓慌了,连忙把张爱玲姐弟拉出来,叫他们乖一点。张爱玲和张子静默默无语,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三轮小脚踏车,似乎各有心事。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张爱玲和弟弟在院子里逗狗玩,突然就能听到楼上父母的吵架声,以及东西摔碎的声音。
这种家庭气氛究竟对孩子们产生了多大影响?答案不好猜测,但张子静的回忆还是留下了线索,“姐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的感受,但我相信,她那时也一定是害怕的。”
无休止的争吵之后,便是身心俱疲。这时,黄逸梵终于下定了决心,她不能也不想维持这段婚姻了。于是她聘请了一名外国律师,负责与丈夫协议离婚。
张廷重本来不想离婚,但大势已去,也只能答应。办手续的那天,他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拿起笔要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又几次放下了。那个外国律师倒是看不下去了,打电话询问黄逸梵是否有商量的余地。黄逸梵只幽幽地说了一句话:“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听闻此语,张廷重才彻底放弃幻想,签了字。根据协议,张爱玲姐弟归父亲抚养,但张爱玲的教育问题要征得母亲的同意。
这一年是1930年,母亲搬出了宝隆花园的洋房,住进了上海的法租界。姑姑张茂渊因为看不惯父亲的所作所为,也一向意见不合,于是搬出去与母亲同住了。虽然父母离婚没有征求过张爱玲的意见,但她倒是赞成的,她不愿意看到他们这样争吵下去。幸好离婚书写明,她和弟弟可以常去看望母亲,这多少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离婚对于父亲的打击倒是不小,他更自暴自弃起来。鸦片不过瘾,他开始打起吗啡来,而且专门雇了一个用人给他打。渐渐地,父亲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亲友、用人们都害怕起来,躲得远远的。他经常独自坐在阳台上,目光呆滞,嘴里嘟哝着什么。后来还是姑姑强制把他送到医院戒毒,大约治疗了三个月,父亲才保下了一条命,不过鸦片还是要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