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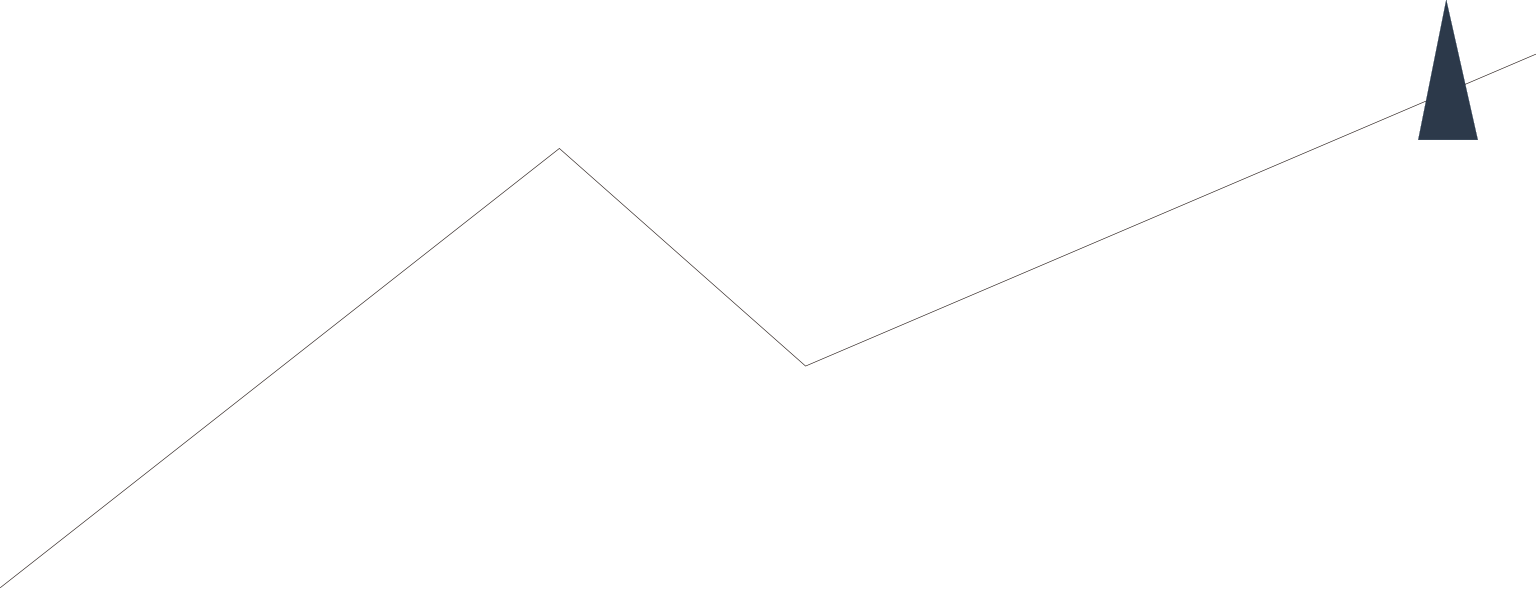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吉诃德神父吩咐女管家准备午餐后,便驱车前往合作社买酒去了。合作社位于通往巴伦西亚的主路上,距离埃尔托沃索镇八公里。当日天气炙热,大地热得仿佛开始冒烟了,神父开的西雅特600是辆二手车,购于八年前,没有空调设备。想到换辆新车遥遥无期,神父不禁感到十分沮丧。据说,狗的年龄乘以七才相当于人的岁数,如此算来,这辆车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可教区居民却不这么看,大家都觉得它该报废了。“吉诃德先生,这家伙该寿终正寝了。”对此,神父只能辩解道:“这可是我的患难伙伴,我向上帝祷告过,祈求它比我命还长。”但鉴于自己此前多数祷告从没灵验过,他只能寄希望于上帝偶发慈悲,可怜可怜他了。
借助往来车辆扬起的尘土,神父确定了主路的位置。他一边开车,一边挂念着西雅特车的命运,为了纪念祖先,他把它叫做“我的罗西纳特
 ”。想到车子锈迹斑斑被遗弃在垃圾堆里的样子,神父心中突然一阵抽搐。他曾盘算过几次,打算购买一小块土地赠予某个教民,前提是后者能为自己的车提供个栖身之地,可惜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而无论如何,随着岁月的流逝,车子终究躲不过生锈的厄运,也许废品场的压碎机才是它最好的归宿。神父忧心忡忡地惦记着车的命运,差一点撞上一辆黑色奔驰车,那辆车停在主路的拐弯处。车里的司机一身黑衣,神父以为对方正从巴伦西亚长途跋涉前往马德里,此时正在休息,于是没停车,继续向合作社开去。直到返程时,神父才注意到司机白色的罗马领,它就像手绢总是象征悲伤一样富有标志性。神父心中忍不住纳闷,自己的同行怎么能买得起奔驰车?待停下车,他才瞧见司机领子下的紫色围领,原来眼前这位同行即使不是主教,也是位高级教士。
”。想到车子锈迹斑斑被遗弃在垃圾堆里的样子,神父心中突然一阵抽搐。他曾盘算过几次,打算购买一小块土地赠予某个教民,前提是后者能为自己的车提供个栖身之地,可惜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而无论如何,随着岁月的流逝,车子终究躲不过生锈的厄运,也许废品场的压碎机才是它最好的归宿。神父忧心忡忡地惦记着车的命运,差一点撞上一辆黑色奔驰车,那辆车停在主路的拐弯处。车里的司机一身黑衣,神父以为对方正从巴伦西亚长途跋涉前往马德里,此时正在休息,于是没停车,继续向合作社开去。直到返程时,神父才注意到司机白色的罗马领,它就像手绢总是象征悲伤一样富有标志性。神父心中忍不住纳闷,自己的同行怎么能买得起奔驰车?待停下车,他才瞧见司机领子下的紫色围领,原来眼前这位同行即使不是主教,也是位高级教士。
吉诃德神父向来惧怕主教,这是有原因的。尽管神父有个赫赫有名的祖先,可在他的主教眼里,他只是个普通农民。主教并不喜欢他。“一个虚构人物怎么可能有后人?”在一次与他人的私下谈话中,主教曾如此诘问道。这番话没多久就传到了吉诃德神父耳朵里。
主教的这番话令与他谈话的人大吃一惊:“ 虚构 的人物?”
“一个徒有虚名,名叫塞万提斯的家伙瞎编出来的人物,小说中很多地方简直令人作呕,若放在佛朗哥将军
 时期,这书想通过审查,门儿都没有。”
时期,这书想通过审查,门儿都没有。”
“但是,主教阁下,埃尔托沃索镇确实有杜尔西内娅
 的房子。门牌上清清楚楚写着‘杜尔西内娅故居’。”
的房子。门牌上清清楚楚写着‘杜尔西内娅故居’。”
“骗骗游客而已。你想想,”主教气冲冲地继续说,“在西班牙语里,你甚至找不到吉诃德这个姓氏的出处。连塞万提斯本人都在书中说,姓氏有可能是吉哈达,盖萨达,甚至是盖哈纳,堂吉诃德临死时又称呼自己为吉哈诺。”
“如此说来,主教阁下,您读过那本书。”
“我连第一章都读不下去,不过我瞥了眼结局。这是我读小说的习惯。”
“也许神父的某位先人叫吉哈达或者盖萨达,这也不好说。”
“那种人何来先人一说
 。”
。”
正因如此,在向奔驰高级轿车里的上级做自我介绍时,吉诃德神父心中不免惶恐:“阁下,鄙人是吉诃德神父,请问我可以帮上什么忙吗?”
“当然,我的朋友。我是墨脱坡的主教。”对方一口浓重的意大利口音。
“墨脱坡主教?”
“虚职而已
 ,我的朋友。这儿附近有修理厂吗?我的车子抛锚了,最好能先吃点东西,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我的朋友。这儿附近有修理厂吗?我的车子抛锚了,最好能先吃点东西,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我的村子里倒是有个修理厂,可惜关门了,修理工今天参加葬礼,他岳母过世了。”
“愿她得以安息,”主教紧握住胸前的十字架,习惯性地顺口说道,随后又补了一句,“真是祸不单行啊。”
“修理工几小时后就会回来。”
“几小时!那附近有吃饭的地方吗?”
“主教,不知您是否愿意屈尊和我共进午餐……埃尔托沃索镇的饭馆都不太像样,要不东西难吃,要不酒难喝。”
“我现在必须要喝上一杯才好。”
“如果您不介意粗茶淡饭,比如牛排……配沙拉,我倒是可以让您尝尝本地的好酒。女管家每次给我准备的饭都多,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我的朋友,你简直是救我于苦难的守护天使。我们走吧。”
吉诃德神父车子的副驾驶位已经被一罐酒占领了,主教是个大高个,却坚持弓身坐在后座上。“我们不要打扰酒。”主教说道。
“阁下,这不是什么好酒,您坐前面会舒服一点……”
“自迦南婚宴
 起,任何酒可都是好东西,我的朋友。”
起,任何酒可都是好东西,我的朋友。”
吉诃德神父像一个被训斥的小孩,一路沉默无语,车子最终抵达了教堂旁的小屋前。主教进屋门必须低头,否则就会碰到脑袋,屋子大门径直通向客厅。“承蒙吉诃德先生款待,这真是我的荣幸。”主教说。听了这话,神父刚才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才稍稍舒缓了一些。
“我自己的主教不喜欢读书。”
“服侍神,热爱文学,两者往往不可兼得。”
主教来到书架前,书架上放着吉诃德神父的《弥撒书》《每日祈祷》和《新约》,研习教义期间翻烂的神学书,以及他喜爱的圣人的作品。
“阁下,恕我失陪片刻……”
吉诃德神父走进厨房,去找女管家。厨房一室两用,既做厨房,又兼做女管家的卧室。有一点必须说明,洗碗池是女管家唯一可以洗东西的地方。女管家身材魁梧,龅牙,上嘴唇还隐约有些胡须。她对任何活物都不信任,却对圣人心存敬畏,但仅限女性圣人。女管家名叫特丽莎,除镇长之外,埃尔托沃索镇谁也想不到称呼她为“杜尔西内娅”,因为没有人读过塞万提斯的大作,除了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镇长和饭馆老板,而后者有没有读过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之后的部分也令人怀疑。
“特丽莎,”吉诃德神父说道,“今天中午有贵客,手脚麻利点。”
“家里只有给你准备的牛排和一份沙拉,还有点剩下的曼彻格奶酪
 。”
。”
“我的牛排够两人吃,主教很随和。”
“主教?想让我伺候他,门儿都没有。”
“不是我那位主教,是一位意大利主教,非常谦逊有礼。”
于是,吉诃德神父将自己的偶遇一五一十告诉了女管家。
“可是,牛排……”特丽莎欲言又止。
“牛排怎么了?”
“总不能让主教吃马肉吧。”
“我的牛排是马肉?”
“一直是马肉。你给的那点钱怎么可能买得起牛排?”
“没其他招待客人的东西了吗?”
“没有了。”
“哦,天啊,天啊。只能祈求上帝保佑糊弄过关了。毕竟我就一直被蒙在鼓里。”
“因为你根本没吃过好东西。”
吉诃德神父拿了半瓶马拉加葡萄酒,心神不宁地回到主教身边。主教喝下一杯后,要求神父再续杯,这让神父欢喜不已,说不定酒精能起到麻痹味蕾的功效。主教整个人陷在摇椅里,这是吉诃德神父仅有的一把椅子,神父心虚地打量着主教大人。他看着慈眉善目,脸蛋光滑圆润,说不定从不用剃须刀。吉诃德神父突然心生悔意,早上在空无一人的教堂做弥撒之后,真该刮刮脸。
“主教大人,您这是在度假吗?”
“说度假有点言过其实,不过我挺享受罗马教廷的这次调职的。我会说西班牙语,所以教皇交给我一个小小的机密任务。神父,在埃尔托沃索你肯定见过很多外国游客吧。”
“并不多,主教大人,这儿游客很少,我们这儿除了博物馆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博物馆有何稀奇之处吗?”
“主教大人,那不过是个小博物馆,就一间房,大小跟我客厅差不多,除了签名没什么有趣的。”
“签名?请再给我来杯酒好吗?大太阳下坐在抛锚的车里,我都快脱水了。”
“抱歉,主教大人,你瞧,我太不会招待客人了。”
“我还是头回听说有签名博物馆。”
“几年前,埃尔托沃索的某位镇长给国家元首写信,请求收集带有名人签名的塞万提斯作品的译本。博物馆收藏颇丰。我认为佛朗哥将军的签名译本堪称镇馆之宝,另外还有墨索里尼、希特勒(那小小的签名好像苍蝇的排泄物)、丘吉尔、兴登堡元帅
 和拉姆齐·麦克唐纳
和拉姆齐·麦克唐纳
 的签名,此人好像是苏格兰首相。”
的签名,此人好像是苏格兰首相。”
“是英国首相,神父。”
特丽莎端着“牛排”走进屋,主客双方分别落座,主教开始做餐前祈祷。
吉诃德神父倒好酒,惴惴不安地望向主教大人,瞧着他将第一片“牛排”送入口中。主教就着酒飞快地将“牛排”咽下肚去,似乎是要消除马肉的味道。
“主教大人,这酒其实挺普通,但当地人颇为自豪地称之为马拉加葡萄酒。”
“酒味道不错,”主教说道,“不过,这牛排……牛排,”主教瞧着盘中的马排,神父的心一下悬到了嗓子眼,他已经做好了谢罪的准备。“这牛排……”主教第三次欲言又止,似乎正搜肠刮肚,想找到一个恰当的诅咒语。特丽莎此时也躲在走廊里偷听。“我从没吃过这种牛排……如此柔嫩可口,我甚至愿冒着亵渎神灵之罪称赞一句,此物只应天上有。我要亲自向你尊敬的女管家表示感谢。”
“她就在这儿呢,主教大人。”
“敬爱的女士,我要和你握手。”主教伸出戴着戒指的手,掌心向下,不像握手,倒像在等对方亲吻他的手。特丽莎却一转身急匆匆跑回了厨房。“我说错话了吗?”主教困惑不解道。
“不,不,主教大人。她只是不习惯服侍主教而已。”
“这位女士虽容貌普通,却面带真诚。现如今,即便在意大利也常常会见到适合做妻子的女管家,这真让人感到尴尬。唉,不过也成就了很多美满的姻缘。”
特丽莎再次飞快地走进屋,放下奶酪,然后又飞快地跑了出去。
“来点我们的曼彻格奶酪吗,主教大人?”
“再给我来杯酒?”
或许受到融洽气氛的激励,吉诃德神父不知哪儿来的冲动,迫切想向对方请教一个问题,他可不敢用这种事骚扰自己的主教。罗马来的主教毕竟与神更亲近,主教对马排的赞不绝口更激发了他的勇气。神父用“罗西纳特”称呼自己的西雅特600汽车绝不是毫无理由的,他觉得用马代指车,主教更容易给出他想要的答案。
“主教大人,”神父问道,“有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懂,相比城里人,我们乡下人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到困惑。”神父面色犹豫,仿佛即将跳入冰水的冬泳者,“您觉得为马祈祷是对神的不敬吗?”
“当然不是,”主教斩钉截铁地答道,“为世间生灵祈祷再恰当不过了。教皇曾教导我们,上帝创造牲畜为人所用,所以他乐于保佑马和我的奔驰车长寿,不过很可惜,我的奔驰车抛弃了我。但我必须承认一点,历史上还没有无生命的东西显露神迹的先例,但就牲畜来说,巴兰的驴显神迹一事可以作为借鉴
 。”
。”
“比起马对主人的用处,我更想为马的快乐祈祷,甚至……”
“没理由不为马的快乐祈祷,那样它会更温顺,更听马主人的话,但我不明白你所谓的‘让马死得其所’这一说法。拿人来说,死得其所指死后和上帝通灵,获得永生。我们可以为马在尘世中祈祷,但无法让其获得永生,否则岂不入了魔道。诚然,宗教历史上曾有过一次运动,试图承认狗可能具备所谓的初灵,但我个人认为,这是感情作祟,是极端危险的想法。岂可仅凭臆测就为此类行为洞开大门。如果说狗有灵魂,那犀牛或袋鼠呢?”
“或者说蚊子呢?”
“没错,神父,我觉得你站在了真理一方。”
“主教大人,还有一件事我也感到不解,上帝创造蚊子怎么是对人好呢?”
“这不显而易见吗,神父。蚊子代表了上帝的惩罚。上帝假借蚊子来教导我们,爱上帝就要忍受苦痛。那令人讨厌的嗡嗡声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谆谆教导。”
像很多单身男人一样,吉诃德神父也有个不幸的坏习惯——藏不住心里话,一不注意心里话就溜出了嘴:“那跳蚤岂不也一样?”主教打量着神父,见对方的目光中并无打趣意味,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中。
“这都是未解之谜,”主教说道,“如果没有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何以体现我们的信仰呢?”
“我不记得我把托梅略索市某人三年前送我的法国白兰地放哪儿了,”吉诃德神父道,“我们现在应该打开这瓶酒。恕我失陪,主教大人……特丽莎也许知道酒在哪儿。”说完他起身直奔厨房而去。
“作为一个主教,他喝得可真不少。”特丽莎说道。
“嘘,小声点。可怜的主教大人正担心他的车呢。他觉得车辜负了他的信任。”
“我倒觉得没准是他自己的错。我小时候在非洲生活过,黑人和主教总忘记给车加油。”
“你真觉得是车没油的问题吗?……不过,主教确实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竟然说蚊子的嗡嗡声……把法国白兰地给我。趁主教喝酒的工夫,我瞧瞧能不能把车修好。”
吉诃德神父从“罗西纳特”的后备箱里拿出一罐汽油,尽管他觉得不会是没油那么简单,但试试总没坏处。结果,还真是车没油了。主教大人竟然不知道车没油了?也许他只是羞于向神父承认自己的愚蠢吧。想到这儿,神父有点替主教难过。这位意大利主教和自己的主教相比,简直天差地别,前者随和可亲,喝年头不久的新红酒也毫不抱怨,还对马排不吝赞美之词。吉诃德神父可不想让主教大人难堪,但如何才能不让主教丢脸呢?神父靠在奔驰车的前机盖上斟酌了许久。假如主教大人没注意油表,那很容易假装成是他不懂的机械问题。无论如何,他都得先加点油再说……
主教对来自托梅略索的法国白兰地颇为满意。不经意间,他在几本课本中发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是吉诃德神父小时候买的。意大利主教一边读,一边面露微笑,若是换做吉诃德神父的主教,这情景简直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神父,你来得正好,我正在读的这段写得真是太好了。不管你的主教作何评价,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塞万提斯必定是个品德高尚的作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忠诚的仆人都要对他的主人坦诚相告,既不夸大其词,亦无所保留。桑丘,我要让你知道,王子听到的会是赤裸裸的事实,绝无任何文过饰非之处,这将会是一个不同的时代。’我的奔驰车是怎么了?难道在英勇骑士的故乡,在这片危险之地,它被男巫施了魔法吗?”
“主教大人,您的车子可以上路了。”
“是上帝显了神通?还是修理工参加完葬礼回来了?”
“修理工还没回来,我瞧了瞧发动机,”神父双手一摊,“问题很麻烦。汽油不多了,不过油的问题好办,我总备着一罐汽油,但主要问题不在汽油。”
“哈,果然不只是汽油的问题。”主教欣然附和道。
“我修了修发动机,我不知道专业术语怎么说,不过着实费了番工夫,车现在已经修好了。主教大人,等到了马德里,你也许要找个专业人士再给瞧瞧。”
“这么说,我可以上路了?”
“除非你想中午打个盹。特丽莎可以把我的床准备好。”
“不,不,神父。你的美酒和上好的牛排,哈,那牛排的美味真让人精神抖擞。另外,我今晚还在马德里约了人共进晚餐,我可不想天黑才到。”
在向主路进发的路上,主教问吉诃德神父:“神父,你在埃尔托沃索镇待了多久了?”
“主教大人,我打小就生活在这儿,只在进修神学时离开过一段时间。”
“你在哪儿学的神学?”
“在马德里。本想去萨拉曼卡,可惜不够资格。”
“你这样的人窝在埃尔托沃索简直是种浪费,你的主教显然……”
“我的主教,唉,他知道我才疏学浅。”
“他能修好我的汽车吗?”
“我指的是神学上的才能。”
“我们的教会同样需要具有实践能力的人。现今的世界瞬息万变,只有对尘间俗事了然于胸,才能更好满足教民的需求。你为不速之客备好美酒奶酪和美味的牛排,足以证明你可以跻身最上流的社会。劝人赎罪悔改是我们的工作,资产阶级中的有罪之人远比农民中的罪人更多。我希望你步你祖先堂吉诃德先生的后尘,去见识一下世界……”
“大家都说他是疯子,主教大人。”
“很多人也这样说圣依纳爵·罗耀拉
 ,但这条路我不得不走,我的车在那儿……”
,但这条路我不得不走,我的车在那儿……”
“我的主教说,那是小说,是作家想象出来的……”
“说不定人类也并不存在,神父,我们可能只存在于上帝的想象之中。”
“您希望我和风车搏斗?”
“正因为和风车搏斗,堂吉诃德才在临死前发现了真理,”主教坐进驾驶室,用圣咏调吟诵道,“去年之巢焉得今日之鸟。”
“这听着很美,”吉诃德神父说道,“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自己也没完全搞明白,”主教答道,“不过听着优美就足够了。”随后,汽车引擎发出轻快的轰鸣声,主教大人开着奔驰车向马德里驶去。待主教大人远去,吉诃德神父才留意到空气中多了一股异香,这是新酿的红酒,法国白兰地和曼彻格奶酪混合而成的香气,不知情的人肯定会误认为这是异域焚香的味道。
转眼几周过去了,吉诃德神父的生活依然如往常一般风平浪静。唯一的区别是神父知道了自己偶尔打打牙祭的“牛排”竟然是马排。对此他一笑了之,好处是再不必因为奢侈而饱受良心谴责了。他时常会想起那位客人,想起那位意大利主教的仁慈谦虚和对酒的热爱。这位主教仿佛他在学拉丁文时读到的异类真神,偶现人间来他家中短暂作客。现在,除了读读每日祈祷文和报纸,神父很少读东西了。其实,每日祈祷文也已不必去读,只是神父还没意识到这点。他特别关注有关宇航员的报道,因为他一直坚信,上帝的天堂一定就在遥远天际的某处。此外就是偶尔翻翻被翻烂的神学课本,确保周日教堂的布道不会与神的旨意背道而驰。
每个月,神父还会定期收到从马德里寄来的神学杂志。杂志里偶而刊登一些批评危险言论的文章——那些邪恶言论有时竟然出自某位红衣主教之口,具体是荷兰还是比利时的主教,神父已记不清了;是某位拥有日耳曼名字的神父说的也说不定,那位神父的名字让吉诃德神父想起了路德
 。神父对这些批评文章并不在意,在他的教区,他无需费心向屠夫、面包师、修理工,甚至是餐馆老板——埃尔托沃索除镇长外最有学识的人——捍卫教会的权威。至于镇长,只要和教规有关的事都可以忽略他,因为主教认为他是一位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事实上,相比他的教民,吉诃德神父更喜欢与镇长在街头聊天,因为和镇长在一起,他就不会有那种当官的优越感。两人都对太空探索的进展颇感兴趣,双方在交谈时,圆滑地互不触碰对方的底线。比如,吉诃德神父绝不会和对方探讨人造卫星和天使相遇的可能性,而在苏联和美国谁在航天事业上更成功的问题上,镇长则采取了科学公正的态度。身为一名神职人员,吉诃德神父觉得两国的航天员并无区别,都是好人,可能也是尽责的父母和丈夫。这些人头戴头盔,身着航天服,那身装束说不定出自同一供销商之手,但无论如何,神父都无法想象加百列或米迦勒
。神父对这些批评文章并不在意,在他的教区,他无需费心向屠夫、面包师、修理工,甚至是餐馆老板——埃尔托沃索除镇长外最有学识的人——捍卫教会的权威。至于镇长,只要和教规有关的事都可以忽略他,因为主教认为他是一位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事实上,相比他的教民,吉诃德神父更喜欢与镇长在街头聊天,因为和镇长在一起,他就不会有那种当官的优越感。两人都对太空探索的进展颇感兴趣,双方在交谈时,圆滑地互不触碰对方的底线。比如,吉诃德神父绝不会和对方探讨人造卫星和天使相遇的可能性,而在苏联和美国谁在航天事业上更成功的问题上,镇长则采取了科学公正的态度。身为一名神职人员,吉诃德神父觉得两国的航天员并无区别,都是好人,可能也是尽责的父母和丈夫。这些人头戴头盔,身着航天服,那身装束说不定出自同一供销商之手,但无论如何,神父都无法想象加百列或米迦勒
 ——当然更不会是撒旦——围着宇航员飞舞。如此,航天飞船若是没有直升上天,必然会大头冲下,旋转着直坠黄泉,跌入永不超生的地狱。
——当然更不会是撒旦——围着宇航员飞舞。如此,航天飞船若是没有直升上天,必然会大头冲下,旋转着直坠黄泉,跌入永不超生的地狱。
“这儿有你的信,”特丽莎将信将疑地对他说,“我哪儿都找不到你。”
“我刚在街上和镇长聊天。”
“那个异教徒。”
“要是没有异教徒,神父就失业了。”
特丽莎大声嚷道:“是主教来的信。”
“哦,天哪,我的上帝。”神父拿着信呆坐了好久,踌躇着不敢打开。主教每次来信准没好事。比如,有一次他将本属于自己的复活节供奉捐给了某慈善组织,该组织有个冠冕堂皇的拉丁名字“囚犯关爱之家”,自称为监狱里可怜的囚犯提供精神援助。最后这帮人却被抓了起来,因为他们企图拯救监狱里大元帅的反对者,这本是神父私下之举,不知何故却被主教知道了。主教破口大骂神父为蠢货,“蠢货”可是基督禁用之词。镇长获知此事后,拍拍神父的后背,称赞他果然不辱伟大祖先的英名,行祖先解放苦囚之善举
 。另外,还有上次……上上次的来信等等,若不是神父的马拉加葡萄酒被墨脱坡主教消灭了,他一定要来杯酒壮壮胆。
。另外,还有上次……上上次的来信等等,若不是神父的马拉加葡萄酒被墨脱坡主教消灭了,他一定要来杯酒壮壮胆。
神父叹了口气,破开红色封蜡,打开信封。果然不出所料,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主教的愤怒。“我收到一封从罗马寄来,令人匪夷所思的信,”主教如此写道,“一开始,我以为这封模仿教廷口吻的信是个恶作剧,是共产主义组织某人搞的鬼,你总说你有义务支持他们,可我一直觉得那帮人的动机晦涩难懂。在请求确认信件真伪之后,我今天突然收到了确认信,信中再次要求我通知你,教皇决定将你升为高级教士。教尊为何心血来潮,我没资格过问,但显然是某位墨脱坡主教做的好事。我从未听过此人,事先也没人和我商量,他就自作主张推荐了你。有一点我必须声明,换作我,是绝对做不出这种事的。谨遵上命,我特此通知你。我现在别无他法,只有祈祷你不要有辱教皇。教区牧师犯下的丑闻会因为他们的无知而得到宽恕,但吉诃德高级教士若是言行不慎铸成大错,影响可就恶劣得多了。请您好自为之,我亲爱的神父,我请求您务必要谨言慎行。我已致信罗马,禀明情况,让吉诃德教士屈尊守在埃尔托沃索这个弹丸之地简直太荒谬了,且会招致拉曼查地区众多有资格的神职人员的怨恨。所以我请求罗马为您提供一个大展拳脚的空间,比如将您调到其他教区,甚至可以考虑让您担任出使任务。”
神父合上信,任其掉落到地板上。“主教说了什么?”特丽莎问道。
“他要把我赶出埃尔托沃索镇。”吉诃德神父绝望地说。特丽莎不忍瞧见神父悲痛欲绝的双眼,赶紧躲进了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