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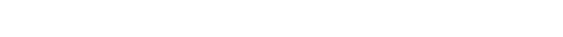
THE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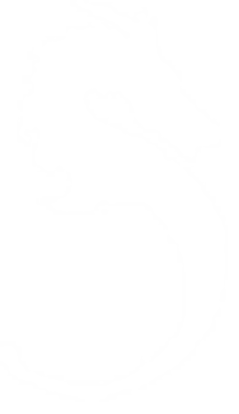
曙光跟史坦尼斯一样,悄然来到。
临冬城内彻夜难眠。人们穿好羊毛衣,披着锁甲皮甲,挤在城墙和塔楼上,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攻击。但天空被点亮时,鼓声也随之消逝,号角又吹了三声,一声比一声近。雪仍在下。
“暴风雪今天一定会停,”一位前次事故中幸存的马夫大声坚持,“一定会停,现在还不到冬天啊。”席恩若是敢笑的话,一定会狠狠嘲笑对方的无知。他还记得在老奶妈的故事里,暴风雪会肆虐四十天四十夜,甚至一整年、十年……直到城堡、市镇和整个国家都被埋葬在百尺积雪下。
他坐在大厅末端,旁边就是马群。他瞅着尔贝、罗宛和一个叫松鼠的棕发洗衣妇朝几片培根油炸的棕色陈面包发起进攻。席恩自己的早餐是一大杯黑麦酒,酒里全是酵母,浓得足以咀嚼。多喝两杯,也许尔贝的计划就不那么疯狂了。
淡色眼珠的卢斯·波顿打着呵欠,带他怀孕的肥胖老婆胖子瓦妲进大厅。之前许多领主和军官已陆续入席,包括妓魇安柏、伊尼斯·佛雷爵士和罗杰·莱斯威尔。威曼·曼德勒坐在桌子远端狼吞虎咽下许多香肠和白煮蛋,他身旁的洛克老伯爵把稀粥送进没牙的嘴里。
拉姆斯老爷随后现身,大步走向大厅前部,边走边扣剑带。 他就要爆发了 ,席恩看得出。 鼓声让他一夜没睡 ,席恩猜测, 要不就是有人惹恼他 。现在,无论谁说错话、眼神不妥,抑或不合时宜地发笑,都可能引爆老爷的雷霆怒火,让自己失去一片皮肤。 噢 , 求您了老爷 , 别看这边 。只消一眼,拉姆斯就能明白他的打算。 我脸上写得清清楚楚 。 他会知道的,他总是知道 。
于是席恩转向尔贝。“这计划行不通,”他声音压得极低,连马都不可能偷听,“没等逃离城堡,我们就会被抓。即便出了城,拉姆斯老爷也会来追猎我们,他会带骨头本和姑娘们一起来。”
“史坦尼斯大人就在城外。按声音判断,他离得很近,我们不用长途跋涉。”尔贝的指头在琴弦上舞蹈。歌手有棕色胡须,但长长的头发基本成了灰丝。“若野种真的来追,他会后悔不迭的。”
想想他的话 ,席恩心想, 相信他 。 告诉自己那都是真的 。“拉姆斯会把你的女人当猎物,”席恩警告歌手,“他会追猎她们,强暴她们,再拿她们的尸体去喂狗。如果追得刺激,他会用她们的名字来命名下一窝母狗。至于你,他会剥了你的皮,他、剥皮人和舞蹈师达蒙把这当成最有趣的消遣,到头来你会恳求他们杀了你。”他用残废的手抓紧歌手的胳膊。“你发誓不让我再落入他手中。你保证过。”他想再听尔贝保证一次。
“尔贝的保证,”松鼠道,“跟橡树一样可靠。”
尔贝本人只耸耸肩。“一定一定,王子殿下。”
高台上,拉姆斯跟他父亲吵了起来。由于离得远,席恩听不清,但胖子瓦妲那张粉色圆脸上的恐惧说明了一切。他听见威曼·曼德勒呼叫更多香肠,罗杰·莱斯威尔被独臂的海伍德·史陶说的笑话逗乐了。
席恩不知自己鬼魂的归宿是淹神的流水宫殿,还是会逗留在临冬城。 要命有一条 , 怎么也比身为臭佬苟活强 。若尔贝的计划失败,拉姆斯会狠狠折磨他们,让他们尝到痛不欲生的滋味。 这回他会把我从脚跟到头颅的皮统统剥掉 , 无论我怎么哀求也不会回心转意了 。席恩体验过的所有痛苦,都比不过剥皮人那把小小的剥皮刀。尔贝很快也会学到这一课。但这到底为什么呢? 为了珍妮 , 她叫珍妮 , 眼睛是错误的颜色 。她只是戏里的演员。 波顿公爵知道 , 拉姆斯也知道 , 但其他人被蒙在鼓里 , 即便是这个挂着狡猾笑容的混账歌手 。 真可笑 , 尔贝 , 你和你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婊子 , 将为拯救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女孩而白白送命 。
当罗宛把他带到残塔的废墟中见尔贝时,他几乎要讲出真相,只是最后一刻才管住嘴巴。歌手似乎执意要营救艾德·史塔克的女儿,若让他知道拉姆斯的新娘只是总管的崽儿,那么……
厅门被猛然撞开。
寒风呼啸,大团大团的蓝白色冰晶席卷进来。霍斯丁·佛雷爵士抱着一具尸体踏步而入,腰部以下全是雪。长凳上的人们纷纷放下酒杯和勺子,目瞪口呆地看着这诡异的一幕。
大厅安静得吓人。
又一起谋杀 。
霍斯丁爵士迈向高台,踏着响亮的脚步,雪从他斗篷上扫下。十来个佛雷家的骑士和武士紧随其后,席恩认得其中一个男孩——大瓦德。他实际上是小个子,生了狐狸脸,瘦得像木棍。大瓦德的胸膛、胳膊和斗篷上溅满血点。
血腥气让厅内的马匹尖声嘶叫,狗儿则从桌下钻出来四处嗅闻。人们纷纷起身。霍斯丁爵士怀里的尸体在火炬光芒映照下闪烁,仿佛包裹着一层粉色结晶——那是冻结的血。
“他是我弟弟梅里之子,”霍斯丁·佛雷把尸体放在高台前的地板上,“却像猪一样被人宰杀,之后推下雪堤。 他还是个孩子啊 !”
死者是小瓦德 ,席恩意识到, 那个大个子 。他瞥向罗宛。 她们一共六人 ,他记得, 其中任谁都能做出这事 。但洗衣妇对上他的眼睛。“不是我们干的。”她强调。
“安静。”尔贝警告她。
拉姆斯老爷从高台上走下来查看男孩的死尸,他父亲则是缓缓起身,睁着淡白的眼珠,严肃又沉静。“肮脏的罪行。”在席恩的记忆里,这是卢斯·波顿破天荒头一遭提高声调,“尸体在哪里找到的?”
“在那个残破的堡垒,大人,”大瓦德回答,“老石像鬼盘踞的地方。”表亲的血凝结在这男孩的手套上。“我叫他别一个人出去,他却一定要去讨债,对方欠他银子。”
“谁欠他?”拉姆斯质问,“给我名字,或当众指出来,小子。我会扒他的皮给你做件斗篷。”
“我哥没跟我说对头的名字,大人,只说自己赌骰子赢了钱。”佛雷家的男孩犹豫了一下,“教我哥赌骰子的是白港人,我不知是谁,但肯定是他们家的。”
“大人!”霍斯丁·佛雷声若洪钟,“事情还不明显吗?谋杀这孩子和其他人的凶手就在这里。是的,他没有亲自下手,他太胖、胆子又小,干不了脏活,但这些罪行都是他指使的!”他猛然转向威曼·曼德勒。“你承认吗?”
白港伯爵一口咬掉半根香肠。“我承认……”他边说边用衣袖擦掉嘴边的油脂,“……我承认自己不太认识这可怜孩子。他是不是拉姆斯大人的侍从?年方几何啊?”
“刚满九岁。”
“真是年轻。”威曼·曼德勒说,“他也算因祸得福吧,若成长下去,迟早会长成个佛雷。”
霍斯丁爵士一脚踢中桌子,将桌面从搁板上踢飞出去,撞在威曼大人的大肚皮上。杯盏乱飞,香肠撒得满地都是,十来个曼德勒的人咒骂着站起来。他们抓起匕首、盘子、酒壶,任何能当武器的东西。
然而霍斯丁·佛雷爵士已长剑出鞘,跳向威曼·曼德勒。白港伯爵想躲,但桌面把他死死卡在椅子上。只见寒光一闪,他的四重下巴被削去三重,空中鲜血飞溅。瓦妲夫人歇斯底里地尖叫,死命抓住夫君的胳膊。“停手!”卢斯·波顿吼道,“ 停止这种疯狂行为 !”眼看曼德勒的人纷纷跳下长凳冲向佛雷的人,波顿的部下赶紧上前维持秩序。有个曼德勒的人抓了把匕首直扑霍斯丁爵士,却被大个子骑士旋身躲开,骑士反手一剑就将来人的胳膊卸下。威曼大人想站起来,却摔倒在地,像只死命挣扎的海象似的在一摊不断扩散的血水中扑腾。他身边的洛克老伯爵大声召唤学士,而狗儿们在周围争抢他的香肠。
足足动用了四十个恐怖堡的长矛兵,才把交手双方强行分开,终止了惨剧。共有六个白港的人和两个佛雷的人丧命,十来个人受伤,伤得最重的是私生子的好小子路顿。他躺在地上哭叫妈妈,一边试图把满满一手滑溜的肠子塞回肚内,眼看是活不了了。拉姆斯从铁腿的长矛兵手头拽过一根长矛,把路顿捅个透心凉,直接了结了他。冲突止息后,大厅里仍回荡着叫嚣声、祈祷声、咒骂声、惊恐的马匹的尖叫和拉姆斯的母狗们的咆哮。铁腿沃顿用长矛柄顿了地板十多次,人们才静下来听卢斯·波顿讲话。
“我看大家都闷得慌,等不及想见血。”恐怖堡公爵说。罗德雷学士站在公爵身旁,胳膊上停了只乌鸦,火炬光芒下,乌鸦的黑羽毛像煤油般闪闪发亮。 它的羽毛打湿了 ,席恩意识到, 公爵手里那张羊皮纸一定也是湿的 。 黑色的翅膀 , 带来黑色的消息 。“但首先应该一致对外,不能自乱阵脚。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史坦尼斯大人。”波顿公爵展开羊皮纸。“他的部队离此不到三日骑程,现今被大雪困住,正忍饥挨饿。说实话,我不想等候他大驾光临了。霍斯丁爵士,请在主城门集结所部骑士和士兵,既然你如此渴望战斗,我们就命你担任先锋。威曼大人,请在东门集结白港部队,随后进发。”
鲜血染红了霍斯丁·佛雷的长剑,几乎直浸到柄,血点洒在他脸上,就像满脸麻子。他放低长剑:“悉听遵命。但等我献上史坦尼斯·拜拉席恩的人头,请允许我再取板油大人的狗头。”
四名白港骑士呈环形护住威曼大人,梅迪瑞克学士伏下来为大人止血。“你先过我们这关。”四名骑士中的长者说。这是个面孔刚硬的灰胡骑士,染血的紫罗兰色罩袍上绣了三只银色美人鱼。
“乐意之至。单挑还是一起上,我都奉陪。”
“ 住口 !”拉姆斯挥舞着血淋淋的长矛,怒吼道,“谁再出言不逊,就吃我一矛。我父亲大人有令!要你们把力气发泄在篡夺者史坦尼斯身上。”
卢斯·波顿点头赞许。“正如我儿所说。等我们料理了史坦尼斯这个心腹大患,再来解决纠纷不迟。”他转动脑袋,冰冷的淡色眼珠在大厅里搜寻,直到发现席恩旁边的诗人尔贝,“歌手,”公爵命令,“过来唱点安抚人心的歌。”
尔贝鞠了一躬。“如您所愿,大人。”他抱起竖琴,漫步踱向高台——途中灵巧地避开了两具尸体——盘腿坐在高桌上。他唱了一首温柔伤感的歌,席恩·葛雷乔伊听不出是什么,当他演唱时,霍斯丁爵士、伊尼斯爵士和其他佛雷的人牵着坐骑,离开了大厅。
罗宛抓住席恩的胳膊。“去打洗澡水。我们马上行动。”
他挣开手。“大白天行动?会被发现的。”
“雪会掩盖踪迹。你是聋子不成?波顿刚才出兵了,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史坦尼斯国王。”
“可是……尔贝……”松鼠小声说。
这完全疯了 。 这是绝望、愚蠢、注定完蛋的行动 。席恩干了杯中最后一点残渣,勉强站起来。“去把你的姐妹们找来。夫人的澡盆需要很多水。”
松鼠听罢一如既往轻手轻脚地溜走,罗宛则留在席恩身边,随他走出大厅。自在神木林找到他之后,这群女人始终贴身监视,从不让他单独行动。她们不信任他。 她们凭什么信任我 ? 我从前是臭佬 , 今后也可能变回臭佬 。 臭佬臭佬 , 决不逃跑 。
厅外的雪没有停。侍从们做的雪人如今成了畸形巨人,足有十尺高,外貌很可怕。他和罗宛走向神木林,两边的雪拔地而起、堆得像墙,连接堡垒、塔楼和大厅的道路成了雪地里挖出的迷宫般的堑壕,每隔一小时就得清理。这冰雪迷宫很容易让人迷路,幸而席恩·葛雷乔伊清楚每一处分支和岔道。
这回连神木林也披上了白霜,心树下的池子结了层薄冰,苍白树干上刻的人脸长出粗短的冰晶胡须。现在这时间,神木林里人多,于是罗宛带席恩离开那些在树下向旧神祈祷的北方人,来到军营墙边的隐蔽处,旁边有个散发出臭鸡蛋味道的暖泥塘。席恩发现泥塘外沿也结了冰。“凛冬将至……”
罗宛恶狠狠地瞪着他:“你无权引用艾德大人的族语。你没这个权利,一辈子都没有。你杀了——”
“你也杀了个孩子。”
“那不是我们干的,我告诉你了。”
“言语就像风。” 她们不比我高尚 。 她跟我是一路货色 。“你们杀了那么多人,凭什么要我相信不是你们干的?黄迪克——”
“——跟你一样臭。臭猪一头。”
“那小瓦德就是猪崽喽?杀了他,挑拨佛雷和曼德勒翻脸,这一招很漂亮,你们——”
“ 不是我们干的 !”罗宛掐他的喉咙,将他推到兵营墙上。她把脸凑到跟他的脸近在咫尺的地方:“再污蔑我们,我就割掉你撒谎的舌头,弑亲者。”
他透过满嘴碎牙笑了。“你不敢,你还要靠我的舌头来欺骗守卫呢。你需要我为你们撒谎。”
罗宛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才放手。随后她在腿上蹭了蹭手套,似乎碰他是种污染。
席恩明知不该刺激她。从某些方面说,她跟剥皮人或舞蹈师达蒙一样危险。但他又冷又累,脑袋嗡嗡作响,连续几天没睡觉。“我做过许多可怕的事……背叛同胞,当变色龙,下令杀害信任我的人……但我没弑亲。”
“是啊,史塔克的孩子不是你兄弟,我们都知道。”
她说的是事实,但完全没领会席恩的言下之意。 他们不是我的血亲 , 即便如此 , 我也从未伤害他们 。 我杀的只是磨坊主的两个儿子 。席恩不愿回想孩子们的母亲。他和磨坊主的老婆相识多年,甚至睡过对方。 她沉甸甸的大奶子上宽阔的黑乳头 , 还有那张很甜的嘴 , 特别爱笑 。 这样的欢乐 , 我大概尝不到了 。
但向罗宛吐实毫无意义,她不可能相信他的解释,正如他不相信她之前的否认。“我的双手染满鲜血,但没有兄弟之血,”他疲倦地说,“而我已受惩罚。”
“还不够。”罗宛背过身。
蠢女人 。席恩或已是废人一个,但还能用匕首。拔出匕首来背刺她并非难事。虽然失去了好多颗牙齿和几根手指脚趾,这也难不倒他。这甚至可说是种慈悲——直截了当解决她,以免她和她的姐妹们在拉姆斯那遭受非人的折磨。
这是臭佬会做的事, 臭佬会这样讨好拉姆斯老爷 。几个婊子想偷走拉姆斯老爷的新娘,臭佬决不允许这等事发生。但旧神记得他的名字,他们叫他席恩。 铁种 , 我是铁种 , 巴隆 · 葛雷乔伊的儿子和派克岛的合法继承人 。他失去的手指抽搐不已,但他控制住自己,没去拔匕首。
松鼠带着其他四个女人回来:憔悴灰发的密瑞蕾、梳着长长黑辫子的巫眼垂柳、粗腰大胸的芙雷亚和带小刀的霍莉。她们个个披了女仆穿的那种暗灰色粗袍,外罩白兔皮镶边的棕羊毛斗篷。 她们没剑 ,席恩注意到, 也没斧头、锤子和其他武器 , 只有小刀 。霍莉的斗篷用银制搭扣扣住。芙雷亚用麻绳做紧身褡,把身体从臀部到胸脯捆得严严实实,这让她看起来更魁梧了。
密瑞蕾给席恩也带了件仆人的服装。“院子里挤满了各路傻瓜,”她警告其他人,“正打算出城开战。”
“这帮下跪之人,”垂柳轻蔑地哼了一声,“他们供奉的老爷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
“他们这是去送死。”霍莉欢欣鼓舞。
“我们也是去送死,”席恩指出,“即便能过守卫这关,又如何把艾莉亚夫人偷走呢?”
霍莉笑道:“六个女人进去,六个女人出来。谁会多看女仆一眼?我们会把史塔克女孩装扮成松鼠的样子。”
席恩瞥了松鼠一眼。 她们身材差不多 , 可以一试 。“那松鼠又怎么脱身?”
松鼠抢先作答:“我会跳窗,直接跳下神木林。我老哥带我第一次翻越你们的长城到南方掠袭时,我才十二岁。我也是那次得到了这个名字,我老哥说我就像林间跳跃的松鼠。后来我又爬过六次长城,每次都能平安返回,一座小小的石塔难不倒我。”
“满意了,变色龙?”罗宛问,“我们开始吧。”
临冬城的厨房很大,独占了一整栋建筑,并和大厅、堡垒等远远分开,以免万一失火殃及池鱼。厨房的味道每小时都在变——一会儿是烤肉、一会儿是烤韭菜和洋葱,一会儿又是新出炉的面包。卢斯·波顿派自己的兵来看守厨房大门。城内有这么多张嘴要养,每一点食物都弥足珍贵,连厨师和帮厨小弟也得看紧。但守卫们都认识臭佬,他们总在他为艾莉亚夫人取热水洗澡时嘲笑他,不过没人敢真的动手伤他——众所周知,臭佬是拉姆斯老爷的宠物。
“臭臭王子来取热水喽,”当席恩带着这群“女仆”现身时,一名守卫唱道,随后为他们打开门,“利索点,别把甜美的暖气放跑了。”
席恩进了厨房,一把抓住一个路过的帮厨小弟。“小子,为夫人准备热水,”他命令,“给我装六桶干净水。拉姆斯老爷要把夫人洗得粉粉嫩嫩。”
“是,大人,”男孩立刻回答,“马上就办,大人。”
结果他的“马上”比席恩预想的长。厨房里的大水壶都不干净,帮厨小弟先刷净其中一个才好倒水。之后又花了无尽的时间把水烧沸,花了二倍的无尽时间把六只木桶装满。尔贝的女人们一直在旁边等待,面孔隐藏在兜帽底下。 她们真是大错特错 。真正的女仆会勾引帮厨小弟,会跟厨子们调情,会在厨房这里尝尝那里品品。然而罗宛和她那帮心怀鬼胎的姐妹们一心只怕惹事,她们阴郁的沉默很快引来守卫们好奇的目光。“梅齐、杰兹和其他女孩呢?”有人问席恩,“就是平常那几个。”
“她们惹恼了艾莉亚夫人,”席恩撒个谎,“上次水还没倒进浴盆就冷掉了。”
热气大团升腾,融化了飘落的雪花,他们呈单行行进,沿冰墙堑壕迷宫返回,每走一步水就冷一分。狭窄的通道里挤满了战士:穿羊毛罩袍和毛皮斗篷的武装骑士,肩扛长矛的步兵,带着未上弦的弓和装满的箭袋的弓箭手、自由骑手、牵马的马夫等。佛雷的人佩戴双塔纹章,白港的人佩戴人鱼三叉戟纹章。他们在暴风雪中朝相反的方向跋涉,碰面时警惕地打量对方,但没动武。 在这里是这样 , 到林子里就很难说了 。
主堡的门由六名恐怖堡的老兵把守。“妈的又洗?”看到热水,负责的军士叫道。军士正把双手插在腋窝里御寒。“昨晚刚洗过,一个成天睡在自己床上的女人能有多脏?”
很脏 , 若是跟拉姆斯同床共枕的话 。席恩心想,他回忆起新婚之夜拉姆斯强迫他和珍妮做的事。“这是拉姆斯老爷的命令。”
“那你进去吧,趁水还没凉。”军士放行,两名守卫随即推开对开门。
门内几乎跟门外一样冷。霍莉踢掉靴上的雪,拉下斗篷兜帽。“我还以为很难缠呢。”她的吐息在空气中结霜。
“老爷的卧室门外还有守卫,”席恩警告她,“那些可是拉姆斯的亲信。”他不敢在这里称他们为“私生子的好小子”,这里不行——说不定会被听见。“拉起兜帽。低头。”
“照他说的做,霍莉,”罗宛催促,“有的人说不定认识你。别惹多余的麻烦。”
于是席恩领女人们上楼梯。 这段楼梯我爬过上千次 。小时候他会跑着上去,下楼时则会三级作一步地跳下来。有回他不小心跳到老奶妈身上,把老奶妈一路撞下楼,也因此挨了在临冬城最重的一顿鞭子。但这顿鞭子跟他小时候在派克岛被两个哥哥殴打欺负相比,算得上温柔。他和罗柏在这段楼梯上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战斗。他们用木剑互相攻打,那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要想在螺旋梯上逼退意志坚定的对手,需要格外努力。罗德利克爵士常说,这就是所谓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但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他们都死了。乔里、罗德利克老爵士、艾德公爵、哈尔温、胡伦、凯恩、戴斯蒙、胖汤姆、老是做骑士梦的埃林、给他打造第一把真剑的密肯,甚至老奶妈,他们都不在了。
还有罗柏,那个比巴隆·葛雷乔伊所有儿子都更亲的兄弟。 罗柏在红色婚礼上被佛雷家族无耻地谋害 , 我应该在那里跟他并肩作战 。 我当时在哪里 ? 我应该跟他死在一起 。
席恩忽然停步,垂柳差点一头撞上他的背。拉姆斯的卧室近在眼前,两个私生子的好小子在门外把守:酸埃林和咕噜。
这肯定是旧神保佑。拉姆斯老爷常说:咕噜没舌头,埃林没脑瓜。他们一个凶残,一个卑鄙,但大半辈子为恐怖堡卖命,盲目服从、不多打听已成习惯。
“我给艾莉亚夫人送热水。”席恩告诉他们。
“先洗洗你自己吧,臭佬,”酸埃林道,“你闻起来像堆马粪。”咕噜咕噜着赞同,也或许那声咕噜意在嘲笑。无论如何,埃林打开卧室门,席恩示意女人们进去。
这个房间向来没有黎明,阴影笼罩一切。壁炉的将熄余烬中,最后一根原木正噼噼啪啪地作垂死挣扎。凌乱的空床边有张桌子,桌上放了根摇曳的蜡烛。 女孩不见了 ,席恩心想, 也许她终于在绝望中跳窗自尽 。可那扇窗明明被紧紧关闭,以抵御暴风雪,上面结满层层冰霜。“她人呢?”霍莉问。她的姐妹们将桶里的水倒进一个巨大的圆木盆,芙雷亚关上卧室门,用自己的身体抵住。“ 她人呢 ?”霍莉又问一遍。外面传来一声号角。 那是佛雷家的集结号 , 他们在做最后的准备 。席恩感到自己失去的手指痒得厉害。
他忽然发现了她。她蜷缩在卧室最黑暗的角落,用小山一样高的狼皮盖住自己。若非她不住发抖,席恩肯定发现不了。珍妮把床上的毛皮搬了下来,试图藏住自己。 她是怕我们 ? 还是以为夫君来了 ?想到拉姆斯随时可能现身,他就忍不住要尖叫。“夫人,”席恩没法叫她艾莉亚,又不敢叫她珍妮,“您没必要躲藏,来的都是朋友。”
毛皮动了动,一只泪汪汪的眼睛向外窥探。 深色的 , 太深了 , 那是一只棕色的眼睛 。“席恩?”
“艾莉亚夫人,”罗宛上前,“您必须跟我们走,而且要快。我们接您去您兄弟那里。”
“兄弟?”女孩从狼皮底下探出头,“可我……我没有兄弟呀。”
她又忘了自己是谁 , 忘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没有,”席恩道,“但以前是有的。您有三个兄弟:罗柏、布兰和瑞肯。”
“可他们都死了。我现在没有兄弟。”
“您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罗宛提醒,“也就是乌鸦大人。”
“琼恩·雪诺吗?”
“我们会护送您到他那里,但您必须马上行动。”
珍妮把狼皮一直拉到下巴。“不,这是个骗局。是他,是我的……我的夫君大人,我可爱的夫君大人,他派你们来,好检验我是不是真的爱他。我爱他,我确实爱他,我爱他胜过世上一切。”一滴泪珠滚落她脸颊。“告诉他,请你们告诉他,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想怎么做都行……和他或……和他的狗……求求你们……他不需砍我的脚,我不会逃跑。永远不会。我会给他生许多儿子。我保证。我指天发誓。”
罗宛轻吹了声口哨。“诸神咒死那男人。”
“ 我会做个乖女孩 ,”珍妮啜泣道,“ 他们把我训练得很好 。”
垂柳皱起眉头。“得想办法让她别哭了。门外那守卫是哑巴,可不是聋子。他们会听见的。”
“ 拉她起来 ,变色龙。”霍莉抽出小刀,“你不行就让我来。 我们得赶紧离开 。把这小贱人拉起来,给她壮壮胆。”
“她尖叫报警怎么办?”罗宛问。
那我们死定了 ,席恩心想, 我告诉过你们 , 这是个蠢透顶的计划 , 但你们不肯听 。尔贝害死了大家,歌手都是疯子。在歌谣里,英雄总能从怪兽的城堡中救出少女,但人生不比歌谣,正如珍妮·普尔不是艾莉亚·史塔克。 她的眼睛是错误的颜色 , 而这里没有英雄 , 只有一群婊子 。即便如此,他还是跪在她身边,替她拉下毛皮,轻抚她脸庞。“你认识我,我是席恩,我们曾生活在一起;我也认识你,我知道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她摇着头,“我的名字……是……”
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她唇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讨论。你现在保持安静。跟我们走,跟我走。我会带你远走高飞,永远地离开他。”
她睁大眼睛。“求求你,”她低声说,“噢,求你了。”
席恩伸手,抱她起来,这动作让他手指的断桩疼得钻心。狼皮从她身上滑落,她什么也没穿,苍白的小乳房上布满牙印。他听见身后有个女人倒抽一口气。罗宛把一堆衣服塞给他:“让她穿上。外面很冷。”松鼠脱得只剩内衣,正在一只雪松木箱里翻找暖和衣物,最后她套上一件拉姆斯老爷的加垫紧身上衣和一条旧马裤——那裤子太大,在她脚上好像船上鼓满的风帆。
在罗宛的协助下,席恩帮珍妮·普尔穿上松鼠的衣服。 若诸神保佑 , 守卫们瞎了眼 , 她或许能出去 。“现在我们出去,下楼。”席恩告诉女孩,“你低着头、拉起兜帽就好。紧跟霍莉,别跑,别哭,也别说话,别看任何人的眼睛。”
“你别离开我,”珍妮说,“请不要离开我。”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席恩保证。这时松鼠钻进艾莉亚夫人的床铺,拉起毯子盖住自己。
芙雷亚打开卧室门。“你给她好好洗了场澡吧,臭佬?”酸埃林劈头问道。咕噜则在垂柳经过时挤了她奶子一下——万幸,他非礼的对象是垂柳,若他去摸珍妮,她一定会放声尖叫,那时霍莉就不得不用藏在袖子里的小刀割他喉咙了。垂柳只扭身绕开了他。
半晌间,席恩只觉头重脚轻。 他们真的没看她 , 真的没发现她 。 我们在他们眼皮底下把她偷了出去 !
但走到楼梯上,恐惧又回来了。待会儿若遇见剥皮人、舞蹈师达蒙或铁腿沃顿怎么办?遇见拉姆斯本人呢? 诸神慈悲 , 不要是拉姆斯 , 撞见谁都行 。说到底,把女孩偷出卧室管什么用?他们仍在城堡里头,而每道城门都关闭上闩,城墙上又挤满哨兵。他们甚至可能连主堡都出不去,霍莉的小刀对付不了六个装备长剑长矛的卫兵。
然而卫兵们只蜷在门边,背向寒风和吹雪,连军士也没多瞥他们两眼。席恩替他和他手下的士兵感到万分遗憾。等拉姆斯发现自己的新娘不翼而飞,无疑会剥光他们的皮,至于咕噜和酸埃林的下场,他难以想象。
出门不到十码,罗宛和她的姐妹们就扔下了空桶。主堡已在风雪中不见影踪,广场成了白色雪原,漫天暴雪里传来各种各样奇特的回音。冰雪堑壕将他们围了起来,起初到膝盖,接着齐腰,再下去超过了头顶高度。他们身在临冬城腹地,本该位于城堡的中心,却看不到城的痕迹。这里好像是长城以北一千里格之远的永冬之地。“好冷。”在席恩身边蹒跚的珍妮·普尔呜咽着。
很快你会更冷 。等出了城,没了城墙掩护,就得迎上寒冬赤裸的利齿。 出得了城的话 。“这边走。”在三条堑壕的交会处,他说。
“芙雷亚,霍莉,跟他走。”罗宛吩咐,“我们去找尔贝。不用等我们。”她话音未落,就旋身钻进风雪,朝大厅而去。垂柳和密瑞蕾紧跟在后,她们的斗篷在风中猎猎作响。
越来越疯狂了 ,席恩·葛雷乔伊心想。即便有尔贝的六个女人掩护,逃亡也困难重重,现在只剩两个,简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事已至此,没法把女孩送回卧室,假装一切没发生。他只能挽住珍妮的胳膊,带她去城垛门。 到那才一半 ,他提醒自己, 就算守卫放行 , 还得想法出外墙 。从前那些夜里,守卫们准许席恩通过,但他向来是单身一人。要带三个女仆通过想必不简单,而若守卫们看见珍妮的兜帽,认出她是拉姆斯老爷的新娘……
扭曲的堑壕通向左边。就在他们眼前、在大雪的帘幕之外,耸立着城垛门,门边一左一右站了两名守卫。在羊毛、毛皮和皮革的层层包裹下,他们活像两头大熊,但手中长矛足有八尺。“谁?”其中一名守卫叫道。席恩不认得声音,那人的面孔几乎被围巾包得密不透风,只露出眼睛,“臭佬吗?”
是的 ,他本想回答,说出的却是:“席恩·葛雷乔伊。我……我给你们带了几个女人。”
“可怜的孩子,一定都冻坏了,”霍莉说,“过来,让咱给暖暖身子。”她从守卫伸出的长矛边滑过,伸手捧住对方的脸,拉下半冻结的围巾,在他嘴上印下一吻。两人嘴唇刚分开,她的小刀便神速地戳进对方的脖子,刚好捅在耳朵下面。席恩看见守卫瞪圆了眼。霍莉退开时,唇上全是血,而守卫嘴里冒出血来。
第二个守卫吓得张口结舌。芙雷亚上前抓住他的长矛,两人抢夺了一会儿,拽来拽去,但女人很快把武器夺走,顺势用矛柄猛敲他额头,打得他踉跄后退。芙雷亚将矛一挽,捅进他肚子,他只来得及嘀咕一声。
一旁的珍妮·普尔却发出高亢、恐怖的尖叫。“噢,这下可好,”霍莉抱怨,“这下把下跪之人全引来了。他们来了, 快跑 !”
席恩一手捂住珍妮的嘴,一手环住她的腰,将她推过已死和垂死的守卫,推过大门,推向冰冻的护城河。也许旧神仍然眷顾他们:吊桥是放下的,以便临冬城的防御者能在内墙外墙之间快速调度。他们身后传来惊慌的叫喊和急促的脚步,紧接着内墙城垛上有人吹响喇叭。
芙雷亚跑到吊桥中央,忽然站定,转身。“你们走。我来挡住下跪之人。”她那双巨手仍擎着染血的长矛。
跑到外墙阶梯下,席恩已是脚步不稳。他把女孩扛在肩头向上爬。珍妮彻底呆了,而她确实很轻……但松软新雪下的阶梯滑溜溜的,爬到一半他摔了一跤,重重地磕到一边膝盖,痛得死去活来,差点把女孩丢下。半晌间,他认定自己到此为止了,然而霍莉拉他起来,两人协力总算把珍妮抬到城上。
席恩靠着城齿,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他听见城墙下的叫嚣。芙雷亚正在雪地里和六七个全副武装的卫兵搏斗。“怎么走?”他朝霍莉吼,“现在怎么走? 我们怎么出去 ?”
霍莉脸上的怒火陡然化为惊恐。“噢,我真该死。绳子!”她歇斯底里地笑起来,“ 绳子在芙雷亚身上 !”她没笑完,就哼了一声,手抓住小腹——那儿插了一支箭矢。她用手压住伤口,鲜血从指间渗出。“内墙上的下跪之人……”她喘气道,随后双乳间中了第二箭。霍莉抓向最近的城齿,却踉跄着落下城墙。雪地里轻轻一声响,大雪抖了抖身躯,掩埋了她。
左边城墙传来呐喊,珍妮·普尔呆呆地看着城下霍莉的尸体,看着她身上洁白的雪毯被染红。席恩知道,内墙上的十字弓手正重新装填,他望向右边,但那边也有人赶来,手握明晃晃的长剑。从遥远的北疆,传来一声战号。 那一定是史坦尼斯 ,他狂乱地想, 史坦尼斯是唯一的希望 。 我们只需逃到他那里 。但呼啸的寒风中,他和女孩无路可逃。
十字弓响起。箭矢从离他不到一尺的地方擦过,撼动了城齿中冻硬的积雪。尔贝、罗宛、松鼠等人不知所终,他和女孩只能自救。 如果被俘 , 拉姆斯会亲手料理我们 。
席恩紧紧揽住珍妮的腰,纵身跳下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