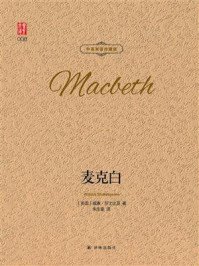当今的社会现实,让我们有必要重温追求最为质朴的真理时所需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对抗那些随处可见的强大偏见。作为准备,我先问几个简单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来有如作为人类思考之基石的公理一般不言自明,不过,一旦涉及具体的行为动机,人们言行便会公然地与此相背离。
人类何以超拔于禽兽?答案就像一个大于半个一样显而易见:因为人有理性。
一个人因何而卓然于世人?我们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此人具备美德。
人类为何会具有激情?经验告诉我们,在与欲望抗争的过程中人类能够收获知识,这是禽兽所不能的。
所以说,理性、美德与知识的多少,决定了人们本性的完善程度与谋求幸福的能力,也区分开了每个人、指引着规范社会的法律。知识与美德是在一个人践行理性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将人类作为一个总体来看,这一点也同样无可争议。
在对人类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过这一番简要的说明之后,似乎我们没有必要再试着去阐明这些看来无可争议的真理。然而仍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令理性蒙尘,种种虚伪的品质仍在冒顶美德之名,各色偶然事件常常使得人们的理性变得混乱甚而被引入歧途,因此我们有必要廓清事实,辨清质朴的真理与偶然的例外。
人们常常被偏见所蒙蔽,并且自己也无从追溯是从何时开始。他们不但没有用自己的理性去根除这些偏见,反而还要为它们辩护。因为要坚持自己的原则,需要坚强的意志,所以当需要克服偏见的时候,许多人因为意志软弱,而临阵退缩或半途而废。我们就这样接受了偏见,它们通常看似有理,其实只是基于片面和狭隘的观点而得来。
让我们回到基本原则上来。偏见先天即有缺陷,却善于粉饰狡辩。可那些思想浅薄的人们总是认为不需花太多精力去识别偏见,还声称这些本质腐朽的观点能够有助于思考。偏见就这样作为可以便利思考的手段被与基本原则不断地相提并论,似是而非地冒顶了基本原则之名,直到真理迷失于模糊的言辞、美德流于形式、知识让位于浮华的虚无。
几乎所有有理性的人都坚信,社会在理论上是按照最明智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并且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上,以至于试图找到证据来证明它的行为看起来都是在冒犯大家。但我们还是必须证明它,否则理性就无法战胜偏见的成规。而我们每天都在看到这些偏见在不断地侵蚀常识,它想证明剥夺男性(或女性)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合理的。
欧洲大众的文明并不完善,不仅如此,我们的文明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人们以天真本性和自由为代价换回来的东西,是否包含着一些美德,能够抵偿他们为了粉饰自己的无知而做出的愚行所带来的痛苦,能够值得他们忍受形式精巧而隐蔽的奴役?人们心目中的最高成就,就是过上富人的光鲜生活、享受被拍马屁者奉承的乐趣以及进行其他种种卑劣的自利之举。自由则沦为伪爱国主义者用来自我标榜的便利工具。地位与头衔的重要性被无限地放大,这令才华卓越之人“不得不低下他们相形见绌的头颅”
 。除了少数例外,有才能的人因为没有地位与财产而专注于博取名位,这是国家的不幸。一个默默无闻的冒险家渴望与王公贵族分庭抗礼、向往三重冠
。除了少数例外,有才能的人因为没有地位与财产而专注于博取名位,这是国家的不幸。一个默默无闻的冒险家渴望与王公贵族分庭抗礼、向往三重冠
 下的名位,在他争得权位的过程中,会有多少人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啊!
下的名位,在他争得权位的过程中,会有多少人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啊!
这其实就是身份、财产与权力世袭制的恶果,几乎所有那些有洞察力的人在为世袭制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时,说的都是亵渎上帝的恶言。照他们的说法,造物主创造了人类,可之后人类却不再听命于他,他们违背天命去盗取天宫的理性之火,神为了惩罚人类的冒犯,便将罪恶隐藏在这星星之火中,传遍世间。
卢梭
 就相信这种是神意让人间充满痛苦与无序的观点。可他也受不了再和矫揉造作的傻瓜们打交道,而迷恋上离群索居。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还用自己少见的雄辩之才力证人生来就是孤独的动物,好让他的幽居生活显得是顺从天命而非出于无奈。他被自己对上帝至善的信仰误导了——上帝只会赐予世间美好,人怎可因自己的感受而怀疑上帝!所以他认为人间确实存在罪恶,但那是人类咎由自取。他没有注意到他为了赞颂神而过分地贬低了人,其实这两者对于神性的至善完美都不可或缺。
就相信这种是神意让人间充满痛苦与无序的观点。可他也受不了再和矫揉造作的傻瓜们打交道,而迷恋上离群索居。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还用自己少见的雄辩之才力证人生来就是孤独的动物,好让他的幽居生活显得是顺从天命而非出于无奈。他被自己对上帝至善的信仰误导了——上帝只会赐予世间美好,人怎可因自己的感受而怀疑上帝!所以他认为人间确实存在罪恶,但那是人类咎由自取。他没有注意到他为了赞颂神而过分地贬低了人,其实这两者对于神性的至善完美都不可或缺。
卢梭的结论建筑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这让他倡导保持自然状态的论点虽然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实际上并不合理。我认为它不合理的原因在于:如果说无论文明如何改进都不会比自然状态更好,那么这其实就是在指责上帝的智慧。一方面相信上帝让世间所有事物按照正确的方式存在,另一方面相信罪恶就是由上帝所创造并且了解的人类造成的。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既不合乎逻辑,也是对上帝的不敬。
万能的上帝造人并将我们置于世间,他看着是好的,才允许它发生:他容许人类在各种原始的欲望中一步步地走向理性,因为他能看到今日的罪恶会在未来升华出美德。我们是他从无名中创造出来的无助的生灵,是他准许我们如此,否则我们如何能游离于他的旨意之外,在罪恶中学习美德?当卢梭热情地为上帝辩护的时候,他怎么会做出那么自相矛盾的论证呢?如果人类永远停留在野蛮无知的原生状态,即使他的妙笔生花也无法在这样的人当中找到哪怕一点可供美德植根的土壤。人是为了完成生死轮回而来到世间的,我们的天命就是完善造物主的世界,可是我们的本性中有与天命冲突的部分需要克服,虽然那敏感漫步者
 对此未经深思而无法领会。
对此未经深思而无法领会。
更进一步地说,如果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物,并且能够不断磨炼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来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如果仁慈的上帝也认同会思考与自省的人类应当有超拔于禽兽的生活方式
 ,那么这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宝贵的天赋。如果是上帝赋予人类这种可以让他们超越那种纯感官层面的、野蛮蒙昧的安适的能力,我们怎能认为这天赋是一种诅咒?若我们只存在于眼下的这个世界,那么有这种天赋也许是不幸的:为何仁慈的造物主要给我们欲望,又给我们思考的能力?这只能让我们怨恨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对于真正的价值产生错误的观念。可他引导我们从只爱自己,走向那种因为领会到他的智慧与美好而兴奋不已的伟大感情。如果这种伟大的感情不是为了帮助我们改进自己的本性
,那么这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宝贵的天赋。如果是上帝赋予人类这种可以让他们超越那种纯感官层面的、野蛮蒙昧的安适的能力,我们怎能认为这天赋是一种诅咒?若我们只存在于眼下的这个世界,那么有这种天赋也许是不幸的:为何仁慈的造物主要给我们欲望,又给我们思考的能力?这只能让我们怨恨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对于真正的价值产生错误的观念。可他引导我们从只爱自己,走向那种因为领会到他的智慧与美好而兴奋不已的伟大感情。如果这种伟大的感情不是为了帮助我们改进自己的本性
 ,他为何要为了奖赏我们的努力而让我们能够领受一种更为贴近他本身的美好呢?我坚信上帝是万能的,所以我认为世间的任何罪恶都是因为上帝让它发生才会存在的。
,他为何要为了奖赏我们的努力而让我们能够领受一种更为贴近他本身的美好呢?我坚信上帝是万能的,所以我认为世间的任何罪恶都是因为上帝让它发生才会存在的。
卢梭力证 原始 的一切都是好的,很多其他人认为 现在 的一切都是好的,而我则认为一切在 未来 都会好的。
卢梭坚持他对于原生状态的赞美,进而还赞颂野蛮。他将法布里西乌斯
 不好的一面隐去不提,无视罗马人征服世界的时候对于被征服的民族从来不讲自由与美德的事实。他热衷于搭建自己的学说,为此不惜污蔑说天才们的种种努力皆是邪恶的,却将野蛮人的道德抬高神化。斯巴达人
不好的一面隐去不提,无视罗马人征服世界的时候对于被征服的民族从来不讲自由与美德的事实。他热衷于搭建自己的学说,为此不惜污蔑说天才们的种种努力皆是邪恶的,却将野蛮人的道德抬高神化。斯巴达人
 被他尊为半神,其实他们野蛮得几乎很难算得上是人类,他们不讲公正和感恩,冷血地屠杀了曾英勇地挽救过他们这些压迫者性命的奴隶们。
被他尊为半神,其实他们野蛮得几乎很难算得上是人类,他们不讲公正和感恩,冷血地屠杀了曾英勇地挽救过他们这些压迫者性命的奴隶们。
就因为厌倦了上流社会矫揉造作的礼仪和美德,这位日内瓦的公民,就像把麦子和麸皮不加分辨地一起扔掉一样,将文明与罪恶也一同抛弃了。他根本没有弄清楚,那令他热切的灵魂深恶痛绝的罪恶到底是文明的产物,还是野蛮的余孽。他看到罪恶践踏着美德,伪善代替了真实。他看到天才被权贵摆布,为他们险恶的目的服务,却从未想过将这种种为害至巨的行为归因于权力的专横与世袭,这种制度与人因智慧超群而自然取得的超越同侪的优势针锋相对。他没有意识到,王权世袭不但使得高贵的血统不需几代就孕育出愚痴的后代,更给无数人树立了怠惰与恶行的榜样。
王权的特质中最可鄙的一点,是人们为了得到至尊的地位所犯下的种种罪恶。卑鄙的诡计、伤天害理的罪行,以及其他种种让人性蒙羞的恶行,都是取得这无上名位的必由之路。而大众竟然还能容忍,这些强取豪夺之人的后代继续安稳舒服地坐在那染血的御座之上
 。
。
当一个社会最主要的管理者只被教授以捏造罪行和一些愚蠢幼稚的例行公事,这个社会除了遍布乌烟瘴气,还能有什么其他可能?人类难道永远都不能变得有智慧吗?他们难道还要继续期望从秕子里收获谷粒、从蒺藜枝头摘取无花果吗
 ?
?
即使所有有利的条件集齐,也没有任何人能有足够的知识和智慧,可以履行国王所拥有的、不受限制的职权。何况国王的尊贵地位就是他修习智慧与美德最不可逾越的障碍。当一个人被奉承和声色犬马包围,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感情和思想?国王的地位
必然
会让他比他最卑劣的臣民还差劲,把无数人的命运系于这样一个软弱无常之人的身上实在是疯狂之举。但我们不能推翻一个强权再代之以另一个强权,因为无论哪个都会让软弱的人被毒害。对权势的滥用证明了人们彼此越是平等,社会上就越多美德和幸福。这一点和其他任何类似的道理一样,都只需简单的推理即可得到,可是它们却招来了很多人的反对。反对者说:如果古老相传的智慧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教会和国家就会陷于险境。他们污蔑那些因为看到人类的痛苦而奋起挑战统治者权威的人是渎神者、是人类公敌。这些恶毒的诽谤,竟被加诸于一位最优秀的人身上
 。虽然他已经离世,可是他宣扬和平的遗音犹在,当我们讨论到这样一个与他的心意如此切近的话题时,我们应该为他默哀。
。虽然他已经离世,可是他宣扬和平的遗音犹在,当我们讨论到这样一个与他的心意如此切近的话题时,我们应该为他默哀。
抨击完神圣的国王陛下之后,我接下来的观点大概不会再引起什么大惊小怪。我坚信任何一个靠着森严的等级来建立权威的职业,都有损德行。
举例来说,常备军就与自由格格不入。军纪的基础在于服从和严苛,要指挥军队建功立业必须要对其有充分的控制权。只有少数的军官能够感受到浪漫的荣誉感所激发的激情——这是一种建立在时下流行观念的基础之上的道德,而大部分下级士兵只能如海浪般听命行事,当他们在上级的命令下热血沸腾地冲锋陷阵的时候,他们几乎不知道也不关心为什么要这样做。
此外,也没有什么能比一帮闲散肤浅的年轻人临时驻扎在乡间更能为害乡里道德的了。他们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跟女人们搭讪,他们的恶行被掩盖在文雅的举止和光鲜的制服之下,因而更加具有危险性。他们时髦的样子,不过是奴隶的徽记,只能证明他们的灵魂中没有足够强大的个性特质。可是纯朴的乡民却不能识破他们文雅之下的轻浮,反而对他们敬畏不已,竞相效仿他们的恶行。所有军队都是专制者手中的锁链,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只为统治服务,已是社会难以承受的罪恶与愚行之重。一个有地位和财产的人,自会步步高升,除了追求奢侈的生活没事可做;而清寒的 正人君子 ,想要凭借自己的本领求得发展而不能,只得依附于人或自甘堕落。
海军的水手与此类似,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恶劣言行更加粗野。在不轮值履责的时候,他们更加懒惰。跟他们相比,陆军的轻浮似乎无伤大雅,甚至可以被称之为是活泼闲散的生活。前者接触的多是男性,所以更喜欢讲笑话和恶作剧。后者总有与上流社会女性交往的机会,惯会说些多情的假话。但不论是粗野地大笑还是斯文地假笑,他们的脑袋里都没有什么思想。
让我再把对比扩大到教士这个需要更多脑力的职业上来。虽然等级制度同样牢牢地控制着这个群体,但是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提升自己。神学院的教育养成了他们的盲从,见习时候他们又看到助理牧师如果想要得到晋升,就要对教区牧师和施主极尽谄媚。世上最强烈的对比,也许莫过于卑躬屈膝、仰人鼻息的助理牧师和仪态雍容的主教之间的区别了。不论他们所激起的是别人的尊重还是轻视,都会让他们无法善尽自己的职责。
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职业的影响,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人也许只是表面看起来通情达理,但如果你深究他的个性可能会发现并非如此。而那些软弱平凡的人,除了体貌特征,简直没有什么特质,他们所有的想法都被权威思想洗脑过,就好像被倒进了酒桶里再也无法分离出来的葡萄酒一样,他们孱弱的思维不足以让他们与他人不同。
因此社会在进化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人因为职业的影响而变成坏蛋或傻瓜。
在社会形成的早期,当人们刚刚开始摆脱蒙昧的时候,酋长和祭司掌握着支配野蛮人行为的力量之源——希望和恐惧——拥有无上的权力。因此,贵族统治自然成为政府最初的形式。但很快各方的利益均衡就被打破了,野心家们引入了君主体制和教会政治,它们都建立在封建所有制的基础上。这似乎就是王权与教权最初的来源,也是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可是这种压迫的制度并不稳定,不能长久,它引发对外战争以及国家内乱,大众在动乱中得到一些权力,迫使统治者让他们的统治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能够公正一些。于是,当战争、农业、商业、文学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统治者就不能继续像以前一样明目张胆地攫取权力,不得不将压迫进行得更为隐蔽
 。这种经过粉饰的压迫,是野心的余孽,又借着奢侈与迷信快速地传播开来。宫廷中那个怠惰的傀儡,先是变成一个穷奢极欲的怪物,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乐,继而将这种不正常的败德之行当作了施行暴政的手段
。这种经过粉饰的压迫,是野心的余孽,又借着奢侈与迷信快速地传播开来。宫廷中那个怠惰的傀儡,先是变成一个穷奢极欲的怪物,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乐,继而将这种不正常的败德之行当作了施行暴政的手段
 。
。
这种散播罪恶的王权统治,把文明的进步变成了祸害,让人头脑不清,让有识之士不得不开始怀疑人类才智的增长到底是产生了更多欢乐还是痛苦?但王权毒药本身的特质也指引我们找到了解毒的方法。如果卢梭将他的研究再提高一个层次,或者他能看到他不屑一顾的迷雾背后的真相,他敏锐的头脑就会立刻开始思索如何在真正的文明中使人类达到尽善尽美,而不会再有回到蒙昧无知时代的可怕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