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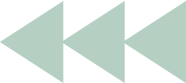
对汉语复合词的发展,迄今已有诸多解释,而大多都是从功能的角度出发的。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如Norman(1988:86)指出:复合词的发展“主要归因于语音的磨损。语音的磨损大大减少了音节对立的数量”,其结果使得语言中的同音字大量增加,因此秦汉以后复合词急剧增加以避免过多的同音词。初一看来,这一假设非常合理,但仔细分析则很难独立。首先,汉语语音从上古到中古汉语的发展,有两点不容忽视:一、复辅音的消失;二、形态性词缀的消失。
先看词缀的消失。Haudricourt(1954)提出:中古的去声来源于上古的音缀
*
-s(Mei 1994,Baxter 1992等)。据此,我们可以推知词根为CVC
 的尾辅音丛:
*
CVC-s。此外,很多学者如Benedict(1972),Bodman(1980),Mei(1994)等指出:上古汉语和古代藏语一样,有一个“具有使役或陈述功能”的前缀
*
s-,如(13)(引自Mei 1994):
的尾辅音丛:
*
CVC-s。此外,很多学者如Benedict(1972),Bodman(1980),Mei(1994)等指出:上古汉语和古代藏语一样,有一个“具有使役或陈述功能”的前缀
*
s-,如(13)(引自Mei 1994):

“林”和“森”的不同就在于有无 * s-:没有的是名词(林),有的是状态动词(森)。这个 * s-可以将一个名词变成非名词成分,具有“去名词化”的功能。据此,音缀 * s可以在CVC型词根上产出 * s-CVC型复辅音。再如,从谐声字的体系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复辅音的痕迹(Baxter 1992:175):

最后,从李方桂(1980:33)的上古汉语的构拟上也可参证上古汉语复辅音的存在。比如(李方桂1980:8):

毫无疑问,汉语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不仅词缀丢失了,复辅音蜕化了,音节结构也随之简化(参见丁邦新1979,李方桂1980,Baxter 1992等)
 。如果形态音缀开始丢失,复辅音大量简化,那么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将从原来的
*
CCVCC变成CV(C)。事实上,中古以后的汉语音节韵尾辅音只能有-m/-n/-ng和-p/-t/-k两套,主要元音前后不再允许复辅音。
。如果形态音缀开始丢失,复辅音大量简化,那么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将从原来的
*
CCVCC变成CV(C)。事实上,中古以后的汉语音节韵尾辅音只能有-m/-n/-ng和-p/-t/-k两套,主要元音前后不再允许复辅音。
毋庸置疑,复辅音的消失必将导致音节对立的急剧减少
 。如果形态性音缀和语音对立都在减少,那么该语言将出现大量的同音字,同时增加了音节表意功能的负担。因此,当时的语言必将发展出其他的方式如“复合词”来减轻音节的表意负担。这就是复合词发展功能说的基本原理。
。如果形态性音缀和语音对立都在减少,那么该语言将出现大量的同音字,同时增加了音节表意功能的负担。因此,当时的语言必将发展出其他的方式如“复合词”来减轻音节的表意负担。这就是复合词发展功能说的基本原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功能上解释复合词的来源初看很有道理,但该说潜藏着许多难以克服的深层困难。首先,功能说的基本理由是:简化的音节所承载的信息量超过了原来音节所能承载的负荷。其实,事实并不尽然。我们知道,有些简化的语音(如尾辅音),其实并未绝对消失,只不过“改头换面”变成其他类型的语音形式(声调)保留下来。从功能上讲,这类新的形式正可作为旧形式丢失的补偿。具体说,
*
-S变成了去声(参见Baxter 1992:135),
 化身为上声(Baxter 1992:320,Pulleyblank 1962:225-227,Mei 1970)。声调的出现至少可以说部分地减少了原有音节所承载的负担
[1]
。仅此一点,复合词发展的功能说便失去了它原有的解释力,更不消说“语音承载信息负荷量的加剧”并不能作为语言发展的促变因素(详论见Labov 1987)。
化身为上声(Baxter 1992:320,Pulleyblank 1962:225-227,Mei 1970)。声调的出现至少可以说部分地减少了原有音节所承载的负担
[1]
。仅此一点,复合词发展的功能说便失去了它原有的解释力,更不消说“语音承载信息负荷量的加剧”并不能作为语言发展的促变因素(详论见Labov 1987)。
在复合词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发现一些支持功能解释的证据,比如:
(17)孟子:(王良)天下之贱工也。
赵岐:(王良)天下鄙贱之工师也。
赵岐使用了两个词“鄙”和“贱”来注释“贱”。“鄙、贱”都有“技艺不高”之义;此外,“贱”还有“便宜,卑贱,轻视”等义。正如焦循(1763—1820)《孟子正义》所示:王良绝非低贱之人,所以“贱”在(17)中的意思只是“技艺不高”,此赵岐所以用“鄙”释“贱”的用心所在:用复合的方式来抵消单音词的多义性。毫无疑问,这种语义上辨析的要求,无疑是复合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复合词具有词义辨析或消除歧解的功能”就必然推出“词义辨析/消除歧解是复合词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结论。事实上,文献事实与这一结论相互矛盾。假如果真“词义辨析/消除歧解”是复合词来源的主要动因,那么可以预测:并列式(如“鄙贱”)将是复合词发展的主要形式,尤其是在发展的初期。原因很简单,按照并列结构形成的复合词最能实现上面所谓消除歧解、辨析词义的功能,其他复合形式如定中式(如“贱工”)并不能“有目的”、“自由”地用来排除单音节词的歧解义项。因此,根据功能的原则,并列式理当是复合的最初形式,然而,事实并不如此。程湘清(1981)的统计数据显示:《论语》中的并列式复合词只占少数,如下表所示(“CC”表示并列式复合词,“MH”表示定中式复合词):
表4 《论语》并列和偏正式复合词的比率

《论语》中的定中式复合词占37.2%,而并列式复合词只占26.7%。并列式少而定中式多的事实否证了功能说。
功能说解释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一时期“反功能型(counter-functional)”复合词的发展。“反功能型复合词”指的是那些“整体的意义无法从其构成成分的意思中推导而得”的复合词。如:
(18)a.动静
察其动静。(《汉书·金日磾传》)
b.车马
大夫不得造车马。(《礼记·玉藻》)
c.市朝
肆诸市朝
 (《论语·宪问》)
(《论语·宪问》)
根据功能的原则,一个词的两个成分必须都具备语义的功能才能参与构成整个复合词的语义,否则无所谓功能。大多数的情况下的确如此。比如,“战斗”(=战和斗)、“是非”(=对和错)、“衣裳”(=上为衣下为裳)等等。不管合成的意义是二者之合还是抽象的概括,有一点很清楚:为了形成一个满足语义的要求而组合起来的复合词,其中每一组合成分都必须具有独立的语义值。如果其中一个意义是零,那么它就没有出现的价值和功能。没有功能的形式,按照功能学说的道理,是不能存在的。
然而(18)中的例子在古汉语中屡见不鲜。它们的存在给功能解释带来巨大的困难。与例(4)相同,这类“偏义复词”的语义只取其中两项中的一项,另一项的意义是空的,等于零:“成败”表达的只是“败” [2] 。(18)中的“市朝”更具说服力:按古人的规矩,行刑罪犯必须在市而不能在朝。历史告诉我们:“肆诸市朝”的“市朝”只可理解为“市”而不能解为“市”和“朝”。
注意:“市朝”的表面意义包含着一个并非说话者实际所指的内容(即“朝”)。显然,听话者必须想办法排除“市朝”中那部分不是说话者所要指的对象。毋庸置疑,这类“偏义复词”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法用功能的方法来解释的,因为它们在增加而不是缓解交际的负担,它们是“反功能”的。如果真像功能说所预设的那样——复合词的发展是为了减少因语音磨损所带来的负担,或是为了满足减少语义歧解的需求——那么“偏义复词”就没有存在的理由,更不要说是复合词发展的结果了。然而事实是,它们不仅存在着而且发展着,这就充分表明,不是功能,而是“求双”的要求在语言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不管由它产生的形式是否会减轻或增加功能上的负担。换句话说,产生双音节形式的压力超越了交际功能的要求。
上述事实不仅否定了纯功能的观点,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为什么上古的语音变化能够容忍一种可能会导致交际障碍的词法运作?我们认为,其原因就是韵律,是双音音步建立的必然结果。
程湘清(1981等)指出: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发展,人们需要更多的词汇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的这一需求推动了复合词的发展,称之为“社会需求功能说”。不可否认,到了汉朝,中国政治统一,国家强大。长期的和平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中外往来,尤其是中印交往的日益频繁,佛教的影响也开始进入日常生活。社会日益复杂,为满足新建立的国家的需求,创新表达手段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但是,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仍存在一个语言学的问题需要解答:如果社会需要更多的词汇和表达手段,为什么派生式形态音缀,如前文所举的“ * -s”、“ * s-”等没有增加反倒丢失了呢?它们的丢失大大减少了词汇总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如果复合词的产生仅仅是社会发展所引起的,那么为什么复合词以双音节形式占优势,而不是三音节或更多的音节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多形态的构词法可以降低音节的负担、增加词汇的总量(如创造单音词或通过词缀构成新词等),如果创造新词是汉语复合词的动机,为什么当时的语言不通过词缀或其他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偏偏利用复合成词的办法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无法解释这一语言变化的内在机制。只靠社会功能来解释,古代汉语复合构词法的奥秘,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程湘清(1981)也提出古代汉语音系系统的简化是由于双音节复合词的发展所致,而复合词的发展则是超语言因素造成的。在汉语的文化传统里,人们优先选择成双事物的平衡美,这一选择的文化倾向导致双音节复合词的发展。毫无疑问,这种解释不仅理论上难以成立,实践上也无法“信徵”。很简单,三音节词东汉以后大量出现,但它们并不平衡。同时,这一假设也无法回答下面这些问题:为什么汉语在汉末发展出五言诗,在唐初发展出七言诗,而没有一直保持完美平衡的四言诗?
注释
[1] 以下事实清楚地表明新声调系统(tone system)的形态作用:由声调不同而相互区别的同源词(etymological words)汉代急剧增加。比如(摘自Chou 1962: 54):

[2] 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参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卷27)
(i)擅兵而别,多他利害。(《史记·吴王濞列传》)
(ii)生女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iii)先帝尝与太后有不快,几至成败。(《后汉书·窦何传》)
现代汉语中也有这类复合词,比如:
(iv)他要是有个好歹,孩子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