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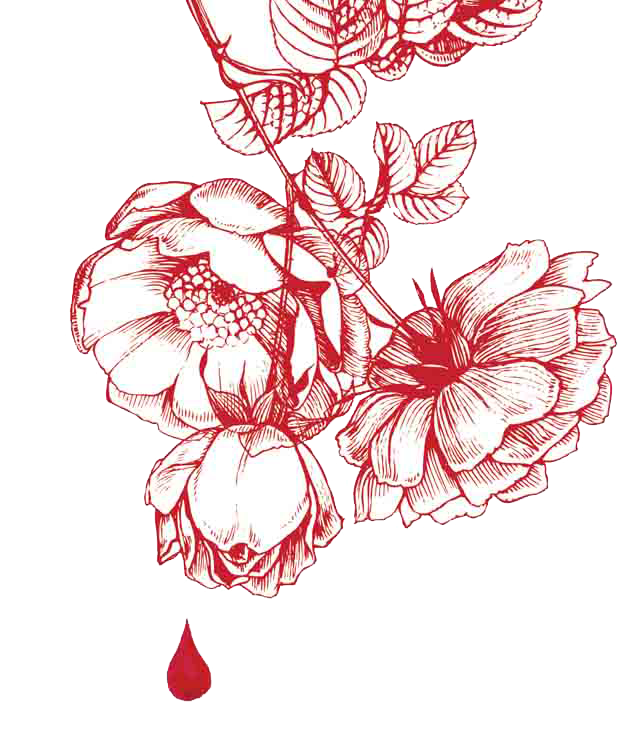
——德国通货膨胀时期中的一段插曲
列车过了德累斯顿两站,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登上了我们这小节车厢,他彬彬有礼地打了招呼,向我颔首致意,再次富有表情地望了我一眼,像是遇见一位故人。乍一看我想不起来,可当他面带微笑刚一说出他的名字时,我马上就想起来了:他是柏林最有声望的艺术古玩商人之一,和平时期我经常在他那里浏览和购买旧书以及作家手稿。我们先是随便地聊了一会儿,突然间他径直说道:
“我得告诉您,我这是从哪儿来的。作为一个艺术商人,这是我三十七年来遇见的一桩奇怪至极的插曲。您大概知道,自从货币的价值像空气一样地不值钱,现在我们这一行的行情是什么样子:一批暴发户骤然间都对哥特式的圣母像、古版书以及古老的铜版雕刻画和古画感兴趣了。根本就无法满足他们的奢望,您甚至不得不防范他们把你的整个家底搜净刮光呢。他们恨不能把衣袖上的纽扣和写字台上的桌灯都买了去。于是收进新的货物就越来越困难了——请您原谅,我突然把这些东西说成是货物,往常这可是令我们感到多少有些敬畏的呢——可是这群坏家伙就是习惯于把一本杰出的威尼斯古版书看作一大堆美元,把一张古尔希诺
 的素描当成几张一百法郎钞票的化身。这股突然涌来的抢购浪潮,其势头锐不可当。于是隔夜之间我就被搜刮得一干二净。我真想把店门一关了事。在我们这样一家老字号里——这还是我父亲从我祖父手里接过来的——竟然只有一些可怜巴巴的劣等货色,过去,在北方这都是些连走街串巷的小贩也不愿放到车上的东西,我为此羞愧至极。”
的素描当成几张一百法郎钞票的化身。这股突然涌来的抢购浪潮,其势头锐不可当。于是隔夜之间我就被搜刮得一干二净。我真想把店门一关了事。在我们这样一家老字号里——这还是我父亲从我祖父手里接过来的——竟然只有一些可怜巴巴的劣等货色,过去,在北方这都是些连走街串巷的小贩也不愿放到车上的东西,我为此羞愧至极。”
“在这种狼狈的境地里,我想出了个主意,去翻阅我们的老账本,搜索一下我们的老顾客,或许可能从他们手中重新买回几件复制品,这样一本陈旧的顾客名单一直都是某种类型的坟墓,特别是在眼下这年代,它对我的用处根本不大。我们早先的那些买主大多数不是早就把他们的收藏送进了拍卖行,就是已不在人世了,对极个别的人也不能抱什么希望。突然间翻出我们的一个老顾客的一整捆来信,我一下子就想起他来,因为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他就再也没有写信向我们订过货和询问过情况了。这些信件大约都是60年代
 以前的,这绝不是夸张!他从我祖父和父亲手里买过东西,可我记不起来,在我经营的三十七年中他进过我们的商店。一切都表明,他一定是一个古怪的、老式的、滑稽可笑的人。这样的德国人已经变得罕见了,只有在偏远的小镇里还有个把这样的人一直活到我们的时代。他写的字都是一种书法艺术,写得十分工整,钱数总额都用尺和红笔画上直道,而在数字下面都是再画上一道,以免出错。这一点以及他所用的简陋的信封和很不起眼的信纸都说明了这个无可救药的外省人的琐细和吝啬。落款处除了签上他的名字之外,他还经常带上一大串烦琐的头衔:退休的林务官、农业学家、退休上尉、一级铁十字奖章获得者。这个70年代的老兵,要是还活着的话,那至少年过八十了。但是,这个滑稽可笑的节俭人,作为一个古老的绘画艺术的收藏家却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聪颖、杰出的知识和出色的鉴赏力。我慢慢地整理他大约六十年之内的订单——最早的一批订货还只是几枚银币的事情——这时我发现,这个卑微的外省人在当时人们用一个塔勒
以前的,这绝不是夸张!他从我祖父和父亲手里买过东西,可我记不起来,在我经营的三十七年中他进过我们的商店。一切都表明,他一定是一个古怪的、老式的、滑稽可笑的人。这样的德国人已经变得罕见了,只有在偏远的小镇里还有个把这样的人一直活到我们的时代。他写的字都是一种书法艺术,写得十分工整,钱数总额都用尺和红笔画上直道,而在数字下面都是再画上一道,以免出错。这一点以及他所用的简陋的信封和很不起眼的信纸都说明了这个无可救药的外省人的琐细和吝啬。落款处除了签上他的名字之外,他还经常带上一大串烦琐的头衔:退休的林务官、农业学家、退休上尉、一级铁十字奖章获得者。这个70年代的老兵,要是还活着的话,那至少年过八十了。但是,这个滑稽可笑的节俭人,作为一个古老的绘画艺术的收藏家却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聪颖、杰出的知识和出色的鉴赏力。我慢慢地整理他大约六十年之内的订单——最早的一批订货还只是几枚银币的事情——这时我发现,这个卑微的外省人在当时人们用一个塔勒
 可以买一大堆精美的德国木刻画的年代里,不声不响地搜集到一批铜版雕刻画,这笔收藏与那些暴发户借以炫耀自己的东西相比,毫不逊色。在半个世纪里,光是他在我们这里仅用极少马克和芬尼成交的,今天的价值就会令人咋舌。除此,可以想象得出,他定也从拍卖行和其他商人手中弄到不少名贵的东西呢。从1914年起我们再也没有从他那里收到过订单了,但我对艺术商界里的事情十分熟悉,这样一批收藏如果进行拍卖或者私下里出售那是瞒不过我的。因此,这个古怪的人现在一定还活着,要不这批收藏就在他的继承人手里。”
可以买一大堆精美的德国木刻画的年代里,不声不响地搜集到一批铜版雕刻画,这笔收藏与那些暴发户借以炫耀自己的东西相比,毫不逊色。在半个世纪里,光是他在我们这里仅用极少马克和芬尼成交的,今天的价值就会令人咋舌。除此,可以想象得出,他定也从拍卖行和其他商人手中弄到不少名贵的东西呢。从1914年起我们再也没有从他那里收到过订单了,但我对艺术商界里的事情十分熟悉,这样一批收藏如果进行拍卖或者私下里出售那是瞒不过我的。因此,这个古怪的人现在一定还活着,要不这批收藏就在他的继承人手里。”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在第二天,即昨天晚上立刻动身,直奔萨克森的一座十分破旧的小镇。当我从简陋的车站穿越城镇的那条主要街道时,我简直不能相信,在这些平庸的、市民气的简陋房屋里,其中某间陋室竟住着一个拥有伦勃朗的最杰出的绘画、丢勒和蒙台纳的木刻人像的人。使我惊讶的是我在邮局询问这里是否住有叫这个名字的林务官和农业学家时,得知这位老先生确实还健在,于是我就在上午前去拜访。应当承认,我的心当时跳个不停呢。”
“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他的住处。他住在那种租费低廉的、土里土气的楼房里,这种建筑物都是在60年代草率匆忙修建起来的,他住在三楼,二楼住着一位老实的裁缝,在三楼的左边挂着一位邮政局长的牌子,闪闪发光;而在右边挂着一个小型的珐琅牌子,上面有林务官和农业学家的字样。我胆怯地拉动了门铃,随即出来了一个年迈的白发女人,她头戴一顶整洁的黑色小帽。我把我的名片递给了她,问是否可以同林务官先生面谈。她感到惊讶,先是怀有某种疑惑似的打量我,随即看了看我的名片。在这远离世界的小镇里,在这老式的房子里,出现了一个从外地来的客人,这可是一件大事。但是她和气地请我稍候,拿着名片,走进房间,我听到她轻轻地说话,随即突然响起了一个男人的洪亮的声音:‘啊,R先生,柏林来的,一家大古玩店的老板……请进来,请进来……我太高兴了!’那个老妇人快步重新走了出来,把我让进屋内。”
“我脱掉大衣,进了房间。在简朴的房间正中,笔直地站着一个健壮的老人,浓髭密髯,身上穿着一件半军用的便服,亲切地向我伸出双手。但他站在那里的这种奇怪的、僵直的姿态与他那外表上不容置疑的高兴非凡和喜出望外的欢迎姿态毫无共同之处。他一步也不朝我走来,我感到一丝愕然,只得走到他跟前,以便和他握手。可当我正要握他的手时,我发现他的那双手仍一动不动保持着水平姿势,不是来握我的手,而是在那儿等我去握。随即我全明白了,这个人是个盲人。”
“早从孩提时代起,在一个盲人面前,我总是觉得不舒服;我明知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可同时又知道,他不能像我看到他那样看到我,这总免不了使我感到某种羞赧和窘迫。当我现在看到白色浓眉下的一双业已死亡了的、僵直的、空无所视的眼睛时,我不得不克制我的愕然。但是这个盲人却不让我有更多时间发怔,我刚一握住他的手,他就使劲地摇动起来,急促地、高兴得粗声粗气地再度表示欢迎。‘稀客啊,’他满脸堆笑地对我说,‘这真是奇迹呀,柏林的一位大老板竟然光临寒舍……可一当某个生意人上路,那就要当心啊……在我们这里,人们常说:要是吉卜赛人来了,那就要紧锁房门,看好钱包……是的,我想得出您为什么来找我……眼下,在我们这个可怜的、走下坡路的德国,生意不好做啊。没有买主了,于是大老板们就又想起了他们的旧主顾,寻找他们走失了的羔羊……但在我这里,恐怕您交不上运气啦,我们这些穷苦人,靠养老金过活的老人,饭桌上有块面包,就够高兴的了。你们现在要的令人发疯的价格,我们再也付不起了……我们这样的人永远也没有份儿了。’”
“我立即解释说,他误解了我的来意。我来这儿不是向他出售什么,我只是偶尔来到这一带,有了机会,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来拜访我们的一位多年的老主顾和德国最大的收藏家之一。我刚一说完‘最大的收藏家之一’这句话,这老人的脸上便起了一种奇怪的变化。虽说他还是笔直地、僵硬地站在房子中央,可是现在他的态度突然显出欢快明亮和扬扬得意的神情。他把身子转向估计是他妻子的方向,说道:‘你听听。’声音里充满了快乐,没有一丝那种在军队里养成的粗鲁语气,而是和气地甚至是温柔地对我说:‘您这真是太好、太好了……您确是不虚此行啊。您可以看到您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的东西,即使是在你们豪华的柏林……有几幅画,在阿尔帕梯纳
 ,在该死的巴黎都找不出比它们更美的了……真的,收藏了六十年,什么样的东西能没有啊,这可不是在马路上随便看得到的。露易丝,把柜子的钥匙给我!’”
,在该死的巴黎都找不出比它们更美的了……真的,收藏了六十年,什么样的东西能没有啊,这可不是在马路上随便看得到的。露易丝,把柜子的钥匙给我!’”
“这时候却发生了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个一直站在他身边、面带微笑客气地静听我们谈话的老妇人,突然向我恳求地举起双手,与此同时猛烈地摇头表示不同意,这个暗示一开头我没有理解。这时她走到丈夫跟前,把两只手放到他的双肩上。‘海瓦特,’她提醒说,‘你还根本没问这位先生现在是不是有时间来看你的收藏呢,现在已经中午了。而饭后你得体息一个钟头,这是医生明确嘱咐了的。饭后你让这位先生看你的东西,然后我们一同喝杯咖啡,不是更好吗?那时安娜·玛丽也在这儿了,她对这些东西很熟悉,可以帮你的忙!’”
“这番话她刚一说完,就立即再次背着什么也察觉不到的老人重复那种迫切乞求的手势。我现在懂得了她的意思。我知道,她希望我现在拒绝观看他的收藏,我很快找到一个遁词,说中午有一个约会。如果能够欣赏他的收藏,我当然感到高兴和光荣,但是在三点钟之前几乎不可能了,在此之后我十分愿意。”
“他像一个孩子被人夺去了心爱的玩具那样恼火起来,老人转过身来。‘当然,’他嘟囔说,‘柏林的先生们从来都没有时间的,可这次您一定得花点儿时间的,这可不是三五幅画,这是整整二十七本画册,每本是一个大师的作品,而且没有一本里是有空页的。那就说好三点,可要准时,否则我们是看不完的。’”
“他又空无所视地把手伸给我。‘您注意,您会高兴——或者恼火。而您越是恼火,我就越是高兴。我们收藏家一向就是这样:一切都弄来给自己,而没有我们给别人的!’他再次有力地摇动我的手。”
“老妇人陪我出门。整个时间里我已觉察到她闷闷不乐、畏葸不安和不知所措的表情。刚一走出门口,她完全压低了声音、结结巴巴地对我说:‘在您来我们这里之前,是否请您允许……请您允许……我的女儿安娜·玛丽去领您前来?……这更好些……更妥当些……您大概是在旅馆用饭吧?’”
“‘当然,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乐于从命。’我说。”
“真的,就在一个小时之后,我在市集广场旁边旅馆的小饭堂里刚吃完中饭,就走进来一个老气的姑娘,她衣着简朴,用目光在搜寻。我向她走去,介绍我自己,说明我已准备停当,可以立即动身去欣赏她父亲的收藏。可她突然脸红了起来,像她母亲一样慌乱窘迫,她问我在去之前可否同我谈几句话。我立刻看出来她很为难。每当她要开口说话时,总是十分差赧,面泛红晕,不安地用手抚弄衣服。最后她总算开始说了,结结巴巴,并且老是一再地慌乱无措:
‘母亲叫我到您这儿来……她把一切都讲给我听了……我们对您有一个请求……在您去我父亲那儿之前,我们是想告诉您,我父亲当然想把他的收藏拿给您看……可是这批收藏……这批收藏……不再是完整无缺的了……其中少了一些……不幸的是,甚至可以说少了很多……’”
“她不得不又停下来喘口气,随即突然望着我,匆忙地说下去:
‘我必须完全坦率地对您讲……您清楚眼下的时代,您会了解这一切的……战争爆发后父亲的双目就完全失明了。早在这之前他的眼睛就经常犯病,而由于激动终于完全失明——战争开始那年,他虽然已七十六岁了,可还是要到法国去打仗,当军队没有像1870年那样长驱直入,他就可怕地激动起来,于是他的视力就急剧减退,要没有这场变故,他一直还完全是健壮的,在这之前不久他还能整小时走动,甚至外出打猎,这是他最喜爱的一种运动。可现在他不能出外散步,他剩下的唯一乐趣就是这批收藏,每天他都得看上一遍……说实在的,他根本不是在看,他根本也看不见了,但他每天下午把画册都拿出来,为的是至少可以用手去摸摸它们,一张接着一张,总是按着固定的次序,这是数十年来他熟记好了的……今天没有什么再引起他的兴致了,我总是给他念报纸上的拍卖价格,他听到价格越高,就越是高兴……可是……可这太可怕了,我父亲对物价、对时代是一窍不通啊……他不知道我们失去了一切,他不知道他一个月的养老金只够两天的生活用……此外还得加上我妹妹和她的四个孩子,她的丈夫战死了……可我父亲对我们经济上的困难一无所知。开头我们节俭地过,省吃俭用,可这无济于事。于是我们开始卖东西——我们当时不动他心爱的收藏——卖我们有的零星首饰,可是,我的上帝,六十年来我父亲把他省下来的每个芬尼都用在买画上了,我们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山穷水尽,我们不知该怎么办……于是,于是母亲和我卖了一张画。父亲要知道的话,是不会允许的,他不知道境况多么坏,他想象不出在黑市里买一口吃的是多么困难,他也不知道我们被打败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割让出去了,我们不再给他念报纸上这一类的事情,免得他激动起来。’”
“‘我们卖了一幅非常珍贵的画,那是伦勃朗的一张铜版蚀刻画。买主给了我们好几千马克,我们希望用这笔钱能过上一年。可是您知道,这钱也太不值钱了……我们把余款存放在银行里,可是两个月后就变得一文不值了。这样我们只得又卖一张,接着再卖一张,而买主汇来的钱老是很迟,等钱到手又不值钱了。随后我们去拍卖行,可在那儿他们也欺骗我们,出的价格是上百万……可是等这几百万马克到我们手里就又变成了一堆废纸。慢慢地就这样把他那批收藏中的最珍贵的卖得一张不剩,用来维持起码的、最可怜不过的生活,而我父亲对此一无所知。
因此,当您今天前来,我母亲十分惊慌……要是他给您打开他的画册,那一切就隐瞒不住了……我们把复制品或类似的画塞到画册里的旧框里去代替我们卖出的画,这样,他抚摩的时候就不会发觉。当他抚摩和数这些画(每一张的次序他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那种喜悦劲儿和他过去眼睛能看得见的时候一样。在这座小城镇里,父亲认为,没有一个人配看他的宝贝……他怀有一种狂热爱着每一张画。我相信,要是他知道了他手里的这批画都早已无影无踪的话,那他会心碎的。这么多年来,您是第一个他要把他的画册给您看的人。为此我请求您……’”
“突然这个女人举起双手,眼睛含着泪水,闪闪发光。”
“‘我们恳求您……您不要使他不幸……您不要使我们不幸……您不要毁掉他这最后的幻想,请您帮助我们,使他相信他要对您讲述的这些画都还在……要是他猜出了都是假的,那他肯定会死去的。或许我们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人总得活下去……人的生命,我妹妹的四个孤儿,这总比画要重要啊……直到今天我们确也没有剥夺掉他的快乐;每天下午有三个钟点他翻阅他的画册,同每张画说话,像同一个活人一样。而今天……今天也许是他最幸福的日子。多年以来,他一直等待这么一天,好向一个行家展示他这些心爱之物;我请求您……用举起的双手恳求您,不要毁掉他的幸福!’”
“她说的这一切是那样感人,我的复述根本无法表达出万一。我的上帝,作为一个生意人,我看到过许多人被无耻地掠夺得一干二净,被通货膨胀弄得倾家荡产,他们宝贵的家私为了换口奶油面包而被骗去。但是这儿,命运创造了另外一番奇特的情景,它使我极为感动。不言而喻,我答应她一定保守秘密,并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
“我们一道前往。在半路上我又愤慨地得知,别人用区区小数的钱欺骗了这两个穷苦的、无知的女人,这更坚定了我去帮助她们的决心。我们上了楼,还没等我们拉门铃,我就听见从房间里面传出来老人高兴的叫喊声:‘进来!进来!’盲人的灵敏听觉使他在我刚一上楼时就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
“‘海瓦特今天等着您看他的宝贝,急得连觉都没睡着。’老妇人微笑着说。她女儿的一个眼色就使她安下心来,知道已经取得了我的同意。在桌面上早就摆满了画册,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刚一握到我的手,来不及说其他的欢迎词儿,就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按在扶手椅上。”
“‘好了,现在我们马上开始——有好多东西要看昵,从柏林来的先生们没有时间哪。第一本画册是丢勒大师的,您可以看得出来,是相当完整的,一张比一张好,喏,这您自己能判断出来的,您看这一张!’他翻开画册的第一张,‘这是《大马》。’”
“于是他十分谨慎地,就像是接触一件易碎的物件似的,用指尖小心翼翼地从画册的纸框里取下一张上面什么也没有的、发黄的纸张,兴高采烈地把这张废纸头摆在自己的面前。他看着它,有好几分钟,实际上他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兴奋地用手把这张白纸举到眼前,脸上奇妙地呈现出一个明目人那样的聚精会神的表情。在他那双瞳仁业已僵死的眼睛里霎时间闪出一种明镜般的光亮,一种智慧的光华。这是由于纸张的反射还是内心光辉的映照?”
“‘喏,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一张极为漂亮的画呢?’他骄傲地说,‘每一个细部都多么清晰,多么细腻——我把这一张同德累斯顿的那一张作过比较,比起来那一张显得呆板、毫无生气。这儿还有收藏家的一些落款!’说着他把这张纸翻了过来,用指甲准确地指着这张白纸背面的一个地方,这使我不由自主地看过去,看那儿是否真的有什么标记。‘这是拿格勒收藏的图章,这儿是雪米和艾斯达依勒的图章;他们,这些著名的收藏家绝不会想到,他们的画有一天竟落到了这间陋室里。’”
“当这个一无所知的盲人那样赞赏一张废纸时,我脊背上不禁感到一阵发冷;看到他用指甲尖一丝不苟地指着那些只存在于他幻想中而实际上看不到的收藏者的标志,真使人难过。我觉得嗓子眼发堵,不知回答什么好;但当我不知所措地向两个女人望去时,看到了那个颤抖的、激动的老妇人乞求地举起双手,于是我镇定下来,开始扮演我的角色。”
“‘真是罕见!’我终于讷讷说道,‘一张美极了的画。’他的脸立刻由于骄矜而泛出光泽。‘这远不算什么,’他得意地说,‘您得先看看那张《忧郁》或者《基督受难》,一张着色的珍品,这样的质量再找不出第二份来,您看看吧。’他的手指又轻轻地在一张他想象中的画上比画着。‘多么鲜艳,色调多么细腻、多么温暖。柏林的古玩商和博物馆的专家们都会目瞪口呆的。’”
“这种狂喜入迷的、喋喋不休的赞赏足足有两个钟头。不,我无法向您描述,看到这一二百张白纸或粗劣的复制品是多么令人难过,但这些白纸和复制品在这个悲惨的、一无所知的盲人的记忆里却是那么真实,他能丝毫不爽地顺着次序赞美着、描绘着每一个细部,十分精确;这看不见的收藏,虽说早已失散得一干二净,可对于这个盲人,对于这个令人感动的、受骗的老人,却依然是完整无缺啊,他幻觉中的激情是那样强烈,几乎使我都开始相信他的幻觉是真实的了。只是有一次他几乎从这种夜游式的状态中被惊醒过来:在他夸奖伦勃朗的《阿齐奥帕》(这一定是一幅珍贵无比的样本)印得多么精致时,同时就用他那神经质的有视觉的手指,顺着印路在描画着,可他那敏感的触觉神经在这张白纸上却感受不到那种纹路。刹那间他的额头笼罩上一层黑影,声音慌乱起来。‘这真的……真的是《阿齐奥帕》?’他嘀咕起来,显得有些困惑。于是我灵机一动,马上从他手里把这张纸拿了过来,并兴致勃勃地对这幅我也熟悉的铜板蚀刻画中每一个细节加以描述。盲目老人业已变得困惑的面孔又恢复了常态。我越是赞赏,这个身材魁梧然而老态龙钟的盲人便越是心花怒放,一种宽厚的慈祥,一种憨直的喜悦。‘这才真是一个行家,’他欢叫起来,得意地把身子转向家人,‘终于有一个懂行的人了,你们也会知道,我的画是多么宝贵了。你们总是怀疑我,责备我把钱都花在我的收藏上。是啊,六十年来,我不喝啤酒,什么酒也不喝,不吸烟,不外出旅行,不上剧场,不买书,我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这些画。你们会看到的,等我离开人世时,那你们就会有钱,比这个城镇的任何人都有钱,和德累斯顿最有钱的人一样富有,那时你们就会对我的这股傻劲儿再次感到高兴呢。但是只要我还活着,哪一幅画也不许离开我的家。得先把我抬去埋掉,才能动我的收藏。’”
“他的手温柔地抚摩着早已空空如也的画册,像抚摩一个活物似的。这使我感到惊悸,但同时也深受感动,在战争的年代里我还从没有在一个德国人的脸上看到这样完美、这样纯真的幸福表情,站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妻女,她们与德国大师的那幅蚀刻画上的女性形象那样神奇地相似,她们来到这儿是为了瞻仰她们的救世主的坟墓,站在被挖掘一空的墓穴之前,她们面带一种惊骇至极的表情,而同时又怀有一种虔诚的、奇妙的狂喜。像那幅画上的女人在听耶稣基督的上天预言那样,这两个上了年纪的、面容憔悴的、穷苦的小资产阶级女人被老人的孩子般的喜悦所感染,半是欢笑,半是泪水。这种景象我从未经历过,它是那样动人。但是老人觉得我的赞赏仍嫌不够似的,他一直不断地翻动画册,如饥似渴地吞饮下我的每一句话。当这些骗人的画册终于被推到一旁,他不情愿地把桌子腾出来供喝咖啡用时,这对我来说如释重负。但我的这种轻松之感,却是针对他那极度兴奋、极为狂乱的快乐的,针对这像是年轻了三十岁的老人的自豪而言的,这使我感到内疚。他讲了许许多多他搜集这些画的趣闻;他拒绝他人的帮忙,不断地站起身来,一再地抽出一幅又一幅的画来,宛如喝醉了酒那样不能自主。最后,当我告诉他我得告辞时,他蓦地一怔,像一个固执的孩子那样满心不悦,气得直跺脚:‘这不行,我还一半都没看完呢。’两个女人极力使这执拗的老人理解,他不应该再挽留我了,要不我就要误火车了。”
“经过无望的挽留,他最后听从了劝告。在告别的时候,他的声音变得完全温和了。他抓住我的双手,面带一个盲人所能表现出来的全部感情,用手指爱抚地一直摸到手腕,像是要更多地了解我,或者是要给予我远非言辞所能表达出的、更多的爱。‘您的访问使我高兴极了,高兴极了。’他开始激动地说,这激动出自他内心深处,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您对我真的做了一件大好事,使我终于,终于,终于能同一个行家一道欣赏我这些心爱的画册。您会看到,您到一个老瞎子这儿来,并没有白来一趟。这儿,在我的妻子面前,她可以作证,我答应,在我的遗嘱上再加上一个条款,把我的这批收藏委托给您这家老字号负责拍卖。您应该有这份荣誉,支配这批不被人知晓的宝贝。’说到这里他把手轻轻地放在已破洗劫一空的画册上面,‘直到它们流散在世上的那一天为止。但您要答应我,印一份精美的目录:这将是我的墓碑,我不需要其他更好的了。’”
“我向他的妻子和女儿望去,她俩聚靠在一起,战栗不时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仿佛她俩成为一体,协调一致地在抖动。可我有着一种庄重的情感,因为这个令人感动的、一无所知的盲人把他那看不见的、早已无影无踪的收藏当作一批珍贵的财富委托给我支配。我激动地应允了他,可是这允诺是永远不会兑现的。在他那对业已死亡的瞳仁中重又泛出光辉。我觉察到,他有着一种出自心底的渴望,要和我亲近;我感到他的手指是那么温柔、那么亲切地紧握住我的手指,满怀着感激和庄严的情感。”
“两个女人陪我向门口走去。她俩不敢讲话,因为怕他灵敏的听觉会听到每一个字;她们望着我,两眼饱含热泪,目光里充满了感激之情。我迷迷瞪瞪地摸着下了楼梯。我真应该感到羞愧,看起来我像一个天使降临到一个穷人之家,由于我参与了一场虔诚的骗局并进行了善意的欺骗,从而使一个盲人复明了一个小时,我实际上却是一个卑劣的商贩,来到这里是想从别人手中搞去一两张珍贵的作品。但我从这里带走的远比这要珍贵得多:在这个阴郁的、没有欢乐的时代里,我又一次活生生地感受到了纯真的热情,一种照彻灵魂、完全倾注于艺术的狂热,而这种狂热我们的人早就没有了。我怀有一种敬畏的感情——我不能说出别的什么来——尽管我还一直有着一种我说不出为什么的羞愧之情。”
“我已走到了街上,上面的窗户咯吱地响动起来,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真的,老人用盲无所见的眼睛在望着估计是我走去的方向,他连这个机会都不放过。他把身子从窗户里探出很远,两个女人不得不费心地扶住他。他挥动手帕,用孩子似的欢快声音喊道:‘一路平安!’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景象:窗口上面白发老人的一张快乐的面孔,高高地飘浮在马路上愁容满面、熙来攘往、行色匆忙的众生之上,乘着一朵幻觉的白云冉冉上升,离开了我们这个令人厌恶的世界。我不由得忆起了那句古老的至理名言——我想那是歌德说的——‘收藏家是幸福的人。’”
(高中甫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