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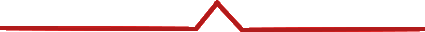
据说古巴格达哈里发哈伦·拉施德
 常会乔装成乞丐以访察民情。聚集在绝对权力周围的谄媚者们包围着哈伦,他只有使用迂回战术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哈伦就是那个著名的伊斯兰国王,他宣布将山鲁佐德处死,可是山鲁佐德会讲好听的故事,讲了一夜又一夜,一共讲了一千夜。哈伦听得入迷,一再推迟执行死刑,最后竟娶她为王后。这个著名的故事生动地描绘出专制体制的形象:那种政体的秩序靠武力来建立,以恐怖来维系,朝令夕改,反复无常。
常会乔装成乞丐以访察民情。聚集在绝对权力周围的谄媚者们包围着哈伦,他只有使用迂回战术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哈伦就是那个著名的伊斯兰国王,他宣布将山鲁佐德处死,可是山鲁佐德会讲好听的故事,讲了一夜又一夜,一共讲了一千夜。哈伦听得入迷,一再推迟执行死刑,最后竟娶她为王后。这个著名的故事生动地描绘出专制体制的形象:那种政体的秩序靠武力来建立,以恐怖来维系,朝令夕改,反复无常。
在专制政体中,有关秩序的最高准则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然而专制体制也不是完全不讲正义的:正义在十分传统的社会里也普遍流行着——习俗主宰一切,人们把普遍流行的正义观念当作自然法则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一个神授的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朝代的兴衰更替遵循着中国人常说的“天命”,但对农民来说,生活并没发生多大变化。君主的智慧主宰一切。公元前11世纪,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发生了冲突,以色列人便到统治他们的先知撒母耳那里说,他们需要一个既能主持正义、又能带领他们打仗的王。撒母耳不赞成这个要求,还警告他们说,这样的王将会剥夺他们的财产,束缚他们的活力。但以色列人仍然坚持要像别的民族一样,立一个王。在当时的中东,“王”就是一个用专制的方式对待民众的统治者,与欧洲立宪制下的统治者很不一样。之后的情形是,以色列人很幸运地拥立了扫罗、大卫、所罗门这些著名的君王,他们使以色列人享有了一段短暂的安定,甚至为以色列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所罗门对两妇人争夺同一婴儿案的裁决
 只是他传奇式智慧的一个最脍炙人口的例证。然而这些贤明的君王最终还是会采取暴虐的举措:最后所罗门规模浩大的工程所带来的沉重负担终于导致了以色列的分裂。
只是他传奇式智慧的一个最脍炙人口的例证。然而这些贤明的君王最终还是会采取暴虐的举措:最后所罗门规模浩大的工程所带来的沉重负担终于导致了以色列的分裂。
“专制主义”是一个笼统的名称,它包含许多不同的类型。非欧洲的各种文明几乎全都不可避免地被不同形式的专制体制统治过,而西方的思想创造则总是遭到各种专制统治者的敌视——从残暴的埃及法老到精神狂乱的罗马君王如卡利古拉和尼禄,还有印度和中国那样的远方异邦的皇帝。在欧洲,追求专制权力的人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欧洲人有时会被某种以诱人的理想主义面目出现的专制体制所蒙蔽——希特勒就使用过这种手法。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专制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离我们都不远。许多国家至今还在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它随时都可能带来痛苦或死亡,人们就像生活在疯人院里。
今天我们将专制主义(连同独裁和极权)定义为一种政体。这会使古希腊人大为惊骇,因为古希腊人的独特(也是他们的民族优越感)恰恰在于他们不同于那些听任专制主义统治的东方邻居。这一观念上的差异告诉我们,政治在我们的文明中占据着如此中心的地位,以至于文化和环境的每一步变迁都会引起政治含义的变化。所以,我们想要理解政治,第一步就必须摆脱现有的未加思索的信念的束缚。为什么最初曾是某些西方国家的精英所从事的一种有限的活动,如今竟被看作是无处不在的人类关注的焦点?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解释这一过程的来龙去脉。
首先要看一看古希腊人赋予政治的价值观。希腊人最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完全不同于东方人。希腊人赞赏埃及、波斯这些东方帝国的绚丽文化,却又鄙视这些国度的统治方式。他们把这种外国制度称作“专制主义”,因为这种体制下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无异于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希腊人是武士,他们鄙夷东方臣民在君主面前匍匐下拜:他们无法忍受公民与当权者之间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两千多年后,我们完全继承了这种对匍匐下拜的习惯性反感,部分的原因是“匍匐下拜”是基督教中用来描述人与神之间的距离的一种意象。谈论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常用domination(支配)这个拉丁语词。古希腊人说的despotes(主人)和古罗马人说的dominus(主人)指的都是奴隶主所特有的那种权力。当代有许多语言符号表明这种意识在我们的自我认知过程中占有未受削弱的中心地位,例如现代英语中的dictatorship(独裁)和20世纪出现的新词totalitarianism(极权)。
专制主义的本质是,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存在对统治者不受制衡的权力的挑战。臣民的唯一任务就是献媚。那里没有国会,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也没有法律来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强权剥夺。一句话,没有公众舆论,只有专制统治者的强音。奇怪的是,臣民的这种被宰制状态倒使一些专制体制成为精神启蒙的著名发源地。在一个国度里,强权的反复无常也会引发一种回应,富有思想的臣民转向神秘主义、禁欲的斯多葛主义或是其他消极隐退的信仰。他们在超越感官的精神世界里找到了生活的真谛,而社会和政治生活则被贬低为一种幻象。这种趋势的后果往往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停滞,只有短暂的繁荣算是例外。
多数社会都起源于军事征服,武力征服之后自然会产生专制制度,所以如果建立的是一种公民秩序或政治秩序,就应当被看作是了不起的成就。
 欧洲人曾在三个著名的历史时期创建过这种秩序,但其中的两次都以公民秩序或政治秩序的崩溃而告终。第一次是古希腊的城邦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专制统治者就攫取了政权。第二次是古罗马时期。罗马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帝国,但帝国的成分实在太庞杂,只有专制政权能防止它解体。第一次的经历产生了斯多葛主义和其他的遁世哲学,第二次历史经历则为基督教的诞生播下了种子。典型的中世纪政治产生于基督教思想和西方的野蛮国家,从中世纪政治中又衍生出现代的政治制度。既然我们依旧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就只好在历史不断的前进中理解政治,我们不知道前进的终点究竟在何方。
欧洲人曾在三个著名的历史时期创建过这种秩序,但其中的两次都以公民秩序或政治秩序的崩溃而告终。第一次是古希腊的城邦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专制统治者就攫取了政权。第二次是古罗马时期。罗马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帝国,但帝国的成分实在太庞杂,只有专制政权能防止它解体。第一次的经历产生了斯多葛主义和其他的遁世哲学,第二次历史经历则为基督教的诞生播下了种子。典型的中世纪政治产生于基督教思想和西方的野蛮国家,从中世纪政治中又衍生出现代的政治制度。既然我们依旧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就只好在历史不断的前进中理解政治,我们不知道前进的终点究竟在何方。
然而我们的确知道,虽然反对专制曾是西方政治传统的主要基石,但如今人们对专制的抵制已经变得暖昧起来。近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人曾梦想运用专制政权所独有的无法抵御的强力来清除我们社会中明显存在着的弊病。在欧洲,专制主义的政治方案,即便十分富有哲理或识见,也会遭到失败,除非是把它的真实本质掩盖起来。既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出幻象频生的剧目,人们就很容易发明出新名称、新观念。20世纪以各种极权主义形式出现的专制体制构筑了一个广大的政治实验场,各式各样创建完美社会的政治设想都在这里进行了演练。这些试验都失败了,这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许多人却没有认识到,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必定与隐藏在我们文明深处的某种倾向相关联。因此,要洞察政治就不能不研究某些征兆——它们或许能揭示我们文明中某一个断层的深处隐藏着什么。
一个众所周知的线索就是当前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私人领域指的是家庭生活以及个人良知的领域——个人良知即个人凭自己的意愿选择信仰和兴趣。这种私人领域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统治权威的国家公共领域支持一个维护公民自主关系的法制体系。具有统治权威的公共法律体系对自己的权力进行限定,唯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治才能存在。正如伯里克利
 在纪念伯罗奔尼撒战争头一年阵亡的雅典人葬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所说:“在私人生活中我们自由而且宽容;但在公共事务中我们严守法规。”当然,无论是就法律还是公民的态度而言,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的实际界限总是在变化。同性恋和宗教信仰过去曾受到公共领域的规制,现在则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然而婚内强奸和残害幼年子女却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律的干预。政治与专制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我们这里说的政治可以粗略地界定为自由和民主政治。
在纪念伯罗奔尼撒战争头一年阵亡的雅典人葬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所说:“在私人生活中我们自由而且宽容;但在公共事务中我们严守法规。”当然,无论是就法律还是公民的态度而言,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的实际界限总是在变化。同性恋和宗教信仰过去曾受到公共领域的规制,现在则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然而婚内强奸和残害幼年子女却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律的干预。政治与专制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我们这里说的政治可以粗略地界定为自由和民主政治。
在典型的专制国家,社会中的一切都是专制君主的财产,但现代社会“公”与“私”的基本界限却被从另一个方向一步步侵蚀了:私人领域受到公共领域限制的部分在逐步扩大。如果任何引起争议的问题都被称作“政治”问题,如果像一个流行的口号说的那样:“个人的一切都属于政治”,那就没有一样东西是在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外了。这种口号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然而它却是20世纪极权主义的基本准则,其后果显然是将个人限定在一个单一的控制体系之内,毁弃现代国家一直承继着的传统:经济、宗教、文化、社会、法律等不同的角色相互独立,各司其职。
“个人的一切都属于政治”之类的口号都是伪装成普世真理的行动计划。这类口号的意思常是模糊的,但口号中隐含的观点一遇气候便会活跃起来,要求实行与我们珍视的如个人自由之类价值观相抵触的政策。人们说,只有提高警觉才能保持自由,而警觉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留意政治语汇,这种语汇常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研究政治学首先就要注意变化的迹象。政治是一个幻觉舞台,粗心的观察者看不出它的底细。现实与幻象是政治研究的两个中心课题。首先碰到的就是政治制度和机构的命名问题。目前世界上流行的主要是西方政治模式,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一种政治体制,还有一套相应的机构和制度:议会、宪法、公民的各种权利、工会、法庭、报纸、部长等等——看起来全世界的政治都在按照同一种模式运行。事实却绝非如此。比如说,日本有一名被称作首相的政府官员,外国政治家就常闹误会,他们会很失望地发现,日本首相无法像其他国家的首脑那样不时颁布国家政策。1936年斯大林颁布了据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宪法,为苏联人民提供了权益和保障。事实上,就在颁布这部宪法的同时,斯大林正在用假审判的手段对苏联高层人士进行“清洗”。成百万的人被枪决。政客爱撒谎,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最让世人迷惑的却是称谓与现实之间的这种扑朔迷离的关系。
首先,“政治”这个名词本身就含义暖昧。一个概念如果过分地延伸就会断裂而失去表意功能。“政治”本来只指君主、国会、部长们的活动,还包括那些帮助或阻碍这些人物取得权力的政治参与者的活动。除此之外的一切活动都属于社会生活或是私人生活的范畴。随着政府权力的扩张,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以某种方式贴上了“政治”的标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这里仅举一例:政府总是要把一切好事都归功于自己,反对党则总是要把一切坏事的账都算到政府头上,于是政府和反对党就在合力传播着一个观念,即一切事情,不管好事还是坏事,都是政策造成的。这种观念使得民众遇事就去向政府请愿,似乎一切利益都可以由政府来施予。这种做法又反过来加强了“一切事物事实上都是政治”的观念。
还有一个因素导致政治的功用和含义日渐扩大。在欧洲,从远古以来政治就一直是君主和大臣们从事的活动,历史主要描述的是他们的业绩。参与政治就等于获得了不朽。1953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第一次夺取政权失败,在法庭上他为自己辩护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他把自己看作一个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凡欲名垂青史的人都会去从政。本可能成为克伦威尔
 的人们不再满足于“不曾害国家流血”,他们再也不甘愿默默无闻地老死在宁静的乡村墓地。
的人们不再满足于“不曾害国家流血”,他们再也不甘愿默默无闻地老死在宁静的乡村墓地。
 他们从政去了。法国革命将这种荣誉带给了本该默默无闻的人物如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夏洛特·科黛、圣鞠斯特等。革命者是往历史这面墙上信手涂抹的艺术家。这是极端的例子,而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希望不朽的热情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在人人可投一票的普选中得到了满足。普选当然是一种通货膨胀,它使选票贬了值,但我们仍然认为选举是一项公民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艾利丝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这是英国报纸的一条大标题,报道一位南非黑人老妇1994年第一次投票的情况。
他们从政去了。法国革命将这种荣誉带给了本该默默无闻的人物如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夏洛特·科黛、圣鞠斯特等。革命者是往历史这面墙上信手涂抹的艺术家。这是极端的例子,而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希望不朽的热情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在人人可投一票的普选中得到了满足。普选当然是一种通货膨胀,它使选票贬了值,但我们仍然认为选举是一项公民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艾利丝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这是英国报纸的一条大标题,报道一位南非黑人老妇1994年第一次投票的情况。
我们现代人(尤其是那些自认为生活在后现代的人们)特别容易对政治的本质产生误解:我们想出了种种巧妙的理由来证明我们的思想比我们的祖先高明得多。所有的文化群体都认为唯有自己信奉的信念最正确,然而今日受过教育的人们尤其无法摆脱当代各种偏见的束缚。比如说,进化的观点就使许多人认为, 我们的 信念都比前人的那些有明显缺陷的观点更伟大。当代流行的思潮的确否定了进化的观点,并明确指出我们的观念带有浓厚的本地域和本时代的烙印;这种思潮还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平等的。表面看来,这种思潮像是一种怀疑主义,将我们从自己祖辈的傲慢中解放出来,因为这好像是把我们的观点降到了与世界上其他人同等的水平。这其实只是一个假象。当代流行的怀疑主义是一种虚伪的谦恭,它掩盖了这样一个顽固的信念:我们的开放心态使我们的相对人文主义比前人的僵化和异族文化的褊狭都要高明得多。
因此,撰写政治学著作的人必须警惕自己所处时代的狭隘偏见。在当代这种危险性决不低于往昔。人们广泛地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所以政治学一直处于通识教育的核心地位。希腊和罗马贵族学习法律、哲学、公共讲演术,以便完成血统高贵者才配承担的政治使命。政治成了一门核心课程,是因为它很快地变成一种自觉的活动。政治活动促使人思索,并产生出一种极优秀的叙述方式。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探索过政治的概念,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生动地记载了政治演变的过程,政治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研究过各种政体以及制度运作的情况,伊索将政治智慧用寓言表达出来,著名的演说家如狄摩西尼和西塞罗创造了最有说服力的论辩形式,诗人写作政治题材的挽歌和讽刺诗,而历史事件中的政治场景最能激发莎士比亚等戏剧家的想象。没有一种认识或艺术创作从不涉及政治题材。
许多学术和艺术作品都是政治的镜子,只有把那些意象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体系,我们才能把握它们的真谛。我们从政治家的急功近利和学究们的清高超脱那里都能学到不少东西,应当把对二者的研究结合起来。马基雅维利
 追寻政治的“有效真理”,那只不过是为政治活动家服务的。“有效真理”有许多疏漏。我们必须从我们政治概念的奠基者——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那里开始,先讨论一下他们的各种不同观点。
追寻政治的“有效真理”,那只不过是为政治活动家服务的。“有效真理”有许多疏漏。我们必须从我们政治概念的奠基者——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那里开始,先讨论一下他们的各种不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