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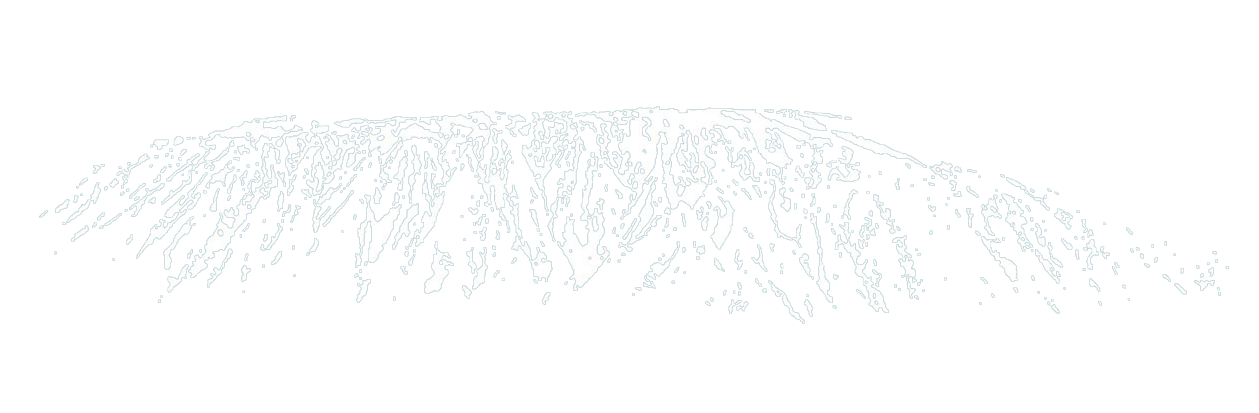

马德里挤满了名叫“帕科”的男孩,这是“弗兰西斯科”的昵称。有一个马德里笑话,说一位父亲来到马德里,在《自由报》的个人广告栏登了一则启事——“帕科,星期二中午到蒙塔纳旅馆来。一切都过去了。爸爸。”结果来了八百名年轻人,不得不出动一队宪兵才驱散他们。但这位在卢阿尔卡公寓当餐厅侍应的帕科,并没有父亲要来原谅他,也没做过什么需要父亲原谅的事。他有两个姐姐,都在这里当客房服务员。之前,他们同村一位女孩也在卢阿尔卡当客房服务员,她的勤劳诚实为小村和小村人赢得了好名声,因此,姐妹俩才得到这份工作。两个姐姐替男孩支付了到马德里的巴士车费,为他谋取了这份当学徒侍应生的工作。他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一个小乡村,那里落后得不可思议,食物匮乏,不知舒适为何物,从记事以来,他就一直在拼命干活。
他长得很壮实,天生一头漆黑的卷发,一口好牙,还有让姐姐们妒忌的好皮肤,脸上总是挂着明朗的笑容。他脚步利落,活儿干得挺好,很爱他的姐姐,她们看起来很漂亮,成熟、精致;他爱马德里,这里至今仍让他觉得难以置信;他爱他的工作,这里灯光明亮,桌布洁净,身上穿的是燕尾服,厨房里食物丰盛,仿佛充满了浪漫之美。
住在卢阿尔卡公寓并在餐厅吃饭的还有八到十二个人,但对于帕科——这三名侍者中最年轻的一个——来说,他在意的就只有那些斗牛士。
二流的剑刺手
 都在这所公寓落脚,它所在的圣朱诺尼莫大街位置很好,食物一流,膳宿也便宜。对一名斗牛士来说,保持表面的光鲜是必要的,即便无关财富,至少也关乎体面,在西班牙,礼数和尊严是最高的美德,比勇气更重要。除非花光了最后一个比塞塔
都在这所公寓落脚,它所在的圣朱诺尼莫大街位置很好,食物一流,膳宿也便宜。对一名斗牛士来说,保持表面的光鲜是必要的,即便无关财富,至少也关乎体面,在西班牙,礼数和尊严是最高的美德,比勇气更重要。除非花光了最后一个比塞塔
 ,否则没有斗牛士会离开卢阿尔卡。从没有哪个斗牛士离开这里搬去一家更好或更豪华的旅馆,二流斗牛士永远不会变成一流的。但从卢阿尔卡潦倒下去倒是很快,因为但凡能赚点儿钱的人都能住这里,客人不要求,账单绝不会出现在他面前,唯一的例外是老板娘发现他已经山穷水尽。
,否则没有斗牛士会离开卢阿尔卡。从没有哪个斗牛士离开这里搬去一家更好或更豪华的旅馆,二流斗牛士永远不会变成一流的。但从卢阿尔卡潦倒下去倒是很快,因为但凡能赚点儿钱的人都能住这里,客人不要求,账单绝不会出现在他面前,唯一的例外是老板娘发现他已经山穷水尽。
眼下就有三名正式剑刺手
 住在卢阿尔卡,此外还有两名非常好的长矛手和一位出色的花镖手。对于长矛手和花镖手来说,卢阿尔卡已经很豪华了。他们的家人都在塞维利亚,春天才来马德里,只是找个落脚处罢了。但他们收入都不错,在接下来的斗牛季里有稳定的工作,雇佣他们的斗牛士签下了不少合同。所以,这三位斗牛士助手里,任何一个都可能比那三个主斗牛士赚得多。在三个剑刺手中,一个病了却装出没事的样子,一个是昙花一现的新手,第三个是个胆小鬼。
住在卢阿尔卡,此外还有两名非常好的长矛手和一位出色的花镖手。对于长矛手和花镖手来说,卢阿尔卡已经很豪华了。他们的家人都在塞维利亚,春天才来马德里,只是找个落脚处罢了。但他们收入都不错,在接下来的斗牛季里有稳定的工作,雇佣他们的斗牛士签下了不少合同。所以,这三位斗牛士助手里,任何一个都可能比那三个主斗牛士赚得多。在三个剑刺手中,一个病了却装出没事的样子,一个是昙花一现的新手,第三个是个胆小鬼。
那个胆小鬼也曾非常勇敢,技艺超群,可在成为正式剑刺手的第一场表演上,被公牛顶破了下腹,伤势十分凶险,从此他就变了个人,倒还保留着当初成功时的好些怪毛病。他快活得过头,有事没事就哈哈笑。春风得意时,他相当热衷于恶作剧,但现在早已不玩这一套。他们敢担保,他是没这心思了。这个剑刺手长了一张开朗的聪明脸孔,举手投足都颇有派头。
生病的剑刺手总是小心翼翼,生怕露了馅,桌上的每盘菜都会去吃上一点。他有大堆的手帕,全都躲在房里自己洗,最近已经在卖他的斗牛装了。圣诞节前他已经卖掉了一套,价格很便宜,
4
月的头一个礼拜里又卖了一套。这些本来是相当昂贵的衣服,被拾掇得很好,现在他手头还有一套。生病之前,他原本前途大好,甚至可以说声势不凡。他不识字,却收藏了一些剪报,上面说,他在马德里的首秀表现得比贝尔蒙特
 还精彩。他独自坐在一张小桌边吃饭,很少抬头。
还精彩。他独自坐在一张小桌边吃饭,很少抬头。
曾经昙花一现的那位剑刺手个头很矮,皮肤黝黑,非常有派头。他也是独占一张桌子吃饭,脸上很少有笑意,更别说大笑了。他来自巴利亚多利德,那里的人全都非常严肃。他有能力,但还没来得及赢得观众的喜爱,这种风格就过时了,他的优点在于勇气和冷静,就算他的名字再出现在海报上,也无法吸引人走进斗牛场了。当年,他的新鲜感在于,他实在是太矮了,几乎看不到公牛的肩隆,可惜,小个子斗牛士也不止他一个,他始终没能让观众记住。
至于长矛手,一个瘦瘦的人,灰发、鹰脸,没那么壮,可胳膊腿儿硬得像铁一样,长裤下总套着一双牧牛人的靴子,每晚都会喝多,总色迷迷地盯着进出公寓的每一个女人。另一个是个大块头,黑皮肤,古铜色的脸,长得很好看,有印第安人似的黑发和一双大手。这两人都是一流的长矛手。尽管人人都知道,前一个因为耽于酒色,身手已经大不如前了。而第二个据说是太顽固好斗,以至于一个赛季里就会换上好几个合作的剑刺手。
花镖手已经人到中年,头发灰白,猫一般灵巧,完全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坐在桌边时就像一个事业顺当的生意人。至少在这个斗牛季里,他的双腿还状态良好,到了场上,机敏的头脑和丰富的经验都足以保证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愁没有工作。但若是双脚不够灵活时,一切就大不一样了,他会慌了手脚,不像现在,场内场外都那样镇定自若。
这一晚,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餐厅,只除了那个鹰脸长矛手,他喝多了;还有一个脸上有胎记的男人,他逢年过节都在集市上拍卖手表,也喝多了;另外还有两名从加利西亚来的教士,他们坐在角落的桌子边,就算没喝醉,也差不多了。那时候,在卢阿尔卡,酒水还是包括在膳宿费中的,侍应刚刚又拿了几瓶瓦尔德佩纳斯的新鲜葡萄酒来送到客人桌上,先是手表拍卖商,然后是长矛手斗牛士,最后轮到两位教士。
三名侍者都站在屋子一头。这里的规矩是,只有自己负责的餐区客人统统走光后,侍者才能下班。但负责两位教士那张桌子的侍应今晚有个约会,要去参加一场无政府工团主义
 者的聚会,帕科答应帮他顶个班。
者的聚会,帕科答应帮他顶个班。
楼上,生病的剑刺手正独自趴在他的床上。昙花一现的那位坐在窗边向外看,琢磨着出去到咖啡馆坐坐。胆小鬼斗牛士把帕科的一个姐姐叫到了他的房里,想拉着她做点儿什么,她正大笑着拒绝。那斗牛士说:“来吧,小野猫。”
“不。”姐姐说,“我干吗要来?”
“找点儿乐子。”
“你酒足饭饱了,现在想拿我当餐后甜点。”
“就一次。有什么坏处呢?”
“别来烦我。告诉你,别来烦我。”
“只不过是小事一件。”
“别来烦我,我告诉你。”
楼下的餐厅里,最高的那名侍者已经误了开会的时间,说:“看看那些喝个没完的黑猪猡。”
“别这么说。”第二个侍者说,“他们都是体面的客人。也没有喝得太多。”
“我看就该这么说。”高个儿说,“西班牙有两大祸害,公牛和教士。”
“这说的当然不是某一头公牛或某一个教士。”第二个侍者说。
“是的。”高个儿侍者说,“只有通过个体你才能攻击到群体。就该杀掉每一头公牛、每一个教士。一个不留。这才能清静。”
“这话留着到你的会上去说吧。”另一个侍者说。
“瞧马德里这乱七八糟的。”高个子侍者说,“十一点半都过了,这些家伙还在胡吃海喝。”
“他们十点才开始吃饭。”另一个侍者说,“你明知道这里有很多饭菜。酒也便宜。他们付过钱了。何况这酒也不烈。”
“有你这样的笨蛋,工人要怎么才能团结得起来?”高个儿侍者问。
“你瞧,”第二位侍者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我一辈子都在工作。以后的日子里也必须工作。我对工作没什么好抱怨的。这本来就是应该的。”
“是啊,只不过没什么技术含量。”
“我一直都在工作。”年长侍者说,“去参加你的聚会去吧。你不用守在这儿。”
“你是个好同志。”高个儿侍者说,“但完全没有头脑。”
“
Mejor si me falta eso que el otro
(没头脑总比没工作好)
 。”年长侍者说,“开会去吧。”
。”年长侍者说,“开会去吧。”
帕科什么也没说。他还不明白政治,但听高个儿侍者说起必须杀死教士和宪兵时,他总能感到一阵战栗。高个儿侍者让他知道了革命,革命总是浪漫的。他本人想要当一个好教徒,一个革命者,有一份像现在这样的稳定工作,同时,成为一名斗牛士。
“去开会吧,伊格纳西奥。”他说,“我会帮你看着的。”
“我们俩。”年长的侍者说。
“一个人就足够了。”帕科说,“去开会吧。”
“ 那,我就走了。 ”高个儿侍者说,“谢谢。”
与此同时,在楼上,帕科的姐姐挣脱了剑刺手的搂抱,熟练得很,就像拳击手破除对手的钳制,她生气了,说:“你们这些饿狼。没用的斗牛士。一点胆量也没有。真有本事,用在斗牛场上去啊。”
“这话说得真像个婊子。”
“婊子也是女人。我也不是婊子。”
“你早晚会是。”
“那也不会是因为你。”
“离我远点。”剑刺手说,遭到了拒绝,他又胆小了起来。
“离你远点?还有什么没离开你的吗?”姐姐说,“想要我帮你整理下床铺吗?我拿钱就是干这个的。”
“离我远点。”剑刺手说,他开朗好看的面孔皱成一团,看起来像要哭了似的,“你这婊子。你这肮脏的小婊子。”
“斗牛士。”她说着,带上门,“我的斗牛士。”
屋子里,剑刺手坐在床边,他的脸仍然皱着。在斗牛场上,他总是硬撑着挂着笑脸,把坐头排的观众吓一跳,他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是这样。”他大声说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他还记得一切都好时的光景,也不过是三年之前的事。他还记得绣金斗牛服的分量,那个 5 月的炎热午后,沉甸甸地压在肩上,那时候他在斗牛场里还和在咖啡馆里一样从容。他准备击杀公牛时,它正低下头,足以撞断木头的牛角又宽又大,角尖已经裂开,他紧盯着公牛的肩峰,那里覆盖着一层黑色的短毛,肌肉隆起,比牛角还高。他记得自己怎样把剑刺进去,手掌抵着剑柄,就像插进一块硬黄油里,很轻松,他放低左胳膊,左肩向前推,身体的重量压在左腿上,可接下来,重心不在腿上了。重量压在了小腹上,公牛抬头,把牛角扎进了他的身体里,得救之前,他两次被高高甩起。以至于到了现在,上场刺杀公牛时——这机会也很少了——他还是无法直视牛角,一个婊子哪里知道,失败之前他究竟经历过什么?她们又能经历过什么,就敢来嘲笑他?全都是些婊子,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楼下餐厅里,长矛手坐着,打量着教士。要是屋里有女人,他就死盯着她们。没有女人,他就饶有兴趣地看一个外国人, 英国人 。这会儿两者都没有,他又毫不客气地盯上了两个教士,自得其乐。这时候,长着胎记的拍卖商站起身来,叠好餐巾,走了出去。桌上还剩了大半瓶酒。如果他结清了卢阿尔卡的账单的话,一定会把酒都喝光的。
两名教士都没有看长矛手。其中一个正在说:“我到这里已经十天了,一直等着见他,整天坐在候见厅里,他肯定不会见我的。”
“有什么办法吗?”
“没有。能做什么呢?个人是没办法对抗权威的。”
“我已经待了两个星期了,一无所获。我还在等,他们也不见我。”
“咱们都是从没人搭理的小地方来的。等钱花光,就可以回去了。”
“回那个没人搭理的小地方去。马德里在乎加利西亚什么呢?咱们那儿是个穷地方。”
“人们能理解咱们的兄弟巴西里奥做的事。”
“我还不确定巴西里奥·阿尔瓦雷斯
 是不是可靠。”
是不是可靠。”
“马德里就是个让人学着懂事的地方。他毁了西班牙。”
“要是他们肯见一下就好了,哪怕拒绝呢。”
“不会的。等着吧,你早晚会受不了,精疲力竭。”
“好吧,我们就瞧着吧。别人能等,我也能等。”
这时,那长矛手站起身,穿过餐厅走向教士们的桌子,停下来,面带微笑盯着他们,头发灰白,脸孔像鹰一样。
“斗牛士。”一个教士对另一个说。
“而且是个好手。”长矛手说着,走出餐厅。他穿着一件灰色夹克,蜂腰,罗圈腿,腿上套着紧身马裤,脚上蹬着他的高跟牧靴,大步流星走出去时敲在地板上嗒嗒作响,脸上带着得意的笑。他固守着自己的职业小天地,生活自成一体,夜夜纵饮,从不把什么放在眼里。这会儿,他点起香烟,在门厅里拿了帽子歪扣在头上,出门向咖啡馆走去。
教士们突然意识到餐厅里已经没有其他客人了,连忙跟在长矛手后面起身离开。现在,除了帕科和那名中年侍者,餐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了。他们收拾好桌子,把酒瓶都拿进厨房。
厨房里还有个洗盘子的男孩。他比帕科大三岁,非常刻薄,一派愤世嫉俗的模样。
“来一杯。”中年侍者说着,倒了一杯瓦尔德佩纳斯递给他。
“为什么不呢?”男孩接过酒。
“ 你呢 ,帕科?”中年侍者问。
“谢谢。”帕科说。他们三人都喝起酒来。
“我得走了。”中年侍者说。
“晚安。”他们对他说。
他走了,留下他们俩单独在一块儿。帕科拿起一条教士用过的餐巾,身体挺得笔直,脚跟牢牢钉在地上,学着斗牛士缓缓挥动斗篷的样子,放低餐巾,头跟着转动,晃动胳膊。他转了个身,右脚微微踏前一步,挥动餐巾做了第二次诱闪,面对那假想的公牛,占据了一点地利,接下来,第三次诱闪,这一次舒缓、从容,时机刚刚好,然后,将餐巾收回腰间,做了一个贝罗尼卡衔接
 ,闪身避开了公牛的一次进攻。
,闪身避开了公牛的一次进攻。
洗碗工——他的名字是恩里克——斜眼瞄着他,带着一丝嘲笑。
“牛怎么样?”他说。
“非常勇猛。”帕科说,“看。”
挺直了腰杆,他连做了四个完美的诱闪,流畅、舒展、优雅。
“牛怎样了?”恩里克围着围裙,端着他的葡萄酒杯,靠在水池边问道。
“还有劲儿着呢。”帕科说。
“真是懒得理你。”
“怎么了?”
“看着。”
恩里克解下围裙,做了四个无懈可击的吉普赛式慢动作,逗引那假想的公牛,最后用一个雷勃列那
 收尾,趁公牛擦身冲过时,将围裙甩出一个利落的弧线,扫过它的鼻子。
收尾,趁公牛擦身冲过时,将围裙甩出一个利落的弧线,扫过它的鼻子。
“瞧瞧我这个。”他说,“可我却在这里洗盘子。”
“为什么?”
“害怕。”恩里克说,“ 恐惧 。你要是站在场上,和公牛待在一起,也会怕的。”
“不。”帕科说,“我不怕。”
“得了吧
 !”恩里克说,“人人都会怕。只是斗牛士能控制他的恐惧,好对付公牛。我参加过一次业余斗牛,吓得半死,只好逃走。人人都以为斗牛很好玩。可到时候你也会害怕的。要不是因为害怕,西班牙所有的擦鞋男孩都能当上斗牛士了。你嘛,乡下小子一个,会比我怕得更厉害的。”
!”恩里克说,“人人都会怕。只是斗牛士能控制他的恐惧,好对付公牛。我参加过一次业余斗牛,吓得半死,只好逃走。人人都以为斗牛很好玩。可到时候你也会害怕的。要不是因为害怕,西班牙所有的擦鞋男孩都能当上斗牛士了。你嘛,乡下小子一个,会比我怕得更厉害的。”
“不会的。”帕科说。
他已经在脑海中演练过太多次了。有太多次,他看着牛角,看着公牛潮乎乎的口鼻,它的耳朵抽动着,手里斗篷一挥,暴怒的公牛立刻低头猛冲过来,蹄子重重踏着地面,擦过他的身侧,当他又一次挥动斗篷时,公牛掉头又冲了过来。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最后用一个漂亮的贝罗尼卡动作收尾,牛被他逗弄得团团转,而他轻快地走开,近身闪避时牛毛挂在了他外套的金饰上;公牛呆呆站着,彻底傻了,观众欢声雷动。是的,他不会害怕。别人会害怕。他不会。他知道他不会怕。就算过去害怕,他也知道,无论如何,他都能做到。他坚信这一点。“我不会怕。”他说。
恩里克又说了一次:“得了吧!”
接着说:“要不咱们试试?”
“怎么试?”
“喏,”恩里克说,“你想象了公牛,可从来没有想象过它们的角。公牛力气很大,角尖活像尖刀,戳到人时就跟刺刀差不多,也能像重棒一样杀人。看这个。”他打开桌子抽屉,拿出两把切肉刀,“我来把它们绑到椅子腿上。然后我把椅子举在面前假装公牛,让你试试看。这刀就是牛角。如果你还能像刚才一样动作,那才算数。”
“围裙借我一下。”帕科说,“我们到餐厅里来。”
“不。”恩里克突然不刻薄了,“还是别试了,帕科。”
“不行。”帕科说,“我不怕。”
“等刀子到眼前时你就会怕了。”
“咱们走着瞧。”帕科说,“围裙给我。”
此时此刻,恩里克正拿过两条脏餐巾,好把切肉刀绑在椅子腿上,他缠好餐巾,打上结,这些刀都利得很,颇有分量。与此同时,帕科的姐姐们——两名客房服务员——正赶去电影院看《安娜·克里斯蒂》里的葛丽泰·嘉宝
 。而两名教士,一个身着内衣,在坐着读他的每日祈祷书,另一个套着长睡衣,正在念《玫瑰经》。所有斗牛士,除了生病那个,全都聚到了福尔诺斯咖啡馆,夜夜如此。大个头的黑发长矛手正在打台球,严肃的小个子剑刺手正和中年花镖手挤在一张桌上,面前是一杯牛奶咖啡,旁边还有几个一本正经的工人。
。而两名教士,一个身着内衣,在坐着读他的每日祈祷书,另一个套着长睡衣,正在念《玫瑰经》。所有斗牛士,除了生病那个,全都聚到了福尔诺斯咖啡馆,夜夜如此。大个头的黑发长矛手正在打台球,严肃的小个子剑刺手正和中年花镖手挤在一张桌上,面前是一杯牛奶咖啡,旁边还有几个一本正经的工人。
好酒的灰发长矛手也坐着,跟前摆着一杯卡扎拉斯白兰地,他正乐滋滋地看着另一张桌子,那里有两名剑刺手,一个是那早已没了勇气的胆小鬼,另一个也刚刚放下剑,重新当起了花镖手,他们身边坐着两个模样憔悴的妓女。
拍卖商站在街角和几个朋友说话。高个儿侍者在无政府工团主义集会上等待发言的时机。中年侍者坐在阿尔瓦雷斯咖啡馆的露台上喝一小杯啤酒。卢阿尔卡的老板娘已经上床睡觉,仰面躺着,枕头夹在两腿间——这是个胖女人,块头很大,诚实、干净、随和,非常虔诚,二十年来每天都为她死去的丈夫祷告,从没间断。生病的剑刺手一个人待在房里,脸朝下趴在床上,正拿手帕捂着嘴。
此时此刻,空荡荡的餐厅里,恩里克已经在餐巾上打好了最后一个结,举起了椅子,椅子腿上绑着刀。他把椅子举过头顶,绑着刀的椅子腿架在他的脑袋两侧,冲着正前方。
“这很重,”他说,“瞧,帕科。这很危险。咱们还是算了吧。”他开始冒汗了。
帕科面对他站着,抖开围裙,两手各捏住围裙的一角,拇指朝上,食指向下,展开它来吸引公牛的注意。
“直接冲过来吧,”他说,“就像一头真正的公牛那样。你愿意冲几次就冲几次。”
“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逗引呢?”恩里克问,“最好是每三次以后就插进一个衔接动作。”
“好的。”帕科说,“现在来吧。哈,
torito
 !来吧,小公牛!”
!来吧,小公牛!”
恩里克低下头,正对他冲上前来。帕科挥动围裙,恰恰掠过刀尖,它们就从他的小腹旁擦过。对他来说,这一切就是真的,真正的牛角,乌黑、光滑,角尖雪白,当恩里克跑过他身边,掉转头来继续冲刺时,就是一头血迹斑斑的怒牛正重重踏着地面跑过,现在它掉转身,像猫一样灵巧,再次对着他缓缓挥动的斗篷奔来。接着又是一次,公牛转身,冲过来,他紧盯着来势汹汹的刀尖,左脚踏前,可这次多了两英寸,他没能避过,刀子一下子插了进去,毫无阻滞,就像插进酒囊一样。滚烫的鲜血一下子喷出来,洒在冷硬的钢刀上。恩里克大叫起来,“哎呀!哎呀!等我把它拔出来!等我把它拔出来!”帕科向前倒向椅子,手里还抓着围裙斗篷,恩里克向外拽椅子时,刀就在他身体里,就在他帕科的身体里转动。
刀拔出来了,他跌坐在地板上,身下一片血泊,温热,越来越大。
“用餐巾按住。按住它!”恩里克说,“按紧。我这就去找医生。你千万要按住伤口,让它少出血。”
“应该准备个橡皮碗的。”帕科说。他在斗牛场里见过这东西。
“我直接冲过来了,”恩里克哭着说,“我只是想让你看看这有多危险。”
“别担心,”帕科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远,“去找医生来吧。”
如果是在斗牛场上,他们会抬着你跑去手术室。要是大动脉破了,来不及进手术室,也会叫神父来。
“找个教士来。”帕科说。他把餐巾死死压在肚子上,还不敢相信自己会出这样的事。
但恩里克已经冲到了圣朱诺尼莫大街上,向通宵服务的急救站跑去。帕科孤零零一个人,一开头还能坐着,接着蜷了起来,终于,倒在了地板上,觉得他的生命正从身体里流走,就像脏水从拔掉塞子的水池里哗哗流走一样,直到结束。他害怕了,觉得头很晕,想要做一个忏悔祷告,他还记得开头:“哦,我的上帝,我诚心忏悔,为一切违逆冒犯,你应享有我全部的爱,我决心……”他尽可能说得快一些,可还是来不及,他晕得厉害,趴在了地板上,很快,一切都结束了。大动脉一破,血流光的速度快得让人难以想象。
急救站的医生上楼来了,警察也在一起,抓着恩里克的胳膊。这时候,帕科的两个姐姐还在格兰大街的电影院里,正对嘉宝的电影大失所望,她们习惯了大明星周身珠光宝气的模样,可她在这部电影里却凄惨得很。观众一点儿也不喜欢这部电影,一直起哄、跺脚,表示抗议。公寓的其他人差不多都还做着自己的事,和出事前一样,只除了那两个教士和灰头发的长矛手,教士已经做完祷告,准备要睡觉了,长矛手端着酒挪到了那两个憔悴妓女的桌上,很快,就和其中一个一起走出了咖啡馆。之前,胆小鬼剑刺手也请她喝了酒。
男孩帕科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了,也不知道在第二天和未来其他日子里,所有这些人会做些什么。他们过得怎么样,结果会如何,他一无所知。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完了。他死了,就像西班牙谚语说的,带着满心幻想。活着时,他还来不及丢失幻想,甚至到了最后,都来不及完成一段痛悔短祷。也来不及对嘉宝的电影失望,它可是让整个马德里都失望了足足一个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