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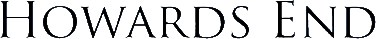

芒特太太踌躇满志地演练过她的使命。她的两个外甥女都是独立性很强的年轻女子,她能帮忙的时候并不多。埃米莉的女儿一向和别的女孩不一样。蒂比出生时,她们失去了母亲,当时海伦五岁,玛格丽特本人也只有十三岁。家遇不测,“亡妇姊妹法案”
 还未通过,芒特太太可以名正言顺地提议来威克姆街料理家务。但是她姐夫生性个别,又是个德国人,当时把这个问题推给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呢,凭着年轻气盛,一口拒绝了,说他们能把事情料理得更好。五年后,施莱格尔先生也亡故了,芒特太太再次提出帮助。玛格丽特不再那么鲁莽,表现得很感激,很客气,但是她回答的实质却和过去一样。“只有再一再二,绝无再三再四,”芒特太太想。可是她哪能袖手旁观呀。她听说,心惊肉跳的,玛格丽特刚到法定年龄,便从过去各种万无一失的投资中撤出钱来,转投海外项目,跟白扔钱差不多。沉默下去就是犯罪。她自己的资金都投资在国内铁路上,她苦口婆心地劝说她的外甥女学她的样子。“到时候我们就合在一起了,亲爱的。”玛格丽特出于礼貌,在诺丁汉铁路和德比铁路投资了几百英镑;后来,尽管海外项目一本万利,诺丁汉铁路和德比铁路渐渐衰落,节节败退的架子也只有国内铁路端得起,可芒特太太始终抱定乐观,说:“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促成的。哪天海外项目破产,可怜的玛格丽特还有一点老底儿可吃。”这年海伦也到了法定年龄,她亦步亦趋地做了同样的事情;她从公债中把她的钱撤出来,不过她几乎不用人督促,就把钱的一部分投资到诺丁汉铁路和德比铁路上了。目前为止,一切还好,但是在社交问题上,她们的姨妈却爱莫能助。姑娘们早晚要出嫁,就是人们常说的“把自己泼出去”,如果她们目前迟迟未动,那她们以后只会更加迅猛地“把自己泼出去”。她们在威克姆街上见识了太多的三教九流之人——不修边幅的音乐家们,还有一个女演员,德国远亲(大家知道外国人是什么样子),以及在欧洲大陆饭店结识的熟人(大家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这样的经历很有趣,而在斯沃尼奇那一带,谁都没有芒特太太热衷文化;不过这样的经历也很危险,不测之难早晚会来。灾难临头,她就在现场,她这是多么英明,又是多么幸运啊!
还未通过,芒特太太可以名正言顺地提议来威克姆街料理家务。但是她姐夫生性个别,又是个德国人,当时把这个问题推给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呢,凭着年轻气盛,一口拒绝了,说他们能把事情料理得更好。五年后,施莱格尔先生也亡故了,芒特太太再次提出帮助。玛格丽特不再那么鲁莽,表现得很感激,很客气,但是她回答的实质却和过去一样。“只有再一再二,绝无再三再四,”芒特太太想。可是她哪能袖手旁观呀。她听说,心惊肉跳的,玛格丽特刚到法定年龄,便从过去各种万无一失的投资中撤出钱来,转投海外项目,跟白扔钱差不多。沉默下去就是犯罪。她自己的资金都投资在国内铁路上,她苦口婆心地劝说她的外甥女学她的样子。“到时候我们就合在一起了,亲爱的。”玛格丽特出于礼貌,在诺丁汉铁路和德比铁路投资了几百英镑;后来,尽管海外项目一本万利,诺丁汉铁路和德比铁路渐渐衰落,节节败退的架子也只有国内铁路端得起,可芒特太太始终抱定乐观,说:“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促成的。哪天海外项目破产,可怜的玛格丽特还有一点老底儿可吃。”这年海伦也到了法定年龄,她亦步亦趋地做了同样的事情;她从公债中把她的钱撤出来,不过她几乎不用人督促,就把钱的一部分投资到诺丁汉铁路和德比铁路上了。目前为止,一切还好,但是在社交问题上,她们的姨妈却爱莫能助。姑娘们早晚要出嫁,就是人们常说的“把自己泼出去”,如果她们目前迟迟未动,那她们以后只会更加迅猛地“把自己泼出去”。她们在威克姆街上见识了太多的三教九流之人——不修边幅的音乐家们,还有一个女演员,德国远亲(大家知道外国人是什么样子),以及在欧洲大陆饭店结识的熟人(大家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这样的经历很有趣,而在斯沃尼奇那一带,谁都没有芒特太太热衷文化;不过这样的经历也很危险,不测之难早晚会来。灾难临头,她就在现场,她这是多么英明,又是多么幸运啊!
火车一路北去,穿行在一个又一个隧道里。路程虽只有一个小时,但是芒特太太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车窗抬起和放下。她通过了南韦林隧道,一时间看见了光亮,倏然又钻入了以悲剧闻名
 的北韦林隧道。她跨越了一座宏大的高架桥,一节节桥梁横亘在平静的草地和台温河
的北韦林隧道。她跨越了一座宏大的高架桥,一节节桥梁横亘在平静的草地和台温河
 梦幻般的水流之上。她绕过了那些政治家的公园
梦幻般的水流之上。她绕过了那些政治家的公园
 。有时,大北方公路和她结伴而行,较之铁路,公路更显得没有穷尽,一个盹儿打了一百年,一觉醒来生活变了,扑鼻而来的是汽车的油烟味儿,跳入眼帘的文化是黄疸病药丸的广告。对历史,对悲剧,对过去,对未来,芒特太太一视同仁,无动于衷;她别无牵挂,只想尽快结束这次旅行,把可怜的海伦从可怕的窘境中拯救出来。
。有时,大北方公路和她结伴而行,较之铁路,公路更显得没有穷尽,一个盹儿打了一百年,一觉醒来生活变了,扑鼻而来的是汽车的油烟味儿,跳入眼帘的文化是黄疸病药丸的广告。对历史,对悲剧,对过去,对未来,芒特太太一视同仁,无动于衷;她别无牵挂,只想尽快结束这次旅行,把可怜的海伦从可怕的窘境中拯救出来。
到霍华德庄园去的车站位于希尔顿——一个大村子,与之类似的村庄沿大北公路一个接一个排列成串,它们可观的规模完全因了来来往往的公共汽车和公共马车。由于近邻伦敦,希尔顿没有乡村的那种萧条,长长的中心街道一经发展,一路两旁便修成了居民区。大约一英里远近,一排瓦屋顶和石板屋顶的房子从芒特太太那分神的眼前闪过,其中一段被沿中心马路紧密排列在一起的六个丹麦人的古坟隔断——士兵的坟墓。通过这六个古坟后,住户变得稠密起来,火车在一片近似镇子的居民区停下来了。
这个火车站,像一路的风景,也像海伦的信,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火车站要通向哪方乡土,是英格兰还是都市的郊区?车站还新,有岛式站台和地下通道,也有生意人追求的那种表面的舒适。但是从车站中仍窥得见当地的生活,人际的交往,就连芒特太太也看出了这些特征。
“我想找一所房子,”她凑近那个票务员小声说。“它名叫霍华德庄园。你可知道它在哪儿吗?”
“威尔科克斯先生!”票务员大声喊道。
他们前边的一个年轻人转过身来。
“她在寻找霍华德庄园。”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无退路,只是芒特太太一时心潮澎湃,顾不上仔细打量生人的样子。不过她记起来那家应该是兄弟两个,很快回过神来,对他说:“原谅我多嘴,请问你是小威尔科克斯先生还是大威尔科克斯先生?”
“小威尔科克斯。我能为你效劳吗?”
“哦,这个——”她吃力地把持着自己。“真是太巧了。你是小的吗?我——”她从票务员身边走开低声说:“我是施莱格尔小姐的姨妈。我应该说明一下自己的身份,不是吗?我是芒特太太。”
她意识到他只是出于礼节把帽子略举一下,非常冷淡地说:“哦,是这样;施莱格尔小姐和我们住在一起。你想见她吗?”
“可能的话——”
“我为你叫一辆马车吧。不,请等一会儿。”他想起来了。“我家的汽车在这儿。我开车送你。”
“那就劳驾了——”
“不客气,你还得等一会儿,他们到售票处去取一件包裹。这边走。”
“我外甥女没和你一起来?”
“没有;我和我父亲一起来的。他坐你那趟火车到北边去了。吃中午饭时你会见到施莱格尔小姐的。你愿意出席午餐,我想?”
“我很高兴出席,”芒特太太说,在没有深入了解海伦的情人儿之前,她还不能明确表态吃午饭。他看上去像个绅士,但是由于他在她身边一阵忙乱,晃来晃去,她的观察力一时失灵了。她只好偷偷地从旁瞅他。从女性眼光看来,他的嘴角明显下塌算不得缺点,四四方方的额头也不是问题。他肤色浅黑,脸面刮得干干净净,看样子习惯左右别人。
“坐前边坐后边?你喜欢坐哪儿?坐前边或许风大。”
“如果可以,坐前边吧;那样我们能够交谈。”
“对不起,等我一会儿——我想知道一下他们在怎么对付那个包裹。”他大步流星地走进售票处,换了嗓门大声喊道:“嗨!嗨嗨!你们怎么搞的,非要我等一整天不可吗?威尔科克斯的包裹,霍华德庄园。瞪大眼睛找一找!”返回后,他用比较平静的声音说:“这车站乱七八糟的,没有一点秩序;要是我管这儿,他们都该统统打发回家。我可以扶你上车吗?”
“你真是太好了,”芒特太太说着,坐进一个奢侈的红皮做的深座位里,顿时被毯子和披肩包裹起来。她表现得要比原本想的客气得多,不过这个年轻人也的确十分和蔼。再说,她有点怕他:他泰然自若,不同一般。“真是太好了,”她又说一遍,并找补道:“这正合我的心意。”
“你说这话太客气了,”他回答说,脸上流露出淡淡的意外之色,只是如同多数稍纵即逝的脸色,没有引起芒特太太的注意。“我主要是开车来送我父亲赶火车的。”
“你知道,我们是今天早上才从海伦那里听说的。”
年轻的威尔科克斯往车里倒汽油,发动引擎,做些与芒特太太说的事儿毫无关系的动作。硕大的车身开始晃动,试图说明事情缘由的芒特太太全身在那些红垫子里随着车身颠上颠下。“母亲见到你会很高兴的,”他嘟哝道。“嗨,喂喂!包裹。霍华德庄园的包裹呀。快快拿出来。喂!”
一个满脸胡子的搬运工走出来,一只手拿着包裹,另一只手拿着登记簿。汽车渐渐增大的轰鸣声和断断续续的叫嚷掺和在一起:“签字,非签不可吗?干吗——等了这么大半天还非要签字吗?你连铅笔也没带一根来?记住,下次我要到站长那里告你的状。我的时间是宝贵的,尽管你的时间也许不值钱。这个。”——“这个”是指小费。
“真是抱歉,芒特太太。”
“哪儿的话,威尔科克斯先生。”
“从村子里经过你不介意吧?要绕好多道,可是我有几件别人托我的事要办。”
“我喜欢从村子里穿行。再说,我有话着急跟你说呢。”
话一出口,她感到很内疚,因为她正在违背玛格丽特的吩咐。毫无疑问只是从字面上讲违背了她的话。玛格丽特只是告诫她别跟局外人议论这件事。不过既然机会让他们俩碰上了,那么,跟这个年轻的当事人本人说说这事,也算不上“不文明不得体”吧。
作为一个不爱多嘴的人,他没有回答。坐在她身边后,他戴上手套和眼镜,他们乘车上路了,那个满脸胡子的搬运工——生活是一件神秘的事儿——羡慕地在后面目送他们。
行驶在火车站路上,风迎面扑来,把灰尘吹进了芒特太太的眼里。但是他们刚刚驱车拐上大北公路,她就喋喋不休地讲起来。“你想象得到的,”她说。“那个消息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什么消息?”
“威尔科克斯先生,”她坦率地说。“玛格丽特把底儿全告诉我了——一样没漏。我看过海伦的信。”
他两眼紧盯着手头的活儿,顾不上看她的脸;他果断地把车开上村里的中心街,把车开得飞快。但是他把头侧向她这边,说:“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你在说什么。”
“说海伦。海伦,当然说海伦。海伦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敢肯定,你就是要我挑起这个话题,我像你一样在惦记她——当然,施莱格尔一家人全都很特别。我没心情干预,可这事实在匪夷所思。”
他们来到一家布商的对面停下车。没有马上回答,他在车座上转过身来,注视着他们通过村子的道路时带起的那溜灰尘。灰尘正在散落,不过没有全部落在他开车走过的那条马路上。一部分路灰已飘进了敞开的窗户,一部分路灰染白了路旁花园里的玫瑰和醋栗,还有一部分路灰跑进村民的肺里去了。“我真不知道他们多会儿才长见识,把路面铺上柏油,”他评论说。随后,一个人拿着一卷油布从布商的店里跑出来,他们又开车上路了。
“玛格丽特不能亲自来,让可怜的蒂比拖累住了,所以我就代她来这儿把话好好说开。”
“对不起,我反应太钝了,”年轻人说着,又把车开到一家商店的外面。“可我还是一点儿没听明白呀。”
“海伦呀,威尔科克斯先生——我的外甥女和你。”
他把风镜推上去,瞪眼看着她,全然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一阵恐惧袭上她的心头,因为连她也开始疑心他们之间出了误会,她只顾履行她的使命,却一开始就误打误撞,铸成大错了。
“施莱格尔小姐和我吗?”他问过后,把嘴唇绷得紧紧的。
“我相信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误会,”芒特太太声音颤抖地说。“她的信的确是那样说的。”
“怎么说的?”
“说你和她——”她收住话,眼帘接着垂了下来。
“我想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不自然地说。“好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那么说,你一点儿没有——”她结结巴巴地说着,脸涨得通红,恨不得自己不曾出生在这个世上。
“哪里的话,我已经跟另一个女士订婚了。”一阵沉默,然后他吸口气突然说:“哦,天哪!保不齐又是保罗干的傻事。”
“可你就是保罗呀。”
“我不是。”
“那你为什么在火车站说你是?”
“我没说过这种话。”
“对不起,你说了。”
“对不起,我没说。我的名字叫查尔斯。”
“小的”对父亲来说可以是儿子,对老大来说可以指老二。两种解释都有道理,后来他们把这点说清楚了。不过他们眼下有别的问题要说。
“你是要告诉我,保罗——”
但是她不喜欢他的话音。他说话的声音仿佛他在跟一个脚夫说话,而且毫无疑问他在火车站已经欺骗了她,她于是也开始生气了。
“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保罗和你的外甥女——”
芒特太太——这就是人类的本质——下决心站在那对情人的一边。她不会让一个严厉的年轻人吓唬住。“是的,他们的确彼此产生了情分。”她说。“我敢说不久以后他们会把这事告诉你的。我们是今天早上听说的。”
查尔斯握紧拳头嚷叫说:“这个白痴,这个白痴,这个小傻瓜!”
芒特太太力图从她的毯子里挣脱出来。“如果这就是你的态度,威尔科克斯先生,我宁可走路去。”
“我求你别干那样的事情。我这就把你送到家了。我不妨告诉你,那件事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阻止的。”
芒特太太并不经常发脾气,一旦发脾气,那只是为了保护那些她所爱的人。话说到这个分儿上她再也憋不住了。“我非常同意,先生。这件事是不可能成了,我定会出面制止的。我的外甥女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眼见她痴情于那种不珍惜她的人,我不会坐在一边袖手旁观的。”
查尔斯把牙关咬了咬。
“考虑到她只是星期三才认识了你弟弟,和你父母相遇也只是在一个萍水相逢的旅馆——”
“你能低声点说吗?身后的店员会听到的。”
“Esprit de classe
 ”——不妨杜撰这个短语用在这里——因为芒特太太正处在这样的状态。她坐在车里浑身发抖的当儿,一个下层阶级的成员把一个铁漏斗、一个带把平底锅和一个花园喷雾器摆在那捆油布旁边。
”——不妨杜撰这个短语用在这里——因为芒特太太正处在这样的状态。她坐在车里浑身发抖的当儿,一个下层阶级的成员把一个铁漏斗、一个带把平底锅和一个花园喷雾器摆在那捆油布旁边。
“放后面了吗?”
“是的,先生。”那个下层阶级的成员消失在一团尘土里。
“我告诫你,保罗分文没有;这事真成了没有一点好处。”
“你放心吧,威尔科克斯先生,用不着告诫我们。我的外甥女很傻,我会好好数落她一顿,把她带回伦敦的。”
“他得在尼日利亚混出点名堂来。他在几年之内不能考虑结婚;他要娶也得娶一个能受得了那里气候的女人,在其他方面呢——为什么他至今还没跟我们说?当然他羞于启齿呀。他知道他充当了一个傻瓜。没错儿,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她气得怒不可遏。
“而施莱格尔小姐则迫不及待地公布了这一消息。”
“我要是个男的,威尔科克斯先生,冲这最后一句话我非扇你几个耳光不可。你不配给我的外甥女擦靴子,不配和她同住一个屋顶下,你竟敢——你实际上已经胆大妄为——算了,我不屑同这样一个人争吵。”
“我只知道她把这件事传开了,他却没有,我父亲出门了,我又——”
“我所知道的是——”
“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不行。”
查尔斯咬紧牙关,把汽车突然开上那条小路。
她惊叫一声。
他们就这样玩起了“谁家更胜一筹”的游戏;爱情要把两个家族的两个成员捏合在一起时,我们总爱玩一场这样的游戏。不过他们以不同寻常的劲头玩这场游戏,一方不厌其烦地声明施莱格尔一家比威尔科克斯一家好,另一方口口声声说威尔科克斯一家比施莱格尔一家好。他们都怒气冲冲,顾不得身份。男的血气方刚,女的激动万分;两个人都在暗中彰显粗鲁的情绪。他们的争吵和大多数争吵大同小异——当时无法避免,事后难以相信。不过这场争论比一般的争吵更徒劳无益。几分钟过去,他们就偃旗息鼓了。汽车来到霍华德庄园前,海伦面色煞白,跑过来迎候她的姨妈。
“朱莉姨妈,我刚接到玛格丽特的电报;我——我本来想制止你来的。事情不是——事情过去了。”
这个高潮让芒特太太难以承受。她忍不住流下泪来。
“亲爱的朱莉姨妈,别伤心。别让他们知道我干了愚不可及的事。那事算不了什么。为了我,打起精神吧。”
“保罗,”查尔斯·威尔科克斯喊着,把手套脱下来。
“别让他们知道。他们还蒙在鼓里呢。”
“哦,我亲爱的海伦——”
“保罗!保罗!”
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从房子里走出来。
“保罗,这事可是真的?”
“我还没有——我还没有——”
“是,还是不是,男子汉;简单的问题,简单的回答。真的还是假的,施莱格尔小姐——”
“查尔斯,亲爱的,”花园里传来一个声音。“查尔斯,亲爱的查尔斯,一个人不应问简单的问题。这世上没有简单的问题。”
他们都静下来了。说话的是威尔科克斯太太。
正如海伦描述的,她拖着裙子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束草。她似乎不属于那两个年轻人和他们的汽车,而属于这所住宅,属于高耸于上面的那棵榆树。大家知道她崇尚过去,知道过去能够传下来的本能的智慧单单传给了她——我们给这种智慧起了一个笨拙的名字:贵族。她出身也许不算十分高贵。但是毫无疑问她念念不忘她的先人,让先人帮助她。她看见查尔斯怒气冲天,保罗吓破了胆,芒特太太泪流满面,这时她听见先人说:“把那些将会彼此伤害至深的人分开。其余的都先推一边儿去。”因此,她没有问什么话。她更没有一如一个左右逢源的社交场合的女主人一般,做出一副任何事都不曾发生的样子。她说:“施莱格尔小姐,把你姨妈带到你的屋子还是我的屋子,你认为哪个好就到哪个去吧。保罗,一定找到埃维,告诉她午餐准备六个人的,不过我还说不准我们是不是下楼用餐。”施莱格尔小姐和保罗按她的吩咐分头行动,她朝大儿子转过身来,见他仍旧站在那辆突突抖动、油烟熏人的汽车旁边,便和蔼可亲地微微一笑,什么话也没说,离开他向她的花园走去。
“妈妈,”他叫道。“你知道保罗又在充当傻瓜吗?”
“事情都过去了,亲爱的。他们已经解除婚约了。”
“婚约——!”
“他们不再相爱了,要是你更愿意这样措辞的话。”威尔科克斯太太说,弯下腰去闻一朵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