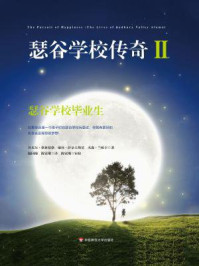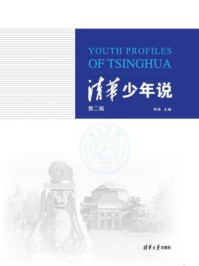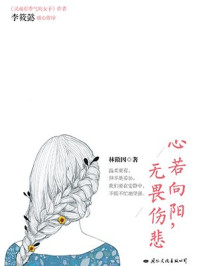我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换过多次,最先入读的小学叫培初小学,位于海防路和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的路口,是一间弄堂小学,由父子俩经营。父亲是个老夫子,通古文,其子也有四十多岁,西装笔挺,在市内另有份差事。我在这里读了三年半,读了不少古文,包括《醉翁亭记》、《赤壁赋》、《桃花源记》、《陋室铭》、《卖柑者言》、《祭十二郎文》以及古诗词等,为我后来阅读与写作打下了一点基础。我读小学时,不仅读报纸不感到困难,连半文半白的《三国演义》之类小说读起来也觉得津津有味。
到了四年级,我转学到路对面的竞华中小学。我们在楼上上课,楼下有个大院子,作为殡仪馆用地。语文改学白话文,学过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都德的《最后一课》、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记载、荷兰小学生堵住海堤透水的故事等。上课时有时会听到马路上传来一片木屐踏地的声响,原来是一群日本小学生在红头阿三(印度警察)带领下前往胶州路的一间日本小学上学,时值寒冬,他们都穿着短裤,赤脚穿木屐,一路上哆哆嗦嗦地快步行走,我们一边在听老师讲《最后一课》,一边听着楼下马路上传来的木屐声,不知是什么滋味。
在竞华中小学中有一门称为劳作课的课程,内容有很多,如将文具店买来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图案中的人物一一剪下来,让他们站在有背景的图案中。最有趣的是文具店中还有用石膏做成的小鸭模子,石膏一分为二,合起来就是中间空出来的鸭子原型,上劳作课时将蜡熔化后倒入半边石膏模子中并立即将两块石膏对准合拢快速上下晃动,然后将它浸入水中冷却,再将石膏模子分开,一个用蜡浇灌而成的小鸭子就做成了。不知今日小学中是否还有这样有趣的劳作课,也不知文具店中是否还有这样的石膏模子出售。
我在竞华中小学读了大概一年,又通过考试,转学至市立余姚路小学,这间小学位于余姚路和胶州路的路口,校址最早属于胶州公园,日本侵占上海后,将胶州公园北边一部分分割出来成为囚禁以谢晋元团长为首的抗日战士的孤军营,抗战后期日本人将孤军转移出上海,孤军营就改成了余姚路小学,现成的一排排营房改变成一间又一间的课室。靠围墙边有一片空地,老师组织我们种洋山芋(土豆),收获后就挖出来分给大家。语文课学的内容留下记忆的是鲁迅的一些作品,如《秋夜》,我对《秋夜》一文之所以会留下记忆,只因文中有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鲁迅当年住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他的屋外有两棵枣树,鲁迅不说两棵枣树,而是写成“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外语课由学英语改学日语,由日本教师上课,日文字母只学片假名,不仅要竖起来背,还要横过来背,日文字母读起来像唱歌一样,很快就能背得烂熟。老师中我至今仍能记住名字的是班主任冯月隐,她家住在跑狗场(今文化广场)附近一条弄堂中,我们几个同学去过她家,她当时在洗衣服。
由于每天只在上午上课,下午自由活动,我们班几乎每天下午都到胶州公园门口马路上踢橡皮球,一天天玩下来,对小小的橡皮球接、传、盘、射已无师自通,橡皮球很小,弹力又足,极难控制,需要眼尖、脚快、身灵活,过去上海的足球在国内所向无敌,可能与孩子们从小踢小橡皮球有关。
小学毕业时,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我先后就读于民光中学和真如中学。
民光中学在胶州路底愚园路口,学校虽无名气,但师资力量不弱,语文教员(陈节庵)、地理教员等都很有水平,尤其是教美术的李丁陇和教音乐的李丁陇夫人郑墨君,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书画家。李丁陇是我国最早赴敦煌临摹壁画同时也是国内第一个举行敦煌艺术展览的书画家,他在课堂上展示的十多幅临摹的敦煌藻井画,色彩斑斓,看后使人惊叹不已;他在黑板上用粉笔快速勾画出的奔马和花卉,使我至今难忘;他给每位学生发一小张山水画,画得很有情趣,要我们照图临摹。他的夫人郑墨君弹奏钢琴教唱外文《101首歌曲》中的若干首,对她来说,音乐只是业余爱好,她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专长是书法和绘画,在上海曾办过个人画展,其书法尤其了得。
像李丁陇这样的艺术巨擘到一个很普通的中学任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而类似李丁陇这种情况,在旧中国并不少见,这其中存在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人事制度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今后在这方面逐步进行改革。
李丁陇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是靠他的天赋,二是靠他的艰苦努力及其对艺术事业的献身精神。从1937年秋至1938年夏,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从西安奔赴敦煌,蜗居洞窟长达八个月,临摹了大量壁画,他曾用诗句描绘出这一段经历:经过千辛万苦到达敦煌时的情景是“纷纷大雪路茫茫,零下二十到敦煌”;住的是“树干暂当攀天梯,干草施作铺地床”;喝的是苦水;吃的是“青稞苦涩肠不适,红柳烧饭泪成行”;八个月下来已和山里野人一样,“骨瘦如柴人颜老,发乱似麻可尺量”。在洞窟内临摹壁画时,由于光线暗淡,他用多面镜子通过折射从洞窟外引进光线,画洞窟顶上的藻井时,用洗脸盆装上半盆水放在藻井图案下方,看着脸盆水中的倒影来画。如此看来李丁陇不仅是临摹敦煌壁画第一人,举行敦煌壁画艺术展览第一人,也是从事临摹敦煌壁画最为艰辛的一位画家。八个月期间他临摹了一百多幅图像,好几百种手的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极乐世界图》、《张骞出使西域就道图》、《成吉思汗远征图》、《千骑万乘图》、《御马图》、《黄泛写生图》、《双百图》、《赣江行迹图》等长幅画卷。他又与颜文梁合作画油画《骏马图》,与徐悲鸿合作画《梅竹图》,与刘海粟合作画《松鹰图》,临摹了《清明上河图》及从徐悲鸿处借来的《东岳大帝春游图》(徐悲鸿称此图为《八十七仙人卷》)。
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在教学与科研管理制度的影响下,晚辈们普遍急功近利,要求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很难再有像李丁陇这种数十年磨一剑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因而也很难再有惊世之作。
李丁陇无论在绘画或书法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补白大王郑逸梅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虚度九十有五了,在这数十寒暑中,所交往的朋好,莫奇于李丁陇、莫畸于李丁陇、莫野于李丁陇、莫苦于李丁陇,以伟大而言,也莫伟大于李丁陇。”刘海粟在20世纪40年代就称赞李丁陇的画作具有“高度的艺术”和“卓越的构思”。在1947年出版的《美术年鉴》中,李丁陇被放在和刘海粟、颜文梁、张大千、徐悲鸿等人同样突出的位置上进行介绍。颜文梁对李丁陇在《御马图》中画的马写下如下的评价:“今李先生此幅较唐之韩幹宋之赵子昂改进多矣。”
李丁陇在书法方面无论是篆、隶、楷、草都有很深的功底,书法家苏局仙老人称他为“墨王”。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书法方面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将王羲之继承和发展后又失传的“古篆八法”重新恢复起来,并写成了一部完整的教材。世人多知“永字八法”,少闻甚至未闻“古篆八法”,而“永字八法”恰恰是被王羲之抛弃后以“古篆八法”取而代之的写字方法。据李丁陇说:“永字八法”只限于学楷书,而“古篆八法”则适用于一切文字,不仅是篆、隶、楷、草,也包括一切洋文;不仅有助于学会写字,还有助于学会绘画,李丁陇著的《八法大纲》分上下卷,上卷讲书法,下卷讲绘画;“古篆八法”不仅有助于学会写字绘画,还可以作为一门气功,锻炼身体。李丁陇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应被埋没的,不然损失的将不仅是他个人,还有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李丁陇在20世纪30年代末从敦煌归来展示他临摹的敦煌壁画并到处奔走呼吁保护敦煌壁画之后,在艺术界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直到解放初,他在上海仍担任艺术界最高的行政职务,之后因各种原因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1989年来广州举办画展,他才为更多人知晓,但至今他的声望远不如书画界中一些在艺术造诣上和他有云泥之别的名人。
当今中国无论在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或理论界,名人甚多,其中不少确实有真才实学,但也不乏名不副实甚至滥竽充数者,如在理论界就存在着一驳即倒的博导,名家与专家之间不一定能画上等号。
真如中学位于真如镇北部的桃浦河畔,真如之名来自于真如镇上的真如寺,寺庙不大,却是宋代古寺,现为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也扩大了好几倍。真如寺的命名是取自佛经“法性真实不虚,表象如常不易”上下句中各一个字。另一说是源自佛家经典《成唯识论》第九卷中的一段话:“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谓此真如,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暨南大学曾在真如火车站(今上海西站)附近建校,因此今日在广州复办的校内有命名为真如苑的学生宿舍,校道命名为真如路,不过将“真如”二字错写成“真茹”了。我有眼不识泰山,在真如中学读书时经常经过这座寺庙,但从未入内参观,识得庐山真面目还是近些年的事了。
真如中学虽是郊区一所普通的中学,但师资力量还不错,印象较深的是音乐教员,名字已记不清,人长得很帅气,记得他说他是上海广播电台的乐队指挥,他教了好多进步歌曲,有抗日的,有反蒋的。这间学校的校长钱颂平和教员左寿山都是国民党员。学校有学生宿舍,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房间内,我住在校外附近的农民家或一家教堂的顶层上。星期六中午放学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我多半是自己来回走路,辨清方向后选乡间小道走,或从曹家渡桥入市区,或从造币厂桥(今江宁路桥)入市区,边走边欣赏江南的田园风光。早晨如果起得早,在晨雾弥漫的树林中,可以见到池塘中的鱼纷纷用力跳离水面,它们可能是想饮露水吧。
江南最美的季节是春季,或阳光明媚,粉蝶翩翩起舞,鸟声响亮;或细雨蒙蒙,水清柳新,远望小桥流水人家。夏秋之交,是我们捉蟋蟀玩的季节。上海的冬季十分寒冷,在近岸的小河上,可见到结成不规则形状的薄冰,但也有它的情趣。真如中学的周围都是农村,放寒假时我独自一人回家,此时大雪纷飞,万籁俱寂,我绕至校门背后,远远见到一株孤零零的梅树,在白白的雪花遮掩下,露出星星点点红色的花瓣,在寒冷的风雪中我裹紧了冬衣,梅花却迎着雪花绽放,我走近树旁,呆看了好一阵子,也忘记拍去洒落在身上的雪花。有了这次赏梅经历,我以后不会再去各赏梅胜地赏梅了。为什么?因为这次经历形成了我的赏梅情趣:第一,必须有雪,无雪不赏梅;第二,无他人或者少人参与,如作为景观引来大量游客,这就不是赏梅而是赏人了;第三,梅树不需多,有一两株即可,孤芳自赏,别有情趣;第四,周围为田野,均是自然风光,无高楼大厦,无车马喧哗。如今看来要满足我这种情趣是很困难的了。
北宋隐居杭州西湖孤山的林逋(967-1028)留下了咏梅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上句写梅树的姿态,是白天,下句写梅花的香味,是夜晚,整首诗都未写出雪中绽放的梅花,也就缺少了情趣,缺少勇斗严寒的傲骨形象。有人考证说,这两句诗有抄袭之嫌,说是五代的江为写的一首诗中就有这样两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14个字中雷同了12个字,这位隐士不怕有人揭发他,也够大胆了。此案是否属实我不敢断言。
我小学毕业时,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初中毕业时,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枪炮声中,我就提前初中毕业了。初中毕业时全班学生捐钱给学校买挂钟,不久我们却发现墙上的挂钟只是一座旧钟,仅在钟壳上写上是由我们班赠送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