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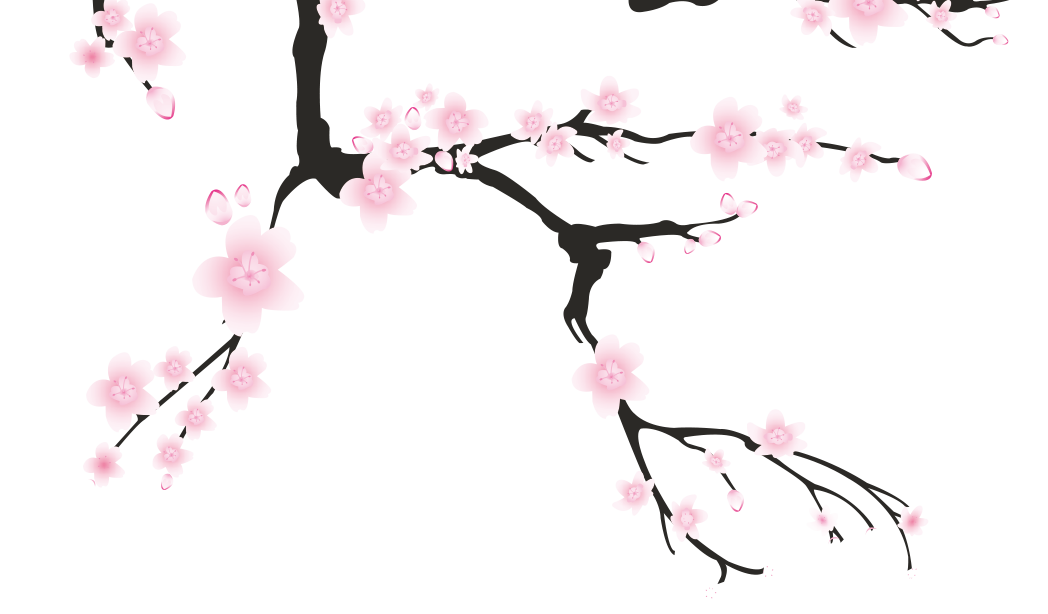
夜色茫茫。
再过一日才是十五,所以这一夜的月亮并未圆到极致,边缘处模模糊糊的,带一点妖异的红色。
山林间有薄薄雾气。
段凌奔跑间呵出来的热气,将那薄雾吹散了一些,让他看清跑在自己前方的那个人——他不知在哪里摔过一跤,跌得满身是泥,因赤着双足,脚上已添了不少细小的伤痕,一头乌发更是来不及束起,只随意地散在肩头。
段凌是半夜被他叫醒的,他仍有些茫然无措,只知道明日教主就要拿他练功,若想活命,今夜非逃不可。
一切都是慌乱而急迫的,唯有握着他的那只手,温暖有力。
不知跑了多久,那人突然停下脚步,转过头来望住段凌。
“再往前就有人看守了,你一个人走吧。”
段凌大吃一惊道:“你不跟我一起走?”
那人摇摇头,将一块乌黑的令牌塞进段凌怀里。他平日嗓音温和,这夜或许是跑得太急的缘故,听起来更为低沉一些,他说:“教主圣令只有一块,若两个人走,当场就会被人识破。”
“但你偷了教主的令牌给我,万一……”
“无事,我自有脱身之法。”那人推段凌一把,催促道,“来不及了,快走!”
段凌握着他的手不肯放,问:“为什么冒险救我?”
月光静静地照在那人的脸上,明眸善睐,一如画中之人。他并未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握了握段凌的手,冲着他微微一笑。
段凌的心怦怦而跳。
他由梦中醒来时,手上似乎还残留着温热的触觉,瞪着床帐看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自己是身处客栈的房间里。
数日前,他与陆修文收拾行装,离开了青州城。陆修文并未说出陆修言住在何处,只让他一路往南行去。
或许是快能见到修言了,他这几日频频梦见从前的事。
年纪尚幼就被恶人掳走,日日担惊受怕,朝不保夕,在那段受尽折磨的日子中,唯有陆修言温柔待他。隔了十年之久,不知修言现在是何模样?
随后他又笑自己傻气,陆修文与他是双生兄弟,就算长大后有所改变,面貌也不会相差太多。
记得从前,两人因为生得太像,时常会被人认错。陆修文又最爱换了修言的衣裳,扮作弟弟的模样欺骗别人,偏偏还总是有人上当。
只有段凌一眼就能分出真假。
他并不是发现了两人容貌上的区别,而是眼神。
陆修文的眼里藏着钩子。
他只要眼角一挑,似笑非笑地睨人一眼,就像能钩下人心尖上的肉来。
段凌有时十分怕他。
而陆修言不同。修言永远是温文沉静的,眼睛清澈明亮,犹如漫漫长夜中的寂静月光。
段凌只是回想起来,都觉得身体有些发热。他看看天色已经大亮,便起身洗漱了一番,然后去敲隔壁的房门。
敲了许久,才听陆修文的声音响起来:“谁?”
“是我。快中午了,你再不出来,我们今天就别想赶路了。”
陆修文应了一声,说:“等我一会儿。”
这一等又是许久,段凌的耐心都快用尽了,才听里面响起“嘭”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
“出什么事了?”
“没事,我不小心摔碎了杯子。”
陆修文说完这句话后,又过了片刻才来开门。
段凌觉得他的脸色格外苍白,不由得问:“你身体还好吧?”
陆修文眨了眨眼睛,道:“其他都好,就是身上没什么力气,师弟可愿背我?”
他边说边伸出手来。
段凌一把拍开他的手:“做梦。”
陆修文哈哈大笑,始终以戏弄他为乐。
段凌再次忍住了掐死他的冲动,去客栈外面套马车,套完了回头一看,见陆修文正扶着楼梯走下来,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段凌看不过去,伸手扶了他一把,又帮他上了马车,道:“来不及吃早饭了,你就吃点干粮吧。”
陆修文轻轻“嗯”了一声,之后就没动静了。
段凌急着赶路,也没去管他,鞭子一扬,马车继续往南。这一条官道不太好走,颠簸了一路,到中午时,段凌才勒住缰绳,将马车停在一棵树下。他回身撩开帘子,却见陆修文已靠着车壁睡着了。
段凌找了干粮出来,边吃边推了推陆修文,问:“要吃东西吗?”
陆修文勉力睁开眼睛,道:“不用,我喝点水就行了。”
段凌递了水壶给他,触到他手背时,却觉一片冰凉。段凌顿知不对,又碰了碰陆修文的额头,虽不像上次生病时那般烫手,却摸到一头冷汗。
“你身体当真无事?”
“当然。”
陆修文说着,却将左手往身后藏了藏。
段凌这才发现他左手紧握成拳,指缝里透出一点刺目的红色。他连忙捉住陆修文的手,扳开手指一看,只见他手里紧紧捏着一块碎瓷片,已将手掌割得鲜血淋漓。
他记得陆修文打碎过房里的茶杯,想必这碎片由此而来,可他为何要弄伤自己?
“你这是发什么疯?”
“没什么,路上太无聊了,我想吓唬吓唬师弟而已。”
陆修文若无其事地丢开手中的碎片,好似流血的并非他的手,更是丝毫也不觉得疼。
段凌扯了布条下来给他包扎伤口,突然间他灵光一现,问:“你身上的毒……是不是发作了?”
在青州时,姚大夫曾说陆修文身中剧毒,且毒已入五脏六腑,根本无药可救。只因数种毒性相互克制,反而保住了他的性命。
一旦发作起来,痛苦可想而知。
陆修文鬓边的头发已被汗水打湿了,因脸色十分苍白,便衬得他的眼眸格外的黑,乌湛湛地望了段凌一眼,道:“歇一会儿就好,不会耽误你赶路的。”
段凌气道:“谁在乎这个?你身体撑不住怎么不早说?是想死在半路上么?”
他有些懊悔自己的粗心。
陆修文一早起来就不对劲,要自己背他时,恐怕是当真没力气走路了,后来将那碎瓷片捏在掌心里,才勉强走下了楼梯。若非刚才偶然发现,他肯定还要硬撑下去。
段凌给他裹好了手上的伤,道:“我去找个大夫过来。”
“不必了,大夫治不了我的病的。”
“兴许能开些药缓解一二。”
陆修文摆了摆手,道:“与其费此功夫,倒不如……师弟留下来陪我说说话。”
段凌呆了一呆,脱口道:“我同你有什么好说的?”
陆修文浑身一颤,像是疼得厉害,整个人都蜷缩起来。段凌见他如此,只好扶住他手臂,让他靠在自己肩上,隔了一会儿,听他低声道:“我跟师弟话不投机,确实无话可说,但修言是我的弟弟,总可以说说他吧?”
提到陆修言,段凌的确有许多事要问,他想了一想,道:“修言这些年过得如何?可是吃了许多苦头?”
陆修文“扑哧”地一笑,说:“我陆修文的弟弟,我难道护不住么?岂会让他遭人欺辱?”
“魔教里讲究的是弱肉强食,你自己练功不慎、走火入魔,尚且成了这般模样,何况是不懂武功的修言?”
“我废了武功后,在教内确是举步维艰,但没过多久,我就让修言离开了天绝教,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起来。”
段凌并不信他道:“教主岂会应允?”
陆修文神色淡淡地说:“我自愿为教主试药,教主自然就允了。”
段凌大吃一惊。
旁人或许不知何为试药,他却最清楚不过了。像他这种被掳来魔教的人,最怕的不是一死,而是被抓去试药。
魔教炼制的丹药,效用各有不同,有的剧毒无比,有的却对练功大有助益,为了知晓其药性如何,教主常在活人身上尝试。
若只中一种毒也就罢了,但是试药之人,却要受千百种毒一同折磨,时而穿肠剧痛,时而奇痒难熬,时而如遭火焚,时而如入冰窟,其间种种惨烈,远胜任何一样酷刑。
段凌曾见过一个试药之人,身上皮肤寸寸溃烂,倒在地上哀呼惨叫,到最后双手双脚都烂完了,只剩森森白骨。最可怕的是这样也还不死,拖着这副身躯在地上爬,蜿蜒出一道长长的血迹。
真正生不如死。
段凌当时年纪还小,吓得做了整夜的噩梦,陆修文后来还嘲笑于他,骗他说要抓他去试药。
没想到……试药之人竟成了陆修文。
可见那教主真是丧心病狂,连自己一手栽培的爱徒也不放过。
又想到陆修文是为了保护弟弟才至如此,心中对他的恶感倒是去了不少,段凌忍不住给他拭了拭汗,说:“你这人虽然心性狠毒,对修言倒是真心维护。”
陆修文微微闭上眼睛说:“那是自然,修言可是我的亲弟弟。”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问:“师弟又为何一心要找修言?”
“修言曾救过我的性命,这就不提了。我从前在魔教时,动辄被人打骂,只有修言替我求情、为我治伤。我早已发誓,等找着他之后,要伴他一生一世。修言若喜欢孩子,我们也可以收养几个当作义子……”
陆修文蓦然打断他的话,问:“若有一人,也像修言那般对你好呢?”
段凌想也不想,立刻说:“我心中只认定了他,旁人再好上千倍万倍,我也不会多看一眼。”
他英俊的脸上微含笑意,目光说不出的动人。
陆修文像被人狠狠踢了一脚,疼得五脏六腑都移了位置,血肉模糊地搅成一团。
他为教主试药多年,再烈的毒也尝过了,却没有哪一次发作起来,似现在这样难熬。他喘了喘气,费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说出一个字来:“好……”
段凌等了半天,也不见他有下文,仔细一看,发现他已靠在自己肩头昏睡过去。但他在睡梦中也不安稳,眉头紧蹙着,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
段凌轻轻拭去他额上的汗,不知怎的,想起许多年前,他初入魔教时,陆修文提着一条银闪闪的长鞭,眯起眼睛打量他的样子。
那时他的鞭法已练得极好了,唰地一挥鞭子,从段凌脸颊边擦过,再重重地打在地上。
段凌吓出一身冷汗。
陆修文便扬了扬眉毛,大笑起来,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师弟啦。”
物是人非。
那个骄傲无比的少年,终究只在梦中了。
陆修文昏睡一夜之后,第二天的精神好了许多。
段凌却不敢再兼程赶路了,一路上对他嘘寒问暖,只把他当作了易碎的瓷器,唯恐他又犯病。浑然忘了自己从前在魔教时,夜夜都要咒骂陆修文一番。
陆修文也不客气,时刻将“师弟”两字挂在嘴边,尽情地使唤他办事。
如此一来,原本一个多月的行程,足足拖了两个月之久。
天气越来越冷,很快就入冬了。
陆修文的身体愈发地差,手脚整日都是冰凉的,段凌看不过去,又给他添了两身冬衣。
陆修言隐居的地方颇为偏僻,他们一开始还走官道,到后来就专拣乡间小路走了,最后连马车也不能行,段凌背着陆修文翻过了两座山,才到了一处风景秀丽的山谷。
谷内的气候比外头温暖一些,四面群山环绕,当中一条溪水潺潺流动,山清水秀,草木郁郁。
段凌他们到时正是傍晚,远远看见一道炊烟袅袅升起。
陆修文拉了拉段凌的衣袖,道:“我自己下来走路。”
段凌依言弯下腰。
陆修文走了几步,转头问:“我今日气色如何?”
段凌见他面色灰白,只一双眼睛仍有些神采,一看就知是病入膏肓之人,心里竟有点不是滋味,犹豫了一下才道:“尚可。”
陆修文点点头,这才继续往前走去。
不多时,就见翠绿掩映之下出现一间小小房舍,造得颇为简陋,但因为是在这样一处山谷里,反倒有种清幽静谧的味道。
暮色四合。
一个男人正在房门外劈柴,他手中的柴刀有些年头了,并不是很锋利,劈得几下,就抬起胳膊来擦一擦汗。
段凌这才看清他的相貌——比陆修文略黑一些,五官有七八分相似,俊眉修目,神色温和,他虽然穿着一身粗布衣裳,却难掩浓浓的书卷气。
段凌不由得停住脚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声大过一声。
那人很快也看见了他们,他飞快地站起身来,又惊又喜道:“大哥!”
陆修文苍白的面孔上多了一丝血色,笑说:“修言。”
陆修言快步走过来,才发现手中还拎着柴刀,忙把刀往旁边一扔,牢牢握住自家兄长的手。
两人虽不再是年少模样,但面对面站在一起时,仍旧如同双生并蒂之莲,光华夺目,俊美如昔。
“大哥终于离开天绝教来找我,是不是你的病已经治好了?”
陆修文叹一口气,道:“外头发生了许多事,世上已无天绝教了。”
“什么?”陆修言怔了怔,再细看陆修文的脸色,眉头微微皱起来,“大哥,你的病……”
陆修文最拿手的就是转移话题,他的眼睛往段凌身上一瞥,道:“我带了个朋友来见你。”
陆修言并未立刻认出段凌,上下打量他几眼,道:“你是……唔,对了,你是阿凌?对不对?”
段凌本有千言万语要对他说,但真见到了人,又说不出话来了,他半晌方道:“是我……”
陆修言瞧瞧段凌,再瞧瞧陆修文,道:“我记得你是大哥的师弟,以前常跟在他后面跑的。嗯,你从前生得高高瘦瘦,如今倒是壮实了很多。”
陆修文道:“师弟练了一身好武艺。”
“那好得很啊。”陆修言温文一笑,问:“一别多年,你今日怎么会跟大哥一起来?”
段凌在江湖上历练了几年,也算见识过大风大浪了,生死关头都不会眨一下眼睛,到了他面前,却莫名地紧张起来,说:“修言,我是为了……”
为了见你而来。
这句话尚未说完,就有人抢先叫了起来。那是一道稚嫩的童音,脆生生道:“爹!”
接着就见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儿从屋里跑出来,一头扑过来抱住陆修言的腿,叫道:“爹,吃饭啦。”
他一边说,一边瞅了瞅站在旁边的两个陌生人,双眼滴溜溜转着,又是害羞又是好奇。
“辰儿。”陆修言笑着抱他起来,道,“这是我常跟你提起的伯父,快叫人。”
陆辰直盯着陆修文看,老气横秋地问:“你就是跟我爹长得一模一样的伯父?”
“是啊。”陆修文摸摸他的头,问,“像么?”
“像是像,不过辰儿认得出来。”
陆修文不禁失笑。
陆修言又指着段凌道:“叫叔叔。”
陆辰这回倒没作怪,干干脆脆地喊了一声叔叔。
他的声音清脆动听。
听在段凌耳里,却如同轰隆一声雷响,震得他半天回不过神。
这男孩儿叫修言什么来着?
爹?
“这是……你的儿子?”
“对,辰儿今年刚满五岁。”陆修言瞧瞧天色,道,“不该让你们站着说话的,晚饭已经煮好了,进去一起吃吧。”
正说着话,又有一人从屋内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少妇打扮的清丽女子,荆钗布裙亦难掩姿色,她走过来轻轻挽住陆修言的胳膊,含笑道:“夫君。”
段凌尚未从之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不料又遭重击,表情都有些麻木了,怔怔地出不了声。
“夫君。”那女子红唇轻启,笑吟吟道,“既然来了客人,怎么不叫人家进屋去坐?”
“是我大哥来了。”
“大哥,你可总算来了,修言日日念叨着你。”那女子立即敛衽为礼,接着又望向段凌,“这位是……”
“这位段公子是我大哥的师弟,亦是我的朋友。”
“段公子。”
段凌嗓子里像卡了什么东西,咽不下也吐不出,勉强道:“陆夫人……”
短短三个字,每个字都像在剜他的心。
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段凌已记不清了,只知道那男孩说了句话,然后全家人一齐笑起来。陆修言拍了拍身旁女子的手,娇妻爱子,其乐融融。
随后他就被请进屋里吃饭。因不知道有客人来,陆夫人只炒两个简单的家常菜,但就算是山珍海味,段凌也是食不知味。一顿饭下来,他几乎一言不发。
家中总共只有两个房间,晚上睡觉时,段凌只好跟陆修文挤在一处。他进了房里还是沉默不语,望着桌上越烧越短的蜡烛,忽然道:“我明日就离开此地。”
陆修文正低头看书,闻言头也不抬,道:“好呀,多谢师弟千里迢迢送我过来。”
段凌一听更来气了,他跑了这么一趟,连表明心迹的机会也无,反倒便宜了陆修文。
“你早就知道修言已经成家了?”
“嗯,我跟弟弟虽然见不着面,但时常互通消息。”
“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师弟没有问起,我为何要说?”陆修文一脸无辜,甚至还故作惊讶道,“难道你从来没想过,修言可能已成亲生子了?”
“我……”段凌气结。
他自己心意坚定,便以为陆修言必定更胜他千百倍,毕竟当初修言可是冒着性命危险救了他!谁料得到……
想到那和和美美的一家三口,段凌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陆修文偏还要煽风点火,啧啧摇头道:“原来是师弟你自作多情。”
又道,“你不如赶紧找个女子成亲吧。等来年生个女儿,还来得及跟辰儿结娃娃亲。”
段凌冷哼一声,将手中的茶杯当作他的脖子,“啪”一下捏得粉碎。
陆修文瞧他一眼,眼底笑意浮动道:“师弟若是不肯死心,也不是毫无办法。”
“什么?”
“在你面前,不还有一个姓陆之人吗?”
段凌呆了一下,当场拔出剑来,就要为民除害。
陆修文不闪不避,故意打了个哈欠,说:“好师弟,还不快帮我铺床?”
段凌差点把床给拆了。
后来想到这是陆修言家的床,他才忍住了没动。但他也不愿跟陆修文挤一张床,所以干脆吹熄蜡烛,在桌边坐了一夜。
天快亮时,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见少年时的陆修言推门而入,依稀是那夜月光下的模样,头发乌黑,眼神明亮,唤他道:“阿凌。”
段凌张了张嘴,刚想说话,就从梦里醒了过来。
屋内暗沉沉的,房门紧闭着,窗外是半明半亮的天色。
段凌顿觉一阵惆怅。
他是再也睡不着觉了,洗漱一番后,他开门走了出去。
山谷里的清晨格外清幽,听得见鸟雀鸣叫之声,透过薄薄雾气,可见云端处现出一丝微光。
段凌信步在溪边走了两圈,没想到正遇见早起打水的陆修言。
“修言……”
“阿凌,怎么起得这么早?睡不习惯吗?”
“不,是前几日睡得太多了,所以早些起来。”
“山中条件简陋,委屈你了。”
“不会,这地方风景秀丽,正适合你跟陆夫人这样的神仙眷侣。”段凌捏了捏拳头,感觉胸口一阵酸涩,却还是说,“我不知道你已经成亲了……恭喜。”
“哈哈,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说什么恭喜?”陆修言拍了拍他的肩,道,“家里没什么好吃的,不过我酿了两坛好酒,晚上一起喝吧。”
段凌瞧着他心无芥蒂的模样,心想或许真是他自作多情了。他心心念念多年的救命之恩,恐怕陆修言早已忘了。
段凌深深地叹一口气,尽量让自己语气自然:“你当年偷出那教主令牌,定是冒了极大的风险,无论如何,我总要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阿凌……”
陆修言愣了愣,刚要开口说话,就听“吱呀”一声,陆修文推开门走了出来。
他自见到弟弟后,气色好了许多,今日穿一身白的,倒不显得脸色如何苍白了,他斜斜地倚在门口,懒洋洋道:“修言,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说着,他望了段凌一眼,问:“师弟不介意吧?”
段凌自然不好同他抢,又想到昨夜被他戏弄的事,他一声不吭地转开头去。
陆修言本就有一肚子话要问自家兄长,只是昨日人多嘴杂,许多话不便提起。这时瞧着天气不错,便向段凌告了声罪,陪陆修文去附近的林子里转悠。
虽然已经入冬,但林中草木仍旧郁郁,远处传来流水的潺潺声,寂静中透着清雅。
陆修言也不多说废话,开门见山道:“大哥跟我说句实话,你的病……究竟如何了?”
陆修文并不立刻答他。他双手负在身后,瞧一眼四周连绵起伏的山峦,指着其中一座山峰,问:“那座是什么山?”
“那是落霞山。每日夕阳西下时,霞光漫天,灿若织锦,只那座山上的景致最是动人,因此得了这个名字。”
“既是看落霞的地方,怎么弟妹这么早就上山了?”
陆修言定睛一看,果然在半山腰发现一道袅娜的身影,他脸上的神情不由得温和几分,道:“辰儿他娘在山上种了两株凤凰树,日日都会上山浇水的。”
陆修文颔首道:“见你们夫妻鹣鲽情深,辰儿又这么聪明懂事,我总算是放心了。”
“大哥……”
“当年是怕你被我牵连,才叫你避世隐居的,如今天绝教已灭,你若觉山中日子清苦,就带辰儿他们搬去外头住吧。”
“在山中住久了,反而嫌外边烟火气太重。”
“是吗?我也喜欢这山谷。”陆修文弯了弯唇角,平静地道,“待我死后,就将我埋在那落霞山上吧,也好日日瞧见云霞漫天的景致。”
他对自己的病一直避而不答,现在突然说出这番话来,倒将陆修言吓了一跳。
“大哥 ! ”他急得鼻尖上都出汗了,“你怎么说这样不吉利的话?”
陆修文神色如常,淡笑道:“每个人都难逃一死,不过或迟或早而已。”
“但是大哥还这么年轻……你从前送我离开天绝教时,曾说过找到了治病的法子,只是要留在教中医治,难道竟是骗我的?”
陆修言说到这里,连眼圈也红了。
陆修文像安抚辰儿那样,轻轻拍了拍他的头,道:“大哥岂会骗你?我当初翻阅古籍,确实找到了治病之法,只是那法子太过古怪,想来只是那位前辈胡乱撰写,当不得真的。天意如此,亦是无可奈何。”
陆修言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却仍劝道:“这法子不行,总有别的法子,世上多有神医高人,未必治不好你的病。”
“弟弟说的也有道理,只是这几日可太冷了,等来年春天,天气暖和一些,再去找那神医吧。”
陆修言并不知道他只剩数月之命,还当是说动了他,正欲细谈此事,却听陆修文道:“方才师弟同你说了些什么?”
“阿凌?他刚才说到教主令牌,又说到救命之恩,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怕是有些误会。”
“没有误会。”陆修文黑眸沉沉,断然道,“你数年前救过他一命,他要报恩,就让他报吧。”
“可我从来没有……”陆修言一顿,恍然道,“大哥,你又扮作我的模样骗他了?”
“他每次都能认出你我,我想瞧瞧有没有例外。”
“大哥你最爱欺负阿凌。不过教主令牌事关重大,你如何偷得出来?教主他……”陆修言不知想到了什么,脸上倏然变色,“教主从前常说,大哥你是难得一见的练武奇才,待他百年之后,教主之位非你莫属。可后来不知为何,教主突然雷霆震怒,说你触犯了教中规矩,将你一身武功尽废了,莫非就是为了此事?是了,是了,阿凌正是那时候不见了……”
陆修文静了一会儿,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问:“修言,我可有求过你什么事?”
陆修言呆了一呆,说:“从小到大,一直是大哥护着我。天绝教那等险恶之地,若不是有大哥在,我早死过千百遍了。”
“好,那你今日便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师弟既然认错了人,干脆让他将错就错,你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陆修言大惑不解:“阿凌说了要报恩的,为何要瞒着他?”
此时日头高升,阳光透过树叶子照下来,风轻轻吹动陆修文的衣摆。陆修言这才发现,他比从前瘦得太多了。但是提到段凌时,他还是忍不住微微一笑,眼中的神情难描难画,足令铁石也动了心肠,他叹息似的低语道:“我家师弟最重情义,我明知自己命不久矣,又何必叫他伤心难过呢?”
段凌等了陆修言一天。
他中午吃了两个陆夫人蒸的馒头,下午又给那个叫陆辰的男孩削了一柄木剑。
陆辰长得更像他娘亲,小脸白白净净的,一双眼睛尤其灵活,老是骨碌碌地转来转去。段凌在溪边练剑时,他就跟着舞动小胳膊小腿,还挺像模像样的。他早上还叫段凌叔叔,到了下午时,已经一口一个师父地喊着了。
段凌看着他汗津津的头顶,想到这是与陆修言血脉相连之人,就狠不下心来纠正他。他甚至忍不住想,或许他可以在这里造一间屋子,与陆修言比邻而居。
只是有一点不好,陆修文肯定也会住下来,以后日日相见,气也给他气死了。接着他想到半年忽忽而过,往后不管他愿不愿意,都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一颗心竟沉了沉,心里说不出的气闷。
陆修言到了傍晚才回来,手中提了一只鲜血淋漓的野兔。
陆修文慢吞吞地跟在后面,朝陆辰招了招手,变戏法似的取出两块糕点来。陆辰这臭小子立刻变节,欢呼着跑了过去,将新认的师父扔在了脑后。段凌无所事事,见陆修言蹲在溪边剥兔子皮,便走过去搭了把手。
“你们午饭是在山里吃的?”
“嗯,打了点野味。”
“晚上有兔子肉,正好可以下酒。”
陆修言扯了扯嘴角,勉强笑了一下。段凌见他眼眶发红,料想已经知道陆修文的事了,他一时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隔了一会儿他才道:“我早上说过,要报你的救命之恩。你日后但有吩咐,纵使是刀山火海,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陆修言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陆修文正在旁边陪陆辰玩儿,凉凉地扫了一眼过来。
陆修言便又将话咽了下去,低头专心洗那只兔子,道:“哪里用得着去闯刀山火海?只要阿凌你过得快快活活的,我……我就别无他求了。”
段凌心中一酸,道:“这是当然。”
陆修言手势熟练,不多时就将野兔洗好了,拎进去剁成小块,再加上八角、茴香一起炒了,香气四溢。陆夫人另炒了两个素菜,虽然只是些山间野菜,但也别有风味。
这顿饭比昨日丰盛许多,陆修言自家酿了梅子酒,这日便开了两坛,正好与段凌对饮。
他俩人心里都不好受,喝起酒来,还真有些得逢知己的感觉。陆夫人天一黑就带陆辰进屋睡了,陆修文也熬不得夜,最后只剩他们两个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
“这梅子酒酿了有七年,我离开大哥也是七年,没想到再次相见,他竟已病入膏肓。”
“哈哈,你不过是七年,我却想了一个人整整十年。”
“我兄弟二人父母早亡,大哥从小就倔得很,为了护着我,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在那天绝教里,他不敢有半点行差踏错。”
“若知道是白白等这十年……哼,我也早就娶妻生子了。”
陆修言酒量一般,段凌也不见得多好,两人醉得糊里糊涂,说起话来牛头不对马嘴,竟也接得下去。
段凌不记得自己喝了多少酒,只知道两坛酒饮尽,陆修言又搬了两坛出来。到后来,他喉咙里火辣辣地烧着,趴在桌上睡了过去。
睡梦中,隐约听见陆修言喊了一声大哥。
等醒过来时,他已经躺在屋内的床上了。他酒劲还没过去,头疼得睁不开眼睛,感觉有人推了推他的肩,在他耳边道:“喝点醒酒汤吧。”
这声音有些耳熟。
段凌勉力睁开双眼,发现面前这张脸也是熟悉的。他不由得笑起来,唤他道:“修言。”
面前那人并不应声。
段凌急了,连忙去抓他的手,又叫一遍:“修言……”
这次的声音轻得很,生怕将他吓跑了。
面前那人静了一会儿,然后笑了笑,低头去喝碗里的醒酒汤。
段凌醉得厉害,脑子里糊成一团,愣愣地问:“汤不是给我喝的吗?”
“嗯,是给你喝的。”
那人凑到段凌跟前来,脸孔忽然变作十年前的模样,像那天在月色底下一般。
接着段凌就尝到了醒酒汤的滋味。气味古怪的汤水并未让他清醒过来,他反而醉得更加厉害,他急切地追逐着,渴望品尝到更多醉人的味道。
有来不及吞咽的汤汁顺着嘴角淌下来,段凌忍不住舔了舔。
有人“嗯”了一声,退了开去。
段凌想起逃出魔教的那个夜晚,陆修言对他笑过之后,也是这样转身离去,从此一别十年。
回忆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段凌突然来了力气,他从床上坐起来,一把抱住了那个人。
“别走……”
那人怔了怔,伸手来扳他的手:“酒还没醒么?别闹了。”
段凌紧抱着他不放,低声地叫:“修言……修言……”
那人一开始还挣扎几下,后来便渐渐安静下来,反手抱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