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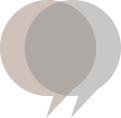
商业最令人吃惊的地方是,商人们往往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金钱上,只把少量的注意力关注于服务,这在我看来是违反了自然程序的。当一桩买卖完成时,厂家和顾客的关系实际上并未结束,而恰恰是刚刚开始。任何把服务放在首位的人,其出路都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汽油马车”是底特律的第一辆——在很长时间内也是惟一的一辆汽车。它被人们认为是讨厌的东西,因为它的响声很大,容易惊吓马匹。同时也会引起交通堵塞,因为无论何时我把它停在镇上的什么地方,在我把它开走之前,总有一大群人围观。在我离开哪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里,总有一些好奇的人想去试着开动它。最后,我不得不带上一条链子,不论我把它停在哪里,都用链子把它锁在电线杆上。随后,警察来找麻烦了,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好像还没有限速的法律。但不管怎样,我要从市长那儿得到特别的许可。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享受着作为美国惟一获得驾驶执照的司机的殊荣。从1895年到1896年,我驾驶着那辆车跑了大约有1000英里。后来,我把它以2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底特律的查尔斯·安斯利(Charles Ainsley)。这是我的第一笔买卖。我制造这辆车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实验,但我还想制造另一辆新车。安斯利想买,我需要这笔钱,在价钱方面我们也毫不费周折地做成了这笔交易。
以这样一种方式制造汽车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我期望着大批量地生产。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得有产品,这可着急不得,欲速则不达。1896年,我开始制造第二辆汽车。它与第一辆车很像,只是轻一些。它同样也是用传送带驱动——这点是我后来才放弃的,因为传送带虽然很好,但在天热时就不行。这正是我后来采用齿轮的原因。从这辆车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与此同时,国内和国外的其他一些人也在制造汽车。1895年,我听说有一辆来自德国的奔驰车在纽约的摩西商店(Macy’s Store)展览。我专门跑过去参观,结果发现它根本不值得一看。它也是用传送带驱动的,但比我的车重多了。我一直在为汽车的轻便而努力,而外国制造者们似乎从未重视过轻便意味着什么。接着,我在自家的车间里又制造了3辆汽车,它们都在底特律行驶了数年。现在,我还拥有原来的第一辆汽车——几年之后我把它从安斯利先生转卖的那个人手中买了回来,花了100美元。
这段时间,我仍然继续着电力公司的工作,并逐渐被提升为月薪125美元的总工程师。但是我的内燃机实验并不被公司的董事长所欣赏——就像当年我父亲不欣赏我的机械才能一样。我的老板并不反对实验,只是反对内燃机实验。直到今天,他的声音似乎依然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电力!毫无疑问,将来会是电力的世界。但燃气——见鬼去吧。”
他的怀疑——用中性的词来说——好像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没有人对内燃机的未来有着最有远见的理解,因为我们正步入电力发展的伟大时代。作为相对新鲜的概念,电力被赋予能做远比我们今天知道的更多工作的期待。不过,我看不出怎样使用电力来达到我实验的目的,即使架空线更便宜一些,也没法用触轮来驱动道路用车,而且也没有一种重量合适的蓄电池能够适用于汽车。一辆电车的活动范围肯定是受限制的,并且还有带着与它所生产的动力成比例的大型电动设备。这并不是说我认为电力不行,只不过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使用电力。但电力有电力的好处,内燃机有内燃机的好处,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代替另一个——这一点真是莫大的幸运。
我拥有最初在底特律爱迪生公司掌管的那台电机。当我们开始建设加拿大的电厂时,我把它从电厂所卖给的一座办公大楼处买了回来,稍微修理了一下之后,好几年来它在加拿大的电厂运行得非常好。由于企业的发展,我们需要建新的电站,所以我把这台曾经的老马达送到了我的博物馆——迪尔伯恩的那间装满我很多机械珍宝的屋子。
爱迪生公司向我提供了公司总监的职位,但条件是我必须放弃研究内燃机,把精力投入到他们认为真正有用的方面。看来,我需要在我的汽车和我的工作之间做出选择了。当然,我选择了汽车,或者说我放弃了工作。实际上我无需选择,因为我已经确信汽车肯定会成功的。我在1899年8月15日辞职,从此将全部精力投身于汽车事业。这也许可以认为是很重大的一步。因为我个人并没有多少积蓄,除了生活费之外,全部的钱都花在了汽车实验上。但我的妻子很赞同汽车不该放弃——我们要么一起成功,要么一起失败。当时并没有对汽车的需求,甚至从未有过对新产品的需求。它们被接受的方式有点像飞机在近年被接受的方式。最初,“不用马拉的车”被认为是异想天开,很多“聪明人”还特别地解释一下,为什么它只能是个玩具,更没有一个有钱人设想它会具有商业价值的可能性。我无法想象,为什么在每一种新的交通工具诞生之初,都会遭到如此多的反对,直至今天,还有一些人摇头晃脑地一边谈论着汽车的奢侈,一边不情愿地勉强承认卡车的用途。而最初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汽车可以成为一种产业,最乐观的人也只是希望它能够发展成为自行车的“亲戚”。当他们发现汽车真的能跑,一些人开始制造汽车,支使他们的最大好奇心是想知道哪辆车是跑得最快的。这种赛车的想法是很奇怪但又很自然的发展。我从不考虑任何赛车之类的事,但公众却总是拒绝不把汽车当作一个跑得快的玩具。因此,后来我们参与了赛车活动。但汽车工业却被这种最初的赛车行为拖了后腿,因为制造者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制造速度更快的车,而忽视了车子的质量。这是投机者们的勾当。
一群投机者们动起了歪脑筋——我一离开电力公司,底特律汽车公司继而就开发了我的汽车。我是总工程师,掌握着小量的存货。有3年多时间,我们继续制造着多少和我的第一辆车相同的车。我们的销量不佳,我几乎得不到任何的资助,用于制造质量好、可以大批销售给公众的汽车。他们只想照订单制造,从每一辆车上获得最高的价格,他们主要的心思看来完全放在了赚钱上。而除了机械方面我别无权力,所以我发现这家新公司不是实现我的理想的驿站,而只是赚钱的工具——但它也没有赚到多少钱。1902年3月,我又辞职了,这次我下定决心再也不受别人的指挥了。底特律汽车公司后来成为了卡迪拉克(Cadillac)公司,归兰德(Leland)所有,他后来加入了汽车业。
我租了公园街81号(81 Park Place)的一个店铺——一间一层的砖房里,继续着我的实验。我想了解商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肯定与我第一次经历中所得到的证明不同。从1902年到1903年福特汽车公司成立,这实际上是进行调查研究的一年。我在自己那间小砖房里努力研制四个汽缸的发动机。同时我试图弄明白商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是不是像我从第一次短短的经验中所感受到的那样,必然是自私自利的刮钱手段。从我描述过的第一辆汽车诞生,到福特公司的成立,其间我总共制造了25辆汽车,其中的19或20辆都是在底特律汽车公司制造的。
此时,汽车从只要能走就成发展到了显示速度的阶段。克利兰德的亚历山大·温顿(Alexander Winton of Cleveland)——温顿车的创造者,那时的全国赛车冠军——他愿意接受所有挑战者的挑战。我设计了一台比我以前制造的更紧凑的双缸密闭式发动机,把它装在底盘架上。我发现这能获得很快的速度,于是我便安排了一场与温顿的比赛。我们在底特律的格罗斯角赛道(Grosse Point Track)相会。结果,我赢了。这是我的首次赛车比赛。
商业最令人吃惊的地方是,商人们往往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金钱上,只把少量的注意力关注于服务,这在我看来是违反了自然程序的。自然程序中,金钱应该是作为劳动的结果而出现,不能放在劳动之前。商业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只要能赚钱就万事大吉,能否提供更好的生产方式无关紧要。也就是说,一件东西的价值并不是看它能为大众提供多少服务,而主要在于它能挣来多少钱,而对于顾客是否满意并不特别在意,把东西卖给他们就完事了。一个心怀不满的顾客并不被认为是一个信任被辜负了的人,而是被当作讨厌的人,或者是为第一次就该做好的工作榨取第二次金钱的来源。比如,汽车一旦被卖出之后汽车制造商便不再关心它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在乎它每跑一英里耗费多少汽油,它确实能提供怎样的服务也不重要。如果它损坏了,需要更换零部件,那么这只是购车人自己倒楣。所谓好的买卖就是以尽可能高的价钱把零件卖出去,这是基于这样的理论:他已经买车,他迫切地需要零件,因此只有乖乖地掏钱。
汽车业并不是建立在我所说的诚实的基础之上,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它并不比一般的行业更糟糕。也许还有人记得,那个时期很多公司是受金融界支撑和扶持的,在此之前只局限于铁路业的银行家进入工业。无论何时,我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可以把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他就应该会为此获得回报,利润和金钱自然会接踵而来;一个企业应该从小的地方做起,才能逐渐地发展壮大;没有积累就意味着浪费时间,意味着这个企业并不适合在这一行业中生存。不过在当时最受欢迎的计划是,争取最大额度的资本,然后售出全部股票和债券,在扣除股票和债券销售的费用、宣传费等各种开销后,剩下的钱便勉强成为企业的资金。“好”的企业,就是能使股票和债券以最高的价格大量出售的企业。对企业来说,重要的是股票和债券而不是工作。我始终不明白,这些企业怎么能够指望一方面获得最大的股利,同时又能以公平的价格出售产品。这真是天方夜谭!
那些自称金融家的人们说,他们的钱值6%或5%的利息。如果一个人向企业投资10万美元的话,这个投资者就有权要求得到一笔收益,因为如果他不把钱投入企业,而是存入银行或保险公司的话,也会得到某一固定的利息。因此,他们理应从企业的运作费用中获取适当的收益,作为这笔钱的利息。这种想法是很多商业服务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金钱并没有特别的价值,它如果不作为流通货币,本身是不值钱的。金钱惟一的好处,就是用于购买劳动工具或原料,因此,如果一个人认为他的钱能够获得6%或5%的利息,他应该把钱投到真正能够得到回报的地方,投入到工业中的钱不应该是利息,而应该成为生产的动力。所有的回报,都应该出现在生产之后,而并非生产之前。
商人们相信,通过注入资金,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如果第一笔资金没有带来收益,那就继续注入资金。这种再次注入资金的过程,简直就是把钱往水里扔。大多数需要重新注入资金的情况,都是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再投资的效果,只不过是把糟糕的管理者们的管理时间延长了而已。这种权宜之计是投机金融家们的伎俩,他们就像秃鹰一样,专门去吃变质的肥肉。如果那些地方经营良好的话,他们是不会往里面砸钱的。投机金融家们认为他们投出去的钱正在使用中,这其实是一种幻觉。他们并没有团结起来,而只是把钱拿出来浪费而已。我绝不想为一个尚未开始工作便想着赚钱的银行家或金融家工作。同时,在我看来,投机也绝非赚钱的正道。我希望能够证明,真正的工商业的惟一的基础就是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赚大钱。
当一桩买卖完成时,厂家和顾客的关系实际上并未结束,而恰恰是刚刚开始。以汽车为例,把汽车卖出去其实还只是某种介绍而已。如果汽车不能提供服务的话,对厂家来说它还不如没作出这介绍,因为他将收获最糟糕的广告——一个心怀不满的顾客。在汽车业的早期,有一种占主流的倾向认为把汽车卖出去就是真正的成就,而至于此后买主手里的车会怎么样并不重要。这是目光短浅的销售态度。就这点而言,我们后来对福特公司的销售原则进行的大讨论是正确的。汽车的价钱和质量无疑都有市场,并且潜力巨大,但我们所做的远不止于这些。顾客一旦买了我们的车,他就被赋予了继续使用那辆车的权利。因此,如果他的车出了任何问题,那都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这辆车修好,使其能够重新使用。
在福特汽车的成功案例之中,早期的服务措施是一个显著的因素。那个时期大多数昂贵的车都只有很糟糕的售后服务。如果你的车坏了的话,你只有依靠当地的修理工——这时你本来是有权利找厂家的。如果当地的修理工是一位有远见的人,手头存有不少零部件(虽然就很多车辆来说,零部件是无法互换的),那对车主来说就是幸运的。但如果修理工是个没有长远打算的人,对汽车的了解又太少,并且贪念极盛,想从每一辆到他这里来修理的汽车身上榨取一大笔钱,那么,即使很轻微的损坏也要等上几个星期,并且最终车主将被狠狠地敲掉一笔修理费。因此,有一段时间,修理工被视为汽车工业的最大威胁。甚至直到1910年和1911年,汽车车主仍被认定是应该被敲竹杠的有钱人。从一开始我们便直面这一问题并很好地解决了它,我们可不希望我们的销售被愚蠢、贪婪的人所妨碍。这是几年之前的事了。正是由于金融控制才使得服务中断,因为金融家指望的是马上得到美元。如果首先考虑的是挣到一定数量的钱,那么除非是靠偶然碰中特别好的运气,有多余的钱用来提供服务,使执行人员有提供服务的机会,否则的话,企业的未来就要被今天所挣的美元断送。
同时我还注意到,在很多从事工商业的人士当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认为他们的工作很辛苦。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能够不用工作,赋闲在家依靠退休金而生活。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场越早结束越好的战争。这是又一个让我无法理解的地方。生活并不是一场战斗,除非是与我们陷入垂头丧气的倾向作战。如果腐朽也是一种成功的话,那每个人只要忍受着无所事事的懒散就可以了。但假如发展才是成功的标准,一个人就必须每天清晨精神抖擞地醒来,并且一整天都保持活力。有许多大企业早已成为“魔鬼”的代名词,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运用一贯僵化的管理办法,把整个企业管理好。虽然那套管理办法在过去是辉煌的,但现在它能否继续辉煌,要看它能否与今天的变化保持一致,而不是奴隶般地听命和尾随着它的过去。生活,就我看来,不是停留于某地,而是永远都在旅行。即使是那些最深切地感到自己是“安居下来的人”也并非安定下来——他很可能是倒退回去了。万物皆流,其义如此。生活是流动着的,我们可以住在同一条街的同一个地方,但住在那里的永远不会是同一个人。
我注意到,人们出于认为生活是一场战斗、而这场战斗可能由于错误的举动而失败这样的幻觉,所以热爱着墨守成规。人们陷入半生不死的习惯泥沼。很少会有鞋匠用新的方式去补鞋,也很少有工匠愿意在他的行当里采纳新的方法。习惯导致某种陈规,每种打破这种陈规的举动都会被看作是自找麻烦。在进行一项有关工作方法的研究,以指导工人尽量减少无用的动作和疲劳时,反对最激烈的正是工人自己。虽然他们也怀疑这是一项想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价值的举动,但真正使他们恼火的是它将干涉他们久已养成的习惯。商人们正随他们的经营走下坡路,因为他们是那么喜欢陈旧的那一套,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这种人现在随处可见。他们不知道昨日已逝,头脑里装的仍然是陈年旧梦。这几乎可以作为一条公式写下来:当一个人开始想到他最终找到了他的方法时,他最好先认真检查一下自己,看他的大脑的一些部分是否还醒着。当一个人感到他被生活“钉住”时,“前进的车轮”定会在下一轮将他毫不留情地抛下。
同时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恐惧:怕成为傻瓜。因此很多人害怕被人认为是傻瓜。我想公众观念对那些需要它的人就像是一支强有力的监督力量。大多数人需要公众舆论的限制,也许这是真的。公众舆论能使一个人变得比他本身更好——即使不是在道德方面更好,至少在他的社会的某些方面会更好。为了正确的事情被当作傻瓜,并不是一件坏事。这种事情的最好之处在于这种傻瓜通常都能活得足够久,来证明他们自己并不是傻瓜,或者他们开创的事业能持续得足够久,证明他们并不愚蠢。
金钱的影响——从一项投资中谋取利润的压力——和它对工作和忽视、潦草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服务的轻视,这些我从很多方面都看到了。这看来是大多数问题的根本原因。这是低工资的原因——没有正确方向做指导是不可能实现高工资的。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自由地工作,但在现行制度下他们不可能自由地工作。在第一次工作经历中,我并不自由,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因为公司一切的计划都是为了赚钱,最后才考虑到工作。所有这一切中最奇怪的是,它坚持重要的是钱而不是工作。在任何人看来,把钱放在工作之前考虑并没有不合逻辑,虽然所有的人都承认利润来自于工作,但其愿望似乎是找到一条挣钱的捷径,但同时却忽视了一条显然的捷径,这就是工作。
再说说竞争。我发现竞争被很多人看作是一种威胁。他们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通过人为的垄断击败他的竞争者。这种观念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只有一定数量的人们愿意购买,因此必须把生意做在别人前面。有人也许会记得,后来很多汽车厂家联合制订了“塞尔登专利法”(Selden Patent),这些厂家可以用合法的手段,控制汽车的价格和产量。他们的想法和很多行业联合会的想法一样——这种荒唐的想法认为,可以以少量的工作获得更多的利润。这种计划,我相信是非常陈旧的。我那时候不明白,现在也仍然不明白人们把自己的工作干好了还不够,却浪费时间在你争我夺上。总有足够多的人们准备并急于购买,只要你能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并以适当的价格——这点既适用于人力服务也适用于商品。
在这段自我思考的时期,我远不是无所事事,我制造了一台四缸发动机和两辆大的赛车。我有很多时间来从事这些,因为我从未离开过我的事业。我不相信一个人能离开他的事业,他应该整天想着它并且整夜梦到它。在上班时间工作,早晨把工作拾起,晚上把工作放下,直到第二天早晨再想着它,这是一个好习惯。这么做可能是最好的。如果你准备一生都沿着别人指定的目标去做——比如成为一个好雇员,那么你可能会是一个负责而的出色的雇员,但却永远当不了一个主管或经理。一个劳动者必须享受劳动时间以外的生活,否则他会疲惫不堪。如果他只想做一个体力劳动者,当收工的哨声响起的时候,他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工作;但如果他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去完成更多的事情,那么哨声便是他开始继续思考的信号——思考过去的一天的工作,思考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具有最强的工作能力和思考能力的人是注定要成功的。我并没有骗人说,那些总是工作的人,那些从不离开自己事业的人,那些绝对想赶在前面的人并且也因此走到前面的人,是不是一定会比那些只有在上班时间才动手动脑的人幸福,因为对这点我也不知道。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对此做出自己的回答,毕竟10马力的发动机,不可能像20马力的发动机那样负荷得更多。那种下班了便不加思考的人,自然不会拥有更多的马力,当然他也没有任何理由抱怨。如果他满足于他所负载的重量,那是他的事情,但他一定不能抱怨别人增加了马力后比他负荷得更多。闲散和工作带来的是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想要闲散,并得到了闲散,那么他就没理由抱怨了。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悠闲的生活,又拥有劳动的所得。
尽管以后的每一年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我发现没有必要改变自己当年对工商业的认识,这些认识具体如下:
1. 金钱若被置于工作之前,便等于扼杀了工作,并破坏了服务的基础。
2. 一个企业如果首先考虑的是赚钱而不是工作,那么失败的恐惧必将降临在它的头上。这种恐惧阻碍了企业的每一条发展之路,它使人害怕竞争,拒绝自身的革新,害怕做出任何的改变。
3. 任何把服务放在首位的人,其出路都是很清楚的——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