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靠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我们也就达到了进一步研究的第一个出发点。但是现在必须稍稍发挥一下这个定义,以便给予它以更大的精确性。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我们有权利把这些条件看成是人所特有的天赋而与所有其他有机存在物不相干的吗?符号系统〔symbolism〕难道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追溯其更深的根源,并且具有更宽的适用域的原理吗?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那么看来我们就必须承认,对于在人类文化哲学中历来占据注意力中心的许多基本问题,我们都是全然无知的。语言、艺术、宗教的起源问题就成为不可解答的,而人类文化则成了一种给定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是孤立的,因此也就是不可理解的。
科学家们总是拒绝接受这样的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一直以极大的努力把符号系统这个事实与其他熟知的和更基本的事实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一直被认作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但不幸的是人们极少带着真正的开放精神来探讨它。从一开始起,它就被另一些属于完全不同的讨论领域的问题搅混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变成了形而上学的争论,而不是给予我们对现象本身的不偏不倚的描述和分析。它成了引起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唯灵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争论的原因。对于所有这些体系来说,符号系统的问题成了一个决定性的问题,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未来形态似乎都以此为转移了。
对于问题的这个方面,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因为我们对自己提出的是更为谦虚和具体的任务。我们将努力以更精确的方式来描述人的符号化态度,以便通过对比把它与存在于整个动物界的另一种样态的符号化行为区别开来。毫无疑问,动物并不总是在直接的方式下对刺激物作出反应的,它们具有间接反应的能力。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所谓替代刺激物的极为丰富的经验证据。而沃尔夫(J.B.Wolfe)所作的一个有趣的实验则证明了“象征性奖赏”对类人猿的有效性。动物能学会对用来代替食物奖赏的各种象征物作出反应,就像对食物本身作出反应一样。
 在沃尔夫看来,各种各样的以及长时期的训练实验的结果已经说明,符号化过程存在于类人猿的行为之中。耶克斯(Robert M.Yerkes)在其最近的著作中描述了这些训练实验,从中得出一条重要的普遍性结论:
在沃尔夫看来,各种各样的以及长时期的训练实验的结果已经说明,符号化过程存在于类人猿的行为之中。耶克斯(Robert M.Yerkes)在其最近的著作中描述了这些训练实验,从中得出一条重要的普遍性结论:
“〔类人猿等的〕符号化过程确实是相当稀少并且很难观察到的。人们完全可以持久地怀疑它们的存在,但是我猜想,它们不久即会被看成是人的符号化过程之先例。这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达到了最令人兴奋的发展阶段,而这时,重要的发现似乎就将来临了。”

对这个问题的未来发展作任何预言都是为时过早的。这个领域必须始终为今后的研究敞开大门。但另一方面,对经验事实的解释总是依赖于某些确定的基本概念的,这些基本概念是必须在经验材料能取得其结果以前就被澄清的。现代心理学和心理生物学就考虑到了这一事实。在我看来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看来,不是哲学家而是经验的观察研究者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他们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归根到底不仅是经验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逻辑的问题。雷弗兹(Georg Révész)近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就是要说明,所谓动物语言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可能在动物心理学的纯事实基础上得到解决。每一个以公正和批判的态度考察过各种心理学文献和理论的人,最终都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问题不可能依靠只是归结为动物的通讯方式和动物靠教授和训练所获得的某些技能就可以弄清楚的。因为所有这些技能都可以有各种极其互相矛盾的解释。因此,归根到底必须找出一个正确的逻辑出发点——一个可以引导我们对经验事实作出符合本来面貌的可靠解释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言语的定义。
 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先给出一个现成的言语定义,而是从尝试性的探讨着手。言语并不是一个单纯而统一的现象,它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所组成的,而这些成分无论在生物学上还是在分类学上都不是处在同一水平面上的。我们必须努力去发现这些成分的秩序和相互关系,就仿佛必须去区分言语的不同层次。最初和最基本的层次显然是情感语言。人的全部话语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属于这一层。但是,有一种言语形式向我们揭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在这里,语词绝不仅仅只是感叹词,并不只是感情的无意识表露,而是一个有着一定的句法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句子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先给出一个现成的言语定义,而是从尝试性的探讨着手。言语并不是一个单纯而统一的现象,它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所组成的,而这些成分无论在生物学上还是在分类学上都不是处在同一水平面上的。我们必须努力去发现这些成分的秩序和相互关系,就仿佛必须去区分言语的不同层次。最初和最基本的层次显然是情感语言。人的全部话语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属于这一层。但是,有一种言语形式向我们揭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在这里,语词绝不仅仅只是感叹词,并不只是感情的无意识表露,而是一个有着一定的句法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句子的一部分。
 确实,即使在高度发展了的理论语言中,与上述那种最初成分的联系也并没有被完全割断。几乎没有一个句子——数学的纯形式的句子或许例外——不带有某种情感或情绪的色彩。
确实,即使在高度发展了的理论语言中,与上述那种最初成分的联系也并没有被完全割断。几乎没有一个句子——数学的纯形式的句子或许例外——不带有某种情感或情绪的色彩。
 在动物世界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类似或相似的情感语言。就黑猩猩而言,苛伊勒(Molfgang Koehler)曾指出它们靠手势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表达程度。用这种方式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表达愤怒、恐惧、绝望、悲伤、恳求、愿望、玩笑和喜悦等情感。然而尽管如此,有一个在一切人类语言中最为突出和不可缺少的成分则是黑猩猩所不具备的,这就是:它们的这些表达根本不具有一个客观的指称或意义。苛伊勒说:
在动物世界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类似或相似的情感语言。就黑猩猩而言,苛伊勒(Molfgang Koehler)曾指出它们靠手势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表达程度。用这种方式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表达愤怒、恐惧、绝望、悲伤、恳求、愿望、玩笑和喜悦等情感。然而尽管如此,有一个在一切人类语言中最为突出和不可缺少的成分则是黑猩猩所不具备的,这就是:它们的这些表达根本不具有一个客观的指称或意义。苛伊勒说:
“可以肯定地证明,猿的语音学的全部音阶是完全‘主观的’,它们只能表达情感,而绝不能指示或描述任何对象。但是它们具有这么多人类语言中所共有的语音成分,以致不能把它们无法说出字音清晰的言语的原因归结为第二性的(舌唇的)限制。它们面部和身体的各种姿势也像它们在声音上的表达一样,从不指示或‘描述’对象。”

这就是我们全部问题的关键: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之间的区别,就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真正分界线。一切有关动物语言的理论和观察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基本区别的话,那就是都没有抓住要害。
 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文献中,似乎还没有一篇能确实地证明,任何动物曾跨出过从主观语言到客观语言、从情感语言到命题语言这个决定性的一步。苛伊勒断然认为,言语肯定是超出类人猿的能力的。他认为,缺乏这种无价技术的帮助,以及在所谓想像力这种极为重要的思想成分方面受到的巨大限制,就是构成动物之所以从未达到文化发展之最小开端的原因所在。
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文献中,似乎还没有一篇能确实地证明,任何动物曾跨出过从主观语言到客观语言、从情感语言到命题语言这个决定性的一步。苛伊勒断然认为,言语肯定是超出类人猿的能力的。他认为,缺乏这种无价技术的帮助,以及在所谓想像力这种极为重要的思想成分方面受到的巨大限制,就是构成动物之所以从未达到文化发展之最小开端的原因所在。
 雷弗兹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断言,言语是人类学的概念,因此应当从动物心理学的研究中整个地排除出去。如果我们从一个清晰精确的言语定义出发,那么我们在动物那里所能看到的所有其他的话语形式就都自动地排除掉了。
雷弗兹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断言,言语是人类学的概念,因此应当从动物心理学的研究中整个地排除出去。如果我们从一个清晰精确的言语定义出发,那么我们在动物那里所能看到的所有其他的话语形式就都自动地排除掉了。
 一直以特别的兴趣研究这个问题的耶克斯,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深信,即使就语言和符号系统而论,在人与类人猿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写道:“这暗示着,我们可能偶然地发现了符号化过程进展中一个较早的种系发生阶段。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除了符号化过程以外,其他各种类型的信号过程(sign process)在黑猩猩身上都是常常发生并且有效地起作用的。”
一直以特别的兴趣研究这个问题的耶克斯,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深信,即使就语言和符号系统而论,在人与类人猿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写道:“这暗示着,我们可能偶然地发现了符号化过程进展中一个较早的种系发生阶段。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除了符号化过程以外,其他各种类型的信号过程(sign process)在黑猩猩身上都是常常发生并且有效地起作用的。”
 然而所有这些仍然肯定是前语言的。即使按照耶克斯的看法,〔黑猩猩的〕所有这些功能性表达,与人的认识过程相比也是极其初步、极其简单而用处有限的。
然而所有这些仍然肯定是前语言的。即使按照耶克斯的看法,〔黑猩猩的〕所有这些功能性表达,与人的认识过程相比也是极其初步、极其简单而用处有限的。
 在这里,发生学的问题不应与分析的及现象学的问题相混淆。对人类言语的逻辑分析总是把我们引向一个在动物世界中根本没有对应物的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成分。一般进化论决不妨碍承认这一事实。即使在有机自然现象的领域中,我们也已经知道,进化并不排斥某种类型的原始创造。必须承认突变和突生进化的事实。现代生物学不再根据早期的达尔文主义来谈论进化了,也不再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进化的原因了。我们可以欣然承认,类人猿在某种符号化过程的发展中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我们仍然要说,它们并没有达到人类世界的门槛,而是仿佛进入了一条死胡同。
在这里,发生学的问题不应与分析的及现象学的问题相混淆。对人类言语的逻辑分析总是把我们引向一个在动物世界中根本没有对应物的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成分。一般进化论决不妨碍承认这一事实。即使在有机自然现象的领域中,我们也已经知道,进化并不排斥某种类型的原始创造。必须承认突变和突生进化的事实。现代生物学不再根据早期的达尔文主义来谈论进化了,也不再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进化的原因了。我们可以欣然承认,类人猿在某种符号化过程的发展中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我们仍然要说,它们并没有达到人类世界的门槛,而是仿佛进入了一条死胡同。
为了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仔细地在信号(signs)和符号(symbols)之间作出区别。在动物的行为中可以看到相当复杂的信号和信号系统,这似乎是确定不移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些动物尤其是驯化动物,对于信号是极其敏感的。
 一条狗会对其主人的行为的最轻微变化作出反应,甚至能区分人的面部表情或人的声音的抑扬顿挫。
一条狗会对其主人的行为的最轻微变化作出反应,甚至能区分人的面部表情或人的声音的抑扬顿挫。
 但是,这些现象远远不是对符号和人类言语的理解。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仅仅证明了,动物可以被训练成不仅对直接刺激作出反应,而且能对各种间接刺激即替代刺激作出反应。例如,一只铃可以成为“午餐的信号”,而一个动物可以被训练成当这只铃没有出现时就不碰食物。但是我们由此所知道的仅仅是,实验者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地改变了动物的进食环境,他靠着有意引入新的因素而使这种进食环境复杂化了。所有那些通常被称为条件反射的现象,不仅是远离人类符号化思想的基本特征,而且甚至还与后者恰恰相反。符号,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而言,是不可能被还原为单纯的信号的。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operators);而符号则是“指称者”(designators)。
但是,这些现象远远不是对符号和人类言语的理解。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仅仅证明了,动物可以被训练成不仅对直接刺激作出反应,而且能对各种间接刺激即替代刺激作出反应。例如,一只铃可以成为“午餐的信号”,而一个动物可以被训练成当这只铃没有出现时就不碰食物。但是我们由此所知道的仅仅是,实验者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地改变了动物的进食环境,他靠着有意引入新的因素而使这种进食环境复杂化了。所有那些通常被称为条件反射的现象,不仅是远离人类符号化思想的基本特征,而且甚至还与后者恰恰相反。符号,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而言,是不可能被还原为单纯的信号的。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operators);而符号则是“指称者”(designators)。
 信号即使在被这样理解和运用时,也仍然有着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则仅有功能性的价值。
信号即使在被这样理解和运用时,也仍然有着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则仅有功能性的价值。
牢牢记住上述这种区别,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了。所谓动物智慧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学哲学的最大难题之一,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人们在思考和观察上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是,“智慧”(intelligence)这个词本身的模糊性总是妨碍了对这个问题的清晰解决。我们怎能希望解答一个其含义连我们都还不理解的问题呢?形而上学家和科学家、博物学家和神学家们都在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意义上使用智慧一词。一些心理学家和心理生物学家们断然拒绝谈论什么动物的智慧,在一切动物行为中他们所看见的仅仅是某种无意识动作而已。这种论点早就有笛卡儿的权威作为后盾了,而在现代心理学中又一再得到重申。桑戴克
 (E.L.Thorndike)在其关于论动物智慧的著作中说道:“动物不会认为一物像另一物,它也不会像人们常常所说的那样把一物错当成另一物;它根本就不思考什么,而只认定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动物对一个特定的、绝对明确的和逼真的感官印象作出反应,而且对一个不同于前者的感官印象作出相似的反应,这就证明它运用了一种靠相似性所作的联想;这种看法乃是神话。”
(E.L.Thorndike)在其关于论动物智慧的著作中说道:“动物不会认为一物像另一物,它也不会像人们常常所说的那样把一物错当成另一物;它根本就不思考什么,而只认定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动物对一个特定的、绝对明确的和逼真的感官印象作出反应,而且对一个不同于前者的感官印象作出相似的反应,这就证明它运用了一种靠相似性所作的联想;这种看法乃是神话。”
 以后的更精确的观察导致了不同的结论。就高级动物而言,它们显然能够解决相当困难的问题,而且这些解决并不是以单纯的机械方式达到,而是反复试验的结果。正如苛伊勒所指出的,在单纯碰运气的解决和名符其实的真正解决之间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区别,以致这两者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至少高等动物的某些反应活动并非只是碰运气的结果,而是由见识所引导,这看来是不可否认的。
以后的更精确的观察导致了不同的结论。就高级动物而言,它们显然能够解决相当困难的问题,而且这些解决并不是以单纯的机械方式达到,而是反复试验的结果。正如苛伊勒所指出的,在单纯碰运气的解决和名符其实的真正解决之间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区别,以致这两者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至少高等动物的某些反应活动并非只是碰运气的结果,而是由见识所引导,这看来是不可否认的。
 如果我们把智慧理解成对直接环境的适应,或是对环境作出的适应性改变,那么我们就确实必须承认,动物具有相当发达的智慧。而且还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的动物反应都是由一个直接刺激物的出现所支配的。动物在其反应活动中是具有各种迂回能力的。它不仅能学会使用工具,甚至还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发明工具。一些心理生物学家由此毫不犹豫地谈论起动物具有的创造性或构造性想像力。
如果我们把智慧理解成对直接环境的适应,或是对环境作出的适应性改变,那么我们就确实必须承认,动物具有相当发达的智慧。而且还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的动物反应都是由一个直接刺激物的出现所支配的。动物在其反应活动中是具有各种迂回能力的。它不仅能学会使用工具,甚至还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发明工具。一些心理生物学家由此毫不犹豫地谈论起动物具有的创造性或构造性想像力。
 但是,不管是这种智慧还是这种想像力,它们都不是人所特有的那种类型。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动物具有实践的想像力和智慧,而只有人才发展了一种新的形式:符号化的想像力和智慧。
但是,不管是这种智慧还是这种想像力,它们都不是人所特有的那种类型。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动物具有实践的想像力和智慧,而只有人才发展了一种新的形式:符号化的想像力和智慧。
此外,在个人心灵的心理发展中,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从单纯实践态度到符号化态度的转化,也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在这里,这一步乃是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进程之最终结果,用通常的心理学的观察方法是不容易识别这个复杂进程的个别阶段的。然而,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对这种转变的一般特性和最高重要性进行充分的了解。可以说,自然本身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实验,从而给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启示:我们有劳拉·布里奇曼〔Laura Bridgman〕和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典型事例——两个盲、聋、哑儿童以特殊的方法学会说话的事例。
 虽然这两个事例是极其著名的,并且在心理学文献中常常被论及,
虽然这两个事例是极其著名的,并且在心理学文献中常常被论及,
 但我仍然必须再次使读者回想起它们来,因为这两个事例或许是对我们现在谈到的那个普遍问题的最好说明。海伦·凯勒的教师沙莉文小姐记下了这个孩子真正开始理解人类语言的意义和作用的确切日期。下面让我引用她的话:
但我仍然必须再次使读者回想起它们来,因为这两个事例或许是对我们现在谈到的那个普遍问题的最好说明。海伦·凯勒的教师沙莉文小姐记下了这个孩子真正开始理解人类语言的意义和作用的确切日期。下面让我引用她的话:
“今天早晨我必须给你写几句,因为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海伦在她的教育中迈出了第二大步——她已经知道,每一件东西都有一个名称,而且手语字母就是她想要知道的每一件东西的秘诀。
“……今天早晨,当她正在梳洗时,她想要知道‘水’的名称。当她想要知道什么东西的名称时,她就指着它并且拍拍我的手。我拼了‘w—a—t—e—r’(水),直到早饭以后我才把它当回事儿。……我们走出去到了井房,我让海伦拿杯子接在水管喷口下,然后由我来压水。当凉水喷出来注满杯子时,我在海伦空着的那只手上拼写了‘w—a—t—e—r’。这个词与凉水涌到她手上的感觉是如此紧密相联,看来使她大吃一惊。她失手跌落了杯子,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脸上开始显出一种新的生气。她拼了好几次‘water’。然后她跌坐在地上问地板的名称,又指着问水泵和井房棚架,突然她转过脸来问我的名字,我拼了‘teacher’(教师)一词。在回家时她一路上都处在高度的兴奋状态中,并且学着她碰到的每样东西的名称,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她的词汇量增加到三十个。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她像个快乐的小仙女,轻快地一会儿走到这件东西旁,一会儿走到那件东西旁,问着每件东西的名称,并且高兴得连连吻我。……现在,每件东西都必需有一个名称了。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她都热切地问着她在家里还没学到的东西的名称。她焦急地教她的朋友们拼写,并且热心地把字母教给她所碰到的每一个人。一当她有了语词来取代她原先使用的信号和哑语手势,她马上就丢弃了后者,而新语词的获得则给她以新生般的喜悦。我们都注意到,她的脸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富于表情了。”

从信号和手势的运用到语词亦即符号的运用这决定性的一步过渡,在这里描述得再清楚不过了。儿童们在这一刻的真正发现是什么呢?海伦·凯勒在此以前已经学会了把某物或某一事件与手语字母的某一信号联结起来。在这些事物与某些触感之间的一种固定联结是在此以前就被建立起来了的。但是一系列这样的联结,即使被重复和扩大,仍然不是对人类言语及其意义的理解。要达到这样一种理解,儿童们就必须作出一个新的和远为重要的发现,必须能理解到:凡物都有一个名称——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含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在海伦·凯勒那里,这个发现是突如其来的。她是一个七岁的女孩,除了某些感觉器官的缺陷以外,有着极为良好的身体状况和高度发达的智力。但是由于疏忽了对她的教育,她在智力上一直极为迟钝。后来,突然出现了决定性的发展,就像产生了智力的进化——这个孩子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了。她懂得了,词的用途不仅是作为机械式的信号或暗号,而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工具。一个新的天地展现在眼前,从今以后这个孩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漫步在这无比宽广而自由的土地上了。
这同样也可以在劳拉·布里奇曼的例子中得到证明。虽然她的故事较不引人注意。在脑力以及智力的发展两方面,她都大大地低于海伦·凯勒。她的生活和教育没有我们在海伦·凯勒那里看到的那种戏剧性成分。然而在她们两人那里,存在着同样的典型因素。当劳拉·布里奇曼学会了手势字母的用处以后,她也突然地达到了这一点,即她开始理解了人类言语的符号系统。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两个例子的惊人相似性。劳拉·布里奇曼的第一个教师德鲁小姐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懂得了手势字母用处后的第一次进餐的情形。她所摸到的每件东西都必须有一个名称;我不得不招呼某个人来帮我伺候别的孩子进餐,因为她使我忙于拼写新词。”

符号系统的原理,由于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个秘诀,进一步的发展就有了保证。显而易见,这样的发展并不会由于任何感性材料的缺乏而被阻碍或成为不可能。海伦·凯勒达到了极其高度的智力发展和理智文化这一例子,就清楚而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证明,人这种存在物在建造人的世界时是不依赖于他的感性材料的性质的。如果感觉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每个观念只不过是一个原始感官印象的暗淡摹本,那么聋哑盲儿童的状况就一定是绝望的了,因为他们不具备人类知识的这个源泉,仿佛就像被从现实世界中放逐了出去一般。但是如果我们研读了海伦·凯勒的自传,那么马上就会意识到这是不真实的,并且我们还同时知道它为什么是不真实的。人类文化并不是从它构成的质料中,而是从它的形式,它的建筑结构中获得它的特有品性及其理智和道德价值的。而且这种形式可以用任何感性材料来表达。有声语言(Vocal language)比摸触语言(tactile language)有着更大的技能上的进步,但是后者在技能上的这种缺陷并没有抹杀它的基本效用。符号思维和符号表达的自由发展,并不会由于摸触记号(tactile signs)取代了有声记号(vocal signs)而受到阻碍。如果这个孩子成功地领会了人类语言的意义,那么在什么样的特殊表达材料中这个意义更容易被理解,那是无关紧要的。正如海伦·凯勒的事例所证明的,人能以最贫乏最稀少的材料建造他的符号世界。至关重要的事情不在于个别的砖瓦而在于作为建筑形式的一般功能。在言语的领域中,正是言语的一般符号功能赋予物质的记号以生气并“使它们讲起话来”。没有这个赋予生气的原则,人类世界就一定会是又聋又哑。有了这个原则,甚至聋、哑、盲儿童的世界也变得比最高度发达的动物世界还要无可比拟地宽广和丰富。
由于每物都有一个名称,普遍适用性就是人类符号系统的最大特点之一。但是,它并非是惟一的特点。与这个特点相伴随相补充并且与之有必然关联,符号还有另一个显著特点:一个符号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极其多变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甚至在一门语言的范围内,某种思想或观念也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词来表达。一个信号或暗号总是以一种确定而惟一的方式与它所指称的事物相联系的。任一具体的和个别的信号都是指称一个确定的个别事物的。在巴甫洛夫的实验中,那些狗能轻易地被训练成只有在给定某些特定记号时才敢吃食;它们只有在听到一个可以由实验者任意选定的特殊声音时才会进食。但是,这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解释的那样就表明它相似于人的符号系统;恰恰相反,它与符号系统乃是相对立的。真正的人类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律性上,而是体现在它的多面性上。它不是僵硬呆板而是灵活多变的。诚然,对这种易变性的充分认识看来是在人类智慧文化发展很久以后才达到的。原始人的智力就几乎从未达到过这种认识。在那里,符号还被看成是事物的一种性质,就像事物的其他物理性质一样。在神话思想中,神的名字乃是神的本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能用神的真正名字来称呼它,那么符咒与祈祷就都是无效的了。这也同样适用于符号化的活动。宗教的典礼、献祭,如果要有效力的话,总是必须以同一不变的方式和同样的程序来实行。
 儿童们在第一次知道并不是一物的每一名称都是一个“专有名称”,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语言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名称时,常常会被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往往认为:一个事物“就是”它所被称呼的。但这仅仅是最初的一步。每个正常儿童都会很快懂得,可以用不同的符号去表达同样的愿望和思想。而这种多样性和易变性,显然是动物世界所没有的。
儿童们在第一次知道并不是一物的每一名称都是一个“专有名称”,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语言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名称时,常常会被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往往认为:一个事物“就是”它所被称呼的。但这仅仅是最初的一步。每个正常儿童都会很快懂得,可以用不同的符号去表达同样的愿望和思想。而这种多样性和易变性,显然是动物世界所没有的。
 早在劳拉·布里奇曼学会说话以前,她就已逐步形成了一套非常古怪的表达方式,形成了她自己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是由音节分明的语音所构成,而是由各种可称为“情感叫嚷”(emotional noise)的叫声所构成的。她在某些人面前习惯于吐出这些声音。这样,这种声音就变得完全个别化了,对于周围的每一个人她都用一种特殊的叫声来致意。利伯博士写道:“每当她不期而遇地碰到一个熟人时,我发现她在开始说话以前总是反复地对那人嚷着一个词,这是表示高兴地打招呼。”
早在劳拉·布里奇曼学会说话以前,她就已逐步形成了一套非常古怪的表达方式,形成了她自己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是由音节分明的语音所构成,而是由各种可称为“情感叫嚷”(emotional noise)的叫声所构成的。她在某些人面前习惯于吐出这些声音。这样,这种声音就变得完全个别化了,对于周围的每一个人她都用一种特殊的叫声来致意。利伯博士写道:“每当她不期而遇地碰到一个熟人时,我发现她在开始说话以前总是反复地对那人嚷着一个词,这是表示高兴地打招呼。”
 但是当这个孩子利用手势语懂得了人类语言的意义时,情况就变了。这时这种声音真正成了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别的人,而是只要环境需要就能改变的。例如有一天劳拉·布里奇曼收到了她以前的教师德鲁小姐的一封信,这时德鲁小姐因为结了婚已经成为莫顿夫人了。信中邀请劳拉·布里奇曼去做客,这使她非常高兴。但是她挑剔地找德鲁小姐的岔子,因为后者在信上的签名是用她出嫁前的姓而没有用她丈夫的姓。她甚至还说,现在她必须为她这位教师创造另一种叫声:因为对德鲁的叫声一定是不同于对莫顿的叫声的。
但是当这个孩子利用手势语懂得了人类语言的意义时,情况就变了。这时这种声音真正成了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别的人,而是只要环境需要就能改变的。例如有一天劳拉·布里奇曼收到了她以前的教师德鲁小姐的一封信,这时德鲁小姐因为结了婚已经成为莫顿夫人了。信中邀请劳拉·布里奇曼去做客,这使她非常高兴。但是她挑剔地找德鲁小姐的岔子,因为后者在信上的签名是用她出嫁前的姓而没有用她丈夫的姓。她甚至还说,现在她必须为她这位教师创造另一种叫声:因为对德鲁的叫声一定是不同于对莫顿的叫声的。
 十分清楚,原先那种“叫声”在这里已经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和十分有趣的意义上的变化:它们不再是与某一特殊的具体场景联在一起的特殊音调了,而是成了抽象名词。因为被这个儿童想像出来的新名字不是指称一个新的个人,而是指称在一个新的关系中的同一个人。
十分清楚,原先那种“叫声”在这里已经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和十分有趣的意义上的变化:它们不再是与某一特殊的具体场景联在一起的特殊音调了,而是成了抽象名词。因为被这个儿童想像出来的新名字不是指称一个新的个人,而是指称在一个新的关系中的同一个人。
我们这个一般问题的另一重要方面现在显现出来了——关系的思想依赖于符号的思想。没有一套相当复杂的符号的体系,关系的思想就根本不可能出现,更不必谈其充分的发展。把对关系的单纯意识看成是预先假定了一种理智的活动、一种逻辑的或抽象的思想活动,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样的一种意识,甚至在最初的知觉活动中就已是必要的了。感觉主义理论惯于把知觉看成是简单感觉材料的精细加工成果。持这种信念的思想家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感觉本身决不仅仅只是许多孤立印象的集合和堆积。现代格式塔心理学已经修正了这种观点并且证明,即使最简单的知觉过程也已经暗含了基本的结构要素以及某种样式或形相(configurations)。这个原理既适用于人类世界,也适用于动物世界。甚至在相当低级的动物生命阶段,这些结构要素——尤其是空间的和视力的结构——也已经被实验所证实。
 因此,单纯的关系意识不能被看成是人类意识的特性。然而,我们在人那里确实发现了一种在动物世界所没有的特殊类型的关系思维。在人那里已经发展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的能力——即在其抽象意义上考虑那些关系的能力。要把握这种〔抽象〕意义,人不能再依赖于具体的感觉材料,即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及动觉的材料,而要考虑这些关系“本身”——如柏拉图所说,就其本身(
因此,单纯的关系意识不能被看成是人类意识的特性。然而,我们在人那里确实发现了一种在动物世界所没有的特殊类型的关系思维。在人那里已经发展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的能力——即在其抽象意义上考虑那些关系的能力。要把握这种〔抽象〕意义,人不能再依赖于具体的感觉材料,即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及动觉的材料,而要考虑这些关系“本身”——如柏拉图所说,就其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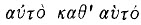 )来考察它。几何学就是人类理智生活中这种转折点的典型例子。即使在初等几何学中,我们也已不限于对具体的个别事物的理解了,在那里我们并不关心物理事物或知觉对象,我们是在研究普遍的空间关系,我们有一套适当的符号系统来表示这些关系。没有人类语言这一准备性的步骤,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在所有那些培养动物抽象化或普遍化过程的实验中,这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明显。苛伊勒成功地证明了,黑猩猩具有对两个或更多的物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一个特殊的物体)作出反应的能力——在两个装有食物的盒子面前,黑猩猩由于先前的一般训练总是挑选较大的盒子——即使被选中的这个盒子在先前的实验中可能是作为一对中较小的一个而被抛弃的。与此相似,它们也具有不是对某一特殊的盒子而是对较近的东西,或较亮的、较蓝的东西作出反应的能力,这都是实验所证实了的。苛伊勒的研究成果被更大的一些实验所确认和引申。这表明,高级动物具有历来所谓的“对知觉成分加以分离”的能力,它们具有从实验场景中挑选出特殊的知觉特性并进而对之作出反应的潜能。就这种意义而言,动物是能够从大小和形状中抽象出颜色,或从大小和颜色中抽象出形状来的。在柯茨小姐(Kohts)所作的一些实验中,一只黑猩猩能够从一大堆在视觉性质上极端不同的东西中挑选出那些有某一共同性质的东西来;例如它能够挑出所有那些具有某一特定颜色的东西并把它们放在一只箱子中。这些例子似乎证明了,高级动物具有休谟在其知识论中称之为能进行“理性的区分”这样一种过程的能力。
)来考察它。几何学就是人类理智生活中这种转折点的典型例子。即使在初等几何学中,我们也已不限于对具体的个别事物的理解了,在那里我们并不关心物理事物或知觉对象,我们是在研究普遍的空间关系,我们有一套适当的符号系统来表示这些关系。没有人类语言这一准备性的步骤,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在所有那些培养动物抽象化或普遍化过程的实验中,这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明显。苛伊勒成功地证明了,黑猩猩具有对两个或更多的物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一个特殊的物体)作出反应的能力——在两个装有食物的盒子面前,黑猩猩由于先前的一般训练总是挑选较大的盒子——即使被选中的这个盒子在先前的实验中可能是作为一对中较小的一个而被抛弃的。与此相似,它们也具有不是对某一特殊的盒子而是对较近的东西,或较亮的、较蓝的东西作出反应的能力,这都是实验所证实了的。苛伊勒的研究成果被更大的一些实验所确认和引申。这表明,高级动物具有历来所谓的“对知觉成分加以分离”的能力,它们具有从实验场景中挑选出特殊的知觉特性并进而对之作出反应的潜能。就这种意义而言,动物是能够从大小和形状中抽象出颜色,或从大小和颜色中抽象出形状来的。在柯茨小姐(Kohts)所作的一些实验中,一只黑猩猩能够从一大堆在视觉性质上极端不同的东西中挑选出那些有某一共同性质的东西来;例如它能够挑出所有那些具有某一特定颜色的东西并把它们放在一只箱子中。这些例子似乎证明了,高级动物具有休谟在其知识论中称之为能进行“理性的区分”这样一种过程的能力。
 但是所有从事这些研究的试验者也都强调这种过程的罕见性、粗糙性和不完善性。动物即使在学会了挑选出某一特殊的特质并且竭力想得到它时,也仍然会犯各种形式的稀奇古怪的错误。
但是所有从事这些研究的试验者也都强调这种过程的罕见性、粗糙性和不完善性。动物即使在学会了挑选出某一特殊的特质并且竭力想得到它时,也仍然会犯各种形式的稀奇古怪的错误。
 即使在动物世界中有某种理性区分(distinctio rationis)的痕迹的话,那么也仿佛已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了,它们不可能得到发展,因为它们不具有人类言语和符号的体系这种无价的和确实不可缺少的帮助。
即使在动物世界中有某种理性区分(distinctio rationis)的痕迹的话,那么也仿佛已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了,它们不可能得到发展,因为它们不具有人类言语和符号的体系这种无价的和确实不可缺少的帮助。
第一个认清这个问题的思想家是赫尔德
 。作为一个研究人性的哲学家,赫尔德希望完全用“人的”话语来提出问题。为了反对语言有超自然的或神赐的起源这种形而上学或神学的论点,赫尔德以对问题本身作批判的修正为出发点:言语不是一件物体,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寻出自然的或超自然原因的物理事物。它是一种过程,是人类心灵的一种一般功能。从心理学上讲,我们不可能用十八世纪的一切心理学派所用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过程。在赫尔德看来,言语并不是理性的人为创造物,也不应当被解释为是一种特殊的联结机制。赫尔德在试图阐明语言的本性时,把他的全部重点都放在他所谓的“反思”上。反思或反省的思想是人的这样一种能力,即人能够从混沌未分、漂浮不定的整个感性现象之流中择取出某些固定的成分,从而把它们分离出来并着重进行研究。
。作为一个研究人性的哲学家,赫尔德希望完全用“人的”话语来提出问题。为了反对语言有超自然的或神赐的起源这种形而上学或神学的论点,赫尔德以对问题本身作批判的修正为出发点:言语不是一件物体,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寻出自然的或超自然原因的物理事物。它是一种过程,是人类心灵的一种一般功能。从心理学上讲,我们不可能用十八世纪的一切心理学派所用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过程。在赫尔德看来,言语并不是理性的人为创造物,也不应当被解释为是一种特殊的联结机制。赫尔德在试图阐明语言的本性时,把他的全部重点都放在他所谓的“反思”上。反思或反省的思想是人的这样一种能力,即人能够从混沌未分、漂浮不定的整个感性现象之流中择取出某些固定的成分,从而把它们分离出来并着重进行研究。
“当人的心智力量行使得如此自如,以致他仿佛能从他所有通过感官获得的感觉洪流的整个海洋中分离出一股波浪,而且能够暂时止住这股波浪而仔细注视它,并且还意识到这种注视——这时人就显示出了反思。当他从涌向他诸感官的全部游离恍惚的意象梦境中,能够集中于醒着的一瞬,自动地细想一个意象,清晰地并更加宁静地观察它,并且抽象出能够向他指明对象是这个而不是另一个的特征时,这时人就显示出了反思。由此,当人不仅能逼真地或清晰地察觉所有的性质,而且当他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性质中的一个或几个性质是与众不同的性质时,这时人才显示出了反思。……那么靠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这种清楚的认识发生呢?通过人必须加以抽象的一个特征,而这个特征,作为意识的一个分子,清晰地呈现出自身。好了,让我们大声说:我们找到了!意识的这个最初字母(initial character)就是灵魂的语言。人的语言由此而创生。”

这里更多地表现为诗意的生动描写,而不是对人类言语的逻辑分析。赫尔德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仍然是完全思辨式的。它既不是从关于知识的一般理论着手,也不是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着手,而是把论据建立在他对人性的理想以及他对人类文化的特征及发展的深刻直观之上。但尽管如此,这个理论仍然包含着最有价值的逻辑和心理学因素。长期以来被人们所研究并精确地描述的那种在动物中存在的一切普遍化或抽象化的过程,
 明显地缺乏赫尔德所强调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标记。然而晚近以来,赫尔德的观点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得到了颇为意想不到的澄清和支持。在语言的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新近研究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大脑损伤而引起的言语〔能力〕的丧失或严重损害,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样一种缺陷改变了人的行为的全部特性。患有失语症或其他同源病症的病人不仅丧失了对语词的运用能力,而且整个的人都经历了相应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在他们的外部行为中是几乎观察不到的,因为在外部行为中他们总是以相当正常的方式来行事。他们能够胜任日常生活的各种工作,有些人甚至在所有这一类的实验中都发挥出相当高的技能。但是一当问题的解决需要某些特殊的理论活动或反思活动时,他们就完全不知所措了。他们不再能用一般的概念或范畴来思考,由于丧失了对普遍物的把握能力,他们只得纠缠于直接的事实和具体的情景。这样的病人是不能完成任何只有依靠对抽象物的把握才能完成的任务的。
明显地缺乏赫尔德所强调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标记。然而晚近以来,赫尔德的观点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得到了颇为意想不到的澄清和支持。在语言的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新近研究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大脑损伤而引起的言语〔能力〕的丧失或严重损害,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样一种缺陷改变了人的行为的全部特性。患有失语症或其他同源病症的病人不仅丧失了对语词的运用能力,而且整个的人都经历了相应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在他们的外部行为中是几乎观察不到的,因为在外部行为中他们总是以相当正常的方式来行事。他们能够胜任日常生活的各种工作,有些人甚至在所有这一类的实验中都发挥出相当高的技能。但是一当问题的解决需要某些特殊的理论活动或反思活动时,他们就完全不知所措了。他们不再能用一般的概念或范畴来思考,由于丧失了对普遍物的把握能力,他们只得纠缠于直接的事实和具体的情景。这样的病人是不能完成任何只有依靠对抽象物的把握才能完成的任务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赫尔德称为反省的思想是何等地依赖于符号的思想。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柏拉图著名比喻中那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赫尔德称为反省的思想是何等地依赖于符号的思想。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柏拉图著名比喻中那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