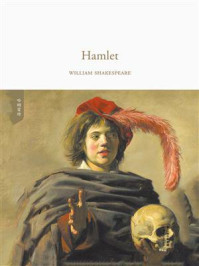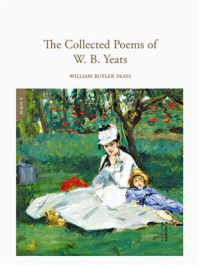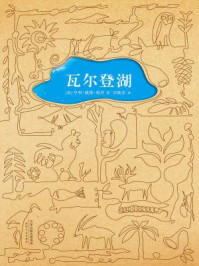这个宝藏长久以来一直是神甫沉思冥想的对象,现在它终于能确保法里亚爱同己子的这个人未来的幸福了,在他眼里,宝藏的价值由此而倍增。他每天都喋喋不休地谈论宝藏如何分配,向唐泰斯解释说,一个人在当今时代,拥有一千三百万到一千四百万财产,能在多大程度上造福于他的朋友;这时,唐泰斯的脸色就变得阴沉了,因为他所立下的复仇誓言在他的脑中出现了,他也想,在当今时代,一个人拥有一千三百万到一千四百万财富,能给他的仇人带去多大的灾难。
神甫没去过基督山岛,但是唐泰斯去过;他过去常常经过这个岛屿,它离皮阿诺扎岛
 二十五海里,位于科西嘉岛和厄尔巴岛之间,他的船甚至在那里停靠过一次。这个小岛自古以来一直荒无人烟,现在仍是这样;它实际上像是一块巨大的几乎成锥形的岩石,似乎是某次海底火山爆发后被推到海面上来的。
二十五海里,位于科西嘉岛和厄尔巴岛之间,他的船甚至在那里停靠过一次。这个小岛自古以来一直荒无人烟,现在仍是这样;它实际上像是一块巨大的几乎成锥形的岩石,似乎是某次海底火山爆发后被推到海面上来的。
唐泰斯画了一张小岛地图给法里亚看,法里亚则指导唐泰斯用什么办法找到宝藏。
不过唐泰斯远没有老人那么热情,特别是没那么自信。当然啦,现在他相信法里亚不是疯子了,他的这个发现让人以为他发疯了,但发现秘密的经过却更增加了唐泰斯对他的敬仰。然而,他仍不能相信,这个宝藏,即便过去存在,现在就一定还在;倘若说他不认为宝藏是幻想出来的,至少也认为它不复存在了。
然而,仿佛命运有意要夺去这两个囚犯的最后一线希望,让他们懂得他们注定该坐一辈子监牢似的,一次新的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了:临海的走廊因为早就有陷坍的危险,近来重建加固了一次,加固了地基,用巨大的岩块堵住了唐泰斯已经填塞了一半的洞。读者该记得,这个防范措施还是神甫向年轻人提议的,否则,他们就要遭到更大的不幸,因为狱方一旦发现他们的越狱企图,肯定会把他俩分开;他们从此就要关在一扇新的,比其他的门更加坚固、更加无情的牢门后面了。
“您瞧,”年轻人带着淡淡的忧郁对法里亚说道,“天主甚至把您称之为我对您的忠诚的那点功德都给抹掉了。我曾答应过永远与您在一起的,现在,我想违背诺言也没这个自由啦;我与您一样得不到那个宝藏了,我俩都出不去了。不过,您瞧,我的朋友,我真正的财富倒不是在基督山阴森森的岩石下等着我的东西,而是您的出现,是我们在狱卒的看管之下每天共同度过的五六个小时,是您灌输在我的脑中的智慧之光,植根在我的记忆里的语言,它们已经长出了富于哲理的分枝了。您对科学知识有深刻的了解,能把它们归纳成条理清晰的原则,使这些分门别类的科学变得明白易懂,便于我掌握,这些都是我的财富,朋友,您用它们使我变得富有和幸福。请相信我吧,请您放心吧,对我来说,这比成吨的金子、成箱的钻石更加珍贵,哪怕那些东西确实存在,而不是像人们清晨看到在海面上飘浮着的,看上去像是坚实的土地,而一靠近就蒸发、升腾、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雾团。尽可能长时间地与您呆在一起,倾听您那雄辩的声音以丰富我的思想,锤炼我的灵魂,使我的身心一旦获得自由时能经受得住巨大而可怕的灾难;用它们来充实我的心灵,使准备自暴自弃的我,自认识您以后,不再伤心绝望;这就是我的财富,真正属于我自己的财富;这个财富并不是虚幻的,而是您确确实实恩施于我的,世上任何君王,即便是恺撒·博尔吉亚家族也罢,都休想从我这里夺走。”
于是,对这两个命运不济的囚犯,往后的日子虽不能说快活,但至少倒也过得很快。法里亚多年来对宝藏守口如瓶,现在一有机会就说个没完。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的右臂和右腿仍然瘫痪不能动,因此他几乎失去了自己享受这笔财富的任何希望了;然而他老幻想着他年轻的伙伴能获释或是逃脱,因此为年轻人感到庆幸。他担心遗嘱在某一天会一时找不到或丢失,于是就强迫唐泰斯熟记在心。唐泰斯能把这个遗嘱从第一个字背诵到最后一个字。这时,他毁掉了另外半张遗嘱,他确信即便别人找到并夺走前半张,也猜不出其全部含义。有时,法里亚整小时整小时地对唐泰斯施授各种教育,这些知识都是他获得自由之后用得上的。一旦他成为自由人了,从他获得自由的那一天、那一时、那一刻起,他只能有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不惜用任何办法直奔基督山岛,找一个不会引起猜疑的借口,一个人呆在那里;一旦到了目的地,一旦只剩下他单独一人了,他就该想方设法去找到那些神奇的洞窟,搜索指定的地点。那地点,读者该记得,是在第二个洞穴的最深的那个角落里。
在这期间,日子过得虽不能说飞快,至少也不致令人不堪忍受。我们提到过了,法里亚没有恢复那一只手和一只脚的功能,但神志是完全清醒的;渐渐的,除了我们已经详述过的种种精神科学的知识而外,他还教会了年轻伙伴怎样做一个耐心而高尚的犯人,怎样懂得在无所事事之中找些事情来做。因此,他俩永远是忙忙碌碌的,法里亚借此免得自己老得过快,唐泰斯则借此免得再想起几乎已经忘却的过去,往事已像夜色中远远的一盏孤灯,现在只是在他记忆的深处时隐时现了。他们再没有新的灾祸临头,在天主的谛视下,时光就这样机械地、平静地流逝,他们就这样生活着。
可是,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在年轻人的内心,也许也在老人的内心里,隐藏着许多被克制着的冲动和被窒息了的叹息,每当法里亚独自留下,爱德蒙回到自己房间去之后,它们就都表露出来了。
一天夜间,爱德蒙突然惊醒,他似乎听到有人呼唤他。
他睁开眼睛,想穿过浓重的夜色看个明白。
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或者确切地说听见了一阵费力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的呻吟声。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焦虑不安,头冒冷汗,他倾听着。不再有疑问了,呻吟声正是从他伙伴的牢房里传出来的。
“崇高的天主啊!”唐泰斯喃喃地说,“难道……”
他迅速移开床,抽出石块,钻进地道,爬到另一端,洞口的石块已经掀开。
在那盏我们提到过的丑陋的、灯火抖抖颤颤的灯的照明下,爱德蒙看见老人脸色苍白,站着靠在木床架上。他是熟悉他那可怕的症状的,当法里亚第一次发病时,这些症状真把他吓坏了。眼下,神甫的脸面又因这些病兆一反常态。
“哦!我的朋友,”法里亚无力地说,“您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吗?我不需要再告诉您什么了!”
爱德蒙痛苦地惨叫一声,神志完全迷糊了,他冲向门口大声叫喊:
“救命!救命!”
法里亚还有最后一点力气能用手臂拦住他。
“别出声!”他说,“要不您就完了。我们只能指望您了,指望如何使您的囚禁生活好受些,或者如何能让您逃跑。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您独自得几年才能重新再做到,但倘若看守知道我们互有来往,这一切顿时就会被摧毁的。再说,您就放心吧,我的朋友,我即将离开的这间地牢,不会长期空着,另一个受难者会来代替我。对那人来说,您就好比是一个拯救天使。那人也许像您一样年轻、强健、坚韧不拔;那人能帮助您逃跑,而我只能妨碍您。您再也不会有一个半身瘫痪的人绑在您身上使您动弹不得啦。天主终于为您做了件好事,把您被剥夺的一切加倍地偿还给了您,现在到了我该死的时候了。”
爱德蒙只能合起双手,大声说道:
“呵!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请别这样说吧!”
刚才他受到突然打击,一时软弱下来;老人的一番话又几乎使他失去了勇气;但现在他又都一一恢复了。
“啊!”他说道,“我已经救活过您一次,我还能第二次救活您!”
说完,他抬起床脚,从缺口里取出药水瓶,里面还剩下三分之一的红色药水。
“听着,”他说道,“这救命药水还有哪。快,快,快告诉我这次该怎么做;有新的办法吗?说吧,我的朋友,我听着呐。”
“没有希望了,”法里亚摇着头说道,“不过没什么;天主创造了人,并在他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对生命的爱,他希望人类竭尽所能保存生命,虽说生活有时是艰难的,但生命永远是珍贵的。”
“啊!对啊,对啊,”唐泰斯大声说道,“我会救活您的,我向您保证!”
“那好,就试试吧!我愈来愈冷了。我感到血涌向我的头脑;我颤抖得厉害,牙齿直打战,骨头似乎都要散架了,现在全身都开始发抖了,再过五分钟,病就要发作,过一刻钟,我就成为一具僵尸啦。”
“啊!”唐泰斯喊道,内心感到阵阵绞痛。
“您照第一次那样做,不过时间别等得那么长。此刻,我的生命的活力全都已耗尽了,死神要做的事,”他指着他瘫痪的胳膊和小腿继续说道,“也只剩下一半了。倘若您在我嘴里倒了十二滴药水,而不是上次的十滴,您发觉我还没有回过来,您就把剩下的全倒进去。现在,把我抱起放到床上,因为我已经站不住了。”
爱德蒙把老人抱在怀里,安放到床上。
“现在,朋友,”法里亚说道,“您是我悲惨的一生唯一的安慰,上天把您给我虽说迟了一些,但总归是给我了,这是一件无比珍贵的礼物,我深深地感激天主;在我即将永远与您分手之际,我祝您幸福、成功,您该得到这些;我的儿子,我为您祝福!”
年轻人跪下来,把头靠在老人的床上。
“特别是,在这庄严的时刻请听我对您说:斯帕达的宝库确实存在;承蒙天主恩准,距离和障碍现在对我都不存在了。我在第二个洞窟的深处看到了宝藏,我的目光穿透了大地,我在如此之多的奇珍异宝面前感到眼花缭乱。倘若您能成功地逃脱,请记住,这个可怜的神甫,大家都认为他是疯子,其实不是的。直接奔向基督山,享用我们的财富,好好享用吧,您受的苦难够多的了。”
老人一阵剧烈震动,中断了讲话。唐泰斯抬起头,看见他的眼球充满了血,似乎大量的血液从他的胸腔涌到了他的脸部。
“永别了,永别了!”老人痉挛地按住年轻人的手喃喃说道,“永别了!”
“啊!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后者大声说道,“呵,天主啊,别抛弃我们!快来救救他,帮帮我的忙……”
“别出声!别出声!”垂死的人轻声说道,“倘若您能救活我,我们就不会分离了!”
“您说得对。啊!是的,是的,请放心,我会救活您!再说,您虽然很痛苦,但看来比第一次要轻些。”
“哦!您错了!我不那么难受,是因为我身上已没有力气再忍受痛苦了。在您这个年纪,你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念,自信和希望是年轻人的特权;然而老人对死看得比较清楚。啊!它在这儿……它来了……结束了……我看不见了……我的思想消失了……您的手呢,唐泰斯!……永别了!……永别了!”
他集中了所有的精力,使尽最后一点力气挣扎着抬起身子。
“基督山!”他说道,“别忘了基督山!”
说完,他瘫倒在床上。
这一次发作十分可怕:他的四肢僵直,眼皮鼓起,口吐红色泡沫,全身一动不动,在这张苦难的床上,这一切取代了不久前还躺着的智者。
唐泰斯拿起灯,放到床头前的一块凸出的石头上,摇曳的灯光就从那里,以一种异样而古怪的光芒,照亮了这张变了形的脸和这个失去生气的僵直的躯体。
他目光凝定,无畏地等待着施用救命药水的时刻到来。
他觉得时候已到,便拿起小刀,撬开牙床,这次牙齿没像第一次咬得那么紧,他一滴一滴地数着,数到十滴,又等着;瓶子里大约还有两倍于滴进去的数量。
他等了十分钟,一刻钟,半小时,毫无动静。他浑身颤抖,毛发竖起,额上凝着冷汗,他用自己心脏的跳动来计秒。
这时,他想该进行最后一次努力了:他把药瓶移近法里亚发紫的嘴唇,他无须掰开那张开后不曾闭上的下颌,便将药瓶中的药水全都倒了进去。
药水产生了电流刺激般的效应,老人的四肢剧烈地抖动了一下,他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令人害怕,他叹出一口气,听上去却像是一声尖叫,接着,颤动的全身渐渐又归于死寂。
只有两只眼睛睁开着。
半小时,一小时,一个半小时过去了。爱德蒙在这焦躁不安的一个半小时里,不时向他的朋友倾下身子,把手贴在他的心窝上,但渐渐感到他的身体变凉了,心脏的跳动渐渐减弱,声音也愈来愈低、愈来愈沉了。
终于一切都未再复苏。心脏的最后一次颤动停止了,脸色变得铁青,两眼仍然睁着,然而眼神无光了。
此时已是清晨六点,天刚刚放亮,它那微弱的光线涌进地牢,使奄奄一息的灯光显得更加苍白。异样的反光映射在死者的脸上,不时地使它出现生命的迹象。在天将明未明之际,唐泰斯还抱有一线希望,但当白天到来时,他明白了,只有他一人与一具尸体呆在一起了。
于是一种极度的、无法克服的恐惧攫住了他,他不敢再按在这只悬在床外的手上,不敢再把眼睛停留在那对固定不动的、泛白的眼睛上,他好几次想把它们合上,但都未奏效,合上又睁开了。他灭了灯,把灯小心藏好,钻进地道去,再尽可能把他头顶上方的石板放端正。
再说,也到时间了,狱卒马上要来了。
这次,狱卒先去看唐泰斯,从他的地牢出来后,再到法里亚的地牢去,而且带去了早饭和内衣。
在狱卒身上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已经知道了发生的事情,他走了出去。
这时,唐泰斯突然急于想知道在他苦难的朋友的牢房里发生的事情;于是他又钻进地道,到了那头正巧听到那个狱卒求援的惊呼声。
不一会儿其他狱卒都进来了,接着,便可听到士兵们沉重而有节奏的脚步声。这样走路在士兵已经成了习惯,即便不在值勤时他们也这样走路。在士兵之后,典狱长到来了。
爱德蒙听到有人摇动尸体时床发出的吱嘎声。他还听到典狱长命令下属向老人脸上泼水的声音,当他看到泼过水后犯人仍然不动时,就派人去找医生。
典狱长出去了;有几句怜悯的话传到唐泰斯的耳朵里,话中还夹杂着嘲讽的笑声。
“行啦,行啦,”一个人说道,“疯子去找他的宝藏去了,祝他一路顺风!”
“他有几百万但买不起一条裹尸布,”另一个人说道。
“哦!”第三个人接着说,“伊夫堡的裹尸布可不算贵。”
“也可能,”先前那第一个人说道,“由于他是教会的人,他们愿意为他破费几文哩。”
“那么他就有幸装进袋子里啰。”
爱德蒙听着,一句话也没漏掉,可是其中的好些话他都不懂。说话声很快就消失了,他觉得在场的人都离开了那间囚室。
然而他仍不敢进去,也许他们留下个把狱卒守尸呢。
于是他一动不动,默不作声、凝神屏气地呆着。
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寂静中漾起了轻微的声音,继而又愈来愈响。
是典狱长回来了,后面跟着医生和几名军官。
又出现了片刻的寂静,医生正走近床,检查尸体。
过一会儿,就开始了问话。
医生诊断出犯人死亡的病因,宣布他已经死了。
问话答话都是那么漫不经心,唐泰斯不禁愤慨起来。他觉得,他自己对可怜的神甫的爱,所有在场的人也都应该感受到一部分才对。
“听了您的诊断我很难过,”医生明确宣布老人确实死了,典狱长听了回答道,“这个犯人性情温和,与人为善,疯得有趣,特别易于看管。”
“啊!”那个狱卒接口说道,“我们甚至可以不必看守他,我敢担保,他在这里可以呆上五十年也决不会有一次越狱的企图。”
“不过,”典狱长又说道,“虽说您满有把握,现在还是要肯定一下犯人是否真的死了,此事很急,倒不是因为我怀疑您的医道,而是出于我的责任。”
囚牢里一时鸦雀无声,在这期间,唐泰斯一直在谛听,他估计医生又一次在查看死者,并为其诊脉。
“您可以完全放心,”医生说道,“他死了,我向您担保。”
“您知道,先生,”典狱长执拗地又说道,“像他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简单的诊断;虽说他看来是死了,还得请您按法律规定的手续办理,把这件事了结掉。”
“那么请人去烧烙铁吧,”医生说道,“不过说真的,这个做法是大可不必的。”
唐泰斯听到下达烧烙铁的命令,打了一个寒战。
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门的转动声,在房间里的来去走动声;不一会儿,一个狱卒走进来说道:
“火盆和烙铁拿来了。”
这时静默了片刻,接着便传来烙炙人体的咝咝声,浓烈而呛人的气味甚至穿过了墙壁,唐泰斯正在那堵墙后惊恐地谛听着。
年轻人闻到人体的焦味,额上冒出了汗,他觉得快要昏过去了。
“您瞧,先生,他是死了,”医生说,“火烧脚跟是关键;可怜的疯子的疯病治好了,从大牢里解脱了。”
“他名叫法里亚吗?”陪同典狱长的一个军官问道。
“是的,先生;照他自己说,这是一个世家的姓氏;此外,他很博学,只要不涉及宝藏这件事,他在一切方面都很明辨事理;不过一说到宝藏,我得承认,他就犟得要命。”
“我们对这种固执的感情称之为偏执狂,”医生说道。
“您对他从来就没什么可抱怨的吗?”典狱长向负责给神甫送饭的狱卒问道。
“从来没有,典狱长先生,”狱卒答道,“从来没有,决没有!相反,从前,他还讲故事给我听,可让我高兴了;一天,我的老婆生病了,他甚至给我开了一个药方,把她的病治好了。”
“哦!哦!”医生说道,“我还不知道我是在与一个同行打交道;我希望,典狱长先生,”他笑着补充道,“您会对他作出相应安排啰。”
“是呀,是呀,放心吧,我们尽可能找一个崭新的袋子把他装在里面。您满意了吗?”
“我们该当着您的面把这道最后的手续办完吗?”一个守门狱卒问道。
“当然,不过得抓紧时间;我总不能一整天呆在这个房间里。”
又传来了来回走动的脚步声;隔了一会,唐泰斯听到了搓揉麻布的声音,床吱嘎作响,还有沉重的脚步声,这似乎是有人抬起尸体时,双脚负重踏在石头地面上的声音,最后又是床受压发出的吱嘎声。
“晚上见,”典狱长说。
“要做一次弥撒吗?”一个军官问道。
“不可能了,”典狱长答道,“堡里的神甫昨天来请一个礼拜假,要到耶尔
 去一趟,我还跟他担保说这段时间犯人不会出什么问题哩;可怜的神甫走得也太着急了点,他本来可以听到安魂曲的。”
去一趟,我还跟他担保说这段时间犯人不会出什么问题哩;可怜的神甫走得也太着急了点,他本来可以听到安魂曲的。”
“唔!唔!”医生带着他这一行人对宗教惯有的不敬口吻说道,“他是教会里的人,天主会考虑到这个情况,不会把一个教士派到他那儿去,让魔鬼得意的。”
这句拙劣的玩笑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这期间把尸体装进麻袋的工作仍在继续。
“晚上见!”干完后,典狱长说道。
“几点?”看门狱卒问道。
“十点到十一点吧。”
“要守尸吗?”
“何必呢?像他生前那样把地牢门关上就得了。”
脚步声走远了,声音越来越小,又传来了关门上锁以及拉铁闩的刺耳的嘎嘎声;接下来便是一片寂静,这片死寂比孤独更凄惨,它渗透周围的一切,一直渗入年轻人冰冷的心里。
此时,他用头慢慢地顶起石板,朝囚室投去探询的一瞥。
囚房里空无一人:唐泰斯钻出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