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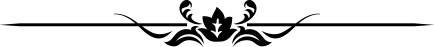

在我们所有的自然资源中,水已变得异常珍贵,绝大部分地球表面为无边的大海所覆盖,然而,在这汪洋大海之中我们却感到缺水。看来很矛盾,岂不知地球上丰富水源的绝大部分由于含有大量海盐而不宜用于农业、工业及人类消耗,世界上这样多的人口正在体验或将面临淡水严重不足的威胁。人类忘记了自己的起源,又无视维持生存最起码的需要,这样,水和其他资源也就一同变成了人类漠然不顾的受难者。
由杀虫剂所造成的水污染问题作为人类整个环境污染的一部分是能够被理解的。进入我们水系的污染物来源很多:有从反应堆、实验室和医院排出的放射性废物,有原子核爆炸的散落物,有从城镇排出的家庭废物,还有从工厂排出的化学废物等。现在,一种新的东西也加入了这一污染物的行列,这就是使用于农田、果园、森林和田野里的化学喷洒物。在这个惊人的污染物mélange
 中,有许多化学药物再现并超越了放射性的危害效果,因为在这些化学药物之间还存在着一些险恶的、很少为人所知的内部相互作用以及毒效的转换和叠加。
中,有许多化学药物再现并超越了放射性的危害效果,因为在这些化学药物之间还存在着一些险恶的、很少为人所知的内部相互作用以及毒效的转换和叠加。
自从化学家开始制造自然界从未存在过的物质以来,水净化的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了;对水的使用者来说,危险正在不断增加。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合成化学药物的大量生产始于本世纪四十年代。现在这种生产增加,以致使大量的化学污染物每天排入国内河流。当它们和家庭废物以及其他废物充分混合流入同一水体时,这些化学药物用污水净化工厂通常使用的分析方法有时候根本化验不出来。大多数的化学药物非常稳定,采用通常的处理过程无法使其分解。更为甚者是它们常常不能被辨认出来。在河流里,真正不可思议的是各种污染物相互化合而产生的新物质,卫生工程师只能绝望地称这种新化合物为“污物”。马萨诸塞州工艺学院的罗尔夫·伊莱亚森教授在议会委员会前作证时认为,预知这些化学药物的混合效果或识别由此产生的新有机物,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伊莱亚森教授说:“我们还没有开始认识那是些什么东西。它们对人会有什么影响,我们也不知道。”
控制昆虫、啮齿类动物或杂草的各种化学药物的使用,现在正日益助长这些有机污染物的产生。其中有些有意地用于水体以消灭植物、昆虫幼虫或杂鱼,有些有机污染物来自森林,在森林中喷药可以保护一个州的二三百英亩土地免受虫灾。这种喷洒物或直接降落在河流里,或通过茂密的树木华盖滴落在森林底层,它们在那儿加入了缓慢运动着的渗流水而开始其流向大海的漫长旅程。这些污染物的大部分可能是几百万磅农药的水溶性残毒,这些农药原本是用于控制昆虫和啮齿类的,但借助于雨水,它们离开了地面而变成世界水体运动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河流里,甚至在公共用水的地方,我们到处都可看到这些化学药物引人注目的痕迹。例如,在实验室里,用从潘斯拉玛亚一个果园区取来的饮用水样在鱼身上做试验,由于水里含有很多杀虫剂,所以仅仅在四个小时之内,所有做实验用的鱼都死了。灌溉过棉田的溪水即使在通过一个净化工厂之后,对鱼来说仍然是致命的。在阿拉巴马州田纳西河的十五条支流里,由于来自田野的水流曾用毒杀芬处理过,致使河里的鱼全部死亡,而这其中的两条支流是供给城市用水的水源。在使用杀虫剂的一个星期之后,放在河流下游的铁笼里的金鱼每天都有悬浮而死的,这足以证明水依然是有毒的。
这种污染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无形的和觉察不到的,只有当成百成千的鱼死亡时,人们才知道这一情况;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污染根本就没有被发现。保护水的纯洁性的化学家至今尚未对这些有机污染物进行过定期检测,也没有办法去清除它们。不管发现与否,杀虫剂确实客观存在着。杀虫剂当然随同地面上广泛使用的其他药物一起进入众多的河流,几乎是进入了国内所有主要水系。
假若谁对杀虫剂已造成我们水体普遍污染还有怀疑的话,他应该读读一九六〇年由美国渔业及野生生物管理局印发的一篇小报告。这个管理局已经进行了研究,想发现鱼是否会像温血动物那样在其组织中贮存杀虫剂。第一批样品是从西部森林地区取回的,在这些地方为了控制云杉树毛虫而大面积喷洒了滴滴涕。正如所料,所有的鱼都含有滴滴涕。后来当调查者对距离最近的喷药区约三十英里的一个遥远的小河湾进行对比调查时,得到了一个真正有意思的发现。这个河湾是在采第一批样品处的上游,并且中间隔着一处高瀑布。据了解这个地方并没有喷过药,然而这里的鱼仍含有滴滴涕。这些化学药物是通过埋藏在地下的流水而达到遥远的河湾的呢,还是像飘尘似的从空中飘落在这个河湾的表面的呢?在另一次对比调查中,在一个产卵区的鱼体组织里仍然发现有滴滴涕,而该地的水来自一口深井。同样,那里也没有撒药。污染的唯一可能途径看来与地下水有关。
在整个水污染的问题中,再没有什么能比地下水大面积污染的威胁更使人感到不安的了。在水里增加杀虫剂而不想危及水的纯净,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造物主很难封闭和隔绝地下水域,而且她也从未在地球水的供给分配上这样做过。降落在地面的雨水通过土壤、岩石里的细孔及缝隙不断往下渗透,越来越深,直到最后形成岩石的所有细孔里都充满了水的一个地带,此地带是一个从山脚下起始、到山谷底沉没的黑暗的地下海洋。地下水总是在运动着,有时候速度很慢,一年也不超过五十英尺;有时候速度比较快,每天几乎流过十分之一英里。它通过看不见的水线在漫游着,直到最后在某处地面以泉水形式露出,或者可能被引到一口井里。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它归入小溪或河流。除直接落入河流的雨水和地表流水外,所有现在地球表面流动的水有一个时期都曾经是地下水。所以从一个非常真实和惊人的观点来看,地下水的污染也就是世界水体的污染。
由科罗拉多州某制造工厂排出的有毒化学药物必定通过了黑暗的地下海流向好几英里远的农田区,在那儿毒化了井水,使人和牲畜病倒、使庄稼毁坏——这是许多同类情况的第一个典型事件。简略地说,它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四三年位于丹佛附近的一个化学兵团的落基山军需工厂开始生产军用物资,这个军工厂的设备在八年以后租借给一个私人石油公司生产杀虫剂。甚至还未来得及改变工序,离奇的报告就开始传来。距离工厂几里地的农民开始报告牲畜中发生无法诊断的疾病。他们抱怨这么大面积的庄稼被毁坏了,树叶变黄了,植物也长不大,并且许多庄稼已完全死亡。另外还有一些与人的疾病有关的报告。
灌溉这些农场的水是从很浅的井水里抽出来的,在对这些井水化验时(一九五九年在由许多州和联邦管理处参加的一次研究中),发现里面含有化学药物的成分。在落基山军工厂投产期间所排出的氯化物、氯酸盐、磷酸盐、氟化物和砷流进了池塘里。很显然,在军工厂和农场之间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了,并且地下水在七至八年的时间里带着毒物在地下漫游了大约三英里路,然后到达最近的一个农场。这种渗透在继续扩展,并进一步污染了尚未查清的范围。调查者们没有任何办法去消除这种污染或阻止它们继续向前发展。
所有这一切已够糟糕的了,但最令人感到惊奇和在整个事件中最有意义的是,在军工厂的池塘和一些井水里发现了可以杀死杂草的2,4-D。当然它的发现足以说明为什么用这种水灌溉农田后会造成庄稼的死亡。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兵工厂从未在任何工序中生产过这种2,4-D。
经过长期的认真研究,化学家们得出结论:2,4-D是在开阔的池塘里自发合成的。人类化学家没有起任何作用,它是由兵工厂排出的其他物质在空气、水和阳光的作用下合成的。这个池塘已变成了生产一种新药物的化学实验室,这种化学药物致命地损害了它所接触到的植物的生命。
科罗拉多农场及其庄稼受害的故事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除了科罗拉多之外,在化学污染通往公共用水的任何地方,是否都可能有类似情况存在呢?在各处的湖和小河里,在空气和阳光催化剂的作用下,还有什么危险的物质可以由标记着“无害”的化学药物所产生呢?
说实在的,水的化学污染的最惊人方面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河流、湖泊或水库里,或是在你饭桌上的一杯水里,都混入了化学家在实验室里没想到要合成的化学药物。这种自由混合在一起的化学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给美国公共卫生部的官员们带来了巨大的骚动,他们对这么一个相当广泛存在的、从比较无毒的化学药物可以形成有毒物质的情况表示害怕。这种情况可以存在于两个或者更多的化学物之间,也可以存在于化学物与其数量不断增长着的放射性废物之间。在游离射线的撞击之下,通过一个不仅可以预言而且可以控制的途径来改变化学药物的性质并使原子重新排列是很容易实现的。
当然,不仅仅是地下水被污染了,而且地表流动的水,如小溪、河流、灌溉农田的水也都被污染了。看来,设立在加利福尼亚州提尔湖和南克拉玛斯湖的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为此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例证。这些保护区是正好跨越俄勒冈州边界的北克拉玛斯湖生物保护区体系的一部分。可能由于共同分享用水,保护区内一切都相互联系着,并都受这样一个事实的影响,即这些保护区像一些小岛一样被广阔的农田所包围,这些农田原先都是被水鸟当作乐园的沼泽地和水面,后来经过排水渠和小河疏干才改造成农田。
围绕着生物保护区的这些农田现在由北克拉玛斯湖的水来灌溉。这些水从它们所浇灌过的农田里聚集起来后,又被抽进了提尔湖,再从那儿流到南克拉玛斯湖。因此设立在这两个水域的野生生物保护区的所有的水都是农业土地排出的水。记住这一情况对了解当前所发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一九六〇年夏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提尔湖和南克拉玛斯湖捡到了成百只已经死了的或奄奄一息的鸟。大部分是以鱼为食的种类:苍鹭、鹈鹕、
 和鸥。经过分析,发现它们含有与毒剂滴滴滴(DDD)和滴滴伊(DDE)同类的杀虫剂残毒。湖里的鱼也发现含有杀虫剂,浮游生物也是一样。保护区的管理人认为水流往返灌溉经过大量喷过药的农田,把这些杀虫剂残毒带入保护区,因此保护区河水里的杀虫剂残毒现正日益增多。
和鸥。经过分析,发现它们含有与毒剂滴滴滴(DDD)和滴滴伊(DDE)同类的杀虫剂残毒。湖里的鱼也发现含有杀虫剂,浮游生物也是一样。保护区的管理人认为水流往返灌溉经过大量喷过药的农田,把这些杀虫剂残毒带入保护区,因此保护区河水里的杀虫剂残毒现正日益增多。
水质的严重毒化使恢复水质的努力归于失败,这种努力本来是应该取得成果的,每个要去打鸭的西部猎人,每个喜爱成群的水禽像飘浮的带子一样飞过夜空时的景色和声音的人,本应都能感觉到这种成果的。这些特别的生物保护区在保护西方水禽方面占据着关键的地位。它们处在一个漏斗状的细脖子的焦点上,而所有的迁徙路线,如我们所知道的太平洋飞行路线都在这儿汇集。当迁徙期到来的时候,这些生物保护区接受成百万只由哈得孙湾东部白令海岸鸟儿栖息地飞来的鸭和鹅;在秋天,全部水鸟的四分之三飞向东方,进入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在夏天,生物保护区为水禽,特别是为两种濒临灭绝的鸟类——红头鸭和红鸭——提供了栖息地。如果这些保护区的湖和水塘被严重污染,那么远地水禽的毁灭将是无法制止的。
水也应该被考虑加入到它所支持的生命环链中去,这个环链从浮游生物的像尘土一样微小的绿色细胞开始,通过很小的水蚤进入噬食浮游生物的鱼体,而鱼又被其他的鱼、鸟、貂、浣熊吃掉,这是一个从生命到生命的无穷的物质循环过程。我们知道水中生命必需的矿物质也是如此从食物链的一环进入另一环的。我们能够设想,由我们引入水里的毒物将不参加这样的自然循环吗?
答案可以在加利福尼亚州清水湖的让人惊讶的历史中找到。清水湖位于旧金山北面九十英里的山区,并一直以垂钓而闻名。清水湖这个名字并不符实,由于黑色的软泥覆盖了整个湖的浅底,实际上它是很浑浊的。对于渔民和沿岸的居民来说,不幸的是湖水为一种很小的蚋虫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繁殖地。虽然与蚊子有密切关系,但这种蚋虫与成虫不同,它们不是吸血虫,而且大概完全不吃东西。但是居住在蚋虫繁殖地的人们由于虫子巨大的数量而感到烦恼。控制蚋虫的努力曾经进行过,但大多都失败了,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当氯化烃杀虫剂成为新的武器时才成功。为发动新的进攻所选择的化学药物是和滴滴涕有密切联系的滴滴滴,这对鱼的生命威胁显然要轻一些。
一九四九年所采用的新控制措施是经过仔细规划的,并且很少有人估计到会有什么恶果发生。这个湖被查勘过,它的容积也测定了,并且所用的杀虫剂是以1∶70×106这样的比例来高度稀释于水的。蚋虫的控制起初是成功的,但到了一九五四年不得不再重复一遍这种处理,这次用的浓度比例是1∶50×106,蚋虫的消灭当时被认为是成功的。
随后冬季的几个月中出现了其他生命受影响的第一个信号:湖上的西方
 开始死亡,而且很快得到报告说已经死了一百多只。在清水湖的西方
开始死亡,而且很快得到报告说已经死了一百多只。在清水湖的西方
 是一种营巢的鸟,由于受湖里丰富多彩的鱼类所吸引,它们也成为一种冬季来访者。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的浅湖中建立起漂流住所的
是一种营巢的鸟,由于受湖里丰富多彩的鱼类所吸引,它们也成为一种冬季来访者。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的浅湖中建立起漂流住所的
 是一种具有美丽外貌和优雅习性的鸟。它被称做“天鹅
是一种具有美丽外貌和优雅习性的鸟。它被称做“天鹅
 ”,因为当它划过湖面荡起微微涟漪时,它的身体低低浮在水面,而白色的颈和黑亮的头高高仰起。新孵出的小鸟附着浅褐色的软毛,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跳进了水里,还乘在爸爸妈妈的背上,舒舒服服地躺在它们的翅膀羽毛之中。
”,因为当它划过湖面荡起微微涟漪时,它的身体低低浮在水面,而白色的颈和黑亮的头高高仰起。新孵出的小鸟附着浅褐色的软毛,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跳进了水里,还乘在爸爸妈妈的背上,舒舒服服地躺在它们的翅膀羽毛之中。
一九五七年对恢复了原有数量的蚋虫又进行了第三次袭击,结果是更多的
 死掉了。如同在一九五四年所验证的一样,在对死鸟的化验中没能发现传染病的证据。但是,当有人想到应分析一下
死掉了。如同在一九五四年所验证的一样,在对死鸟的化验中没能发现传染病的证据。但是,当有人想到应分析一下
 的脂肪组织时,才发现鸟体内有含量达百万分之一千六百的滴滴滴大量聚集。
的脂肪组织时,才发现鸟体内有含量达百万分之一千六百的滴滴滴大量聚集。
滴滴滴应用到水里的最大浓度是百万分之〇点〇二,为什么化学药物能在
 身上达到这样高的含量?当然,这些鸟是以鱼为食的。当对清水湖的鱼也进行化验时,这样一个画面就展开了——毒物被最小的生物吞食后得到浓缩,又传递给大一些的捕食生物。浮游生物中发现含有百万分之五浓度的杀虫剂(是水体中曾达到过的最大浓度的二十五倍);以水生植物为食的鱼含有百万分之四十到三百的杀虫剂;食肉类的鱼蓄集的量最大,一种褐色的鳅鱼含有令人吃惊的浓度:百万分之二千五百。这是民间传说中的“杰克小屋”故事的重演,在这个序列中,大的食肉动物吃了小的食肉动物,小的食肉动物又吃掉食草动物,食草动物吃浮游生物,浮游生物摄取了水中的毒物。
身上达到这样高的含量?当然,这些鸟是以鱼为食的。当对清水湖的鱼也进行化验时,这样一个画面就展开了——毒物被最小的生物吞食后得到浓缩,又传递给大一些的捕食生物。浮游生物中发现含有百万分之五浓度的杀虫剂(是水体中曾达到过的最大浓度的二十五倍);以水生植物为食的鱼含有百万分之四十到三百的杀虫剂;食肉类的鱼蓄集的量最大,一种褐色的鳅鱼含有令人吃惊的浓度:百万分之二千五百。这是民间传说中的“杰克小屋”故事的重演,在这个序列中,大的食肉动物吃了小的食肉动物,小的食肉动物又吃掉食草动物,食草动物吃浮游生物,浮游生物摄取了水中的毒物。
以后甚至发现了更离奇的现象。在最后一次使用化学药物后的短时间内,就在水中再也找不到滴滴滴的痕迹了。不过毒物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湖,它只不过是进入了湖中生物的组织里。在化学药物停用后的第二十三个月时,浮游植物体内仍含有百万分之五点三这样高浓度的滴滴滴。在将近两年的期间内,浮游植物不断地开花和凋谢,虽然毒物在水里已不存在了,但是它不知什么缘故却依然在浮游植物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种毒物还同样存在于湖中的动物体内。在化学药物停止使用一年之后,所有的鱼、鸟和青蛙仍被检查出含有滴滴滴。发现肉里所含滴滴滴的总数已超过了原来水体浓度的许多倍。在这些有生命的带毒者中有在最后一次使用滴滴滴九个月以后才孵化出的鱼、
 和加利福尼亚海鸥,它们已积蓄了浓度超过百万分之二千的毒物。与此同时,营巢的
和加利福尼亚海鸥,它们已积蓄了浓度超过百万分之二千的毒物。与此同时,营巢的
 鸟群从第一次使用杀虫剂时的一千多对到一九六〇年时已减少到大约三十对。而这三十对看来营巢也是白费劲,因为自从最后一次使用滴滴滴之后就再没有发现过小
鸟群从第一次使用杀虫剂时的一千多对到一九六〇年时已减少到大约三十对。而这三十对看来营巢也是白费劲,因为自从最后一次使用滴滴滴之后就再没有发现过小
 出现在湖面上。
出现在湖面上。
这样看来整个致毒的环链是以很微小的植物为基础的,这些植物始终是原始的浓缩者。这个食物链的终点在哪儿?对这些事件的过程还不了解的人们可能已备好钓鱼的用具,从清水湖的水里捕到了一串鱼,然后带回家用油炸了做晚饭的菜肴。滴滴滴一次很大的用量或多次的用量会对人产生什么作用呢?
虽然加利福尼亚州公共卫生局宣布检查结果无害,但是一九五九年该局还是下令停止在该湖里使用滴滴滴。从这种化学药物具有巨大生物效能的科学证据来看,这一行动只是最低限度的安全措施。滴滴滴的生理影响在杀虫剂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毁坏肾上腺的一部分,毁坏了众所周知的肾脏附近的外部皮层上分泌皮质激素的细胞。从一九四八年就知道的这种毁坏性影响出现在狗身上,这种影响在如猴子、老鼠或兔子等实验动物身上还不能显露出来。滴滴滴在狗身上所产生的症状与发生在人身上的爱德孙病的情况非常相似,这一情况看来是有参考价值的。最近医学研究已经揭示出滴滴滴对人的肾上腺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它的这种对细胞的毁坏能力现正在临床上应用于处理一种很少见的肾上腺激增的癌症。
清水湖的情况向公众提出了一个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控制昆虫,使用对生理过程具有如此剧烈影响的物质,特别是这种控制措施致使化学药物直接进入水体,这样做是否有效可取呢?只许使用低浓度杀虫剂这一规定并没有多大意义,它在湖体自然生物链中的爆发性递增已足以说明,现在,往往解决了一个明显的小问题,而随之产生了另一个更为疑难的大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并越来越多。清水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蚋虫问题解决了,对受蚋虫困扰的人固然有利,岂不知给所有从湖里捕鱼用水的人带来的危险却更加严重,且难以查明缘由。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毫无顾忌地将毒物引进水库正在变成一个十分平常的行动。其目的常常是为了增进水对人们的娱乐作用,尽管以后不需要再花钱将此水加以处理使其适合于饮用。某地区的钓鱼者想在一个水库里“改善”钓鱼娱乐,他们说服了政府当局,把大量的毒物倾倒在水库里以杀死那些不中意的鱼,然后由适合钓鱼者口味的鱼孵出取而代之。这个过程具有一种奇怪的、仿佛爱丽丝在奇境中那样的性质。水库原先是作为一个公用水源而建立的,然而附近的乡镇可能还没有对钓鱼者的这个计划来得及商量,就不得不既要去饮用含有残毒的水,又要付出税钱去处理水质,为之消毒,而这种处理决非易事。
既然地下水和地表水都已被杀虫剂和其他化学药物所污染,那么就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不仅有毒物而且还有致癌物质也正在进入公共用水。国家癌症研究所的W·C·惠帕教授已经警告说:“由使用已被污染的饮水而引起的致癌危险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引人注目地增长。”实际上于五十年代初在荷兰进行的一项研究已经为污染的水将会引起癌症危险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以河水为饮用水的城市比那些用像井水这样不易受污染影响的水源的城市的癌症死亡率要高一些。已明确确定在人体内致癌的环境物质——砷曾经两次被卷入历史性的事件中,在这两次事件中饮用已污染的水都引起了大面积癌症的发生。一例中的砷是来自开采矿山的矿渣堆,另一例的砷来自天然含有高含量砷的岩石。大量使用含砷杀虫剂可以使上述情况很容易再度发生。这些地区的土壤也变得有毒了。带着一部分砷的雨水进入小溪、河流和水库,同样也进入了无边无际的地下水的海洋。
在这儿,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孤立存在的东西。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世界的污染正在怎样发生着,我们现在必须看一看地球的另一个基本资源——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