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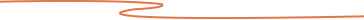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梳过一种马尾辫:头发全部拢到脑后高高束起,然后用大红玻璃丝紧紧勒住。幼儿园阿姨为我梳头时,在我的头发上是很舍得用力的,每每勒得我两只眼角吊起来,头皮生疼,眼里闪着泪花。我为此和阿姨闹别扭,阿姨说,你的头发又细又软,勒得越紧头发才会长得越壮。长大些,当我对农事稍有了解,知道种子播入泥土,所以用脚踩紧踩实,或用碌碡压紧压实,为的是有助于种子生根发芽继而茁壮成长。这时我会想起幼儿园时代我的马尾辫,阿姨似乎把我的头发当做庄稼侍弄了。但她的理论显然是可疑的,因为我的头发并未就此而粗壮起来。
读小学以后,我梳过额前一排“刘海儿”的娃娃头。到了中学,差不多一直是两根短辫。那是文化贫瘠的时代,头发的样式也是贫瘠的,辫子的长度有严格限制,过肩者即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在校女生没人留过肩的辫子,最大胆者的辫梢儿,充其量也就是扫着肩。我们梳着齐肩的短辫,又总是不甘寂寞地要在辫子上玩些花样,爱美之心鼓动着我们时不时弄出点藏头露尾、扭扭捏捏的把戏。忽然有一阵把辫子编得很高,忽然有一阵把辫子编得很低;忽然有一阵把两根辫子梳得很靠前,忽然有一阵把两根辫子梳得紧紧并在脑后。忽然有一阵市面上兴起一种名曰“小闹钟”的发型,就是将头发盖住耳朵由耳根处编起,两腮旁边各露出一点点辫梢儿,好似闹钟的两只尖脚。正当我们热衷于“小闹钟”这种恶俗的发型时,忽然有传闻说这是一种“流氓头”,因为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青年都梳着这种头在社会上作乱。我们害怕了,赶紧改掉“小闹钟”,把两只耳朵重新从头发的遮盖下显露出来。
成人之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社会对头发的限制消失了,从城市到乡村,中国女人曾经兴起一股烫发热潮。在那时,烫成什么样似乎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头发需要被烫。呆板了许多年的中国女人的头发是有被烫一烫的权利的。我也曾有过短暂的烫发史,只在这时,我才正式走进理发馆。从前,我和我的同学几乎都没有进理发馆的经验,我们的头发只需家里大人动动剪子即可。我走进理发馆烫发,怀着茫然的热望。老实说我对理发馆印象不好,那时的理发馆都是国营的,一个城市就那么几家,没有竞争对手,理发师对顾客的态度是:爱来不来。即使这样,理发馆也总是人头攒动。我坐在门口排队,听着嘈杂的人声,剪刀忙乱的嚓嚓声,还有掺着头发油泥味儿的热烘烘的水汽,还有烫发剂那么一股子能熏出眼泪的呛人的氨水味儿……这人声,这气味,屠宰场似的,使我内心充满一种莫名其妙的羞愧感。好不容易轮到我,我坐上理发椅,面对大镜子,望着镜子里边理发师漠然的眼神,告诉她我要烫荷叶头。我须看着镜子里的我和镜子里的理发师讲话,这也让我不安。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面镜子里总叫人有些难为情,特别当她(或他)如此近切地抓挠着你的头发,又如此冷漠地盯着他们手下你的这颗脑袋。现在想来那真是一种呆板而又无趣的发型,可是理发师并不帮你参谋或者给你建议。我顶着一头孤独的“荷叶”回家,只觉得自己又老又俗。
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再烫发,一把头发用橡皮筋在脑后拢住,扎成一拃长的刷子。我的同事介绍给我一位陈姓理发师,说他人好技术也好,虽然是做“男活儿”出身,但“女活儿”你提要求他也能剪。我找到了陈师傅所在的理发馆,陈师傅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五十岁左右,老三届吧,人很敦厚,经常有本地领导同志慕名前来,他理那种程式化了的干部头最拿手。但他的确很聪慧,我提的要求,诸如脑后这把刷子的位置啦,刷子梢儿不要呈香蕉形而要齐齐的好比刷子一样啦,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并不是每个理发师都能达到,可是陈师傅就行。他开动脑筋,过硬的基本功加经验,他成功了。
我的发型好像就这么固定了下来,亲人、朋友、同事都觉得这样子不错,显得五官突出,也有那么点成熟的干练劲儿。谈不到时尚,也绝不能说落伍,而且省事。以至于不知何时我变得必须得留这种发型了。曾有好心同事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告诉我:“你若改变发型,必会让很多人不相信你。”这话分量可不轻,吓住了我,却也愈加诱我生出逆反心理,我跃跃欲试,气人似的,非要改变一下发型不可。
我萌生了剪短发的念头,半年之间曾几次走进美发厅(如今各种美发厅和发廊已遍布各地),又几次借故逃出。我想我这是对自己的发型太在意了,太在意了反倒是在虐待自己了。剪个短发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什么了不起呢剪个短发?于是在那个夏天,去北京出差时,我痛下决心似的走进了住地附近的一间名叫“雪莱”的美发厅。这里环境幽雅,照应顾客的都是些发型、装束均显时尚的年轻人。一位身材瘦高的发型师迎上来问我剪发还是烫发,我说我要剪短发,他立即将我引至一张理发椅上坐好,递上厚厚两本发型图册请我翻阅,另有一位小姐为我送上一杯纯净水。我来来回回翻着书,见里面多是些夸张的富有戏剧性的发型设计,不免心中忐忑,预感此行恐怕是“凶多吉少”,并在这时想起了陈师傅——陈师傅固然老派,却是稳妥的。而我在这样一个时尚和幽雅兼而有之的场面上,不知为什么显得格外孤立和无助。我有些烦躁,翻书的手势就猛了,猛而潦草,像是挑衅。因为我刚刚享受了小姐一杯纯净水的服务,仿佛没有理由站起来就走,我离开的理由只能是他们的态度不好啊。只要这发型师显出一点儿不耐烦,我便能理直气壮地站起来告辞。但是这位年轻的发型师很耐心,他富有经验地对我说,您留这种发型很长时间了吧,长发换短发一般都得有个心理过程。没关系,您慢慢选择。发型师的话使我的心安定下来,我不由自主把自己的职业告诉他,请他帮我做些参谋。他斟酌片刻,认真指给我几种样子,分析了我的发质,还建议我不要烫头发——尽管烫发比剪发的价钱要高很多。这位年轻人给了我一种信任感,我觉得我的头发不会糟蹋在他手里。
发型师在我的头发上开始了他的创造,我也试着自信地看着镜子里的我。我逐渐看清这新的发型于我真是挺合适,这看上去非常简单的造型,修剪的过程却相当复杂,好比一篇简洁的小说,看着单纯,那写作的过程却往往要运用作者更多的功力。临走时我问了发型师的名字,他叫孟文杰。
以后当我的头发长了需要修剪时,我会很自然地想到孟文杰和他的美发厅。这并不是说,除了孟文杰就没有人可以把我的头发剪好,不是的。孟文杰的确有精良的技术和对头发极好的感觉,他的认真、细腻、流畅和利落的风格,他将我的并不厚密的头发剪出那么一种自然而又丰满的层次,的确让我体会到头发的轻松和人的轻松。但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这间美发厅里的几个年轻人和他们营造的气氛,那是一种文明得体、不卑不亢的气氛。不饶舌,不压抑,也没有“包打听”。谈话是自然而然的,时事政治,社会趣闻,天上地下,国内海外……他们是那样年轻,大都二十出头,却十分懂得适可而止。他们也少有“看人下菜碟”的陋习,生客熟客他们一样彬彬有礼。某日我碰见一位言语刻薄的女客正冲孟文杰大发脾气,孟文杰和几位小姐不还口也不动怒,耐心对她做着什么解释。我以为这女客走后他们定会在背后嘀咕她几句——在商店、在公共场所,营业员当着顾客和背对顾客经常是两张脸。但是他们没有,即使面对我这样的熟客,他们也没有流露心里的委屈。我想这便是教养吧,我对他们的技艺和教养肃然起敬。
不过你也别以为这里会呈现一派家庭味儿的不分你我,热情礼貌归热情礼貌,算账时一分一厘都很清爽。没有半推半就的寒暄,或者假装大方的“免单”。这就是平等,平等的时候气氛才轻松。
这是一些不怎么读小说的人,因为熟了,有时候他们也读我的小说。一位姓常的小姐尤其喜欢和我讨论我的小说的结尾。这位常小姐告诉我她擅长讲故事,每当遇到伤心的女友对她诉说自己的伤心事时,常小姐便会讲自己一个比女友更伤心的故事给她听。常小姐说其实我一半都是编的呀,我想只有你的故事比她更伤心,才能让她停止伤心你说是不是?常小姐她实在应该去写小说呢。有时我把自己的新书送给他们,孟文杰往往带着职业本能品评新书,他指着封面上我的照片说:“您耳边这绺头发翘起来了,是上次我没剪好。”假如我很长时间不去“雪莱”,他们也会说起的,计算着几个月了,我应该去了……我知道这不是对所谓“名人”的想念,地处王府井闹市,他们眼前、手下经常流淌着名人和名人的脑袋。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友好心情,我为此而感动。
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除了与你耳鬓厮磨的爱人,还有谁和你头发的关系最亲密呢?正是那些美发师啊。他们用自己诚实、地道的劳动,每天每天,善待着那么多陌生的潮水一般的头发,在那么多头颅上创造出美、整洁、得体和千差万别的风韵,让我想到,在我们的身体上,还有比头发更凡俗、更公开、却又更要紧的东西吗?而美发师这职业,是那么凡俗,那么公开,又那么要紧。多少女性想要改变心情时,首先就是从头发上下手啊。“今天我要对自己好一点,去美发厅做它一个‘离子烫’!”有一回我去镜框店买镜框,听见女店主正对她的熟人说。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陈师傅了,他曾托同事捎话给我,希望我去他那儿让他看看,看我到底剪了个什么样的头,他能不能也学学。
陈师傅的话使我感觉到我对他的一种背叛,还有一点儿凄凉。我的头发“投奔”了一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这本身仿佛就是对陈师傅的不够仗义。不过话也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我们的头发不再可能重复几十年前那被限制的时光,面对头发就永远存在丰富而多样的竞争。
这让人激动,也让人觉出生活的正常和美好。

百日照

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