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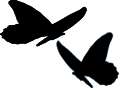

中国向来只说苍颉造文字,然后书契易结绳而治,所以文字的根本意义,还在记事。到了春秋战国,孔子说“焕乎其有文章”,于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了;在这里,于文字之上,显然又加上了些文彩。至于文章的内容,大抵总是或“妙发性灵,独拔怀抱”(《梁书·文学传》),或“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北齐书·文苑传序》),或以为“六经者道之所在,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元史·儒学传》),程子亦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而六经之中,除诗经外,全系散文;《易经》《书经》与《春秋》,其间虽则也有韵语,但都系偶然的流露,不是作者的本意。从此可以知道,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韵文系情感满溢时之偶一发挥,不可多得,不能强求的东西。
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
自六朝骈俪有韵之文盛行以后,唐宋以来,各人的文集中,当然会有散体或散文等成语,用以与骈体骈文等对立的;但它的含义,它的轮廓,决没有现在那么的确立,亦决没有现代人对这两字那么的认识得明白而浅显。所以,当现代而说散文,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外国字Prose的译语,用以与韵文Verse对立的,较为简单,较为适当。
古人对于诗与散文,亦有对称的名字,像小杜的“杜诗韩笔愁来读,似遣麻姑痒处搔”,袁子才的“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学阮庭诗”之类;不过这种称法,既不明确,又不普遍;并且原作大抵限于音韵字数,不免有些牵强之处,拿来作我们有科学知识的现代人的界说或引证,当然有些不对。
(选自郁达夫所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