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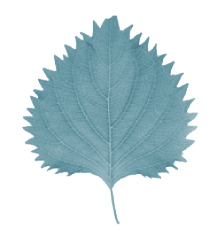 03
03
我们生活在一个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吸收,也在这个系统中思考。
——詹姆斯·道格拉斯
当我开始营养学研究生涯时,我很傻很天真。干草场、挤奶棚,儿时的这些成长环境让我在面对目前科学界的阴暗面时有些措手不及。一些科学工作者贪婪、狭隘、极端不诚实和愤世嫉俗,更别谈一些官员因一些重大发现会妨碍他们的仕途,而对此视而不见这样惊人的事例了。
我进入研究院,渴望从事我理想中的科学研究。我想不到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些更好的了:学习新的知识,选择想要研究的课题,然后与学生和同事分享和讨论一些想法。我欣赏科学方法的透明性和完善性:在真实权威的科学依据面前,个人的意见和偏见都消失不见;一个严谨的科学试验像精美地布置好餐桌,邀请真理来进餐一样;真诚的提问能驱走无知,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发现科学以前是,现在是,并且可能就是那样——只要研究人员小心翼翼,不在“正常”科学的界限之外追求政治上错误的想法。你可以怀疑、询问和研究你喜欢的任何事情,直到你越过由偏见所定义,并由扶持了几乎所有科学的金钱利益所强化的边界。
常态科学。这难道不是一个奇怪的词吗?常态科学意味着任何事情都不能挑战主流范式——被普遍认同的世界的情形。“正常”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好”或“更好”;它只意味着研究员被限制而不能询问那些被认为答案已知、不再作为讨论对象的问题。在我大部分的生涯中,我发现自己触碰到了科学范式的无形边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最终决定完全冲破它们。这就是我如何得知这么多关于那些边界的情况:有时你不得不跨过界线,才找得到它们在哪儿。
范式可怕的地方之一在于:它几乎不可能从内部被感知。一个范式可以是包罗万象的,以至于它看起来好像包含了一切。让我们来看一个盛行了千百年现在却已被作废的范式,那就是太阳是绕着地球旋转,而不是地球绕着太阳旋转这一理论。你不能抱怨当时的人们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因为当人们走出去的时候,看到地球纹丝不动,而天上的太阳、月亮、行星和星星都在移动。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声称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他这一行为是在挑战人们的常识,挑战一个持续了数千年的科学认知,以及怒火中烧的宗教信仰团体。实际上,哥白尼的理论解释了当时流行的地心说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然而,即便他有科学依据,也没能改变他最终的命运。正如哲学家般的作曲家保罗·西蒙(Paul Simon)所说:人们只会听他们想听的东西,而忽略不想听的。
我不是想把自己比喻成哥白尼,只是他的故事是一个广为人知的、陈腐范式阻碍科学进步和真理发现的例子。在完美的世界中(在我开始研究生涯时就信奉的完美世界),当不完善的范式显示出其局限性时,科学方法就会马上去完善它。但是那些因提出这些范式而功成名就的人,这时则表现得像一个受到威胁的独裁者一样。他们会不计一切代价地集结权利,并且当他们越受到挑战时,他们就会变得越卑鄙和危险(当这些范式涉及一些权贵的金钱利益时,这个现象则更加明显——此现象我们将稍后再做讨论)。
有一次我摆脱一个盛行的营养学范式,发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事情:你可以从一个范式的外面去了解其内部的许多东西。设想一条对其他环境一无所知、一直快乐地生活在海里的鱼多芮。有一天它被一张渔网捕住了,然后被打捞起来,最后被扔在一艘船的甲板上。这时它不得不承认,它原来那种以为全世界都是水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假如它能成功挣脱渔网,扑通一声又跃回海里,它会怎样对它的同伴描述它所看到的景象呢?如果它们能像人类一样做出反应,它们又会做何反应呢?“可怜的多芮疯了,它是在吹牛和撒谎呢。”实际上,所发生的事不过是:多芮现在清楚地认识了海洋——许多生存环境中的一个。它现在认识到,海洋是有边界的。并且它对水这种元素的性质也多了一些理解。因为在经历过干燥的空气后,它现在能感知到水的湿润和清冽了。它现在也知道,水也有某种知觉,会对尾巴和鳍的滑动做出某种特殊的反应。宇宙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事物真相,现在多芮能够把大海列入这些浩瀚的事物真相之一了。
我的“出水之旅”让我被我的同事们冠上了异端者的名号。但是我和多芮不一样,我不是被扔出范式的。我只是朝着一个离岸边越来越近的方向游啊游,直到我最后抵达了陆地。我在研究界里的奇异之旅源于我对“离群值观察”的昂然兴趣和不懈追求。离群值部分,是一种与既得观察结果的剩下部分不符合的一种数据。它是一个奇怪的闪光点,是一种反常结果,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东西——这种非同寻常的东西如果被我们坦然面对的话,能对我们现有理解的完善性提出质疑。
离群值观察的结果有时候是错误的,比如由于天平坏了,或者两根试验管被意外地调换了,有可能是由这类原因而导致观察结果错误。而有时候,离群值观察是有人故意而为之所形成的错误观察结论,因为有一些研究者想要出名(或者发财)。所以人们对于那些与普遍认知相冲突的科学数据持怀疑的态度也是正确的。毕竟,我们不希望我们对整个宇宙的理解会随着那些随意的测量结果而变来变去。
处于最佳状态的科学方法会看着离群值的观察说:“证明给我们看啊,证明那并不是一个意外、一个错误,或者是一个谎言。”换句话说,就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再现试验结果,十分详细地描述试验过程,以便于他人可以重复试验,然后看他们是否能得到同样的试验结果。如果一个离群值试验结果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那它就该被并入我们的知识库并改变我们已有的范式。
不幸的是,科学家也是人,他们并不能总是呈现出科学方法的最佳部分。当一些研究发现威胁到他们的毕生研究成果的正确性时,他们会变得十分不理性和极度有戒备心。当一些证据会威胁到他们的资金时,他们会变得极其卑鄙。他们的这些变化你都能察觉到,因为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他们会停止对证据的争论,而开始出言不逊。
当我发现了一个离群值观察的时候,我踏上了这条奇异的道路。我当时的观察结果对动物蛋白有益于人体这一深入人心的营养学观点产生了质疑。
因为我来自于乳牛场,所以我想我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将会是:想出一个方法从家畜身上得到更多的蛋白质。毕竟,世界上有数以亿计的人都因为营养不良而饱受折磨,而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蛋白质缺乏。如果我们能提供数量充足而又价格实惠的牛奶和肉类,我们就能减少数不清的病痛折磨。正如一首创作于1947年的流行乡村歌曲里唱道:如果每个都儿童每天能喝上鲜奶,如果每个工人都有充裕的时间娱乐,如果每个无家可归者都能住进舒适的房间,这世界就会变成一个美好的世界。不再无家可归,每周都有人性化的工作,还能享受牛奶,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吗?
这个研究课题对我来说十分完美。我的整个童年就是在挤牛奶和与我们的顾客分享这种美味中度过的。我的兽医医学、生物化学以及营养学学术背景让我能够理解和使用这些知识去控制动物饲养,以增加人类的食品供应量。一些牛肉和炼乳企业一直以来也非常乐意对我们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资金。所以当我发现动物蛋白对人体有害的证据时,我比任何人都更难以抛弃之前所有的一切想法。
回顾过去,我发现使我筋疲力尽的是,当涉及离群值观察时我那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我相信,我的工作就是发现真相,不论随之而来会有什么结果。我对蛋白质的研究让我逐渐发现,整个现代科学界的范式有一个巨大的缺陷。
我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做了一项令人感到困惑甚至是恐惧的观察,从此以后我便开始踏上了这条离经叛道之路。你可以从以下的简介中了解我当时的观察:在菲律宾,蛋白质摄入量最多的孩子最有可能患上肝癌。这个发现是如此怪异,它与我所了解,以及我自认为我所掌握的知识是如此背道而驰,所以我当即决定查找一下科学文献,了解一下是否有人曾发现蛋白质与癌症的这种关系。
一群印度研究者有过这样的发现。他们做过一个名为“黄金标准”的临床试验,即控制一个变量来进行试验。实验者们给两组小鼠喂食一种叫作黄曲霉毒素的致癌物。在一组小鼠的食物中加入20%的动物蛋白(即酪蛋白),另一组小鼠的食物中不加入蛋白质,只是让它们摄入需要从蛋白质中获取的5%的能量。试验结果是什么呢?食物中加入了20%的蛋白质的第一组中,小鼠们要么患上了肝癌,要么就是出现了癌症的前期机能障碍症状。而第二组中没有一只小鼠出现癌症症状(你可以从第2章讨论关于影响深度的那部分去追溯这个试验)。
回忆过去,也许工作中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喝两口酒,然后上床睡觉,再也不想工作的事儿。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去做这样具有争议性的课题其实比我当时想象得还要危险。虽然我当时也逐渐意识到,科学研究不完全是一个不计个人利益的、发现真相的过程,但是我还是天真地以为,这个世界会欣赏(和回报)那些能够消除癌症折磨的发现。
我当时确实是在一丝不苟地工作,而且我也成功地在潜在批判者的雷达下飞行了好几年。我先后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建立了研究实验室,来研究营养物质在致癌和抗癌方面的作用。我们进行了非常保守的实验,来观察蛋白质、霉和癌细胞的生物化学特性。在烧杯、试管以及高倍显微镜这些科学技术面前,任何批评家和期刊编辑都是一样的。除了我们这群疯狂的科学家还在不顾一切怀疑地慢慢证明:不仅过量食用蛋白质会促进癌症的生成和发展,而且过量食用某一种蛋白质也会如此。人口与疾病控制的研究显示,食用动物蛋白与癌症有着惊人的内在联系。该研究结果与我们的小鼠试验结果一致。
当我说蛋白质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食物呢?可能不是菠菜和甘蓝,虽然这些植物每一卡路里含有的蛋白质是一小块牛肉的两倍多。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蛋白质意味着肉、牛奶和鸡蛋。我们对蛋白质的喜爱由来已久。我们可以从“蛋白质”这个词了解我们有多推崇这种营养物质:蛋白质的词根,proteios,是个希腊词,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长期以来都认为最优质的蛋白质来源于动物。1839年,赫拉尔杜斯·穆德(Gerardus Mulder)发现了蛋白质这种营养物质。不久之后,著名的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又紧接着宣称动物蛋白(高质量蛋白)就是代表生命本身的一种物质。这种认为动物蛋白就是高质量蛋白的说法还可以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解释——比起植物蛋白,人类身体由动物蛋白质构成并且也更容易吸收动物蛋白。
所以想一想,当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动物蛋白是引发癌症的罪魁祸首,而不是植物蛋白时,我们该会有多惊讶。最显著的致癌物是酪蛋白或牛奶蛋白,当这种致癌物质以20%的量加入到我们的实验小鼠的食物中时,几乎毫无例外地导致了它们得癌症。植物蛋白,例如来源于燕麦和大豆中的蛋白,就算大量食用,也不会产生促进癌症生成的作用。
事实上,在1983年,我在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改变蛋白质的摄入量来实现促进或者抑制小鼠早期的癌症恶化。令人惊异的是,当人们长期摄入微量的蛋白质时,癌症会被抑制;如果转而食用大量蛋白质,又会促进癌症恶化。这种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当癌症被激活时,它会迅速地扩散。而当癌症被抑制时,它则完全不扩散。通过少量地改变蛋白质的摄入量,就能够引起癌症发展的重大变化,不论是好的变化还是坏的变化。
是的,我们最近确实在进行一些离群值观察。这些发现的部分意义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相对较低的会引发癌症的蛋白质摄入量。大多数的致癌物研究中(例如,食品染料中的致癌物、热狗中的硝酸盐,以及如二噁英之类的环境毒素),实验室动物被喂食的毒素,是它们在自然界中会遇到的毒素数量的成百上千倍,我们观察发现:人类的日常蛋白质摄入量,或者说是推荐的蛋白质摄入量,会引发最显著的致癌效果。
这个时候我知道,我们手头上的这个实验发现是非常有争议的。我们需要设计更加无懈可击的实验方案,严格地记录实验结果,并且在证明癌症与蛋白质的关系时要尽可能地坦诚。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我们长期以来的研究,并且在一个十分严谨并且有许多同行会阅读的科研期刊上发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为了把我们的研究进行下去,为了得到十分必要但角逐激烈的资金资助,我们必须根据公认的研究标准,一丝不苟地进行研究。
由于我们严格地遵循了研究标准,所以即使这个研究课题的本身充满了争议,我们还是得到了资金资助。连续27年来,我们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得到了资金支持,这些资金让我们能够去了解许多动物蛋白的属性和它在人体内的生物化学作用。我们也了解到,当蛋白质被摄入后,是如何在细胞内起作用进而诱发癌症的。和印度科学家对小鼠的研究结果一样,我们的研究也是有人相信有人质疑。一些激动人心又颇具争议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在我们研究的早期,我被皮特·麦基(Peter Magee)邀请到坦普尔大学菲尔斯研究院的医学院去做一个报告。皮特·麦基是肿瘤学领域主流期刊《癌症研究》( Cancer Research )的主编。报告结束后,我和皮特一同进餐,其间我跟他讲起一个我们最近正在进行的新实验。这个实验可能会变得十分具有争议性。我想要把蛋白质促进癌症的显著效果与强有力的化学致癌物所产生的广为人知的明显效果相比较。我告诉皮特,我猜想动物蛋白的致癌效果可能更令人担忧。他对此相当怀疑,就像一个顶尖期刊的主编应该怀疑的那样。当一个科学范式受到攻击时,攻击者就得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寻找攻击证据的任务。
我们目前的范式包括:环境中的一些有害物质会导致癌症,在与癌症抗衡的战争中,更多的物质也被发现,从而帮助我们减少暴露在这些有害物质之下的机会。然而目前的范式却不包括以下内容:在致癌这个方面,比起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我们所吃的食物起到了更强有力的决定性作用。我之前曾表明,与摄入强效致癌物相比,我们食用的营养物质的细微变化与癌症发展势态更加息息相关。我问《癌症研究》期刊的主编皮特,如果我们真的得到了这样的实验结果,他是否会考虑把我们的研究发现发表在他们久负盛名的期刊的封面。要感谢他的是,虽然他对我们的研究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他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与当时大多数的癌症专家一样,他也认为是化学致癌物、病毒,以及遗传问题导致了癌症,而不是我们食用的营养物质的细微改变。但是,如果我能够证明我奇异的观点并让他认可,他将会接受我们的研究发现,并发表我们的研究结果。
实际上,我们进行的新实验的实验效果比我预期得还要好,实验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发现:与化学致癌物的剂量相比,动物蛋白的摄入量对癌症的发展起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我想把我们激动人心的实验发现作为专题发表在《癌症研究》封面上的希望却破灭了。该杂志的主编皮特退休了,而继任主编和编审委员会正在进行改革。他们想取消有关营养物质对癌症的影响这一方面的栏目,决定把有关营养学和癌症关系方面的稿件交由《癌症流行病学》( Cancer Epidemiology , Biomarkers & Prevention )来处理,这样一来,他们成功地把营养学方面的研究降低到二等地位上。他们想要一些更能引发读者思考的文章——尤其是研究结果与化学、病毒和基因有关的、致力于找出癌症在分子水平上如何作用的文章。他们认为,像我们当时做的那种营养学对癌症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几乎都算不上是科学研究。
与此同时,当我们取得了更多的蛋白质是如何显著地影响癌症的有力证据后,我在韩国首尔的世界营养学大会上做了一个专题报告。许多研究者都聆听了这场报告。我之前的同事也在听众席中,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提倡多食用蛋白质,而不是少量食用蛋白质的研究者。在问答环节,他站起来感叹道:“科林,你正在谈论的都是些美味的食物啊!不要把它们从我们的生活中带走!”
他对我们的研究结果并没有什么质疑,他所关心的只是,我正在试图破坏他对动物蛋白的个人喜爱。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对于人们对他们饮食习惯的强烈感情来说,我们的研究正变得像一根避雷针一样。即使像科学家这种理性又重视数据的人,当他们发现证据,证明了自己所喜欢的食物也许会给他们带来致命的伤害,他们也会陷入一种长期的歇斯底里状态中。这还真是一个触及人们敏感神经的话题啊!这个故事最悲伤的部分在于,我的提问者在那以后就葬身于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了。他死于一种由动物蛋白引起的心脏疾病,去世时他还非常年轻。
我们的研究陆续提出了许多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奇异想法:这些想法主要都是说,所谓的高质量蛋白质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质量。将蛋白质这种我们重视的营养物质与癌症——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疾病的发展联系起来,真是太诡异了!我们最推崇的营养物质导致了我们最畏惧的疾病(未来还会有什么样奇异的事情发生呢!)。
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医学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医学教育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应邀到该学校做一个病例研讨报告。因为当时我们正要发表在中国做的全国性调研的调研结果(我已经在《救命饮食》上对此次的调研结果做了详细说明),所以,我就根据我们对蛋白质的研究发现以及其他研究小组的观察结果,简单地谈了一下癌症与不均衡营养之间的关系。我向他们详细地展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当蛋白质的食用量减少时,癌症就会发生逆转。而后,我推测,未来我们可以用营养学的方法来治疗身患癌症的人们。然而除了这个推测之外,在这方面我不能说得太多,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到底能用什么具体的营养学方法来治疗癌症。
那天晚上晚些的时候,我被外科手术系、化疗系和放射系这三大系的系主任邀请共进晚餐,这三大系都涉及癌症的治疗。在我们的谈话期间,外科系的系主任问我,当人们得知自己得了癌症之后,我说用营养学疗法有可能会影响癌症的发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指出,我们有充足的基本证据来证明这个猜想。比起商业性极强但是风险却极高的疗法,如一些新式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法,我们能得到更多的证据。真的,它们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营养学疗法的潜在好处是:它能够完全抑制癌症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实验数据所得到的这种可能性非常高。从保健的角度来说,营养学疗法的弊端没有。我们都了解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法的副作用,也知道这些疗法看起来比遥远处的星星还小的成功率。因此,我们当然有理由给营养学疗法一个机会。
外科系主任听完后马上说,他绝不允许他的病人尝试营养学疗法,来代替他所熟知的外科疗法治疗癌症。接下来他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外科手术治疗乳腺癌的巨大优势。但是化疗系主任则认为,外科系主任的说法有争议,并且认为化疗比外科手术更有效果。正当坐在我左边的外科系主任与坐在我右边的化疗系主任争辩时,坐在我对面的放射系主任说,他们两位的观点都有一些问题。我因为不知道谁的论说更有道理,所以只是坐在那里听。现在我回忆起这件事,还觉得当时的场面挺有趣的,不过当你考虑到因为这些人的意见而导致病人死亡和饱受折磨时,你就不会觉得有趣了。
在那时候,我记录下了三件有趣的事。第一件事就是,对于外科手术疗法、化学疗法和放射性疗法这三种治疗癌症的方法,优秀的医疗工作者不能就哪一种方法最好达成一致的意见。第二件事,他们很难接受营养学疗法。因为他们觉得,至今都没有发现一些例子,能表明它的确对人类起作用。我也没有发现。第三件事,也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很明显他们对营养疗法一点都不感兴趣,甚至他们都不想讨论该方法,而这些方法探索了营养学作为一种癌症治疗方法的可能性。20多年之后,这个讨论还是一样的。很显然,当一些证据浮出水面,表明营养物质对癌症的影响时,我和这些先生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大多数的肿瘤学家还是推崇用传统的三大疗法之一来治疗癌症,他们对营养学疗法没什么了解,也没什么耐心。
从那以后,我做过两次演讲。其中一次是由两所久负盛名的医学院资助的,观众主要是癌症研究人员和癌症治疗专家。另一次是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在这次演讲中,我简单地回忆了20年前发生的这则故事,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虽然时钟依然滴滴答答地走着,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没发生变化。因为只要不是一种新的手术疗法、一种化学混合物,或者是一种放射性治疗方案,那么营养学在癌症这一领域是不会被接受的。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和我意见不一致的人都是某种武断的、心胸狭隘的野蛮人。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期待(并且希望)其他研究员能来挑战我的发现。鉴于相信研究结果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使这些结果接受检验,以确保准确并证明它们不是粗心、简陋的研究结果。我欢迎那些批评我统计方法的人。当有人试图重复试验我的某项发现时,即使他们的目的是证明我是错误的,我也会感到兴奋。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的一些批评者一直帮我指出我的下一步研究,或者帮助我加强某项研究设计,抑或是帮助我想出新方法来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是科学方法发挥的最大效用:我们不是为了个人荣耀和财富而竞争,而是为最高的真理和幸福而服务。
然而,攻击和反驳我的发现不仅仅是正常的科学探索过程。在很多情况下真正的问题是:我提出的问题威胁到了权威的研究和医学范式。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和他人不断提问,得到的答案超出了狭隘科学所强加的严格的心理界线。
我们已经发现,当牛奶蛋白的摄入量达到一定的水平时,会显著提高实验性癌症的增长率,这不在营养范式的范围之内。
我们已经发现,通过改变实际的营养物摄入量,可以引发或终止实验性癌症的增长,但这也不在癌症治疗的范式范围之内。
我们发现,这些影响是由多重机制共同作用导致的,这也不在医疗范式范围内。
我们也发现,癌症增长率与其说是由基因控制的,倒不如说是由营养控制的,这不在科学范式的范围内。
我们已表明,相比化学致癌物,食物中的营养成分是诱发癌症的决定性因素,这不在癌症治疗和管理机构的范式范围之内。
我们发现饱和脂肪(就此而言,还有脂肪总量、胆固醇)不是心脏病的主要诱因(也有动物蛋白),这不在心脏病学的范式之内。
我可以继续列举。我只是感激我不是生活在过去的年代里,那时“异教徒”会被软禁,或者因为他们的观点而遭受火刑。
科学研究领域之外的读者可能对这些发现并不感到震惊,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真正在医学研究团体内部的所有人来说,它们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现象(邪说)。这些发现中大多数——我可以列举更多——部分地归因于运气,但在进行了第一次不可能完成的观察(高含量酪蛋白“导致”癌症增长)之后,我逐渐意识到我已经偏离到了常态科学的范式。
刚刚尝到了禁果的滋味,我就被它迷住了。在意外地偏离了狭窄和笔直的道路之后,我对现存范式外的平原景色中可能隐藏着的其他东西越发好奇。然后通过公共政策工作,我开始了解范式为什么会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我发现,范式之内的观点通常和之外的观点截然相反,因此使得范式的界线更加清晰。
你可能在想,所有这些关于范式之内和范式之外的讨论看起来抽象甚至学术。这个论证为什么会非常重要呢?事实上,决定一种观察是不是异端邪说非常重要。在医学研究领域,意料之外的发现常常被忽视。研究员不理会它们,说类似这样的话,“这不可能正确。”因此这些发现可能永不见天日(或出现在专业出版物中)。实际上,它们可能是珍宝,或者指出我们视之如常的认知中的错误之处,或者启示一个新的思考维度。
古往今来,大多数哲学书籍都是关于探索难以捉摸真理的研究。我们制定规则引导思维,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些规则,尽管对于表达、共享当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利——在科学和其他领域中——也可能限制了我们。我们提出假说,然后创造或者寻找证据去“证明”它们。
另一种追求真理的方法,由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这种方法试图证明我们的假说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去找寻我们精神范式的边界并加以拓展,看它们能否经得起审查。我们能否找到证据证明我们的假说是错误的?我们能够认真地对待这些证据吗?有时,我情不自禁地想,我们的规则和策略是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频率使我们偏离了现状?
我一直喜欢在我的研究中探索离群观察值。它们促使我思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得到的(或至少是注意到的)观察结果多数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远远多过已被分享的结果。然而,在搜集了足够多的这种邪说之后,我慢慢发现它们的新兴模式暗示着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从这种观点出发,称它们为“原理”比邪说更有意义。案例如下。
在对中国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生活在城市的中年人血液中胆固醇的平均值为每分升127毫克,而农村成年人的人均胆固醇含量为每分升88~165毫克。那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每分升127毫克这个数值会因为过低而被认为有危险。当时美国“正常的”血清胆固醇含量范围是每分升155~274毫克(平均每分升212毫克),而且在西方的研究对象中有一些令人惊奇的证据显示,当总胆固醇水平低于每分升160毫克时,自杀、车祸、暴力事件和结肠癌的发生率更高。那么我是否可以假定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村居民都属于自杀、车祸、暴力和结肠癌的高危人群呢?当然,我们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相反,我们发现,胆固醇平均含量为每分升127毫克的中国农村居民,事实上比自认为胆固醇含量处在正常水平的美国人要健康得多。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可能我们的胆固醇测量方法(我们如何收集并分析血样)存在缺陷。为了遵循波普尔原理来试图否定自己的假设,我采用其他测量方法并针对3个不同地点(康奈尔、北京和伦敦)重复这些分析,以此竭力否定自己的发现。所有的分析结果反映了相同的低胆固醇水平。现在我们不得不搞清这个显而易见的矛盾:最健康的中国人的胆固醇水平在美国被认为太低而存在危险。
进一步的检查表明,对中国人来说,每分升88~165毫克的范围,相当于美国人每分升155~274毫克的范围,这种较低的胆固醇水平对多种癌症和相关的严重疾病有着较强的预防作用。在美国人口中,我们并没有观察到中国人口所显示出的低胆固醇和健康之间的关联,这是因为美国人几乎不可能有那么低的胆固醇水平。对中国人展开的观察研究显示,每分升88毫克的胆固醇水平比每分升155毫克更健康,我们简直不可能从对美国人口的研究中获得这样的发现。
另一个令我偏离“常识”的离群值的例子是我们有关酪蛋白的发现。十几年来,酪蛋白一直是一种备受赞美和尊崇的蛋白质,可是它居然能够诱发癌症,并且这一研究结果可信度很高。奇怪的是,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人想要说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酪蛋白是迄今为止人们认定的与癌症关系最密切的化学致癌物。异端发现的影响,就像中国农村居民极低的血液胆固醇水平,一直处在许多铰链之中,在此基础上,我们打开了对营养和健康关系认知的新大门。
有趣的是,酪蛋白对癌症的影响被证明太过离谱,以至于首次发现这一影响的印度研究员都不想承认自己的发现。他们的研究比我们要有限得多。他们不愿意关注酪蛋白诱发癌症的长期影响,而是关注酪蛋白在快速缓解大量单剂量致癌物毒性作用时的效果——这两种作用截然相反(我们将在第二部分深入剖析这两种影响)。换句话说,他们通过关注一个不重要的细节远远避开了研究的重大影响。
我很高兴我没有偏离正轨,因为我注意到关注那些可能被忽视或丢弃的意料之外的观察结果通常会有回报,特别是当这些观察亟待解释的时候。当我随着一些离群观察值进入模糊领域,我童年和早期研究生涯支持动物蛋白的信仰(并最终与之背道而驰)开始慢慢动摇——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了。当这些异端邪说累积得足够多的时候,它们之中相互关联的部分开始浮现。这些相互关联的部分变成原理,然后成为成熟的理论,替换了范式,从而改变了我的世界观。研究异端邪说的回报或许会令人振奋,或许值得我付出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代价。
事实上,当我开始讲述我那些超越常规的研究发现时,我的社会和专业同时发生了改变。怀疑论和沉默,委婉地说,变得更加平常。但是回报一直是丰厚的,我毫不犹豫地鼓励年轻人追随我的脚步。(当他们问我,正如一些人曾做过的那样,他们怎样才能做到我所做到的事情,我告诉他们非常简单,不要害怕提出问题,即使所有人告诉你这是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当需要捍卫自己的观点时,就做好准备运用最棒的科学和逻辑。)
当被认定为处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下,超越范式的看法可能会让人获益良多,并且这种方法还具有一定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奇怪的意料之外的研究结果联系在一起,开始为我塑造一个新的世界观。并且它们看起来越来越正确。如果这世界观触及生死问题,个人热情就会出现,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这时这些范式的界线将变得清晰并且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既然你已经了解了我与僵化范式的邂逅,那么现在是时候与大家分享我从这些问题中所学到的东西了。它们与盛行的科学和医学范式有关。
这些最初的偏离值变成异端的问题,从这些问题又得到了异端的答案,一系列异端的原理就这么产生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曾试图将这些原理应用到一个范式中,但是这个范式太大以至于我没能发现它。只有当我开始质疑科学方法机制本身时,我才跳出这个最大的、限制力最强的、最为狡猾的范式:简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