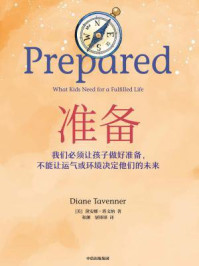我对我的这次旅行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同样地,我也会对自己初次进城的情况进行详细介绍。这样做是为了便于你在脑海中把这种不太有希望的开始,和我以后成为这个城市的重要人物的远景作一个对比。因为我所有的好衣服要等着从海道运来,所以我就一直穿着工作服。长途跋涉使得我浑身都是脏兮兮的,口袋里装满了衬衫和袜子。我没有一个熟人,也不知道去哪里落脚;因为远行、划船和缺乏休息而感到十分疲倦。我感到饥饿难耐,但是我所有现金只有一荷兰盾和一个先令的铜币。我把铜币付给船老板作为船钱,他起先不肯收,因为我划了船,但我坚持要他收下。一个人很穷的时候,他可能比有钱的时候更慷慨,也许这是因为害怕别人认为他小气。
进城后我走到大街上,四处打量,在市场附近看到了一个手拿面包的男孩。我以前经常拿面包当饭吃,当问完他在哪里可以买到面包后,我立即走到他指给我看的那个面包店——就在第二街那里。我想要和波士顿那里一样的硬面包,但是在费城好像没有这样的做法;于是我又打算要一个三便士的面包,但是也没有。由于我没有考虑到或者说不知道两地货币价值有所不同,费城的东西相当便宜,所以最后我便要他们给我价值 3 便士的任何面包,于是我得到了三个很大的面包——我对他给我的面包数量大为吃惊,但还是接了下来。由于口袋里面没有地方放,所以我就一只胳膊下夹一个,嘴巴里面吃着另外一个。我就这个样子从市场路到了第四大街,经过了我未来岳父里德先生的门口。我未来的妻子——她这个时候正好在门口,她看到了我,觉得我的样子非常滑稽可笑,事实上我确实就是那个样子。转了一个弯后,我来到了板栗街和胡桃街的一段,一路上我都吃着我那面包。又转了个弯以后,我发现自己回到了市场街我们的船所停靠的码头附近,我在那里喝了点河水。由于我吃了一个面包后就饱了,所以就把剩下的两个面包给了一个妇女和她的孩子。她们是和我一起坐船来的,现在正准备继续她们的行程。
吃过饭后,我又到大街去溜达了。街上衣冠楚楚的人多了起来,他们都朝着一个方向走去。于是我便加入他们的队伍,进入了市场附近的教友会的大教堂里面。我坐在他们中间,四处观望,没有发现有人发表演讲。由于前天晚上缺乏睡眠和过度劳累,我十分困倦,于是就睡着了,一直睡到会议结束。散会时,一个好心人把我叫醒了。这就是我第一次在费城进去过或者说睡过觉的房子。
我向河边走去,一路上我都格外关注人们的脸庞,直到遇见了一个我觉得脸庞和善的教友会教徒。我问他外地人可以到哪里住宿。那时我们恰巧在“三个水手”的店牌附近。他回答:“这里就可以!这里就是接待外来旅客的地方,但这个地方的声誉不好,你要是愿意的话就跟我走,我可以带你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他把我带到了水街的克鲁克旅馆。我在那吃了顿饭。店主趁我吃饭的时候问了我几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可能因为他觉得从年龄和外表来看我像个逃犯。
吃过饭以后,睡意又袭来了。店主把我领到我的铺位那里,我衣服都没脱就睡下了,一直睡到晚上 6 点被叫醒去吃晚饭。吃过饭,我又早早地去睡觉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我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整洁一点儿,然后去了安德鲁·布雷福德印刷厂。在那个地方,我碰到了那个厂主的父亲,就是我在纽约认识的那个老人家。老人家是骑马来的,他比我先到费城。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他儿子很客气地招待了我,并且请我吃了早餐。但他告诉我,他的厂子现在不缺人手,因为他最近刚招到了一个人。不过,镇上刚开了一家印刷所,店主叫凯默,他可能会要我;如果不行的话,他欢迎我住在他家,并会给我点零活干干,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老人家说他愿意和我一起去凯默老板那里。我们一见到印刷店的老板,布雷福德就对他说:“朋友啊,我带来了个年轻的印刷匠给你,你也许会需要他的。”凯默问了我一些问题,给了我一副字盘,观察我如何操作。之后,他告诉我,会尽快叫我来上班,尽管他现在没有事情让我做。随后就和布雷福德攀谈起来,他把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老人布雷福德当做来自镇上的对他充满善意的人,讲了目前的经营情况和对未来的计划。布雷福德没有告诉他自己是镇上另一家印刷所老板的父亲。当凯默说他不久就可以得到本城绝大多数生意的时候,布雷福德巧妙地问了几个问题并做出对凯默的话很怀疑的样子,就这样,很容易地就套出了凯默的靠山是谁,打算采用什么方式开展工作。我站在旁边听到了他们所有的谈话,立即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一个是后生晚辈,一个是老滑头。布雷福德把我留给凯默就走了。当我告诉凯默布雷福德是谁的时候,他大吃一惊。
我发现,凯默的印刷厂里只有一台老式的印刷机和一套旧的小号英文铅字。这个时候他正在用那套铅字排印前面讲到的阿奎那·罗斯的《挽歌》。罗斯是个聪慧的年轻人,具有高尚的品格,在镇上很受人尊重,他既是议会秘书,也是个不错的诗人。凯默自己也写诗,但是水平一般。或许不应该称他在写诗,他只是把自己的思想直接用铅字排印出来而已。由于没有稿子,只有两盘活铅字,而《挽歌》又有可能需要所有的铅字,所以没有人可以帮上他的忙。我努力把他的印刷机整理了一下——那个机器他还没有用过,他对那个东西一窍不通。这样那个机器就可以印刷了,我答应等他那个《挽歌》一排好我就来印刷。我回到了布雷福德的家里,他暂时给我安排了些杂活干,我在那里吃住。几天以后,凯默叫人找我回去印刷《挽歌》。现在,他又弄到了另外两只活字盘,并且有本册子要重印。他就叫我来干活了。
我发现这两位印刷店的老板对印刷业并不在行。布雷福德并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基本上是个文盲。至于凯默,他倒有些学问,但他只会排字而不懂得印刷。他是法国先知派的教徒,可以假装和教派的同仁一样热情和激动。那个时候,他并不是特别信仰某一宗教,他每样都信一点,以便随机应变。他对人情世故完全不懂。后来,我还发现,在他的性格里有种无赖气。他不喜欢我在他那里工作却在布雷福德那里住。事实上,他有间屋子,但却没有家具,所以他没有办法安排我住宿,但他安排我住在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里德先生处。这个时候,我的衣物已经运过来了,我把自己收拾了一下,在里德小姐眼中,我的外表比她第一次看见我在街上吃面包的时候体面多了。
我现在开始和镇上的一些年轻人有了来往。那都是些喜欢读书的年轻人,晚上和他们一起度过是很开心的。由于我的勤劳和节俭,我有了一点积蓄。我生活得很开心,我尽量去忘掉波士顿,希望没有人会知道我住在这里。当然,我的朋友柯林斯除外,我在写信给他的时候叫他替我保密。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回到了波士顿,这比我原来计划的时间早多了。我有一个叫罗伯特·霍姆斯的姐夫,他是一艘单桅帆船的船长,在波士顿和特拉华之间开船做生意。他在离费城 40 英里的纽卡斯尔听说了我所在的地方,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十分有诚意地劝我回去。他说在我突然离开波士顿出走以后,我波士顿的朋友都很挂念我,他还向我保证了大家对我是满怀善意的,如果我回去的话,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我写了封回信给他,感谢他的劝告,并详细告诉了他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这样他就不会认为我离开波士顿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不可理喻了。
威廉·基思爵士是这个州的州长,他那个时候正在纽卡斯尔。当罗伯特·霍姆斯船长,也就是我的姐夫接到我的信的时候,他正和州长在一起。他同威廉·基思爵士谈起了我,还把我的信递给他看。州长看了我的信,当姐夫告诉他我的年龄时,他似乎很吃惊。他说,我看起来是个前程似锦的年轻人,应该给予鼓励;他说费城的印刷业水平很低,如果我在费城开家印刷厂肯定可以成功;他还说,他愿意为我招揽公家的生意,并在其他方面就他能力所及帮助我。这些话是姐夫后来在波士顿告诉我的,但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有一天,当我和凯默在窗旁做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穿着考究的州长和一位绅士(后来我知道那是纽卡斯尔的弗兰奇上校)穿过街道,径直向印刷所而来,还听到了他们敲门的声音。
凯默以为是找他的,连忙匆匆下楼。但是州长却向他打听我的事情,并且走上楼来,用一种我过去并不很习惯的礼节对我夸奖了一通,并说他希望认识我。他还责怪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为什么不去见他。他还要把我带去酒馆,他说他正要和弗兰奇上校一起去那里品尝一下上好的白葡萄酒。我简直受宠若惊,凯默却呆若木鸡。但我还是和州长、弗兰奇上校一道去了酒馆,就在第三街街角那里。我们边喝边谈,他建议我创办自己的印刷厂,并说成功的希望很大。他和弗兰奇上校都向我保证,要用他们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为我招揽军政两方面的生意。当我说我不知道我父亲在这方面会不会给予我帮助的时候,威廉·基思爵士说他会给我父亲写封信,在信里他会阐述我计划的优势所在,他相信他一定可以说服我父亲。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将带着他写给父亲的信,搭乘第一班船回波士顿。在这之前,这件事情还要保密,我像往常一样回到凯默那里工作。州长现在经常邀请我一起吃饭,用一种异常和蔼、随便、友好的态度和我交谈,那对我而言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大概在 1724 年 4 月底,有一艘开往波士顿的船来到费城。我借口回家去看我的朋友而离开了凯默。州长给了我一封很厚的信,他在信中对我父亲说了很多夸奖我的话,并极力推荐我在费城开办印刷厂,说这一事业必能使我有个远大前程。我们的船在开入海湾的时候碰上了暗礁,船漏水了。外面波涛汹涌,我们得不停地抽水,我也加入其中。经过了大概两个星期,我们平安地抵达了波士顿。我离开家已经有七个月了,我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霍姆斯还没有回来,也没有写信谈我的情况。我的不期而归让全家大吃一惊,所有的人都为我的归来感到十分高兴,对我热烈欢迎,只有哥哥除外。我去他的印刷所看他,那个时候我比在他那儿工作的时候穿得更考究——一身笔挺时髦的西装,口袋里还挂了一只表,身上还有差不多 5 英镑银币。哥哥勉强接待了我,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就又去做他的事情了。
印刷所里的工人都好奇地问我到哪里去了,那个地方怎么样,我喜欢不喜欢那个地方,等等。我对费城大加赞扬,说自己在那里过得很开心,并表示了我将回到那个地方的强烈愿望。他们之中有人问那个地方的钱是什么样子的,我掏出一把银币来,在他们面前展开。这种银币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因为波士顿只用纸币。然后我逮住一个机会让他们看我的表,最后,我送了他们一点钱买酒喝就走了。那个时候,哥哥的脸色还是很阴沉,他表现得闷闷不乐。我的这次拜访让他很不高兴,尽管母亲后来劝我们重归于好,希望我们以后像兄弟那样和睦相处,不过哥哥说我在其他人面前侮辱他,他决不会忘记也决不会原谅我。但是,在这一点上,他误会了我。
当父亲接到州长的信的时候,他显然很吃惊。但他好几天都没有向我提起这件事情。当霍姆斯姐夫回来的时候,父亲把这封信给他看,问他是否知道威廉·基思爵士,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父亲还说威廉·基思一定是个考虑不周的人,他竟然让一个还要三年才成年的小孩子去创业。霍姆斯姐夫说他很赞成这个计划,但我父亲明白那个计划并不恰当,他最终还是断然拒绝了。随后父亲写了封措辞委婉的信给威廉·基思爵士,感谢他对我的赞助和好意,但他拒绝资助我建立印刷厂,因为他觉得我还太年轻,他不能相信我能管理这样一个需要如此巨额资金才能建立的重要企业。
我的朋友柯林斯那个时候是邮局的一个办事员,他听了我在新地方的事情很高兴,于是也决定去那里。当我还在等父亲的决定的时候,他已先走一步。他从陆路去了罗德岛。他把他大量的数学和自然哲学的书留了下来,叫我带着一起到纽约去。他说他会在那里等我。
尽管父亲不赞成威廉·基思爵士的建议,但他很高兴我能从当地如此有声望的人那里得到这样一封赞赏有加的信。他对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凭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打扮得这样体面感到很欣慰。因此,当他看到我和哥哥不可能在一起做事的时候,就同意我返回费城。同时,父亲提醒我要尊重那里的人,尽力得到人们的尊重,不要去毁谤和诋毁别人——他认为我这方面的倾向很严重。他还告诉我要勤奋工作,节俭地生活,这样到21 岁的时候就可以有积蓄开办自己的印刷厂了。到了那个时候,如果资金有所不足,他会帮助我的。这就是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全部,还有标志着父亲和母亲爱子之心的一些小礼物。带着他们的祝福和赞许,我登上了前去纽约的船。
我们乘坐的单桅帆船停靠在罗德岛的新港后,我去拜访了约翰哥哥。他已经结婚并在那里住了几年了。他对我很热情,一直对我爱护有加。他有位朋友叫弗农,有人欠弗农 35 英镑,欠钱的人就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哥哥希望我代弗农收这笔债,并代为保管,直到我接到通知——告诉我怎么汇给他为止。然后,哥哥就给了我一张单子。这件事情后来带给我很多不安。
在新港,又有很多前往纽约的乘客登上了船。其中有两位年轻的女人和一位严肃但精明、像管家婆似的教友会妇人,还有她们的仆人。我对那妇人很有礼貌,乐意为她帮点小忙。我想这给她留下了好印象,因此,当她看到我和两个年轻女子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火热,她们好像也在鼓励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她就把我拉到一边说:“年轻人,我很担心你。你没有朋友在身边,好像对这个世道了解也不深,不知道一些人对年轻人所设的圈套。相信我,这两个女子不是什么好人,这我可以从她们的举止看出来。如果你不当心的话,她们就会陷害你。你根本不认识她们,我劝你还是不要和她们来往。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的安全,是出于好意的。”我开始并不相信那两个年轻女子如妇人说的那样坏。于是妇人便提点了我一些她所观察到的她们的可疑的言行和举止——这些我都没有注意到。后来我意识到,妇人说的都是对的。我感谢她对我的忠告,并且表示会按她讲的去做。
当船到达纽约的时候,那两个女子邀请我去拜访她们,并告诉了我她们的住处,我没有答应。幸亏我没有去,第二天,船主就丢了一把银勺子和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从舱房里被偷走的。船主知道那两个女人是妓女,就申请了搜查令去搜她们的住所,结果找到了失窃的东西,小偷也受到了处罚。这次,船在途中幸运地避开了暗礁,但在我看来,和航船避开暗礁相比,我能避开这两个妓女对我的意义更为重大。
在纽约,我找到了柯林斯,他比我先到几天。我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是好朋友。我们经常一块儿读书,但他看书和学习的时间比我多,他还是个数学天才,远比我厉害。当我还在波士顿的时候,我有空就和他待在一起聊天。他从来不喝酒,头脑清醒,还相当勤奋,深得一些牧师和绅士的尊敬。他看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但是,在我离开波士顿的日子里,他染上了喝白兰地的恶习。我从他本人和其他人那里得知,当他到纽约以后就天天喝得醉醺醺的,举止行动十分古怪。他还学会了赌博,输光了自己的钱,以至于我不得不替他付房租和担负他到费城的路费,以及他在费城的生活费,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负担。
那个时候,纽约的州长是伯内特(伯内特主教的儿子),他听船长说他的乘客中有个年轻人带了很多书籍,他就要求见见我。这样我就去见他了。如果柯林斯没有喝醉的话,我会带他一起去的。州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领我参观了他的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真大啊。我们针对书和作者谈了很多,这使我获得了州长的青睐。对我这样一个穷小子来说,这是十分让人激动的事。
我们继续前往费城。在路上,我收到了别人欠弗农的那笔钱。如果没有那笔钱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完成我们的旅程的。柯林斯希望在某地当个会计,不知道别人是从他的呼吸还是从他的举止中得知了他是个酒鬼的事实,所以尽管他有推荐信,但还是没有找到工作。他继续和我一起吃住,并由我付账。当他知道我拿到弗农的钱以后,他就不断地向我借钱。他承诺等他一找到工作就还钱给我。最后,他借走了那么多钱,我感到非常愁苦,我担心万一人家叫我汇钱过去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他继续酗酒,为这件事情我们经常吵架。因为只要有一点醉,他就会变得很暴躁。有一次,我们和几个年轻人在特拉华州一块划船玩儿,但轮到他划时,他却不肯划。他说:“你们得划船把我送到家里去。”我说:“我们决不会替你划的。”他就说:“你们必须得划,要不就在水上过夜。你们看着办吧!”“让我们划吧,这不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吗?”其他人说。但是他的行为让我很生气,我坚决不同意。所以他发誓说必须要我划,要不然就把我扔到河里去。然后他就站到横板上,看着我。当他跑过来抓我的时候,我伸手抓住他的腿,然后站起来,把他头朝下扔到水里去了。我知道他水性很好,所以对此并未在意。在他靠近船帮的时候,我们连着划了几下,让他没有办法靠近船。每当他靠近的时候,我们就一边问他是否同意划船,一边连着划几下让船从他身边滑过。他气愤极了,越发地固执,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划船。到了最后,看到他开始显露出疲态,我们便把他捞了上来。晚上我们把浑身湿透的他送回了家。打这以后,我们之间难得有一句好话。后来,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船长受一个叫巴巴多斯的绅士的委托,要给这位绅士的儿子找一位老师,他偶然碰到了柯林斯,就答应送柯林斯去巴巴多斯那里。后来科林斯就走了,走之前他承诺一领到钱就汇给我以还清债务。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没有他的音信。
动用弗农的钱是我一生中所犯下的重大错误之一。这件事情表明,父亲认为我还年轻,不能管理重要企业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当威廉·基思爵士读到我父亲给他的信的时候,他说我父亲太谨慎了。他说,对人不能一概而论,谨慎不一定和年龄相生相伴,年轻人并不一定就不谨慎。“既然他不支持你,”威廉说,“那就由我来亲自帮助你吧。给我一张你需要从英国置办的东西的清单,我去为你买。可以等你以后有能力再还我。我很期望本地能有一家优秀的印刷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很诚恳,我丝毫不怀疑他说的话。迄今为止我一直把想在费城开印刷厂的秘密深埋心底,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如果当时有某个深知州长为人的朋友知道我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话,肯定会告诫我州长这个人并不可靠。但我才听别人说起州长这个人从来都是空许愿而不去兑现的。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主动要求他帮助我,我怎么能认为他的慷慨帮助是没有诚意的呢?我相信,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我给了他一份开办一个小印刷厂所需物品的清单。照我估计,购置这些大概需要 100 英镑。他很高兴,但是询问我,要是我能够去英国亲自挑选铅字并检查各种机器的部件是不是更好。“而且,”他又说,“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结识一些人,为日后卖书和文具的生意开拓渠道。”我认为这样做是有益处的,就同意了州长的建议。“那么,”他说,“做好准备坐安尼斯号去。”那艘船是那个时候唯一的一艘一年一次往来于伦敦和费城的船只。但那时离安尼斯号启程的日子还有几个月,于是我便继续在凯默那里做事。同时,心中为柯林斯借钱的事情焦虑不安,每天担心弗农叫我汇钱过去。不过,这件事几年之内都没有发生。
我想我还忘了告诉你,当我第一次坐船从波士顿去费城的时候,我们的船停靠在布来克岛。旅客们开始捉鳕鱼吃,并且捉了很多。迄今为止,我坚守不吃荤食的信条。这种时候,我和我的导师特里昂站在一条战线上,他认为捉一条鱼就等于杀一次生。因为鱼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伤害我们,所以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杀害它们。这些似乎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这之前,我是很喜欢吃鱼的,当热气腾腾的鱼刚从炸锅里拿出来的时候,闻起来真香啊!我在爱好和原则之间犹豫了好长时间,直到我想起,有人在端上来的鱼的胃里发现了小鱼。那个时候我想:“既然你可以吃小鱼,我为什么不能吃你呢?”因此,我就痛快地吃了一顿鳕鱼。从那以后,我又开始和别人一样吃荤了,只是偶尔吃素食。做一个有理智的生物是如此方便,因为你总是可以找到或者建构一个理由去做你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情。
凯默和我相处得很不错,并且我们总能就一些事达成共识,因为他并不知道我打算独自开办印刷厂的事情。他一直保持着往日浓厚的热情并且热衷于辩论。因此,我们经常在一起辩论。我常使用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术,先选用一些看起来显然离我们的辩题很远的问题,之后渐渐地把他引入矛盾和困境之中。他经常陷入我用这种方法构建的圈套。到最后,连他的谨慎都变得有些滑稽了,因为他总是先问:“你到底想干什么?”然后再回答我那些再普通不过的问题。但是,这却使他对我的辩论才能有了很高的评价,因此他很认真地提议我和他一起建立一个新的教派。他负责布道,我则负责和对手论辩。不过,当他向我解释教条的时候,我发现其中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正是我所反对的,除非我也可以加入点自己的意见或者介绍下我的一些看法。
凯默留着长长的胡子,因为摩西法典里说“不许损毁胡须一角”。也因此才把安息日定在星期六,这两点对他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两点我都不喜欢。不过在他答应不吃荤食的情况下,我可以同意他的那两点。“我怀疑”,他说,“那样的话,身体会吃不消的。”我向他保证,身体可以受得了,而且那样对身体还有更多的好处。他平常吃得很多,因此我想,如果他半饿半饱一定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我能陪他的话,他可以试一试。我同意了,并且坚持了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饮食固定由一个邻居妇人送来。她从我这里拿走一份 40 种菜肴的菜单,按照不同的时间给我们送来,在这些菜单上没有鱼肉也没有鸡鸭。这种理念那个时候非常适合我,因为那样很便宜,每周每人不会超过 18 个便士。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连续好几次吃四旬斋都严格按照规则来办,突然从吃平常饭转为吃斋饭,或从吃斋饭变成吃平常饭,这种变换没有给我带来一点不适应。因此,我就想,那种所谓的改变要循序渐进的建议没有一点道理。我快乐地过着我的日子,但是可怜的凯默却感到难以忍受,他已经厌倦了这个计划。他一直渴望大吃一顿,所以他就叫了一份烤猪,并邀请我和他的两个女性朋友跟他一起去吃。但烤猪上得太快了,他抵制不了那个诱惑,在我们到之前就把它吃光了。
这段时间,我连续向里德小姐求了几次爱。我对她很是倾慕,并且也有理由相信她对我也有相同的情感。但是,她母亲认为不应操之过急,因为我们都很年轻——才 18 岁多一点。况且,我还要进行长途旅行。如果要结婚的话,还是等我回来以后——当我像我所期待的那样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以后,那样会更合适一些。也许,她认为我的期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十拿九稳。
这个时候,我主要的朋友是查尔斯·奥斯本、约瑟夫·沃森和詹姆斯·拉尔夫,他们都是喜欢读书的人。前两个人是镇上著名的公证人查尔斯·布罗格顿的书记员,后面那个是一位商店职员。沃森是一个十分诚实正直、聪明的年轻人。其他两个人的宗教信仰观念很淡薄,特别是拉尔夫。拉尔夫就像柯林斯那样,老是不能让我安生,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奥斯本则是个聪明坦率的人,对朋友真诚友爱,但是,在文学方面他太挑剔了。拉尔夫仪表堂堂,人很聪明,口才相当好,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这样好口才的人。这两个人都很喜欢诗歌,并不时写些小作品练笔。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四个人经常一起到斯古尔克河附近的小树林里快活地散步,在那里我们轮流朗诵我们的作品,并谈论我们读过的作品。
拉尔夫喜欢研究诗歌,他从不怀疑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诗人,并且会因此而致富。他认为即使是最优秀的诗人刚开始写诗的时候,也会像他那样有很多瑕疵。奥斯本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他确定拉尔夫没有写诗的天赋,劝告他不要好高骛远,而应该把心思都放到他的本行上去。拉尔夫虽然没有天赋,但是凭着他的勤奋和本分,他可以先做代理商,然后逐渐地自己创业。我很赞成偶尔写点诗娱乐一下的观点,同时还可以改进自己的语言风格,除此之外,我则没有别的想法。
为了提高我们的文学水平,大家建议,下次聚会的时候每人拿出一篇自己的作品,供彼此观摩、批评、改正。由于我们的目的只在于提高语言使用和表达方式,所以大家一致赞成改写赞美诗的第 18 篇,这是一篇描写上帝降临的诗歌。当聚会的日子临近的时候,拉尔夫来找我,告诉我他的诗已经改好了,我告诉他,由于我一直没有空,也没有兴趣,所以我还没有写。然后,他让我看了他的诗,并征求我的意见。我读了一下,对其十分赞赏,在我看来,那真是一首好诗。“现在,”他说,“奥斯本经常说我的作品没有任何长处,由于嫉妒,他总是会把它批评得体无完肤。他对你并不嫉妒。因此,我希望你把这首诗拿去,就说是你写的。我则会装作因为没有时间而没写的样子。我们看看他会说什么。”我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立即重抄了一遍,这样看起来就是我写的了。
聚会的时间很快到了。最先读到的是沃森的作品,里面有些好句,但相比之下瑕疵更多。接着读奥斯本的诗,确实比沃森写的强多了。拉尔夫对它们作了公正的评论——既批评了它们的不足之处,也称赞了它们的优点所在。然后他说他自己没来得及写。轮到我读时,我表现出很扭捏的样子,好像在请求他们放我一马,还摆出时间不够等借口,但他们都不接受我的理由,一定要我把诗拿出来。所以,我就把拉尔夫的诗拿出来读了一遍,并且重复了一遍。沃森和奥斯本甘拜下风,对之称赞不已。拉尔夫对之作了些批评,并建议作一些修改,但我却对之进行了辩护。奥斯本这个时候又跳出来反对拉尔夫,说拉尔夫的评论和他的诗一样好不了多少。于是拉尔夫就不再争辩。在他们一起回家的路上,奥斯本表达了他仍然想对我的诗表示赞赏的愿望,并且说他当着我的面不好这样说,以免我觉得他在奉承我。“但是,谁能想到”,他说,“富兰克林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来,这样绘声绘色,刚强有力,热情奔放。甚至写得比原诗还好,他平常讲话的时候好像并不会用词,笨嘴拙舌的。天啊,他的诗写的太好了!”当我们第二次聚会的时候,拉尔夫道破了这件事的玄机,大家笑了奥斯本一阵子。
这件事情坚定了拉尔夫做一名诗人的决心。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阻止他,但是没有效果,一直到波普的出现为止。不过拉尔夫后来成为了一名非常出色的散文家,我以后还会谈到他。对于其他两个人,以后很可能不会再有机会被提到了——沃森几年以后就死在了我的怀里。我难过极了,他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奥斯本去了西印度群岛,在那里,他成了很有名的律师,赚到了很多钱,但他也在事业鼎盛的时候去世了。我们两个曾经有过庄严的约定,那就是如果谁先死去,如果可能,他应该对对方作个友情访问,告诉对方他在那个世界过得怎么样,但奥斯本却没有遵守他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