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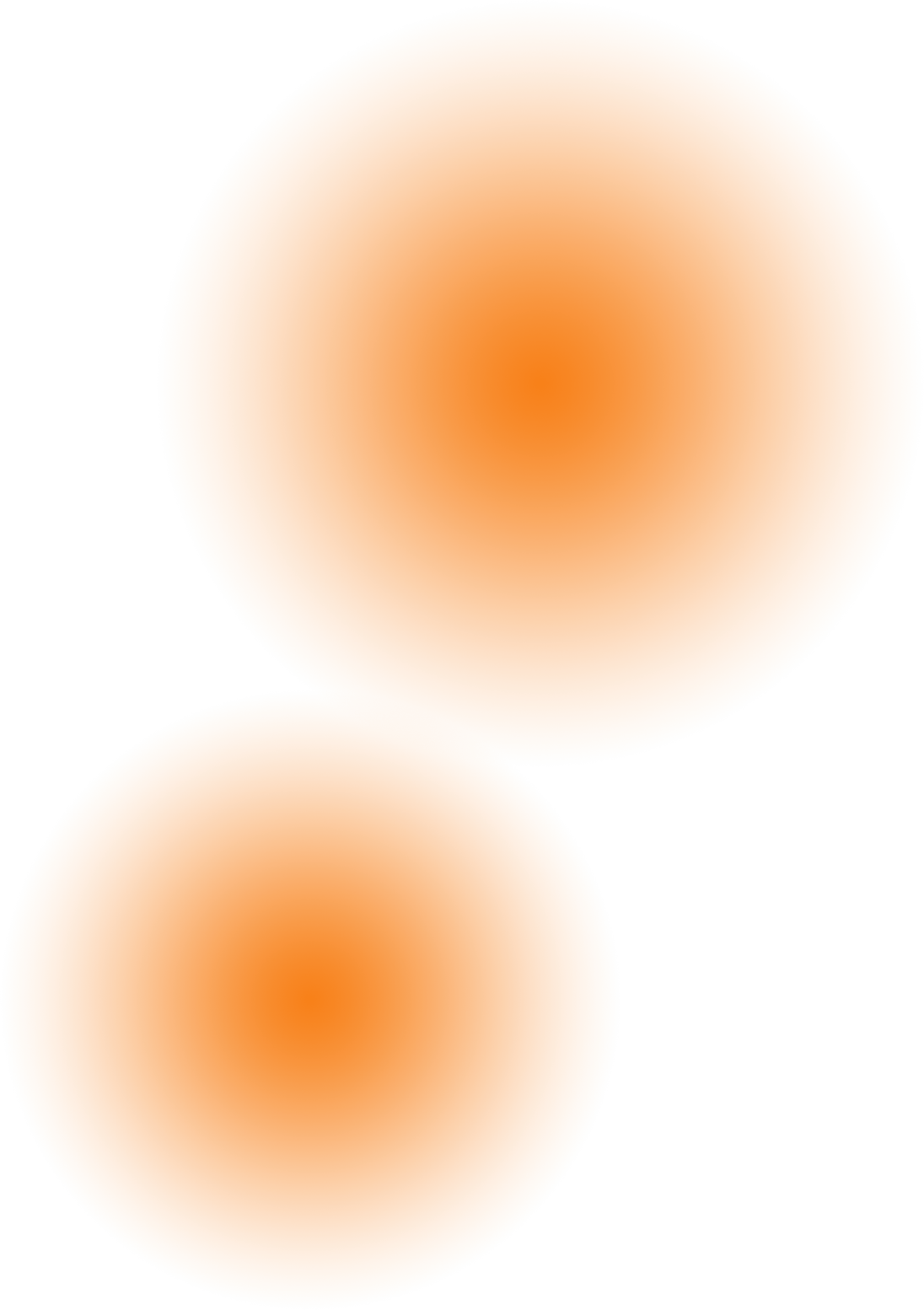
 爱是什么
爱是什么
我拥有了语言的钥匙后,总是想尽快地运用它,一般说来,有听力的孩子学习语言是很快的,因为他们可以轻松地明白别人说出来的话,并且加以模仿。但是耳聋的孩子却必须经历无数的痛苦煎熬,慢慢才能学会,但无论如何艰辛,结果总是无比美妙。我从每一件东西的名称慢慢学起,由断断续续地发音,进展到可以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进行无限美妙的想象。
起初,老师告诉我一些新鲜事,我很少提问题,我脑子里的概念模模糊糊的,而且掌握的词汇也很少。而随着知识的增长,我的单词量越来越大,我问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常常是就一个问题一再地发问,一再地思索,一定要探个究竟。有时从学到的一个新词中,常常联想到自己的种种经历。
还记得有一天早晨,我第一次问莎莉文小姐“爱”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知道的字还不很多,我在花园里摘了几朵紫罗兰拿给我的老师。她想吻我,可我那时除了母亲外,不喜欢别人吻我,莎莉文小姐用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我,在我手上拼写出“我爱海伦”几个字。
“爱是什么?”我问她,那时候我识字还不多。
莎莉文小姐把我搂得紧了一些,用手指着我的心说:“爱在这里。”我第一次感觉到心脏的跳动,但对老师的话和动作依然迷惑不解,因为当时除能触摸到的东西外,我几乎什么都不懂。
我闻了闻她手中的紫罗兰,一半儿用文字,一半儿用手势问道:“爱就是花的香味儿吗?”
老师回答说:“不是。”
我又好好地想了想。此时,温暖的阳光正洒落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爱吧?”我指着阳光射来的方向问:“爱就是太阳吧?”
在我看来,太阳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了,万物因为它的照耀才得以茁壮生长。但莎莉文小姐总是摇头,我又困惑又失望,也很奇怪,为什么她不明明白白地告诉我,爱到底是什么呢?
一两天过后,我正用线把大小不同的珠子穿起来,按两个大的、三个小的这样的顺序,结果总是弄错。莎莉文小姐在一旁耐心地为我纠正错误,弄到最后,我发现有一大段穿错了,于是,我用心想着,到底应该怎样才能把这些珠子穿好。莎莉文小姐碰碰我的额头,使劲地拼写出了“想”这个字。
灵光一闪,我顿时明白了这个词指的就是在我头脑里正进行的活动。于是,我第一次领悟了抽象的概念。
我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坐了好半天,想的不是放在膝上的珠子,而是竭力想根据这一新概念理解“爱”的意思。那天,太阳躲到云彩的后面,下着一阵阵的小雨,但突然间光彩夺目的太阳从南面露出笑脸。
我又问莎莉文小姐:“爱难道不像太阳吗?”
她回答说:“爱有点儿像太阳没出来前天上的云。”
她似乎意识到我仍然是困惑的,于是又用更浅显、但当时我依然无法理解的话解释说:“你摸不到云彩,但你能感觉到雨水,你也知道,在经过一天酷热的日晒之后,要是花儿和大地能得到雨水会是多么高兴呀!爱也是摸不着的,但你却能感到她带来的甜蜜,没有爱,你就不快活,也不想玩了。”
刹那,我领悟了其中的道理——感到仿佛有无数条无形的绳索连接着我与他人的心灵,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千丝万缕的情感吧!
莎莉文小姐从一开始教我,就像对待其他耳朵不聋的孩子那样,总是跟我对话,唯一的区别是,她把一句句话拼写在我手上,而不是用嘴说。当我找不到单词或习惯用语来表达思想时,她便提供给我,有时我答不上来的,她甚至提示我应该回答的话。
这种学习过程持续了多年,一个耳聋的孩子不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掌握最简单的生活用语,更别说立即加以运用了。正常的孩子学说话是靠反复模仿,听到大人说话,大脑跟着进行思考,联想到谈话的内容,同时学会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耳聋的孩子是无法进行这个过程的。莎莉文小姐意识到这一点,用各种方法来弥补我的缺陷。她尽最大可能反反复复地、一字一句地重复着一些日常用语,告诉我怎样和别人交谈。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主动张口和别人交谈,又过了更长一段时间,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听不见或看不见的人是很难体会到交谈的愉悦的,而既听不见又看不见的人在与人交流中遇到的困难就更难以想象了,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分辨谈话者语调的高低升降、语气的强弱轻重变化,也就无从知晓其中所饱含的意义,同时,他们又看不见对方脸上的表情,无法从中觉察出其内心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