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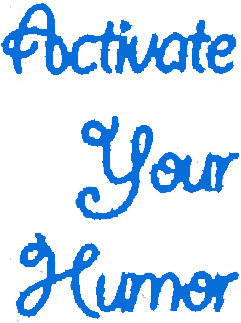
 智慧等于幽默
智慧等于幽默
幽默是一切智慧的超越。有人认为“幽默是能飞的智慧”。钱仁康说:“幽默是一切智慧的光芒,照耀在古今哲人的灵性中间。凡有幽默素养的人,都是聪敏颖悟的。”林语堂说:“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生产出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花,因为幽默没有其他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我国古人也把幽默和智慧看得密不可分,如《史记》中有“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我们先来比较两个有关幽默与智慧的例子。
据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回忆,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政界要人兹比格曾在自己家中设宴招待他。席间,兹比格评论道:“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于别人。”邓小平回答道:“我们这样说吧,”他停了一停,然后说,“在东亚,中国菜最好;在欧洲,法国菜最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头子之一戈林,曾问一名瑞士军官:“你们有多少人可以和我们作战?”
“五十万!”
戈林说:“哈哈!如果我百万大军压境,你们就无可奈何了。”
“不,先生,那正好一枪俩。”
例一可称得上机智的好例子。兹比格的评论实际上是指责中国人和法国人一样,自傲自大。弦外之音,还有一层深意:如果你们中国人和法国人到一起,那又将会怎样呢?话虽不多,却把对方逼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回答:“不对”,虽然可以回击兹比格傲慢的批评,但同时却要带来自己否定中国文明高于别人的后果。如果回答:“是的”,虽然肯定了中国文明高于别人,却又难以解答中国人和法国人碰到一起究竟谁更高的问题。可以设想,一般人如果遇到这种场面,确实够为难的。而邓小平则先以“我们这样说吧,”为开头,对兹比格的话不作正面回答,轻轻一转,就避开了兹比格的话锋。言外之意是,我既不同意你的看法,又不反对你的看法,我有另外的看法。仅此一句,就使说话者的自得立即消逝,而使自己将可能出现的被动变为主动。紧接着,邓小平又一停,逼着听话者急于想知道他到底想讲什么,不仅牵住了听者的注意力,而且加重了即将说出的后半句的分量,然后说:“在东亚,中国菜最好;在欧洲,法国菜最好”;答话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特别是由于幽默语所产生的时间效应,巧妙地把中国人和法国人分开,根本不承认二者具有同一特点,这就使兹比格一概而论的武断批评不能成立。并用“在东亚,中国菜最好;在欧洲,法国菜最好”这样一个公认的、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委婉而又有力地证明:中国和法国的文明,确实有公认的高于别人之处。邓小平用自己的机智巧妙地回答了兹比格的难题,一方面避免了让对方难堪、窘迫,使宴会仍能保持友好的气氛;另一方面,也回敬了美国人盛气凌人的指责与批评。
例二可称得上幽默的好例子。瑞士军官以自己的幽默战胜了法西斯侵略者的狂妄,表现出不卑不亢、不畏强权的坚强气概。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大体上可以分辨出什么是机智,什么是幽默。但是,就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机智回答中也含有幽默的成分,而瑞士军官的幽默则显示了他的聪明与智慧。可见,机智与幽默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再看“讽刺”与“幽默”的例子。
有一次著名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法国旅行,在去迪照恩的火车上,他十分困倦,打算睡上一觉。因此,他请求列车员当火车到迪照恩时把他叫醒。他首先解释说他是一个非常嗜睡的人。“当你叫醒我时,我可能大声抗议”,他对列车员说,“不过,无论如何只要把我弄下车去就行了。”于是,马克·吐温睡着了。当马克·吐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间,并且火车已经到了巴黎。他立刻意识到列车员在迪照恩忘记把他叫醒了,他非常生气。他跑向列车并冲他大声嚷道:“我一生从来没生过这样大的气,也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马克·吐温说。列车员平静地看看他说:“你的火气还没有我在迪照恩推下去的那个美国人的一半大呢!”
从以上这例子大家基本上可以体会出讽刺与幽默的不同。近乎纯幽默的例子中,大家也能体会到对那个粗心的列车员的善意的嘲讽与批评。可见,讽刺与幽默也不是水火不容的。讽刺与幽默是既有区别而又相交相融的。
再来看一个“滑稽”与“幽默”的例子。
马克·吐温心不在焉的毛病是很有名的。一天,马克·吐温外出乘车。当列车员检查车票时,马克·吐温翻遍了每个衣袋,都没有找到。这个列车员认识他,就安慰马克·吐温说:“没有什么大关系,如果实在找不到,也不碍事。”
“咳!怎么不碍事,我必须找到那张该死的车票,不然我怎么知道到哪儿去呢?”说完,马克·吐温和列车员都笑了。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出滑稽与幽默的区别。滑稽就是幽默的技巧用得过火的浅俗的幽默。“滑稽”在我国古代和近代则几乎是“幽默”的代用词。大体说来,把招笑的技巧用得过火而又没有多少内容,不能使人回味的就是“滑稽”,而技巧用得适中又有引人思索回味内容的就是“幽默”,二者也没有什么精细明确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