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读者的眼中,俄罗斯著名作家布宁(1870—1953)的名字可能比不上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的响亮,甚至连他的写作技巧也会显得有些陈旧而似嫌落伍。但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布宁在上个世纪前20年在俄国曾红极一时,到了60年代后的苏联,他又盛名重显。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绝不容忽视的:他是俄国“白银时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是俄国最优秀的侨民作家之一,他被欧洲文坛推崇为20世纪“最出色的俄罗斯作家”和“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
然而,他似乎又是一个始终坚持自我与时代永不合拍的文学天才:他将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视作“文学的堕落”与“群魔乱舞”,他对十月革命风暴的来临感到十分惊恐。在国内革命战争的战火中永远地西去巴黎而离开了他“家父的庭院”——依恋而又思念终身的俄罗斯大地。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现实,他在创作着关于生与死、爱与恨的作品,向往着人间的真情。战后,他反对侨民文学团体将接受苏联国籍的作家除名,但他又拒绝了苏联驻法大使希望他重新归国的邀请……难怪高尔基说,他的天才,“纯美得如同一块未经抛光的白银,他从不将其打磨成利刃,也不将其戳向应该戳的地方”。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于1870年诞生在俄罗斯中部一个古老显赫却日渐破败的庄园贵族家庭。在先祖卓越的文化名人中就有俄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茹科夫斯基,与普希金同时代的著名女诗人安娜·布宁娜。俄罗斯传统的贵族庄园文化不仅意味着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贵族地主生活方式,更包容着像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这样一些俄罗斯文豪的文化传承,与大自然、普通农民天然的紧密联系,无拘无束的自由时空,质朴得让人心醉的民风民俗,充满人间温情的歌谣传说……正是这些深厚的文化积淀构成了作家贵族血缘惯性的基因。布宁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承继还来源于他的副博士长兄,一个民粹主义革命党人对他的影响与教育。后者是他的思想启蒙人,成就了他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热爱、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他说:“我几乎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无论对自身蓝色的高贵血液,还是对与这一血液相联的一切的失落都采取一种全然无所谓的态度。”
独立不羁的个性、对民族与人类文化传统的不懈追索和探求使得布宁成了一个“永远的浪迹天涯者”,无有归宿的“风卷球”
 。他19岁出走家乡,此后一生在外漂泊:或在奥廖尔地方报纸编辑部打工,或在哈尔科夫与民粹主义革命者为伍,或在波尔塔瓦置身于托尔斯泰主义者中间,或在敖德萨与作家费德洛夫共处,或在卡普里与高尔基相伴,或漫游西欧、中东寻求人类古代文明的源头……这些经历滋润并磨砺着他的现实人生,也使他一生的精神追求历久弥新:他仰慕过民粹主义革命家,崇尚过托尔斯泰主义者,亦在佛教和基督教学说中寻求过生命存在的意义。
。他19岁出走家乡,此后一生在外漂泊:或在奥廖尔地方报纸编辑部打工,或在哈尔科夫与民粹主义革命者为伍,或在波尔塔瓦置身于托尔斯泰主义者中间,或在敖德萨与作家费德洛夫共处,或在卡普里与高尔基相伴,或漫游西欧、中东寻求人类古代文明的源头……这些经历滋润并磨砺着他的现实人生,也使他一生的精神追求历久弥新:他仰慕过民粹主义革命家,崇尚过托尔斯泰主义者,亦在佛教和基督教学说中寻求过生命存在的意义。
布宁以其独特的文学创作题材与现实主义风格于19世纪90年代踏上文坛: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他的小说都凝聚着一种对生命的独特思考,由一种对生命的强烈信念与依恋生发出的对生命的强烈感受。尚在创作初期,他便在庄园贵族之家的生活方式渐渐远去的历史现实中,发掘着“荒凉的诗情”。他透过宗法俄罗斯生活进程中有力、富饶、稳固、和谐渐次被枯竭、荒凉、凌乱、死亡所取代的现实,为生命中美与永恒价值的失落感到悲哀。他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发表于20世纪初,以其成名作短篇小说《安通苹果》命名的短篇小说集中。
作家对1905年—1907年俄国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在其文学创作中对俄国愚昧落后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愤懑与抗议,积极参与了高尔基组织的知识出版社的活动,却也为自己能够离开动荡的俄罗斯,身处“3000俄里之外”的巴勒斯坦、埃及而深感庆幸。
中篇小说《乡村》(1909)与《苏霍多尔》(1910)是他在20世纪头10年创作的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两部曲。书中展现了庄园贵族文化衰败后的俄罗斯农村中的可怕、贫瘠、非人的生活以及乡村居民精神的空虚与无能,揭示了在丑陋、畸形的文化状态中真、善、美、和谐的毁灭。由此确立了布宁创作的审美视点和诗学特征:不从社会成因,却是从俄罗斯民族性格与斯拉夫人的心理传承来阐释俄国的社会悲剧,一以贯之的高度的寓意性和象征性。作家在两部曲中以他对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的独特理解与高尔基进行着论争。针对后者关于城镇小市民代表着俄罗斯民族主体及生活方式特征的论断,布宁在他的小说中说:“她(俄罗斯,笔者注)整个是农村,你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他不无悲观地认定,俄罗斯社会的民族基础不在城镇,而在乡村,构成乡村主体的是农民、市民与颓败的庄园小贵族,是他们决定了俄罗斯发展的未来。因此,任何的民主改革只能被国家黑暗的“基原”所扭曲,因循守旧的乡村环境不可能产生先进生活的基因,而正在取代旧式生活方式的资产阶级的“新兴力量”只能瓦解、扼杀宗法俄罗斯的绿洲。
从1909年3月起,布宁开始在欧洲、中东、亚洲漫游。作家在印度与锡兰(现斯里兰卡)等国周游期间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受到佛教关于世界、苦难、欲望、诱惑等哲学思想的影响,其创作离开了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心理的探讨,进入了更为宏大的对人类与宇宙关系的思考中。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从民族本位的立场转向了人类本位的立场,不是以一个俄罗斯作家的身份,而是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以一种全人类的期待视野来认识世界、西方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理解人的生命、生与死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四海之内皆兄弟》(1914)、《旧金山来的绅士》(1915)、《同胞》(1916)等短篇小说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同时他也开始了一系列爱情小说的创作,如《最后一次幽会》(1912)、《爱情学》(1915)、《阿强的梦》(1916)、《卡齐米尔·斯坦尼斯拉瓦维奇》(1916)等。
布宁无法接受“充满动荡、战乱、饥饿而又缺乏理性”的俄罗斯。具有强烈政论色彩的《该诅咒的日子》(1918—1920)远远超出了文学的界限,作家在其中表达了对“魅力四射”的旧俄罗斯分崩离析的哀怨与绝望,对崇尚暴力的人群的强烈讽刺和对俄罗斯历史与未来的思考。
1920年1月26日,作家怀着对俄罗斯的无比眷恋,乘坐异国轮船从敖德萨经黑海西去欧洲,最后在法国定居,从此开始了作家人生与创作的新的历史阶段。
在侨居国外的岁月里,布宁日夜思念祖国,深感孤独、悲观与失望。他全身心地沉浸在文学创作之中,以巨大的艺术才情写出了大量的回忆性小说、哲理小说、爱情小说。短篇小说《完了》(1921)记述了他逃离俄国时的凄苦情景。在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1925)中作家揭示了爱情这一人类两性独特的情感现象的悲剧性本质及其与死亡的联系。此间,他先后在柏林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耶利哥的玫瑰》(1924),在巴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米佳的爱情》(1925)、短篇小说集《中暑》(1927)、《诗歌选集》(1929),短篇小说集《鸟儿的倩影》(1931)、短篇小说集《上帝之树》(1931)等。这些作品或表达在艰难时世的夹缝里人的生存,或凝注于爱情、生命与死亡的思考,或表现日常生活、人生突发事件中的悲剧。
布宁在二三十年代创作的这些中短篇小说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文体家的全部丰采:浮雕式的细节描写,凝练的叙事语言,日常生活情景,人类永恒命题美学阐释的具体性与可感性,生命与历史题材的超时空性。作家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说:“称我为现实主义者意味着不了解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我。”在布宁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代主义特征:他发展了尚在世纪初就显现出来的一种小说与诗歌美学合成的风格特色,他努力探索并表达人的本能欲望的悲剧理念,述说人类生存状态的不可知性,体现了一种具有宇宙意识的哲学精神。
自传体抒情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1927—1937)是布宁这类新型小说的一个集中体现。布宁以虚构主人公阿尔谢尼耶夫的口吻叙述了与作家不无共性的人生经历与人生感受。主人公的一生其实只包括二十余年人生经历,但小说却涉及了人的出生、成长、爱情、宗教、死亡以及俄罗斯历史、民族性格、灵魂等重大哲学命题。虚构与现实的两重性决定了作品叙述主体的两重性:显性的虚构主人公叙事者和一个隐性的经历了人生沧桑的老年作者叙事者,作品又以后者的人生经验审视前者的生活立场。往昔与今日的交织,生活片断与思绪流动的交织,使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兼有生活叙写与意识展现的诗性特色。小说凸现的是对高度情感化的生活的直接印象,但它又全无现实主义作品中事件发展的有序性与人物性格行为变化的因果性。“生活的无所不在的自发性”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叙事人的生活印象、人生感悟、心灵历程才是小说的真正内容。评论家称,它“有点像哲理性的长诗,又有点像交响乐式的图画”。1933年,布宁因“以严谨的艺术才能在小说中塑造了典型的俄罗斯性格”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把自己所得的大部分奖金捐献给了陷于贫困处境的俄国侨民,表现出一个侨民作家热爱祖国与民族同胞的思想情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的俄国侨民处境十分艰难。布宁生活拮据,精神苦闷,时刻在为祖国的命运担忧,但他仍然收留受到当局迫害的难民,为犹太艺术家提供避难处。这段时间作家的主要创作成就是他的由三十八篇小说构成的短篇小说集《暗 径》(1946)。这是俄罗斯文学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被称为“爱情百科全书”的爱情小说集。作家以生动曲折的故事,恣肆灵动的语言,朴实简练的叙事,展现了人类爱情的色彩斑斓的风景,诠释了人间情与爱的丰盈厚重,其中有少年男女真情实爱的被扼杀(《露霞》),有阴差阳错造就的爱的永诀(《在一条熟悉的街上》),有永恒期待却又在瞬间死亡的爱的苦痛(《在巴黎》),有肉的诱惑与灵的神圣的难能和谐(《纯贞的星期一》),有化作永恒憧憬的爱情的追忆(《寒冷的秋天》),有由生命冲动引发的一个男人同时对两个女性的追求(《卓依卡与瓦列里娅》)……
作家在晚年的创作中又为其丰富多彩的叙事文体增添了一种在20世纪颇为时尚的新体裁——哲理性随笔:《托尔斯泰的解脱》(1937)与《回忆》(1950)。前者描叙了作为作家、思想家和普通人的托尔斯泰的生命历程,分析了这位哲人对生命与死亡、爱情与婚姻、人生与道德的看法,后者回忆了勃洛克、高尔基、沃洛申、阿·托尔斯泰等作家的生平与创作。
1953年10月8日,布宁在巴黎逝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巴黎市郊的俄国侨民公墓。
本文集收聚了布宁的十二篇短篇佳作,它们创作于不同的时期,篇幅大小不一,但基本包容了作家创作的主要题材,不同的文体与叙事风格。
《安通苹果》、《旧金山来的绅士》、《耶利哥的玫瑰》、《陈年旧事》是布宁很有代表性的抒情哲理小说。
《安通苹果》是作家具有印象主义色彩的叙事名篇。作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旧俄帝国渐趋衰颓的历史进程中展现了一个个不无凄凉的贵族庄园日常生活场景,并用细腻、充满诗意的现实主义笔法将发生在俄国地主庄园的点点滴滴的生活印象与遗迹描绘得栩栩如生,使整个故事由简单的叙述逐步完善成具有电影特写镜头效果的场面展示,将一种俄罗斯文学少有的华丽与震撼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使得小说获得了文化观照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价值。读者在小说中可以感受到融贯小说通篇的苍凉、朴实、纯美与深情的意境。作品中“寻求美与永恒的融合”的这一主旨同样体现在《旧金山来的绅士》中。现代物质文明的浮华与灿烂、财富与奢侈,其实不过是过眼烟云,它们无法拯救“新世界的主人”于死亡,难能与深不可测的浩瀚海洋的波涛抗争,亦无法救治人类精神的寂寥与苦闷,美与永恒只孕育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机勃勃的青春之中。微型短篇《耶利哥的玫瑰》以具有诗意名称的野生刺草——耶利哥的玫瑰比喻生命的永恒。“存在过经历过的东西不会灭亡!只要我的心灵,我的爱,我的记忆活着,就不会有离别和失落。”《陈年旧事》(1922)叙述了发生在遥远的莫斯科的春天,三个不同历史身份的人的邂逅。人与人的相遇相知无不是一种缘分,每一次离别未必不是永诀,人生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们理应满怀友情与亲情,何需仇视争斗,相煎太急?
文集中占主要篇幅的是爱情小说,共有七篇。它们大都收集在作家的爱情小说集《暗 径》中。
《最后一次幽会》讲了两个活得很不幸福,甚至有些悲凉的中年男女,从青春时期的相慕,到深涉人世的相知,直至最后灵肉的相偎相依,主人公毫不犹豫地用十五年光阴换回了与她的“最后一次幽会”。小说标题像是一声幽忧悲远的哀怨,失伴灵魂的呼号,一桩未了情的了结。《爱情学》中聪明绝顶的贵族地主赫沃辛斯基二十多年来始终不渝地爱着一个并不漂亮,年纪轻轻就死去的侍女卢什卡,以至于神经失常,终生未愈。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升华的却是一种爱的哲学:爱是一种令人难以名状的生命现象,它能让人非梦非醒,大智大狂;女子并非因她美丽才可爱,是因她可爱才美丽,只有可爱的女子才是男人心灵的主宰。《暗 径》展示了欲与爱的分离:在爱的新鲜感消失之后贵族将军的忘却与女仆对爱情的忠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小说写出了爱的人生经验,这是一篇能使人变得清醒起来的关于爱情的作品。《纳塔莉》细腻而真实地描写了一位充满欲望而又渴望真情的青年男子对爱的苦苦的荡人心魄的寻觅。《大乌鸦》记录着在物欲主宰的尘世中爱的变形与扭曲。青春妙龄女郎叶莲娜以一种情人的方式热恋着男青年,却最终难以抗拒富裕的物质生活,嫁给了青年的父亲。《惩罚》中的主人公玛莎是个很敏感的女人,天性浪漫,多情善感,常常会与男人一见钟情,却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情感。以欲主导的爱变成了一种不知所终的等待、猜忌与负担。陷入绝望之中的她叹道,她并非墨杜萨
 ,只不过是个不幸的女人,“就是母鸡也有一颗心啊!”《犹太地之春》讲述的是一次考察队员与部落少女的爱或是欲的奇遇,作家为两人的欢娱找到的理由是:情爱与性爱是无需在道德上释然、感情上释放的规则的。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努力在历史的记忆与艰难的现实中发掘爱情的美好、苦难与悲剧,展示世事的寒凉辛酸,发出对真情的呼唤。作品在伤感的灰暗中总有人性的光点在闪耀,从而冲淡了爱情的悲剧气氛,使其演化为一种作家醉心的古典之美,弥合了灵与肉、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以期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和谐。
,只不过是个不幸的女人,“就是母鸡也有一颗心啊!”《犹太地之春》讲述的是一次考察队员与部落少女的爱或是欲的奇遇,作家为两人的欢娱找到的理由是:情爱与性爱是无需在道德上释然、感情上释放的规则的。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努力在历史的记忆与艰难的现实中发掘爱情的美好、苦难与悲剧,展示世事的寒凉辛酸,发出对真情的呼唤。作品在伤感的灰暗中总有人性的光点在闪耀,从而冲淡了爱情的悲剧气氛,使其演化为一种作家醉心的古典之美,弥合了灵与肉、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以期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和谐。
《蛐蛐儿》是文集中唯一一篇叙说人生苦难的小说。读者无疑会为马具匠“蛐蛐儿”丧子的人生苦难一掬同情之泪。然而,小说既无意揭示农奴制度的罪恶,也丝毫没有对农奴主老爷太太作社会批判,相反,作者在小说中营造了一种浓浓的主人与奴仆和谐共处、一起伤感人生无常的氛围。
布宁的小说大都采用了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但作品中却没有托尔斯泰的创作中一贯彰显的说教者的话语腔调,使叙事真正回到了质朴的生活现场,回到了人物本身的自然角色之中,少有创作主体理性思维对叙事的强制性干预,而是让人物沿着自己的个性与命运自由自在地畅行。小说充满不少具有隐喻性的意象,比如“安通苹果”、“耶利哥的玫瑰”、“暗 径”等,它们都具有纵深言说的诗学品质。短篇小说是无法掺水的凝练文字,布宁的短篇小说更是十分精致的。这种精致不在于情节的突兀和细节的雕琢,而在于人物灵魂深处的隐痛得到了最具穿透力的表达,准确与精当,这点读原文会得到最真切的感受。布宁是位经典的小说家,经典的文体家,实在名不虚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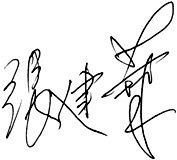
(张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