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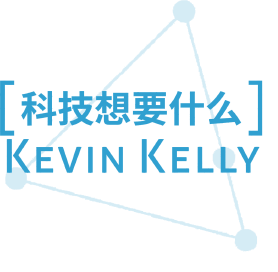
第二、三、四章,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凯文·凯利从三个层面解答同一个问题:“技术元素”是如何起源的?
借助于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发现的大量史料,凯文·凯利梳理了工具、语言伴随人类进化的简略历史。这是探索“技术元素”起源的第一层。
对使用简单器具狩猎、筑巢和切割食物的猿人,甚至更多的灵长类动物来说,工具的使用其实并不稀奇。用生物学家贾里德·戴蒙德的话说,5万年以前的类人猿虽然能灵巧地使用工具,但“脑子里缺根弦”,这根弦是动物和“现代智人”的分水岭;接上这根弦的标志,是“语言的发明”。
语言与工具(技术)的这种伴生关系,一直伴随着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从非洲、美洲、澳洲的原始部落大迁徙中,千挑万选的植物种子、驯养的家禽、粗糙但越来越合手的工具,是文明演进的活化石。
但是,凯文·凯利的目光并没有在此止步。
“科技驯化了我们”,这件事情更为重要。使用工具的人类祖先,他的牙齿、胃、毛发、脚趾,都缓慢地发生着变异,这种进化,其实是“与技术同步进化”的过程。
在凯文·凯利看来,漫长的共同演化,使技术、工具远远不是冷冰冰的名词。它是有灵性的、充满活力的,它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精灵,要么推动我们前进,要么阻碍我们;它不是静态事物,而是动态过程”。
技术并非外在于人,是建立对技术的“亲近感”的重要内容。倘若将技术全然当做“身外之物”,或者“形而下者的器物”,那种割裂感才是真正要命的。
技术,是人的“第二肌肤”,一直是,将来也是。
为了预测科技的发展方向,我们需要了解它的起源。这并不容易。我们越深入追溯技术元素的发展史,它的起源就越显得遥远。因此,让我们从人类自己的起源——史前某个时期开始,那时人们主要生活在非人造环境中。没有科技,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先于人类出现。其他许多动物比人类早数百万年使用工具。黑猩猩过去用细枝条制作狩猎工具(当然现在仍然如此)从土堆中取食白蚁,用石块砸开坚果。白蚁自建巨大的土塔作为家园。蚂蚁在花园里放养蚜虫,种植真菌。鸟类用细枝为自己编织巢穴。有些章鱼会寻找贝壳,随身携带,作为移动住宅。改造环境,使之为己所用,就像变为自身的一部分,这种策略作为生存技巧,至少有5亿年的历史。
2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首先砸碎石块做成刮削器,为自己添加利爪。到了大约25万年前,他们发明用火烧煮食物——或者说使食物易于消化——的简单技术。煮食相当于人造胃,这是一种人造器官,使人类的牙齿和颚肌变小,食物品种也更多。技术辅助型狩猎也同样古老。考古学家发现过一个石枪头插入一匹马的脊椎,一根木矛嵌在10万年前的马鹿的骨架中。这种使用工具的模式在此后的岁月里只是更加频繁地出现而已。
所有技术,例如黑猩猩的钓白蚁竿和人类的鱼竿,海狸的坝和人类的坝,鸣禽的吊篮和人类的吊篮,切叶蚁的花园和人类的花园,本质上都来自自然。我们往往会把制造技术与自然分开,甚至认为前者是反自然的,仅仅是因为它已经发展到可与自然始祖的影响和能力相匹敌。不过,就其起源和本质来说,工具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具有自然属性。人是动物——毋庸置疑,也是非动物——毋庸置疑。这种矛盾性质是我们身份的核心。同样,技术是非自然的——从定义上说,也是属于自然的——从更广泛的定义上说。这种矛盾也是人类身份的核心。
工具和容量更大的脑明白无误地宣告进化史上人类时代的开始。第一个简单石器出现的考古时期,也就是制造该石器的类猿人(具备人的特征的猿)的大脑开始向目前的大尺寸发育的时期。类猿人250万年前降生到地球上,手里拿着粗糙的、有缺口的石刮削器和石斧。大约100万年前,这些智力发达、挥舞工具的类猿人穿越非洲,到南欧定居下来,在那里进化成尼安德特人(脑容量增大);后来又进入东亚,进化为直立人(也有更大的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类猿人的三条支线全部都在进化,留在非洲的那支进化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人类形式。这些原始人类成为完全的现代人的确切时间存在争议,有人说是20万年前,而无争议的最晚时间为10万年前。10万年前,人类跨越了门槛,此时从外表上看,他们已与我们相差无几。如果他们中的某一个打算与我们一起去海滩散步,我们不会注意到有什么问题。另一方面,他们的工具和大多数行为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东亚的直立人难以区别。
此后的5万年变化不大。非洲人的骨架结构这一时期保持不变,他们的工具也没有多少改进。早期人类使用草草制成的带有锋利边缘的大石块切割、戳刺、凿孔和叉鱼。但这些手持工具没有专门化,不随地域和时间变动。在这个时期(被称为中石器时代)的任何地方或任何时间,某个类猿人捡到一块这样的工具,它都会和数万英里之外或者相差数万年的同类工具——不论其制造者是尼安德特人、直立人还是智人——相似。类猿人就是缺乏创新。正如生物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评价的那样:“尽管他们的大脑不小,但少根弦。”
接下来,大约5万年前,缺的那根弦被安上了。虽然早期非洲人类的躯体没有变化,但是基因和思维发生了巨变。类猿人第一次满脑子主意和创新意识。这些新生的充满活力的现代人,或者说现代智人(我用这个称谓来区分他们和更早的智人),离开祖先在东非的家园,进入新地区。他们在草原上分道扬镳。就在1万年前农耕文明的历史即将拉开帷幕时,他们的人数出现了相对短暂的爆发式增长,从非洲的数万人猛增至全世界的约800万。
现代智人在全球迁移并在各大洲(除了南极洲)定居的速度令人吃惊。他们用5000年的时间征服欧洲,又经历15000年到达亚洲边缘。现代智人的部落从欧亚大陆经大陆桥进入现在所称的阿拉斯加后,只耗时数千年就占据了整个新世界。现代智人以执著的精神进行扩张,此后的38000年里他们的征服速度达到每年1英里(2公里)。他们不断前进,直到能抵达的最远处才停下脚步,这个地方就是南极洲的最北端陆地。智人完成在非洲的“大跃进”后,历经不到1500代,成为地球史上分布最广泛的物种,居住地遍及这个星球的所有生物带和每一条河的流域。现代智人是前所未有的最具侵略性的外来生物。
今天,现代智人分布的广度超过了已知的任何大型物种,没有其他任何可见物种占据的地理和生物生态位比智人多。现代智人的占领总是迅速的。贾里德·戴蒙德评论道,“毛利人的祖先抵达新西兰后”,只携带少量工具,“显然在不到1个世纪的时间内就找到全部有价值的石料来源,又用了几个世纪就将栖息于世界上某些最崎岖地带的新西兰恐鸟屠戮殆尽”。这种在数千年的持续稳定后突如其来的全球扩张只有一个原因:技术革新。
当现代智人的扩张刚刚起步时,他们将动物的角和长牙改造为矛和刀,巧妙地以动物之利器还治其身。5万年前扩张序幕开启的那段时光,他们制作小雕像和最早的首饰,绘制最早的画,将贝壳制成项链。尽管人类用火的历史很长,但最早的炉床和避火设施大约是在这个时期发明的。稀有贝壳、燧石和打火石的交易出现了。几乎同一时间现代智人发明了渔钩和渔网,以及将兽皮缝制成衣物的针。兽皮精心剪裁后的余下部分被扔进坟墓。从那时起,一些陶器上开始出现编织的网和宽松织物的印记。同一时期现代智人还发明了狩猎陷阱。他们的垃圾中有大量的小型毛皮动物的骨骼,但没有脚;现代使用陷阱的捕猎者仍然按这种方式剥掉小动物的皮,将脚部与皮留在一起。艺术家们在墙上描绘身着皮大衣、用箭和矛猎杀动物的人。重要的是,与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的简陋发明不同,各地的此类工具在细节上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技术。现代智人已经开始创新。
现代智人制作保暖衣物的思维能力打开了通向北极地区的大门,钓鱼器械的发明使人类有能力开拓世界上的海岸和河流,特别是热带地区,那里缺乏大型动物。现代智人的创新让他们能够在很多新气候带繁衍壮大,而寒带地区及其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尤其有助于创新。对于历史上的采猎部落,家园的纬度越高,需要(或者已经发明)的“技术单元”就越复杂。与在河中捕捉鲑鱼相比,在北极气候条件下捕猎海洋哺乳动物使用的工具明显先进得多。现代智人迅速改进工具的能力使他们得以很快适应新生态圈,其速度远远高于基因进化曾经达到的速度。
在迅猛占领全球的过程中,现代智人取代了其他几个同时居住于地球的类猿人种(存在不同血缘通婚的情况),包括远亲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的规模很小,人数通常只有18000。尼安德特人作为唯一的类猿人统治欧洲数十万年后,携带工具的现代智人来到这里,此后前者又延续了不到100代便消失了。这是历史的一瞬间。诚如人类学家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指出的那样,从地质学角度看,这个取代过程几乎转瞬即逝。考古记录上几乎不存在过渡期。按照克莱因的说法:“尼安德特人今天在这,第二天克鲁马努人(现代智人)就来了。”现代智人的遗迹层总是在顶部,从未出现在底部。现代智人甚至不一定对尼安德特人进行了屠杀。人口统计学家计算过,繁殖率只要有4%的差距(考虑到现代智人可以捕获更多种类的动物,这是个合理的期望值)就可以在数千年内让生育率更低的一方退出历史。这种数千年内灭绝的速度在自然进化史上没有先例。令人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一系列由人类造成的短期内物种灭绝中的第一次。
尼安德特人本应像21世纪的我们一样觉察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一股新的生物学和地理学意义上的力量崛起了。若干科学家(包括理查德·克莱因、伊恩·塔特索尔和威廉·卡尔文,以及其他许多人)认为这个发生于5万年前的“事件”就是语言的发明。在此之前,类猿人一直是智慧物种。他们可以制作粗糙的工具(虽然是无计划的),使用火,也许就如同极其聪明的黑猩猩。非洲类猿人大脑尺寸和身高的增长已达到平衡,但脑的进化还在继续。“5万年前发生的,”克莱因说,“是人类社会运转系统的一次变革。也许某处的变异影响了大脑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导致语言的形成,按照今天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就是出现了快速生成的有声语言。”与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拥有更大容量的脑不同,现代智人发育出神经元重新组合的脑。语言改变了尼安德特人式的思维,使现代智人首次能够带着目的、经过思考后进行发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用简练的语言赞美道:“在思维的进化历程中,语言的发明是所有步骤中最令人振奋、最重要的。当智人从这项发明中受益时,人类进入一个跳跃式发展阶段,将地球上的其他物种远远甩在身后。”语言的创造是人类的第一个拐点,改变了一切。有了语言的生活对那些没有语言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语言使交流与合作成为可能,加速了学习和创造过程。如果某人有了新构想,在其他人了解之前,向他们进行阐述,与之沟通,新构想就能快速传播。不过,语言的主要优点不在于交流,而在于自动产生。语言是技巧,让思维能够自我质疑;是魔镜,告诉大脑自己在想什么;是控制杆,将思想转化为工具。语言掌握了自我意识和自我对照的捉摸不定的无目标运动,从而能够驾驭思维,使之成为新思想的源泉。没有语言的理性架构,我们无法获知自己的精神活动,自然就不能思考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大脑无法表词达意,我们就不能有意识地创造,只能偶有收获。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思想零碎孤立,直到我们用可以自我交流的系统工具驯服思维,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我们的思维需要驯化,我们的才智需要表达工具。
一些科学家相信,事实上是科技激发了语言。向运动中的动物投掷武器——石块或木棍,用足够的力量击中并杀死目标,这需要类猿人的大脑进行仔细的计算。每一次投掷都要求神经中枢大量连续的精确指导,这一过程只在刹那间完成。但是,与计算如何抓取空中的树枝不同,大脑必须在同一时间计算这一掷的若干选项:动物加速还是减速,朝高处还是低处瞄准。接着大脑必须描绘出结果,以便在实际投掷之前判断出最佳可能性——完成所有这些思考的时间不到一秒。诸如神经生物学家威廉·卡尔文这样的科学家相信,一旦大脑提高想象多幅投掷场景的能力,它就将真正的投掷过程转变为一系列快速闪过的念头。大脑用投掷语言替代投掷木棍。因此,技术被赋予的新用途就是创造原始但有益的语言。
语言难以捉摸的才能为现代智人部落的扩张开辟了很多新地域。与远亲尼安德特人不同,现代智人能够快速调整工具用以狩猎、设置陷阱捕捉更多种类的大型动物以及收集并处理更多类型的植物。有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局限于几种食物来源。对他们骨骼的检测显示,他们缺乏鱼身上具有的脂肪酸,而且日常饮食主要是肉类,但肉的种类不多,有一半的饮食是毛茸茸的猛犸象和驯鹿。尼安德特人的消亡可能与这些巨型动物的灭亡有关。
现代智人作为兴趣广泛的采猎者而发展壮大。人类子孙数十万年绵延不绝,证明只要几种工具就足以获取足够的营养繁衍后代。现在我们得以来到世间,是因为采猎在过去的岁月中发挥了作用。关于历史上采猎者的饮食的分析显示,他们能够摄取足够的能量,符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针对他们的体型推荐的标准。例如,人类学家发现历史上的多比人(Dobe)平均每天采集含有2140卡路里热量的食物,鱼溪部落(Fish Creek)为2130卡,亨普尔湾部落(Hemple Bay)为2160卡。他们的菜单上有不同的植物块茎、蔬菜、水果和肉类。根据对垃圾中骨头和花粉的分析,早期现代智人的确如此。
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断言,野人——在这里他指的是作为采猎者的现代智人——的生活“危险、粗俗,且短暂”。其实,尽管早期采猎者寿命的确很短,生活经常受到战争的威胁,但并不粗俗。他们不仅凭借仅有的十几种原始工具获得足够的食物、衣服和居所,得以在各种环境中生存,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这些工具和技术还为他们提供娱乐。人类学研究证实现代采猎者不是一整天都在打猎和采集食物。一位名叫马歇尔·萨林斯的研究人员总结道:采猎者每天在必需的日常食物获取上花费的时间只有3~4个小时,其中包括他所谓的“银行家时间”
 。不过他的这一惊人结论的证据是有争议的。
。不过他的这一惊人结论的证据是有争议的。
根据范围更广的数据,关于现代采猎部落收集食物所耗费时间的更加现实并且争议更小的平均数是每天大约6小时。这个平均数掩盖了日常行为的大幅变动。1~2小时的小憩或者一整天用于睡觉并不少见。外部观察者几乎普遍注意到觅食者工作的非连贯性。采集者也许连续数天非常努力地寻找食物,然后在这一周余下的时间里就靠这些食物生活。人类学家把这种循环称为“旧石器时代节奏”——工作一两天,休息一两天。一位熟悉雅马纳(Yamana)部落——也可能几乎所有狩猎部落都是如此——的研究者写道:“他们的劳动事实上更多的是一时兴起,依靠偶尔的努力,他们能够积累相当多的食物,维持一段时间。然而,之后他们表现出想要无限期休息的欲望,在此期间,身心完全放松,不会显得很疲劳。”旧石器时代节奏实际上反映出“食肉动物节奏”,因为动物世界的伟大狩猎者——狮子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表现出同样的行为方式:短暂的爆发式捕猎,直至筋疲力尽,接下来的日子休养生息。狩猎者,与字面定义不同,几乎很少外出狩猎,捕获猎物的成功次数不是那么多。以每小时获取的热量计算,原始部落的狩猎效率只有采集效率的一半。因此几乎所有的觅食文化中,肉食都用于款待客人。
季节变化也有影响。对食物采集者来说,每个生态系统都会产生“饥荒季”。在寒冷的高纬度地区,深冬到初春时的饥荒季更加严重。其实,即使在热带地区,各个季节中获取最喜爱食物、水果辅食和至关重要的大型动物的难度也有差异。此外,还有气候变化因素:延长的干旱、洪灾或风暴期可能打断每年的食物获取模式。这些以日、季和年计的大干扰意味着,很多时候采猎者吃得肚皮鼓鼓,另一方面,很多时期——而且的确如此——他们会忍饥挨饿、营养不足。这段营养不足的时间对幼儿是致命的,对成人来说则是可怕的。
所有这些热量的变化导致旧石器时代节奏在任何时间段都有可能出现。重要的是,这种爆发性“工作”情非所愿。当你主要依靠自然系统提供食物时,工作越多,收获不一定越多。两倍的工作量不一定能产生两倍的食物。无花果不能催熟,成熟时间也不能精确预测。同样,大型动物兽群的到来也不能预知。如果没有储备余粮或合理耕种,就必须从粪便中取食。为了保证食物供给,采猎者必须马不停蹄离开废弃的食物源,寻找新来源。可是如果永不停息地奔波,余粮及其储运工具就会减慢你的速度。在很多现代采猎部落中,不受财物拖累被认为是一种好习惯,甚至可以带来声望。你行囊空空。聪明的替代策略是,需要什么东西时再去制作或者搜寻。“能干的猎人会囤积猎物,他的成功是以损害自己的名望为代价的。”马歇尔·萨林斯说道。此外,生产余粮的成员必须与大家分享多余的食物,这降低了他们生产余粮的意愿。因此,对采集部落而言,储备食物是损害自身社会地位的行为。真实的情况是野外迁徙时必须忍受饥饿。如果干旱期减少了西米的产量,再怎么延长劳动时间也不会增加食物的产出。因此,采集部落在吃饭问题上采取非常有说服力的计划安排。发现食物时,所有人都很努力地劳动。找不到食物也不用发愁:他们会饿着肚子围坐闲聊。这个非常合理的方法经常被误解为部落的懒惰,事实上,如果靠天吃饭,这是个合乎逻辑的策略。
我们这些现代文明社会的上班族看到这种轻松的工作方式可能会心生嫉妒。每天3~6个小时,远远少于发达国家中大多数成年人的工作时间。而且,当被问及对现状的感受时,多数被现代文明同化的采猎者对目前的物质生活很满足。一个部落很少拥有一件以上的人工制品,例如只有一把斧头,原因是:“一件东西难道不够吗?”某些情况下,需要时才使用这件物品,更多的情形是,等到需要某种制品时再做一件。一旦该物品被使用了,通常的结局是被丢弃,而不是保存。这样就不需要携带或留意多余物件。向部落居民赠送毛毯或刀具之类礼物的西方人常常郁闷地看到一天后这些礼物就被弃若敝屣。部落居民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表现出最大限度的一次性文化。最好的工具、人工制品和技术都是用后即弃。甚至人工修建的精巧住所也被视为临时性的。部落或家族在迁徙途中可能搭建一个休息场所(例如竹屋或小冰屋),只用一晚,第二天一早就丢弃了。多户人家居住的大宅也许会在数年后遗弃,而不是保留。耕地有着相同的遭遇,收割后就会被放弃。
马歇尔·萨林斯观察到这种无忧无虑的自给自足和知足常乐,宣称采猎部落是“原始的小康社会”。其实,由于部落居民大多数日子里能获取充足的热量,并且他们的文化并不一味追求更多,因此更合理的结论也许是采猎部落“物资充足但不富足”。根据大量与原住民相关的历史记载,我们知道他们经常——如果不是定期的话——抱怨吃不饱。著名人类学家科林·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记录道,虽然姆布蒂(Mbuti)人时常歌颂森林之神,但也经常抱怨饥饿。采猎者的诉苦通常与每顿饭都要吃的糖类主食——例如mongongo
 果仁——的单一有关。当他们谈到食物短缺或者饥饿时,指的是缺少肉食,脂肪摄取量不足,以及对饥饿期的厌恶。他们为数不多的科技在大部分时间里为他们带来足够但不丰富的食物。
果仁——的单一有关。当他们谈到食物短缺或者饥饿时,指的是缺少肉食,脂肪摄取量不足,以及对饥饿期的厌恶。他们为数不多的科技在大部分时间里为他们带来足够但不丰富的食物。
平均水平达到充足与达到富足之间的细微差别对健康有重要影响。当人类学家评估现代采猎部落妇女总生育率(生育年龄中婴儿安全出生的总数)时,发现这个数字相对较低,总计大约为5~6个婴儿——与之相比,农耕社会为6~8个。有几个因素降低了生育率。也许是因为营养不均衡,导致部落女孩青春期推迟至16~17岁(现代社会女性13岁开始)。推迟的女性月经初潮以及较短的寿命延误并缩短了生育的时间窗口。在部落中,母乳喂养通常持续时间更久,延长了两次生育之间的间歇期。大多数部落给婴儿喂奶,到2岁或3岁时停止,还有一些部落母乳喂养的时间长达6年。此外,许多女性骨瘦如柴,又极为活泼,就像西方同类型女运动员一样,月经期经常无规律,或者完全没有月经。有理论认为,女性需要维持“临界肥胖度”以产生卵子,很多部落妇女因为饮食量变动而缺乏这种肥胖度,至少部分年份是这样。当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有意识地禁欲,为已出生的孩子留出生存空间,部落居民有理由这么做。
儿童死亡率在采猎部落中非常高。一项针对不同大陆的25个部落历史时期的研究表明,平均25%的幼儿在1岁前死亡,37%在15岁前死亡。人们发现,在一个传统的采猎部落,儿童死亡率为60%。大多数历史上的部落人口增长率几近于零。罗伯特·凯利在他的采猎部落研究报告中称,这种停滞是明显的,因为“当过去的迁徙者定居下来时,人口增长率上升了”。所有条件都同等的情况下,农作物的稳定性养育了更多人。
许多小孩幼年夭折,另一方面,寿命较长的采猎部落居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生活很艰难。根据对骨骼压痕和切口的分析,一位人类学家认为尼安德特人身体的伤口分布与在专业竞技人员身上发现的相似——大量头部、躯干和手臂创伤,就像与愤怒的大型动物近距离遭遇时所受的伤一样。目前还未发现活过40岁的早期类猿人的残留物。因为极高的儿童死亡率拉低了平均预期寿命,如果年龄最大者只有40岁,那么寿命中间值几乎可以肯定小于20。
一个典型的采猎部落只有很少的儿童,没有老人。这样的人口结构也许能解释访问者与保持历史原样的采猎部落接触时共有的印象。他们评论道:“每个人看上去都极为健康强壮。”部分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处于壮年期,年龄在15~35岁之间。如果我们参观城里有着同样年轻人口结构的新潮社区,也许会有同样的反应。部落的生活方式适合年轻人,属于年轻人。
部落居民寿命不长的一个主要后果是祖父母辈的缺失。考虑到女性17岁左右就开始生育,30多岁死亡,普遍的现象是孩子们成长为青少年时就会失去父母。寿命短对个人来说非常糟糕,对群体也是极其有害的。没有祖父母,久而久之,传授工具使用知识变得十分困难。祖父母是文化的中转站,没有他们,文化就会是一潭死水。
想象一下这样的社会,不仅缺少祖父母,而且没有语言,例如现代智人之前的人类社会。知识怎么能代代相传?你的父母在你成年之前便去世了,他们传授给你的知识不可能超越你未成年时所能学到的。除了最亲密的同龄人,你不会向其他任何人学习。创新和文化知识不会得到传承。
语言让思想融合交流,从而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创新得以孵化,通过儿童实现代代相传。现代智人制造出更出色的捕猎器械(例如投枪,使得体重轻的人类能够在安全距离之外杀死危险的大型动物)、钓鱼工具(带刺的鱼钩和渔网)和烹煮方法(用高温石头不仅可以烧肉,而且能从野生植物中获取更多热量)。从开始使用语言算起,他们获得所有这些技术,只用了100代人的时间。更好的工具意味着更好的营养,这有助于进化速度的提高。
营养改善的主要长期后果是寿命的稳定增长。人类学家雷切尔·卡斯帕里(Rachel Caspari)研究了768名类猿人的牙齿化石,这些类猿人生活于亚欧非三大洲,时间从500万年前到“大跃进”为止。她断定“现代人寿命的猛增”大约始于5万年前。不断延长的寿命导致隔代教养的出现,产生所谓的祖母效应:这是一个良性循环,通过祖父母的言传身教,越来越多的有效创新得以应用,可以进一步延长寿命,使人们有更多时间发明新工具,从而增加人口。不仅如此,寿命延长“提供选择优势,促进人口增长”,因为人口更密集提高了创新的速度和影响,这对增加的人口是有益的。卡斯帕里认为,引发现代行为创新最基本的生物因素是成人生存能力的增强。寿命增长是人们获得科技后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结果,这并非巧合。
15000年前,世界正在变暖,全球冰盖消融,现代智人的队伍不断扩张,所使用的工具也越来越多。他们使用40种工具,包括砧板、陶器以及合成器械,也就是用多块材料——例如许多小燧石片和一个手柄——拼凑而成的矛和刀。尽管仍然主要靠渔猎采集为生,现代智人偶尔也会尝试定居生活,返回故土看管最喜爱的食物产地,针对不同生态系统制作专用工具。我们从这一时期位于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埋葬地得知,衣服也从通用型(一件简单的上衣)发展为细分型,例如帽子、衬衣、外套、裤子和鹿皮鞋。自此以后人类工具越来越专业化。
在适应不同的河流流域和生态群落后,现代智人部落的种类急剧增加。他们的新工具反映出家园的特性:河岸居民有很多渔网,草原猎人有多种枪头,森林居民会设置多类陷阱。他们的语言和外表不断分化。
不过,他们也有许多相同特征。大部分采猎者各自组成平均人数为25人的家族式团体,成员都有血缘关系。在季节性节日或宿营地,小团体会集合成数百人的较大部落。这种部落的功能之一是通过通婚传播基因。几乎没有人口扩散。在寒冷地区,部落的平均人口密度低于每平方公里0.01人。大部落中的200~300个成员,也许是他们一生中遇到的所有人。也许会认识部落以外的人,因为可能要跋涉300公里去进行实物交易,或者说物物交换。有些用于交易的物品是身上的装饰品和项链,如内陆居民需要的海贝和渔民需要的禽类的羽毛。偶尔,脸部彩绘所用的颜料会被拿来交换,但它们也可用于壁画或雕刻木像。随身携带的几件工具应该是骨钻、石锥、针、骨刀、挂在矛上的骨制鱼钩、一些刮削石器,也许还有几把石刀。一些刀片要用藤条或兽皮制成的绳索绑在骨头或木柄上。当人们围着火堆蹲下时,有人会敲鼓,或者吹骨哨。人死后,会有为数不多的财物作为陪葬品。
但是,不要以为人类社会的这种进步有如田园牧歌。在走出非洲踏上伟大征程的2万年里,现代智人是造成90%当时存在的巨型动物灭绝的帮凶。他们使用弓箭、矛和诱逼等创新方式杀光乳齿象、猛犸象、新西兰恐鸟、长毛犀牛和巨骆驼——几乎所有四条腿的蛋白质丰富的大型动物。到距今1万年前时,地球上超过80%的大型哺乳动物完全消失。由于未知原因,北美有4个物种逃脱了这场厄运:美洲野牛、驼鹿、麋鹿和北美驯鹿。
部落之间的暴力争斗也很盛行。部落内部成员的和睦与合作法则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经常让现代人羡慕不已,但对部落外的人不适用。部落为了争夺某些资源而诉诸武力,在澳大利亚是争夺水潭,在美国是狩猎区和野生稻田,在太平洋西北部则是河流和沿海的滩岸地带。没有仲裁系统或者公正的领导者,因偷窃物品、女人或财富象征(例如在新几内亚,猪就是这样的象征)而导致的小范围冲突可能激化为几代人的战争。采猎部落间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是晚期农耕社会的5倍。(每年死于“文明”战争的人占总人口的0.1%,与之相比,部落战争为0.5%。)实际的战争死亡率因部落和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因为与现代世界一样,一个参战部落可能会破坏很多人的和平生活。总而言之,部落流动性越大,就越倾向爱好和平,因为他们完全可以逃离冲突。而一旦战争真正爆发,就会是惨烈致命的。当原始部落的战士数量与文明社会的军队大致相当时,前者通常会击败后者。凯尔特部落打退罗马人,柏柏尔人重创法国人,祖鲁人战胜英国人,美国军队用了50年时间才击败阿帕奇部落。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在关于古代战争的研究著作《文明之前的战争》(War Before Civilization)中写道:“民族史学者和考古学家发现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原始的史前战争和历史上文明社会的战争一样恐怖,令人印象深刻。实际上,由于原始社会的战争更加频繁,过程更加残酷,其致命程度远远高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文明社会的战争是格式化的,注重规则,危险性相对较低。”

图2-2 战争死亡率比较。原始部落和现代国家每年战争而死亡人数占人口百分比
5万年前语言革命还未发生时,世界缺少有重大意义的科技。此后的4万年,每个人天生就是渔猎采集者。据估计,在此期间有10亿人探究过携带少量工具可以走多远。这个没有多少科技的世界提供“足够的”物资。人们可以享受清闲时光和令人满意的工作,而且感到快乐。除了石器,再没有别的科技,人们可以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节奏和风格。大自然掌控你的肚子和生活。它是如此巨大,如此丰富多彩,如此亲近,极少有人可与之分隔。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令人感觉神圣。然而,由于缺乏科技,儿童死亡的悲剧不断重演。意外事故、战争和疾病意味着平均寿命远远低于原本应有的一半——也许只有人类基因支持的自然寿命的四分之一。饥饿随时袭来。
但是最明显的是,没有重大科技,所谓的悠闲时光不过是重复传统生活方式。新事物绝无可能出现。在你的狭小天地里,一切由你做主。但生活的方向只能按照祖先的足迹亦步亦趋,周边环境的循环变化决定了你的生活。
事实证明,尽管大自然广阔无垠,它还没有慷慨到让一切皆有可能的程度。思维可以做到这一点,可它的潜能还没有充分开发。一个没有科技的世界足以维持人类的生存,但也仅此而已。只有当思维被语言解放、被技术元素激活,超越5万年前自然界的束缚,更加广阔的天地才会敞开大门。实现这种超越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我们从中收获的是文明和进步。
我们和走出非洲的人类还有差异,我们的基因与我们的发明共同进化。事实上,过去的1万年,我们的基因进化速度比此前600万年的平均速度快100倍。不必对此感到惊讶。我们把狼驯化为狗(包括所有种类的狗),并养牛、种植谷物等,这些动植物的祖先已不可考证;同时我们也被驯化了,自我驯化。我们的牙齿不断缩小(这要归功于烹煮),肌肉变得纤细,体毛渐渐褪去。科技驯化了我们。如同快速改造工具一样,我们也在快速改造自己。我们与科技同步进化,因此深深依赖于它。如果地球上所有科技——所有最新的刀和矛——都消失,人类的存在不会超过几个月。现在我们与科技共生。
我们迅速并且深刻地改变自己,同时也改变了世界。我们从非洲崛起,占领了这个星球上每一块适合居住的流域,从那一刻起,我们的发明开始改变我们的家园。现代智人的狩猎工具和技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凭借这些技术,他们可以杀光大型的食草动物(猛犸象、巨型麋鹿等),这些动物的灭绝永远地改变了整个草原生物群落的生态状况。一旦占统治地位的食草动物绝种,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有利于新的食肉动物和植物物种以及它们的所有竞争者和同盟军的兴盛,这些动植物构成了变动后的生态圈。就这样,少数类猿人氏族改变了数以千计的其他物种的命运。当现代智人学会控制火时,自然界受到这种强大科技的进一步大规模改造。如此微不足道的技巧——点燃草场,用逆火加以控制,然后引火烹煮谷物——破坏了各个大陆的大片地区。
此后,发明被不断复制,农业在全世界传播,这些过程影响的不仅是地球表面,还有厚度为100公里的大气层。耕作破坏了土壤,使二氧化碳含量上升。一些气候学家相信,8000年前开始的早期人为取暖阻止了新的冰川期的到来。农耕技术的广泛采用干扰了自然的气候循环,这种循环原本会使现在地球最北端的大部分地区重新冰冻。
无疑,就在人类发明使用古代植物的浓缩物(煤炭)而不是新鲜植物作为燃料的机器后,它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加剧了大气平衡的变动。随着机器使用这种储藏量丰富的能源,技术元素有了长足发展。诸如牵引发动机这样的以石油为能源的机器改良了农业生产率和传播方式(使这一古老的趋势加速),接着更多的机器以更快的速度产出更多的石油(新趋势),导致加速度的叠加。今天各类机器排出的二氧化碳大大超过了所有动物的排放量,甚至接近地质力量产生的排放量。
技术元素的巨大影响力不仅来自其规模,而且与自我放大的特性有关。一项突破性的发明,例如字母表、蒸汽泵,或者电能,可以引发进一步的突破性发明,例如书、煤矿和电话。这些科技进步反过来又引出其他突破性发明,例如图书馆、发电机和互联网。每一步都增加新的推动力,同时保留已有发明的大部分优点。某人有了想法(例如旋转的轮子),通过交流进入其他人的大脑,衍生出新想法(将旋转的轮子安放在雪橇下面,使它更容易拖动),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平衡被打破,变化出现了。
然而,不是所有的科技导致的变化都是积极的。产业化的奴隶制,如过去强加于非洲的那种体系,由装载俘虏漂洋过海的航船启动,受到轧棉机的激励,这种机器可以低成本加工由奴隶种植并收割的纤维。没有科技的推动,如此大规模的奴隶交易不会为人所知。上千种合成毒素大量破坏人类和其他物种的自然循环,这是由小发明引起的大祸害。战争,是由科技造成的强大负面力量经过放大的极其危险的结果。科技创新直接导致可怕的杀伤性武器的产生,这些武器可以让社会遭受全新的暴行。
另一方面,负面结果的纠正和抵消也来自科技。大多数早期的文明社会都实施过种族奴隶制,史前时期很可能也经历过,现在一些边远地区仍然在延续这一制度,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彻底灭亡归功于通信、法律和教育方面的科技发展。检测技术和替代品可以消除合成毒素的日常使用。监控技术、法律、协商、治安维持、法庭、城市媒体和经济全球化能够缓和、抑制并最终减少战争的恶性循环。
社会进步,即使是道德进步,终归也是人类的发明。它是我们意愿和思维的有益产物,因此也属于科技。我们可以断定,奴隶制不是好理念,公正的法律是好理念,对裙带关系的偏好是恶劣的思维。我们可以认为某项惩罚性条约不合法,可以通过文字的发明来激发人们的责任意识,还可以自觉地扩展志同道合的朋友圈。这些都是发明,是大脑思维的产物,与灯泡和电报一样。
这种促使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是由科技驱动的。社会进化需要渐进的推动力,历史上每个社会组织的产生都是通过注入新科技实现的。书写这一发明令成文法律的公正彰显出来。标准铸币这一发明使贸易更加普遍,鼓励创业精神,加速自由理念的形成。历史学家林恩·怀特评价道:“很少有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也很少有发明具备马镫这样的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在怀特看来,与马鞍搭配的矮马镫的使用方便了骑手在马背上使用武器,这使骑兵在对阵步兵时处于有利地位,有钱买马的君主也具有优势,于是欧洲的贵族封建制度就这样催生出来。马镫不是唯一因为有助于封建制度而受到指责的技术。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著名评论:“手工作坊孕育了封建主社会,蒸汽作坊孕育了产业资本家社会。”
复式记账法于1494年由圣方济各会修道士发明,从而使企业得以监控现金流并首次操作复杂的业务。威尼斯的银行业因复式记账法而崛起,开启了全球经济大门。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鼓励基督教徒自己解读本教的原始文本,导致基督教内部出现“抗议”这一特有的反宗教理念。早在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现代科学之父——就意识到科技正日益强大。他列举了三种改变世界的“实践艺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他宣称:“似乎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时代的开端对人类事务产生过像这些机械发明这样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帮助建立科学方法,加快发明的速度,从而导致社会的持续变动,就像一颗接一颗的观念种子打破了社会均衡。
表面上看,像时钟这样的简单发明引发了深远的社会效应。时钟将连续的时间流分割成可计量的单位,而时间一经拥有面孔,就露出专横嘴脸,指挥你的生活。计算机专家丹尼·希利斯相信,时钟装置可用来理解科学及其众多文化派生物。他说:“我们可以用时钟的机械结构来比喻自然法则的独立作用。(计算机按照预设规则呆板地运行,因此是时钟的直接派生物。)一旦我们能够把太阳系想象成钟表式的自动机器,那么将这种思维推广到大自然的其他方面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于是科学过程就这样开始了。”
工业革命期间,我们的发明改变了日常生活。新机器和便宜的燃料为我们带来大量食物、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和大烟囱。这个技术阶段是肮脏的、破坏性的,人们常以非人道的方式建设和管理社会。生铁、砖石和玻璃的坚硬、冰冷及不易弯曲的特性使高楼的遍地开花显得与人类——如果不是所有的生物——格格不入、互不相容。它们直接吞噬自然资源,因此给人们留下邪恶的印象。工业时代最糟糕的副产品是浓黑的烟尘、黑乎乎的河水和在工厂里劳动的黝黑的暴躁工人,这些距离我们所珍视的自我认知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想要相信工业化本身就是异化的,甚至更糟。将硬邦邦、冷冰冰的物质对社会的占领视为罪恶并不难,虽然这样的罪恶是必要的。当科技渗入我们古老的生活习性中时,我们认为它是异己之物,像对待传染病一样对待它。我们欢迎它的产品,但心怀罪恶感。一个世纪前,人们认为科技被上帝宣判有罪,这本应是荒唐可笑的。科技是一种可疑的力量。两次世界大战将创新产生的杀戮能力完全释放出来,巩固了科技作为迷人的撒旦的名声。
在我们从各个时代科技进步过程中寻找这种异化特性并进行净化后,它不再显得那么冷酷。我们开始看透科技的物质伪装,认为它首先是一种行为。虽然有外壳,但它的核心是柔软的。1949年,约翰·冯·诺伊曼——制造出第一台可用计算机的天才——认识到,计算机正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科技:“短期内以及更遥远的未来,科技将逐渐从强度、材质和能量问题转向结构、组织、信息和控制问题。”科技不再只是个名词,它正在成为一种力量,一种生机勃勃的精灵,要么推动我们前进,要么阻挡我们。它不是静态事物,而是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