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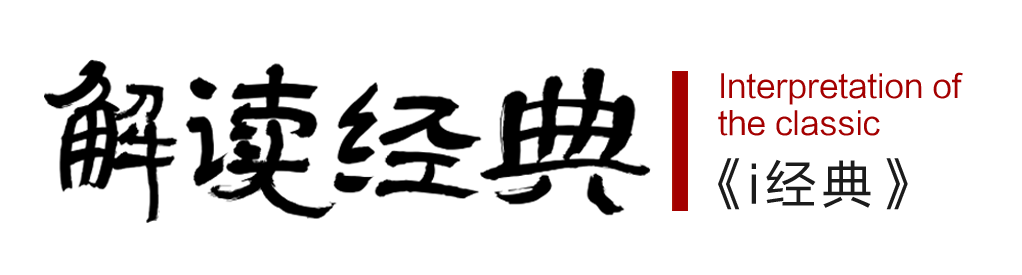
班扬曾描述了这样一个梦境:一个背负着沉重包袱的人手里拿着一本书,一面念一面不住地流泪,最后浑身颤抖着发出一声悲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梦中人名叫基督徒,他背上的包袱叫做原罪,手中的那本书叫做《圣经》,尽管原罪已经把他压得直不起腰来,他也绝不会放弃,只是虔诚地阅读《圣经》,期望能从中得到救赎。这本《天路历程》影响很大,据说当年投奔新大陆的欧洲人很多就带着它投奔美国。
但是,这个追求道德纯洁和完善的文化传统现在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两次世界大战带来极大的破坏,战后铁幕的高高耸立,对人类的震动非常之大。在残酷的战争和大屠杀罪行中,政府和政治家们头顶的光环在逐渐褪色,自由、博爱、平等的理想在渐渐崩解,理性和良知被践踏在脚下,整个西方社会出现了普遍的幻灭感,人们在不断反思和迷惑:我们的罪行真的可能被救赎吗?

《时光》也是如此。二战之后,原本乐观地认为黑暗从此远去,可这个期望不久就被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相继打破,尤其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越战,感受格外深刻,这点在开篇就表露无遗。在故事的一开始,虽然两仪师们将黑暗给予封印,可至上之力却被污染,转眼之间,原本依靠的力量就成了世界毁灭的根源。所有从真源获取力量的男性两仪师的结局都只能是变得疯狂,连开场的序章能听到的都是弑亲者痛苦的呻吟。
“这都是因为他。因为他傲慢地相信男人能够与创世主比肩,能够修复被破坏了的创世主的造物。他的傲慢让他有了这种结局。”这一段与其说是黎明之君的心理独白,倒不如说是那个被战争蹂躏的时代下人们对文明危机的一种直观感受。男性两仪师象征的破坏性力量,成了原罪的一种象征,在乔丹的笔下,女性占据了兰德大陆的主导地位,甚至有个国家男性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很多人不能理解身为男性作家的这种安排,将罗伯特·乔丹误解为极端女权主义者,而这一切并非为了卖座弄的噱头,其实更大的可能是源自那种对于力量黑暗面的深深疑惧。
与此同时,尽管在《时光》随处可见托尔金的影子,连《纽约时报》的评论都讥讽道“罗伯特·乔丹开始统治由托尔金一手开创的世界”,可是和《魔戒》那种传统基督教式的说教不同,大堆大堆的诡计阴谋、政治角逐、两性争斗,不仅直接表现在黑暗势力的入侵,更多地是出现在了善良阵营内部。这种善良之间斗争,反应出的是现代工业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疏远和冷漠,现实世界开始蜕变成一种异己,人性的善良在现实经验面前不值一提,一种若隐若现的孤独充斥在真龙的心里。拉尔夫最后痛苦地掉下眼泪,哀悼的是人类纯真的远去,而《时光》中兰德对两仪师的怀疑,怀疑的是人心中也许永远无法战胜的黑暗。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表示罗伯特·乔丹已经从根本上抛弃了人文主义的精神,恰恰相反的是,他对人的发展具有着更大的期待和追求。比如用太极双鱼来作为两仪师的标识,用转轮作为时光之轮的原型,田园牧歌般的旅族,都标志着作者一种有意识的尝试,想从古老的东方思想中找寻人类文明前进的希望。他所憎恨的是虚假的真善美,一旦直面残酷的现实,这些就会被摔得粉碎,带来的也只会是颓废的绝望,就像黎明君主一样将自我吞噬。只有真实的善良才可能具有真正的价值,只有用真实的善良的眼光才能从黑暗中掌握这个世界、掌握自我。在《世界之眼》结尾的战斗中,与《地域伯爵:黄金军团》的那一声自然在工业文明面前倒下的悲鸣完全不同,随着一株参天巨树从牺牲了的绿巨人中拔地而起,在巨森灵浑厚深远的歌声中,人性的善良似乎也得到了重生。我相信,不管乡间少年们走向何处,走向何等的黑暗,妖境中的巨人花园都能在真龙的心中留下永久的回忆,让黑暗不再降临兰德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