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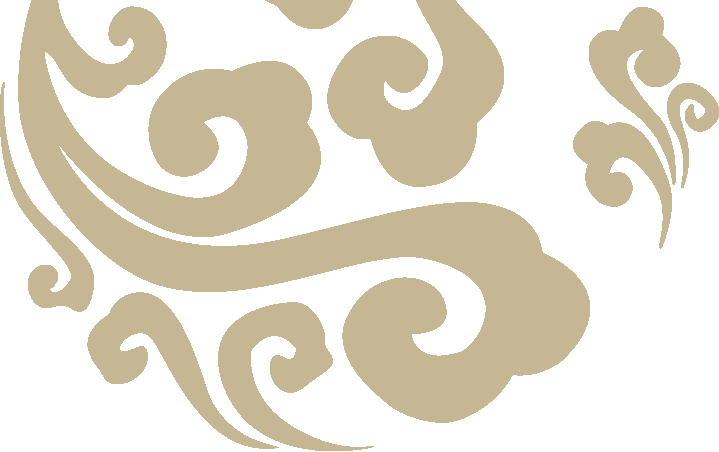
自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于民国十年(
1921
)发表后,红学研究出现一个新典范(
paradigm
)。许多学者相信“《红楼梦》是以曹家史实及雪芹个人经验为骨干和蓝本,然后加以穿插、拆合”,
 故致力于考证曹雪芹(
c1714-c1763
;
故致力于考证曹雪芹(
c1714-c1763
;
 名霑)的家世与生平,期盼能因此理解《红楼梦》的主题与情节,此一趋势令原本属于文学领域的“红学”延伸出属于史学范畴的所谓“曹学”。然因探索《红楼梦》的历史背景将不仅仅牵涉曹家,故笔者在本书中乃视“曹学”为广义“红学”的一部分。
名霑)的家世与生平,期盼能因此理解《红楼梦》的主题与情节,此一趋势令原本属于文学领域的“红学”延伸出属于史学范畴的所谓“曹学”。然因探索《红楼梦》的历史背景将不仅仅牵涉曹家,故笔者在本书中乃视“曹学”为广义“红学”的一部分。
有关曹雪芹之研究在其籍贯议题上达到巅峰,除了大量相关论文外,迄今竟然已有十几本专书析探此事,
 但依旧众说纷纭。“辽阳说”、“丰润说”等派相互辩难,惟因各有弱点,且又牵涉主观的地方意识与期盼的观光收益,以致各持己见,无法得到共识。对有些学者而言,
但依旧众说纷纭。“辽阳说”、“丰润说”等派相互辩难,惟因各有弱点,且又牵涉主观的地方意识与期盼的观光收益,以致各持己见,无法得到共识。对有些学者而言,
此一发展似已到了反客为主的地步;但不可否认,由于红学的受到重视,也增强了大家对清史尤其是八旗制度的兴趣与认识。
笔者原本是红学的门外汉,但因四年前在研究明亡清兴以及西炮传华的历史时,意外接触到学界有误认曹雪芹先祖曹振彦为红夷大炮教官的论述,遂开始研读相关材料。从而发现自吴桥兵变(
1632-1633
)以迄三藩之乱(
1673-1681
)的半个世纪中,包括曹氏家族在内的大量辽人(此一名词在明末即已行用,专指定居关外的汉人),迅速崛起于军事和政治的主舞台,并自边陲进入内地,
 协助清朝统治省级以下的各层行政单位,惟具体的相关研究并不多。
协助清朝统治省级以下的各层行政单位,惟具体的相关研究并不多。
由于“国方新造,用满臣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谙习满汉语文、典制与民俗的辽人,遂在清政权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如顺治一朝辽人即占全国总督和巡抚缺的约
77%
,布政使与按察使的
48%
,道员的
34%
,知府的
39%
,州县正官的
21%
。
 为透过较典型的个案及较扎实的研究,更清楚掌握此一特殊现象,笔者决定以曹雪芹等辽人家族在明末清初的发迹历程作为案例,希望能充分运用红学界先前丰盛的成果,以深化对清史的认识。
为透过较典型的个案及较扎实的研究,更清楚掌握此一特殊现象,笔者决定以曹雪芹等辽人家族在明末清初的发迹历程作为案例,希望能充分运用红学界先前丰盛的成果,以深化对清史的认识。
在过去十五年间,学界共出现千篇以上有关《红楼梦》的硕博士论文,但其中有关考证或版本者,竟只有十篇左右,这与资深学者间沸沸扬扬的论争形成强烈对比。
 此或由于年轻一代多认为红学的学术门坎颇高,其中又牵涉许多跨领域的知识,且因学界与红友们先前已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资料搜寻,故评估在短期内难有重大突破。尤有甚者,红学社群中火药味浓厚的派别之争,可能亦导致年轻学者不敢
此或由于年轻一代多认为红学的学术门坎颇高,其中又牵涉许多跨领域的知识,且因学界与红友们先前已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资料搜寻,故评估在短期内难有重大突破。尤有甚者,红学社群中火药味浓厚的派别之争,可能亦导致年轻学者不敢
踏进这块学术界的雷区。即如学界巨擘余英时先生,也曾说过“《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只要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笔墨官司”,并宣称从此只愿当一个红学的忠实读者。

然而,史学的研究环境在最近几年已发生滔天巨变。笔者在拙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首揭“
e
考据”之概念,指出随着古籍的大量景印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网际网络和资料库的普及,即使目前的数字环境仍未臻理想,但一位文史工作者往往有机会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在较短时间内通过逻辑推理的布局,填补探究历史细节时的隙缝。
 当然,许多未数字化的文献仍得用传统方式去发掘和耙梳,但我们已开始拥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们十分陌生却又梦寐以求的环境,且或已有条件提供红学蜕变或升华所需的动力。
当然,许多未数字化的文献仍得用传统方式去发掘和耙梳,但我们已开始拥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们十分陌生却又梦寐以求的环境,且或已有条件提供红学蜕变或升华所需的动力。
笔者因此在本书中尝试利用新的文史研究环境与方法,发掘新史料并带入新视角,希冀能以之作为 e 时代历史考据的范例。由于初涉红学,对相关背景知识和二手研究的掌握还不够全面,故论述间肯定会出现一些不周全或讹误之处,但深盼通过理性的批评与对话,能引发更多人对红学进行跨领域的学术激荡。
我转治红学的过程颇不顺利,初次申请研究补助时就遭拒,匿名评审以极主观的话语指出“无论从文学或史学的观点,本计划之执行与否,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学术意义”。拙文《〈红楼梦〉中“借省亲事写南巡”新考》被中研院某期刊退稿时,亦遭严词批评曰:
一个不信自传说,也不信文学创作必须有原型才能落笔,也不采史事取向的研究者,就会觉得这篇论文无聊、毫无意义……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绝不等于作品就必是亲身经历的。本文却要由此去找出曹雪芹乃亲耳听闻而作之证据,岂非思惟之跳跃。
从前述话语我们应可体会部分学界中人对红学研究的浓厚偏见。
笔者在想,若“新红学”的先行者胡适先生仍在世,不知他将如何面对这些批评?但也许我最该关心的是,适之先生不知会否欣赏我的努力?当中有些看法还直接挑战他先前的研究。我这人很容易自我感觉良好,相信胡先生在读到拙著的许多新发现时应该会极兴奋。
过去三、四年间笔者共发表了二十几篇相关论文,但本书并非论文集,而是将已有的成果重新消化并改写,部分观点和讹陋也藉此机会改订,并大幅增写了一些弥补隙缝的内容。尤其,费尽心力制作了百馀幅图表,以呈现较特殊之材料或较重要之人脉网络,这些大多是先前所未见的,希望能藉此在论述的过程中提供更具体的证据。
本研究的过程要感谢许多前辈及学友的指教与帮忙,其中包括波士顿大学的白谦慎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的薛龙春教授、台湾大学的刘广定教授、新竹中华大学的马以工教授、葡萄牙中国学院的金国平教授、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胡文彬教授及刘梦溪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庄吉发教授、北京中国社科院的定宜庄教授及刘小萌教授、丰润的宣玉荣先生、淮阴师范学院的张一民先生等等。
特别要点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瑞龙老师以及跟随我多年的游博清博士,他们无怨无悔地协助我购置相关出版物并查阅罕见文献,瑞龙更细心扮演此书文字编辑的角色。而我的助理卢正恒先生则不辞艰劳地耙梳满汉文的八旗档案,杨勇军博士与高树伟先生亦率直地提出许多批评与建议。这些小友连同这几年修习我所开设 e 考据课程的同学,他们一起见证并参与了我的学术冒险。
惭愧,脑海中有几位该志谢之人的名字却总想不起来,只好忝颜归罪于年逼耳顺的记忆力,到底是“江湖催人老”。面对 e 时代无限美好的旭日,眼前的学术生涯却已近黄昏,只能勉力尝试去登临周遭的山岳,并将亲见的景致以及亲历的感受让更多人分享。
最后,必须要感谢的是广大红迷,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资料或观点,往往有效缩短了我进入一陌生议题的学习过程,甚至提供一些极有帮助的研究切入点。网友虽然有时不是很理性,但他们却是 e 世代“学习共同体( learning community )”(借用日本教育学者佐藤学教授所提出并推动之概念)中的重要元素,并协力创造了 e 考据时代的特殊研究环境,由于书中引注不易且常难以溯源,只能在此一并致意。
2014 年 9 月定稿于风城脉望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