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回
第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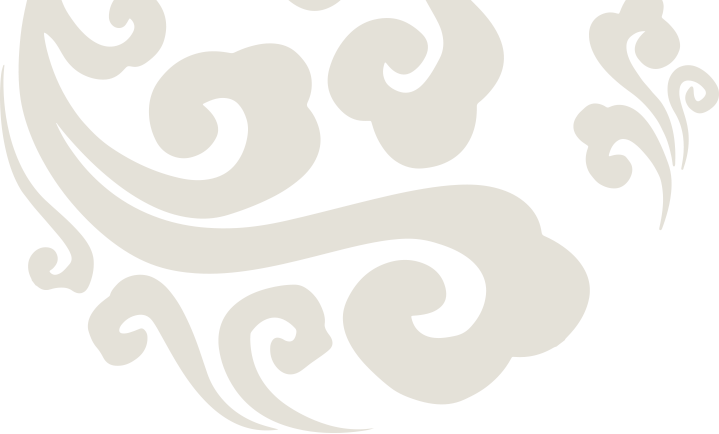
却说寺中有一老僧,出见匡胤。匡胤知非常僧,向他拱手。老僧慌忙答礼,且道:“小徒无知,冒犯贵人,幸勿见怪!”匡胤道:“贵人两字,仆不敢当,现拟投效戎行,路经贵地,无处住宿,特借宝刹暂寓一宵。哪知令徒不肯相容,并且恶语伤人,以至争执,亦乞高僧原谅!”老僧道:“点检作天子,已有定数,何必过谦。”匡胤听了此语,莫明其妙,便问点检为谁,老僧微笑道:“到了后来,自有分晓,此时不便饶舌。” 埋伏后文。 说毕,便把坠地的两僧唤他起来,且呵责道:“你等肉眼,哪识圣人?快去将客房收拾好了,准备贵客休息。”两僧无奈,应命起立。老僧复问及匡胤行囊,匡胤道:“只有箭囊弓袋,余无别物。”老僧又命两徒携往客房,自邀匡胤转入客堂,请他坐下,并呼小沙弥献茶。待茶已献入,才旁坐相陪。匡胤问他姓名,老僧道:“老衲自幼出家,至今已将百年,姓氏已经失记了。” 正史不载老僧姓氏,故借此略过。 匡胤道:“总有一个法号。”老僧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老僧尝自署空空,别人因呼我为空空和尚。”匡胤道:“法师寿至期颐,道行定然高妙,弟子愚昧,未识将来结局,还乞法师指示。”老僧道:“不敢,不敢。夹马营已呈异兆,香孩儿早现奇征,后福正不浅哩!”匡胤听了,越觉惊异,不禁离座下拜。老僧忙即避开,且合掌道:“阿弥陀佛,这是要折杀老衲了。”匡胤道:“法师已知过去,定识未来,就使天机不可泄漏,但弟子此时,正当落魄,应从何路前行,方可得志?”老僧道:“再向北行,便得奇遇了。”匡胤沉吟不答,老僧道:“贵人不必疑虑,区区资斧,老衲当代筹办。” 有此奇僧,真正难得。 匡胤道:“怎敢要法师破费。”老僧道:“结些香火缘,也是老衲分内事。今日在敝寺中荒宿一宵,明日即当送别,免得误过机缘。”说至此,即呼小沙弥至前,嘱咐道:“你引这位贵客到客房暂憩,休得怠慢!”小沙弥遵了师训,导匡胤出堂,老僧送出门外,向匡胤告辞,扶杖自去。
匡胤随至客房,见床榻被褥等都已整设,并且窗明几净,饶有一种清气,不觉欣慰异常。过了片刻,复由小沙弥搬入晚餐,野簌园蔬,清脆可赏。匡胤正饥肠辘辘,便龙吞虎饮了一番,吃到果腹,才行罢手。待残肴撤去,自觉身体疲倦,便睡在床上,向黑甜乡去了。一枕初觉,日已当窗,忙披衣起床,当有小沙弥入房,伺候盥洗,并进早餐,餐毕出外,老僧已扶杖伫候。两下相见,行过了礼,复相偕至客堂,谈了片刻。匡胤即欲告辞。老僧道:“且慢!老衲尚有薄酒三杯,权当饯行,且俟午后起程,尚为未晚。”匡胤乃复坐定,与老僧再谈时局,并问何日可致太平。老僧道:“中原混一,便可太平,为期也不远了。”匡胤道:“真人可曾出世?”老僧道:“远在千里,近在眼前,但总要戒杀好生,方能统一中原。” 赵氏得国之由,赖此一语。 匡胤道:“这个自然。”两下复纵论多时,但见日将亭午,由小沙弥搬进素肴,并热酒一壶,陈列已定,老僧请匡胤上坐,匡胤谦不敢当,且语老僧道:“蒙法师待爱,分坐抗礼,叨惠已多,怎敢僭居上位哩?”老僧微哂道:“好!好!目下蛟龙失水,潜德韬光,老衲尚得叨居主位,贵客还未僭越,老衲倒反僭越了。” 语中有刺。 言毕,遂分宾主坐下。随由老僧与匡胤斟酒,自己却用杯茗相陪,并向匡胤道:“老衲戒酒除荤,已好几十年了,只得用茶代酒,幸勿见罪!”匡胤复谦谢数语,饮了几杯,即请止酌。老僧也不多劝,即命沙弥进饭。匡胤吃了个饱,老僧只吃饭半碗,当由匡胤动疑,问他何故少食?老僧道:“并无他奇,不过服气一法。今日吃饭半碗,还是为客破戒哩。”匡胤道:“此法可学否?”老僧道:“这是禅门真诀,如贵客何用此法。” 天子玉食万方,何必辟谷。 匡胤方不多言。老僧一面命沙弥撤肴,一面命僧徒取出白银十两,赠与匡胤。匡胤再三推辞,老僧道:“不必,不必!这也由施主给与敝寺,老衲特转赠贵客,大约北行数日,便有栖枝。赆(jìn)仪虽少,已足敷用了。”匡胤方才领谢。老僧复道:“老衲并有数言赠别。”匡胤道:“敬听清诲!”老僧道:“遇郭乃安,历周始显,两日重光,囊木应谶。这十六字,请贵客记取便了。”匡胤茫然不解,但也不好絮问,只得答了“领教”两字。当下由僧徒送交箭囊弓袋,匡胤即起身拜别,并订后约道:“此行倘得如愿,定当相报。法师鉴察未来,何时再得重聚?”老僧道:“待到太平,自当聚首了。” 太平二字,是隐伏太平年号。 匡胤乃挟了箭囊,负了弓袋,徐步出寺,老僧送至寺门,道了“前途珍重”一语,便即入内。

匡胤遵着僧嘱,北向前进,在途饱看景色,纵观形势,恰也不甚寂寞。至渡过汉水,顺流而上,见前面层山叠嶂,很是险峻,山后隐隐有一大营,依险驻扎,并有大旗一面,悬空荡漾,烨烨生光。旗上有一大字,因被风吹着,急切看不清楚。再前行数十步,方认明是个“郭”字,当即触动观念,私下自忖道:“老僧说是‘遇郭乃安’,莫非就应在此处么?” 回顾前文。 便望着大营,抢步前趋。不到片刻,已抵营前。营外有守护兵立着,便向前问讯道:“贵营中的郭大帅,可曾在此么?”兵士道:“在这里。你是从何处来的?”匡胤道:“我离家多日了。现从襄阳到此。”兵士道:“你到此做甚么?”匡胤道:“特来拜谒大帅,情愿留营效力。”兵士道:“请道姓名来!”匡胤道:“我姓赵名匡胤,是涿州人氏,父现为都指挥使。”兵士伸舌道:“你父既为都指挥,何不在家享福,反来此投军?”匡胤道:“乱世出英雄,不乘此图些功业,尚待何时?” 壮士听者! 兵士道:“你有这番大志,我与你通报便了。”看官!你道这座大营,是何人管领,原来就是后周太祖郭威。他此时尚未篡汉,仕汉为枢密副使。隐帝初立,河中、永兴、凤翔三镇相继抗命。李守贞镇守河中,尤称桀骜,为三镇盟主。郭威受命西征,特任招慰安抚使,所有西面各军,统归节制,此时正发兵前进,在途暂憩。凑巧匡胤遇着,便向前投效。至兵士代他通报,由郭威召入,见他面方耳大,状貌魁梧,已是器重三分。当下问明籍贯,并及他祖父世系。匡胤应对详明,声音洪亮。郭威便道:“你父与我同寅,现方报绩凤翔,你如何不随父前去,反到我处投效呢?”匡胤述及父母宠爱,不许从军,并言潜身到此的情形。郭威乃向他说道:“将门出将,当非凡品,现且留我帐下,同往西征,俟立有功绩,当为保荐便了。” 郭雀儿恰也有识。 匡胤拜谢。嗣是留住郭营,随赴河中,披坚执锐,所向有功。至李守贞败死,河中平定,郭移任邺都留守,待遇匡胤,颇加优礼,惟始终不闻保荐,因此未得优叙。 无非留为己用。
既而郭威篡立,建国号周,匡胤得拔补东西班行首,并拜滑州副指挥。未几复调任开封府马直军使。世宗嗣位,竟命他入典禁兵。 历周始显,其言复验。 会北汉主刘崇,闻世宗新立,乘丧窥周,乃自率健卒三万人,并联结辽兵万余骑,入寇高平。世宗姓柴名荣,系郭威妻兄柴守礼子,为威义儿。威无子嗣,所以柴荣得立,庙号世宗。他年已逾壮,晓畅军机,郭威在日,曾封他为晋王,兼职侍中,掌判内外兵马事。既得北方警报,毫不慌忙,即亲率禁军,兼程北进。不两日,便到高平。适值汉兵大至,势如潮涌,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朔方铁骑,横厉无前,差不多有灭此朝食的气象。周世宗麾兵直前,两阵对圆,也没有什么评论,便将对将,兵对兵,各持军械,战斗起来。不到数合,忽周兵阵内,窜出一支马军,向汉投降,解甲弃械,北向呼万岁。还有步兵千余人,跟了过去,也情愿作为降虏。周主望将过去,看那甘心降汉的将弁,一个是樊爱能,一个是何徽,禁不住怒气勃勃,突出阵前,麾兵直上,喊杀连天。汉主刘崇见周主亲自督战,便令数百弓弩手一齐放箭,攒射周主。周主麾下的亲兵,用盾四蔽,虽把周主护住,麾盖上已齐集箭镞,约有好几十支。匡胤时在中军,语同列道:“主忧臣辱,主危臣死,我等难道作壁上观么?”言甫毕,即挺马跃出,手执一条通天棍,捣入敌阵。各将亦不甘退后,一拥齐出,任他箭如飞蝗,只是寻隙杀入。俗语尝言道:“一夫拼命,万夫莫当。”况有数十健将,数千锐卒,同心协力的杀将进去,眼见得敌兵搅乱,纷纷倒退。 是匡胤第一次大功。 周主见汉兵败走,更率军士奋勇追赶,汉兵越逃越乱,周兵越追越紧。等到汉主退入河东,闭城固守,周主方择地安营。樊爱能、何徽等军,被汉主拒绝,不准入城,没奈何仍回周营,束手待罪。周世宗立命斩首,全军股栗。 应该处斩。 翌日,再驱兵攻城,城上矢石如雨。匡胤复身先士卒,用火焚城。城上越觉惊慌,所有箭镞一齐射下。那时防不胜防,匡胤左臂竟被流矢射着,血流如注,他尚欲裹伤再攻,经周主瞧着,召令还营。且因顿兵城下,恐非久计,乃拔队退还,仍返汴都。擢匡胤为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世宗三年,复下令亲征淮南。淮南为李氏所据,国号南唐,主子叫作李璟。 南唐源流,见《五代史》。 他与周也是敌国。周主欲荡平江淮,所以发兵南下。匡胤自然从征,就是他父亲弘殷,也随周主南行。先锋叫作李重进,官拜归德节度使。到了正阳,南唐遣将刘彦贞引兵抵敌,被重进杀了一阵,唐兵大败,连彦贞的头颅也不知去向。匡胤继进,遇着唐将何延锡,一场鏖斗,又把他首级取了回来。 这等首级,太属松脆。 南唐大震,忙遣节度皇甫晖、姚凤等,领兵十余万,前来拦阻。两人闻周兵势盛,不敢前进,只驻守着清流关,拥众自固。清流关在滁州西南,倚山负水,势颇雄峻,更有十多万唐兵把守,显见是不易攻入。探马报入周营,周主未免沉吟。匡胤挺身前奏道:“臣愿得二万人,去夺此关。” 又是他来出头。 周主道:“卿虽忠勇,但闻关城坚固,皇甫晖、姚凤也是南唐健将,恐一时攻不下哩。”匡胤答道:“晖、凤两人,如果勇悍,理应开关出战,今乃逗留关内,明明畏怯不前,若我兵骤进,出其不意,一鼓便可夺关;且乘势掩入,生擒二将,也是容易。臣虽不才,愿当此任!”周主道:“要夺此关,除非掩袭一法不能成功。朕闻卿言,已知卿定足胜任,明日命卿往攻便了。” 世宗也是知人。 匡胤道:“事不宜迟,就在今日。”周主大喜,即拨兵二万名,令匡胤带领了去。
匡胤星夜前进,路上掩旗息鼓,寂无声响,只命各队鱼贯进行。及距关十里,天色将晓,急命军士疾进,到关已是黎明了。关上守兵,全然未知,尚是睡着。至鸡声催过数次,旭日已出东方,乃命侦骑出关,探察敌情。 如此疏忽,安能不败。 不意关门一开,即来了一员大将,手起刀落,连毙侦骑数人。守卒知是不妙,急欲阖住关门,偏偏五指已被剁落,晕倒地上。那周兵一哄而入,大刀阔斧,杀将进去。皇甫晖、姚凤两人,方在起床,骤闻周兵入关,吓得手足无措。还是皇甫晖稍有主意,飞走出室,跨马东奔。姚凤也顾命要紧,随着后尘,飞马窜去。可怜这十多万唐兵,只恨爹娘生得脚短,一时不及逃走,被周兵杀死无数。有一半侥幸逃生,都向滁州奔入。皇甫晖、姚凤一口气跑至滁城,回头一望,但见尘氛滚滚,旗帜央央,那周兵已似旋风一般追杀过来,他不觉连声叫苦,两下计议,只有把城外吊桥赶紧拆毁,还可阻住敌兵。当下传令拆桥,桥板撤去,总道濠渠宽广,急切不能飞越,谁知周兵追到濠边,一声呐喊,都投入水中,凫水而至。最奇怪的是统帅赵匡胤,勒马一跃,竟跳过七八丈的阔渠,绝不沾泥带水,安安稳稳的立住了。这一惊非同小可,忙避入城中,闭门拒守。
匡胤集众猛攻,四面架起云梯,将要督兵登城,忽城上有声传下道:“请周将答话!”匡胤应声道:“有话快说!”言毕,即举首仰望,但见城上传话的人并非别个,就是南唐节度使皇甫晖。他向匡胤拱手道:“来将莫非赵统帅?听我道来!我与你没甚大仇,不过各为其主,因此相争。你既袭据我清流关,还要追到此地,未免逼人太甚。大丈夫明战明胜,休要这般促狭。现在我与你约,请暂行停攻,容我成列出战,与你决一胜负。若我再行败衄,愿把此城奉献。”匡胤大笑道:“你无非是个缓兵计,我也不怕你使刁,限你半日,整军出来,我与你厮杀一场,赌个你死我活,教你死而无怨。”皇甫晖当然允诺。 自己还道好计,其实不如仍行前策,弃城了事,免得为人所擒。 匡胤乃暂令停攻,列阵待着。约过半日,果然城门开处,拥出许多唐兵,皇甫晖、姚凤并辔出城,正要上前搦战,忽觉前队大乱,一位盔甲鲜明的敌帅,带着锐卒,冲入阵来。皇甫晖措手不及,被来帅奋击一棍,正中左肩,顿时熬受不起,阿哟一声,撞落马下。姚凤急来相救,不防刀枪齐至,马先受伤,前蹄一蹶,也将姚凤掀翻。周兵趁势齐上,把皇甫晖、姚凤两人都生擒活捉去了。 这是匡胤第二次立功。 小子有诗咏道:

大业都从智勇来,偏师一出敌锋摧。
试看虏帅成擒日,毕竟奇功出异才。
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这位敌帅是赵匡胤了。欲知以后情状,请看官续阅下回。
读宋太祖本纪,载太祖舍襄阳僧寺,有老僧素善术数,劝之北往,并赠厚赆,太祖乃得启行,独老僧姓氏不传,意者其黄石老人之流亚欤?一经本回演述,借老僧之口,为后文写照,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于此可以见呼应之法焉。至太祖事周以后,所立功绩,莫如高平、清流关二役,著书人亦格外从详,不肯少略,为山九仞,基于一篑,此即宋太祖肇基之始,表而出之,所以昭实迹也。

 第三回
第三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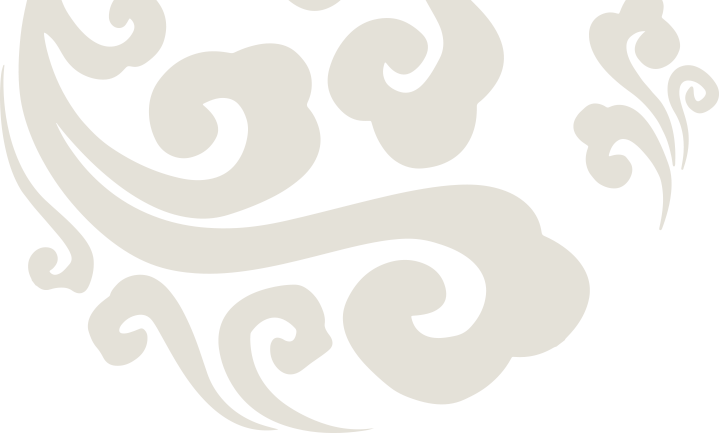
却说皇甫晖、姚凤既被周兵擒住,唐兵自然大溃,滁州城不战即下。匡胤入城安民,即遣使押解囚虏,向周主处报捷。周主受俘后,命翰林学士窦仪至滁州籍取库藏,由匡胤一一交付。既而匡胤复欲取库中绢匹,仪出阻道:“公初入滁,就使将库中宝藏一律取去,亦属无妨,今已籍为官物,应俟皇帝诏书,方可支付,请公勿怪!”匡胤闻言,毫无怒意,反婉颜谢道:“学士言是,我知错了!” 惟能知过,方期寡过。 过了一天,复有军事判官到来,与匡胤相见,两下叙谈,甚是投契。看官道是何人?乃是宋朝的开国元勋,历相太祖、太宗二朝,晋爵太师、魏国公,姓赵名普,字则平。 太祖受禅,普实与谋,此处特别表明,寓有微意。窦仪亦宋太祖功臣,故上文亦曾提出。 他祖籍幽蓟,因避乱迁居洛阳,匡胤本与相识,至是由周相范质荐举,乃至滁州,旧友重逢,倍增欢洽。会匡胤部下,受命清乡,捕得乡民百余名,统共指为匪盗,例当弃市。赵普独抗议道:“未曾审问明白,便将他一律杀死,倘或诬良为盗,岂非误伤人命?”匡胤笑道:“书生所见,未免太迂,须知此地人民,本是俘虏,我将他一律赦罪,已是法外施仁,今复甘作盗匪,若非立正典刑,如何儆众?”赵普道:“南唐虽系敌国,百姓究属何辜?况明公素负大志,极思统一中原,奈何秦、越相视,自分畛域?王道不外行仁,还乞明公三思!” 已阴目匡胤为天子。 匡胤道:“你若不怕劳苦,烦你去审讯便了。”赵普即去讯鞫,一一按验,多无左证,遂禀白匡胤,除犯赃定罪外,一律释放。乡民大悦,争颂匡胤慈明。匡胤益信赵普先见,凡有疑议,尽与筹商。赵普亦格外效忠,知无不言。适匡胤父弘殷亦率兵到滁,父子聚首,当然欣慰。不料隔了数日,弘殷竟生起病来,匡胤日夕侍奉,自不消说。谁料扬州警报,纷纷前来,周主也有诏书颁达,命匡胤速趋六合,兼援扬州。原来滁州既下,南唐大震,唐主李璟遣李德明乞和,愿割地罢兵,周主不许。德明返唐,唐主遂挑选精锐,得六万人,命弟齐王李景达为元帅,向江北进发,直抵扬州。扬州本南唐所据,与六合相距百余里,同为江北要塞。是时正由匡胤父弘殷受周主命,夺据扬州。弘殷西还入滁,留韩令坤居守。令坤闻唐兵大至,恐寡不敌众,飞向滁州求援。周主又敦促匡胤出师,匡胤内奉君命,外迫友情,怎敢坐视不发?无如父病未痊,一时又不忍远离,公义私恩,两相感触,不由的进退彷徨,骤难解决。当下与赵普熟商,赵普答道:“君命不可违,请公即日前行。若为尊翁起见,普愿代尽子职。”匡胤道:“这事何敢烦君?”赵普道:“公姓赵,普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嫌,公父即我父,一切视寒问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普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 后世如袁某等人,强认同姓为同宗,莫非就从此处学来? 匡胤拜谢道:“既蒙顾全宗谊,此后当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答礼道:“普何人斯?敢当重礼。”于是匡胤留普居守,把公私各事,都托付与普,自选健卒二千名,即日东行。

既至六合,闻扬州守将韩令坤已弃城西走,不禁大愤道:“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事去了。”便派兵驻扎冲道,阻住扬州溃军,并下令道:“如有扬州兵过此,尽行刖足,不准私放。”一面遗书韩令坤,略言“总角故交,素知兄勇,今闻怯退,殊出意料。兄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名,而今安在”云云。韩令坤被他一激,竟督兵返旆,仍还扬州拒守。
可巧南唐偏将陆孟俊从泰州杀到,令坤誓师道:“今日敌兵到来,我当与他决一死战,生与尔等同生,死与尔等同死。如或临阵退缩,立杀无赦,莫谓我不预言!”兵士齐声应命。令坤即命开城,自己一马当先,跃出城外。各军陆续随上,统是努力向前,拼命突阵。唐将陆孟俊即麾军对仗,不防周兵盛气前来,都似生龙活虎一般,见人便杀,逢马便斫,没一个拦阻得住,霎时间阵势散乱,被周兵捣入中坚。孟俊知不可敌,回马就逃,唐兵也各寻生路,弃了主帅,随处乱窜。韩令坤如何肯舍,只管认着陆孟俊紧紧追去,大约相距百步,由令坤取箭在手,搭住弓上,飕的一声,将孟俊射落马下。周兵争先赶上,立将孟俊揿住,捆绑过来。令坤见敌将就擒,方掌得胜鼓回城。 此功当归赵匡胤。 左右推上孟俊,令坤命絷入囚车,械送行在,正拟派员押解,忽由帐后闪出一妇人,带哭带语道:“请将军为妾作主,脔割贼将,为妾报仇。”令坤视之,乃是新纳簉(zào)室杨氏,便问道:“你与他有什么大仇?”杨氏道:“妾系潭州人氏,往年贼将孟俊攻入潭州,杀我家二百余口,惟妾一人为唐将马希崇所匿,方得免死。今仇人当前,如何不报?”原来杨氏饶有姿色,唐将马希崇掳取为妾,至韩令坤攻克扬州,希崇遁去,杨氏为令坤所得,见她一貌如花,也即纳为偏房,而且很加宠爱。此时闻杨氏言,即转讯孟俊。孟俊也不抵赖,只求速死。令坤乃令军士设起香案,上供杨氏父母牌位,爇(ruò)烛焚香,命杨氏先行拜告,然后将孟俊洗剥停当,推至案前,由自己拔出腰刀,刺胸挖心,取祭杨家父母,再命左右将他细剐。霎时间将肉割尽,把尸骨拖出郊外,喂饲猪犬去了。 为残杀者鉴。 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南唐元帅李景达闻孟俊被擒,亟与部下商议进兵,左右道:“韩令坤雄踞扬州,不易攻取,大王不如西攻六合,六合得下,扬州路断,也指日可取了。” 不能取扬州,乌能取六合?唐人全是呆鸟。 景达依计行事,乃向六合进发,距城二十里下寨,掘堑设栅,固守不出。匡胤也按兵勿动。两下相持约有数天,周将疑匡胤怯战,入帐禀白道:“扬州大捷,唐元帅必然丧胆,我军若乘势往击,定可得胜。”匡胤道:“诸将有所未知,我兵只有二千,若前去击他,他见我兵寥寥,反且胆壮起来,不若待他来战,我恰以逸待劳,不患不胜。” 前时攻清流关,妙在速进,此时屯兵六合,又妙在静待。 诸将道:“倘他潜师回去,如何是好?”匡胤道:“唐帅景达是唐主亲弟,他受命为诸道兵马元帅,俨然到此,怎好不战而遁,自损威风?我料他再阅数日,必前来挑战了。”诸将始不敢多言。又数日,果有探马来报,敌帅李景达已发兵前来了。匡胤即整军出城,摆好阵势,专待唐兵到来。不一时,果见唐兵摇旗呐喊,蜂拥而至,匡胤即指挥将士,上前奋斗。两下金鼓齐鸣,喧声震地,这一边是目无全虏,誓扫淮南,那一边是志在保邦,争雄江右。自巳牌杀到未牌,不分胜负,两军都有饥色。匡胤即鸣金收军,李景达也不相逼,退回原寨去了。
周兵闻金回城,由匡胤仔细检点,伤亡不过数十名,恰也没甚话说。既而令将士各呈皮笠,将士即奉笠献上。匡胤亲自阅毕,忽令数将士上前,瞋目语道:“你等为何不肯尽力?难道待敌人自毙么?”言毕,即喝令亲卒,把数将士缚住,推出斩首。众将茫然不解,因念同袍旧谊,不忍见诛,乃各上前代求,吁请恩宥。匡胤道:“诸将道我冤诬他么?今日临阵,各戴皮笠,为何这数人笠上留有剑痕?”言至此,即携笠指示,一一无讹。众将见了,愈觉不解。 我亦不解。 匡胤乃详语道:“彼众我寡,全仗人人效力,方可杀敌致功,我督战时,曾见他们退缩不前,特用剑斫他皮笠,作为标记,若非将他正法,岂不要大家效尤,那时如何用兵?只好将这座城池,拱手让敌了。”众将听到此言,吓得面面相觑,伸舌而退。转眼间已见有首级数颗,呈上帐前。 军令不得不严,并非匡胤残忍。 匡胤令传示各营,才将尸首埋葬。翌日黎明,便即升帐,召集将士,当面诫谕道:“若要退敌,全在今日,尔等须各自为战,不得后顾!果能人人奋勇,哪怕他兵多将广,管教他一败涂地哩。”诸将一一允诺,匡胤复召过牙将张琼,温颜与语道:“你前在寿春时,翼我过濠,城上强弩骤发,矢下如注,你能冒死不退,甚至箭镞入骨,尚无惧色,确是忠勇过人。今日拨兵千名,令你统率,先从间道绕至江口,截住唐兵后路,倘若唐兵败走,渡江南归,你便可乘势杀出,我亦当前来接应,先后夹攻,我料景达那厮,不遭杀死,也要溺死了。” 独操胜算。寿春事,从匡胤口中叙出,可省一段文字。 张琼领命去讫。
匡胤令将士饱食一餐,俟至辰牌时候,传令出兵。将士等踊跃出城,甫行里许,适见唐兵到来,大家争先突阵,不管甚么刀枪剑戟,越是敌兵多处,越要向前杀入。唐兵招架不住,只得倒退。景达自恃兵众,命部下分作两翼,包抄周军,不意围了这边,那边冲破,围了那边,这边冲破。忽有一彪人马,持着长矛,搠入中军,竟将景达马前的大纛(dào)旗钩倒。景达大惊,忙勒马退后,那周兵一哄前进,来取景达首级。亏得景达麾下拼命拦截,才得放走景达,逃了性命。唐兵见大旗已倒,主帅惊逃,还有何心恋战?顿时大溃,沿途弃甲抛戈,不计其数。匡胤下令军中,不准拾取军械,只准向前追敌。军士不敢违慢,大都策马疾追。可怜唐帅景达等,没命乱跑,看看到了江边,满拟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闻号炮一响,鼓角齐鸣,刺斜里闪出一支生力军,截住去路。景达不知所措,险些儿跌下马来。还是唐将岑楼景稍有胆力,仗着一柄大刀,出来抵敌,兜头碰着一员悍将,左手持盾,右手执刀,大呼:“来将休走!俺张琼在此,快献头来!” 张琼出现。 楼景大怒,抡刀跃马,直取张琼。张琼持刀相迎,两马相交,战到二十余合,却是棋逢敌手,战遇良材,偏匡胤率军追至,周将米信、李怀忠等都来助战,任你岑楼景力敌万夫,也只可挑出圈外,拖刀败走。这时候的李景达,早已跑到江滨觅得一只小舟,乱流径渡。唐兵尚有万人,急切寻不出大船,如何渡得过去?等到周兵追至,好似斫瓜切菜,一些儿不肯留情,眼见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几个善泅水的,解甲投江,凫水逃生,有几个不善泅水的,也想凫水逃命,怎奈身入水中,手足不能自主,漩涡一绕,沉入江心。岑楼景等都跨着骏马,到无可奈何的时节,加了一鞭,跃马入水,半沉半浮,好容易过江去了。 这是匡胤第三次立功。

南唐经这次败仗,精锐略尽,全国夺气。独周世宗自攻寿州,数月未克,正拟下令班师,忽接六合奏报,知匡胤已获大胜,亟召宰相范质等入议,欲改从扬州进兵,与匡胤等联络一气,下攻江南。范质奏道:“陛下自孟春出师,至今已入盛夏,兵力已疲,饷运未继,恐非万全之策。依臣愚见,不如回驾大梁,休息数月,等到兵精粮足,再图江南未迟。”世宗道:“偌大的寿州城,攻了数月,尚未能下,反耗我许多兵饷,朕实于心不甘。”范质再欲进谏,帐下有一人献议道:“陛下尽可还都,臣愿在此攻城!”世宗瞧着,乃是都招讨使李重进,便大喜道:“卿肯替朕任劳,尚有何说。”遂留兵万人,随李重进围攻寿州,自率范质等还都;并因赵匡胤等在外久劳,亦饬令还朝,另遣别将驻守滁、扬。
匡胤在六合闻命,引军还滁,入城省父。见弘殷病已痊可,并由弘殷述及,全赖赵判官一人日夕侍奉,才得渐愈。匡胤再拜谢赵普。至别将已来瓜代,即奉父弘殷,与赵普一同还汴。既至汴都,复随父入朝。世宗慰劳有加,且语匡胤道:“朕亲征南唐,历数诸将,功劳无出卿右,就是卿父弘殷,亦未尝无功足录,朕当旌赏卿家父子,为诸臣劝。”匡胤叩首道:“此皆陛下恩威,诸将戮力,臣实无功,不敢邀赏。” 何必客气 。世宗道:“赏功乃国家大典,卿勿过谦!”匡胤道:“判官赵普,具有大材,可以重用,幸陛下鉴察!” 以德报德。 世宗点首。退朝后,即封弘殷为检校司徒,兼天水县男;匡胤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赵普为节度推官。三人上表谢恩,自是匡胤父子,分典禁兵,桥梓齐荣,一时无两。相传唐李淳风作《推背图》,曾留有诗谶一首云:
此子生身在冀州,开口张弓立左猷。
自然穆穆乾坤上,敢将火镜向心头。 近见《推背图》中,此诗移置后文,闻由宋祖将图文互易,眩乱人目,故不依原次。
匡胤父子,生长涿郡,地当冀州,开口张弓,就是弘字,穆穆乾坤,就是得有天下,宋祖定国运,以火德王,所以称作火镜。还有梁宝志《铜牌记》,亦有“开口张弓左右边,子子孙孙万万年”二语。南唐主璟,因名子为弘冀,吴越王亦尝以弘字名子,统想符应图谶,哪知适应在弘殷身上,这真是不由人料了。欲知匡胤如何得国,且看下回分解。
宋太祖之婉谢窦仪,器重赵普,皆具有知人之明,而引为己用。至激责韩令坤数语,亦无一非用人之法。盖驾驭文士,当以软术牢笼之,驾驭武夫,当以威权驱使之,能刚能柔,而天下无难驭之材矣。若斫皮笠而诛惰军,作士气以挫强敌,皆驾驭武人之良策,要之不外刚柔相济而已。观此回,可以见宋太祖之智,并可以见宋太祖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