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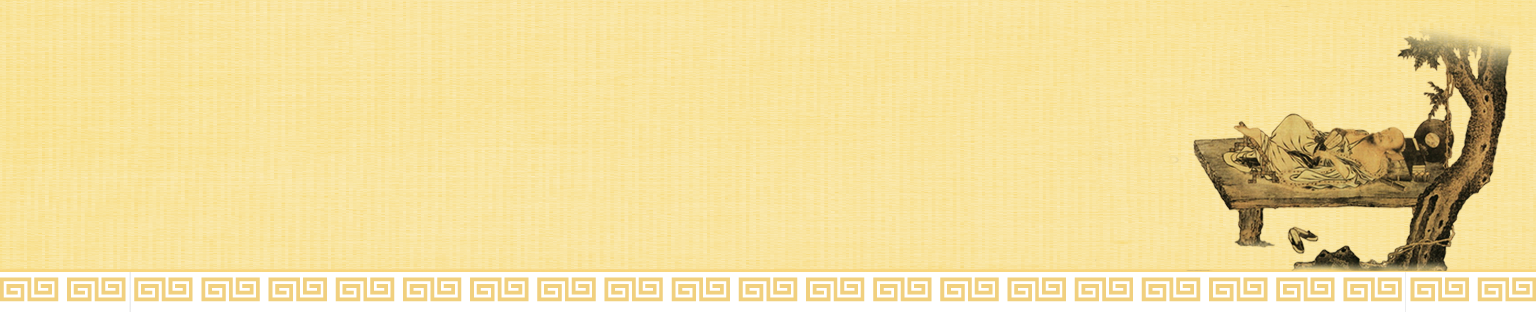
老聃之役
 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
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
 之山。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
之山。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
 仁者远之。拥肿
仁者远之。拥肿
 之与居,鞅掌
之与居,鞅掌
 之为使。居三年,畏垒大壤。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之子始来,吾洒然
之为使。居三年,畏垒大壤。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之子始来,吾洒然
 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馀。庶几其圣人乎!子胡不相与尸
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馀。庶几其圣人乎!子胡不相与尸
 而祝
而祝
 之,社而稷之乎?”
之,社而稷之乎?”
庚桑子闻之,南面而不释然。弟子异之,庚桑子曰:“弟子何异于予?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闻至人,尸居
 环堵之室
环堵之室
 ,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垒之细民,而窍窍焉欲俎豆
,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垒之细民,而窍窍焉欲俎豆
 予于贤人之间,我其杓
予于贤人之间,我其杓
 之人邪?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
之人邪?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
弟子曰:“不然。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鲵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㜸狐
 为之祥。且夫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而况畏垒之民乎!夫子亦听矣!”
为之祥。且夫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而况畏垒之民乎!夫子亦听矣!”
庚桑子曰:“小子来!夫函
 车之兽,介
车之兽,介
 而离山,则不免于网罟之患;吞舟之鱼,砀
而离山,则不免于网罟之患;吞舟之鱼,砀
 而失水,则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称扬哉!是其于辩也,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简发而栉,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
而失水,则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称扬哉!是其于辩也,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简发而栉,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
 。吾语汝: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吾语汝: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南荣趎
 蹴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长矣,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若此三年,则可以及此言矣。”南荣趎曰:“目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盲者不能自见;耳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聋者不能自闻;心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与形亦辟矣,而物或间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谓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趎勉闻道达耳矣!”庚桑子曰:“辞尽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
蹴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长矣,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若此三年,则可以及此言矣。”南荣趎曰:“目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盲者不能自见;耳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聋者不能自闻;心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与形亦辟矣,而物或间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谓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趎勉闻道达耳矣!”庚桑子曰:“辞尽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
 ,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鸡之与鸡,其德
,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鸡之与鸡,其德
 非不同也,有能与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
非不同也,有能与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
南荣趎赢
 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南荣趎曰:“唯”。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南荣趎惧然顾其后。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谓乎?”南荣趎俯而惭,仰而叹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问。”老子曰:“何谓也?”南荣趎曰:“不知乎?人谓我朱愚
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来乎?”南荣趎曰:“唯”。老子曰:“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南荣趎惧然顾其后。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谓乎?”南荣趎俯而惭,仰而叹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问。”老子曰:“何谓也?”南荣趎曰:“不知乎?人谓我朱愚
 。知乎?反愁我躯。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愿因楚而问之。”老子曰:“向吾见若眉睫之间,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规规然若丧父母,揭竿而求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怜哉!”
。知乎?反愁我躯。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愿因楚而问之。”老子曰:“向吾见若眉睫之间,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规规然若丧父母,揭竿而求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怜哉!”
南荣趎请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恶,十日自愁,复见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夫外韄
 者不可繁而捉,将内揵
者不可繁而捉,将内揵
 ;内韄者不可缪而捉,将外揵。外内韄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内韄者不可缪而捉,将外揵。外内韄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南荣趎曰:“里人有病,里人问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犹未病也。若趎之闻大道,譬犹饮药以加病也,趎愿闻卫生
 之经而已矣。”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
之经而已矣。”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
 不嗄
不嗄
 ,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掜
,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掜
 ,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瞚
,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瞚
 ,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据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
,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据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
南荣趎曰:“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谓冰解冰释者能乎?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
 ,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是谓卫生之经已。”曰:“然则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儿子乎?’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
,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是谓卫生之经已。”曰:“然则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儿子乎?’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

老聃有个门徒叫庚桑楚,独得老聃的真传,在北边的畏垒山上居住,他辞退炫耀聪明的奴仆,疏远标榜仁义的侍婢,只与淳朴善良的人住在一起,差遣那些勤劳勇敢的人为他做事。就这样过了三年,畏垒山一带获得大丰收。畏垒山一带的百姓见面之后都说:“庚桑楚刚来畏垒山的时候,我们都微微吃惊感到诧异。如今我们对收成按日计算感到不足,但一年总的收成也还是富足有余。庚桑楚恐怕就是圣人了吧!大家何不共同像供奉神灵一样供奉他,为他建立宗庙呢?”
庚桑楚听到大家对他的评论之后,面向南方,心里很不高兴。弟子们感到奇怪。庚桑楚说:“你们对我有什么感到奇怪呢?春天阳气蒸腾勃发百草生长,正当秋天时节庄稼成熟果实累累。春天与秋天,难道无所遵循就能够这样吗?这是自然规律的运行与变化。我听说道德修养极高的人,像没有生命的人一样虚淡宁静地生活在斗室小屋内,而百姓纵任不羁全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现在畏垒山区的百姓,都私下议论,想把我推举为贤人来供奉,我难道是那种爱出风头的人吗!我面对老聃的教导而感到焦虑。”
弟子说:“不是这样,深八尺,长一丈六尺的小水沟,大鱼在里面无法转动身体,而小鱼却来去自如;巨兽在小土丘上无法隐藏自己,而狐狸却可以兴风作乱。况且尊奉贤人,授权给能人,把利禄先赏赐给善人,古代的尧舜就是这样,何况畏垒山区百姓呢?先生就听他们的吧!”
庚桑子说:“小子们,过来,含车的巨兽。单独离开山林,就不免于受到网罗的祸患;吞船的大鱼,因潮汐激荡而离水搁浅于岸,就会受蝼蚁的困苦。所以鸟兽不厌山高,鱼鳖不厌水深。要全形养性的人,隐身之所,也是不厌深远罢了。至于尧与舜两个人,又哪里值得加以称赞和褒扬呢!尧与舜那样分辨世上的善恶贤愚,就像是在胡乱地毁坏好端端的垣墙而去种上没有什么用处的蓬蒿。选择头发来梳理,点数米粒来烹煮,计较于区区小事又怎么能够有益于世啊!举荐贤人就会使人们相互欺诈,使用智谋,百姓就会出现相互欺诈。这数种做法,不足以给人民带来好处。人们追求私利向来心切,导致有的儿子杀了父亲,有的臣子杀了国君,白天抢夺偷盗,光天化日之下在别人墙上打洞。我告诉你,天下大乱的根源,必定生于尧舜的时代,它的流弊又一定会留存于千年以后。千年之后,必然会出现人吃人的悲剧啊!”
南荣趎恭敬地端坐着,说:“对于我这样年纪大的人来说,该如何学习才能达到你所说的那种境界呢?”庚桑子说:“保全你的形体,保持你的天性,不要让自己思虑劳累。这样经过二年,你就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了。”南荣椨说:“盲人的眼睛与常人的眼睛,在外形上看不出有何不同,而盲人却看不见东西;聋子的耳朵与常人的耳朵,在外形上看不出有何不同,而聋子却听不到声音;狂人的心与常人的心,在外形上看不出有何不同,而狂人却不能自适。我的形体与别人的形体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想要知道至道之言却不能,想来恐怕有什么东西堵塞着吧?如今先生对我说:‘保全我的身形,保持我的天性,不要让自己思虑劳累’我只不过勉强听到耳里罢了!”庚桑楚说:“我的话已经讲完了。小土蜂不能孵化出豆叶虫,越鸡不能孵化天鹅蛋,而鲁鸡却能够做到。鸡与鸡,它们的禀赋并没有什么不同,有的能做到有的不能做到,是因为它们的本领原本就有大有小。拿现在说我的才干就很小,不足以使你受到感化,你何不到南方去拜见老子?”
南荣趎带足干粮,走了七天七夜来到老子的住所。老子说:“你是从庚桑楚那儿来的吧?”南荣趎说:“是的。”老子说:“你为什么带这么多人来?”南荣趎以为真的有人,恐惧地回过头看自己的身后。老子说:“你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南荣趎惭傀地低下头来,然后又仰面叹息:“现在我已忘记了我自己的答案,因此也忘记了自己想提出的问题。”老子说:“什么意思呢?”南荣趎说:“不聪明,人们说我愚昧无知。聪明,反而给身体带来愁苦和危难。不具仁爱之心便会伤害他人,推广仁爱之心反而给自身带来愁苦和危难。不讲信义便会伤害他人,推广信义反而给自己带来愁苦和危难。这三句话所说的情况,正是我忧患的事,希望因为庚桑楚的引介而获得赐教。”老子说:“刚来时我察看你眉宇之间,也就借此了解了你的心思。如今你的谈话更证明了我的观察。你失神的样子真像是失去了父母,又好像在举着竹竿探测深深的大海。你确实是一个丧失了真性的人啊,是那么迷惘而又昏昧!你一心想返归你的真情与本性却不知道从哪里做起,实在是值得同情啊!”
南荣趎回到寓所,求取自己所喜好的东西,舍弃自己所讨厌的东西,整整十天愁思苦想,再去拜见老子。老子说:“你正在去伪存真,自我反省,为什么还闷闷不乐呢?可见心中仍有恶念滋生。被外物束缚的人,不可患得患失,惊惶失措,只要心神内守,便可从内部解脱。被心事缠累的人,不可焦虑烦躁,急于求成,只要开阔胸襟,便可从外部解脱。内心和外界都有牵累的人,即便富有道德,也不能超然获释,何况是刚刚学道的人呢!”
南荣趎说:“村里有人生病,邻里前去看他,他能说出自己的病情,而能够把自己的病情说个清楚的人,那就算不上是生了重病。像我这样的听闻大道,好比服用了药物反而加重了病情,因而我只希望能听到养护生命的常规罢了。”老子说:“护身养性的原则,能使人保全纯一的天性吗?能不丧失本性吗?能不用占卜就先知道吉凶祸福吗?能使人止于本分吗?能让人知足吗?能不去效法别人而只是自求吗?能往来无拘束吗?能懵然无知吗?能像婴儿那样天真无邪吗?婴儿整日放声哭叫而喉咙没有沙哑,这是纯任和顺之声自然发出的缘故;婴儿整日握着手而手不会拳曲,这是合于本性的缘故;婴儿整日看着而不眨眼,这是目光没有偏滞在外物上的缘故;行走起来不知道去哪里,平日居处不知道做什么,接触外物随顺应合,如同随波逐流、听其自然:这就是养护生命的常规了。”
南荣趎说:“那么这就是至人的最高思想境界吗?”老子回答:“不是的。这仅只是所谓像冰冻消解一样自然消除心中积滞的本能吧?道德修养最高尚的人,跟人们一块儿向大地寻食而又跟人们一块儿向天寻乐,不因外在的人物或利害而扰乱自己,不参与怪异,不参与图谋,不参与尘俗的事务,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走了,又心神宁寂无所执着地到来。这就是所说的养护生命的常规。”南荣趎说:“那么这就达到最高境界了吗?”老子说:“没有达到。我曾告诉你说:‘能像婴儿那样天真无邪吗?’婴儿行动时不知要做什么,走起路来不知要到哪里去,形体像枯树枝而内心如死灰。像这样,祸也不会到,福也不会来。没有祸福,哪里还会有人为的灾害呢!”
宇
 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谓之天民;天之所助,谓之天子。
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谓之天民;天之所助,谓之天子。
学者,学其所不能学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辩者,辩其所不能辩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钧败之。
备物以将形,藏不虞
 以生心,敬中以达彼,若是而万恶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内于灵台。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见其诚己而发,每发而不当,业入而不舍,每更为失。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幽闲之中者,鬼得而诛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后能独行。
以生心,敬中以达彼,若是而万恶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内于灵台。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见其诚己而发,每发而不当,业入而不舍,每更为失。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幽闲之中者,鬼得而诛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后能独行。
券
 内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费。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费者,唯贾人也,人见其跂,犹之魁然。与物穷者,物入焉;与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亲,无亲者尽人。兵莫憯
内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费。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费者,唯贾人也,人见其跂,犹之魁然。与物穷者,物入焉;与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亲,无亲者尽人。兵莫憯
 于志,镆铘为下;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
于志,镆铘为下;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

心境安泰镇定的人,就会发出自然的光芒。发出自然光芒的,就会人现其形,物现其状。人能守静修炼,才能具有恒常的本性;有恒常的本性,人们就会依附于他,自然也会帮助他。人们来依附的,称他为天民,自然帮助的,称他为天子。
学习的人,想学习他不能学到的东西;实行的人,想实行他不能做到的事情;辩论的人,辩他所不能辩的。知识的探求在他所不能知的境域停止,便达到最高的境界。如果不遵循这一点的话,自然注定要失败。
具备形成耳目之物以养形体,深敛外在情感不作任何思虑而使心境快活并富有生气,谨慎地持守心中的一点灵气用以通达外在事物。如果达到这种境界还有种种灾祸到来,那都是自然安排的结果,而不是人为的结果,不足以扰乱德性,不能纳入高于万物的内心。心灵有主见而行之义无主见,不可有意把持,还看不见诚成于己就向外发作,每次发作都是不恰当的,外事一旦侵扰心中就不会轻易离去,即使有所改变也会留下创伤。在光天化日下做了坏事,人人都会谴责他、处罚他;背地里做坏事的,会受到鬼的谴责。能够坦然地面对他人,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良心,才能够无忧无虑地独来独往。
名分合乎自身,行事就不显于名声;名分超出自身,就是心思也总在于穷尽财用。行事不显名声的人,即使平庸也有光辉;心思在于穷尽财用的人,只不过是商人而已,人人都能看清他们在奋力追求分外的东西,还自以为泰然无危。跟外物顺应相通的人,外物必将归依于他;跟外物相互阻遏的人,他们自身都不能相容,又怎么能容纳他人!不能容人的人没有亲近,没有亲近的人也就为人们所弃绝。兵器没有什么能对人的心神作出伤害,从这一意义说良剑莫邪也只能算是下等;寇敌没有什么比阴阳的变异更为巨大,因为任何人也没有办法逃脱出天地之间。其实并非阴阳的变异伤害他人,而是人们心神自扰不能顺应阴阳的变化而使自身受到伤害。
道通其分
 也,其成也毁也。所恶乎分者,其分也以备;所以恶乎备者,其有以备。故出而不反,见其鬼;出而得,是谓得死。灭而有实,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
也,其成也毁也。所恶乎分者,其分也以备;所以恶乎备者,其有以备。故出而不反,见其鬼;出而得,是谓得死。灭而有实,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
出无本,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
 ,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
,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

从道的观点来看事物是齐一无别的,万物总体的分就是众体的成,新事物的成又是旧事物的毁,因此,不管怎样分散,它的分散是完备的;所以不管怎样完备,还是追求更大的完备。所以,这种人心神离散外逐欲情而不能返归,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心神离散外逐欲情而能有所得,这就叫做接近于死亡。真性已经泯灭而徒具形骸的人,属于鬼的一类。把有形的东西看作是无形,那么内心就会得到安宁。
产生没有根本,消逝没有踪迹。具有实在的形体却看不见确切的处所,有成长却见不到成长的始末,有所产生却没有产生的孔窍的情况又实际存在着。具有实在的形体而看不见确切的处所的,是因为处在四方上下没有边际的空间中。有成长却见不到成长的始末,是因为处在古往今来没有极限的时间里。有生,有死,有出,有入,来无影、去无踪的,是造物的门户。所谓造物的门户,就是“无有”。万物生于“无有”。“有”不能从“有”生出,必定生于“无有”,而“无有”是“无”和“有”的统一。圣人游心于这种境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将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
 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为首,以生为体,以死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为友。是三者虽异,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为首,以生为体,以死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为友。是三者虽异,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有生,黬
 也,披然曰移是。尝言移是,非所言也。虽然,不可知者也。腊者之有膍
也,披然曰移是。尝言移是,非所言也。虽然,不可知者也。腊者之有膍
 胲
胲
 ,可散而不可散也。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为是举移是。
,可散而不可散也。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为是举移是。
请常言移是。是以生为本,以知为师。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实;因以己为质,使人以为己节,因以死偿节。若然者,以用为知,以不用为愚,以彻为名,以穷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与学鸠同于同也。

古时候的人,他们的才智已经达到最高的境界。什么样的是最高境界呢?有认为宇宙初始是不曾有物的,这种观点是最高明的,最完美的了,不可以再添加什么了。再次一等的人认为宇宙初始已经存在事物,他们把产生看作是另一种事物的失落,他们把消逝看作是返归自然,而这样的观点已经对事物有了区分。再次一等认为宇宙初始确实什么都没有,后来产生了生命,有生命的东西又很快地死去;他们把无看作是头,把生看作躯体,把死亡看作是尾脊。谁能懂得生死存亡是一体的,我就跟他交朋友。以上三种认识虽然各有不同,但从万物一体的观点看却并没有什么差异,犹如楚国王族中昭、景二姓,以世代为官而著显,屈姓,又以世代封赏而著显,只不过是姓氏不同罢了。
世上存在生命,乃是从昏暗中产生出来,生命一旦产生彼与此、是与非,就在不停地转移而不易分辨。让我来谈谈转移和分辨,其实这本不足以谈论。虽然如此,即使谈论了也是不可以明了的。譬如说,年终时大祭备有牛牲的内脏和四肢,可以分别陈列却又不可以离散整体牛牲;又譬如说,游观王室的人周旋于整个宗庙,但同时又必须上厕所。像这些例子全都说明彼与此、是与非在不停地转移。
请让我再进一步谈谈是非的转移和不定。它是以生命为根本,以智能为指导,因而滋生出是非。果真有名与实的区别,因而把自己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让人以自己为节操的榜样,以至于用死来偿节。像这样,就是以用于世为聪明,以不用于世为愚蠢:以显达为荣耀,以困厄为耻辱。如此转移的正是现在的人,犹如蜩与学鸠一样,同样是无知的。
蹍
 市人之足,则辞以放骜
市人之足,则辞以放骜
 ,兄则以妪,大亲则已矣。故曰,至礼有不人,至义不物,至知不谋,至仁无亲,至信辟金。
,兄则以妪,大亲则已矣。故曰,至礼有不人,至义不物,至知不谋,至仁无亲,至信辟金。

误踩了街市上行人的脚,就要赔礼说自己太放肆,误踩了兄长的脚就要加以抚慰,踩了父母的脚连抚慰也不用了。因此说,最好的礼仪就是不分彼此视人如己,最好的道义就是不分物我各得其宜,最高的智慧就是无须谋虑,最大的仁爱就是对任何人也不表示亲近,最大的诚信就是无须用贵重的东西作为凭证。
彻
 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道者,德之钦
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道者,德之钦
 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谟
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谟
 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动以不得已之谓德,动无非我之谓治,名相反而实相顺也。
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动以不得已之谓德,动无非我之谓治,名相反而实相顺也。

所以,应当撤除意志的紊乱,解开心灵的枷锁,去除德性的拖累,沟通大道的障碍。高贵、殷富、显达、威严、功名、利禄六者,是错乱意志的;容貌、举动、色彩、情理、辞气、意志六者,是束缚心灵的;憎恶、偏爱、喜悦、愤怒、悲哀、欢乐六者,是拖累德性的;舍弃、依从、获取、给与、知虑、技能六者,是阻碍大道的。只要这四方面所包含的二十四种内容不在胸中作怪,就可以做到内心的平正。内心平正就会宁静,宁静就会明澈,明澈就会虚空,虚空就能恬适顺应无所作为而又无所不为。大道,是自然的敬仰;生命,是盛德的光华;察性,是生命的本根。合乎本性的行动,称之为率真的作为;受伪情驱使而行动,称之为失却本性。知识,出自与外物的应接;智慧,出自内心的谋划;具有智慧的人也会有不了解的知识,就像斜着眼睛看,所见必定有限。有所举动却出于不得已叫做德,有所举动却不是为了自我叫做治,追求名声必定适得其反,而讲求实际就会事事顺应。
羿工
 乎中
乎中
 微而拙乎使人无己誉。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
微而拙乎使人无己誉。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
 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虫能虫,唯虫能天。全人恶天,恶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虫能虫,唯虫能天。全人恶天,恶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后羿善于射中微小的目标而不善于使人不奉承自己;圣人善于顺应天时而不善于处理人事;只有全人才能做到上应天德而下契人性。即使人们把全人当做虫子,他也会这样看待自己;虽然把自己看做虫子,也是完全符合自然的。全人讨厌“天”是讨厌人为的“天”,何况把天理与人性对立起来呢!
一雀适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是故汤以胞人
 笼
笼
 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笼之而可得者,无有也。
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笼之而可得者,无有也。

一只麻雀向羿飞来,羿必然能够将它射落。但若麻雀不飞进他的射程,就有逃脱的可能性。要是扩大范围,把天下当做鸟笼,麻雀就无处脱逃了。所以,商汤以厨工之职笼络伊尹,秦穆公用五张羊皮笼络百里奚,都是因人之情,顺其所好。如果不投其所好,想笼络人心,那是不可能的。
介者拸
 画,外非誉也;胥靡登高而不惧,遗死生也。夫复謵
画,外非誉也;胥靡登高而不惧,遗死生也。夫复謵
 不馈而忘人;忘人,因以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出怒不怒,则怒出于不怒矣;出为无为,则为出于无为矣。欲静则平气,欲神则顺心。有为也欲当,则缘于不得已。不得已之类,圣人之道。
不馈而忘人;忘人,因以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出怒不怒,则怒出于不怒矣;出为无为,则为出于无为矣。欲静则平气,欲神则顺心。有为也欲当,则缘于不得已。不得已之类,圣人之道。

砍断了脚的人不图修饰,因为已把毁誉置之度外;服役的囚徒登上高处不存恐惧,因为已经忘掉了死生。对于谦卑的言语不愿作出回报而忘掉了他人,能够忘掉他人的人,就可称作合于自然之理又忘却人道之情的“天人”。所以,敬重他却不感到欣喜,侮辱他却不会愤怒的人,只有混同于自然顺和之气的人才能够这样。怒气虽发而不是有心发怒,那么,这怒气就是无怒而发,在无为的情况下有所作为,所作所为就是出于无为了。要安静就要平气,要通灵就要顺心。要使自己的作为合乎天道,就要寄托于不得已。不得已而作,才是圣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