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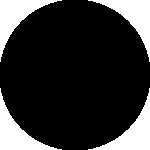
这本书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对《人间词话》的随文讲解,更着力处是将《人间词话》放进哲学、美学与时代的大坐标里。
1954年12月27日,傅雷给远在波兰的长子傅聪写信,叮嘱他保重身体以备战钢琴比赛,最后还不忘记以“舵工”的姿态指导他读书要领:“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一个人没有性灵,光谈理论,其不成为现代学究、当世腐儒、八股专家也鲜矣!”艺术总是相通的,钢琴家也需要借《人间词话》这把金钥匙来开发性灵,正所谓功夫在琴外,在一切技巧之外。但是,这把金钥匙易得而难用:“《人间词话》,青年们读得懂的太少了;肚里要不是先有上百首诗,几十首词,读此书也就无用。”
傅雷这番话虽然指出了《人间词话》的阅读门槛,却一点也不会令人生畏。肚里储备百余首诗词而已,这虽然算不得天下最简单的事情,至少也和“困难”二字绝不沾边。今天的中学生、大学生毕竟和傅雷时代的同龄人不同,只要按部就班地上过语文课,几乎都能轻松跨过这个门槛。所以傅雷在六十年前的告诫,在今天看来反而变成一种莫大的鼓励。
也许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人间词话》在今天被指定为中学生语文课外读物。但是,傅雷及其笃信者们实在大大低估了《人间词话》的阅读门槛,或者说,百余首诗词的阅读储备无论如何都要算是所有门槛中最容易跨过的一个。
这倒不是说王国维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有意搞得多么高深莫测,而是因为《人间词话》是处于新旧时代之交与中西学术之交的一部极特殊的理论著作,它的传统性使我们无法按照现代学术论文的严谨风格来理解它,它的现代性又使我们无法遵循中国古典文论的惯常套路来分析它。它在含而不露地以康德、叔本华的美学体系来阐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而康德和叔本华,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是两个何等令人生畏的名字啊,更何况王国维时而以中国传统诗论那种大大有欠严谨的表达形式来表达西方美学的严密体系……
所以《人间词话》可谓美学界的《红楼梦》:因为杰出,所以被仰望;因为复杂,所以使太多研究者以恋爱般的狂热投入聚讼纷纭的浪潮,由此开辟出各式各样的解读路径。认为《人间词话》通俗易懂的,也只有真正的门外汉了。
为了便于普通读者理解,我在这本书里除了仔细分析理论背景之外,还会更多地列举一些诗词实例,以作品选讲配合理论思辨,做足百余首诗词的积淀。事实上,本书总共选讲的诗词在二百五十首左右。
乍看起来,《人间词话》太符合今天这个快餐时代的阅读风格:两三句话便是一个独立章节,只是作者零星记录下来的心得随感而已,既没有回环往复的逻辑思辨,亦不见构建理论体系的宏大规模,就连语言也只是古汉语里最易读的那一类罢了。但是,倘若我们真的以睡前三五分钟随手一翻的姿态阅读《人间词话》,就会不自觉地陷入无数个陷阱里去。
最害人的陷阱是一些再常见不过的语词,譬如“境界”。
“境界”是《人间词话》最核心的概念,但它与“精神修养”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叔本华美学体系的一件中式外衣而已。倘若王国维存心将《人间词话》写成一部理论专著,那么他对“境界”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一定会做出精准的阐释,并且会在全文当中一以贯之地使用这个术语,而他偏偏写的是一部札记或随笔,于是既不曾界定过自己的特殊概念,甚至同一个“境界”时而做美学术语来用,时而做日常语词来用,读者稍不留心就会混淆;再如“理想”“赤子之心”“优美”“宏壮”“崇高”“关系”“限制”等,各有其西学背景,背后是一整套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体系;再如“兴趣”这样的词,另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专门概念,也不能以interest简单视之。
阅读常会遇到这样的语词陷阱:有些词汇一望可知是专业名词,但有些专业名词披着日常词汇的外衣,常常能够迷惑读者。比如一本书的题目是Plant Tissue Culture,三个单词都很普通,翻译过来是“植物手纸文化”,但这其实是一本生物学专业书,正确的译名是《植物组织培养》。
俞平伯曾在《重印〈人间词话〉序》中盛赞这部词话“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这话一点不错,王国维正是以十足的厚积做十足的薄发,而读者纵然不至于“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读”,至少也要做好相应的知识储备才行。
王国维在美学上的一大贡献是以西方的哲学、美学来分析、解释中国文学,所以为了读懂《人间词话》,我们首先要读懂王国维的西学背景,而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这部《人间词话》并非凭空立论,而是一部“对话之书”,时时处处都在针对着他那个时代的词坛风气,与当时词坛名宿和曩昔词学大家隔空过招。矫枉难免过正,所以我们若不想仅从字面上偏颇地理解王国维的一些观点,就有必要多做一些功课,了解他的对手们都有怎样的看家本领。
譬如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一个点或一个线段,只有看清这个点或线段所在的坐标,才能够正确理解它的意义。这正是我这本书最着力要做的事情:梳理出王国维的学术背景,梳理出有清一代的文学背景,将《人间词话》准确标识在由这两个坐标轴交叉而成的大坐标里。我很希望读者可以从这个大坐标里获得高屋建瓴的视角和融会贯通的体验,如此一来,《人间词话》的许多难点便可以不待解而自解,不待辨而自明。这也是我自己一以贯之的读书方法,我想这个方法是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阅读态度更为认真的读者不妨从本书附录“《人间词话》背景谈”读起。虽然许多背景性质的、具有坐标意义的知识点我都会在正文当中随文讲解,但为了增加正文的顺畅感,我还是将若干内容,尤其是理论性太强的内容,放到附录里集中解决。
阅读《人间词话》还有一个难点,那就是西方哲学、美学的许多观点往往有违常识,尤其有违中国人的常识。比如“美是客观的,不会有‘各花入各眼’的情况”,康德如是说;“理性不是科学的基础,直观才是”,叔本华如是说……
这些观点倘若出自无名鼠辈之口,发表于某个人声鼎沸的论坛上,无论其论证过程如何严密,都只会受到群起而攻之的待遇,使批评者们享受一场以智商和学养自矜的狂欢。当然,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先哲们某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高深见解确实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立锥之地,但即便是那些彻头彻尾的谬论,也曾在思想史上光耀一时,在文明的进程里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石。换言之,一些观点即便是错的,亦不失为伟大的错误,而伟大的错误往往比细小的真理更值得我们重视。
《人间词话》评论词作,任何引述几乎都是一带而过,这在当时丝毫不曾侮辱读者的学养。但毕竟时过境迁,今天《人间词话》的读者已不再是清末民初长袍马褂的饱学宿儒了,以至于太有必要对书中的引述做出详尽的解读。
通常意义上的诗词讲解,重点无非是时代背景、人物生平和字词释义,但既然《人间词话》是一部美学之书,那么我对诗词的讲解也会相应地突出诗艺的一项:哪是好诗,哪是不好的诗,为什么好,或者为什么不好,都有道理在。
中国的文艺评论有两个不算太好的传统,一是以玄解玄,一是以不解为解:前者爱说一些玄之又玄、大而无当的话,解释之语简直比被解释的对象更需要解释;后者过分强调审美的主观性,说一首诗为什么好,因为“我觉得好”,为什么觉得好,因为“心领神会,不可言说”。
所以我很乐于引述朱光潜的一番见解:“如果你没有决定怎样才是美,你就没有理由说这幅画比那幅画美;如果你没有明白艺术的本质,你就没有理由说这件作品是艺术,那件作品不是艺术。世间固然也有许多不研究美学而批评文艺的人们,但是他们好像水手说天文,看护妇说医药,全凭粗疏的经验,没有严密的有系统的学理做根据。我并不敢忽视粗疏的经验,但是我敢说它不够用,而且有时还会误事。”
如果朱先生看到今天的图书市场,一定会惊叹于有那么多的“水手说天文,看护妇说医药”的读物大行其道。原因无他,最能贴合外行人阅读趣味的作者往往也是和这些读者一样的外行人。于是,当谬论因为泛滥而变成了我们的常识,我们对一切真知灼见自然也就培养出相当强大的免疫力了。
幸或不幸的是,文艺理论的一大功能就是把所谓不可言说的东西清晰地言说出来。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做,也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么做,甚至有人觉得似懂非懂、朦朦胧胧的感觉才是最好的。这也无可厚非,“禅客相逢只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我尊重弹指派的深不可测,但我是讲理派。
最后要说的是,我曾在2009年出版有《人间词话讲评》,当时限于篇幅,仅仅讲解了《人间词话》全部六十四章中的前二十三章。今天终于有机会续成完璧,并且对2009年版做了很大程度上的修订。毕竟几年过去,我又有了许多新的想法。
苏缨
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