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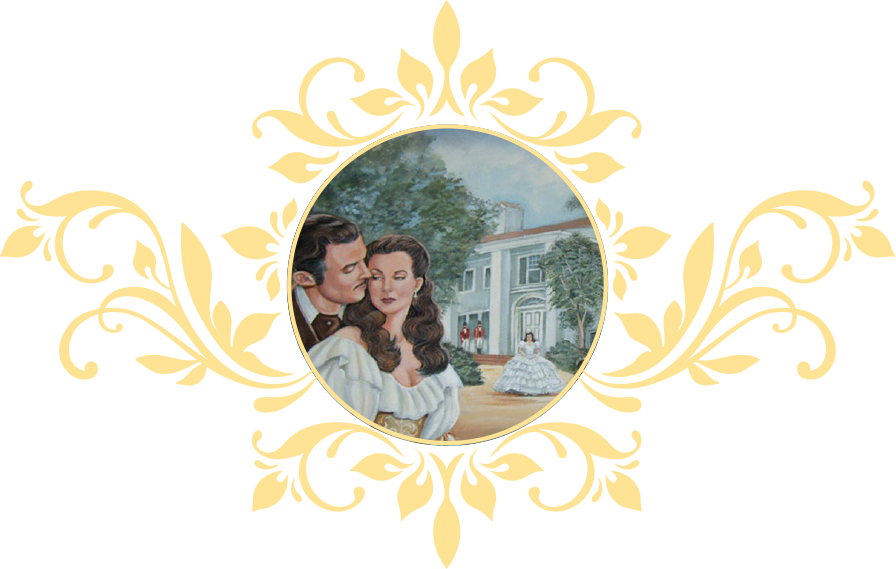



当晚吃饭的时候,因为母亲不在,思嘉在饭桌上打点着,但她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她听说的有关希礼和媚兰的可怕消息使她的心绪躁动不宁。她非常希望她妈妈能从斯莱特里家回来,因为,家里要是没有她,思嘉就感到茫然若失,孤独无助。斯莱特里一家及他们那没完没了的疾病有什么权利让埃伦离开自己的家呢?而此时此刻的她,思嘉,又是多么需要她。
餐桌上气氛沉闷,毫无生气。嘉乐如打雷般的大嗓门在她耳边响个不停,最后,她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已把下午跟她的谈话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着从萨姆特堡传来的最新消息,还不时在桌上擂着拳头,在空中挥舞着手臂以示强调。嘉乐已经养成习惯,在饭桌上总是他在唱主角。思嘉则常常想着自己的心事,很少听进他的话。可是今晚,她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抵御住他的声音,虽然她尽力竖起耳朵,想听见能说明埃伦已归来的车轮声。
当然,她不打算告诉妈妈她的满腹心事,因为如果埃伦知道自己的女儿居然会想要一个已经跟另一个女孩订婚的男人,她一定会大吃一惊,伤心不已的。但是,置身于她生平碰到的第一个悲剧当中,她需要她妈妈在她身边,这能带给她安慰。只要埃伦在她身边,她总是感到很安全,因为事情再糟,只要埃伦在那,她总能使事情好转起来。
一听到车道上传来车轮转动的吱嘎声,她马上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可车轮声却绕过屋子直往后院去了,她只好重新坐下。这不可能是埃伦,因为她总是从房子前面的台阶那里下车的。接着,从黑漆漆的后院传来黑人的说话声和尖笑声。从窗户看出去,思嘉看见几分钟前离开饭厅的波克手里高举着一个燃烧着的松节,有人正从车上下来,但只看得见模糊的身影。笑声和谈话声在黑夜中此伏彼起,听上去欢快亲切,无忧无虑,轻声细语如温柔的喉音,尖声喊叫则像乐声。接着就听见脚步声走上后面游廊的台阶,进了通往主房的过道,停在餐厅外的过道里。一小阵耳语声之后,波克走了进来,他身上惯有的一本正经的模样不见了,双眼不停地转动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嘉乐先生,”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满脸放光,一副当新郎官的得意之态,“您新买的女奴到了。”
“新买的女奴?我没新买什么女奴呀。”嘉乐说着,瞪着眼睛佯装不知。
“有的,您买了,嘉乐先生!哦,她现在正等在外面想和您说话呢。”波克回答着,一边笑,一边还激动地搓着双手。
“那就把你的新娘带进来吧。”嘉乐说,波克于是转身叫他的妻子进来。她刚从卫家的种植园来到这里,成为塔拉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她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她十二岁的女儿,瑟瑟缩缩地伏在她妈妈的身边,几乎被她妈妈宽大的花布裙给完全挡住了。
迪尔西身材高大,身板挺直。她古铜色的脸一动不动,没有皱纹,年龄在三十到六十岁之间。从相貌上看,她显然有印第安人的血统,这比黑人的特点还更突出。她那红色的皮肤、高而窄的前额、高耸的颧骨、底部扁平的鹰钩鼻梁,还有下面黑人所特有的厚嘴唇,一切都表明了她是两种血统的混血儿。她沉着冷静,走起路来有一种高贵气质,甚至超过了嬷嬷的,因为嬷嬷的气质是后天学来的,而迪尔西的则是与生俱来的。
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并不像大多数黑人那样含糊不清,措辞也较为谨慎。
“小姐们,晚上好。嘉乐先生,对不起,打扰您了。但我还是要到这来再次谢谢您买下了我和我的孩子。很多先生曾经想买我,但他们不想连我的孩子也一同买下。就为了您使我不用忍受和孩子分离的痛苦,我也得谢谢您。我一定全心全意地为您效劳,让您看看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哦——哦。”嘉乐尴尬地清清喉咙。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的慈善之举被别人说穿了,他为此感到颇不好意思。
迪尔西转身面对着思嘉,一种看似微笑的表情使她眼角现出了一些皱纹。“思嘉小姐,波克告诉过我,您曾叫嘉乐先生把我买下来,所以,我打算把我的普里西给你做贴身侍女。”
她把手伸到身后,把那小女孩拉到前面来。她是个皮肤呈褐色的小不点,双腿骨瘦如柴,就像小鸟一样,头上用细绳绑着无数的小辫子,硬邦邦地直竖起来。她的目光锐利,机敏,不会漏过任何东西,脸上则是一副装傻的模样。
“谢谢你,迪尔西,”思嘉回答道,“但恐怕嬷嬷会有意见的。自我出生起,她就是我的贴身女仆了。”
“嬷嬷年纪大了。”迪尔西说,那副平静的神态一定会使嬷嬷大发雷霆的,“她是个好嬷嬷,可你现在是个年轻小姐了,需要一个好的侍女,而我的普里西已经伺候英蒂小姐有一年了。她的针线活和梳头的本领都不比成年人差。”
在母亲的督促下,普里西突然行了个屈膝礼,对思嘉咧嘴笑了,搞得别人禁不住也要对她报以回笑。
“真是个伶俐的小女孩。”思嘉想着,然后大声说道,“谢谢,迪尔西,妈妈回来后再谈这件事好了。”
“谢谢小姐。晚安。”迪尔西说完,转身和孩子一起离开了餐厅,波克讨好地跟在后面。
饭后的杯盘碗盏收拾完后,嘉乐又重新开始演说,可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他的听众对他的言辞就更无赞赏可言了。他大扯着喉咙预言战争即将爆发,老用反问句问别人诸如南方是不是还能再容忍北方佬的侮辱这类问题,可只是得到了略显无聊的“是的,爸爸”或“不,爸爸”这类回答。卡丽恩正坐在大灯下的一块跪垫上全神贯注地看一本爱情小说,书中的女主人公自情人死后就做了修女。卡丽恩沉浸在小说中,不禁潸然泪下,眼前似乎出现了她自己头戴白色修女帽的模样,免不了有些兴奋。苏埃伦一边在绣她笑称为“嫁妆箱”的刺绣品,一边寻思着明天的野餐会上有没有可能把斯图尔特·塔尔顿从她姐姐身边引开,用她所具有而思嘉却没有的女性魅力来迷住他。而思嘉呢,则在为希礼而心烦意乱。
爸爸明明知道她伤心欲碎,他怎么还能够没完没了地谈论萨姆特堡和北方佬呢?正如许多年轻人一样,她认为人们竟然如此自私,居然全然不顾她内心的痛苦,而且,在她几乎心碎时,世界却一如既往,毫无变化,这简直使她吃惊极了。
她心里已经像是刮过了一阵旋风,很奇怪,他们坐在其中的餐厅居然还是平静如水,一无二致。过去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沉重的红木桌子和餐具柜、既大又重的实心银器、光亮的地板上铺着的鲜艳的碎毡小地毯,所有的一切都还原地不动,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这个餐厅既亲切又舒适。通常,思嘉很喜欢晚饭后和家人聚在那里的颇为宁静的几个小时。可是今天晚上,她看到它就厌恶。要不是害怕她父亲会大声质问她,她早就开溜了。她要从黑暗的过道溜到埃伦的小办公室去,坐在那张旧沙发上,把心里的痛苦都给哭出来。
屋里所有的房间中,思嘉最喜欢那间。每天早晨,埃伦就在那个房间里,坐在高高的写字台前,一边理着种植园里所有的账目,一边听着监工乔纳斯·威尔克森的汇报。有时候,一家人还在那里悠闲地消磨时间。埃伦手拿鹅毛笔在账簿上记着账,嘉乐坐在那把旧摇椅上,姑娘们则赖在那张坐垫已经凹陷进去的沙发上。沙发太破旧了,没法摆在屋子前面。思嘉很希望自己现在能和埃伦一起待在那里,这样她就可以把头伏在妈妈的腿上,安安静静地哭上一阵。妈妈难道就此不回来了吗?
就在这时,砾石车道上传来了车轮碾过路面的刺耳的声音,接着,埃伦柔声遣退车夫的低语声飘进房来。埃伦快步走进餐厅时,所有人都热切地抬头看着她。她的裙摆款款飘动,脸上现出疲惫而忧伤的神情。随着她走进房间,一阵美人樱香囊的淡淡香味扑鼻而来。这香味似乎总是从她裙子的褶皱处散发出来,思嘉的意念里总是把这种香味和她妈妈联系在一起。嬷嬷跟在后面几步远处,手里拿着皮袋子,下嘴唇拉得老长,前额往下耷拉着。嬷嬷边摇摇摆摆地往前走,边唧唧咕咕地自顾自唠叨着,但还会注意不让自己的嘀咕太大声,以免被别人听懂,但又要有一定的音量,以表示自己心里是绝对持不赞成态度的。
“我这么迟才回来,真对不起。”埃伦说着便把斜削的肩膀上的方格披巾拉下来,递给思嘉,走过她身边时,还拍了拍她的脸蛋。
她的归来使嘉乐像着了魔一样脸上大放异彩。
“小孩受洗了吗?”他问。
“受洗是受洗了,但他死了,可怜的孩子。”埃伦说,“我曾担心艾米也活不成,可我现在认为她能活下去了。”
姑娘们把脸转向她,既吃惊又迷惑不解,只有嘉乐达观地摇摇头。
“哦,小孩还是死了好,不用说,可怜的没有父——”
“时间不早了,我们现在最好还是祈祷吧。”埃伦打断嘉乐的话,语气非常自然。要不是思嘉很了解她妈妈,她就不会注意到这句插话的用意了。
要能知道艾米·斯莱特里的孩子父亲是谁,那倒是件挺有趣的事。但是思嘉知道,如果等着从她妈妈那里听到这件事的话,那她是永远也无法知道真相的。思嘉怀疑是乔纳斯·威尔克森,因为她经常看见他和艾米黄昏时沿着大路散步。乔纳斯是个北方佬,至今还孤身一人。他只是个监工,这个事实使他永远无法步入县里上流社会的生活圈。只要有点社会地位的家庭,就不会让女儿跟他结婚。他所能交往的人就只有斯莱特里一家以及和他们一样地位低贱的人。因为在受教育方面比斯莱特里一家高出好几个级别,他不想和艾米结婚也是很自然的事,不管他在黄昏时有多经常跟她一起散步。
思嘉叹了口气,因为她的好奇心强着呢。许多事情就发生在她妈妈的眼皮底下,可对她来说,却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只要是埃伦认为不正当的事,她就对它们不屑一顾。她试图把思嘉也调教成这样,但并没有成功。
埃伦已走到壁炉架边去取念珠,它们总是放在炉架上的镂花小首饰盒里。这时,嬷嬷语气强硬地说话了。
“埃伦小姐,祈祷前你得先吃些晚饭。”
“谢谢,嬷嬷,可我不饿。”
“俺得亲自去给你弄饭,你必须先把饭吃了。”嬷嬷说。她的前额因生气现出不少皱纹。她开始走向过道到厨房去。“波克!”她大声叫道,“叫厨娘生火。埃伦小姐回来了。”
地板在她肥胖的身体重压下吱呀作响。她在前面过道里的自言自语也越来越大声,餐厅里所有的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俺已经说了不止一次了,给那些白人穷鬼帮忙没半点好处。他们都是些懒惰虫、忘恩负义的窝囊废、没出息的贱骨头。埃伦小姐犯不着自己累死累活地去伺候他们,他们不配。要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有黑奴伺奉他们了。俺早说过——”
她顺着那长长的露天过道走去,声音也慢慢远去。这露天过道上面有顶篷,直通向厨房。要让主人知道在所有的事情中,她持的是什么立场,在这方面,嬷嬷很有自己的一套。她知道,如果白人对在嘟哝自语的黑人哪怕表示一点点在意,那也是有失体面的。她也知道,白人主人为了维护面子,就必须对她说什么置之不理,就算她在隔壁房间近乎大喊大叫也是白搭。仅此一点就可以使她免受责骂,无疑别人也会对她对事情所持的看法留有印象。
波克走进餐厅,手里端着一个托盘、银制餐具及餐巾。他后面紧跟着年仅十岁的黑人男孩杰克。他一只手在匆匆忙忙地扣白麻布上衣的扣子,另一手拿着一根拂尘。这拂尘是用报纸剪成的细纸条绑在一根比他人还高的芦苇秆上制成的。埃伦原有一根用漂亮的孔雀毛制成的拂尘,但只在特殊场合才动用。由于波克、厨娘和嬷嬷都固执地迷信孔雀毛不吉利,所以每次动用前都要先在家里进行好一番争执。
嘉乐为埃伦拉开椅子。埃伦一坐下来,四个声音立即在她耳边回响。
“妈妈,我新舞裙上的花边松了,可明晚在十二棵橡树的舞会上我要穿,你能不能给我缝缝呀?”
“妈妈,思嘉的新裙子比我的漂亮,我穿粉红色的就像丑八怪一样。干吗不让她穿我粉色的那件,我来穿她绿色的裙子呢?她穿粉色的也不错。”
“妈妈,明天晚上我能不能也待到舞会结束呢?我都已经十三岁了——”
“郝太太,你信不信——嘘,孩子们,别闹了,要不我得去拿鞭子抽你们一顿了!凯德·卡尔弗特今晨去了亚特兰大,他说——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好让我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他说那里都闹翻天了,人们的话题总离不开战争、民兵训练、组建骑兵部队。他还说,从查尔斯顿传来的消息说,他们对北方佬的侮辱已经再也无法容忍了。”
埃伦一脸倦容,听着这一片吵闹声,埃伦嘴角泛起一丝微笑。她首先对丈夫说话,就像身为妻子应该做的那样。
“如果查尔斯顿那些好人们都这么认为,我敢说,我们很快也会有同样的看法的。”她说,因为她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除了萨凡纳以外,整个美洲大陆大多数名门望族都出在那座不大的海滨城市查尔斯顿,而这一观念正是查尔斯顿人普遍的共识。
“不,卡丽恩,明年才行,亲爱的。那时你就能待着参加舞会,也能穿大人的衣服了。到那时,我这粉色脸蛋的小家伙会多么快活啊!别把嘴翘得老高的,亲爱的,你可以去参加野餐会,记住,你也可以待到晚餐结束,但要等到十四岁以后才能参加舞会。
“把你的衣服给我,思嘉。祈祷完我会把花边缝好。
“苏埃伦,我可不喜欢你说话的口气,亲爱的。你粉色的衣服很漂亮,配你的肤色很合适,就像思嘉的衣服也很配她的肤色一样。不过,明晚你可以戴我的石榴石项链。”
站在她妈妈身后的苏埃伦得意地对思嘉皱了皱鼻子,因为思嘉也正盘算着请妈妈把项链借给她。思嘉对她伸了伸舌头。苏埃伦是个牢骚满腹、自私自利、令人讨厌的妹妹,要不是有埃伦管束,思嘉肯定会经常刮她耳光。
“我说,郝先生,再跟我谈谈卡尔弗特先生说的有关查尔斯顿的消息吧。”埃伦说。
思嘉知道,她妈妈一点也不关心战争和政治,认为它们都是男人的事,聪明的女人决不会关心这些事的。但这能让嘉乐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就能使他高兴,埃伦对丈夫的兴致总是考虑得很周到的。
嘉乐也就接着谈他的新闻。嬷嬷把一道道菜放在主人面前,有顶端烤得金黄的松饼、油炸鸡脯肉,还有一盘切开的黄澄澄的红薯,不但在冒着热气,融化的黄油还在往下滴。嬷嬷拧了小杰克一把,他便赶忙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站在埃伦背后慢慢地前后摇动着那纸条绑成的拂尘。嬷嬷站在桌边,看着食物一叉一叉地从盘子里被送到嘴里,仿佛一旦看到什么懈怠的迹象,她就打算把食物硬塞进埃伦嘴里似的。埃伦也在很用心地吃着,但思嘉可以看出,她太累了,根本就不知道她在吃什么,只是嬷嬷那张毫不宽容的脸迫使她不得不吃下去而已。
埃伦吃完了所有的食物,站起身来。此时嘉乐才谈到一半呢。他正对北方佬的不光彩行径发表看法,说他们要解放黑奴,却又不肯为黑奴的自由花一个子儿。
“我们要祈祷了吗?”他问,口气颇为不情愿。
“是的。已经这么迟了——哦,实际上已经十点了。”正好钟在嘤嘤嗡嗡地报着时。“平时卡丽恩到这时早该睡着了。波克,把灯拉下来,嬷嬷,把我的祈祷书拿来。”
在嬷嬷沙哑的低语声催促下,杰克把拂尘放在角落里,着手收拾桌上的盘子。嬷嬷则在餐具柜的抽屉里摸着寻找埃伦那本用旧了的祈祷书。波克踮起脚尖,抓住灯链上的环,把灯慢慢拉下来,直到桌子上方都笼罩在灯光中,而屋顶退为一片片暗影。埃伦弄好裙子,双膝跪在地上,把祈祷书打开放在面前的桌面上,十指交叉放在书上。嘉乐跪在她身边,思嘉和苏埃伦跪在桌子对面,那是她们祈祷时一贯跪的位置。她们把多褶的衬裙折了好几层垫在膝下,这样,跪在硬地板上就更不会痛了。卡丽恩年纪太小,跪在桌边不舒服,她于是跪在一把椅子前面,肘部放在椅子上。她喜欢这种姿势,因为祈祷时她很少不睡着的,而这种姿势可以躲开她妈妈的注意。
一阵脚步和衣裙沙沙作响的声音,屋里的黑奴们都在门边跪了下来。嬷嬷边跪下嘴里边大声嘟哝着,波克直挺挺地跪在地上,侍女罗莎和蒂娜穿着宽大、亮丽的印花布裙,显得优雅极了,厨娘虽戴着雪白的帽子,可满脸憔悴,脸色蜡黄,杰克哈欠连天,一脸蠢相,尽可能躲得远远的,不让嬷嬷的手指够着他,怕她掐他。他们的黑眼睛都发出期待的亮光,因为和家里的白人一起祈祷是一天中的一件大事。应答祈祷中那古老而生动的词句及带着东方色彩的比喻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使他们心中的某种欲望得到了满足,所以他们吟唱着应答词的时候总是摇头摆脑的:“上帝,怜悯怜悯我们吧。”“主啊,怜悯怜悯我们吧。”
埃伦闭上眼睛开始祈祷,她的声音抑扬顿挫的,既像在催眠,又像在抚慰。埃伦感谢上帝给她的家、家人及黑奴带来健康和幸福的时候,黄色的光圈中人人都低着头。
在她为住在塔拉屋檐下的所有人以及她父亲、母亲、姐妹、三个夭折的孩子及“所有在炼狱中可怜的灵魂”都祈祷完以后,她把白色的念珠放在修长的十指之间,然后双手交叉地捻着念珠,开始念《玫瑰经》。这就像吹过了一阵和风,白人和黑人的喉咙里同时作出了应答:
“圣母玛利亚,上帝之母,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吧,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临终的时刻。”
思嘉虽然伤心痛苦,强忍眼泪,但她还是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宁静与安详,就像往日这种时候给她带来的感觉一样。白天的失望之情及对明天的恐惧心理减退了一些,留下了一种希望的感觉。这种安慰剂并不是因为她的心灵飞到上帝身边给她带来的,因为宗教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口头上的信仰,而是她看到了妈妈脸上的那种安详的神情。她妈妈正抬头看着上帝的神座及上帝的圣者和天使,祈求上帝为所有她所爱的人祝福。每次埃伦对天说话的时候,思嘉总是确确实实感觉到天是听得见的。
埃伦祷告完后,总是找不到念珠的嘉乐偷偷摸摸地用手指数着遍数开始祷告。他的声音单调低沉,索然无味,思嘉的思绪也随着他嘤嘤嗡嗡的声音而四散开去。她知道她必须好好审视审视自己的良心。埃伦教导过她,每天结束时,她都有责任认认真真地审视自己的良心,承认自己所犯的无数错误,祈求上帝原谅自己,并给予自己不再重复这些错误的力量。但此时的思嘉却在审视自己的心灵。
她低下头,把头靠在十指交叉的双手上,这样她妈妈就看不到她的脸了。她的思绪便又伤感地回到希礼身上。他真正爱的其实是她,思嘉,可他怎么可能计划和媚兰结婚呢?而且他还知道她爱他爱得有多深,他怎么能够刻意伤她的心呢?
紧接着,她的脑际突然掠过一个新颖的念头,这个念头就像流星一样闪闪发亮,在她脑际一晃而过。
“哦,希礼一点也不知道我在爱着他!”
这意外的念头让她大吃一惊,她几乎喘出口大气来。有好一会,她喘气不匀,脑袋瓜都僵化了,就像瘫痪了一样,但紧接着思绪又接着向前驰骋。
“他怎么会知道呢?他在身边时,我总是表现得很拘谨,一副正统的淑女样,大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态。他很可能会认为我根本不在乎他,只把他当成一个朋友。没错,所以他从来不说什么!他觉得他的爱是毫无希望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看上去如此——”
她的思绪迅速回到往昔的岁月,那时她曾发现他用那种奇怪的神情望着她,他那灰色的眼睛完全遮盖了他内心的想法,就像他心灵之窗的窗帘一样。可有时候,他的眼睛大睁着,没遮没拦的,清澈坦然,眼里还有一种痛苦而绝望的神情。
“他一定伤透了心,因为他认为我爱的是布伦特,或是斯图尔特,亦或是凯德。他很可能是这么想的。假如他得不到我,那还不如和媚兰结婚,好让他的家里人高兴。可是,如果他知道我真的爱他的话——”
她那变化无常的情绪从悲哀的最低谷一下飞登到幸福的顶峰。这就是希礼沉默不语、行为古怪的原因。原来他不知道!她极愿意去相信这一点,而虚荣心也促使她相信这一点,进而把相信变成确信。如果他知道她爱他,他一定会奔到她身边来的。她只要——
“噢!”她不由得心花怒放,手指抠着低垂的前额,“我有多傻呀,直到现在才想到这一点!我必须想法让他知道。如果他知道我爱他,他就不会和她结婚了!他怎么可能和她结婚呢?”
她突然意识到嘉乐已经祈祷完毕,她妈妈正看着她呢。她不禁吃了一惊,赶忙开始祈祷,机械地数着念珠,声音里融入了很深的感情。这使嬷嬷睁开眼睛,探究似的瞥了她一眼。她祈祷完后,轮到苏埃伦,接着是卡丽恩,也都开始祈祷,可她的思绪因那令人着魔的新想法而继续向前驰骋。
就是现在也还不算太迟!县里私奔之事太经常发生了,已经订婚的男方或女方却突然和另外一个人出现在圣坛前结为夫妇。而希礼的订婚甚至都还没宣布!是的,时间还有的是!
如果希礼和媚兰之间没有爱,只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约定的话,那他违约和她结婚怎么就没有可能呢?假如他知道她,思嘉,爱他的话,他一定会这么做的。她得想个法子让他知道。她一定会想出办法的!然后——
思嘉突然从兴致勃勃的梦想中回到现实中来,因为她竟然疏忽了应答祷文,她妈妈正责备地看着她。她一边重新加入祷告行列,一边却睁开眼睛飞快地扫了一眼整个房间。跪着祷告的人影、柔和的灯光、黑奴们在昏暗的阴影处摇头晃脑,即便是一小时前她看到就恨之入骨的那些熟悉的东西,转瞬间又都蒙上了她的感情色彩,房间似乎又重新变成个可爱的地方。此时此刻的此情此景,她是永远也无法忘怀的!
“至诚的圣母玛利亚。”她妈妈吟颂道。歌颂圣母的《玫瑰经》开始了。思嘉乖乖地应答道:“为我们祈祷吧。”同时,埃伦便用温柔的女低音歌颂着圣母的美德。
从孩提时代起,对思嘉来说,这一刻便是敬慕她妈妈的时刻,而不是敬慕圣母的时刻。也许这是对圣母的亵渎,但大家重复着那些古老的词句时,思嘉虽闭着眼睛,但似乎还能透过眼睛看见埃伦仰头朝上的面孔,而不是神圣的圣母玛利亚的面孔。“病人的康复之神”、“智慧的源泉”、“罪人的庇护人”、“神秘的玫瑰”——它们都是无比美丽的词句,因为它们都是埃伦所具有的美德。可是今晚,由于思嘉兴奋异常,她便在这整个仪式中,从被他们轻声念颂的词句中,从应答祷文的囔囔声中,感受到一种她以往从未体验过的美感。她的心里在真诚地感谢上帝,因为在她的脚下已经开辟好一条道路——可以使她从她悲哀的境地中走出来,直通希礼的臂弯。
最后一声“阿门”念完时,大家都站起身来,身体多少都有点僵硬了。蒂娜和罗莎一起把嬷嬷从地上拉起来。波克从壁炉架上拿下一个长长的点火纸捻,在灯火上点燃,走进过道。在蜿蜒而上的楼梯对面有个胡桃木餐具柜,因为太大而不便放在餐厅里用,只好放在这里。它宽大的柜顶放着好几盏灯,还有一排插满蜡烛的烛台。波克带着一种夸大的尊贵神情点燃一盏灯和三根蜡烛,就像是国王寝宫的第一内侍在为国王和王后点灯照明,让他们入寝室就寝。他把灯高举过头顶,领着这队人马走上楼梯。埃伦挽着嘉乐的手臂跟在波克后面,姑娘们各自拿着一根蜡烛,跟在他们后面上了楼。
思嘉进了房间,把蜡烛放在抽斗柜上,用手在黑暗的衣橱里摸着寻找要缝的舞裙。她把裙子搭在手臂上,悄悄地穿过走道。父母的卧室门微微开启着,还不等她敲门,埃伦的声音便传到她耳里,声音很低,但很坚定。
“郝先生,你必须解雇乔纳斯·威尔克森。”
嘉乐却大声叫起来:“可我上哪去再找一个不会欺骗我的监工呢?”
“必须解雇他,马上,明天早晨就得让他走人。大个子萨姆是个不错的工头,他可以接管监工的职责,直到你雇到另外一个监工为止。”
“啊,哈!”嘉乐的声音又响了,“这么说,我可是明白了!是那可敬的乔纳斯睡了——”
“一定要解雇他。”
“这么说,他就是艾米·斯莱特里生的孩子的父亲,”思嘉寻思着,“噢,原来如此。你还能指望一个北方佬男人和一个白人穷鬼的女儿做出什么别的事情来呢?”
接着,她特意停了一会,让父亲那唾沫乱溅的话有时间慢慢消失,然后敲了敲门,把裙子递给她妈妈。
到思嘉脱了衣服,吹灭蜡烛躺在床上时,明天如何行动也已经详详细细地计划好了。这个计划并不复杂,她像嘉乐一样,头脑里只有要达到的目标,于是,她的双眼就只盯着这个目标,也只考虑能达到目标的最直接的几个步骤。
首先,她得表现得“傲气十足”,就像嘉乐所要求的那样。从她到十二棵橡树时起,她将表现出快活且最富有生气的自我。不要引起任何人怀疑她曾因希礼和媚兰订婚之事而消沉沮丧过。而且,她将和在场的每一个男人调情逗乐。这对希礼是很残酷,但这会增加他对她的渴望之情。她不会疏忽每一个已到婚龄的男人,老到苏埃伦的男友、长着姜黄色胡须的老弗兰克·肯尼迪,小到媚兰的哥哥,腼腆、内向、爱脸红的韩查理。他们都将蜂拥在她身边,就像蜜蜂围着蜂巢转一样。希礼也一定会从媚兰身边被吸引到她的崇拜者这个圈子中来。然后,她将设法摆脱众人,单独和他在一起待几分钟。她希望一切将按计划进展,要不然的话,事情就麻烦多了。假如希礼没有走那第一步,那她就只能亲自迈出这一步了。
最后,当他们终于单独待在一起时,其他男人围着她转的那一幕在他脑海里还历历在目,他就会得到一个新的印象,那就是,那群人中的每个人都想要她,于是,他的眼里又会现出那种忧伤而绝望的神情。接着,她就会让他知道,尽管她很受欢迎,可全世界所有的男人中,她还是会选择他,这样她就能让他重新高兴起来。她羞涩、甜蜜地承认这点时,在他心里,她的地位就会比原先高出一千倍。当然,她这么做时应该表现出大家闺秀的风范。她连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大胆地对他说她爱他的话——那是绝对不行的。但是怎么告诉他,这只是个细节,她一点也不为此而心烦。她曾经对付过这种情形,现在也能够再次获得成功。
她躺在床上,朦胧的月光洒在她身上,她想象着整个场景。当他意识到她确确实实是爱他时,脸上就会现出惊喜的神情。此时此刻,她似乎看到了他的这种表情,而且还听到了他叫她嫁给他的话语。
自然,她得说,嫁给一个已经和另一个姑娘订婚的男人,这种事情她连想都不敢想。但他会一再坚持,最后,她就会让自己被他说服。然后,他们就会决定,当天下午就逃到琼斯伯勒去,并且——
噢,明天这个时候,她可能就已经成为卫希礼太太了!
她从床上坐起身来,双手抱着膝。有好一会,她陶醉在身为卫希礼太太——希礼的新娘的幸福中!可紧接着,她的心里掠过一丝凉意。如果事情没有按此计划发生呢?假如希礼没有恳求她跟他一块私奔呢?但她坚决地把这种想法硬从脑海中赶走了。
“现在我可不考虑这一点。”她坚定地说,“假如我现在考虑这一点,这会使我感到沮丧的。如果他爱我,事情就没有理由不按我想让它们发生的方式进行。而且,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她扬起下巴,长着一圈黑睫毛的淡绿色的眼睛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埃伦从没告诉过她,希望和让希望变成现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生活也还没教会她捷足未必先登的道理。生活如此美好,失败是不可能的,漂亮的衣裙和清秀的面孔便是征服命运的武器,这个年方二八的少女躺在银色的月影之中,抱了无比的勇气盘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