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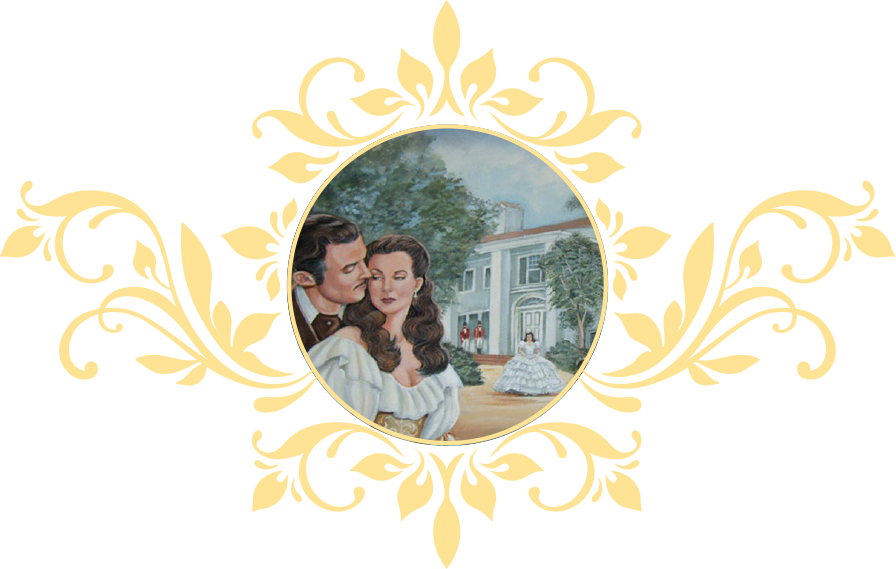



不到两个星期,思嘉便成了一位妻子,又过了不到两个月,她已成了寡妇。她曾经如此匆匆忙忙,这般不费心思便承担起这些契约上所规定的义务,如今很快就又解脱了。但她再也无法体验未婚时那种无忧无虑的自由了。寡妇身份倒是紧接着婚姻接踵而至,但使她感到沮丧的是,当妈妈的日子也跟随而来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思嘉回想起一八六一年四月最后那些日子时,对那些细节,她的记忆从来就不是太清楚。时间和所发生的事重叠交叉,像一场并非现实、没有理性的梦魇一样,混杂在一起。到她去世的那一天,对那些日子的记忆一定会有空白点的。对她接受查理和举行婚礼之间的那段时间的记忆,更是特别模糊。两个星期!订婚时间这么短,这在和平时期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时本来应该有一年半载的礼节性的间隔期。但是南方已经燃起了战火,各种事件就像被一股劲风刮过似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相继发生,过去日子里那种不紧不慢的步调一去不复返了。埃伦双手绞在一起,建议往后推一推,好让思嘉或许能够更加慎重地把这件事再考虑考虑。但思嘉对她的恳求充耳不闻,满脸不高兴。她要结婚!而且必须快点,两个星期内就得结婚。
希礼的婚礼已从秋天提前到五月一日,这样,只要骑兵连一旦被召参战,他便可以随军开拔。知道这一点后,思嘉把她的婚礼定在他的婚礼前一天。埃伦表示反对,但查理以新近才发现的口才恳求她同意,因为他急于要到南卡罗来纳去参加韦德·汉普顿的团队。嘉乐也站在两个年轻人这一边。他因战争热已是激动万分,对思嘉找了这么一个如意佳婿感到很高兴。战争在进行当中,他还站在一对年轻恋人的爱情之路上碍手碍脚的,他成什么人了?埃伦被搞得心烦意乱的,最后也只好和南方其他的妈妈们一样让步了。她们从容不迫的世界被搅得乱七八糟的,而在把他们裹胁向前的强大力量面前,她们的恳求、祈祷和建议根本无济于事。
整个南方都陶醉在一股热情和激动的情绪当中。每个人都知道,只要打一仗就可以结束战争,而每个年轻小伙子都赶在战争结束以前去报名参军——而且在冲到弗吉尼亚去给北方佬痛击一番以前,赶紧跟自己心爱的人结婚。县里有几十对新人借战争之机举行了婚礼,但也没什么时间可用来为分别痛苦一番,因为每个人都太忙了,也太激动了,无暇顾及那些一本正经的思想和眼泪。女人们在做制服,织袜子,卷绷带,男人们则忙着军训和练射击。每天都有一火车一火车的士兵经过琼斯伯勒到北部的亚特兰大和弗吉尼亚去。有些支队穿着猩红、浅蓝或浅绿的制服,是社会—民兵连队中精选出来,看上去非常令人赏心悦目;有些小股部队却穿着家纺的衣服,戴着浣熊皮帽;还有其他没穿制服的,他们只穿绒面呢和上好的亚麻布做的衣服。全都是未经过全面的严格训练的半拉子,武器装备也不全,可都激动得发狂,大喊大叫的,好像是在去野餐的路上一样。看到这些人的样子,县里的男孩全都着慌了,害怕还没等他们到达弗吉尼亚战争就会结束,所以,为骑兵连出发参战的准备便也紧锣密鼓地加速进行着。
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思嘉的婚礼也在准备过程中。还没等她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已经穿上埃伦的婚纱,戴上她的面纱,挽着父亲的手臂,顺着塔拉宽大的楼梯拾级而下,去面对一座挤满宾客的房子了。后来,她就像回忆梦境中的情景一样,还记得墙上几百支蜡烛烛光点点,她妈妈的脸上带着慈爱,有点迷惑不解的样子,嘴唇无声地嚅动着,在为女儿的幸福祈祷。嘉乐满脸通红,一是喝了白兰地的缘故,二则是为女儿和一个既有钱,名声又好而且是个世家大户的人结婚而感到很自豪——希礼手里挽着媚兰正在台阶底部站着。
她看见他脸上的表情时,心想:“这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的。这只是一场噩梦。我会醒过来,发现这全都只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可不能想,要不我会在这么多人面前尖叫出来的。现在我可不能想,我要在以后能忍受的时候再想这件事——在我看不到他的眼睛的时候。”
一切都好像在梦境中一样。通道两旁站满了满脸是笑的人们,查理猩红色的脸和结结巴巴的声音,还有她自己的回答,都清晰得令人吃惊,但又显得非常冷淡。还有后来人们对他们的祝贺、亲吻、祝酒以及舞会——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像做梦一样。连希礼吻她面颊的感觉以及媚兰温柔的低语“现在我们成了真正的姐妹了”都是那么的不真实。那令人神魂颠倒的魅力使查理那丰满而易动感情的姑妈韩白蝶小姐目瞪口呆。可就是这引起的激动之情也带上了一丝梦魇的意味。
但是,当舞会和祝酒终于结束,当黄昏最后到来时,来自亚特兰大的宾客能挤就全都挤进塔拉和监工房里,睡在床上、沙发上及地上的地铺上。所有的邻居也都回家去休息了,准备第二天去忙活在十二棵橡树举行的婚礼。这时,那梦境般的恍惚在现实面前便像水晶玻璃一样破碎了。这个现实便是,面露羞赧之色的查理穿着睡衣从她的梳妆室里出现了,他躲避着她向他投来的诧异的目光。此时的她正躺在床上,床单拉得很高。
当然,她知道结过婚的人是共睡一张床的,但她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这于她的母亲和父亲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可她从未把这条规则用在自己身上。现在,她突然意识到自己都为自己做了些什么,这从烧烤野餐会以来还是头一次。这个她从来没真正想跟他结婚的陌生男人要和她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而她的心却因为自己匆促的行动和永远失去希礼而痛苦得快要碎了。想到这一点,她觉得这一切太令人无法忍受了。当他犹犹豫豫地向床边走去时,她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道:
“如果你走近我,我就大声叫起来。我会的!我会的——用我最大的声音叫起来!从我这滚开!你不要碰我!”
这样,查理的新婚之夜便在角落里的一张扶手椅上度过了,但他并没有感到特别的不高兴,因为他理解,或者说,他认为他理解他的新娘羞涩和微妙的情感。他愿意等她的畏惧感慢慢减退,只是——只是——他叹了口气,一边挪动身子以找到一个舒适的睡姿,因为他很快就要离开家参加战争去了。
尽管她自己的婚礼犹如梦魇一般,但希礼的还更糟。在几百支蜡烛的烛光映照下,思嘉身着婚礼后第二天穿的苹果绿裙装,站在十二棵橡树的游廊上,身边挤着和前一天晚上一样的那群人,看着韩媚兰那张普通的小脸蛋在变成希礼太太的过程中大放异彩,成了美人。现在,永远失去希礼了。她的希礼。不,现在不是她的希礼了。他曾经是她的吗?这一切在她脑子里全混在一起了,而她的头脑又是如此疲倦,如此迷茫。他曾经说过他爱她,但又是什么把他们分开了呢?要是她能记得就好了。通过和查理结婚,她堵住了县里爱传播流言飞语的人们的嘴,可对于现在,那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有一度似乎是很重要的,可现在却好像一点也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希礼。现在他走了,而她却已经和一个她不但不爱他,而且打心眼里就瞧不起他的人结了婚。
噢,她有多后悔呀。她经常听说有人总跟自己过不去,但迄今为止她还把这只当做一种修辞手法。现在,她终于知道这个说法的含义了。她疯狂地希望自己能摆脱查理,安全地回到塔拉,重新做一个未婚姑娘。和这愿望混杂在一起的想法便是:她知道这只能怨自己一个人。埃伦曾试图阻止她,可她不听她的。
这样,在希礼举行婚礼的那天,她整个晚上都茫然地跳舞,机械地说话,脸上还带着微笑,还为这个毫不相干的问题感到纳闷:人们怎么就这么傻,会认为她是个幸福的新娘子,却看不出她的心其实都要碎了?哦,感谢上帝,他们看不出来!
那天晚上,嬷嬷帮她脱了衣服,然后向她告别离开后,查理害羞地从梳妆室出现了,心里还在想着自己是否要在马毛椅上度过第二个夜晚。这时,她不禁放声大哭起来。查理爬上床,坐在她身边,想去安慰她。她一言不发地哭着,直哭到眼泪干了,最后才躺在他肩膀上无声地啜泣着。
要不是发生了战争,那就会有一星期时间让他们在全县拜访客人,还会有为这两对新人举办的舞会和烧烤野餐,然后他们就会出发到萨拉托加或白硫磺泉去蜜月旅行。如果没有战争,思嘉还得穿上婚礼后第三天、第四天及第五天穿的衣服到方丹家、卡尔弗特家及塔尔顿家去参加为庆祝她的婚礼而举办的晚会。但现在既没有晚会也没有蜜月旅行了。婚礼举行后一个星期,查理出发去参加韦德·汉普顿上校的部队去了,而两个星期以后,希礼和骑兵连也出发了,使整个县犹如丧失亲人一般。
在那两个星期中,思嘉从来没有单独见过希礼,也没有私下和他说过一句话。他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曾在塔拉稍作停留,和他们告别。即使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她也没有私下和他谈过话。媚兰戴着帽子,围着披巾,有了一种新近才有的主妇般的尊贵神情,挽着他的手臂,稳重而严肃。塔拉的所有成员,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全都出来送希礼去参战。
媚兰说:“你应该吻吻思嘉,希礼。她现在是我嫂嫂了。”于是希礼弯下腰,用冰凉的嘴唇吻了吻她的面颊。他拉长着脸,一副严峻的样子。思嘉从这一吻中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快乐,因这一吻是在媚兰的怂恿下才有的,所以,她心里闷闷不乐。媚兰分别时紧紧拥抱了她,几乎让她透不过气来。
“你会到亚特兰大来看我和白蝶姑妈的,对不对?噢,亲爱的,我们太想你来了!我们想对查理的妻子了解得多一些。”
又过了五个星期。这期间,查理从南卡罗来纳寄来了羞羞答答、欣喜若狂、充满爱意的信件,诉说他的爱,战争结束后对未来的计划,为了她要成为战斗英雄的理想以及对他的上司——韦德·汉普顿的崇拜。到第七个星期,来了一封由汉普顿上校亲自发来的电报,而后是一封信,一封善意、尊贵的慰问信。查理死了。上校本来早就要拍电报的,但是查理认为自己的病只是小毛病,不想让他的家人担心。这个不幸的男孩不但被他认为自己已经得到的爱欺骗了,而且也被他想在战场上获得荣誉的极大希望欺骗了。他得了麻疹,又并发了肺炎,只到了南卡罗来纳的营地,连北方佬的影子都没看见,便无声无息地迅速离开了人世。
到了产期,查理的儿子出世了,因为当时很时髦把男孩的名字用父亲的指挥官的名字来命名,所以孩子被叫做韦德·汉普顿。思嘉知道自己怀孕时曾经绝望地哭过,并且希望自己也死去算了。但在她的十月怀胎期,身体不适的时候很少,而且不怎么痛苦就生下了他,恢复得也很快。嬷嬷私下曾告诉她,这是极为正常的——女人们应该多受罪。她对孩子并没多少爱,虽然她可以掩饰这一实情。她本不想要他,所以不喜欢他的到来,可现在他还是来到了人间,但他似乎不可能是她的孩子,不可能是她的骨肉。
生下韦德后,她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时间短得让人感到很丢脸。虽然如此,她在精神上却觉得神情恍惚,像生了病一样。充满活力的她变得萎靡不振的,即使整个种植园的人都努力想让她恢复过来也无济于事。埃伦成日里皱着眉头,忧心忡忡的。嘉乐比往日更会诅咒发誓了,还从琼斯伯勒给她带来毫无用处的礼物。连老方丹医生在他的硫磺补剂、糖浆及药草都没法使她振作起来之后,也只好承认连他都感到困惑不解了。他私下告诉埃伦,思嘉一会烦躁不安,一会无精打采,是因为她伤透了心。但是,如果思嘉想说话的话,她就会告诉他们,这其中的烦恼与此大相径庭,而且比这复杂得多。她没有告诉他们,这是因为生活太无聊了,而且,确确实实当了妈妈以后,她感到很茫然,最重要的是,由于希礼不在,这才使她看上去有这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她感到非常无聊,而且这种无聊的心境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自从骑兵连去参战之后,县里就不再有什么娱乐和社交活动。所有有趣的年轻小伙子都走了——塔尔顿家四个男孩,卡尔弗特家两个,方丹家的,芒罗家的,还有从琼斯伯勒、费耶特维尔及拉夫乔伊来的每个年轻而有魅力的男子。只有老人、残疾人和妇人才留了下来,她们成天就只是编织,做针线,为部队种植更多的棉花和玉米,饲养更多的猪呀羊呀牛呀什么的。除了苏埃伦年届中年的男朋友弗兰克·肯尼迪带领的军需部队每个月打这经过去收集供给外,从来就看不到一个真正的男人。军需部队的男人并不是会令人非常激动的人,而弗兰克那羞怯的讨好奉承使她更加烦恼,最终发现自己很难对他礼貌相待。要是他和苏埃伦能早日完婚就好了!
就算军需部队的人有趣得多,这对她的心境也无济于事。她是个寡妇,心已经进了坟墓。至少,大家都认为她的心已进了坟墓,并且希望她能有相应的举动。这使得她很烦躁不安,尽管她努力去做,但她还是回忆不起任何有关查理的事,唯一记得的就是她告诉他要和他结婚时他脸上现出的那副死前的小牛犊的神情。可即使是这幅画面也在慢慢地被淡忘。但她是个寡妇,她得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未婚女孩的快乐于她是不合适的。她非得庄重肃穆、冷淡孤傲不可。埃伦看到弗兰克手下的中尉在花园里给思嘉荡秋千并使她尖声大笑之后,特别详细地强调了这一点。埃伦非常苦恼地告诉她,一个寡妇要成为别人闲言碎语的对象,别提有多容易了。和一个普通妇人相比,寡妇的言谈举止要加倍地谨慎。
“只有上帝知道,”思嘉一边乖乖地听着她妈妈温柔的声音,一边想,“婚后的女人根本没什么乐趣可言。所以,寡妇还不如死了的好。”
寡妇还得穿着可怕的黑衣裙,连镶上一点点镶边使它看上去更有生气一些都不行,还不能戴鲜花,扎缎带,配花边,甚至首饰也不能戴,只有用亡夫的头发做的缟玛瑙胸针和项链才行。帽子上的黑绉面纱必须长达膝部,只有守寡三年以后,才能缩短至肩部。寡妇从来就不能快快乐乐地说话,肆无忌惮地大笑。即使微笑的时候也必须是忧伤且带悲剧色彩的微笑。而且,最可怕的是,无论如何,她们都不能对有绅士陪伴表现出一点点兴趣。如果哪位绅士如此没教养,敢暗示对她感兴趣,她也必须以一种尊贵且经过斟酌的词句提到自己的丈夫,好让他死心。“哦,是的,”思嘉消沉地想,“有些寡妇最后在人老珠黄、青筋凸现的时候也有再婚的。虽然,只有老天才知道,她们在邻居的众目睽睽之下是如何应付的。而且,这一般都是一些拥有一个大种植园和一打孩子的绝望的老寡妇。”
结婚就已经够糟的了,但成了寡妇——噢,那生活就永远结束了!人们谈到查理走后,小韦德·汉普顿给了她多大的安慰时,他们有多傻啊!他们说,现在她活下去就有奔头了,他们真是太傻了!大家都在说,她有了这个遗腹子,留下了爱情的印记,这真是太好了。她自然也不想去纠正他们的想法。但这一想法离她自己的心思是相距最远的。她对韦德的兴趣很少,有时还很难记得他确确实实是她的骨肉。
每天早晨醒来后,在睡眼惺忪的那一刻,她会重新成为郝思嘉。屋外阳光灿烂,照在她窗外的木兰花上,反舌鸟在欢唱,煎咸肉的好闻的香味悄悄地飘入鼻腔。她便无忧无虑,年轻快乐了。接着她便会听到因肚子饿而躁动不安的号啕大哭,这总是——总是使她大吃一惊,一边还想:“哦,屋里有个婴儿呢!”这以后,她才会记得这是她的孩子。这太令人茫然不解了。
而希礼!噢,最重要的是希礼!她平生第一次对塔拉心怀恨意,恨那从小山坡上往下通到河边的长长的红土路,恨那栽满泛出新绿的棉花丛的红色的田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木、每一条小溪、每一条小路、每一条马道都使她想起他。他已属于另一个女人,而且已经去打仗了。但垂暮时分,他的幽灵还在困扰着她,还站在走廊的阴影中用慵懒的灰色目光对着她微笑。每次听到从十二棵橡树沿着河边的道路迤逦而来的马蹄声,她无不忘情地想起——希礼!
她现在恨透了十二棵橡树,而她一度曾爱过它。她恨它,但又总被它吸引到那去,这样她就能听到卫约翰和姑娘们谈论他了——听他们读他从弗吉尼亚寄来的信。它们令她伤心,但她还得听。她不喜欢脖子僵硬的英蒂和又愚蠢又爱唠叨的哈尼,也知道她们同样不喜欢她。但她无法不接近她们。每次从十二棵橡树回来后,她便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连晚饭也不起来吃。
她拒绝吃东西,这比任何别的事都令埃伦和嬷嬷更担心。嬷嬷端来了令人看了垂涎欲滴的食盘,暗示说现在她已经是寡妇了,高兴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但思嘉却一点食欲也没有。
当方丹医生严肃地告知埃伦,伤心常常会导致体质衰弱,而妇女因衰弱消瘦会引发死亡时,埃伦脸都白了,因为她心里也有这种担心。
“没什么法子了吗,医生?”
“换个环境,在这个世界上,这对她是最好的办法了。”医生说,心里急于摆脱一个他无法医治的病人。
这样,毫无兴致的思嘉便带着她的孩子出发了,先去萨凡纳拜访了她郝家及罗比亚尔家的亲戚,然后又去查尔斯顿埃伦的姐妹波琳和尤拉莉家。但她比埃伦预计的提早一个月便回到了塔拉,对她的提早归来也未作任何解释。萨凡纳的亲戚对她都很好,但詹姆斯和安德鲁及他们的妻子都已上了年纪,成天只满足于安安静静地坐着谈论往昔的日子,这思嘉一点也不感兴趣。罗比亚尔家也是一样,而查尔斯顿更是一团糟,思嘉这么想。
波琳姨妈和她的丈夫住在河边的一个种植园里,那里比塔拉偏僻多了。她丈夫是个小个子老头,有一套正规而冷淡的礼数和一副生活在往昔岁月里的神情,看上去漫不经心的。他们最近的邻居也在二十英里外,通往那里的是一条黑漆漆的路,从还是丛林的柏树沼泽地和橡树林里穿过去。橡树上幕状的灰色苔藓摇摆不定,给了思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而且总是令她想起嘉乐讲的有关爱尔兰的鬼魂在闪着微光的灰色雾霭中游荡的故事。那里什么事也没有,成天就只是编织,晚上则听凯里姨夫大声朗读布尔沃—利顿开导人的作品。
尤拉莉幽居在查尔斯顿炮台处的一座大房子里。前面是一座围墙很高的花园,而她的生活更是兴味索然。思嘉习惯了绵延起伏的红色山丘那宽广无边的景色,在这里觉得就像在蹲监狱一样。这里比波琳姨妈那多一些社交活动,但思嘉不喜欢登门拜访的人,他们那神态、传统及对家世的注重都让思嘉反感。她知道,他们全都认为她父母的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不知道罗比亚尔家的人怎么会嫁给一个新来乍到的爱尔兰人。思嘉感觉到尤拉莉姨妈背地里为她辩解。这使她火冒三丈,因为她和她父亲一样并不在乎家世。她对嘉乐及他所获得的成功感到很自豪,因为那是在没有人帮助,只靠他自己精明的爱尔兰头脑获得的。
查尔斯顿人还动不动就把炮轰萨姆特堡的事引以为荣!老天,他们难道没有意识到,就算他们没有傻乎乎地开枪燃起战火,其他一些傻瓜也照样会去做的吗?听惯了佐治亚山地人们欢快的声音后,平原地带人平平的慢吞吞说话的声音在她看来似乎很造作。她觉得,如果她再听到把“棕榈树”说成“棕哦榈树”,“房子”说成“房——子”,“不”说成“不哦——”,“妈妈和爸爸”说成“妈啊妈和爸啊爸”这类声音,她就会叫喊起来。这使她极为烦躁,以致在一次正式的拜访中,她模仿了嘉乐的爱尔兰土腔,使得她姨妈很苦恼。这以后,她便回到了塔拉。与其让查尔斯顿的口音弄得痛苦不堪,还不如被对希礼的思念折磨来得好。
埃伦日夜忙活着,让塔拉生产出双倍的产品来支援南部邦联。当她的大女儿从查尔斯顿回到家里时,看到她身体瘦弱,面色苍白,说话尖刻,她不禁吓坏了。她自己也体验过伤心的痛苦,夜复一夜,她躺在鼾声大作的嘉乐身边,试图想出能让思嘉减轻苦恼的办法。查理的姑姑——韩白蝶小姐给她写了好几封信,敦促她让思嘉到亚特兰大去长住一阵,现在埃伦第一次慎重地考虑起这个问题来。
她和媚兰两人孤零零地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既然连查理也走了,她们便没有了男性的保护。”白蝶小姐在信中写道,“当然,还有我的哥哥亨利,但他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但也许思嘉已经告诉过你有关亨利的情况。我身体不好,不能在信中写更多有关他的情况了。如果思嘉能到这来跟我们住在一起,梅利和我会感觉更自在,更安全的。三个寂寞的女人在一起总比只有两个强。而且,也许亲爱的思嘉能发现什么能减轻她的悲伤的东西,就像梅利在做的,到医院里去照料我们的勇敢的孩子们——当然,梅利和我也很想看看亲爱的小宝贝……”
这样,思嘉的箱子连同她的丧服又重新被打点一番,和韩韦德及他的保姆普里西一道,带着满脑子埃伦和嬷嬷对她行为准则的告诫及嘉乐给她的换成南部邦联纸币的一百美元,出发到亚特兰大去了。她并不特别想去亚特兰大。她认为白蝶姑妈是老太太中最愚蠢的人,而且,要和希礼的妻子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个念头就已经够令人厌恶了。但是县里能勾起她回忆的事太多了,现在已不可能再待下去,所以,换一换环境总是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