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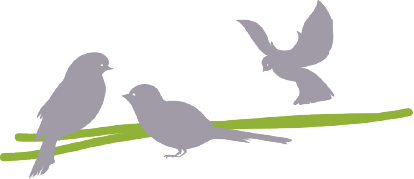
梅吉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她回来了。她和老布鲁伊·威廉姆斯一起坐着邮政卡车向德罗海达而来,朱丝婷放在她座位旁的一个篮子里。布鲁伊见到她十分高兴,急于想知道她在过去的四年中都做了些什么。但是,当他们接近庄园的时候,他陷入了沉默,推想她一定是希望安安静静地回家。
又回到了棕色和白色之中,回到了尘土之中,回到了北昆士兰如此缺乏的令人惊叹的纯洁和闲适之中。这里没有恣意横生的植物,再也用不着耗神费力,手脚不停地收拾房间了。这里只有像灿烂的星空一样缓慢转动的老一套的生活。袋鼠比以往更多了。还有那可爱的、匀称的小芸香树,如此丰满、安详,几乎显得忸怩。卡车上空的粉翅鹦鹉在喧闹着,翅膀下露出一片粉红色。鸸鹋在飞奔着。兔子连蹦带跳地从路上跑开,身后蹬起一团白土烟。褪了色的死树干兀立在草原中。森林的蜃景滞留在远方弧形的地平线上,它们是从迪班—迪班平原上折射过来的,只有那森林底部飘忽不定的蓝影才说明它们并非真景。乌鸦凄凉地、令人焦虑地聒噪着,这久违的声音是她日思夜想的,但却从来没有想过会听不到这声音。干燥的秋风卷起的朦胧尘雾像是在下着一场暴雨,而这片草原,大西北银灰色草原就像在感谢天恩似地逶迤直接天穹。
德罗海达,德罗海达!魔鬼桉和懒洋洋的、高大的胡椒树上,翻飞着嗡嗡叫的蜜蜂。畜牧围场和乳黄色砂岩的建筑依然如故,迥然一色的绿草坪围绕着大宅。花园里盛开着秋天的花卉,香罗兰和百日草,紫菀和大丽花,金盏草和金盏花、菊花、月季花、玫瑰花。史密斯太太目瞪口呆地站在砾石面的后院里,随后,她便大笑着喊了起来。明妮和凯特跑了过来。有力的胳膊拥着她,就像链条缠绕着她的心。德罗海达是家,这里就是她的心脏,永远是。
菲走出来看看她们在这里为什么大惊小怪。
“嗨,妈。我回来了。”
那灰色的眼眼神色未变,但是梅吉从她的眼神里仍然可以看出,妈妈是感到高兴的,只不过她不知该怎么表达出来而已。
“你离开卢克了?”菲问道,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才使史密斯太太和女仆们发觉她是孑然一身回来的。
“是的。我再也不会回到他身边去了。他不想要一个家,不想要他的孩子们或我。”
“孩子们?”
“是的。我又要生另一个孩子了。”
仆人们发出了一片噢噢哟哟之声。菲用那审慎的声音说出了她的看法,把高兴压在心底。
“要是他不想要你,那你回家来是正确的。在这儿我们会照顾你的。”
这是她旧日的房间,能眺望家内圈地和花园。新婴儿生下来以后,将和朱丝婷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哦,在家里多好啊!
鲍勃见到她也很高兴。他越来越像爸了,变成了一个有点驼背的、肌肉发达的人,好像太阳把他的皮肤和骨头都烤出了颜色。他也同样有一种温和的力量,但也许是由于他从来也没有当过一个大家的长者,因此缺乏爸爸那种慈父的风度。而且,他也像菲。沉静,富于自制力,感情不形于色,见解不闻于声。梅吉猛然间惊讶地想到,他已经三十过半了,仍然没有成婚。随后,杰克和休吉也回来了,他们俩就像和鲍勃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没有他那种权威。他们用腼腆的微笑欢迎梅吉回家。她想,一定是这样的,他们太腼腆了,这是大地的性格,因为大地不需要感情的表达或社交的风度。它需要他们给予的,就只是默默无言的爱和全心全意的忠顺。
这天晚上,克利里家的男人全都呆在家里,卸那辆詹斯和帕西在基里装上了玉米的卡车。
“梅吉,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旱的天,”鲍勃说道“,两年没下雨了,一滴都没下。兔子的祸害比袋鼠还严重,它们吃的草比绵羊和袋鼠加在一起还多。我们想试着人工喂养,可你知道绵羊是怎么回事。”
梅吉最了解的就是绵羊。它们是一群白痴,连理解生存基本之道的能力都没有。这些带毛的贵族老爷在繁殖选育中完全被培养成了一种智力低下、平平庸庸的畜牲。除了草或从它们天生的环境中割来的灌丛以外,绵羊什么都不吃。但是,这里偏偏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割灌丛来满足上10万只绵羊的需求。
“我可以派上用场吧?”她问道。
“可以呀!梅吉,要是你还像以前那样骑马在内围场干活的话,就可以多一个男人去割灌丛了。”
正如双生子所言,他们永远不离开家了。14岁的时候,他们永远离开了里弗缪学院,那时,他们还不能以足够的速度跑过这片黑壤平原呢。他们的相貌已经像青少年时代的鲍勃、杰克和休吉了。老派的斜纹布和法兰绒的衣服已逐渐被大西北牧场主的服装替代:白色的厚毛头斜纹棉腰布,白衬衫,宽边的平顶灰毡帽,平跟的半腰松紧帮马靴。只有那一小撮住在基里棚屋区的土著居民才模仿美国西部的牛仔,穿着流行一时的高跟靴,戴着斯特森帽
 。对一个黑壤平原的人来说,这身打扮是一种无用的装腔作势,是异域文化的一部分。一个人穿着高跟靴是无法穿过灌木丛的,而他却不得不常常穿过灌木丛,而一个斯特森帽又太热、太沉了。
。对一个黑壤平原的人来说,这身打扮是一种无用的装腔作势,是异域文化的一部分。一个人穿着高跟靴是无法穿过灌木丛的,而他却不得不常常穿过灌木丛,而一个斯特森帽又太热、太沉了。
栗色牝马和黑阉马已经死了,马厩里空空如也。梅吉坚持说,她骑一匹牧羊马也很好,可鲍勃还是到马丁·金的牧场去为她买了两匹有部分纯种血统的役用马—一匹是黑鬃黑尾的米色牝马,一匹是长腿的栗色阉马。由于某种原因,失去了那匹栗色老牝马对梅吉的打击比她和拉尔夫的分手还要大。这是一种滞后反应,栗色牝马的死似乎使他已离去的事实显得更为揪心。但是,再次到围场上去,骑马带狗,吸着被咩咩叫的羊群踏起的灰尘,望着飞鸟、天空和大地,这真是太好了。
天干旱得厉害。在梅吉的记忆中,德罗海达的草地总是能设法挺过每次干旱的,但这次就不同了。现在,草地显得斑斑驳驳,在一丛一簇的草之间露出了黑色的地面。地面上网着细密的裂纹,就像是一张张干渴的嘴。弄到这步田地是兔子的过错。她不在的四年中,它们突然在一年之中大量地繁殖了起来,尽管她认为在这之前,它们就已成为了一大祸害。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它们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饱和点。到处都是兔子,它们也吃宝贵的牧草。
她学会了下兔夹子,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不愿看到那些可爱的小东西被钢齿弄得血肉模糊。但她是一个相当热爱土地的人,不会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面前畏葸不前。在要活下去的名义下开杀戒算不得残酷。
“让上帝惩罚那个把第一批兔子运到这里的想家的英国佬吧。”鲍勃抱怨地说道。
兔子不是澳大利亚的土产。它们被多愁善感的人们引进过来,大大破坏了这个大陆的生态平衡。在这里,绵羊和牛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这些东西从被引进来的那一刻起就是遵循科学方法放牧的。澳大利亚没有天生的食肉兽来控制兔子的数量,进口的狐狸繁殖不起来。人肯定是一种非天然的食肉者。但是这里人太少,兔子太多了。
在梅吉的肚子大得不能再骑马之后,她的日子都是在庄园里和史密斯太太、明妮、凯特一起度过的,为那在她肚子里蠕动的小家伙做衣服,打毛衣。他(她总是把那小家伙想成“他”)是她的一部分,朱丝婷永远不会成为这部分的。她没有受恶心或情绪低落的折磨,急切地盼望把他生下来。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个缘故,朱丝婷被忽视了。现在,这个浅色眼珠的小东西已经由一个没头脑的婴儿变成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小姑娘。梅吉发现自己对这个变化过程和这孩子着了迷。从她对朱丝婷淡然处之以来,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现在她渴望给她女儿以无限的爱,紧紧地抱着她,吻她,和她一起笑。被人有礼貌地拒绝是一种打击,可是,朱丝婷正是这样对待她的每一个充满柔情的表示的。
詹斯和帕西离开里弗缪学院的时候,史密斯太太本打算把他们再置于她的羽翼之下,后来她沮丧地发现,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的围场上。于是,史密斯太太便转向了小朱丝婷,并且发觉她也像梅吉那样被拒之于千里之外。朱丝婷似乎不想让人紧抱,亲吻或逗着笑。
她走路和说话都开始得很早,九个月的时候就会了。她一旦能够用腿站起来,能支配那发音清晰的舌头,就自己走路,能准确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既不吵吵嚷嚷,也不反抗,只是性格极其刚强。关于基因梅吉根本不懂,但是,假如她懂的话,她也许就会知道这是克利里、阿姆斯特朗和奥尼尔血统混合的结果。
但是,最让人吃惊的是,朱丝婷竟顽固地拒绝微笑或放声大笑。德罗海达的每一个人都曾绞尽脑汁地做出怪样,想让她稍稍咧嘴笑笑,但都没有成功。说到这种天生的一本正经,她倒是胜她外祖母一筹。
10月的第一天,朱丝婷正好16个月的时候,梅吉的儿子在德罗海达降生了。他几乎早生了四个星期,而且使人措手不及。她很厉害地宫缩了两三次,便破水了。他是由刚刚给医生挂完电话的史密斯太太和菲接生的。梅吉几乎没有时间扩张盆骨。疼痛微乎其微,折磨很快就过去了,以前恐怕很少有过这样快的。尽管她不能不感到一阵剧痛,但由于他如此突然地降生到世界上,梅吉还是觉得好极了。生朱丝婷的时候,她的乳房完全是干瘪的,这次奶水却充足得直往外流。这回不再需要奶瓶了。
他长得真漂亮!个子又大又苗条,完美无缺的小脑壳上长着一头淡黄色的鬈发,活灵活现的蓝眼睛,这双眼睛后来丝毫也没有改变颜色。它们怎么会变化呢?它们是拉尔夫的眼睛,就像他长着拉尔夫的手,拉尔夫的鼻子和嘴,甚至拉尔夫的脚那样。梅吉未免太过分了,她竟然十分感谢卢克的身材和肤色与拉尔夫十分相像,面貌也十分相像。但是那双手,那眉毛的样子,那毛茸茸的额前发尖,那手指和脚趾的形状却更像拉尔夫,不像卢克。希望最好谁都不记得是哪个男人长着这种样子吧。
“你想好了他的名字吗?”菲问道,孩子好像很喜欢她。
当她抱着他站在那里的时候,梅吉望着她,心里十分高兴。妈妈又要去爱了,哦,也许她不会像爱弗兰克那样去爱他,但至少她会产生某种感情的。
“我打算叫他戴恩。”
“多古怪的名字!怎么?这是奥尼尔家族的名字吗?我想你和奥尼尔家的缘分尽了吧?”
“这和卢克毫无关系。这是他的名字。不是别人的。我讨厌家族的姓氏。这就好像希望把某个不同的人的一部分安到一个新人的身上。我直截了当地管朱丝婷叫朱丝婷,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名字,而我管戴恩叫戴恩也是同样道理。”
“唔,确实很有道理。”菲承认道。
梅吉疼得缩了一下,她的乳房奶水过足了“。妈,最好把他给我。哦,我希望他饿了!而且,我希望老布鲁
 能把吸奶器拿来。不然,你得开车到基里去买一个。”
能把吸奶器拿来。不然,你得开车到基里去买一个。”
他饿了。他使劲拉着她,笨拙的小嘴把乳房吮得发疼。她低头望着他,望着他那紧闭的眼睛和乌黑的、尖梢金黄的睫毛,望着他那酷肖其父的眉毛和那不停地吮动着的小脸蛋。梅吉爱他爱得心发疼,比他吮奶产生的疼痛还要厉害。
有他就够,也只能满足于他一个。我不会再有孩子了。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你爱那个上帝胜于爱我,你决不会知道我从你—从他那里偷来了什么。我永远也不会把戴恩的事告诉你的。哦,我的孩子!把他换到枕头上去要比躺在她的臂弯里舒服得多,也更容易看到他那张完美无瑕的小脸儿。我的孩子!你是我的,我永远不会把你的身世泄露给别人。最不能泄露的就是你的父亲,他是一个教士,他是不能承认你的。这样不是妙极了吗?
4月初,轮船抵达了热那亚港。拉尔夫大主教在百花怒放、一派地中海春光中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乘上了一趟开往罗马的火车。本来他提出要求是可以乘一辆梵蒂冈的小汽车去罗马的,但是,他害怕感觉到教会的气氛再次紧紧地包围他,他想尽可能把这一刻推迟。不朽城
 真是名不虚传,他想道。他透过出租汽车的窗子凝视着那些钟楼和穹顶,落满了鸽子的广场和罗马的圆柱—柱基已经在地下深埋了好几个世纪。哦,对他来说,它们都是多余的。对他重要的是罗马那称之为梵蒂冈的一部分。在那里,除了豪华的公共建筑外,就是豪华的私邸。
真是名不虚传,他想道。他透过出租汽车的窗子凝视着那些钟楼和穹顶,落满了鸽子的广场和罗马的圆柱—柱基已经在地下深埋了好几个世纪。哦,对他来说,它们都是多余的。对他重要的是罗马那称之为梵蒂冈的一部分。在那里,除了豪华的公共建筑外,就是豪华的私邸。
一位穿着黑色和米色相间的长袍的多明我会
 修道士领着他穿过了高大的大理石走廊,这里面的青铜雕像和石雕像抵得上一座博物馆。他们经过了一些风格各异的画像,有乔托
修道士领着他穿过了高大的大理石走廊,这里面的青铜雕像和石雕像抵得上一座博物馆。他们经过了一些风格各异的画像,有乔托
 的、拉斐尔
的、拉斐尔
 的、波堤切利
的、波堤切利
 的、弗拉·安吉利科
的、弗拉·安吉利科
 的。他现在是在一位大红衣主教的接待室里,无疑,家境富裕的康提尼—弗契斯家族给它可敬的后代子孙们的环境大增光彩。
的。他现在是在一位大红衣主教的接待室里,无疑,家境富裕的康提尼—弗契斯家族给它可敬的后代子孙们的环境大增光彩。
维图里奥·斯卡班扎·迪·康提尼—弗契斯红衣主教坐在一个房间里,这房间里布置着象牙和金制的摆设,色彩富丽的挂毯和画,铺着法国地毯,陈列着法国家具。那只戴着闪闪发光的红宝石戒指的光滑的小手向他伸了出来,欢迎他。拉尔夫大主教高兴地垂下目光,穿过房间,跪了下来,接住那只手,吻着那戒指。他把自己的面颊贴在那只手上,知道他不能说谎,尽管在他的嘴唇触到那超世俗的权力和世俗权威的象征之前他曾打算恢复往日的神态。
维图里奥红衣主教将另一只手放在那弯下去的肩膀上,向那位修道士点了点头,示意他退下去。随后,当门轻轻地关上时,他的手便从那肩膀向头发上移去,停在了那黑密的头发上,轻轻地把那半挡在前额上的头发向后弄平。这头发已经发生了变化,用不了多久,就不再是乌黑如漆,而是铁灰色了。那弯下的脊背直了起来,两肩向后移去,拉尔夫大主教直直地抬头看着他主人的脸。
啊,起变化了!那张嘴瘪了进去,显得十分痛苦,更加无助了。那双颜色、形状和相互搭配如此漂亮、优雅的眼睛,和他记忆中的那双似乎永远是他身体一部分的眼睛完全不一样了。维图里奥红衣主教总是有一种幻想,认为耶稣的眼睛是蓝色的,和拉尔夫的眼睛一样:镇定,不为他所目睹的一切所动,因而能囊括一切,理解一切。不过,这也许是一种错误的幻想。没有眼神的表达,一个人怎能感知到人性和自己的痛苦呢?
“喂,拉尔夫,坐下吧。”
“阁下,我想忏悔。”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谈一谈,用英语谈。这些天,到处都是耳朵,不过,感谢耶稣,幸亏没有听得懂英语的耳朵。请坐,拉尔夫。哦,见到你太高兴了!我失去了你那聪慧的忠告、推理能力和你那至高无上的友谊。他们没有给我一个能及我爱你一半的人。”
他能感觉到自己脑子已经猛地一下子变得发僵了,觉得自己的头脑是在用呆板的语言进行着思维。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比大部分人都清楚地了解一个人在交往中的变化,甚至讲话时语言的变化意味着什么。那些偷听的耳朵对极其流畅的英语口语是无能为力的。于是,他在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正对着那穿着鲜红波纹绸的瘦小的身影。这件衣服的色彩变幻不定,鲜红的色泽与其说是其本身色彩醒目,倒不如说它与周围的环境融成了一体。
几个星期来他所感到的极度的厌倦似乎减轻了一些。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渴望这次会面。这时,他心里已经有了底,他会被理解、被宽恕的。由于他的失节,由于他的为人处世不像他原来所渴望的那样,由于他使一位风趣、仁慈而又忠实的朋友大失所望,他感到神明内疚。他的罪愆就在于他走进了这个纯洁的地方时,自己再也不是个纯洁的人了。
“拉尔夫,我们是教士,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是另一种东西,一种我们没有成为教士之前的东西。尽管我们是孤傲的,但我们也无法逃避这一点。我们是男人,有男人的弱点和失算之处。无论你告诉我什么,也无法改变我们在过去的年代的共事中我对你形成的印象。无论你告诉我什么也不能使我低估你,或减少对你的爱。因为这许多年来,我知道,你已经摆脱了我们那种内在的弱点和人性,但是我知道,这种东西肯定在你身上苏醒过,因为我们大家同样有过这样的事。甚至连教皇本人亦是如此。他是我们之中最谦恭、最富于人性的人。”
“我违背了我的誓言,阁下。这是不能轻易宽恕的。这是亵渎神圣。”
“当你许多年之前接受了玛丽·卡森太太的财产时,你就已经违背了安贫乐穷的誓言。那是遗留给慈善事业和管区众教徒的,不是这样吗?”
“那么,三个誓言都被破坏了,阁下。”
“我希望你叫我维图里奥,就像以前那样!拉尔夫,我既没有感到震惊,也没有感到沮丧。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意旨。我想,你也许已经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这种教训通过危害性较小的途径是学不到的。上帝神秘莫测,他的天机超乎我们可怜的理解力。不过我认为,你所做过的事不是轻佻的,你誓言的遗弃不是无价值的。我太了解你了。我知道你是个禀性高傲的人,极其热爱成为一个教士的想法,有强烈的独往独来的意识。你需要这种特殊的教训来压压你那傲骨,使你明白你首先是一个男人,并非像你想象的那样孤高,这是可以允许的,对吗?”
“是的,我缺少人情味,并且相信,从某种角度来说我渴望成为上帝那样的人。我犯下的罪孽是深重的、不可原谅的。我不能宽恕自己,所以,我怎能希望神的宽恕呢?”
“这是傲慢,拉尔夫,傲慢!宽恕不是你的职责,你还不明白吗?只有上帝才能宽恕。只有上帝!对于诚心诚意的忏悔,他是会宽恕的。你知道,他曾经宽恕了那些伟大得多的圣徒,以及名副其实的恶棍所犯下的罪孽。你认为恶魔撒旦就不会被宽恕吗?他在他反叛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宽恕了。他之所以遭罹地狱之苦的命运,是他自己的过错,不是上帝要这样的。他不就是这样说的吗?‘宁为地狱之王,不作天堂之仆!’因为他不能克服自己的傲慢,不肯使自己的意志服从另一个人的意志,尽管那另一个人就是上帝本人。我不想看到你犯同样的过错,我最亲爱的朋友。人情味是你所缺少的一种素质,但这正是造就一位大圣人—或一个伟大的人的素质。在你没有把宽恕这种事留给上帝去做之前,你是不会获得真正的人性的。”
那坚定的脸庞抽动了一下“。是的,我知道您是对的。毫无疑问,我必须承认我的现状,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把我身上现存的这种傲慢彻底根除的人。我忏悔,因而我将坦白,等候宽恕。我确实感到痛悔。”他叹了口气;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他那审慎的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在这个房间里无法表达的—内心冲突。
“但是,维图里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我是无能为力的。我既不能毁灭她,又不愿这灭顶之灾落到我的头上。当时,似乎不存在着选择的问题,因为我确实爱她。这不是她的过错,我从来没有想把这种爱情发展到肉体的程度。你知道,她的命运变得比我的命运更重要了。在那一刻之前,我总是首先考虑到自己,认为我比她更重要,因为我是一个教士,而她则是低人一等的人。但是,我明白我要对她的生存负责……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本来可以让她在我的生活中消失的,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把她珍藏在我的心中,而她已知道这一点。倘若我真的把她从我心中驱除,她是会知道的。那样,她就会成为我无法影响的人了。”他笑了笑“,您知道,我已经坦白了许多情况。我稍稍尝试了一下我自己创造出的东西。”
“就是那玫瑰吗?”
拉尔夫大主教的头往后一仰,望着那制作精巧的天花板以及天花板上那镀金的装饰和莫兰诺吊灯“。那还能是谁呢?她就是我唯一企图塑造的人。”
“那么她,这朵玫瑰将会安然无恙吗?你这样做不会比拒绝她使她受到的伤害更大吧?”
“我不知道,维图里奥。我希望我知道就好了!那时,好像那样做是唯一可行的。我没有普罗米修斯
 那样的先见之明,卷进狂热之中使一个人的判断力极低。此外,那也很简单……就发生了!不过我想,也许我所给她的,她大部分都需要,认识到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份。我并不是说她不知道她是一个女人。我是说我不知道。要是我第一次认识她时她是一个女人的话,事情也许就是另一种样子了,可是我认识她的许多年中,她只是个孩子。”
那样的先见之明,卷进狂热之中使一个人的判断力极低。此外,那也很简单……就发生了!不过我想,也许我所给她的,她大部分都需要,认识到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份。我并不是说她不知道她是一个女人。我是说我不知道。要是我第一次认识她时她是一个女人的话,事情也许就是另一种样子了,可是我认识她的许多年中,她只是个孩子。”
“拉尔夫,你的话听起来倒挺一本正经,而不像是做好了接受宽恕的准备。这很伤感情,对吗?你是能够有足够的人性去屈服于人类的弱点的。这件事确实是由于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才做出来的吗?”
他吃惊地望着那双黑如深潭的眼睛,看到那双眼睛中反映出了自己的身影,像是两个身量极小的侏儒“。不,”他说道“,我是个男人,就像男人一样在她身上发现了我未曾梦想到的快乐。我不知道一个女人的感觉是那种样子,也不知道女人会成为穷欢极乐的来源。我曾想过永远也不离开她,这不仅是由于她的身体,也是由于我就是愿意和她在一起—和她谈话,或不和她谈话,吃她做的饭,向她微笑,分享她的思想。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思念她的。”
那灰黄色的苦行僧的面容竟然使他想起了在离别的那一刻梅吉的脸,流露出了精神上的重负,但是,尽管那脸上带着重重心事,哀伤和痛苦,依然显出要坚决走到底的神情。他了解什么呢?这位穿着红绸衣的红衣主教唯一醉心的人性似乎就是钟爱他那只没精打采的阿比西尼亚猫。
“我不能忏悔我和她在一起的那种方式,”由于红衣主教没有开口,拉尔夫便接着说道“,我忏悔我打破了像我生命一样神圣和具有约束力的誓言。我再也不能以一如既往的那种见解和热情来履行我教士的责任了。我心怀凄楚地忏悔。”但是梅吉呢?在他说到她的名字的时候,他脸上的那种表情使维图里奥红衣主教转过身去,他的思想也开始激烈斗争起来。
“忏悔梅吉就是杀害她。”他把疲倦的双手捂在眼睛上“,我不知道这话是否说清楚了,或是否接近于说出了我的意思。我似乎一辈子也无法充分表达出我对梅吉的感觉。”在红衣主教转过来的时候,拉尔夫从椅子上俯身向前,看见自己那一对身影变得大了一些。维图里奥的眼睛像镜子,它们将看到的东西反射回来,丝毫也看不到它们背后的东西。梅吉的眼睛恰好相反,它们可以直通深处,一直通到她的灵魂“。梅吉就是一种天福,”他说道“,是我的一个神圣的东西,一种不同的圣物。”
“是的,我理解,”红衣主教叹了口气“,你这样的感觉很好。我想,在我们上帝的眼中,这将使大罪减轻。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你最好去向乔吉奥神父忏悔,不要去找吉勒莫神父。乔吉奥神父不会曲解你的感情和你的推论。他会看到真相的。吉勒莫神父的认识能力差一些,也许会认为你由衷的忏悔是有问题的。”一丝微笑像淡淡的阴影一般掠过他的嘴角“,我的拉尔夫,他们,那些倾听所有这些忏悔的人,也是男人。只要你活着,就不要忘记这一点。只有在他们从事教士职业的时候,他们才是上帝的容器。除此之外,他们也都是男人。他们所给予的宽恕是来自上帝的,但那些倾听和判断的耳朵都是属于男人的。”
门上传来谨而慎之的敲门声。维图里奥红衣主教默默地坐了下来,望着被端到有镶嵌装饰的桌上的茶盘。
“你知道吗,拉尔夫?从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些日子起,就养成了喝午茶的习惯。他们在我的厨房里把茶弄得相当不错,尽管一开始他们还不习惯。”当拉尔夫大主教向茶壶走去的时候,他自己动起手来“,啊,不!我自己来倒。这使我能开心地当‘母亲’”。
“在热那亚和罗马的街道上,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穿黑衬衣的。”拉尔夫大主教一边望着维图里奥红衣主教倒着茶,一边说道。
“那是领袖
 的特殊追随者。我的拉尔夫,我们将面临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教皇毫不动摇地认为,教会和意大利世俗政府之间没有任何龃龉,而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其他所有问题上一样,是正确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必须保留对我们所有的孩子予以帮助的自由,哪怕是出现一场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将以天主教上帝的名义发生分裂,互相厮杀的战争。不管我们的心和感情站在哪一方,我们必须永远尽力保证教廷超脱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际争端之外。我希望你到我这里来,是因为我相信,不管你眼睛看到了什么,你脑子里的想法是不会形诸于色的,是因为你具备我所见到过的最佳的外交头脑。”
的特殊追随者。我的拉尔夫,我们将面临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教皇毫不动摇地认为,教会和意大利世俗政府之间没有任何龃龉,而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其他所有问题上一样,是正确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必须保留对我们所有的孩子予以帮助的自由,哪怕是出现一场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将以天主教上帝的名义发生分裂,互相厮杀的战争。不管我们的心和感情站在哪一方,我们必须永远尽力保证教廷超脱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际争端之外。我希望你到我这里来,是因为我相信,不管你眼睛看到了什么,你脑子里的想法是不会形诸于色的,是因为你具备我所见到过的最佳的外交头脑。”
拉尔夫大主教苦笑着“。不管我这个人怎么样,您还是要让我继续我的生涯,对吗?我真不知道,假如我不是碰到您的话,我将会怎样?”
“哦,那你会成为悉尼大主教的,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职位,”红衣主教粲然一笑,说道“,但是我们的生活道路并不是由我们掌握的。我们当年能相遇是命该如此,就像我们现在注定要在一起为教皇工作一样。”
“在这条道路的尽头我看不到成功的可能,”拉尔夫大主教说道“,我认为,结局终将是那种永远公正的结局。谁都不会喜欢我们的,所有的人都将谴责我们。”
“这个我明白,教皇陛下也明白。但是我们别无选择。然而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在私下为领袖和元首
 的早日垮台而祈祷,对吗?”
的早日垮台而祈祷,对吗?”
“您真的认为将要发生战争吗?”
“我看不出避免这场战争的任何可能性。”
红衣主教的猫轻手轻脚地从一个充满阳光的角落里走了出来,它刚刚在那里大睡了一觉。它跳到了那鲜红的、闪闪发光的衣襟上,动作有些笨拙,因为它太老了。
“啊,谢芭!向你的老朋友拉尔夫打个招呼,你曾向我表示过你宁愿要他。”
那凶恶的黄眼睛傲然地注视着拉尔夫大主教,随后便合上了。两个人都纵声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