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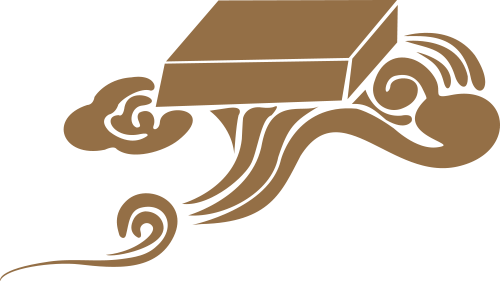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世子在宋国见过孟子后,去楚国了,等于出国访问,待了多久?是半年啊,或者一年啊?不知道。出国访问回来,问题就来了,这一段谈话是两人又见面了。孟子一看,滕世子出国访问以后,他的颜色、表情、行为不大对啊。唉,看你这个样子,大概出国走了一趟回来,看到外面都是富国强兵嘛,楚国也逞强得很,你对我所讲人性本善,应由道德领导政治的话,好像有所怀疑。
由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面带惶惑之色的英俊小伙子——滕世子,他怀疑,他彷徨,他求上进而又畏惧,自觉不堪胜任,但又不能安于现实,更不肯自甘堕落。
孟老师眼光犀利得像电光,他直截了当地便针砭到滕世子的内心深处。
世子并没有讲话,但孟子一眼就看出来,就像后世禅宗祖师的教育法。所以孟子直截了当地说“夫道,一而已矣”。世子,你还怀疑什么呢?道,就是这个,更没有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政治,这一个真理,就是一个、一贯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看法、讲法、学说,都是偏见。其实,天下的大道,是不二法门。孟子讲出一番理由,叫滕世子坚定信念,相信传统文化道德政治精神,不要变。
换言之,尧舜之所以为尧舜,其内圣——内在修养达于圣境的成就,也全在于这个心啊!你心里已经感觉到“今是而昨非”,那么,自己此心已转化了,只要你能拿出大勇气、大智慧,肯直接承当下来,立即可以转凡成圣了。
这一节书,使我们想起了孔子曾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此时此景,也正是孟子对滕世子说的“夫道,一而已矣”,是同一模式,同样的情景,只是不知滕文公当时的体会程度而已。不过,看他后来毅然决然地尊奉孟子之教,实行“三年之丧”的孝行,似乎他领受得很深。至于说他还没有做到如孟子所期望的,成就周文王一样之业,那也是限于时势,姑且归之于天命可也。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这个观点来看,那么,孟子一生得意的弟子中,滕文公应该算是其中的第一人了。
同时在这里,也使我们想起晚唐时代,禅宗的一段故事。当时有一位夹山大师,去向船子和尚参学问道。船子传了心地法门给他,叫他立即回去好好修持求证。夹山在辞别临行之时,还再三回头,似乎还有不敢自肯安心之处。这时船子和尚站在他自己的船上,便高声叫着夹山说:喂,你以为我另外还有特别的秘密没告诉你吗?他说了这句话,自己便将小船弄翻,连人带船,翻到河水中去了。他只有以这样一记最后的杀手锏,来坚定夹山信得自心即佛的道理。当然,这是出世法,是禅宗的教授法。孟子对滕文公的教授法,是入世法,是现身现世圣贤的教授法。可是,他们的用意,都是为了再三说明别无二法的真理,这两种方式确有异曲同工的妙趣。
接着,孟子为了成就滕世子,也因为他行将担当国家的重任,孟子用了雷霆万钧的力量,加强他入世负荷重任的信念。孟子同时引证三位古人的名言和事实,引用过去历史的经验和三个要点,来告诉滕世子。
“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首先引用过去齐国的名人成覸,对齐景公说的话。齐景公是滕文公的长辈,他的宰相是晏子,有这么一个好宰相,齐景公在历史上还比较有名,是一个还可以的领袖。成覸的意思是说,要做就做好的领袖,做文王、武王一样,不错!他们是大丈夫男子汉,可是我们也是男子汉大丈夫,何必怕呢?不要怀疑自己,拿出精神来做。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孔子的学生颜渊也曾经说过,一个立志做学问道德的人,假使出来做事的话,怕什么?舜也是种田,出身很落魄,最后做了一代的圣王,难道舜他是什么天生特别的人吗?舜是一个人,我颜渊也是一个人,彼此同样是人,他能做到难道我不能做到吗?应该也能像舜一样。一个人道德修养,要有这个气派。
“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鲁国的贤人公明仪也说过,周文王以百里之地起家,建立了周朝,是统一中国七八百年的治平天下。文王的一切,足为我们所师法,我绝对相信周公的名言,他绝不会欺骗我的。
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说,你不要怀疑,拿出勇气来,担当国家的大事。现在,你出国看了,哎哟!我那个地方只有县那么一点大,怎么能治得好,跟楚国比,或者跟齐国比呢?你不要怕,滕国的幅员虽然很小,地形不整齐,但是也还有五十里地,与周文王起家的时候,也差不多吧!重要的是要能截长补短,虽然是小国,如果你以大无畏的精神,实行内圣外王之道,政治做得好,也可以使它变成一个至善的国度,也可以给人家做榜样。但是问题在于你自己是否有勇气,肯不肯下决心、下狠心去改变。
孟子说,古书上讲,譬如一个人生病,要想身体恢复健康去吃药,药吃对了,人会发晕。《书经》上记载(《商书·说命篇》),也说过类似这种情形的话。等于医生治病一样,对于一个百病丛生、临死垂危的绝症,要想把它挽救回来,只有胆大心细,投下特效的药剂才行。不过,强烈的特效药剂,吃下去吃对的话,开始反而更显得头昏脑胀,甚之有更坏的反应。发晕以后,等药性完全吸收了,精神就来了。但是如果投下去的药剂分量不够,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不好也不坏,那等于白吃,是毫无效果的。这点你要特别考虑清楚,我们治理国家同医生看病一样,你将来就位,政治上要下狠心、下决心,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这正是孟子自作“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批注,可说是画龙点睛之笔。
孟子对于当时还是世子的滕文公,首先教导了他修心养性的内养之学,并培养他身为人君,有君子之度的内圣风格。不过,他用了机锋的教授法,单刀直入。同时在后面一段话,尽其所能地启发他自有的灵智和决心,要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时的局面艰难重重,实在很不容易。如果我们明了战国初期时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环境,你就会对滕文公和滕国,寄予无限的同情;也才可能知道孟子的这个特别门生——滕文公,实在了不起。果然他的一生,并没有辜负孟子的教育之恩,也没有辜负他自己后来为君之德。
这要怎样研究才可知道呢?很简单,熟读《孟子》,反复研究,用经史合参的方法,便知道了。这一段是记载滕文公在世子时期与孟子的问答。他的父亲定公过世以后,他继位主持国政,面临问题,又向孟子提出具体的请示。这一段便要回转来查阅《梁惠王》下章末段中的记载,然后将前后两段贯串起来研究,便可了然于胸了。
非常遗憾的,从宋儒以后,硬生生地把这些要点,始终局限于孟子论“性善”学说的范围,致使孟子的内则成圣、外则成王的大机大用,统统扼杀于坐谈性命微言之中,岂不是和“依文解义,三世佛冤”一样吗?但是,我们这样研究,当然也绝对不可背离原文而凭空假设,否则,也就是“离经一字,允为魔说”了。例如朱熹集注说: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见于此,而详具于《告子》之篇。然默识而旁通之,则七篇之中,无非此理。其所以扩前圣之未发,而有功于圣人之门。程子之言信矣。
我们如果也依照朱熹的这种见地来说,那就是“如局限此义于性善之域,似有齐通衢于仄径之嫌,矫枉过正,殊足憾焉!”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把孟子这段话只局限于“性善”之说,岂不是把大路缩小改为羊肠小道了吗?
说到孟子在本节中后半截教导滕世子文公的大机大用,很明显的,有四则:
第一则,他提出了历史的佐证,历史的经验,引用成覸对齐景公的问答。这一则没头没尾的话,很妙。成覸说,他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怕他什么来哉!这个“他”,指谁啊?如果是指历史的圣人,如尧舜、文武,那有什么可怕的呢?那只有景仰才对。既然提出了彼此都是一个大丈夫,又何必怕他。那么,这所怕的,当然不是历史上的圣人,一定是当时互相对立,势均力敌,或强过于齐景公之人吧!因此可知齐景公善用晏子,能够在春秋末期称霸一时,也确是经过一段艰苦辛酸的奋斗而来的。妙就妙在这里,在当时的滕国,处于战国紊乱之间,在岌岌可危中求生存,所以孟子首先引用了成覸这些话,以勉励滕世子——文公,不是没有深意的。至少,内抱圣贤之志,外修王霸之业,纵使不能图王,也可望于称霸,只在你自己的努力而已。
第二则,孟子引用颜渊讲大舜的话来勉励他。历史的名言故事多的是,要讲先王先圣,上有唐尧,下有大禹,都不讲,为什么单单用颜渊讲大舜的话来对滕世子讲?由于大舜的大孝吗?滕文公并非不孝。而且他的父亲滕定公,虽非大圣大贤,在历史上也并无甚令人非议之处。那么,是为了什么?那是因为大舜能躬耕于畎亩,来自田间,起于艰苦之中。所以必须要有颜渊安贫乐道之志以自处,有大舜起于艰辛之德以自勉,才能使滕之小国,坚强艰危地矗立于战国局势的狂风骇浪之中。
第三则,孟子引用了周公说周文王可以师法的故事。后来滕文公继位以后,也一再请教小国如何自处的问题。孟子的答复始终不离这个原则,要他师法文王。这一段可参阅《梁惠王》下章的几则对话。孟子环顾当时的世局,再三告诫滕文公,实在顶不住时,避地远徙,脱离现实的世局,图建千秋万世以后子孙大业的大计,这是一条路线。若不然,只能有为有守,尽忠职责,死守父母之邦,保存一分天地正气的气节,也是一条路子。
第四则,他告诫滕世子的,是继位以后如何力图改革、富国强政的原则,参读本章后面一节,便可一目了然了。
所以我说这一节所记述的,是孟子教导滕世子文公入世的大机大用。这样去看,也许不会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