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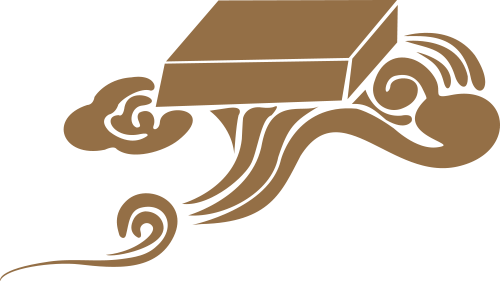
在我今天看来,对人性的几个问题,中国后世学术界很多人,都以孟子这里所谈的这段话拿来辩论。也就是把孟子说的“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和告子说的“生之谓性”,来讨论人性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人性,须要了解形而上人性的“本体”问题,与形而下人性的作用与现象的问题,“未生之前谁是我,既生之后我是谁?”究竟有没有一个“我”?假如有,这个“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生的?怎么死的?有形无形?唯物还是唯心?正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假定是上帝创造了万物,又是谁创造了上帝?假如说,上帝是上帝的妈妈造的,上帝的妈妈是上帝的外婆造的,那么谁又生了上帝的外婆的外婆的外外婆?假如说是佛造的,谁又造了佛?或者说,人生本来是如此的,那个“本来”又是什么?这就是哲学,就是大科学,也是宗教的根源。就像说地球是圆的,又是谁使它圆的?哲学与科学都是要想追寻这种问题的答案。
世界上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迄今约五千年,事实上当然不止五千年,因为地球的形成,据说就有好几十亿年了。地球上最早是先有人呢?还是先有蚂蚁或蟑螂呢?不管先有什么,那最早的第一个始祖,又是哪里来的?这就是哲学,也是科学,也是宗教。
任何一种宗教,开始时都是为了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后来,宗教自己无法解答,就设定了一个界限,就是不准问,信就好了,告诉你这样,就是这样。哲学也是信,例如说,房子里是亮的,但是总得打开一条门缝,让我看到里面一点点,我才会信,这是哲学家的态度。至于科学的态度,则是一定要进去看看,体会一下才信。所以宗教、哲学、科学,都是为了追求一个本性,一个宇宙万有的本来,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孟子在这里所谓的人性,不是讲形而上人性的本体问题,而是人性的作用与现象。孟子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人皆有之,但这些也都是生下来以后的。中国的道家分先天与后天,先天就是形而上的,后天就是形而下的。先天也就是父母未生以前,那个本性为先天;父母怀胎以后,在胎中已经是后天了。问那些怀过孕的母亲们就知道,有的胎儿在胎中很安静,有的胎儿就会拳打脚踢的,所以人在娘胎就已经是后天了。而本书记载告子说“生之谓性”,就是指离开娘胎以后,这样说来,告子说的这个人性是属于后天的后天了。
所以后世的学术界,是以后天人性的理论,去推测形而上的人性本体。就像孟子说的,这个白就是那个白,那个白就是这个白,也就是天生的盲人弯了手臂成鹅头状,再学两声鹅叫,就认为是白,而形象与白是不相干的。
由此我们了解,本节讨论人性的问题,是以“生之谓性”的这一个阶段的“人性”来讨论的,换言之,是讨论后天的人性。但孔子的思想并不是这样,在尚存的资料中,孔子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根据《论语》及有关资料,我们发现,孔子在这一方面的学术思想非常高深,子贡说他罕言天道事,就是孔子很少说形而上这方面的事。换言之,就是孔子认为这班学生,还不够程度来听这个问题。所以当子路问他,人死以后是不是还存在?又往哪里去?孔子就批评他:“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说,不必问死后到哪里去,先要研究生从哪里来,先要了解生的问题;现在活着的许多问题,都不能了解,如何能了解死后与生前的问题。
孟子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有其时代的原因的。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已经由春秋到战国战乱了三百多年。说到战乱,近三十年来,在台湾安定中出生成长的人,听到战乱一词,不会有所感受;而五十岁以上的人,对于战乱的苦难艰危,感受太深了。在战乱之中,人的生命毫无保障,一次战争下来,人就大量死亡。像秦国的白起,打一个胜仗,被他活埋的俘虏就是四十万;这些人都是母亲十月怀胎,三年哺乳,费了多少心血劳苦抚育长大的。像这样三五年一次战争,几百年下来,打得民不聊生,而且民穷财尽。
一个社会的动乱越多,人的思想渐渐就对生命起了怀疑,人为什么有这许多苦难?人生是为了什么?人又是怎么来的?人为什么如此争斗?为了这些问题去寻求答案。所以哲学思想的发达,都是在社会极动乱的时候。在极苦难的时代,会产生大学问家、大哲学家;太平时代则产生艺术家、文学家,创作一些艺术品,供人欣赏。所谓“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这句话,正是太平人语。
所以在变乱的时代,就研究人性的问题了,因此,孟子、告子他们的时代,远比孔子时代更为严重地来辩论这个问题,这也是历史文化的时代趋势。由古代就可以了解现代,在苦难的时代,才提出人道、人权、民权这些问题来争论,如果在太平时代,自然不需要去讨论这些问题。
现代青年该注意的问题,孟子在后面就会说到:“富岁子弟多赖。”台湾这三十年来,在社会富有安定、繁荣之中,青年们太舒服了,赖皮的也太多了,慢慢到了嬉皮青年的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