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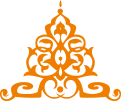
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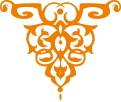
彭玉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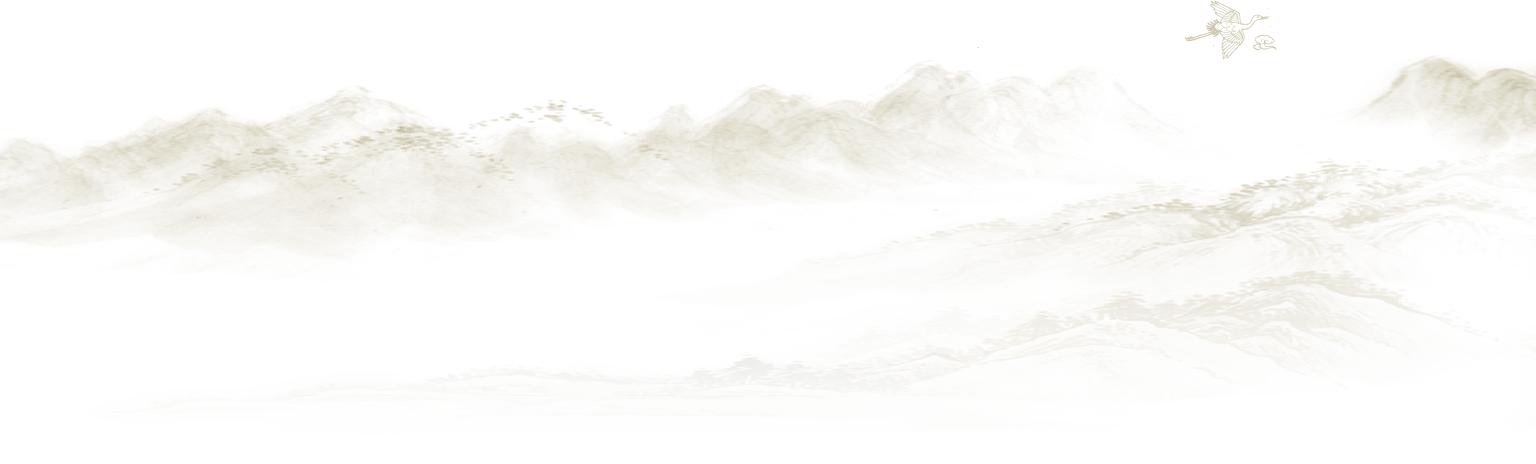
清词素称中兴,其中词学之发达,乃是其中之关键,从云间派、浙西派、常州派到临桂派,词派转换之间,词学思想的纷争也交叉其中。迄晚清之时,词学理论的门户之争渐趋消歇,而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相继而起,蔚然而成有清一代词学之璀璨结响。其中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不仅在三本词话中时序最早,而且其涉猎范围最广,篇幅最富,在以核心范畴为主,持以批评词史,总结理论方面,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都堪称是导夫先路之作。20世纪30年代,吴梅《词学通论》名动一时,其中许多观点即取资于《白雨斋词话》,因而其价值和意义值得充分估量。
陈廷焯 (1853-1892),原名世焜,字耀先,一字亦峰,镇江丹徒(今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陈氏一生以读书、著述、授徒为务,曾随父亲陈铁峰流寓泰州、黄岩等地,其生平《丹徒县志摭馀》和《续志》有简略记载,《续纂泰州志》亦将其列入“人物流寓类”。陈氏幼承庭训,早年致力诗词,中年潜心医理,笃志古文,而其志则在于经世济时,“尝言四十后当委弃辞章,力求经世性命之蕴”(王耕心《白雨斋词话·序》。本文以后所引用有关《白雨斋词话》文本及序跋文字,仅在引文后括注篇名或卷数)。
陈氏一生交游颇广。居丹徒时,曾过镇江,在焦山松寥阁有题壁。寓居泰州时,到过靖江、宜陵等地,集中并有纪游之作。己丑年(1889)为赴礼闱试去过北方,途径山东等地。迁居浙江黄岩时,道经南京、杭州等地。早年也曾南下广东等地。陈氏所到之处,广交学友,切磋学问,尽览当地名胜。
陈氏为人性情忧郁,年十四,读谢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诗句而“为之拍案惊绝,十馀日不敢起视焉”(陈廷焯《骚坛精选录》卷七,未刊,手稿今藏陈氏后人处),后来随着家道中落,流寓异乡,屡困科第,以“怨”命题的诗词频见于《白雨斋诗抄》、《白雨斋词存》之中。王耕心《序》说他“父兄之劳,靡不肩任;宗族之困,莫不引为己忧”。家族是如此,个人志向的困顿更是如此,其《出东门》诗云:“但看古来豪杰士,功名坎壈空尔为。矧余驽钝力不足,忧愁郁结当告谁?”则其忧郁的性情其实是渗透到许多方面的。
陈廷焯治学精苦,对经史根究义理,贯穿本原;对诗文取法乎上,标格甚高,早年作诗更是不屑于杜甫以外之人物。陈氏一生著述较富,其弟子包荣翰说他“著作林立”,王耕心也言及陈氏去世后“遗书委积,多未彻编”,可惜大都散佚。据笔者考索,约有以下八种:
1. 《词则》,词选,分大雅、放歌、闲情、别调四集,以“大雅”为正,三集副之。凡24卷,选词2360首,手稿今存陈氏后人处,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
2. 《白雨斋词存》,词集,凡46首,有光绪甲午年(1894)刻本。
3. 《白雨斋诗抄》,诗集,凡82首,有光绪甲午年(1894)刻本。
4. 《云韶集》,词选,凡26卷,选词3434首,为早期选本,未刊,手稿今藏南京图书馆。
5. 《词坛丛话》,词话,不分卷,凡106则,唐圭璋《词话丛编》有收录,手稿今藏南京图书馆,位列《云韶集》之前。
6. 《骚坛精选录》,诗选,残本,现存合六朝、盛唐诗选,附评,未刊,手稿今藏陈氏后人处。
7. 《希声集》,诗选,凡六卷,一称八卷,未见稿本、刻本,或已佚。《白雨斋词话》卷十云:“余选《希声集》六卷,所以存诗也;《大雅集》六卷,所以存词也。”《大雅集》乃其词选《词则》四集之一,则《希声集》是否为其一大型诗选之一部分,待考。
8. 《白雨斋词话》,词话,详下。
另有《唐诗选》和《二十九家词选》两种拟作,虽纲目初具,但未必成书。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自序》撰述于光绪十七年(1891)末,而其初稿则完成于1890年,并曾亲携初稿请王耕心为序,此后可能经过一年多的修订而定稿。故王耕心在《白雨斋词话序》中虽然提到陈廷焯去世之时,遗书“多未彻编”,但“手录《词话》,已有定稿”,故十卷本词话的定稿工作可能一直持续到陈廷焯去世前不久。陈廷焯对于词话的付梓是谨慎的,其甥包荣翰《白雨斋词话跋》云:“亦峰舅氏……所著《词话》八卷……荣请付梓以公诸世,舅氏不许,谓:‘于是编历数十寒暑,识与年进,稿凡五易,安知将来不更有进于此者乎?’则舅氏之浸润沉潜于此道,岂寻常诣力所能造也耶?”包荣翰此跋当作于八卷本编订之后,故有“《词话》八卷”云云,而其中所谓“数十寒暑”云云,则是就陈廷焯学词体悟之经历而言的,固非词话具体写作所历之时间。
就目前流传的情形来看,《白雨斋词话》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为八卷本,凡696则,有光绪甲午(1894)刻本,附《白雨斋诗抄》、《白雨斋词存》,此后唐圭璋《词话丛编》收录之《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杜维沫校点本《白雨斋词话》等,均出此甲午刻本;二为十卷本,凡738则,手稿今藏陈氏后人处,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末附唐圭璋《后记》),齐鲁书社有屈兴国校注之《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上、下册)。
为什么一种词话会出现两种版本?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十卷本为陈廷焯生前所定稿,故其自序有“萧斋岑寂,撰《词话》十卷”云云。但光绪甲午年(1894)初刻之时,已将手稿本删去42则,重新厘定为八卷。删除重订的工作可能是在陈廷焯父亲陈铁峰的授意下,由陈廷焯门人许正诗、王宗炎、包荣翰等完成的。汪懋琨、王耕心之序、包荣翰之跋都提及此事,而许正诗《白雨斋词话跋》言之更为明晰:
先师陈亦峰先生……既殁二年,太夫子铁峰先生整其遗著,得若干帙。正诗与同门王雷夏诸君子因有剞劂之请,而铁峰先生谦抑至再,以为不足传,仅许刻其《词话》八卷,并请诗词附焉。
许正诗特别提到陈廷焯尊翁“仅许刻其《词话》八卷”。然则馀出的两卷是陈铁峰删略,还是陈廷焯门生所为,言语之间仍不免模糊。唐圭璋在影印本《白雨斋词话·后记》中说:
初,陈氏殁时,尊翁铁峰老人尚健在,令陈氏门人许正诗、王宗炎、包荣翰等删十卷为八卷,于光绪二十年(1894)木刻行世。
唐圭璋的这一结论或许只是以情理推测的,但确实是可能性最大的。
那么,删略的原则是什么?诸家序跋均未明言。笔者粗加对勘,发现删削、修改之条目或为陈廷焯自评己词的内容,或为语涉纤艳而宗旨略背其沉郁顿挫之说者。前者之例如:
《蝶恋花》一调最为古雅。……余曾赋四章,非敢云抗美古人,要亦不外《离骚》“初服”之义。(卷六第27则)
……己卯九月,余作《买陂塘》一阕,呜咽缠绵,几不知是血是泪,盖天地商声也……(卷六第33则)
余曾作《菩萨蛮》云:“青山断续江如带……春归人不归。”起二语嫌着力,余皆悲郁而和厚,有风人遗意。(卷十第58则)
寂寞空城鼓角鸣,敌楼西望旅魂惊……此余丙戌年《杂感》中四律也。声调极悲壮,而不免过激,发之于诗尚可,发之于词则伉矣。(卷十第59则)
删削的条目中约有一半属于这一类,或许陈廷焯尊翁觉得不宜自评若此,有失著述体例,故请删略。另有一部分条目内容与此相类,但措语尚有分寸,故或斟酌其词,或合并数则为一则,以省篇幅。其例如十卷本卷六第40、41则自评自己所作艳词之法,八卷本仅取第40则开头一节,将“然如《菩萨蛮》十二章”以下文字悉数删除,并接以第41则的内容,即使所保留或衔接部分的文字,也略有润色。
或是出于维护陈廷焯已沉郁顿挫为理论核心的需要,十卷本卷三若干论及浙西朱彝尊、董以宁诸家艳词、妖词而位置大体相接续的18则词话也被一例删除。如:
竹垞艳词,确有所指,不同泛设,其中难言之处,不得不乱以他词,故为隐语,所以味厚……(卷三第58则)
竹垞《西江月》结句云……凄丽而幽索,总非凡艳。(卷三第60则)
……国初诸公多好为艳词,未有如竹垞之空前绝后者。虽非正声,亦令人叹赏不置。(卷三第61则)
董文友,词中之妖也,与王次回《疑雨集》可谓匹敌。《满江红》十二章,置之《蓉渡集》中,无乃不类。(卷三第70则)
《花影词》不过如倚门卖笑者流,并不足为词之妖。《蓉渡词》乃真足惑人矣,此妖之神通也。(卷三第72则)
例多不烦举,但对浙西诸家艳词的这类评论的整体性删除,其目的或因陈廷焯出语略显随意,或这类词话的存在可能影响到陈廷焯理论的逻辑性、严密性,故为矜慎起见而删除。
至于那些词话内容虽然保留下来,但进行过少量文字加工的情形也颇为多见,翻检原书,自可一一勘察,这里不再说明。
可以发现,经过删订后的八卷本词话,不仅散漫的文字被剔除了,而且内容更为紧凑,理论的周密性得以加强。所以相形之下,八卷本的理论价值更为突出了。当然,从考察陈廷焯词学思想的原生形态或丰富性角度而言,十卷本的价值也不容忽视。
一般说来,陈氏早期推崇浙派,创作与论述都受其影响,选本《云韶集》及《词坛丛话》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浙派以朱彝尊为首,成于康、乾间。康熙戊午(1678)年《词综》刻版问世后,浙派所讲究的清灵醇雅,把人们稔熟的目光从唐五代北宋引向清雅而有思致的南宋,给深受明词啴缓习气和淫曼情调熏染的前清词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朱彝尊《词综·发凡》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陈廷焯沿朱氏《词综》之绪并扩充了明清词而成《云韶集》一编,自称是“以竹垞太史《词综》为准”,在具体词人词作的选录上,他也与朱氏抑扬同道。他的《词坛丛话》在对姜夔、张炎的崇尚以及“极工极变”说上,都与朱氏前呼后应。但是,陈廷焯因身世而产生的忧郁气质以及自幼积蓄的入世精神,都使他与浙西词派若即若离,这“若离”部分的渐生渐发,最终使他归诸常州派门下。
陈廷焯以其“沉郁顿挫”词说而在当时词坛自树一帜,推进了常州派理论的发展。但“沉郁”说并非陈氏闭门苦思,一朝所得,它在陈氏早期著述中留有清晰的痕迹。如他评辛弃疾《浪淘沙·山寺夜作》说:“沉郁顿挫中,自觉眉飞色舞。”(《云韶集》卷五)评周邦彦的《兰陵王·柳》说:“又沉郁又劲直,有独往独来之概。”(同上卷四)等等。此外,陈氏还通过对部分词人词作的具体品评,显示出他对“沉郁”词说的朦胧体悟,如评周邦彦的《六丑·蔷薇谢后作》说:“如泣如诉,语极呜咽,而笔力沉雄,如闻孤鸿,如听江声,笔态飞舞,反复低徊,词中之圣也。”(同上)又如评陆游的《双头蓬·华发》说:“沉郁顿挫,极淋漓宛转之致,明是哀时伤事,一片血泪,而说来一丝不露,意境虽极悲凉,遣词却极婉约,那得不令人心折。”(同上卷七)合观这两段评语,已经比较接近后来的“沉郁”说,从中可清楚地看到陈氏“沉郁”词说的历史演变。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云:“廷焯受词学于庄棫,而接迹于常州二张之派也。”(《集部·词曲类》)陈氏自己也曾说过:“余词得力处,半有蒿庵一言,半有道农、子薪辩论之功也。”(《词话》卷七)因此,陈氏的词学渊源虽以庄棫及二张为主,而道农与子薪的“辩论之功”也是不容忽略的。
庄棫字中白,江苏丹徒人,有《中白词》一卷。庄氏为常州派后期重要作手,与谭献齐名,并与陈氏同里且有戚谊,年长22岁,陈氏呼为“姨表叔”。陈、庄初遇于光绪二年(1876),这一次相遇是陈氏词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词话》云:“自丙子年(1876)与希祖先生(按,即庄棫)遇后,旧作一概付丙,所存不过己卯(1879)后数十阕,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卷六)此后双方又有数次见面,而每次相晤,必谈论竟夕,教改旧作,探讨词艺,认识逐渐加深。光绪四年(1878),庄氏对陈说:“子知清真、白石矣,未知碧山。悟得碧山,而后可以穷极高妙。”(《词话》卷五引)陈氏后来述作《词语》曾回忆及此,言语之间,不胜慨叹。他说:“余初不知其言之恳也。十馀年来,潜心于碧山,较曩时所作,境地迥别,识力亦开,乃悟先生之言,嘉惠不浅。”(卷六)他以其词的得力处归于“半有蒿庵一言”,足见得他对庄氏的敬重。《词话》对中白词就颇为称赏:“近时词人,庄中白尚矣,蔑以加矣,次则谭仲修。”又说:“余观其词,匪独一代之冠,实能超越三唐两宋,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自有词人以来,罕见其匹。”(卷五)语或稍过,但情意可见。
陈廷焯在领会庄棫的理论之后,遂由“庄”而接迹于张惠言、张琦。张惠言为常州派开山,当浙派末流竞事绮藻、堕入恶趣之时,张惠言及其弟张琦出《词选》一编,重整词风。由乐府以上溯《风》、《骚》,阐意内言外之旨,以“深美闳约”的温庭筠、韦庄词为极境。在张惠言看来,大凡词之佳构,“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词而己”(《词选序》)。张氏本此倡寄托、比兴之说,主张从思想内容上尊崇词体,并提出创作和衡鉴词的两项标准:缘情造端和低徊要眇。陈氏心折于此,他说:“诗词所以寄感,非以徇情也,不得旨归,而徒骋才力,复何足重?”(《词话》卷一)这是对“缘情造端”的张论。而他忌词的“一直说去,不留馀地,虽极工巧之致,识者终笑其浅”(同上),则是考虑到词体“低徊要眇”的艺术特点的,与张氏同调而精微过之。
伴随着对“二张”的恭奉,陈氏由早期倾向于浙派,转而对朱彝尊、陈维崧、厉鹗大加指责,他首先从根本上否定浙派的词学纲领——汪森的《词综序》,认为是“不知词中源流正变”,只是阿附竹垞之意。在他看来其具体不足有二:一是以姜夔醇雅为宗而归诸“句琢字炼”,这是舍本逐末,所以陈氏讥为“甚浅陋,不知本源之言”;二是认为白石涵盖南宋诸家,陈氏也不以为然,他说:“谓白石拔帜于周、秦之外,与之各有千古则可,谓南宋名家以迄仲举,皆取法于白石,则吾不谓然也。”(《词话》卷十)这一论见确实针砭了浙派为树立宗派而夸大白石的习气。
陈氏词学观的形成,还受到他的同道学友的影响,也就是所谓道农与子薪的“辩论之功”。李慎传字君胄,号子薪,又号承霖,丹徒人。生卒不详。曾任江宁县训导,国子监学正,有《植庵集》。据陈氏《植庵集序》说:“光绪乙亥(1875)仲夏,始识李君子薪于海陵……往来无间者七阅寒暑。”子薪仕履坎坷,序云:“酒酣耳热,未尝不慷慨悲歌,思有以自奋。”他年逾四十始习倚声。序称他“词则取径玉田,而犹不废猛起奋末之音,则遇为之也”,也颇能知人论世。子薪对庄棫极为尊敬,他曾说:“庄希祖词,穷极高妙,竟难于位置,即置之清真、自石间,尚非其驻足处。”(《词话》卷六引)所以庄棫去世后,子薪亟欲得其全稿以付梓,崇仰之情,可见一斑。子薪对庄棫的崇敬,在某种程度上当也促进了陈氏对庄棫理论的接受程度。
子薪词学,没有直接见之于文字的流传,所谓“辩论之功”,也只能是仿佛而已。但道农却有一篇《白雨斋词话·序》在,略可窥见他与陈氏的词学来往。道农即王耕心,河北正定人。官南河侯补同知,工诗古文辞,尤精内典,著有《贾子校正》、《龙苑文稿》等。陈、王初识于同治之季,后并结为姻亲,相知很深。道农论词有所谓“文心文辞”说。所谓“文心”,就是指作者的性情,词的作用与意义就在于抒发性情。他说:“文心之源,亦存乎学者性情之际而已。为文苟不以性情为质,貌虽微,人犹得抉其根,不工者可知。所谓词者,意内而言外,格浅而韵深,其发摅性情之微,尤不可掩。”陈氏《词话》也雅重性情,他说:“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泄。古之为词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悦己也。”(卷十)其间意脉是相通的。道农还认为,词人好上溯的《风》《骚》,其实只是一种文辞之源,而无关于文心,此即所谓“文辞”说。他说:“故词之为体,诗以为祢,曲以为子,识者为之,莫不沿溯汉魏,游衍屈、宋,以蕲上窥《三百篇》之旨,欲谓不如是不足以澂其源、涉其奥,其说亦既美矣。然予尝以为此文辞之源,非文心之源也。”此论近似性灵说,和陈氏推源于风骚不同,可见当时辩论之激烈。
总之,陈廷悼的同学渊源是丰厚的,他广泛吸取营养,建构自己的理论沐系。其中对“二张”与庄棫的汲取尤多,其词学观念的纲纲目目,都大体可从他们那里寻得端绪。当然,这些对陈氏来说,不是一种简单的承袭,机械的组合,而是熔铸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审美趣味,这种熔铸在经过与同道论辩切磋之后,益发趋于稳固。因而陈氏词学思想的扭转,既有时代和环境的召唤,也有他自身审美观念的潜移默化,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同等的注意的。
《白雨斋词话》是陈氏后期重要的词学著作,体现了其词学的最高成就。白雨,古训为大雨、暴雨,亦峰取为斋名,或含深意。《白雨斋词话》自序云:“萧斋岑寂,撰《词话》十卷。”则“白雨斋”意即“萧斋”,亦即岑寂之斋。杜甫《寄柏学士林居诗》有“青山万重静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萝。乱世飘零予到此,古人成败子如何。”“白雨”一词,略含怅惘之情,亦峰斋名,或出于此。在《白雨斋词存》、《白雨斋诗抄》中曾有三次涉及到雨,一是《摸鱼儿》之“留君少住,愿剪烛西窗,一杯相属,同听夜深雨”,一是《路出靖江怀亡友王竹庵》之“黄芦苦竹秋萧瑟,肠断江楼暮雨天”,一是《过伍子祠》之“斜日西陵路,临江故址存。悲风怨种蠡,苦雨泣兰荪”。无论是“夜深雨”、“暮雨”、“苦雨”,总之,雨给亦峰的感觉是沉重的,愁苦的,他在岑寂的白雨斋中观雨、听雨,引发感慨,营构其词学理论体系。所以以“白雨”名斋名书,其中应寓有深意。《白雨斋词话》的理论核心是沉郁说。自序尝称《词话》曰:“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一是。”可以说,一部《白雨斋词话》就是沉郁说的理论阐述和批评实践的结合。沉(古文作沈),《说文》解作“陵上滈水也”。段注以为湛没之“湛”即其假借,意为“没也”。郁,《说文》释为“木丛者”,段注引毛笺《秦风》“郁彼北林”曰:“郁,积也。”又引郑司农注《考工记》等,说郁即“宛”,段注并曰:“宛与蕴、蕴与郁,声义相通。”可引申为宛曲、宛转之义。陈氏沉郁说含义虽丰,而要义不出于此。《词话》云:“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卷一)则“沉”关乎词的思想的深厚,“郁”关乎艺术韵味的悠长,两者虽有侧重,但其实是彼此依存的。合而论之,则沉郁是陈氏对词的总体的审美规范,它的基本内容有情感与作法两大部分。
陈氏《词话序》曾称,论词而本诸《风》、《骚》是为了“正其情性”,而沉郁的作用之一就是要“见性情之厚”,因此,沉郁正是情性的艺术外观。性关乎天分,又系于学养,“性动为情”,“性”最终是以“情”的形式出现的。陈氏说:“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泄。古之为词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悦己也。”(《词话》卷十)陈氏释“沉郁”,其实对情感即已大体规定。他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孳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词话》卷一)这种对愁怨情感的青睐,其实也体现了陈氏对词体的看法。沉郁说首先要求作者性情忠厚,要“思无邪”,所以陈氏上溯《风》《骚》,以屈原忠君爱国、忍辱负重为榜样,将一己之感情受约于政治、伦理、道德之下。因此,陈氏沉郁说的情感有着种种的规范。
陈氏认为情感之沉,无过于悲怨,所以沉郁有时也径称悲郁。词可以怨是词的一种特质。璞函送春词曰:“青子绿阴空自好,年年总被东风误。”陈氏评曰:“意味极厚,词之可以怨者。”(《词话》卷八)其实,在陈氏看来,词不仅“可以怨”,也应该怨,只是这种怨是由作者性情之怨而行于词意之怨的。陈氏评史位存《谒金门》词就集中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团扇先秋生薄怨,小池风不断’,神似温、韦语。然非其中真有怨情,不能如此沉至,故知沉郁二字,不可强求也。”(《词话》卷四)陈氏论沉郁之情感而强调以怨为核心,这和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密不可分。中国文学从来就有一条与“怨”并行的创作道路,屈原抑郁下僚而作《离骚》,司马迁穷困委顿愤作《史记》等等,都以创作实践证明了“怨”给文学带来的巨大生命力。陈氏踵论前贤曰:“诗以穷而后工,倚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词话》卷十)约略而言,陈氏论怨亦含三个方面:一是怨必由身世之感而来,心中有泪,笔下才会呜咽。如王沂孙咏物诸词,俱含有一掬亡国之泪,借物以咏写其哀。二是怨行之于文必以吞吐出之。怨情感物而动,发自内心,表达却可以有不同形式,而在“要眇宜修”的词中,情感的表达却必须是温厚的、有度的,即使是怨情,也必须运意高远,吐韵妍和。所以怨的表现还有个方式与程度问题。陈氏说:“黍离、麦秀之悲,暗说则深,明说则浅。”(《词话》卷八)三是从鉴赏的角度看,含有怨情的作品容易感发读者的情绪。《词话自序》云:“夫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因此,沉郁说的宗旨是既感其所感也感其所不感,是从读者体悟之广而言的。
沉郁说是陈廷焯总的创作原则,因而它在情感规范之外,也有对表现这种情感的方法规范。沉郁究竟何指?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是指词的总体风格,但这一说法殊嫌牵强。“沉郁”一词,一般认为是从杜甫《进雕赋表》中而来。杜文云:“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给,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杜甫在这里自评其述作“沉郁顿挫”而未明其义,使人难以索解。参照《词话》,则评杜诗沉郁者,常及乎意境二字,卷九云:“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顾其力量充满,意境沉郁,嗣后为诗者,举不能出其范围。”则杜氏“沉郁”似与意境相关,非指风格显乎其然。《词话》评辛弃疾词亦可为证,其云:“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沉郁。”(卷一)如果我们要寻找沉郁非风格的内证,则也极为容易。卷一自述撰《词话》之旨在“洞悉本原,直揭三昧”,卷十分辨唐宋词派也云:“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则一。”而“本原”何谓呢?卷四在评江昉《练溪渔唱》时云:“句琢字炼,归于纯雅,只是不深厚。盖知学南宋,而不得其本原。”陈氏于此“本原”后小缀数语:“本原何在?沉郁之谓也。不本诸风骚,焉得沉郁?”直示本原在沉郁,故推诸风骚,为得沉郁,亦复为得本原,本原、沉郁是密不可分的。明乎此,我们自然不能把唐宋名家词的整体风格都说成是沉郁。流派的归类,大旨以风格为准,把不同的风格都建筑在同一本原上,其实是指某些创作群体在作法上的某种一致性。笔者研绎《白雨斋词话》,认为沉郁是陈氏最高的也是审美的艺术规范,因为“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词话》卷一)。沉郁必须体现在词中,所以与词的作法有密切联系,也就是说,词的作法也必须有相应的规范。卷一云:“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顾沉郁未易强求,不根抵于风骚,乌能沉郁,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而陈氏释“沉郁”,除了在寄托、情感的弃浮薄上有特定要求外,对词之作法也有相应的规定,所谓“意在笔先,神馀言外”,所谓“若隐若现,欲露不露”,所谓“终不许一语道破”等等,和历久相沿的比兴之义极为相合。卷八释“兴”,语言也并无多异,“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可见,沉郁是藉诸比兴来实现的,它与作法有着天然的联系。
唐五代词不必说,“不可及处正在沉郁”。陈氏于两宋词家,誉为“未有不沉郁者”凡六家,即北宋之张先、秦观、周邦彦,南宋之姜夔、王沂孙、史达祖。如果我们结合《白雨斋词话》的批评实践,则会发现,陈氏推许的每一首词几乎都是从作法起解的。卷八言:“周、秦词以理法胜,姜、张词以骨韵胜,碧山词以意境胜,要皆负绝世才,而又以沉郁出之,所以卓绝千古也。”这种作法,陈氏冠以总名曰“顿挫”。沉郁顿挫本是合成词,陈氏在《词话》中则一分为二,以顿挫达致沉郁。所以在某些场合,陈氏以顿挫置于沉郁之前。如卷七评周、秦之异同曰:“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沉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卷九更曰:“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因此,沉郁之作法,也即是指顿挫之法。
沉郁说虽非直接关乎风格,但因为其毕竟是关乎词体内外的艺术规范,由于这种规范的普遍意义,形诸作品,也就自然地呈现出某种共同的倾向,这种倾向有助于风格的构成。陈氏认为,诗词一理,因为他们同本《风》《骚》,但是诗之沉郁,可纳之于古朴、冲淡、巨丽、雄苍四者之中。而“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以词”,沉郁是词的最高也是唯一的审美准则。如评吴文英词“超逸中见沉郁”,苏轼词“超旷中见沉郁”等等,实质上是说明以沉郁为原质而构成的不同风格。由于词的风格以沉郁为原质,所以陈氏把传统的豪放、婉约词风都归之于沉郁的推衍。《词话》云:“诚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沉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否则豪放嫌其粗鲁,婉约又病其纤弱矣。”(卷一)因此,对于词之风格,陈氏另有他独特的体认,他的沉郁是所有理想、风格得以构成的必要条件,所以,词人借此可以调和不同的风格而成就一种新的涵盖面更广的风格。但同时必须指出:沉郁虽可铸成不同之风格,而其自身却非别为一种新的风格。本诸沉郁的风格大致偏向于婉约。两宋词人,全部沉郁者凡六家,即北宋之张先、秦观、周邦彦,南宋之姜夔、王沂孙、史达祖,全部是婉约之格律派词人,审美倾向十分明显,其他如对苏轼、辛弃疾、贺铸、吴文英、张炎等,虽也时或以沉郁相称,而为其所赏者,则也并非大声铿锵者。如《词话》评辛弃疾《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曰:“龙吟虎啸之中,却有多少和缓。”(卷八)稼轩此词即是比较温厚的。所以沉郁的风格指向虽然是宽广的,而深契于陈氏审美观的却又是有限的。
陈廷焯倡沉郁说而推诸风骚,其中包含有对本于忠厚性情而产生的悲凉情绪的张扬,而这也是他对悲剧艺术的审美规范。中国的悲剧理论一向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但富于悲剧意味的创作却是古已有之了。《诗经·泉水》曰:“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庄子·山木》市南僚进言于鲁侯曰:“游于无人之境”、“大莫之国”,则可以“去君之累,除君之忧”,等等,都是早期作家忧患意识的文学折射。《离骚》的哀怨情调更是历来为人们所共识的,陈廷焯和常州派词人洞察其中奥窔,亟命风骚者,也是意图在词学中肯定和渲染这一种情调,因此,沉郁说与悲剧美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或者说,沉郁说就是以悲剧美为宗旨的。陈氏是重视词的悲剧情调的,如史位存有送春词“青子绿阴空自好,年年总被东风误”,便被认为是“词可以怨”的例子,冯延巳《蝶恋花》四阕也为陈氏评曰:“情词悱恻,可群可怨。”(《词话》卷一)陈廷焯沉郁说的情感基调以怨为核心,也是体现了这一点。当然,从“词可以怨”到进而形成悲剧美,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沉郁的表现过程。所以我们说沉郁说是浸透着悲剧艺术精神的。
陈廷焯的词学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陈廷焯的诗学目前还完全是一个空白,至其诗学与词学之关系更乏人问津。实际上除了其诗选《骚坛精选录》外,《白雨斋词话》中也有相当丰富的诗学材料,加上陈廷焯相当数量的诗歌创作,(陈廷焯著有《白雨斋诗钞》,由同里高寿昌评选,其受业甥包荣翰校订,并经陈廷焯父亲陈铁峰审定,光绪甲午年,由许正诗等与其《白雨斋词话》和《白雨斋词存》一同刊行,今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白雨斋诗钞》不分卷,存诗78首,诗尾间附有高寿昌简短评语。陈廷焯诗歌的实际数量当远在78首之上,高寿昌在其《闺中秋咏》十四首题下注曰:“亦峰喜为香奁体,余悉裁汰之。”故入选的诗歌只是其中部分而已。)其诗学的源流本末还是大致可以厘清的。
诗与词是陈廷焯致力的两个重要领域,他认为诗与词实际上是同体异用的关系,本原一致,但表现各异。诗不仅是词的源头,(关于诗、词文体体性的转变,陈廷焯《骚坛精选录》选录隋代侯夫人《看梅》诗“砌雪无消日,卷帘时自颦。庭梅对我有怜意,先露枝头一点春。”并评论说:“音节近词,诗之入于词也,盖以渐而入矣。”从音乐及其相关语言句式的不同,揭示出从诗到词的渐变轨迹。)而且也是学词的基础,“诗词一理,然不工词者可以工诗,不工诗者断不能工词,故学词贵在能诗之后。若于诗未有立足处,遽欲学词,吾未见有合者”(《词话》卷九)。像王沂孙等人的诗歌虽然不能卓立千古,但“要其为词之始,必由诗以入门,断非躐等。”(《词话》卷九)陈廷焯以温厚为体、沉郁为用以论词,其批评话语虽来自于杜甫的文章,其理论内核也与他对杜甫诗歌特点的感悟有关,但其立论的本原其实还是以《诗经》《楚辞》为原点的,他在《词话》自序中说:“……飞卿、端己首发其端,周、秦、姜、史、张、王曲竟其绪。而要皆发源于《风》《雅》,推本于《骚》《辩》。”这八家的词被陈廷焯誉为“沉郁”的典范,而其根源正在其对《风》《骚》艺术精神的传承和宏扬。而《风》《骚》的最大特点即在忠厚沉郁,《词话》卷一云:“作词之法,首贵沉郁……不根柢于《风》《骚》,乌能沉郁?十三国变风,二十五篇楚词,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白雨斋词话》对词史的钩勒、对词人词作的品评,其批评标准正在于这些词人对《风》《骚》精神是把握还是疏离。
“《风》《骚》为诗词之源”(《词话》卷九),而《风》《骚》的忠厚缠绵又同是诗和词的根本,(《词话》卷九云:“温厚和平,诗教之正,亦词之根本也。”)这是陈廷焯并治诗词且将诗学与词学多加贯通的根源所在,所以在陈廷焯的思想体系中,“沉郁”是连接诗与词的重要纽带。不过陈廷焯同时也认为“沉郁”在诗与词中间的表现方式和重要程度是有差异的,他说:“诗词一理,然亦有不尽同者。诗之高境,亦在沉郁,然或以古朴胜,或以冲淡胜,或以巨丽胜,或以雄苍胜。纳沉郁于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即不尽沉郁,如五七言大篇,畅所欲言者,亦别有可观。若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词话》卷一)又说:“诗词皆贵沉郁,而论诗则有沉而不郁,无害其为佳者。杜陵情到深处,每多感激之辞,盖有万难已于言之隐,不禁明目张胆一呼,以舒其愤懑,所谓不郁而郁也。作词亦不乎是,惟于不郁处,犹须以比体出之,终以狂呼叫嚣为耻,故较诗为更难。”(《词话》卷六)又说:“诗之高境在沉郁,其次即直截痛快,亦不失为次乘。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次乘也。”(《词话》卷十)陈廷焯三复其言,申论诗与词在“沉郁”问题上的不同取向。在陈廷焯看来,诗歌的“沉郁”只具有或然性,且表达方式比较自由;而词的“沉郁”则具有必然性,且是唯一和最高的价值标准。而在语言表现上,陈廷焯认为诗与词具有“同体而异用”的关系,他说:“温厚和平,诗词一本也。然为诗者,既得其本,而措语则以平远雍穆为正,沉郁顿挫为变,特变而不失其正,即于平远雍穆中,亦不可无沉郁顿挫也。词则以温厚和平为本,而措语即以沉郁顿挫为正,更不必以平远雍穆为贵。诗与词同体异用者在此。”(《词话》卷十)这是诗与词在“沉郁”问题上的同中之异。在《骚坛精选录》中,沉郁固然是入选的基本标准,但他对汉魏的风骨,谢朓、鲍照等人的清刚之气,以及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冲和淡远,也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可见其诗学之豁达。而词则端正“沉郁”一路,毫不松懈,其诗学与词学理念之不同,就其批评实践即已表现得很充分了。
在诗词发展的规律方面,陈廷焯持基本相同的观点:即大体经过创古、变古、失古、复古的过程。他在《词话》卷十中说:
温、韦创古者也。晏、欧继温、韦之后,面目未改,神理全非,异乎温、韦者也。苏、辛、周、秦之于温、韦,貌变而神不变,声色大开,本原则一。南宋诸名家,大旨亦不悖于温、韦,而各立门户,别有千古。元、明庸庸碌碌,无所短长。至陈、朱辈出,而古意全失,温、韦之风,不可复作矣。贞下起元,往而必复,皋文唱于前,蒿庵成于后,《风》、《骚》正宗,赖以不坠,好古之士,又可得寻其绪焉。
这是他以温、韦之词为正宗而梳理出来的简明词史发展观,即大体以唐五代为创古时期,代表人物是温庭筠和韦庄;两宋为变古时期,代表人物是晏殊、苏轼、辛弃疾、周邦彦、秦观等人;清代前中期为失古时期,代表人物是陈维崧、朱彝尊;清代中后期为复古时期,代表人物是张惠言、庄棫。陈廷焯大力标举温、韦的词宗地位,其实还是立足于“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的词的本体意识,与他论词而必上溯《风》《骚》的思维定式是一致的,因为“飞卿词全祖《离骚》,所以独绝千古”,“飞卿《菩萨蛮》十四章,全是《楚骚》变相,古今之极轨也”,“韦端己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是词中胜境”(《词话》卷一),温、韦两人对于确立词中的《风》《骚》传统,具有奠基的意义,所以陈廷焯独致青睐,并以此作为词史发展的基点和支点。
陈廷焯对诗歌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认识与此相仿佛。他在《词话》卷六中说:
《楚辞》二十五篇,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宋玉效颦,已为不类。两汉才人,踵事增华,去《骚》益远。惟陈王处骨肉之变,发忠爱之忱,既悯汉亡,又伤魏乱,感物指事,欲语复咽,其本原已与《骚》合。……嗣后太白学《骚》,虚有形体;长吉学《骚》,益流怪诞;飞卿古诗,有与《骚》暗合处,但才力稍弱,气骨未遒,可为《骚》之奴隶,未足为《骚》之羽翼也。
又说:
余谓自《风》《骚》以迄太白,诗之正也,诗之古也;杜陵而后,诗之变也。(《词话》卷九)
他认为李白的诗尚在古人的绳墨当中,而杜甫则“无一篇不与古人为敌,其阴狠在骨,更不可以常理论”,所以他明确反对以李白为“变”而以杜甫为“正”的说法,因为杜甫在不悖离《风》《骚》的前提下,将汉魏六朝的面目洗脱殆尽,“不变而变,乃真变矣”(卷九)。杜甫的“变”实际上是一种“化”,他说:“不知古者,必不能变古,此陈隋之诗所以不竞也。杜陵与古为化者,惟其与古为化,故一变而莫可复兴。”(《词话》卷九)这种“化”其实就是在继承“古”的基础上,结合特定时代和个人超迈绝伦之才,从而熔铸成一种新的牢笼百家的传统,旧传统中的“古”也就在这种新传统中淹没无痕了。所以虽然词史发展在唐宋创古、变古,元明和清代前中期失古以后,到了清代中后期尚可再行复古;而诗歌的发展则有些特殊,创故、变古与复古在杜甫之前就已完成了轮回,杜甫之后就是新的天地了,所以他说:“诗有变古者,必有复古者。(原注:如陈伯玉扫陈、隋之习是也。)然自杜陵变古后,而后世更不能复古。(原注:自《风》《骚》至太白同出一源,杜陵而后,无敢越此老范围者,皆与古人为敌国矣。)何其霸也!”(卷九)这是陈廷焯在诗词历史观念上的同中之异。
陈廷焯倡导的创作途径是由诗以入词,从《骚坛精选录》与《白雨斋词话》的对勘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类似或可以互证的地方,特别是在对于“沉郁”在诗词中的不同地位和表现形态,两本的观点十分接近。所以《骚坛精选录》的编选年代虽然难以确考,但其以杜甫沉郁为宗,上溯《风》《骚》的批评理念,与其在《白雨斋词话》中表现的理念颇为相似,两书的编撰年代当不会相差很远。鉴于陈廷焯的词学思想在光绪二年(1876)以后发生了从崇尚浙西派到偏宗常州派的重要转境,(《词话》卷六云:“自丙子年与希祖先生遇后,旧作一概付丙,所存不过已卯后数十阕,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则《骚坛精选录》一选当编选在1876年(丙子)以后至《白雨斋词话》撰成的期间。很可能他的学术理念是在诗歌中渐趋成熟以后,再移之于论词的,则《骚坛精选录》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就更显珍贵了。
陈廷焯诗学和词学的根基是建立在对杜甫诗歌的理论解读上的,他从早期诗歌创作追步杜甫,到后期在《骚坛精选录》和《白雨斋词话》中全面解析杜甫,杜甫的身影通贯一生。他以《风》《骚》的忠厚沉郁为诗词共有之本源和本原,标举以沉郁顿挫为特征的杜甫诗歌为创作典范,梳理诗史的发展,形成了自成一格的创古、复古、化古的理论格局,并以杜甫的“化古”为诗史一大结穴。在此基础上,陈廷焯把作为诗学核心之一的“沉郁”升格为词学核心的唯一,力辨其在诗词体性和表现形态方面“同体异用”的关系,体现了其诗学与词学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彼此区别,建构了相当完整的诗学和词学体系,在理论发达但理论形态相对涣散的晚清,颇具理论疏凿手段,已肇新诗学和新词学理论体系之端倪。他大力提倡的忠厚之性情、沉郁之境界、顿挫之姿态和风骨之意蕴,在晚清朝代更替、内忧不断、外患频仍的时代巨变时期,特别是甲午之战以后,在诗词创作界竟得以鲜明体现,王鹏运、朱祖谋等的《庚子秋词》即与陈廷焯之学说契若针芥。(徐珂《近词丛话》云:“光绪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京城,居人或惊散,古微与刘伯崇殿撰福姚,就幼霞以居。三人者,痛世运之陵夷,患气之非一日致,则发愤叫呼,相对太息。”三人约为词课,拈题唱酬,后集为《庚子秋词》。李佳《左庵词话》卷下则称《庚子秋词》“多悲愤苍凉之作”。郭则沄《清词玉屑》评论《庚子秋词》“皆隐约其词”。综合诸家所论,则“沉郁”二字,实可概括《庚子秋词》的基本风格特征。)而自端木埰、王鹏运、况周颐绵延一线的“重拙大”说以及王国维的境界说等,其理论内涵与沉郁说之间正有着丝丝缕缕难以分割的关系,(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解释“重”就是“沉着”,又说“填词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韵,去成就不远矣”,“真字是词骨”,等等。“重拙大说”的基本内涵,与陈廷焯解释的“沉郁”说完全可以沟通。王国维“境界说”中“有我之境”对悲哀之情的重视,也正是沉郁说的一个重要内涵。)则陈廷焯的文学思想不仅是传统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结,对于晚清的诗词创作和诗词理论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引导意义。
本书所用底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白雨斋词话》手稿本,对勘齐鲁书社1983年版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上、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唐圭璋《词话丛编》本《白雨斋词话》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杜维沫校点本《白雨斋词话》等。希望能给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读本。
编者按: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用红色小字夹注的形式,对原著所引词句出处、人名字号和著作作了简单注释(仅限于每段首次出现)。而原文之夹注,则排以黑色小字,以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