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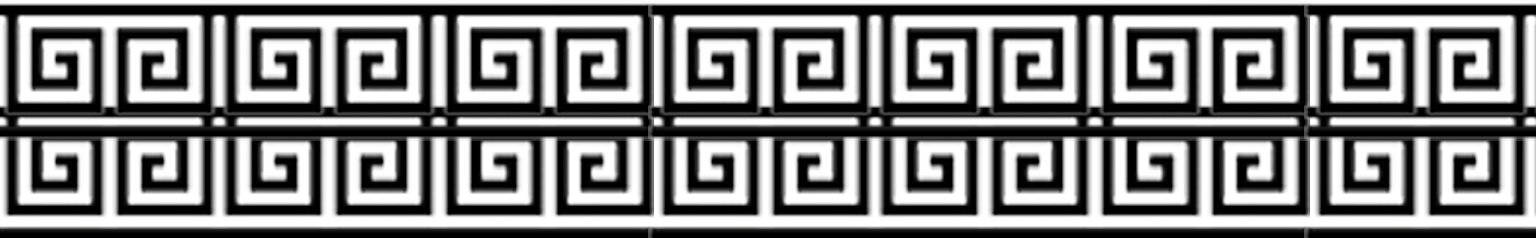

记1978—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
老校友回忆,“文革”前中央美院附中有位看门老汉,每接电话,头一句总是曼声应道:
“我中央啊!”
这不是笑话,真人真事,亦且老汉懂语法,说得并没错:“中央美术学院”一词,主语不是“美院”,而是“中央”。1980年全国青年美展借人大会堂开大会,每张桌子搁块各省的字牌,我理所当然朝着“北京”那桌走,半道给人一把拉开,引去“中直”那一桌。我不懂,问了,原来是“中央直属”之意,意思是中央美院不归北京管。我当下反感:一帮画画的,闹这些名堂做甚?!坐不片刻,就去四川东北那几桌找穷哥们儿抽烟聊天去。
中央美院的前身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名平实。其时“北平”不是京都,“国立”亦非“中央”之意,而“专科学校”自有专科的规矩——与我在纽约做了十几年近邻的金高先生,即在1948年入北平艺专,是个民国学生,1952年毕业,可就成了光荣的中央美院毕业生。日常闲谈,她说起美院五十多年前上课的情节:
原来金高那代学生的一年级教学,竟由徐悲鸿亲自任课,戴泽辅助。徐先生教大家怎样起稿、怎样观察、怎样校正修改、怎样收束一幅画,以至纸张铅笔之类工具用法,都在讲演之列。有位学生自作主张将炭黑涂满全纸,擦出石膏的亮部,徐先生进来,一声不响,亲手抹净,然后告诫全班信守步骤,不可胡来。学生若是出外写生,回校后,徐院长常会自己跑去宿舍看他们的画儿。
二年级任课老师是谁呢:吴作人与董希文。到了三年级,好规矩大致养成,这才交由李宗津冯法祀等青年教师带学生,包括“解放区”来的画家,其中就有70年代末教过我的林岗先生。“嗨,那会儿他还是个帅小伙子!”金高笑说,“咱们班男生跟他说话,勾肩搭背呢!”
以上国立艺专的老规矩,今天听来简直天方夜谭:如今艺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谁在教?
金高的夫君王济达,雕塑家,是1953年美院附中建校第一批学生,只见得徐悲鸿先生一面:“哎呀,当时那份儿崇敬啊!咱们这些孩子在礼堂里排成一溜,挨个儿走到徐先生跟前,鞠一躬。徐先生穿件白西装,坐那儿,朝我们笑笑,点点头,过了没几天,他就死了。”
那年我才出生。二十五年后考上美院,正是“文革”后各地高校全面恢复招生的1978年,距今,也正好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前,“文革”乍歇,百事待兴,所有单位的“老领导”、“老权威”要么刚刚被“解放”,惊魂甫定,要么政治结论尚在“待批”之际,以致许多重要的官位职衔虚悬着,中央美院院长之名前面遂加一“代”字:怎么代法,不知,谁在“代”,亦不知,一说朱丹,一说古元,一说罗工柳,所以至今我也说不出上学那年“代院长”到底是谁。直到翌年年底,尘埃落定:正式出任院长的,是美术界头号大“右派”江丰先生。
记得那天全体师生大礼堂开会,文化部部长黄镇起立宣布江丰任命,众皆鼓掌。接着又宣布:“吴作人先生任名誉院长”,又是鼓掌。吴先生穿件中山装,因与隔在桌子另一端的黄镇相距甚远,特意欠身前倾,浅笑着,遥向部长,点头示意。
江丰复出一事,颇可一说。全国“右派”的正式平反是在1979年,此前,国中“左”“中”“右”势力尚在明暗间彼此较量,较量的焦点,自然是人事安排,文艺界亦不例外。一时间,院内上下忽儿窃窃议论江丰亦在复出名单之列。此事非同小可:江丰案,牵连美院五六十年代密密麻麻的人事与恩怨,建国后美院头一场重灾便自江丰获罪始,“文革”,是其后的升级与失控,中老年两代教师备受创伤。待局势和缓,我辈上学,于是有“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给我们私下里讲说美院旧账——不记得怎么一来,我所在的油画研究班便有美院60年代老大学生张颂南、老附中生孙景波等几位动议:写大字报吁请江丰复出,看看能否赢得院内老师的签名支持——此举若由教师出面,动辄触及众人的宿疾旧怨,殊不宜,若非及时呼吁,则一旦他人就任,易之晚矣。
不久,大字报果然写了出来,谁纂的文稿,写些什么,忘干净了,抄写者竟是我,抄完了摊在教室地面,墨迹湿漉漉的。是在夜里,灯亮着,有谁叫了侯一民先生进来看,他看着,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还未表态,当时仍然健在的赵域老师到了——这赵域老师怪人一个,延安资格,进城后据说满可做到师团级之类,却是硬要学油画,结果后半生给了美院了——只见他喜滋滋读了一遍,口气干脆:
“老侯啊,我看可以,就这样贴出去!”
我们于是蜂拥下楼,“就这样贴出去”,贴在老美院U字楼正厅的破墙面上。翌日,大字报剩余的纸面签满了老师的名字,凡美院声名卓著的画家,均在其中,恕不一一。
如今想来,此事真可哀可笑:“文革”后美院高层人事的更易,开其端绪者居然仍是典型的“文革”方式,其时大字报余风犹炽,正式禁止的中央规定是在一年之后。而美院这一纸签名是否果真促成江丰的复出,我也懵然不知:或许被用作上报文化部的基层“民意”?抑或高层早有打算?老江丰在美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年,连美院60年代的大学生也没见过他,新生更不了解,大家慷慨激昂要他出山,小半是年轻人欢喜起哄,多半是当年急待局势变化的普遍心态吧。

50年代初,江丰受命接管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自左至右:庞薰琹
不久后的一天,我竟和别的几位同学坐在江丰破烂的家里了。谁的主意,谁引见,说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寻到长安街西端一条沿街的胡同口,经人指点,只见老先生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活像看管自行车的居委会老头:这就是那位解放后接管美院、江丰、苏天赐夫人、林风眠、关良、苏天赐。即诅咒国画家的极左分子么?(讽刺而合理的是,不少被“错划”的党内“右派”正是顽固的左派。)这就是那位30年代“一八艺社”的左翼木刻家么?(日后在鲁迅与艺社青年的合影中,我怎么也认不出哪位是他。)他长得和我外婆一模一样,讲话轻声细气……又过了不知多久,一辆黑色轿车轻轻开进美院:老江丰大衣拐杖,慢慢下车,正式上班了。
那时美院的书记是谁呢?书记是陈沛。这样的延安派老革命现在是看不到了,说话音节顿挫,总像作报告,“文革”中自不免斗过一斗,此后照样披件呢大衣,戴顶干部帽,精神抖擞。1979年寒假将届,陈书记站在大礼堂正中,身后是黑压压刚吃完聚餐的全体师生成扇形环绕着他,环绕着大礼堂撤走座椅的空地,只听他扬声说道:
“同志们!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以毛泽东式的手势朝空中猛一挥,他提高嗓音: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语毕,喇叭一阵杂音爆响,随即是被过分放大音量的《蓝色多瑙河》,旋律猛烈,弥漫全场。大家漫入空地,磕碰着,哗笑着,拢腰搭肩,群相旋转,跳起被禁止十多年的交谊舞。
投考美院不知院长为谁,但我确知谁将是指导老师:在一份报纸的下端,1978年出现了中央美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栏目:
教授,吴作人。
副教授,侯一民、林岗、靳尚谊。
就学两年期间,我们总共只见过三次吴先生:一次由林岗老师领去拜望,只听林岗不称他院长,不叫他老师,只管叫“同志”—那时面对前辈与领导,不像今日,必职称官衔口口声声——第二次是吴先生视察我班,因不识众生,怕漏了哪位,于是同在场每个人握手浅笑,很客气。当天的教诲也仅记得“一幅画,你们要知道画,也要知道不画”。我听了,仿佛大有所悟,现在明白了,却还是做不到。
末一次便是毕业展览了,照例是对每幅画浅笑点头,轻轻说一两句评语,很慈祥,也很客气,最后在展厅前台阶上与大家合影留念,被众人簇拥着站在当中间。
尚谊老师,我预先见过的,是在1977年夏中国美术馆全军美展上。我有一画挂在那里,靳先生走过,问了名姓,爽快直接说了一番话,意思是:就这样画,造型可以,色彩还要练!
我诧异:原来北京名家这样的没有虚饰,面见晚辈即如平辈的同行。而此前此后我所见到的美院中年辈老师,几乎都是这样的不虚饰,不夸张,见人正派而坦然——虽是早经“文革”风雨,不免持重老成,却是洗不掉解放后第一代革命书生的书生气。
1974年,我曾混在江西几位画家中拜访过林岗先生逼仄的小家。是在夜里,灯光昏暗,詹建俊、赵域、林岗各自一枚小板凳围坐着,人手一册笔记本,听钱绍武朗声宣讲自己的人物素描,时或记录、大笑、诘问,在极细微的什么话题上停下来,安静地讨论。其时“文革”骚乱未止,这些人均在“靠边”状态,顶多是被审慎地起用着,他们既没有被允许讨论艺术,也没有被要求讨论艺术,而竟是这样的坐拢着,兴味盎然,端详一张张素描。我目睹这奇怪而动人的一幕,于今念及,如在昨日。
1977年我单独拜访詹建俊先生,也在夜里,他一件件取出他的画,耐心等我看完,小心放回去——这慷慨与耐心似乎因他的身高显得格外漫长——他所谓的家只有一间屋子,不到二十平方米吧,画框必须严密地堆叠、抽出、归存。
那时美院的名家根本没有画室。林岗老师长叹:我们在美院占的地方,也就是油画系教师信箱的那一格小格子。
初访杜键老师,他正画着年前死去的毛、周、朱。握过手,他侧身让我看画,平静地说:“哪里画得不舒服,你就说。”我居然真的说了什么,而他居然沉吟思忖,与面前这二十出头的小子认真地讨论。
这都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他们的平均年龄四十出头,早已名满全国,个个没有职称。“文革”抹杀一切职称,而似乎没有人在乎这些:我看不出这几位老师在乎,我们,散在地方的知青画家盼望拜见久仰大名的北京画家,更是谁也不想到是去拜见一位教授—直到上学后我才知道,侯、林、靳三位甚至连副教授也不是,只为开科招收研究生,美院才向教育部申请了非正式的临时职称。
是在我们考试的末一日,此前从未见过的侯一民先生走进考场,面对一群陌生人,茫然而稳重地站定,仪表堂堂。在我们南方人看来,他像大部分中央美院的中年教师那样,既非教授,也不是官,却是有威仪、有官相。我被介绍给他,他于是转身看住我,缓缓地开腔:
年轻人,你们可没给“文革”耽误啊。
那年侯先生四十六七岁,俨然尊长——今天,我已倏然到得“天命”之年,面见二十多岁的各地考生,真想大叫:
年轻人,你们全给考试耽误啦!
开学那天,老教授出现了:蒋兆和、李可染、艾中信、罗工柳、戴泽、刘开渠、王合内、许幸之……差不多每位老人的花白头发都向后梳着。我格外心仪的董希文与王式廓不在其中,他们同于1973年郁病而死。我远远端详这群劫后余生的老画家依次走进会场,不知道他们谁是谁,班中老生随即悄悄指点。未经指点便即吸引我注意的是位漂亮的老头:白胡子、木手杖,目光炯炯,环视全场——叶浅予先生。多年后在哈佛与巫鸿夜谈,说起“文革”初年附中学生痛殴叶浅予,巫鸿在场,惊怵不堪,以至奔回宿舍以拳击墙,不久,巫鸿也被打成“反革命”——我至今记得这群老教授进场的一瞬,全体流露恍然“复出”的神情:十年动乱,他们终于重回讲坛,以被尊敬的方式面见后生,他们轻微地欣悦而亢奋,显然与开学仪式暌违已久,同时,又分明流露轻微的不适,或可解读为隐秘的心有余悸,满座青年,恐怕使他们不由得忆及在同一场所被晚生批斗的往事?
那是令人动容的瞬间,介于辛酸与侥幸之间。我随即留意到老教授们另有一种集体气质——真是好不难说,并非因为名声与年龄——使他们与中年教师截然不同。那是什么气质?如今我有了简单的结论:他们全是民国人,和他们的老院长一样,只是比徐先生命更长。
那次会见的详细,统忘记了。之后一年,另两位50年代便即出局的美院才子调回母校。一是朱乃正,放逐青海二十年,一是袁运生,发配东北十七年,他们都是“右派”分子,当年被扫地出门时,才不到二十岁。他们却有着我久已熟悉而与美院老师相异的另一种气质:是“右派”的,因我父母均为“右派”;也是江湖的,因我是“文革”江湖的晚生。运生老师其时才画完机场壁画,我们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头一次看到中国人画这样的画,那天他探头进门寻找孙景波,头发蓬乱直竖,刚从云南写生回来。乃正师与景波相熟,到美院那天在我俩合住的宿舍长谈竟夜,上海人,中低音,与之对几句沪语,一时仿佛忘年交。临睡,我就隔壁同学上铺,乃正师在我铺上欣然留卧,翌日告诉我,那是他被迫离开二十年后,头一次走进校尉胡同五号母校大门。
忽一日,有位消瘦的老者在U字楼走廊向教室内张望,如那时所有复出者,面目沧桑而兴奋莫名:是冯法祀先生。那时我不知道谁是冯法祀。我们随即被叫到隔壁教室:一幅大画横在那里,调子灰暗,气氛肃杀,是冯先生50年代创作的《刘胡兰》,满篇尘土,内框严重倾斜——上个月我在中国美术馆装修完毕的新展二层又见到这幅大画,立时想起初见冯先生——“你看这里!”他拉着我直指画面中铡刀下的血迹,“我专门杀了一只鸡,对着鸡血当场写生啊!”
这位刘胡兰的歌颂者也是老“右派”,那天他获准调离流放二十年的戏剧学院,回到他早年执教的学院。他与艾中信先生40年代即追随徐先生左右,不久,就在系办公室听他俩争先恐后慷慨激昂讲说徐先生旧事。
徐先生走得是忒过早了。他要是亲睹弟子们日后的际遇,还会以他“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座右铭相予教诲么?
“文革”时期的上海,我有位英俊画友,见面看画,神色鄙夷:
“你不懂色彩。色彩,要浓郁,你懂吗?”他漂亮而严厉地盯着我,教我“浓郁”二字怎样写法。再就是关于我的“笔触”,他也鄙夷得有道理:“要拙!拙,你懂吗?”
我们背地里叫他“浓郁”。“浓郁”传达了他的老师的结论:上海人基本上不懂油画。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年跟随的老师,是一位分配到上海的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生。
在我学画的年代,一位出身中央美院的画家必是被外地同行们随时提醒着他的出身,远远地敬畏着,奈何不得——不因这家伙画得怎样,也不因他姓甚名谁,而仅仅因为他的出身:
“中央美术学院”。
我未曾想到的是,不但外地,即便到了外国,出身中央美院的家伙仍竟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身份,仿佛党员。有几回纽约穷哥们儿聚会,电话通知,对方竟是卑怯:“你们中央美院同学聚,不合适吧?!”日后我与一两位海外校友终至疏远,便实在是看不起他们吃饭走路、见面握手的一脸“中央美院”相。
画友“浓郁”后来倒是并没投考美院,“文革”收束,他娶了拉丁女子,去了意大利国了。
今日的中央美院恐怕应该改称“北方美术学院”:上海人在考生中早已绝了迹,江南人也稀罕得很。如今中央美院的考生“大户”是哪儿呢:东北、山东、河南、河北……怎么会呢?我离开太久,不得知。在我上学那两年,各系同学的来路广得多了,单是我这一届便有五六位上海人,近二十位江南人。而中央美院建院初期的青年教师中,据尚谊老师给我计算,全院只有三位真正的北京人:“我、詹大、侯一民。”上辈师尊,更是绝少北方人:徐悲鸿苏南人,吴作人皖南人,古元、李桦、罗工柳广东人,董希文绍兴人,江丰本贯浦东,死后遗嘱是骨灰撒在黄浦江。
说来这也是民国的渊源了。我总以为旧上海其实等于纽约,人往那里跑:小小美术圈,除去日后留在南方的老画家,就我所知,或暂或久涉足上海的中央美院老前辈便有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叶浅予、吴作人、董希文、许幸之……而美院两代中老年教师,倒反不倨傲,不轻佻,大抵平实自尊,这些“美院旧部”说起“美院旧事”,还对美院历年的身世际遇,摇头叹息,虽则叹息之中,还是对美院的牵挂与惜爱。
话说得远了,还得说回来。
1998年,美院号称建院八十年,解放前那段不算,此后五十多年的毕业生论百上千,我所熟识的,只能是78届本科班与硕士班老同学。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之中,有昂然入仕的,有翩然出家的,有成功成名的,有默默单干的,有远在域外的,自也有告老退休的——数说老同学,唯在老同学群集之时才有意思,此处叙述,别人怕未必有兴味听,而所有艺术学生的生活大抵一样。在我的记忆中,老同学们无非是在美院破食堂欢声哗语排队买饭,在U字楼入夜的灯光下忽然窜到旁系教室寻衅笑闹,或中夜翻墙走去吉祥剧院吃水饺,吃完,自亦翻墙回来。我记得宿舍过道警告关灯的铃声忒过惊心,某夜抄条木棍,上前一挥,将那铁铃给砸哑了。
此后八九十年代入学的学生,多有豪杰,譬如留校的刘小东,下海的方力钧等,都是我佩服的才子。我虽是讨厌一切因名校背景而高视阔步的活傻×,但美术界看来看去,有时倒也暗中佩服中央美院——近年前卫圈出格出众的恶作剧,稍一打听,十之五六是在美院泡过一泡,而后在外聚众滋事。譬如动辄脱光了弄作品的张洹,河南人,原在美院进修班混了两年;宋庄有位女子偷拍宾馆群妓,那录像直见性命,问起来,也是美院的晚生;我还得认识一位小女生,毕业前好好画着规规矩矩的油画,来年就献身“行为艺术”,足足熬了好几斤人油……数十年来,论人才辈出、论活力外泻,中央美院确乎是一肇事的渊薮,成才的窝点。而其中最有种的老叛徒,即“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生,名叫栗宪庭。
类似的坏名单开下去,恐怕真不少:我所以暗中佩服中央美院,不为混迹校内的骄子,而宁是野在校外的逆种,他们是美院“正传”的“异类”,却反证了中央美院之所以是中央美院——远溯五十多年前,接管美院的军代表艾青、出掌美院的江丰,便是民国年间理当通缉远避延安的老牌文艺逆子,侯一民李天祥二位尚在十八九岁年纪,明里是学生会头目,暗中是北平市地下党员,哪里肯安分守己。再上溯七八十年前的徐悲鸿,意气激昂,挑战祖制,私奔东瀛,远赴巴黎,事事争风气之先,岂不更是“五四”一代艺术家老牌逆子中的头牌?
美院是大气的。毁誉不论,有一个美院摆在那里,人会到里面去,又会从里面走出来:进去出来,出来进去,同是美院的学生,日后可以是不同的艺术家,走不同的路,做不同的人。
而时代曾经欺负美院,美院也不免欺负学生:在我毕业那年,有一天照例在U字楼长长的走廊走,老校友朱乃正远远招手:“过来,过来,有件东西给你看。”
那是一枚陈旧的毕业证书,证书首页端端正正的黑白照片上,是十八九岁一脸稚气的朱乃正:作为“右倾”的惩罚,这份毕业证书扣留不发二十年,那天早晨,校方刚刚把证书发还给行将五十岁的老同学。
今天,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惭愧,眼下我正在艺术学院混这份莫名其妙煞有介事的差。每年我得重复填写同样的表格,重申我是男性、多大年龄、在什么单位、是什么职称……但我拒绝填写所谓“科研项目”这一栏。在当今所谓“学科建设”叫嚣“专业划分”的闹剧中,“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讽刺么?不,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不记得在学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上课头天,我们围着靳先生团团坐好,他就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靳先生忽然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
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侯先生讲课扼要简单:我调出一块军装的青灰色,得意了,等他夸,侯先生看看军装,看看画,笑眯眯地说:“你再调,你还得调,你得调到说不出那是什么颜色,才是好颜色!”画鞋子,他走过站一站:“记住,要画脚,不要画鞋子。”然后笑眯眯走掉了。
有一天,林岗老师忽然叫我出教室:“丹青啊,就像你当知青那会儿大胆画,你怕什么呢!”他在过道的暗影里很殷切地对我说,急得眉毛皱起来。
是的,在学两年,我能记得的教诲就是这么几句话。艺术教学是什么呢,艺术教学就是几句话——虽是几句话,还看谁在说。
徐先生的教导我辈是听不成了。那年靳先生给我学过徐先生的江南口音:“要画一万张素描。”如今全国美院历届学生的素描怕有百万千万张吧,黑黢黢,脏兮兮,面面俱到而面面俱不到,没有感觉,没有斯文,没有灵性,没有人味道,那是绘画的绝路呀——我真想听听徐先生怎么说。
奇怪,现而今,这样的素描还数中央美院考前班孩子画得顶顶好,前时我在校尉胡同一所地下室的考前班墙上领教好几张“中央美院”派的素描范本,和文艺复兴素描大统毫无关系,和徐悲鸿手订的素描小传也毫无关系,可也叫我真佩服:在我混饭吃的学院,怕是四年级本科生也画不出来。
如今素描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考试收钱;教学也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众人的饭碗——艺术学院,现在“学院”重要,“艺术”次要,很次要。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艺术是得跟人走,人在艺术在,人在教学在。昔年上海、杭州、北平三家艺专不相让、不买账,还真有点学派的模样。据江南老牌艺术学生说,上海艺专讲的是米开朗琪罗、凡·高、毕加索,杭州艺专则言必称拉斐尔、塞尚、马蒂斯。北边呢,徐先生临过伦勃朗,推崇法国的大卫,佩服俄国的列宾,赞赏延安的古元,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画的是“田横五百士”,素描人体亮出来,品相端正,至今也还没人画得过。
再譬如中央美院建立三所工作室:吴先生果然有比利时一套;罗先生果然有苏联一套;董先生被说成“油画民族化”一面旗,下笔有敦煌的遗韵,青瓷的风采,可他弄的毕竟是油画,解放前在越南转手学过一点法国的意思……总之,三家工作室,一路是一路,一家是一家,直到“文革”全作废。此后作风,靳先生说的是实话:到他这一代,全是苏联那一套。
苏联那一套也实在有一套,早先苏联的革命画,我们至今也还画不周正,学不像。可我近时看见八九十年代梅里尼柯夫主掌的列宾美术学院,面目全非,只剩一块牌子算是老字号——说开去,如今的北大哪里是蔡元培的北大?如今的清华哪里是梅贻琦的清华?
然而还是叫北大,还是叫清华。
不足怪。中央美院早已不是徐悲鸿的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早已不在帅府园——不足怪:人活一世,脱胎换骨,何况一所偌大的学院。中央美院五十多年来怎样脱胎换骨,怎样物是人非,我仅待了三年,没有资格说,但见此后人才英才怪才庸才一届一届冒出来,足见美院活力盛,美院性命长。有句话倒是说出大实情:人问清华领导,清华教学有什么好方子?回答是:因为考生好。好考生冲着老牌子,一年一年自会来。这道理移来中央美院说,也是一回事。
只是当代中国,艺术算老几?七年前中央美院被连哄带逼迁出帅府园,暂居酒仙桥,落户花家地,似乎又有希望在……中国教育有“希望工程”一词,真是会说话:“工程”怎样且不管,“希望”总可以不断不断“希望”下去吧。
巴黎美术学院仍在巴黎旧址。列宾美术学院仍在彼得堡旧址—在北京市中心,中央美院总算被彻底拔除,扫荡干净了。今岁,U字楼、留学生楼、南楼陈列馆将陆续夷为平地——狠好,狠好,免得走过看见,徒然念旧。全中国今已面目全非,美院算什么?美院迁移,说破了,事属公然的驱赶,批块野地,拨几亿钱,不是打发,不是安抚,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帅府园旧址不足惜,只要“中央美院”牌子在,仍然可骄傲。一部“中央美院史”是一部“骄傲史”,在一代代师生继往开来的枉自骄傲中,别忘了早先“文革”的屈辱,别忘了近前这笔深刻的轻蔑。
2003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