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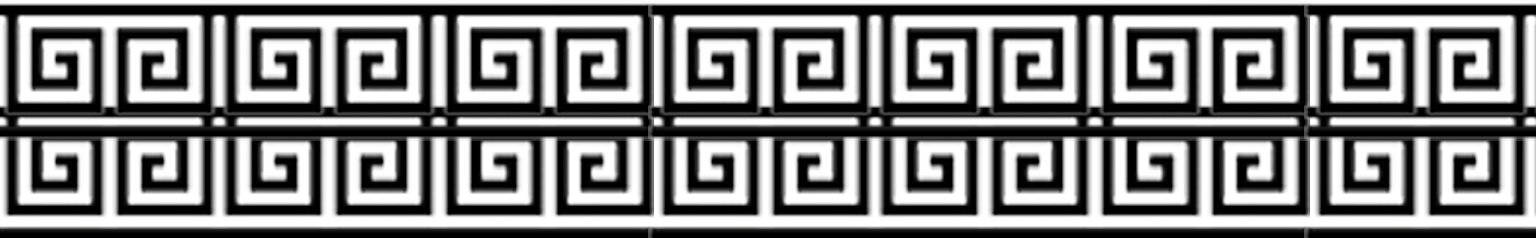

2003年上海批评家春季沙龙座谈会 “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书面发言
这次会议的议题是有问题的。但这问题很有意思——
“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文艺批评”不是一回事:其“所指”,与字面大异其趣。
“批评”,即英文“criticism”,是绕道日本翻译过来的,与“自我批评”连成一句,成了国产货,意思完全不一样——说轻了,可以称之为“泛批评”,是五十多年来人际关系中的“软性策略”,大致起到让步、致歉、作姿态、圆场子、息事宁人等等效用。说重了,则应称之为“政治仪式”,是组织生活内部的“硬性规定”,是各级同志或被迫、或主动、或对内、或对外的表态方式,起到告饶、过关、退一步、下台阶、以便自保等等效用。
“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传起于延安时期,很前卫,很管用,它不是真的“批评”,而是整合队伍、便于掌控的辅助手段。到了和平年代,“批评与自我批评”、“敌我与内部矛盾”成为我国泛政治生活中两大“武器”。邓小平同志著名的“三起三落”,都是靠高瞻远瞩的“自我批评”才能再起,才能复出。小小文艺界,所有老权威均曾一再作过“自我批评”,或升级为敌我矛盾,“低头认罪”,或降级为内部矛盾,“从新做人”。
那么,谁来判别您的错误属于哪一种“矛盾”呢,还是权力。
要之,在现代中国,“批评”是“权力”与“正确”的代名词;“自我批评”则是“检讨”与“认输”的代名词。通俗地说,由“批评”一方使用,即“我是对的,你是错的”,由“自我批评”的一方使用,即“你是对的,我是错的”。
最微妙的一层是:如果权力一方主动“自我批评”,意即“我错了,但我作了自我批评,因此我仍然正确”。
美国流行的“政治上正确”,倒是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神似。只是中美两国文化渊源政治制度不同,在“权力”与“正确”面前,两国国民采取的态度与方式,有所不同。在中国,“批评与自我批评”长期扭曲批评,封锁批评:在提倡这句话的漫长年代,正是中国在任何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批评、没有批评的年代。
改革开放二十年,此一名词在世俗生活中大幅度失传、失效了,没人当真,没人惧怕。但它和五十年来的政治词汇一样,内化为我们的日常用语和思维习惯,还给编入电脑字库。只是我们的批评家同志会沿用这句话,居然丝毫不觉有异,实在有点令人惊讶,我很自然想起从小听惯的社论台词:
“同志们!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与会代表作了充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一致的认识……”等等、等等。
深一层分析,“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儒文化的转世投胎。一面,儒文化从来代表“权力”与“正确”;另一面,儒文化主张“仁”、主张“和为贵”、主张“中庸之道”。儒文化将家事与国事等同,落实为人际关系,国事家事出了问题,儒文化主张给你面子,给你转圜的余地,给你表态的机会,相对于西方古典极权,儒文化比较阴柔而智慧、巧妙而堂皇。中国人精擅自嘲、自责、自贬,都是人际关系的护身法。圣主犯了错,则给臣民下“罪己诏”。到了20世纪,这一切乃“古为今用”,翻译成漂亮的现代语,即“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次会议定名为“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出于什么原因?发生了什么事?谁要来批评我们?我不清楚。
在座人数很多,是否代表国内批评界整体?还是其中某一部分?我也不清楚。
但从议题中我看出一个意思。这意思也许诸位并不自觉,但分明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权力——没有权力,没有权力意识,一个群体不会公开说:让我们来批评与自我批评吧。
话说今天,我们许多艺术家批评家的业务身份与行政身份,已经合一,当了官。整个文艺圈大大小小的行政领导,甚至个别党政领导,都是原来的职业艺术家或批评家。
其中,批评家的权力身份最为特殊:他可能没有行政职务,但有批评权,假如他有行政地位,不消说,权力就更大。这类身份的批评家,即新兴的展览策划人。
近年,策划人更具有国内国际的双重权力,构成艺术界一大新兴行业,没有他们,当代艺术的大好形势不可设想。所以国外机构、国内官方都离不开策划人。因此,今日一位艺术家遇见一位策划人,相当于二十年前遇见一位干部,一位领导。
总之,虽然我们的文艺界出现可疑的多元局面,也不论诸位的批评思想如何分歧、有无官衔职位,我们的行政所属仍然是单一结构,使众人得以从中分享权力。直白地说,我们都拿着国家的俸禄,我们所属的学院、画院、美术馆、美协、研究院,全是国家的,官办的,统统归文化部、宣传部领导,这两个部,当然,归中央领导——犹如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环环围绕着“中央”。
变化只有一项:过去,官方对我们意味着他者,今天,我们就是官方。
或曰:近二十年中国出现了大批个体艺术家。是的,但他们在权力图表中的位置是暧昧的,不确定的,不奏效的,犹如每一环公路之间的地段,随时会被拆迁、征用、重组,面目全非。
近年一系列新的施政方针,为这一单元结构设计了新的文化形态——非官方艺术被清理筛选后,先后正名,忽然被整合到“行政管理”与“文化产业”内。如此,在中国,一大群艺术家批评家出身的行政官员正在以新的“政治上正确”替换旧的“政治上正确”,有效塑造新的官方艺术。整个中国美术界目前所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即再次确认权力,重组权力。
是的,今日发生的一切是多年前不可想像的,大家简直忘了自己的背景和来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胡说八道:我回国后看见,美术界的官方性质丝毫没变,不但没变,而且我们的权力比二十年前大得太多了。
我忽然明白:中国现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中国当今美术界,是行政美术界。
我不是在描述可悲的图景。相反,我乐于看见今天的权力景观。在中国,艺术家与批评家唯有获得官方权力,才能真正参与国家的转型,推动文化的进步。这种新的权力结构有效弥合了官方与在野艺术愚蠢的分裂与对立,无可估量地拓展了当代艺术的可能性,它本身就在塑造一个更聪明、更理性、更现实,因而更具包容性的官方。
问题是,在这新的官方文艺形态中,批评能做什么?它的对象是什么?它的后果又是什么?
“批评”大约分两种:
一是“权力的批评”,主语是“权力”,自上而下,代表正确。
一是“批评的权力”,主语是“批评”,不附属权力实体,不标榜正确,它的前提,是与批评对象始终保持距离。
在上述权力结构中,今日批评家的问题不在批评,而在如何面对批评与权力之间天然的矛盾。
除了个别单干户或私人机构的雇员,我们的权力背景是一样的,学术背景更为单一:当代中国艺术家批评家都是广义上的同学、同事、校友或上下级关系,大家都是自己人,一家人。这种关系可能因人因事发生局部摩擦,但在整体上,这种集体关系同另外两个更大的背景,有效软化、无形制约着艺术批评:
一是文化背景,我们生活在一个历来重视人际关系的国家。
二是政治背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效管理言论空间的国家。
如此,在中国,即便是激烈的批评,其实都相当温和,相当客气,批评者均长期习惯于有所避讳而严格自律的表述方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过去不可能,现在仍然不可能,因为批评言论必然触及大家共同的三大背景:
行政格局,人际关系,政治国情。
改革开放以来,批评与批评家的处境大有改善。可是权力关系与人际关系乃是批评的天敌——当批评家既是批评的主体,又是权力的主体时,这种奇怪的身份合一,必然而自动地为难批评家,就像家长要面对众多族人与亲戚一样。
好在“批评”的涵义之一即“评论”,评论的涵义之一即“赞美”,赞美又可衍生为“宣传”、“粉饰”、“包装”之意,自然而然地,中国的批评乃成为一种大规模的“装饰性文本”。
装饰性文本的功能,又落实为筛选艺术家。批评家之难以出言批评,即艺术家并不渴望真的批评——在单元权力结构中,艺术家怎会渴望真的批评呢?他渴望的是尽快被列入“装饰性”名单。
诸位应该清楚这份名单有多重要。我猜,今日批评家必定被许多难缠的艺术家所困扰。另一极端负面的例子是,我听说,一位著名的当代艺术策划人约一位年轻女画家去酒吧,被婉言拒绝,他于是在电话中问道:你还想不想在美术界混?
此事无涉批评,但有涉权力——这位批评家说出了一个朴素简单的事实,那就是:
中国只有一个美术界。
那位女画家的命运微不足道,重要的是批评的命运:“批评的权力”是双向的,其命运是彼此批评;“权力的批评”是单向的,其命运是很难遭遇权力之外的批评。于是,很自然地,出于历来的规矩,我们的批评家想起了“自我批评”这句话。
我愿强调: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批评必然体现为权力。我们所把握的究竟是“批评的权力”还是“权力的批评”?如果是后者,那么,“自我批评”乃是逻辑的结果。
我愿强调:我相信诸位“自我批评”的诚意——在这唯一的美术界之外,有哪个势力相当的群体或个人会批评我们,并果然奏效吗?
但“自我批评”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不是真的批评。
美国没有文化部,没有美协。艺术家全部个体,所谓“美术界”由画廊构成,推出艺术家,批评家批评,佼佼者进入美术馆。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设有文化部,但大多附属外交部,作对外文化交流,不管艺术家。在西方,艺术活动发生严重问题,社会管,法律管,政府不管。政府插手,宪法会管,而政府经常败诉。
80年代,西方发生策划人及其制度,那是美术馆试图主动介入当代艺术的行政举措,设计展览的主题、焦点、针对性,此是常识,不细说。策划人的钱哪里来?美术馆、基金会、大企业。这些机构几乎全属私人——以纽约为例:大都会、现代馆、古根海姆、惠特尼四大美术馆,全部私营——批评家怎么活?受雇于学院、报纸、杂志,包括画廊,而所有这些机构,几乎全是私人的,国家不管。
要之:西方没有官方美术界。所谓多元,在西方,即意味着策划人遭遇策划人,权力遭遇权力,批评遭遇批评。
大家知道,所谓西方的民主,即权力分散。批评的权力,于是也分散在各种批评家手里,发出各种批评。我在纽约遭遇九届惠特尼双年展,每届更换策划人,而每届双年展都被各大报纸、杂志激烈批评,然后是没完没了的反批评。
因此,我不能想像西方批评家坐在一起“自我批评”。因为一旦吃了批评这碗饭,他就准备,而且实际上就被置于持续的批评之中,这种被批评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中国批评界同行的想像与承受力。例如60年代早已名满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大批评家阿多诺,即曾在大学讲坛被学生夺了话筒,轰下台去。在西方,重要的哲学、美学与批评文本,几乎都有来自反面的对立的批评文本——有时是大部头专著——所有我们熟悉的西方现代思想家与批评家,终其一生,以至身后,均面临来自同行的质疑、批评,甚至攻击。
中国批评家不可能被置于这种批评的原生态之中。我们的身份与地位非常稳妥,其差异,只是行政地位或职称级别——二者其实是一回事——我相信多数批评家人品正派,但是大家知道:在权力结构中,人品相当次要,重要的是,在中国,批评家与艺术家真正的关系,已被长期置于领导与被领导、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或曰:西方不也如此?非也。西方艺术家与策划人之间有一庞大的中介,即数以千计的画廊。画廊——亦即市场——乃是西方艺术的生态与温床,艺术家从中出土茁壮,尔后,由批评家或策划人采集奇花异草,栽培标榜。例如被称为“教父”的纽约大画商李奥·卡斯岱里单独发现、豢养,并推动了普普艺术第一代画家。玛丽·布恩则单独推出了新表现主义第一代画家。卓越的画廊主人是真正的伯乐与弄潮儿,是美术馆与策划人背后真正的影响者,甚至操纵者,他们是艺术家真正追慕、巴结、崇敬而惧怕的人。
中国不然。中国有限的画廊与暧昧的市场,是庞大官方美术界的“外围装饰”,不可能向高层——不伦不类地,我们称之为“学术界”——输送精英,中国所有值得一提的画廊全都依据官方名单,亦步亦趋,选择精英。在我们的精英名单中,几乎没有一位重要的艺术家毫无官方背景,纯然出自民间与画廊。
要之,西方的模式是:艺术家—画廊—策划人(批评家)—美术馆。
相反,中国的模式是:艺术家—策划人(批评家)—美术馆—画廊。
或曰:目前在国际上成功的中国前卫艺术家难道先找画廊再出头吗?非也,因为画廊文化远未成熟,官方艺术无比庞大,西方人只有两种渠道接近我们:一是官方名单,一是由本土策划人引领,直接将车子开进圆明园、宋庄、苏州河沿岸,或任何隐蔽着前卫艺术家的角落。
在这样一种特殊情境中,中国批评家与策划人的权力于是尤为凸显、无可替代:对外,他是高级的“文化掮客”,越过并总揽画廊的功能,是中外文化权力的中介者;对内,他兼具选择权、批评权、策划权、行政权,调动官方资源,提供官方舞台。于是,西方人必须借助中国策划人选择艺术家,这是我们单元权力结构中的“对外功能”;对内部分,则密密麻麻的艺术家好比有待圈养认领的羊群,策划人,是使他们得以靠近权力、被纳入权力的人。
我手边有一册8月号《美术观察》,专题是“批评的困惑和批评家的处境”。其中王林同志提出:为了批评的独立,我们不能依附体制。
问题是:我们怎可能不依附体制?我们自己根本就是体制,不然本次会议岂能召开,近年所有活动岂能发生。真正的灾难是:如果摆脱体制,弄得像西方那样,大家难道散伙、下岗、单干?
我所谓的“权力”,不是说谁在欺负谁,谁在受欺负。说破了,所谓体制,就是饭碗。四十多年前毛主席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体制警告大家,并成功地使大家随时随地自我警告:“千万不要忘记饭碗。”
五十多年来,我不记得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所有文艺家如此珍惜权力: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迅速发育时,文艺界、教育界、知识界顶要紧的根本不是艺术,不是教育,不是知识,而是饭碗—我们成功了:国家学院与官方美术界从来没有如此庞大、铺张、奢侈,我们此刻就坐在四星级宾馆里——我们究竟要批评什么?我们付得起批评的代价吗?

栗宪庭。选自人物访谈集《纯粹》。
有人付出代价。栗宪庭同志就是一例。他脱离公职,以匹夫之勇划分出一拨非官方美术群体,并自任早期的策划人;不消说,他必定遭遇官方批评界同行明里暗里的批评与排斥——作为“批评的权力”,此乃“咎由自取”——但是他成功地发出了声音,同时,在今天看来,他是个失败者。为什么呢?很简单:他冒犯了行政格局与人际关系,破坏了批评界整体性的装饰功能,自外于权力的核心。在这样一个集体文化中,个人的批评,过去无法发出,现在无法生效,形势比人强:最近几年的新形势,证明他不代表中国式的“先进文化”,不代表“与时俱进”的“时”。
但我仍然不时听见批评的声音:过去,李小山曾经单独挑战中国画,彭德曾经痛骂美术界。今天,有几位我不记得名姓的批评家,或公开宣称成都双年展毫无意义,或痛陈当前文化状况的腐败或堕落——想必他们暂时没有饭碗之虞——在这类与西方相比属于小吵小闹的声音中,我看见,大家没有忘记“批评的权力”。
我们需要权力,我们又需要批评。在这两难之外,我们手中必须端着饭碗——怎么办?
我给大家说件小事情:
七十多年前,有位文艺青年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愤怒的信,痛批鲁迅提倡世界语的主张乃是汉奸罪行,要他给全国读者下“罪己诏”。
鲁迅答道:我不是皇帝,何来“罪己诏”一说?
鲁迅也不是官,更不自称“作家”、“批评家”、“知识分子”,他只是自己一个人——我们可以从鲁迅批评与批评鲁迅,来看看“权力与饭碗”、“批评与个人”的关系:
近十来年,国中出全了鲁迅在世时左中右老中青各色人等痛骂他的文章,是老先生回骂文字的数十倍——请注意:重要的不是这批人互相痛骂,而是他们除了批评的权力外,没有别的权力。以上这位青年虽则常识混乱,但他和当时批评鲁迅的人,如梁实秋、高长虹、四条汉子之类,全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们根本不怕鲁迅,因为鲁迅不是文化部部长、作协主席,只是一个老头子。他们彼此的关系,就像现在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艺人,谁也不怕谁。此其一。
鲁迅先生的文章再激烈,再孤傲,但没有丝毫权力感。他有过的“职称”远不及在座诸位批评家:他任绍兴中学校长一年,是个乡镇文人;短期任职教育部“佥事”,近乎科员;在京期间不是“正高级”教授,薪水常欠;他有作家的盛誉,但民国没有“作协”;他短期入伙当时的“反动”组织“左联”,没有俸禄,被通缉,随时躲藏——到了晚岁,鲁迅的实际身份是旧上海弄堂里一介居民。此其二。
在鲁迅的文字中详细记录着谋饭碗的过程。80年代经济学家千家驹曾纂文透露:鲁迅至死领着蔡元培嘱咐教育部拨予他的高额薪水。但此事一不说明鲁迅利用政权,二说明当时的政权尚且容得了鲁迅,三说明当时的教育部懂得文化。于是鲁迅照样领钱,照样批评。此其三。
鲁迅过世十三年,他的声名地位被高度权力化,弄得谁都不敢反对他,简直应了西方的古谚:伟大的文学家是无冕皇帝,而他的敌友也被权力化,或整人,或被整,一律噤声,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敌我与内部矛盾”的边缘内外挣扎起落。此其四。
鲁迅说:孔夫子是权势者捧起来的,结果他身后也被权势者捧起来。鲁迅骂孔夫子,其实骂的是权势。今人如王朔骂鲁迅,不知他是否注意到:他和鲁迅是同一身份的人,都是单干户,都没有单位、没有职称、没有官衔。此其五。
王朔开骂,已是批评之声再度蜂起的近二十年。文坛艺坛大大小小的历史名人,几乎都有人撩拨,为什么呢,因为已故文艺家背后的权势相对减弱,在世的文艺人则谁也不服谁。自然,人们比较地敢于咒骂死去的人,然而,在近二十年人们再度贬抑鲁迅的过程中,他的幽灵从身后的光环中走出,回到他在30年代的孤立状态,不论我们敬重他还是讨厌他,他不再被“权力”与“正确”所左右,他再度变成“单独一个人”。此其六。
鲁迅不能回骂了。但他言论俱在,继续行使着批评的权力:前年一份杂志封面印着一句话:“我们今天骂的,鲁迅全都骂过了。”此其七。
或曰:批评者不会犯错?不必知错?不用反省么?非也。批评的对错是非,均已在批评文本中。深刻的批评,本身即是反省。而读者、时代、历史自会判断,批评者只管一件事,就是批评。
批评永在语境之中,批评只有在“被批评”、“再批评”的过程中循环,方才成其为批评——“自我批评”中断了这一过程,亵渎了真的批评,就此而言,“自我批评”是伪批评——真的批评是什么呢?不过是说话,不过是“百家争鸣”。所谓“百家”,拆开来算,不过是一个一个“个人”,一如“百花齐放”,不过一朵一朵而已。
据学者说,真正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只有两回,一是两千五百年多年前的先秦时代,一是上世纪五四运动前后。最近据周海婴回忆录及黄宗英等人在《南方周末》上证实:鲁迅先生要是不死,毛泽东说得很坦率:要么不作声,要么蹲班房。
座位排在鲁迅身后的郭沫若、沈雁冰,臣伏于“权力的批评”,交出“批评的权力”,作了多次情辞恳切的自我批评,遂得存身。倔强如陈寅恪,选择沉默,但拒绝自我批评。而毛主席了不起,他没说要鲁迅先生“自我批评”——他懂得鲁迅,懂得什么叫作“批评的权力”。
至于真正的批评必要非凡的人格、学养、境界、文采,也是常识,不消多说。那位要鲁迅下“罪己诏”的哥们儿,鲁迅轻轻一拨,岂是对手,所以鲁迅在世的大寂寞,不是没的批评,而是没的对手。西方的批评,譬如尼采痛批瓦格纳,托尔斯泰痛批尼采,普鲁斯特驳圣伯夫书,萨特与加缪绝交书等等,两边都是人物、都是好汉,两边都是单枪匹马,背后没有权力,他们唯一的权力,就是一枝笔。
当个单枪匹马的批评家,实在不容易,他先得解决饭碗问题。这一层,鲁迅晚年也早有大实话说在前面。面对不甘平顺的青年,他的劝告既不是革命,也不是读书,老先生提高嗓门说:顶要紧的事,是银行里要有一点钱。

左起:郭沫若、许广平、冯乃超、田汉。郭、冯、田三位同志均曾与鲁迅交手打笔仗,彼此使用“批评的权力”,谁也不怕谁。待老先生去世,又捧着花朵围拢到墓碑前,还请来许广平。时在1948年。
话说得有点远了:忽儿去和西方比,忽儿去和先秦时代、五四运动比,未免太乖张。史论专业出身的批评家应该知道,文艺从来服务于权力。一部艺术史,不过是权力的历史。所以西方史论专业开了一门新课,名曰“艺术赞助史”,给你细算一笔历史的经济账:千百年来,到底是谁养着艺术和艺术家?
在西方,追求艺术自由言论自由是启蒙运动后的事,不过两百多年;获得言论与批评的自由,不过上百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不过二十年,事情必得一件一件来,只是今天要来谈批评,话要说说清楚而已。
但国中的艺术家似乎又将批评的要求放得太低、看得太重:花钱买一篇装饰性批评,志满意得,拿去评职称、谈价钱;遭遇几句吞吞吐吐的“商榷”,恼怒惶急,以为丢面子、跌身份。我是“文革”过来人。“文革”期间,艺术家无权无利,见面全是谈艺术,今天的艺术家有权又有利,见面无心谈艺术。艺术家尚且不谈艺术,批评家谈什么批评呢?——在我们的权力文化与利益结构中,我只能说,有怎样的艺术家就有怎样的批评家,有怎样的批评家,自亦有怎样的艺术家——这不是谁的错,这是眼下的现实。
所以我以上的说法也不是“批评”,仅只陈述我们置身于怎样的权力结构中。最近北大的改革,外界最平实的说法是:整个体制不变,结构不变,北大能否单独改革?凭什么单独改革?批评的情境一模一样:真要弄批评的哥们儿,还得慢慢来。
或曰:中国比以前进步太多、自由太多了。是的,没错,但这种“自由”于我们是属“庆幸”,非属“当然”,而获利的阶层可以这么说,生意人可以这么说,如果艺术家愿意,也可以这么说,唯独批评家不该这么说——批评之所以是批评,就因为真的批评总是不满的,怀疑的,不合作的。
当批评与权力合一,批评势必成为装饰;当批评成为装饰,意味着我们的艺术乃是对应于装饰之物:事已至此,自然而然地,批评家与艺术家双方势必或则迎合,迎合不洽者,于是彼此不满;或则交易,而交易不洽者,乃彼此诅咒。此或王林同志为何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了批评的独立,批评家不要依附艺术家——我也听到艺术家对批评家怨怼之辞——可是批评家若离了艺术家,他批评什么呢?我想,王林同志所厌弃者,其实是急功近利的艺术家;艺术家所厌弃者,也是急功近利的批评家。总之,在我们的单元权力结构中,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一定是扭曲的,功利的,不真挚,也不真实,因遍在其间的行政格局与人际关系成功地消解批评,而在当代文化中,失去批评的艺术,不成其为有价值的艺术,失去艺术的批评,不成其为有价值的批评——艺术家与批评家双方真正的困境是:在最需要批评之处,批评无能为力。
真的艺术,真的批评,不是彼此依附——“依附”这句话,正道破当今艺术家与批评家彼此利用的关系——艺术与批评是一体的两面,互为因果:好的艺术必具批评价值,好的批评必具艺术价值。在我心目中,什么是批评家与艺术家顶顶理想的关系呢?说来也不过是些不着边际的空话——
我以为,子期与伯牙是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好关系,子期死了,伯牙好琴破摔,拉倒不干。金圣叹与六大才子书,董其昌与宋元先师,也是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好关系——在金先生与董先生那里,艺术家与批评家身份合一——民国的齐如山与梅兰芳是好关系,梅先生演一场,齐先生回家给他一封信,一百多封写下来,何其珍贵的文艺与批评。鲁迅与年轻木刻家也是千载不遇的好关系,不但作文鼓吹,还请日本人教他们,自己当翻译,自己出钱给他们印画册,半夜里还给他们一个一个写回信。
西方人也有好多大侠客,与艺术家情同战友,义比讼师:左拉、波德莱尔与印象派哥们儿,那是好关系;斯塔索夫与巡回展览派哥们儿,也是好关系;安德烈·纪德追述陀斯妥耶夫斯基,罗兰·巴特追述纪德,苏珊·桑塔格追述罗兰·巴特……都是伟大的个案研究,伟大的隔代知音。
是的,批评家与艺术家不应该彼此依附,彼此利用,而是彼此敬重,彼此仗义,彼此坦然。在我们暂时难以摆脱权力的催眠与困扰前,请容我再说两句空话:
一、批评是一门伟大的艺术。请诸位批评家好好批评、痛快批评,不必自我批评。
二、真正的艺术渴望批评。而每件作品第一位严厉的批评者,应该是艺术家自己。
2003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