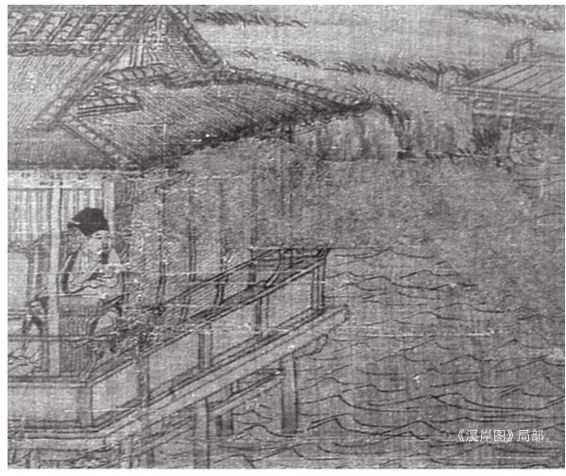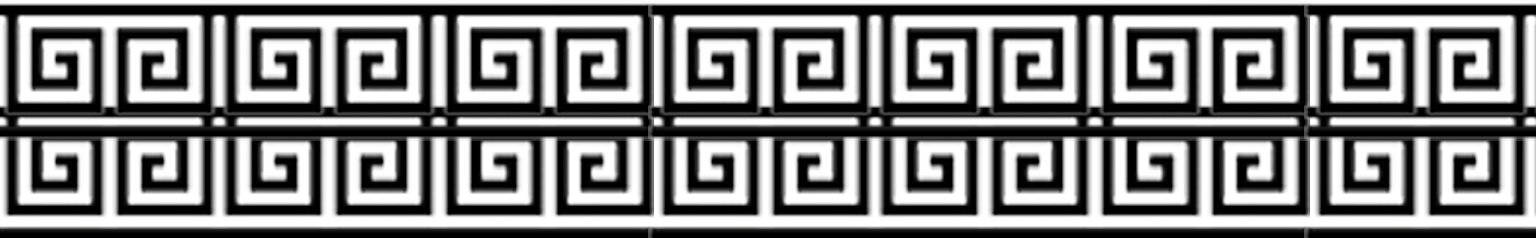

据说董其昌自称和尚投胎,前世的庙门、法号,说来凿凿有据,看他笔迹,神秀俊逸,而他曾被描述为一名松江恶霸。“因循陈腐”的“四王”画主王时敏,在曾鲸为他描摩的绣像中正当年少,目光端凝,英气逼人。元人王蒙可惜没有肖像传世,他曾对镜自夸:“我父亲生出儿子,怎这等好相貌!”那年去五台山,倒是在和尚群撞见几位美少年担柴走过,眸子不见半点尘俗气,只是当今出家人手下写得好字、画几笔像样的山水画么。
先师容颜渺不可寻。零星轶事而别有深意者,却不见时人称引。如倪瓒有洁癖,传说竹林雨后,他是非要差人以长竿将林间落叶勾除尽净,不使狼藉的。
现时我们活在另一个中国,是另一群中国人。“中国文化”,不说也罢,如今唯余地名、人口,方言喧哗。种性还在,“大好河山”,也还在的,一时拆不尽,虽然名山胜景处多已架起进口的缆车。今年,长江三峡将有多少古镇为千年江水所淹没,沿岸山势从此堕落,陡然矮下去了。
山水画传统的千年记忆,则由百年“新国画”所遮蔽。记得第一次在纽约及台北的博物院拜见中国古典山水画,自宋及清,连篇累牍,中原的大山大水,怎在这里呢。那年南京书画家董欣宾初访大都会美术馆,当夜来电话,说是进了中国收藏馆“心理平衡多了”。那么,他在探看洋画之际,心理是失衡的。
晋唐宋元的遗迹,要么散落各国,要么封锁在京津沪沈宁官家深库中。半世纪内偶有展示,次数稀缺如日食月食。图册是在陆续上市了,说是光大传统,意恐想要卖钱。今春喜获纽约徐世平以电脑精制的原寸高仿真手卷顾恺之《女史箴图》,下真迹一等,犹胜二玄社系列。捧回来,如走江湖般辗转京沪宁请画道师友过目:众皆愕然。《女史箴图》窄小古旧,通篇仙气,唯梳妆女子一段公开付印,其余七分之五六,国中无人见过——傅抱石湘女,衣带颺颺,远宗顾恺之,而他生前谅必无缘得见女史箴全图——其中一段山景,山间画着虎、兔、麋、鹿,另有雏凤飞向上端,上端画着日月。众人见及此段,莫不出声嘘叹:原来晋人初涉山水,是这样的天真憨娈,敦煌《舍身饲虎图》山景、展子虔《游春图》笔法,于是豁然可见出处与来路了。
伟大的山水画家!伟大的中国山水画!
海内外关于中国山水画的学术研究与文物鉴定,从未像今天这样庞杂而郑重,俨然显学。那年关于现存纽约董源《溪岸图》真伪的盛大争论,即是对簿“国际”公堂的大案。今岁,《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在北京拍卖场拍价千万,不论真伪,到底还是给一位比利时人重金卷走了。
此情此状,说来壮观而虚空——在中原本土几代人的文化生活、品性教养与视觉经验中,传统经典的“真身”与“本相”,几乎是“缺席”的,如此,而我们居然从未停止描绘并谈论山水画……
“文化史”、“风格史”、“笔墨论”、“境界论”、“老庄哲学”、“禅宗源流”、“道家自然观”、“文化发生学”、“艺术本体论”、“结构主义”、“历时性”、“共时性”、“图式研究”等等等等,是今人阐述古典中国画传统的理论迷宫——这是进步。这就是现代学术。
可是我们以哪种话语才能有效谈论中国山水画?
是远自谢赫及至晚清诸家的堂堂古文,还是民国“国画革命”左右两翼半文半白的铿锵辞令?是1949年后“历史唯物论”的标准官话,还是近二十年“美术研究”术语森然的翻译体与理论腔?
古典画论原是一整套精致的“形容词”谱系,犹如珍贵的画局留白,既可妙悟,亦足误解。今天,此一绵密渊深的“美文”系统完全脱离“语境”,不再与古典山水画同其呼吸,而沦为时人寻章摘句的失效词语,有效启动着误读的循环,衍生更多的歧义。
山水画经典,则形同“人质”,在世界范围被扣押着,隔离着,又处于今日学术话语的包围中,孤立无援。董其昌们想必难以辨认自己的言说:他能读懂今日的美术文论么?“国画”二字,古时就没有。倘若宋元匠师联袂出席京沪“国画研讨会”,谅必有口难言。虽则同其种姓,“我们”与“他们”,其实早已是文化的“异类”。
当此“国画研究”的盛世,我们是否更懂得,更能领悟,更会“观看”古典山水画?
记得赵无极被问到中国画家如何面对东西方传统时说:“拥有两个传统,要比只有一个传统好。”这话说得诗意。其实,他之所谓“两个传统”,一在欧美,一在中国历史的深处,并不属于我们。
西画百年,百年西化:百年间的本土油画与“新”国画,才是我们几代人的真“传统”,由这传统,新中国的种种新艺术,于焉发生,渐次步入“现代”。在一件90年代的装置作品中,涂满墨迹的宣纸碎片将一套仿明桌椅包裹起来。不论旨意为何,作者认识到: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画分明解体,早已解体了。
这意思,国画家断不能同意。虽曾有生在新中国而就读国画系的李小山一声大叫:“国画死了!”可是此后的新国画只见其多,不见其少,什么缘故呢?
是非曲直早经争辩过了,再辩,总不免落入当代史论的话语泥沼。“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除了以水墨工具玩弄“观念”的“前卫”作品,李小山叫过一叫,中青年国画家们忽而集体念“旧”了,其证据,就是边界模糊定义暧昧的“新文人画”开始主动翻寻旧图式:这可是百年前“国画革命党”深恶痛绝的逆流,逆流所向,多少其旧亦新、其新亦旧的新国画,就此蔚然相习。
绘画,乃至文化的“生死”,原是西来的思路,中国文化不讲这一套。然而世纪初决意痛改前“非”的国画新党信誓旦旦要来改造水墨画,其势,会同文学革命、文化革命及至整个国家的革命,贯穿世纪。几代人你对我错是有公论也好没公论也罢,总算去年前年,国画油画各有号称“百年”的大展隆重推出了。
记忆应该还在:“国画死亡论”原是清末民初“国画革命”的旧话重提,其间八十多年,“国情”大异——上世纪初西化飙起,国体尚属帝制;“国画革命”兴,而道统余绪犹存。此后,以1949年为界,清末民国新旧杂陈的诸般“传统”俱告注销,后三十年,“国画革命”则质变为“革命国画”,到了80年代,五四“新党”大半作古,末代英雄悉数步入暮年。面对空前的历史遗患与文化断层,国中于是有“告别革命”的共识。
要之,头一次“死亡论”是血气方刚革命者对千年旧传统施以诅咒;第二次“死亡论”,则是隔代晚生对百年新国画运动的绝望与背弃。可是众人的施展空间与文化资源,到头来哪比得当年的革命前辈:前辈革命,传统文脉尚且还在,更有寿星黄宾虹齐白石辈砥柱中流,权作门面……革命已矣,如今要来“反革命”,除了百年硝烟,此外别无所有。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了,也还要靠人去做。上世纪80年代文化事态,一面有“前卫新潮”得理不让的悍然举事,逼促西化百年的逻辑结果提前揭晓,即时势所趋之“国际化”与“现代化”;一面,则有新文人画“旁门左道”式的旁敲侧击,其情状,深涉百年西化间歇发作的“中国情结”与“民族心理”,实属文化“家事”,诚哉“剪不断”而“理还乱”。在“现代主义”中国版创作生态中,“国画”再要玩下去,则李小山另一平实之论“国画作为保留画种”,便是众人的命运。
国画的“国”字,贬了。国画的“画”字,除了生财,唯剩下两件法宝:一是工具,二是图式——凭借国画革命尘埃落定的历史“能见度”,我们“想起”了伟大的古典传统。
“传统”本来无事。赵孟頫天天临一遍兰亭序,董其昌口头禅是子久与元稹,齐白石偏要给青藤八大做走狗——其间八百年,谁说起“传统”两个字:那是日本过来的翻译词。
“国画”,原亦无事。民国初年各地多少文人乡绅寻常无事画着玩,结果是好端端一件风雅事,国画革命烟尘起,几代人说法太多,心思太重,一下笔仿佛有涉国本,情结解不开。
国画革命,多半是给逼出来的。
西方的艺术革命原亦不过“家事”,进退自主,动静得宜,无有外来文艺强势扰,不伤体面,一路到现在——是我们自己起家变,可怜斯文千年的水墨画临了吃这番惊吓,伤筋动骨,将本折利,结果是戴一顶“国画”高帽子。
革命的“历史必然”论,传统的“山穷水尽”说,也还是西人唯物史观的现成思路,人家用来得法,套来自家,怎不强扭硬掰。政制政体兜底撤换或者非要剧烈的革命吧,艺术则如高山流水风景好,不然中国的礼乐绘画何来延绵千年的命。
中国的书法、山水画,西方的雕刻、交响乐——看来看去,西洋人几百年的风景画,美则美矣,作法太实而味道太咸,唯文艺复兴添作背景的近山远山倒是自出“旷观”,颇见“远意”,斯宾格勒即曾指说,风景画的没落是到工业革命期的印象派,因失尽文艺复兴“宇宙观”。怎么比呢?画“山水”本非画“风景”,中国古典山水画的早熟与高迈,只能归于中国文化的大神秘。
理论是尴尬的。指说传统文化的存亡明灭,弄不好就没有台阶下。齐白石亲历三朝,何等乱世,迄至下笔,俱如空白——中国历史世面见得多,凶吉盛衰,婉转夷然。许多事,中国人是做得而说不得,反之亦然:佯狂而潜伏,放诞而养晦,不肖抑或至孝,造反忽儿归顺——老把戏总能兜得转。此即中国式的自欺自救,自强而自适,画家则不闻“家事国事天下事”,闻知亦当无事,据守画案,磨墨理纸,习性便是自然。相较于西人西画的煞有介事闹革命,中国人柔韧圆通能委曲,是福气,也是厉害。


传说战场息鼓,苦雨相随,雨歇,蒲公英星星点点——80年代国画圈内外泥脚裹足,举步维艰,而居然有新文人画应运而生,看似背时悖势,实则化机缘——接着便是战后的休养生息,鸡犬之声相闻,此亦千年荣枯循环往复的老模式:十余年来,国画圈热烙喜气,货色暴增,花草秀木姑不论,总算是画家群敬革命情结文化是非而远之,心未平则气甚和,有笔战而无戾气,各人自便,自灭而自生:所谓文化“生态”者,本来如此,早该如此。
国画无事。如今画家们放松了,不再追问他们画的是不是“国画”,也不再有任何律令追问他们。
传统亦无事。世纪末的国画家与古人隔岸遥望,不再恓惶而诅咒。1949年来最完整的传统经典集册源源上市,图像历历,恍若冥界的纸鹤,“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画家最为富有而可供支配的资源,其实是图像与图式。我们全是“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家:此事殊可表说。
百年新国画的既成图式兼以本土油画、版画、壁画,以怎样的方式酿成当代山水画的“图式化”?此一大话题;反之,经此交缠,山水画的“图式化”以怎样的方式“传染”其他画种,此亦一大话题——“图式化”,排斥感受力与深度表达,是创作的宿忌;图式,则蕴涵极度丰富的文化符码:图式化与图式,不是一回事。
在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中,宋元明清经典图式,与我们的视觉经验最为阻隔,也来得最迟。
这一隔一迟,并非仅指印刷物的面市迟早,更是指经典长期缺席、百年新国画当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失忆、错位、误解,以及寻求记忆:那是文化断层的因果链,至今我们仍未摆脱此一断层无微不至的后遗症。
五六十年代古典山水画图册精而少,贵而禁,革命年代的晚生看不到,也不要看,是属“有眼无珠”;80年代“文革”乍歇,传统国画印刷品粗而杂,平而陋,争看争购,似乎有眼而无心。近十年出版盛世,不消说,至此,我辈精神“盲流”步入中岁,知省思而求见识,心眼初具了——所谓“看山是山”三段说,在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上,总算接近由表及里之途:五十年来唯此一时段,古典传统始以空前精良的图像,与我们素面相对,素面相认。
国画革命实于古典传统无伤,而在识赏的眼光逐代昧失,以至视而不见,见而不识。有谁愿意承认:当代中国人并不真正“懂得”中国画?经典之为经典,乃因其自身的生命与说服力。《女史箴图》高仿真手卷的展示效果,如博尔赫斯所言:“读到荷马史诗精彩文句的一瞬,古人就在‘此刻’,并没有死亡。”手卷展开,光芒自历史深处照射而来。有位“前卫”油画家看罢,无以言对,说他接受了一次“爱国教育”——古典传统“情境还原”的未来进程,总还要落实为质直的观看。
认知传统不是逆向回归,而是借助历史的维度认知自己。精读图式是慧眼精明之士的案头生涯;而经典图式的“来世”必环伺大量同质异型的作品。中国绘画早就是高度自觉的“图式循环”——好比明清书法是晋唐传统的“美术化”,明季,尤其是董其昌以后的山水画,即是“图式循环”的历史,犹如同一曲式的无穷变奏。民初时论曾将之贬斥为“泥古”、“因循”,殊不知此一传统“基因遗传”的“生理周期”,比之晚近西方后现代绘画的所谓“戏仿”与“挪用占有”,早了几百年,而明清诸家的“拟古”、“仿古”云云,即于此道直言不讳。
我们真是小看而错看了古人,他们都是当时的“前卫”人士。
图式来自前代,观看属于此时。同一经典,我们的赏看,与彼时董其昌的赏看,其感知,已幡然有别,一如董其昌赏看董、巨、倪、黄,大异于董、巨、倪、黄的时代。艾略特有言,大意是“每有新作出,传统均将为之移动,并赋予新的位置与观点”。杜尚一再坚持:是观看者在“创造”一件作品——就此而言,古人岂非早就郑重其事,将传统以历历图式“托孤”予我们?
传统只剩下图式了,余事无从追究。文人画的“三绝”、“四全”之类,俱往矣:从山林走进“单位”,隐士当了“干部”,袈裟换成“西装”,不及百年,中国画家身份人格蜕变如此,从何谈起?整个世界已经变换,历史便是如此——今日欧洲人正以种种新的方式回应巴罗克图式的丰富启示,中国人也常会忽然想起辉煌的过去:当代山水画野心如何?我们能不能从经典图式中寻求轮回转世,重新构架大唐大宋的伟大遗骸?
三年前的暮春,我在一座江南古镇深巷底,见院门口两位小姑娘倚定板桌,正襟端坐,就一册肮脏稀烂的《芥子园画谱》旧版本,一笔一笔勾松树。那天风日妍静,堂屋竹椅斜着一位打瞌睡的老太爷,据说九十多岁了,正是她们的画师。
我伫立观看,如幻似真,诚不知作何感想。院校国画系的临摹课,见得多了。眼前一幕,你说是“传统命脉”在,言重了,说是“文化草根”旺,则悬想古昔,无从感慨起,然而我还是感动了。中国的所谓“庙堂”与“民间”,早已荡然无存,徒具其表的“表”,全不是从前那回事。可是你四乡走一走,今日农家镇民电视摩托用归用,堂屋间还是竞相挂挂俗陋喜气的山水花鸟画,旁边配两条红对联。村夫知道什么“南北宗”呢,他们啧啧称奇的还是本镇本乡的书画家。
有山在而水自流。我们都承认晋唐宋元大传统望之弥高,无可企及,可是中国人是山水花鸟树石兰竹画到现在不厌烦,那是顽强的惰性,而这惰性,恐怕才能使历史记忆得以牵连。唯物论的“历史主义”者认定,过去的真相不会失去,可是本雅明却洞察过去的真相转瞬即逝,永不再现,除非我们持续对抗遗忘。
我们遗忘的事物还少么?江南古镇的一幕只是历史的残渣,等不及老画师过世,小姑子长大,古镇就拆了吧。我常在思忖约翰·伯格的话:“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国画革命的问题不在革命,而在割断历史。没有一种绘画如中国古典山水画那样追究历史,我们的先师甚至不是画家,而是深味历史的人,他们直接在纸面上陈述“历史”,将历史置于他们的“现在时”。诚如卢辅圣在《中国文人画通鉴》所言,此乃人类艺术史的“孤例”—明清画家用意所指是山水画千年道统,走的是反方向的正路;国画革命者所怨怼者,则是清末的衰蔽,于是壮怀激烈。若清一代画路果然气短途穷,则百年之后的今天,就我所知,为数不少的当代山水画家已跨越韶光,再度瞩目并谈论隋唐与宋元的绘画。
我们是迷失的几代人。回过头去,有大眼界在。
本月,为纪念上海博物院成立五十周年,来自各地共七十多件晋唐宋元的经典真迹将要公开展示。掐指算来,这可是建国以来头一席传统经典的盛宴——整整五十年!去是一定要去的,这也是我第一回在神州境内,在自己生长的城市,亲眼瞻拜数量可观的古代经典。
将观众和真迹隔开的那道玻璃,足以成全我们与暌违过久的真迹相对凝视——山高水长,俱在眼前,历史断层,无可度越,然而玻璃是清澈透明的。愿观众身在此端的凝视,除了视网膜功能,而竟承接今朝与夙昔迢迢千年的文化渊源。
2002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