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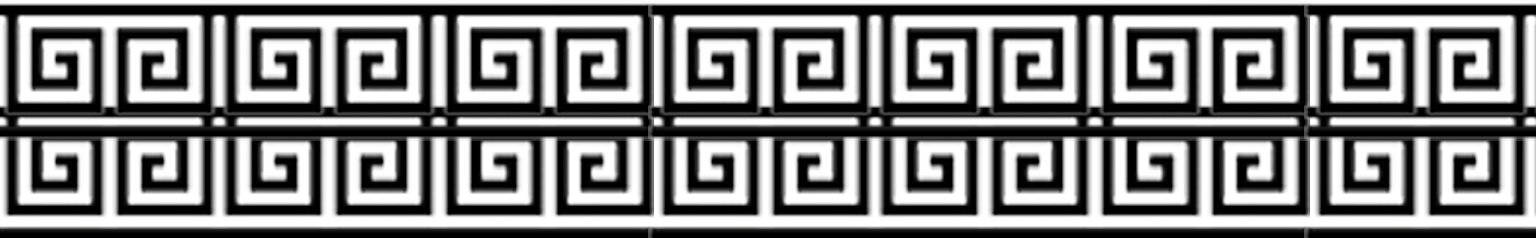
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人文讲堂讲演
诸位同学、诸位老师:
今天有荣幸被请到贵校出席百年校庆,我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此前不知道南京有一所大学叫作“东南大学”,更想不到她有百年历史。待我收到贵校的邀请函,才知道这就是南京工学院的前身。
现在我被贵校请来当嘉宾,并没有这份资格,我只是个喜欢画画的人。不错,我正在担任所谓绘画博士生的导师,是一名所谓责任教授,但是我要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什么叫作“美术博士生”,我也不知道什么人有资格教这样的博士生。当我每年审看博士生报考表格时,我发现自己既不具备报考的学历,更不具备国家规定的种种条条框框。说到学历,除了二十多年前在中央美院上过两年所谓研究生课程,我的文化程度只是小学毕业生。小学毕业那年,“文革”爆发,我的两年初中全是下工厂,去农村,或者观看老师被批斗,根本不上课。到了十六岁,我就和千万名知青给塞进火车,送到农村种地去,一去就是八年——我常常说:所谓“知识青年”的意思,就是指没有知识的青年。
所以要说知识,在座诸位比我多,要说学历,在座诸位更比我高。
我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贵校邀请函明明白白印着“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人文大讲堂”。“人文”这样大的话题,我当不起:没有足够的知识,“人文”从何谈起?而我竟被请到我所不知道的大学讲“人文”,说明我连“常识”也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一代人的“文化常识”与“历史记忆”,很早就被切断了。
所以我今天的讲题,叫作“常识与记忆”。
我给大家讲一件小事情。去年,我受命给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画一幅大画叫作“国学研究院”,画面上的主角是七十年前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五位前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为了收集素材,我去清华大学校史馆询问研究院故址在哪里,馆员都说不知道。我急了,于是在校园内王国维自沉碑周围特意先后询问十几位年龄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师或职员,结果呢,不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本校有过这样一所研究院,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清,并复述“国学研究院”这几个字——
“什么?‘博学研究院’?”他们一脸茫然,掉头走开。
我自己知道么?在给清华大学叫来帮忙教书前,我仅听说过以上五位老先生的名字,要不是那幅创作,我也不知道清华大学有过这么一所“国学研究院”,问了人,才知道早在1952年,清华大学的人文学科就给全部砍掉了,那一年,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
一晃五十年过去,国家忽然想起“人文传统”、“国学研究”这些字眼,忽然要来纪念“国学研究院”,忽然要来做今天这样的“人文大讲堂”——所以不但是我,连国家也常常失去记忆的。
还好,总算又记得了。回头我要问问“东南大学”的校名,是怎样在贵校历史中失去记忆,又恢复记忆的。

上中五图自左至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摄于1925年前后。下图:油画《国学研究院》局部,画于2001年。自左至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当然,有些事情最好忘记,不说为好,可是我的记忆力偏偏不坏,居然记得。是什么事情呢?说来有趣,当校方领导陪我参观清华大学校园时,我忽然发现一幢主楼似曾相识,仿佛多年前在电视里看到过,我问:这里是不是1966年万人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现场?回答说,正是这里。接着,领导指着著名的刻有“清华园”三字的校门石牌坊,说这座起于清朝末年的牌坊在“文革”初期被砸毁,是红卫兵喝令当时被批倒的学者教授们动手砸毁的,然后在那里竖立了一座毛主席雕像,直到“文革”结束,才仿照老清华的模样重新建起来。现在那里天天有游人争先恐后拍照留念,其实那座“清华园”牌坊是假的,年龄只有二十几岁。
这就是我的记忆。这是“人文”的记忆么?不是,可是大家不要小看这记忆:就是在这样的记忆中,我们几代人失去了常识与记忆。
今天,全国院校,全国的教育,大谈“人文”——可是大家要知道,一个民族忽然要来大谈“人文”,不是好事情,正相反,它说明人文状况出现了大问题。面对这样的大问题,以我的看法,咱们先别奢谈所谓“人文”,我们要紧的是先来恢复常识和记忆。
可是我们失去的常识和记忆太多了,从何说起?今天,我们还是从绘画说起吧。
但是绘画的范围很广,话题很多,在座诸位不一定都是绘画专业的同学,那么,我就以“美术馆”为话题说说看,因为美术馆开放给所有人。
二十年前,我为什么去到纽约?不是为了移民、发财,而是为了到西方开眼界,看看油画经典的原作。当我走进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上下古今的西方油画看也看不过来,可是没想到就在那里,我从此开始了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启蒙,认清了我们民族从上古到清末的艺术家谱:在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华盛顿,伦敦与台北故宫,我所看到的中国艺术经典,竟是我在中国大陆所能看到的上百倍,而且十之八九是精品。
那么,中国大陆的艺术珍品和大量文物还剩多少?放在哪里?仅以北京为例,据故宫古典书画文物鉴定家单国强先生说,故宫所藏书画约有九万多件,他任职三十多年来,仅只看过其中的三分之一,而1949年迄今,故宫展出的书画总量不超过一万件。照此说法,中国人不出国境,就应该看得到大量炎黄祖宗的艺术品,从美术馆得到美术的常识,由美术史牵连文化的记忆。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财,缺乏太多设备,更主要的原因,我们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面。要好好清理国宝,以今日世界的高水准永久陈列,还不知道要过多久。
单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齐白石老先生。齐先生去世后,他的手稿、草图和晚年的精品,全都捐献北京画院,几个月前,我有幸亲眼看到这批珍贵的文物,总有上千份吧,居然还像半个世纪前那样,以最简陋的方式,就像我们家里收拾早年的信札账单那样,折叠着,放在旧信封或破烂的塑料袋里。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没有这笔闲钱,也没有心思好好整理,装裱,展示,还幸亏靠着画院保护着,珍藏着,动也不敢动。
中国只有一个齐白石,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画家,可是与他差不多年龄上下的西方画家,譬如长寿的毕加索,在法国西班牙两国不知有多少纪念馆,故居,美术馆,专门陈列他的每张纸片,早死的凡·高,则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公园里占有一座面积很大的个人美术馆,朝拜者每天络绎不绝。凡·高生前冷落,死后享受世界声誉,然而齐先生生前就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可是今天,人民还是没有地方去看一眼人民艺术家的画。
在南京,诸位有什么地方可以随时去看看齐白石的画?或者,诸位有什么地方可以随时去看看金陵画家傅抱石、钱松喦、宋文治、魏紫熙、亚明等老先生的画吗?(学生齐声回答:看不到!)几天前,魏老先生的追悼会刚刚开过,解放后号称新金陵画派的时代,就此结束了。这要是在日本、欧洲,早已建立他们的纪念馆美术馆,但在中国,我们只有追悼会,以后,也只有他们作品的拍卖会。别说全国,就是南京一地的老百姓,还是看不到。
所以前年我回到北京定居,发现我又变得像出国前一般无知,在我们的故宫,在国家美术馆,还是看不到民族艺术五千年的详细脉络,更看不到几件经典的原作。大家知道,绘画是视觉艺术,看不到真东西,一切都是空谈,就像一群聋子在那里谈论音乐。可是我们全国上下的千万名画家和更多的艺术爱好者,居然也就空口谈艺术,谈了半个多世纪,像我这样的无知,今天还要给无知的学生去上课。
两个月前,我在纽约买到电脑精印的几份珍贵手卷: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北宋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北宋李公麟的《海会图》,清代王原祁的《辋川别业图》,清代顾见龙的《春宵秘戏图》。人但凡得了宝贝,忍不住要显宝,我就捧着手卷给学生去上课,大家看呆了,别说没见过,就是听也没听说。上个礼拜,我又捧去给母校的老院长靳先生、新院长潘先生,还有老师兄老同学看,看过之后,靳先生一人就订购了其中四套,潘先生说5月访纽约,要代中央美院买一批回来,用于教学。
这就是我们高等美术学院的“人文”现状:我们要到国外去买民族艺术经典的复制品,假如不买,我们连这复制品也没得玩。
可是以上手卷只是中国艺术的沧海一粟。大家知道不知道,除了欧美数百座重要的美术馆,全世界评选出十大美术馆是哪几座?现在,我来念一念:
意大利梵蒂冈美术馆
法国卢浮宫美术馆
英国大英博物馆
俄国冬宫美术馆
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
墨西哥玛雅美术馆
美国大都会美术馆
埃及开罗美术馆
德国柏林美术馆
土耳其君士坦丁美术馆
偌大的亚洲,没有,一座也没有。

卢浮宫二层宫殿南廊。石栏上端等身大小的雕像都是法兰西著名历史人物。
前面说到故宫,公元1407年,明成祖下令起造紫禁城,当时西方人才刚从中世纪醒来不久,文艺复兴三杰还没生出来,所以要说我们故宫的岁数,远在梵蒂冈卢浮宫之上。可是今日的紫禁城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博物馆,只是皇宫旧址,因为故宫深院的大量书画文物,就好比一座声名远扬的大饭馆,除了挂出皇家仿膳的漂亮菜单,基本上不营业,不开饭。
中国,是亚洲最大,最古老,文化艺术最丰厚的国家,我们动不动就说“上下文明五千年”,到今天,神州大地勉强符合国际收藏标准、陈列规范、开放制度与教育功能的,只有一座上海博物馆,而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广度、深度、类别、级别,可能还不如美国一所大学的美术馆。但我要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有了这么一座比较像样的美术馆。最近,故宫开始了建国以来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大修整,据说要恢复乾隆盛世的模样,到2008年开放给奥运会的各国游客看。大家知道,申办奥运会哪里是为了体育,而是不折不扣的超级政治任务,可是没有这项政治任务,钱拨不下来,事办不起来,所以我有保留地谢谢天,谢谢地,但我紧跟着就要问一句:假使奥运会没给安在北京城,2008年没有这回事,故宫怎么办?
凡是先进国家,尤其是维持民族自尊的国家,都会高度重视美术馆,那是民族的荣耀,国家的脸面。诸位有一天到罗马、巴黎、伦敦、纽约去看看,美术馆天天人山人海。诸位说说看:美术馆为什么那么重要?美术馆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们一天到晚说“世界”、“世界”,你怎样认识世界?看世界地图?读历史书?读世界新闻?读参考消息?读杂志上关于世界的报道?不是,你要真正能够感性地,全面地,实实在在地了解世界,应该走进美术馆。

凡·高的弟弟提奥给哥哥写信的信封,今阿姆斯特丹凡·高美术馆将此信封印成薄纸袋,为出售凡·高作品明信片包装之用。
美术馆的“美术品”,博物馆的“物”,都不是顶要紧的。要说书画,要说文物,我们有,而且有的是,可是,美术馆不是挂几幅画,摆几件文物的地方,也不完全是开展览的地方,美术馆博物馆顶顶要紧的,是它的文化形象,是它的社会角色,是它的教育功能,是它在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中活生生的作用,美术馆,是一本活的大百科全书,因为美术馆的对象不仅仅是艺术家,而是所有人。
英国人约翰·伯格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伯格,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本雅明的追随者,本雅明的思想来源,是大名鼎鼎的马克思同志。我们的国家奉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今天所有大学生都要考马克思主义,学马克思主义,很好,我们来想想这段话:如果这段话是对的,有道理的,那么,我们今天怎样才能“始终”将自己“置身于历史”?我们怎样看待“过去的艺术”,并从中确认我们今天的“政治”立场?我相信,方法,途径,许许多多,可是谁会想到美术馆?
美术馆,以我的定义,就是提供文化常识,储存历史记忆的场所。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想出很多法子来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等等等等,可是教育部部长蔡元培先生大声呼喊:“美育代宗教”,他把美育提高到宗教的高度,他清楚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传统宗教意识,但他认为“美育”是有可能的,比宗教还根本,还有效。但是,“美育”的最高标准和最起码的条件,是要有国家美术馆。可惜在蔡先生的时代,国家不断打仗,国民政府把故宫的国宝装了几百几千箱,运过来运过去,60年代弄出台北故宫博物院。大陆这边呢,快要一个世纪过去了,蔡先生的理想有没有实现?他这句话的涵义,多少人懂得?他这句话,又有多少人记得?要说“美育”,我们今天出了个所谓“五讲四美”,层次很低,不过是要有礼貌,守规矩,走横道线,别随便吐痰之类,说明什么呢?无非说明我们的社会五不讲,四不美。
我想,要是我们全国大城市都有以上所说的大型国家美术馆,情形不至于这个样子。我在国外十多年,就眼看有自己美术馆的国民,与没有美术馆的国民,很不一样,大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二十年前,描绘机场壁画的袁运生先生造访西北敦煌,写成一篇《魂兮归来》的文章,呼唤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其实,魂是叫不回来的,西方人也叫不回希腊艺术与文艺复兴的魂,我所要呼唤的,只是“常识与记忆”。为什么呢,因为西方人似乎知道“魂不附体”这句古谚,他们精心留存着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的“体”,只要“体”还在,所谓文化的“魂”,就有个依附之所——要我说,文化艺术的“体”,就是美术馆。
可是从我归国两年的见闻看,我们好像不在乎常识,不在乎记忆,我们所竭力构筑的,似乎总是所谓“上层建筑”——我们的艺术学院在教所谓“美术学”,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所谓博士生正在逐年递增,我们的美术界天天高谈所谓世纪性、国际性、历史性、当代性等等耸人听闻的大话题,种种杂志、研讨会、拍卖会、博览会、双年展以及名目繁多的活动,办得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级别与名称越来越高,远远看过去,我们的文化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欣欣向荣……可是在这一切的热闹与喧嚣中,美术馆,作为一条无法替代的认知途径,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一个巨大的文化实体,却是长期悬置、长期缺席。用中国人的老话说,这就是文化上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大家知道,无源之水是死水,弄得再漂亮,不过像个游泳池;无本之木是长不高大的,弄得再好看,也不过像个大盆景。
历史的失忆症,必然引发更多的失忆。美术馆只是整个文化问题的一小部分。如前所述,就在清华大学的九十年校庆,就在校方抬出国学研究院的辉煌过去,试图借此重振人文传统时,我在校园里遇到的却是无知与失忆。而今天,在一所我不知道的大学里,我竟充当所谓“人文大讲堂”的演讲人,岂不讽刺?
可是有人会说,这算什么大不了的大事吗?是的,没什么大不了,这只是“知道”与“不知道”的问题。苏格拉底被引述最多的命题是“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们的命题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大规模失落的常识与记忆,说不过来,这是沉重的话题,我的发言应该结束了。在结束前,容我添几句有点亮色的话——
今天,在恢复常识与记忆的工作上,能够使我们欣慰的,发生希望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空前兴旺的出版业,大家知道,书本就是知识,读书就是要你“知道”。我归国后最振奋,最开心的事,就是我们的书店终于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每本书似乎都在问我:“你知道吗?”或者说,每本书都在提醒我:“同志,你不知道!”——虽然,今天我们出版的书籍种类与品质,还远远不能和发达国家比,但却是建国以来最像样,最应该的那么一种局面。
所以,另一件令人宽慰的事就是校园里的年轻人,就是在座各位。我在开始时说,诸位的知识比我多,学历比我高,诸位,就是未来的国家栋梁。我任课两年以来,一面感到惭愧,因为整个我这一代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知识结构与人格成长很有问题的人,如今已经占据了教育岗位,是国家最主要的师资群体。另一方面,我发现新一代青年已经大大区别于我们,开始接受比较宽广的知识系统,开始从长期意识形态的迷瘴里走出来,没有这个前提,谈不上“人文”。但是全方位恢复常识与记忆,又从常识与记忆中逐步建构高层次的文化意识,是个漫长的过程,我愿意说,在在座诸位同学身上,这一过程有希望真正开始。
为了恢复常识,恢复记忆,重建人文的漫长过程,我愿以《易经》里的三句话送给大家,这三句话只有十二个字:
大人虎变
小人革面
君子豹变
什么意思呢?“大人”,指的是“王”,“统治者”,不必细说;“小人革面”,则忽儿这样,忽儿那样,靠着变脸讨生活的角色,我们平时见得多了,也不必细说——要紧的是第三句话。
用今天的说法,所谓“君子”,接近于“知识分子”,指的是有文化,有教养,有立场,有品格的人——“君子”这两个字,也属于我们失忆的词语了——那么,“豹变”是什么意思呢?古人说话是非常形象,非常准确的。大家在动物园里或电影里见过修长美丽的豹子吗?那一身好皮,无比精致,无比高贵,可是您要是见过刚养出来的小豹子,简直没法看,皮毛黏滞,浑浊肮脏,像一团烂泥,哪里想到长大后会慢慢生就那一身好皮毛。“君子豹变”就是说,你要想从丑陋到美丽,从幼小到壮大,从无知到有知,逐渐成为一个有品质的人,你要慢慢地来,慢慢地蜕变……翻译成现在的话,大概相当于所谓“十年种树,百年育人”的意思吧,但这话给我们说滥了,依我看,古人许多话,远比今人说得漂亮,说得真确,可是给今人忘记了。我就是因一位尊长告诉我这句话,这才知道,牢记在心。
诸位不论是什么性别,学的是什么专业,今后做什么社会角色,都希望有出息吧?或许,有人会变成大王,那可好极了,有人终究还是“小人”,那也奈何不得,可是我猜,将来诸位是升官发财也好,是白领蓝领也好,谁都愿意自己变成一个“君子”,当得起“君子”这样的美称吧?
我的话说完了,谢谢大家。
2002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