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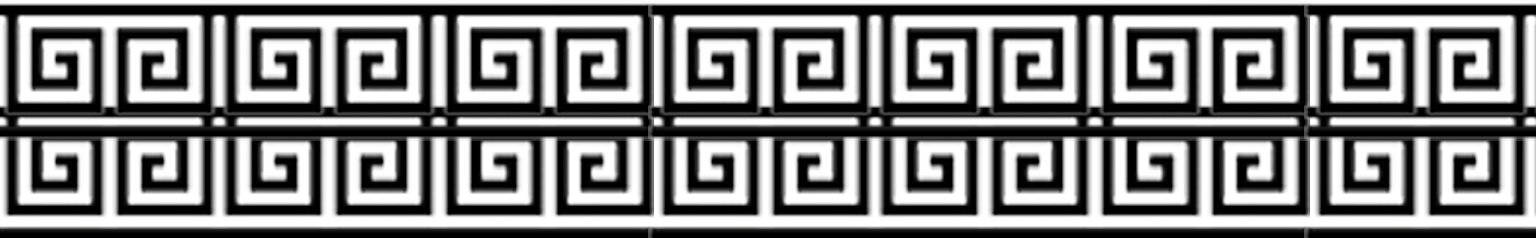

这不是“我自己”起的题目——事情是这样子:《收获》杂志明年改版(真抱歉,我从未读过《收获》),编辑说是要开辟作家或艺术家谈论“自己”的专栏,在电话里几番情词恳切向我要稿子,终于推托不过,我说,非要写,出个题目,发几句问吧,于是电传传过来,给了这题目。
我不愿谈论我自己。我的家不挂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画——不为什么,也没想过为什么。平时偶尔发表文字,编辑索要照片,我也不寄。不知起于何时,中国的书刊作兴发表一张以至一张以上的作者照片(十九彩色,彩色照片真难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麻烦读者看自己?你怎么知道读者愿意看见你?
可是好几位编辑语重心长劝过来:“随俗吧!这是读者的愿望。”
谁是读者?他们在哪里?就算真有读者坐在我跟前,我也不知如何“说说我自己”——人只要是坐下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谈自己”,而我是读到文章里出现太多的“我”字,便起反感,因我向来怕见进门坐下滔滔不绝大谈自己的人。
今岁我回国存身,不走了。人一旦成了所谓远来的和尚,归国的游子,即便仍是黄脸一张,“读者”总不免过来瞧一眼——采访,座谈,约稿,热乎乎地,都是抬举,都该解作善意。好吧,豁出去,我就三陪小姐似的陪一阵,陪过一阵,总会四散的吧,然而难办的是临了还要提供自己的照片拿去印,怎么办呢,挨得过初一挨不过十五,我终于屈服,就范,随了几回“俗”。新近接受ELLE杂志(即叫作《世界服装之苑》)的采访,就给要去几张与家人一起的照片,因编辑说是要给读者“亲切感”。事先征求女儿的意思,不料她就高兴叫道:YES!同学们可以在ELLE上看见我!——她倒预先知道谁是她的“读者”了,而且中文版ELLE拿到美国去,怕是比法文原版还吃香。
自己拍照自己看,没什么。谁手边没有自己的相片呢,可是一朝发表流布,譬如在ELLE连篇累牍的朱唇、香肩、玉臂、秀腿之间忽然撞见“我自己”,我登时变成身份不明的“读者”——昨天,11月号ELLE上了市,封面是美国影星“甜宝贝儿”布兰妮,侧身斜睨着,一对丰乳在滑亮的铜版纸上几乎跌出来。打开,翻下去,心惊肉跳,闯了祸似的:“我自己!”
在“我”与“自己”的画作之间,感触怎样呢?9月,我的个展在北京展过,10月即开始了从湖北发端的巡回。在武昌那个空阔陌生的展厅,我又目睹一百六十多幅大大小小自己的画从货柜里一件件取出:有点亲腻,有点烦。二十年来年年办展,自己的画,自己早已看熟、看厌,每当这样的打点布置自己的展览,我多少像是置身事外,并茫然惊异于自己的冷漠。这茫然的惊异,外人不易觉察,我心里是知道的,此刻无妨说出来:那其实出于一种难以弃绝的自顾与依恋,仍算是轻微的热度吧。
但这都是后台的“内心活动”,纸面上的“文字处理”。人在现场,“我”与“自己”往往还是不知如何坦然相处,犹如当年初出道。
只要有观众,我向来羞于走进张挂自己作品的展厅中去——不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多年前读到一篇关于马奈的回忆文字:他也竟羞于走近沙龙里自己的画幅跟前去,朋友拉他,他固执拒绝,停在远处。我知道,我岂能自比马奈,但是人同此心。幼年在体育场看见球手投中,满场叫好,那球手却总是埋首疾步跑开去,毫不理会周围的响动,而那神色又分明听见并知道周围的响动的。胡兰成对此自有他的说法,他似乎格外倾心于他的说法,他说:古人箭中靶心的一刻,每在心里叫声“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是“在众人里看见了自己”。
放学了,一群小孩子,欢天喜地连打带闹,这时最怕爹娘冷不防窜出来,连名带姓叫回家。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是吗?好像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每在大画家的回顾展厅里徘徊不去,我常会想起那位罗马总督手指耶稣说的话:“瞧——这——个——人。”是啊,我常想,真有所谓“艺术史”么?没有这单个单个的“人”,艺术史是什么?
在作品上签署姓名的传统是十分晚近的故事,相传始于乔多。乔多的时代,相当于我们的元末吧?中国艺术家的署名史,似乎要久远得多了。但我们可知道兵马俑的作者是谁?敦煌的作者又是谁?
“艺术家”一词是翻译过来的。在敦煌与兵马俑的时代,那些伟大的作品并不被看作是艺术,“艺术”一词,也是翻译过来的。
纪德(抑或是福楼拜?)说:“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
签名只是签名。如今满世界的油画行货张张都签名,在中国,许多作者用的是拼音字母,斜体,飘逸,粗看以为是英文,是法文,其中最快的快手,一天能刷几十张。真的,在行货上,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我长久迷惘于委拉斯开兹的魅力。在他的画中,只见艺术,不见艺术家。
小时候翻墙越界,手腕子给大人捉牢了,拽到办公室,桌子一拍:讲!此刻,我若犯事败露扣在局子里,我将被迫“说说我自己”,正式的说法,即“坦白交代”——我愿坦白,我自认很坦白,只怕我说出的话,编辑、读者不要听。
编辑在电传里问:什么因素、什么时刻使你萌生了、确认了要当一名“艺术家”的想法?
我不知道,也不记得。至今我羡慕能够留起络腮胡子的人,我真想知道是什么因素、在什么时刻,他们的胡子开始“萌生”,并“确认”为络腮胡子,而我却没有。
编辑又问:面对现在艺术学院最年轻的艺术学生,如果他不知道您,会如何?
在今年出席的几次座谈会上,“最年轻的学生”递给我的字条会这样的提问:“请谈谈您的初恋,还有中年的欲望。”底下加个小括弧,歪歪斜斜写着:“一定要回答呀!”我“会如何”呢?我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男生女生根本不讲话。至于中年的欲望,请诸位等到中年再问吧。
编辑还问:听说两次您的流泪,一次是在伦勃朗画前,一次是在学生面前。
胡说!我从未在“伦勃朗”或“学生”面前流过泪。在别的时刻或场合,我确曾纵容过自己的眼泪,有时,那简直是欢欣的经验,但除非“刑具伺候”,我绝不招供详细,直到我愿意将之转化为别的叙述方式。罗兰·巴特在他追念亡母的著作《明室》中,母亲以及母亲的照片是贯穿全书的话题,可是在书中的大量照片里既没有他的母亲,也没有他自己。他坦白,但什么也没交代。他说:
“我要发表心灵,而不公开隐私。”
年轻的达利初访毕加索:“先生,我今晨抵达巴黎,没去卢浮宫,先来看您!”
毕加索应声答道:“你做得对!”
艺术家自当如是看自己。凡·高同志要算是倒霉的,但他在给亲兄弟的信中说:“有一天,全世界会用不同的发音念我的名字。”
这算是“隐私”还是“心灵”?20世纪初,据说散在巴黎蒙马特高地的“盲流画家”中有位老兄每天早起将脑袋伸出阁楼天窗对着大街吼叫着:我是天才,我是天才!
看来我不配是个艺术家,不因谦虚,或因我是中国人。少年时,我在穷山沟里好像曾经躲进被窝偷偷默念过“我是天才”之类谵语,因是过期太久的陈年“隐私”,可以“发表”,聊供读者笑一笑。当代中国艺术家总算敢于公开求声名,放狂话,遑急旷达,旷达而遑急,似也渐与西方人连同一气。我就不止一次在国中关于艺术的文字中读到引自安迪·沃霍的话:
“每人出名五分钟。”
二十多年前,我时或被人告知我已出了名。近年回转来,小小美术圈的同行居然依旧记得“陈丹青”。只是这点若有若无的小名声,与“我自己”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每见围上来要求签名的“最年轻的艺术学生”,我总是感到委屈而失措:替他们委屈,替他们失措。我签,但即便是伦勃朗或毕加索此刻坐在正对面,我一定不会走上去要求签个名。我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我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齐白石说他甘愿给青藤八大磨墨理纸当走狗,绝对真心话。
编辑的电传还说:即使现在,也有人不断在对《西藏组画》做解读。不见得吧,要真是那样,我该怎样解读这“不断的解读”?那是我的“声名”还是“我自己”?关于那些画,倒是四川美院一位学生说得最痛快。他生长在拉萨,与我老交情,看到后来一拨拨画家跑去画西藏,他脱口而出:打倒陈丹青!
上个礼拜我遇见了陈丹青,真的!还是在湖北,讲座过后,同学们又挤过来要签名。忽然人丛里钻出一位能说会道的小姑娘,江西人,属羊,与我闺女一般大——大家哄笑了:原来这姑娘与我同名又同姓——名叫“丹青”的同志我知道好几位,同名同姓,现前面见,却是第一回——我们彼此瞪着,傻笑,不知如何是好。她要是个男子,与我同龄,我就可以模仿安迪·沃霍聪明而善良的恶作剧,聘请这位陈丹青为我抛头露面开讲座。不是吗?在众人的朗声哄笑中,我俩终于并排站站好:这回是我要求与“陈丹青”合个影。
临了,陈丹青同志一定要我为她写句话,我就写:
丹青:你怎么也叫陈丹青?接着签了我的名。
但随即我就后悔了:凭什么人家不能也叫陈丹青?我该这样写:
丹青:我也名叫陈丹青。
2000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