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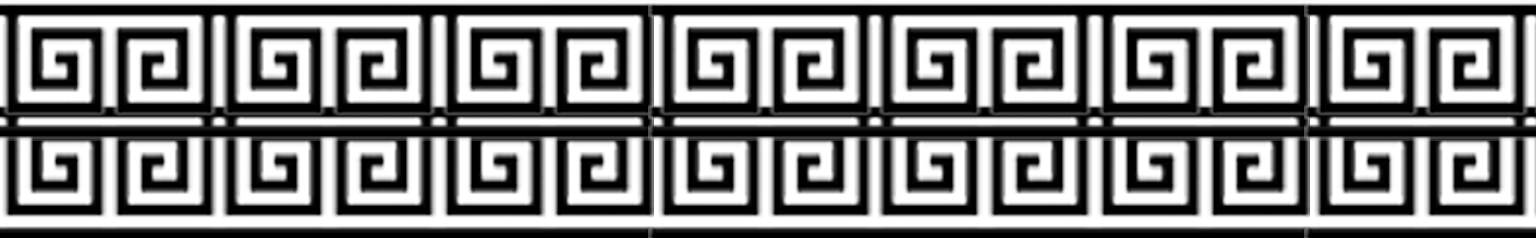

回忆上世纪70年代沪上油画精英
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赖礼庠、邱瑞敏、王永强、刘耀真、严国基……我与这群上海美专毕业生打照面,竟远在1968年,地点是在上海淮海中路今地铁站口至陕西南路整段水泥墙前,拨回记忆去,只见以上画家一字排开,高据木梯,手握大号油漆刷,每人奋笔涂画一幅巨大的毛主席油画像——当其时,政府机关悉数瘫痪,大学院校全部关闭,抄家、造反、游行、抢权,“文革”叫嚣响彻申城——那天淮海路春阳和煦,我混进围观的人群中,14岁年纪,眼看毛润之眉眼鼻唇在笔触油漆间渐次成形,不禁神旺。
我不知道这些画家姓甚名谁,他们也不知道那天在昔日霞飞路上的集体亮相,使他们成为日后70年代上海市最重要的油画家。
多年后,我才知道其中的魏景山、陈逸飞、邱瑞敏、王永强、刘耀真,均属1965年甫告成立的“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新成员,夏葆元、赖礼庠、严国基被分在别的单位,不知他们三位是否参与了那次淮海路行动?那次行动不是“全国美展”而胜过“全国美展”,不似“行为艺术”而胜似“行为艺术”——“文革”飙起,权威靠边,舞台空出,新人登场,我所见证的淮海路一幕,便是以上画家从上海美专60年代本科预科结业后首次出动的大场面。
三十六年过去了。那段墙面早已拆除,种满鲜花,竖起欧美时装广告牌。今日申城画家与70年代沪上油画精英群经已隔代而隔阂,几近形同陌路。大家还记得他们、说起他们么?我不愿忘记,因他们都是我的好老师:在没有艺术学院的70年代,他们影响了上海滩所有向往油画艺术的青少年。
我现在要来说起他们。那是上海美专校友们的集体记忆,也是我私人珍藏的青春记忆——此刻我不知是在怀想长辈抑或回望一群年轻人:70年代初,他们在我眼里都是气宇轩昂的“大人”,现在想来,他们当时的平均年龄不过二十五岁上下,真真年纪青!
只是从何说起?从哪位说起?
民国沪上文化盛世的种种风流,前些年出书出刊,闹猛过了。倒是要来还原70年代上海文艺的真情境,反而很难:日新月异的上海滩仿佛自有一种集体的默契,存心失忆,大家不说起。纳博科夫有本书题曰“说吧,记忆”,是的,谁没有记忆。这本关于上海美专的纪念册恐怕多有讲述吧,此刻我读不到,而很早以前我就想清理自己的记忆。
好像是在经历淮海路“油画震撼”的翌年,我最先望见的创作出自赖礼庠,原作高悬在大光明电影院——何以是大光明电影院,不记得了——画题似乎是“湖南农民运动”?只见画中红旗横向飘扬,两侧密集排列的暴动队身佩刀枪,杀气腾腾,正中间,毛泽东本人阔步走来……两年后,我有幸混进上海美术馆边厅蹭在赖礼庠身后,原来他是位中山装笔挺的绅士,语带微笑,斯文透顶,墙边靠着他刚完成的一幅油画,画着一位慈祥的老工人,而刚刚被所谓“工人画展”主事者当场拒绝。
人群中,当年在野油画新秀汤沐黎单膝跪下凑近细看,再三再四审视画面,然后发问:“那么赖礼庠你说说看,你这块红布用了几种红?”
作者笑而不答,汤沐黎:“玫瑰红?朱标?锌钛白?”作者仍然笑而不答。多年后在西方博物馆眼见文艺复兴经典,我也弄不明白那使目睛略微晕眩的暗红色如何配置:想起赖礼庠,想起汤沐黎。
没有杂志、没有媒体、没有电话、没有网络,那年月所有消息不胫而走——下一波“油画震撼”是在1971年,我已是一介知青,从赣南山沟流窜回沪,立即得知上海滩头条“油画新闻”:根据1969年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政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重点组织创作同名油画系列,严国基画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陈逸飞画第二乐章“黄河颂”、夏葆元画第四乐章“黄河愤”……消息确凿:“黄河”系列的创作地点就在外滩附近的《解放日报》社。
当年的报社岂能随便出入?当年的创作岂是未经审查而能公之于众——江湖画友或则看过,或则没看过,或没看过而说看过的,或看过了而说不像样的:有说夏葆元画那钢刃的闪光全部使用刮刀,皮肤的颜色居然掺了群青与钴蓝,有说陈逸飞画面上稀薄的部分得见布纹,厚堆的部分干脆破开颜料管直接挤上去……我迷失在各种口传版本中,心事重重,望眼欲穿。
此情此状如今真不易说得周全。日后我在书中读到昔年印象派小子群相窥探德拉克罗瓦一静一动,新作甫出,争睹为快:原来人同此心!而在同一世代,同一城市,年轻人瞻望年事稍长的名家,翘首企盼之状,诚哉心同此理:1971年前后,上海与全国因“文革”暴乱中止油画创作长达五年,虽说谁都知道那时的油画无非政治宣传,但众人渴望一看,更兼作者啼声初试,耸动其事者大有人在。再者,上海美专生尚且60年代得以亲见民国前辈些许原作,盛大苏联油画展也曾来过上海,到了扫荡一切的70年代,我辈长大成人,初涉油画,眼界未开,于是“黄河”系列之出,非同小可——那真是我们平生头一回遭遇同代人的大创制!
这份心思,今时的少年或能有所同感么?

《黄河愤》局部,夏葆元,1971年。这幅大画从未展出,也未发表,却是我辈少年时心目中最重要的油画创作。
不记得是在当年还是翌年,忽一日,经由大师兄徐纯中慷慨引领,我做梦似的登上《解放日报》老式殖民建筑的石砌楼梯,站在“黄河”系列大画布前……文字是无力的,我放弃描述。是什么使一组作品显得重要而神秘?端看它何时诞生,以何种状况被看见,还有:被什么人看见——真好比《红灯记》歌词“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那年我将届十八岁,心中唯有一念:我也要画大油画!
“黄河”被撤销了。1972年形势逆转,中日建交。除了1977年北京全军美展接纳了陈逸飞的《黄河颂》,其他几幅从未面世。70年代初,画坛中老年权威悉数靠边,创作局面原已万马齐喑,此时有“黄河”系列出,本该是上海乃至全国油画创作的重头戏,那年,外地油画家群曾为此专程组团来沪,寻看受阻,竟在报社街区坐地不去,有如抗议——就在我进入报社那一天,我结识了夏葆元。
时风真是大变了。今日人在官家而正当走红的艺术家,会无事人一般与陌生家伙随意说话么?我看见如今校园里十七八岁的艺术考生像被驱使的草狗,美术界三流角色也懒得搭理年轻人——那天夏葆元眉目英俊走过来,额发飞扬盘旋,“吉人之辞寡”。他仔细看过我递上去的农民素描头像,友善地打量我:
“萧传玖。你学萧传玖,要看尼古拉·费申。”
说来,这也是隔代失传的风习了:江南沪地绘画圈彼此看画从来词句精当,不套术语,不作兴学院腔,如今却是湎于兀谈而言不及义了;尤可贵者,美专才子及美专老师如俞云阶、孟光、张隆基——日后我有幸当面请教这几位老师的老师——他们与晚生、初习者、无名画家面见接谈,总是言笑生风,如晤友朋,从不作施教状。此后我与葆元熟腻,他给我画像,我给他画像,得意之际,免不住话头里寻着机会问问他:你看我画得怎么样?
葆元偏头想想,只一句“任伯年”。这话说得多好呢:抬举夸奖,诙谐的警告——任伯年善画,然而是能品,而葆元这样说,意思是相信眼前的瘪三能够听懂他的话。

左图:葆元为我画的炭笔素描肖像,1976年,原作已遗失。
右图:中坐着深色衣服者是上海美专时期的青年夏葆元。摄于上世纪60年代。
什么是性情教养,我以为这就是性情与教养。上海美专毕业生虽则全都画着造反年代的革命画,却是平日里一派斯文谦和,看过去非常之“上海”。上海所谓“老侠客”怎样气质呢,葆元便是,只不过他当时太年轻,而我竟至于从此走路甩手有意无意模仿夏葆元——同年我结识了刘耀真,耿介有礼,行事说话一点不晓得敷衍,今时想来真好比张爱玲时代的女书生。她看出我辈与她周旋恐怕是为认得魏景山与陈逸飞,于是爽然引见,同时结识了邱瑞敏与王永强。
奇怪。这几位才俊个个生得一表人才好模样,年纪青青,待人真心,一次见过,就说“下次来白相”——那时“油雕室”位于瑞金路长乐路,全上海迷油画的小青年对那里是个个望之沮丧而心心念念——我就日后经常去“白相”,好比小阿弟弯到隔壁弄堂面见大兄长,彼此招呼过,他们便手里停下来,对着画面说是“看到哪里不舒服”就“讲讲”。我有什么资格呢?然而那时的画家请教成风,彼此都诚恳。邱瑞敏一向谦和,谁提句意见他就认真想。我曾临摹王永强一沓炭笔素描的黑白照片,说给他听,他竟脸上红起来,大叫难为情;魏景山更是不能夸,他会害羞退开,站在边边上。那年他画一位火车司机,落选了:革命火车头怎能通篇黑气呢?面色白皙的魏景山全不知怎样弄虚作假、“主题先行”,他不过借个画题有滋有味画油画,画中央那青年司机一双污黑结实的大皮鞋,正面透视,形色交织,简直北欧的哈尔斯,众人前看后啧啧称奇,他管自笑笑走开去,一脸标致,真是有教养。
1972年,“文革”后首次全国美展揭幕北京,影响之大,我们这些半吊子油画草寇从此想入非非要来摆弄所谓主题大油画——陈逸飞魏景山合作的《开路先锋》获选进京,初件运走了,两人复制一件挂在南京路上海美术馆,观者如堵。我为看清为首工人腰间那枚铜吹哨,周围拥挤,心里崇拜,汗淋淋几乎对不准目光的焦距—陈逸飞,戴副眼镜,众人堆里似乎数他最年轻,不记得怎样一来,已是他带着单位的同仁到我家里来“白相”,每次人在楼梯口就一迭声连名带姓叫上来。日后他左右逢源摊子铺得开,原是天生忙碌会办事,那时他就头绪多,帮这个买把小提琴,忙那个联络调回来,我后来赣南乡下混不开,也是逸飞几句话荐我找人帮帮忙而有后来流窜苏北一场戏,到得江北,我好像也只送袋花生米算是谢谢他。那时我能看到世界名画集,便是他特意领进单位图书馆陪我看,结果两人张冠李戴错把克里姆特当成女同志……《黄河颂》之后,陈逸飞的年少气盛之作是巨幅双联画《红旗颂》,气势宏大,呕心沥血,也被官家所否决,出不了油雕室的门,直到1996年上海举办所谓“现实主义回眸展”,我才见《红旗颂》正式挂在墙面上,想起当年油雕室壁角里有个家伙全身披挂旧军装,挎着冲锋枪给他画,一站就是好几天。那时逸飞画画好认真,1976年他与魏景山雄心勃勃接手北京军事博物馆《占领总统府》大订件,前后折腾一年多,为了捉摸红旗怎样飘,不知哪里借来庞大的鼓风机,通上电源,对准红旗使劲吹。钢盔枪械子弹壳之类更是从远郊军区借来一大堆,与魏景山两人勾头耸肩爬在木架上,一五一十描质感。
那年陈逸飞仅止二十九岁。我今在学院奉命招收所谓博士生,告诉“博士”说:三十好几还来啃外语、诌论文,休想沾得了艺术的边——当年上海美专小青年出身顶高是本科,陈逸飞不过预科班,然而青春无价,才华不等闲,他们是二十岁出头便在画布上一仗一仗打过来。如今市面上或有瞄着陈逸飞不服气而说闲话的,闲话说过,请哪位说者自己也来一板一眼从头做做看。
葆元、景山、逸飞、礼庠……他们的创作上海滩上几次三番遭批判,还要被否决。被谁否决呢?几十年过去,现在这陈年公案可以索性说说穿:面上是当年官家的“左”,内里是美术同行的“嫉”:因名头、年龄大于上海美专的浙江美院有一派,60年代毕业后大抵占据“文革”时期沪上美术机构的好位置,瞧着上海美专才子有声有色蹿起来,心里阴暗而手里有权——这类同行暗算的老把戏,说来不足道,只是葆元逸飞当年的声名因此很奇怪:既是官方一流“正角”,又是极“左”年代的“落选英雄”,既是“文革”作品的当然作者,又是勤习苦练的技巧主义者;他们的素描习作被拍成照片到处流传,既是“地下”的,又是“公开”的——其时美术圈“习作”成风,大家一天到晚画素描:下笔要肯定,造型要精确,线条要潇洒,总之,迥异于当年形制粗糙的“工农兵”素描,其况味,介于德加、门采尔、柯勒惠支、谢罗夫,隐约间还有北欧的佐伦……70年代真有那么一种“上海式”素描,似乎天然地自外于“文革”的主流与教条,以致我们对外地的素描嗤之以鼻。实在说,当年有谁不曾以炭笔写生,而写生者有谁不曾苦心习染这种“上海素描”风?有如“非典型传染病”,被重点传染者的上海画家不计其数,我所熟识的有吴健、赵渭凉、汪铁、许明耀、汤沐黎、夏予冰、韩辛,还有一个我——除非70年代出生的一辈,即便今日,上海画圈子里谁不知道这素描的源头始自夏葆元?
多年后我在江浙、中南、北方,甚至新疆西藏的青年画家那里意外发现夏葆元素描模糊不堪的黑白照片,显然被几度翻印,传看再三,临摹再三。当我北上就学,中央美院复出任教的林岗、靳尚谊与朱乃正都曾向我说起:你们上海有一位夏葆元。如今堆在书店里的素描范本也叫作素描么?为什么没有上海美专两代师生的素描集?为什么没有一本个人素描集,作者名叫夏葆元?
许多作品从未面世,并非仅止“文革”的禁忌,而是当年大家画画只为真欢喜,哪想到可以据此又评职称又换钱——魏景山曾在1975年前后自去拉萨,之后安静地给我看四十多幅场景写生,技艺卓越,自信而风流,与善画西藏的吴作人董希文相较,另备一格。其时我尚未有西藏行,日后初履高原,心里追念那些画,手下学不像。近时在纽约饭局向他问起,他唯淡然说“不晓得放在哪里”,说时,同样害羞而无所谓。夏葆元,形迹潇洒,忧郁而俏皮,众人笑谈,他常是优雅沉默,腼腆机警,间或嘴里弄出轻微的声响,我也竟想学,可惜学不像……游荡江湖岁月荒荒,葆元的信寄到了,有一信曾使我怎样的感动:他在末尾写道,“请不要因为我的夸奖而骄傲起来”。他职事“工艺美术研究所”,委曲十多年,不给他机会画油画,自《黄河愤》之后无事四出,画画素描,随画随送不介意,最多的一次,一日连画九幅。素描之于葆元,宁是一种沉默的方式,无所谓“基础训练”,无所谓素材累积,不过是才气与“白相”。70年代末“文革”收束,葆元与林旭东连手绘制鲁迅及老舍小说黑白水粉连作,画意雅隽,至今仍有圈中人佩服之至,不能忘怀——我但愿并不为葆元的私谊而夸张记忆,日后我不再忠实仿效他,因无法仿效的是才气,可是谁不曾追慕过值得仿效的人物呢。
而美专才子知己知彼。“文革”晚期陈逸飞一度猛画素描,整开纸,沉甸甸抱出来给人看。其时他的声名已然超过美专老同学,尚且修心养技不懈怠。那天我们从西洋比到国中,此人说到彼人,马路上骑着自行车大谈怎样才是好素描,逸飞忽然说:
“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学夏葆元。”
是的,我记得那一刻,夏日迟暮,我们在林阴道中边骑边谈,路过普希金铜像那一带。
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陈逸飞、邱瑞敏尚在沪上,见著于沪上,其余油画才子早已风流云散:赖礼庠、魏景山、夏葆元、王永强、刘耀真、严国基先后定居大洋彼岸,前数年国基逝世了,而最早的移居者离去上海超过二十年——“文革”初期那一天,阳光透过淮海路梧桐枝叶照亮他们年轻的背影,斑斓耀眼,如今,他们的平均年龄将届六十岁了。他们昔日的声名因“文革”而起,自亦以“文革”的枉然一空而被沪地所淡忘;别无选择地,他们只能事奉当年的政治宣传,然而他们有才气——论才气,论品质,若非言过其实,上海美专60年代毕业生远胜今日学院的许多专家与名家,一如样板戏的要角实乃建国后不可多得的英才。他们是幸运的,而他们也可惜:生逢其时,得逞其才,才不逢时,则不免随时势所消损。此后生逢其时的新人物今已遍在上海,而上海的美术界应该记得上海曾经有过的人物:民国沪上的西画盛世,不说也罢,要说日后好好说,值此“上海美专”建校纪念,我以校外的晚辈,为文追述这所学校的教育功德、教育有方,感谢这所学校为上海培育的好人才。
而人才的“人”,人才的“才”,可遇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遇:上海美专虽则规格平平,命途短暂,分明地处上海而被上海的时势所委屈,说来,不是区区美专不配上海之名,乃是上海素称人杰地灵之名而委实对不起美专,以致近比浙江美院、远较中央美院,势不均而力不逮。然详察当年上海美专师生两代的资质,其实蕴蓄牵连着民国沪上的教育水准及人文余脉,虽为时所抑,终至消散,尚远非今日艺术院校种种“加大力度”的所谓教育措施差堪比拟。近二十多年,沪上美术学院增至四所之多,就学毕业的人数何止百千,较之昔时,有才之“人”多寡?育人之“才”若何?可以开另一话题——我今眼看艺术学生喜获种种学位,总觉得那是公然的谎言:今时的孩子果然得到像样的艺术教育么?而我每填写履历中所谓“自习绘画”,也其实迹近谎言:“文革”十年我们无缘上学,但我分明师从上海美专的才子们,有样学样,耳濡目染,一路言笑十多年。
谨愿这篇文字不涉过多的情感与褒誉,谨愿这群上海画家集体归返他们本该在上海岁月中轻重得宜的位置。美专的诸位良师恩师,必有弟子心里记得,美专别种画科的俊杰,亦自有其他俊杰说起。以上几位油画家的种种精彩是我个人的交代——整个70年代,我竟糊涂到从未与他们站一块儿拍张照片留念想。如今我每念及上海,就会想起他们,念及他们,就会想起上海。
2004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