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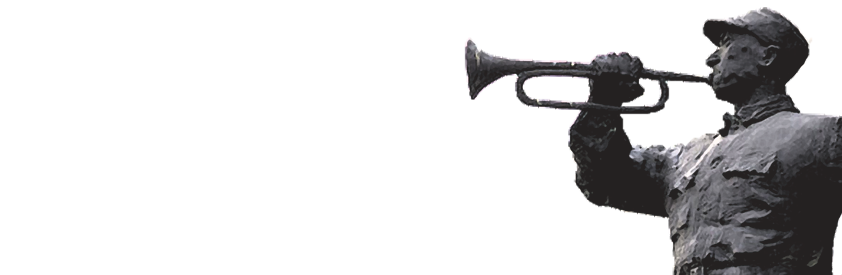
我们见到的飞机种类,不可算少,但还从来没有见过披挂红布条的飞机。那鲜红的布条衬着碧蓝色的天空,拂着云彩,御风而来,确实标致而新鲜。那是一架日本投降代表的飞机,这些压迫我们五十余年,侵我国土十四年的敌人,来芷江接洽投降事宜。
我们有六架野马式驱逐机去警戒这架挂红布的降机。空军第五大队十七分队队长林深先、队员许志俭、二十七中队队长周天民、队员娄茂吟,美国队员葛兰芬、乐威等六个幸运儿去担任这个任务。10时5分,这六架野马已经在常德上空盘旋着等待了。绕了三圈,周天民先在西南方向、洞庭湖上空五千英尺高度左右发现了一个小黑点,一摇翅膀招呼僚机娄茂吟看那架似曾相识的机子,那是一架九七式双发动战斗机改装的运输机。驾驶员兴奋起来,一推头冲到那机旁,打开照相机,对着挂红布条的飞机拍了一个优美的姿态。
日本降机找错了目标
驾降机的那位日本驾驶员,他过了溆浦以后,根据他偷袭的经验,到芷江是沿江而飞的。然而这次,他的神经太紧张了些,把洪江误认为是芷江,当他到了洪江的沙湾机场时,以为就是芷江机场了,作下降姿态。降到一千英尺了,周天民在交叉飞行中间,还能辨别方向,知道他飞错了,急忙摇翼示意,降机犹未知觉,他就冲到降机的驾驶舱前去伸手比了一个310度的转弯,才把他转正了方向。
降机绕圈子到芷江来,将多花二十分钟的时间,这可急坏了机场等候的中外记者和机场外边的千万观众。五大队又派了三架野马式战机去迎接。
11时30分,这一机群到达了机场上空,周天民往机舱外探望了一下,喊了一声:“好家伙!有这么多人呀!”他在指挥降落的地点俯冲了一下指示降机降落,周领着他的僚机先行落地。这架两翼尖和尾端挂着三条四公尺长红布的飞机,就在千万人仰望的五十英尺低空绕机场飞一周。有人还颇欣赏那架机子的美观,那绿花斑的机身,绘着红太阳,飘着红布条。

在日军投降代表的座机降落之前,首先抵达芷江机场上空的是中国空军的野马式战机,中国战机一出现,期待已久的机场军民一片欢呼雀跃(约瑟夫·德 / 摄)The Mustang of Chinese Air Force flew to the sky above Chihkiang airfield before the Japanese surrender representatives’plane. At the sight of the Mustang,waiting people in the airfield burst into hurrah. (Photographed by Joe Day)

过了一会儿,徐徐到来的是第二架战机,即日军投降代表乘坐的双引擎运输机(约瑟夫·德 / 摄)The second fighter,which the Japanese surrender representatives took,arrived. (Photographed by Joe Day)
机场警戒是美国宪兵,接待日代表是中国宪兵。降机着陆以后就滑行到指定的地点,记者群和中美空军人员似潮水一般地往那边拥挤去。美国宪兵大声呼叫着,维持了一条仅可行一部吉普车的狭小人巷。摄影记者则挤在一起,等候车子到来。

原国民党新六军第十四军司令部的少校作战科科长王楚英回忆:
8月21日10时左右,我空军中尉周天民等驾驶三架野马式战斗机(P51型),在洞庭湖上空西北方向发现一架带有红色风幡、机翼上下漆有日本国旗的飞机。当证实确系日方洽降代表乘坐的飞机后,三架野马式战斗机遂分列于日机前后引导其向芷江飞行。
机群到达溆浦县城上空,本应沿洪江西飞,可日方驾驶员在途经洪江湾机场时,误以为已经到达目的地,准备降落。周天民断定日机搞错地点,先摇动机翼,又盘旋一周,以手示意,日方驾驶员才由中方飞机领航,向芷江机场飞去。
1945年8月21日这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一大早,王楚英就和其他几位负责警卫任务的同志,驱车到芷江城各处巡视,检查今井武夫住处的接待准备和警卫工作。那天芷江城到处彩旗招展,扎有巨大“V”字的牌楼矗立在城门口和主要道路上。沿机场到城内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并排站着武装宪兵和新六军士兵,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芷江的军民在晨曦中即群聚街头,欢庆抗战胜利,都想亲眼看一看日军投降的场面。

日军运输机进入机场跑道,缓缓行驶(约瑟夫·德 / 摄)The Japanese Mitsubishi arrived. (Photographed by Joe Day)
首先落下来的是周天民的飞机。周天民的飞机一降落,机场外人群沸腾了一阵,有人放鞭炮,不少人还把自采的野花向中方飞机方向抛去。第二架落下的是今井武夫乘坐的飞机,王楚英当时忙着警卫,没注意群众反应。但事后很多人告诉他,当时围观群众纷纷向着日方飞机方向吐唾沫,扔鸡蛋。
日本的飞机停稳后,王楚英站到了飞机舷梯下。机门打开,陆军总司令部陈参谋上前迎接。今井武夫身穿黄色夏季日本陆军制服,佩少将领章,立于机门旁,立正向陈参谋询问:“我可以下来吗?”陈回答:“全部下机。”
今井武夫的声音,克制中有些不屑。王楚英心想:“投降了还这么牛气?”王楚英说自己是强压胸中的怒火,紧盯着今井走下飞机。
直到今井将佩刀呈给中方时,弯下了腰,王楚英才松了口气。“他总算还知道他们失败了,是来和我们商议投降事宜的。”
今井一行依次下机,并排肃立在舷梯旁,接受陈参谋查阅名单和证件,并由宪兵检查随身行装。检查完毕,中外记者纷纷摄影,今井默然无语,神态忧伤,举止呆板,任人拍照。

魏鸿祥1944年9月参军到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特务团机枪一连,1945年1月提升为准尉特务长,4月参加了湘西会战,8月被抽调参加芷江受降典礼筹备处,负责会务工作。《我见证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刻》回顾了当时的场景:

日军飞机抵达之后,飞行员操作飞机停靠妥当(约瑟夫·德 / 摄)The Japanese Mitsubishi landed slowly. (Photographed by Joe Day)
芷江受降时,我在芷江受降典礼筹备处,参加会务工作。
1945年8月21日,芷江机场秋高气爽,碧空万里。上午11时,机尾系着长长的红布条标志的日本降机,在几架中国军机的偕行下缓缓降落。瞬间,数千名中美官兵、记者蜂拥而上,有的拍照,有的撕扯红布作为留念。
布满弹痕的日本降机缓缓打开机门,日本降使日军驻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出现在机舱门口。早已等候在机门前的陈应庄和陈昭凯上前询问今井武夫。
这时我突然发现,一直领导我们“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筹备处”的国民党新六军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和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陈昭凯上校,都换成了少校军衔。后来我才知道,考虑到军衔对等原则,陈应庄和陈昭凯奉命在接机前换上少校军衔。
陈应庄先核对日本降使机组人员的名单,随即检查了他们所携带的五只皮箱。随后,日方人员在陈应庄的引导下,分别坐上四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在宪兵的监护下,驶向了位于潕水河畔的七里桥会场。
在从机场前往会场的十多公里路上,挤满了前来观看的群众。人群中,不断有人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争罪犯”“血债血还”等口号。尽管有宪兵把守,但人群仍然不断拥向路中间,阻挡车队行进。汽车就这样开开停停,走得很慢。


有的群众发现无法接近日本人,干脆从地上拣起石块砸向他们,很多石块打在吉普车上“叮当”作响。宪兵进行制止时,老百姓就骂道:“你们还保护他们?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呀!”
这时的今井武夫一行由刚下机时的面无表情,变成了面带戚容、脸色惨白,犹如过街示众的囚犯,今井武夫高昂的脑袋这时也略微低了下来,与其随行的人员更是把头沉得低低的。我想那一刻,他们感受到中国人对侵略者的憎恨。这段路程对于我们来说太短,但对于日本降使来说却太长。

当时重庆《大公报》记者顾建平的《芷江观光》记载:
昆明记者一行,21日下午以两小时的飞航赶到湘西的芷江。飞机抵达机场时,将近日暮,第一眼看到的,便是机场靠东的一边已经停着一架绘有旭日旗徽的中型飞机。
其时,天阴,雷雨忽作,我们正在避雨,看见有吉普车四辆结队驰来,上插一尺见方的白旗,在我宪兵监视保护之下驶至敌机旁边,我们以为他们将要起飞离境,冒雨前去看看这群接洽代表的神色嘴脸,盟军多人亦跑来“观光”以后,才知道他们当晚将宿于芷江,不拟飞回,特来把飞机内外照料一下。他们最后拿出三大块浅绿色的油布,蒙盖飞机的发动机部位。在蒙蒙细雨之下,爬上爬下工作着,任我们将他们摄成照片与电影。

1945年8月21日11时15分,战败国代表,也就是日本的投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及其随从,乘专机到达湖南芷江机场,来参加历史性的签字仪式At 1 1:15,August 21,1945,representatives of the defeated nation Japan,i.e. Deputy Chief of Japanese army in China,Brigadier General Imai Takeo,and his companions arrived at Chihkiang airfield in their Mitsubishi plane to attend the historic signing ceremony of surrender.
敌机为绿色,从油漆的痕迹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原来是银色,临时加以涂饰,前部两面各用黑色着“六力式”的日文,翼下系着宽一寸的红绸长条。但只余左翼的一条。尾部右翼的红绸均被美军剪去,大约分作纪念品。这几个日本人身穿旧的草绿色军服,足踏黄色五成新的长筒皮靴。其中两人蓄着道地日本式的小胡子,黄昏时分,他们在雨中仍乘坐插着白旗的吉普车驶回在空军总部为他们特设的宿舍。
芷江,是敌军三个月以前对中国发动最后攻势的目标,想不到三个月以后的今天,这雪峰山西麓的边城,“终于发现了敌人”,而这八名“皇军”却不是来“占领中国空军重要基地”,乃是代表全部在华的日军向中国接洽无条件投降的。
八个日本人,今井武夫少将、桥岛芳雄中佐、松原喜八少佐、前川国雄少佐等,昨晚向我们表示,日本虽被中国战败,但并不仇恨中国;中日是“同文同种”,“都是亚洲人”。他们把“中日亲善”的旧套重新搬出来,背得那么熟练,说得那么甜蜜而肉麻,叫人听来却是那么可怕。他们说:“日本的陆军没有战败,打败仗的是海军、空军和工业的无法追上美国,美国的原子弹尤其不讲人道。”他们又说,驻华日本的武器可以完全而且完整地向中国缴出,决不破坏,可惜精锐的武器多不在中国云云。
他们临睡以前,问我方有没有给他们预备拖鞋,另,他们都没有带蚊帐,要求借几顶,免得回去打摆子。但是我们事先并没有为战败国的日本代表想得这么周到。

通讯《芷江——国史上第一个受降城》记载:
8月21日的早晨是晴朗的。芷江在欢喜中醒来,这个筑在水两岸的小城,人口不足五万,向来很少受人注意,湘黔公路筑成后,它才在西南交通网中占一个位置。但自从去年美国在此地建筑了飞机场,今年4月它又成为敌人进攻目标,知道它的人就渐渐多起来。然而,它被选为接受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的地点,却是它梦想不到的光荣。
家家户户挂起国旗,在公路进入街道的地方,搭起了彩楼,上面四个大字“胜利之门”。潕水大桥上,柏枝在两边桥栏饰出许多“V”字,桥头又是两处彩楼,一边是“正义大道”,一边是“和平桥梁”,城中警岗所在,立着五级的柏枝宝塔,警察在下面踌躇满志地指挥行车,墙上面处处红纸国语,充满胜利的喜悦。人人都在说着,日本投降代表就要在城东的机场降落了。
这是一所广阔的机场,有宽阔的跑道,跑道间长着很茂密的丛草,经常有几十架飞机停歇。今天早上9点钟,场上的站房附近,已经等候着许多人,成百部吉普车,还有许多别种式样的军车,排列在路边,更多的车还正沿泥泞道路驶来。
热情的美国人,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从各地赶来,机场上几乎全是他们,受降的念头教他们高兴,他们急于想看见骄妄残忍的敌人怎样吞下这一颗自作自受的苦果。但是,他们不会完全懂得这次受降的意义吧!这是中国人民八年多来血泪的收获。它所带来的希望和欢喜,和它所带来的问题与戒慎,怕只有担负了战争的全部重担的中国士兵和农民才能充分领会。
而且,这次受降完全由中国方面主持,美军只站在一个顾问的地位。中国方面愿意把典礼弄得简单、严肃,乃至冷淡的程度,握手、军乐、欢呼都是不允许的。其实,何总长前一日晚间已经到达芷江,四个方面军的司令也都来到,第一招待所里充满了星章的将军,但来接待日本代表的是一位少校,此外仅有师管区的郑司令和担任警戒的新六军的团长,中国方面的人显得特别少,只有警卫的士兵,冷然握着枪杆站立。他们代表中国的士兵、农民,在这次受降中充当真正的主角。

中美盟军正在现场指挥车队的交通秩序,安排每一辆车的乘坐人员(约瑟夫·德 / 摄)China-US Allied Forces were directing the motorcade,arranging passengers for every vehicle. (Photographed by Joe Day)

日方投降代表和中美迎接军官先后上车,中国军队用插有白旗的吉普车,运载着日本人,绕场一周之后,前往会场(约瑟夫·德 / 摄)Representatives from both Japanese surrender troops and China-US Allied Forces got on the jeeps. Japanese surrender representatives sat on jeeps with white flags. After going a circle round the airfield the jeeps moved forward to the Japanese surrendering hall. (Photographed by Joe Day)

日军受降代表着褐色军装坐在吉普车第二排右座(约瑟夫·德 / 摄)A Japanese surrender representative in brown uniform sat in the right seat in the second row. (Photographed by Joe Day)
记者团聚在指定日本代表登车的地点。两辆为他们准备的吉普车上插有白旗,挺引人注意。摄影记者急于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到处攒动,和中国的警卫弄得不大愉快。
10时才过,四架飞机在东方出现,来到机场上空,一架是盟方银色战斗机,一架是深色的双引擎机,翼下清楚地漆着两个太阳徽。人群开始骚动。八年来它一直是残忍和狂妄的象征,一年前它们还满载炸弹来到芷江,今天它载的却只有屈膝。忽然间一架战斗机顽皮地从高空对准日机冲去,又巧妙地掠过了机头,引起地面上一片愉快的哄笑。
……
日本代表也带着矜持坐在车上,只有桥岛不时左顾右盼。车开动了,第二辆车如约开到记者群前面停下,顿时镁光横飞,一片照相机的响声,谁都怕这三分钟去得太匆匆。一位少将带了个相机预备照,看见司机不耐烦的样子,怕他不守约,放弃了自己的机会,过去拿钟看看时间,一直到整三分钟才放走那吉普。这时候没有一个日本人动弹一下,全都挺直地坐在车上,眼光下垂,只有那中国司机不愿意地掉过脸去,避免把自己跟这些沮丧的形象摄在一起。
三分钟后车辆开向不远的空军总站去,日本代表的住所安置在里面,给他们最简单的食宿,外面安下三道岗卫,没有特别命令,谁都不许进去。
……
到下午三时半,今井就到七里桥中国陆军总部(前为空军四大队队部)谒见萧参谋长毅肃。总理遗像面前中间坐着萧参谋长,右边冷副参谋长和中国译员,左边是美军柏德诺准将和他的译员。陈少校引今井步入会议厅,今井面对萧参谋长行了一个鞠躬,萧参谋长并未起立回礼,今井坐下后,桥岛坐右,前川坐左。摄影记者又蜂拥而前,闪烁着镁光,有一位美国摄影记者,拿着镜箱,以临进之紧张姿势,挨近今井面部拍了一个特写镜头,颇觉潇洒。

李英记载了采访芷江见闻:
1945年8月20日上午,报社派我和陆铿去湖南芷江采访日本受降仪式。我们到了那里才知道受降仪式的地点改在9月9日的南京,芷江只是中国政府命令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他的代表前来听候指示的地方。
21日上午10时,由美军飞行员驾驶三架F-47战斗机飞临洞庭湖上空,监护冈村宁次代表今井武夫副参谋长一行乘坐的飞机。
我们赶到飞机场,只见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好容易才挤进采访棚,刚坐下不到十分钟,就听见隆隆的机声由远而近,今井武夫乘坐的飞机出现在芷江的上空,绕场三周,一则表示对中国军民致意,一则向地面请示:是否准许他们降落。临场指挥官命令侍从从地面发出准许降落的信号,日机才徐徐降落在芷江机场上。

今井武夫等人下机检验身份后,前往指定的帐篷休息。今井武夫(前右二)身旁为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外交部人员邵毓麟、舒适存等After authentication,Imai Takeo and his companions went to have a rest under the tent. Imai Takeo (second from right,front row) sat with Deputy Chief of Chinese ground forces Leng Xin,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ese Foreign Affairs Department:Shao Yulin and Shu Shicun.
日机一行八人,除今井武夫外,尚有他的随行人员: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国雄,翻译木村辰男等等。
舱门打开后,木村辰男首先出现在舱口上,他先向中方的翻译官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然后恭敬地问:“我们可以下机吗?”中方翻译官指示他们:“经中国宪兵检查后可以下飞机。”戴钢盔的中国宪兵进机舱检查后退了出来,今井武夫才率领他的七个随行人员垂头丧气地一个个下了飞机。这时,两辆插有白旗的中型军用吉普开了过来,八个受降使者上了汽车,中国司机驾车绕场一周,这时机场上的中国人群情激愤,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严惩日本战犯!”“中国人的血不能白流,血债要用血来还!”
今井武夫已经再也没有昔日趾高气扬的神气,一张脸绷得像死人的脸,站在车上,冷汗直流,身体发抖,不住地用白巾擦额上的冷汗。
尽管今井武夫肩佩少将军衔,身着草绿戎装,脚蹬马靴,曾努力撑着想不失日本极右军人的骄横,但在这时却再也撑不下去了。
说起今井武夫,中国人并不陌生。1918年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长期在日本参谋本部工作,任过日本驻华副武官,参与策划成立汪伪政府,他万万没有想到也有今天。
吉普车把今井武夫一行八人引到临时搭建的帐篷内休息,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及外交部司长邵毓麟,命令他们的随行人员,验明今井武夫八人的洽降代表的授权证明,才又送他们至住所听候指示。
当天下午3点,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正式接见今井武夫一行,向他们发布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指示。
接见会场设在离芷江市区约五公里外的陆军总部。主席台正中萧毅肃神情肃然,萧的两侧坐着中美代表,台下两侧坐满了从重庆、昆明、成都等地飞来的军政官员及新闻记者。
我见今井武夫和他的随行人员神色沮丧地走进会场,立正,向萧毅肃行九十度鞠躬,然后如同面对上级长官似的挺直地站立。

吴其轺1918年出生于福建闽清,1936年,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学习。学校没有固定的训练场所,学习生涯无异于一次长征。他和他的同学们从杭州一直走到了昆明,由于条件限制,吴其轺并没有受到多少专业飞行训练。1941年毕业后,他被编入中国空军第五大队,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驻守芷江机场,军衔上尉。“芷江”这个地名在吴其轺的生命中有重要的位置。湖南省芷江县,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城,因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曾经保护和锻造了中国空军的有生力量;曾经给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提供机场而名震中外。
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作降使到芷江请降。吴其轺接到命令,随中队长张昌国中校前往岳阳上空押解降使飞机。上午10点50分左右,吴其轺在洞庭湖上空发现一架飞机向西飞来。不一会儿,能清楚地看到这架飞机的机头机尾悬挂着长长的红布条。
此时,张昌国通知:目标出现。接着,中方四架飞机都将机翼摇动,向日机发出信号:我们是来押解你们的,而非打击你们。吴其轺驾驶P-51战斗机,跟随张昌国在靠近日机时,拍了拍飞机头,用大拇指向后指了指,表示跟我们来,日机跟着吴其轺和战友们驾驶的飞机向芷江飞去……上午11时11分,在吴其轺和战友的押解下,日机循芷江上空绕场三周,向中国军民赔礼、道歉、乞降。11时25分飞机降落。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的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低头走下飞机。
今井武夫在满脸铁青的中国军人的示意下,摘掉随身携带的军刀,交给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日本军人无一人随身携带枪支和弹药。
美军援华空军给日本军人代表准备了从机场到洽降驻地的军用吉普车。吉普车的右方插着白色的旗子……
下午3时20分,中日两国在芷江举行洽降会谈。中国战区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将四份备忘录交给今井武夫,今井武夫签署了备忘录的收据,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部署图……
“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 芷江受降,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洗雪百年国耻,抵御外敌入侵首次胜利最后的一页。

抗战老兵史文召回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亲历:
8月21日快晌午时,芷江飞机场上空像打雷似的,好多架中国战机转来转去,其中一架首先降落。不一会儿,一架涂着“红膏药”的日本大飞机落了下来。飞机前头挂着白旗,尾巴后拖着长长的红布条。据说这是事先命令日本人做的记号。紧接着,又有两架中国战机降落。“红膏药”上下来的是日本代表,有七八个光头鬼子,领头的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特务头子今井武夫。挨个儿被检查后,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躬着腰从神气的四十团官兵面前走过,上了同样挂着白旗的汽车。白旗就跟招魂幡一样,日本鬼子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他们是来乞降的。日本人后来说得要好听些,叫洽降。下午,中国代表萧毅肃参谋总长、冷欣副总长等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第一至第五号交给今井武夫。备忘录具体规定了中国受降日本投降的事项。第三天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召见了日本乞降代表,命令日本在南京签订投降书。

日军投降代表乘坐挂有白旗的吉普车离开机场Japanese surrender representatives,Imai Takeo and his companions were on the way to the building where the treaty was to be signed.
日本代表走时,头勾得更低了。真是大快人心!

严怪愚的《芷江受降侧记》回顾:
12时11分,日机飞临芷江上空;20分,驶向指定地点着陆。飞机两翼下面各缀有日本国旗一面,两翼末端各系以四公尺长的红色布条。25分,在严密保护下启开机门。陆军总部派陈少校(实际上是新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接待。今井武夫在机舱口立正,问陈少校是否可以下机?陈答称:“现在可以下机了!”今井着军装,佩军刀,首先下机,面有戚色,缄默无语。陈少校检查前来联系人员的名单,宪兵草草检查行李后,12时30分,陈少校即引导今井及其随员等八人,分乘吉普两辆入城。中外记者沿途拍照,今井横目挺胸,手握军刀,情绪颇为紧张。
日本投降专使住的招待所距机场约两公里,周围设有数层宪兵岗哨严加戒备(据说足足用了一营的兵力),不让老百姓接近,也不许新闻记者进入采访。
21日下午3时20分,陈应庄等两位少校引今井及其随员分乘吉普开赴会场。会场正中桌旁坐着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右方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是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翻译官王武上校(其他翻译人员都立在王武左右)。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将领及文职人员顾毓琇、刁作谦、刘英士、龚德柏等亦都列席。中美新闻记者数十人,从走廊一直挤到会场外面。


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一行在前往签字会场的吉普车上Japanese surrender representatives left the airfield on jeeps with white fl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