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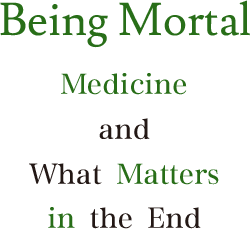
在医学院读书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包括死亡。第一个学期,我得到一具皮革似的干尸用于解剖,但那仅仅是了解人体解剖学的一个途径而已。对于衰老、衰弱和濒死,我仍旧一无所知,教科书也几乎只字不提。这个过程如何演变、人们如何体验生命的终点、对周围人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好像都无关宏旨。在我们看来,教授们一门心思地教导我们如何挽救生命,以为那才是医学教育的目的,眷顾垂死的生命完全是一个“界外球”。
记得我们只有一次讨论到死亡。当时,我们用了一个小时讨论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那是在每周一次的医患关系论坛上——学校希望借此把我们培养成更全面、更人道的医生。有几个星期,我们演练身体检查时的礼仪;另外几个星期,我们了解社会经济和人种对健康的影响。有一个下午,我们思考的内容是,当伊万·伊里奇因某种无名的无法医治的疾病病倒、情况持续恶化时,他所遭受的痛苦。
故事的主人公叫伊万·伊里奇,45岁,是圣彼得堡中级地方法院的法官,他的生活重心围绕着有关社会地位的各类小事情。有一天,他从楼梯上掉下来,摔伤了一侧的身体。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疼痛不仅没有渐渐消退,反而加剧了,以致他无法再工作。曾经“聪明、圆滑、活泼、随和”的他变得忧心忡忡,虚弱不堪。朋友和同事纷纷回避他,他的妻子找来的医生一个比一个诊费高昂。每个医生的诊断结果都不同,他们开出来的处方也没什么明显的效果。对伊里奇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折磨,这一状态令他怒火中烧。
“伊万·伊里奇最痛苦的是,”托尔斯泰写道,“由于某种原因,他们都接受了这样的欺骗和谎言,即,他不是快要死了,而只是病了。他只需要保持平静的心情,接受治疗,然后,就会出现非常好的结果。”伊万·伊里奇心里也曾经产生过希望的火花,以为情况会逐渐好转,但是,随着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人变得越来越憔悴,他终于明白了正在发生什么。他的苦闷和对死亡的恐惧与日俱增。但是,死亡并不是他的医生、朋友或者家人能够给予他支持的一个主题。而这正是造成他最深刻的痛苦的原因。
“他希望得到同情,可是没有一个人给予他这样的同情,”托尔斯泰写道,“在经过漫长的挣扎之后,某些时刻,他最渴望的是(虽然他羞于承认)有人能够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地同情他。他渴望得到宠爱和安慰。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公务员,胡须都白了,所以,他知道他的渴望是徒劳的。然而,他仍然这样渴望着。”
在我们医学生看来,伊万·伊里奇周围的人没能给予他足够的心理纾解与心灵抚慰,也没有承认他的状况,这乃是一种性格和文化缺陷。对我们来说,托尔斯泰的故事展现的是19世纪晚期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一切都显得粗糙,近乎原始。正如我们相信,无论伊万·伊里奇得的是什么病,现代医学都可能治愈,我们也自然而然地把诚实和善意视为任何一个现代医生的基本责任。我们信心十足地认为,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满怀同情。
我们全力聚焦于知识的进步。虽然我们知道如何表达同情,但是完全不能确信我们懂得怎样进行恰当的诊断和治疗。我们上医学院是为了了解身体的内在运行过程、身体病理学的复杂机制,以及人类积累的阻止疾病的许多发现和大量技术。除此之外,我们不曾想象我们需要丰富社会、心理、文化方面的修养。于是,我们没把伊万·伊里奇的故事放在心里。
然而,在经历外科实习和当医生的几年间,我遇见了许多被迫面对衰退和死亡现实的病人。我很快就认识到,自己没有做好帮助他们的充分准备。
开始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是低年资的外科住院医师。在我最早的一篇文章中,我讲述了约瑟夫·拉扎罗夫的故事。他是一位市政府的行政官,几年前,他的妻子死于癌症。此时,60多岁的他也患了无法治愈的癌症——一种转移性的前列腺癌。为此,他消瘦了近50斤,腹部、阴囊和双腿都积满了液体。有一天,他一觉醒来,发觉右腿无法动弹,大便失禁,于是住进了医院。那时候,我是医院神经外科组的实习生。我们发现癌症已经扩散到他的胸椎,对脊椎构成了压迫。很显然,癌症已无法彻底治愈,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对他进行干预。然而,应急放疗没能缩小癌症病灶。于是,神经外科医生给了他两个选项:一是安宁缓和医疗;二是实施手术,切除脊椎处生长的肿瘤包块。拉扎罗夫选择了手术。作为神经外科组的一名实习生,我的任务是履行知情同意手续,并取得他的签字,确认他理解手术风险并希望施行手术。
我站在他的病房外,汗湿的手里拿着他的知情同意书,竭力思考该如何开口跟他把这个话题谈明白。我们都希望手术能够阻止脊椎损伤继续发展,但是手术治不好他的病,也不能纠正瘫痪,更谈不上使他恢复过去的生活。无论我们做什么,他都最多只能有几个月的存活机会,而且,手术本身也有危险。要进入脊椎,需要打开他的胸腔,切除一根肋骨,拿掉一叶肺叶,手术中失血量会很大,以他的虚弱状态恢复起来很困难。而且,术后发生各种并发症、导致重要器官衰竭的风险相当高。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手术可能会恶化病情,缩短他的寿命。但是神经外科医生已经仔细斟酌过这些风险,拉扎罗夫自己也确定选择做手术。此刻,我需要做的只是敲门进去,完善术前的各项手续。
拉扎罗夫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形容枯槁。我说我是实习生,需要获得他同意手术的签字,确认他了解手术的风险。我说手术可以切除肿瘤,但是可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比如瘫痪或者中风,也有可能导致死亡。我尽量用委婉的语气把情况说清楚,但是,他还是一下坐了起来。当他同在病房的儿子质疑选择做手术是不是明智时,拉扎罗夫很不高兴。
“别放弃我,”他说,“只要我还有任何机会,你们一定要让我尝试。”他签完字后,我出了病房。他儿子跟出来,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他的母亲死在监护室里,死的时候全身插满了管子,戴着呼吸机。当时,他父亲曾经说过,他绝不想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时至今日,他却坚决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可见一个理智的人在死亡降临的时候还是无法舍弃求生的欲望。
那时,我觉得拉扎罗夫的选择很糟糕,现在的我仍然这么认为。他的选择之所以糟糕,不是因为手术有那么多风险,而是因为,手术根本不可能给予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排便节制能力、体力,以及过去的生活方式。他冒着经受漫长而可怕的死亡的风险(这正是他最后的结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幻想。
从技术的角度讲,他的手术很成功。经过八个半小时的努力,手术团队切除了侵蚀他脊椎的肿块,用丙烯酸黏合剂重建了椎体。手术解除了脊椎的压力,但是他一直没能从手术中恢复过来。他住在监护室,并发了呼吸衰竭、系统性感染,卧床不动又导致了血栓,然后,又因治疗血栓的血液稀释剂而引起了内出血。病情每天都在恶化,最后终于不得不承认他在向死亡的深渊坠落。第十四天,他的儿子告诉医疗组,我们应该停止“治疗”了。
我的任务是去除维持拉扎罗夫生命的呼吸机。我进行了检查,调高了吗啡静脉滴注,以免他缺氧。心里想着万一他听得见我说话呢,我俯身靠近他,告诉他我要取出他嘴里的呼吸管。我取出管子期间,他咳了几声,眼睛睁开了一小会儿,然后又闭上了。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吃力,然后终止了。我把听诊器放在他的胸口,听着他的心跳逐渐消失。
十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讲起拉扎罗夫先生的故事时,它对我内心冲击最大的不是他的决定之糟糕,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刻意回避诚实地讨论他的选择。我们不难解释各种治疗方案的特定风险,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触及其疾病的真相。他的肿瘤医生、放疗医生、外科医生以及其他医生给他做了几个月的治疗,而他们都知道,这些治疗根本医不好他的病。关于他的情况的基本真相,以及我们的能力的最终局限,我们都未曾讨论过,更遑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了。如果说他是在追求一种幻觉,那么,我们也同样如此。他住进了医院,扩散到全身的癌症导致他部分瘫痪,连恢复到几个星期前的生活状态的机会都完全不存在。但是,我们似乎没有能力承认这一点并帮助他去坦然面对。我们没有承认,没有给予安慰,也没有给予引导。我们提供给他另外一种治疗,告诉他也许会有某种非常好的效果。
跟伊万·伊里奇遭遇的原始的、19世纪的医生们相比,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实际上,考虑到我们加诸病人身上的披着新技术外衣的折磨,甚至可以说,我们比他们更不如。这一境遇已足以让我们反思,到底谁更原始。
现代科学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命的进程。跟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比起来,我们活得更长、生命质量更好。但是,科学进步已经把生命进程中的老化和垂死变成了医学的干预科目,融入医疗专业人士“永不言弃”的技术追求。而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做好准备去阻止老弱病死,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濒死的情形十分复杂,生命此时能否获得有品质的复苏,我们并不敢妄断,因为人们对于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比较陌生。1945年之前,大多数死亡发生在家里。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比例降至17%。而在家中亡故的人,多是因为死得太突然,来不及去医院(如严重的心脏病、中风,或者剧烈损伤),或者住得太偏远,来不及赶到能够提供帮助的地方。目前,在美国和整个工业化国度,对高龄老人和垂死者的照顾已经转由医院和疗养院来负责。
于是,医院成为起死回生的地方。作为医生,对于医院却有着另一个角度的理解。虽然我的父母都是医生,但我今天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崭新的。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人死去,所以在看见的时候,我感到震惊。倒不是因为我由此想到了自己将来会怎么死去,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个念头——即便是看见自己的同龄人死去。我穿着白大褂,他们穿着病号服;我不太能够颠倒角色。然而,我可以想象我的家人处于他们的位置。我目睹了几个家庭成员,我的妻子、父母以及孩子们罹患严重的、危及生命的疾病。即便在最紧急的情形下,良医妙药也总是能帮他们渡过危机。所以,我震惊的是眼见良医妙药没能让病人恢复健康。当然,理论上我知道一部分病人可能会亡故,但是,面对每一个实际的病例,死亡好像都不应该发生,都是一种意外。一旦失治,我们奉行的战胜一切敌人的信念似乎就被打破了。在我心里一直有一种迷惑:这是在玩什么游戏,为什么总是要我们胜出?
每个新医生、新护士都会面临濒死和临床死亡。第一次遇见,有人会哭,有人会完全呆住。当然,也有些人几乎不在意。最初看到人死,我非常警觉,不断提醒自己克制,总算没有哭出来。但是,我会常常梦见死亡。在反复发生的噩梦中,我父母的尸体出现在我家里——在我的床上。
我惊恐地想:“怎么到这儿的?”
我知道,如果我不偷偷地把尸体送回医院,我就会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甚至犯下刑事罪。我设法把尸体塞进汽车后备厢,但是,尸体太重,抬不起来。或者,倒是塞进去了,却发现像汽油一样的黑色血液渗出来,流得行李厢到处都是。或者,我真的把尸体弄回了医院,放上轮床,推着它从一个大厅冲向另一个大厅,到处找,却总也找不到病人曾经住过的房间。有人朝我喊“嘿”,并拔脚追我。我惊醒了,屋里一片漆黑,妻子睡在我旁边。我满身大汗,心跳过速。我觉得这些人都是我杀死的。我失败了。
其实,患者死亡并不代表医生的失败。死亡是极正常不过的现象。死亡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死亡也符合事物的自然规律。在抽象的意义上,我知道这些真理,但是,我缺乏具体的认知——它们不仅对于每个人是真理,而且,对于我面前的这个人,这个由我负责治疗的人,也是真理。
我的同行舍温·努兰(Sherwin Nuland)大夫在他的著作《死亡的脸》(How We Die)中写道:“我们之前的历代先人预期并接受了自然最终获胜的必要性。医生远比我们更愿意承认失败的征兆,他们也远不像我们这么傲慢,所以不会予以否认。”但是,当我行进在21世纪的医学跑道上,学习使用令人生畏的技术武器时,我恰恰不懂“不那么傲慢”的真正含义。
作为一名医生,你想象自己会获得工作的满足感,结果工作的满足感却变成了能力的满足感。这种深刻的满足感类似于一个木匠因为修复一只破损的古董柜子而获得的那种满足感,或者,类似于物理老师因为使得一个五年级的学生突然认识到了原子是什么而获得的那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部分是因为自己有助于他人,但同时也来自于技术娴熟,能够解决困难、复杂的问题。你的能力给你一种安全的身份感。所以,对于一名临床医生来说,对于你的自我认识的威胁,最严重的莫过于解决不了病人的问题。
无人可以逃脱生命的悲剧——那就是,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每个人都在不断老去。一个人甚至可以理解并接受这一事实,那些已故和垂死的病人不再萦绕于我的梦境,但这与知道怎样对付回天无力的病例是两码事。我身处这个充满英雄主义的行业,因修复生命的能力而取得成功和荣耀。如果你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也知道技术上该怎么办,但病情却严重到不可以解决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事实令人困扰,并导致了麻木不仁、不人道,以及某种特别的痛苦。
把死亡作为医学的技术极限和伦理选择问题来思考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医学还很年轻。事实证明,救治失败并不是医学的无能,而是对生命进程的尊重。
本书讨论死亡的现代经验:作为会老、会死的高级动物是怎么为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的?医学如何改变了死亡体验却又无法改变死亡的牌局?我们关于生命有限性的观念产生了怎样的迷茫?我做了10年的外科医生,如今也人到中年,我发现不论是我还是我的病人,都觉得当前的状态难以忍受。但我也困惑,答案应该是什么,甚至是否可能有任何充分的答案,这些都还不清楚。然而,作家和科学家的双重体验让我相信,只要揭开面纱,抵近观察,就可以把这团“乱麻”厘清。
无须同临终老人或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相处太长时间,你就可以本能地意识到,医学经常辜负其本应帮助的人们。我们把生命的余日交给治疗,结果为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好处,让这些治疗搅乱了我们的头脑、削弱了我们的身体;我们在各种机构,比如疗养院和监护室,度过最后的时光,刻板的、无形的惯例使我们同生活中真正要紧的东西相隔绝。我们一直犹犹豫豫,不肯诚实地面对衰老和垂死的窘境,本应获得的安宁缓和医疗与许多人擦肩而过,过度的技术干预反而增加了对逝者和亲属的伤害,剥夺了他们最需要的临终关怀。人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 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此,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
抚旧追新,无限感慨中我决计写下这本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死亡可能是一个敏感而忌讳的话题。作为医生,我深知生命是一条单行线,一步一步走向衰弱和死亡,生老病死的进程不可逆;但对于大众来说,有人会感到惊骇。无论怎样小心翼翼地措词,仍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话题太残酷,可能会让人们联想到这个社会准备舍弃病人和老人。其实,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拒绝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以及衰老与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我们的末期病人和老人才会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好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待解的问题,我们正在为生命的末期关怀开辟安宁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的新路径。到那一天, 生的愉悦与死的坦然都将成为生命圆满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