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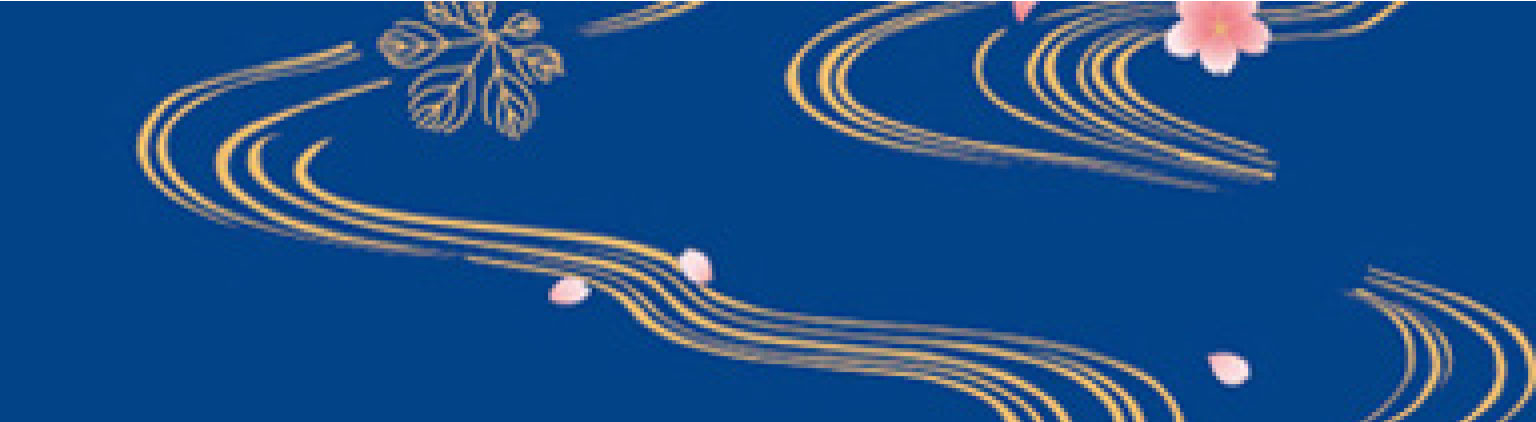
L U O S H E N G M E N

空荡荡的城门洞里,除了一只蹲在斑驳陆离朱漆大圆柱上的蟋蟀外,只有他一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城门下避雨。
空荡荡的城门洞里,除了一只蹲在斑驳陆离朱漆大圆柱上的蟋蟀外,只有他一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城门正对着朱雀大街,平日总该有两三个头戴斗笠和软纱帽的行人前来避雨,但是现在只有他一人。
若问何故,只因近两三年来,京都天灾人祸,地震、台风、大火、饥馑等诸多原因将偌大的京城搞得凋敝不堪。据记载,当时把佛像和佛具打碎,把涂了朱漆和雕饰金银箔的木头放在路边当柴火卖的事情不胜枚举。京城尚且如此,城门的修缮更是无人问津,任其荒废后,便成了狐狸栖息和盗贼蛰伏之地。久而久之,无主尸体便被遗弃至此,故日落黄昏之际,此处阴森恐怖,无人靠近。
人迹罕至,乌鸦便集结成群,盘旋聒噪。落日时分,乌鸦就像撒了满天的黑芝麻般清晰可见。毋庸置疑,它们是为了啄食尸体而来的。今日也许时辰已晚,竟然一只也没有。但是在那些即将坍塌、裂缝处长满青草的石级上,随处可见乌鸦的粪便,星星点点。家将穿着一身洗得褪色的青衣,一屁股坐在七级石阶的最高一级,茫然地望着大雨。一颗硕大的痤疮在右侧脸颊冒出头来,让他好生心烦。
笔者前面写道“家将在此躲雨”,实指雨停之后他不知该何去何从。平日,还可回到主人家中,但就在四五日前,他已被主人扫地出门。前文也提到,当时的京城已是破败不堪,眼下这个家将被侍奉多年的主人赶走,亦不过是个小小的缩影而已。所以,与其说是“暂时在此避雨”,不如说“走投无路”更为贴切。而今日的天气更加渲染了这位平安时代家将的凄凉心绪。雨,刚过申时就开始下,到现在也无停歇的迹象。家将一边为明天的生计犯愁——再怎么苦思冥想也无济于事,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朱雀大街的雨声。
雨将城门紧紧困住,哗哗的雨声从四面八方袭来。暮色沉沉,抬眼望去,门楼顶上斜刺的飞檐上挂着沉重的乌云。
既然无济于事,就只能不择手段了,优柔寡断只有死路一条——死在土墙边、街道旁,像死狗一样被人从门楼上抛尸荒野。如果孤注一掷呢?家将的思路又回到了这里。想到“如果”,他不敢继续想下去,虽然默认了背水一战,但是跨出这一步就无回头路了,只能沦为强盗。他还没有想好,还缺乏足够的勇气。
家将打了一个大喷嚏,吃力地站起身来。夜已深,恐怕只有火盆才能驱赶这寒气了,风伴着夜色肆无忌惮地在柱间呼啸。那只待在柱子上的蟋蟀早已不知去向。
家将缩着脖子,耸着青衣衬着黄色内衫的肩头,打量着门楼四周,心中想要的是有个能遮风挡雨,掩人耳目,还能将就睡一晚的地方,无论如何也好度过今晚。恰好一条通往门楼的宽大朱漆梯子映入眼帘,楼上如果有人,也不过是些死人,于是,他边留意不让木制刀把的长刀脱鞘,边抬起穿草鞋的脚迈向楼梯的最下级。
片刻之后,在通往城门楼的楼梯中段,出现一个人影,猫着腰,屏着呼吸,窥视着上面的光景。而楼上射来的光,惨淡地照在他的右脸上,隐约可见其短须中红肿发脓的痤疮。他本以为上面全是死人,所以根本没有多加理会,孰料,走上几级阶梯后,发现不知是谁点了火把,火苗四处晃动。昏黄的火光,映射出布满蜘蛛网的阁楼。他心中暗想,在这月黑风高之夜,敢在这城门楼上点火之人,绝非等闲之辈。
他蹑手蹑脚地爬到这陡直楼梯的上方,低下身子,伸长脖子,战战兢兢地向楼内打量。
果然如传闻所言,楼内胡乱地堆放着几具尸体。火光照到的地方比想象的要小,看不出到底有多少具尸体。昏暗中只依稀见得各种尸体,不分男女,有的还衣不蔽体地杂乱无章地被堆放在一起。而且看不出曾经有生命的迹象,就像一堆泥捏的假人,张着嘴,伸着胳膊,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肩膀和胸脯这些凸出的部位,在朦胧的火光中,更加凸显出凹陷部分的阴暗沉闷,就像哑巴一样的死寂。
尸体腐烂的恶臭,让他不禁捂住了鼻子。但是,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惊讶地都忘记了用手来捂住鼻子。因为某种强烈的感觉,几乎让他失去了嗅觉。
他定睛一看,死尸堆里蹲着一人,那人身穿棕黑色衣服,又矮又瘦,满头白发,是个猴子般的老妪,右手还攥着一个点着的松明子,正在窥探一具尸体的脸。从长发上看,应该是具女尸。
家将六分惊恐四分好奇,竟然一时忘记了呼吸。那种感觉,古语云“全身的汗毛都炸开了”。这时,老妪将松明子插在地缝中,两手搭在女尸头上,像母猴给小猴抓虱子一般,一根一根地拔着头发,头发应声而落。
随着头发一根一根地被拔下,家将的恐惧也在一点一点地消失。同时,对老妪的憎恶也随之升起,不,仅是对老妪可能还不够确切,应是对一切邪恶事物都越发地反感。此时,倘若有人问他刚才在门洞里思及的是“饿死”还是“当强盗”,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他嫉恶如仇的内心也如老妪的火把一样,愈演愈烈。
当然,他不知道老妪为何要去拔死人的头发,不能简单将此归结于善恶是非。但就月黑风高之夜在城门上拔死人头发这一点,也已经是罪不可恕。当然,他已将刚才打算做强盗之事抛至九霄云外了。
于是,家将双脚发力,一个箭步从楼梯上跳了上去,手按木柄长刀,大步流星走向老妪,老妪自是被吓一跳。
老妪看到家将,就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
“嘿!你哪里走?”
家将一边大声呵斥,一边挡住在死尸堆里慌不择路的老妪。老妪想强行过去,溜之大吉。家将不依不饶,一把推了回去。于是两人在死尸堆里扭打了起来,当然胜负早已注定,家将抓住她像鸡爪子一样瘦骨嶙峋的手臂,将她按倒在地。
“你在干吗?老实交代,不说有你好看的。”
家将推开老妪,“嗖”的一声拔出长刀,将雪亮的刀刃晃在老妪面前。可是老妪默不作声,噤若寒蝉,两手发抖,气喘吁吁地抽动着双肩,眼珠似要掉出般睁大双眼,固执地紧闭双唇。此时,家将觉得老妪已是砧板之肉,刚才那股强烈憎恶的烈火,也渐渐熄灭,流露出的是得逞后的喜悦和满足。于是,他向老妪,缓缓说道:
“俺不是什么官府差人,只是过路的,所以不会绑你见官。只要告诉我在你城门上干什么就行了。”
老妪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死死地盯着家将。她瞪着发红的眼睛,像食肉鸟一样目露凶光,接着像咀嚼什么似的,动了动满是皱纹、几乎和鼻子挤在一起的嘴唇,尖尖的喉结在细细的脖颈上蠕动。上气不接下气、乌鸦般的声音传至家将耳中。
“拔了这头发,拔了这头发,是用来做假发的。”
老妪平淡无奇的回答,令家将颇感失望,刚刚退去的憎恶和蔑视又一齐涌上心头。他的神情,老妪似乎也看出来了,手里捏着刚从死人头上拔下来的头发,用癞蛤蟆咕咕似的声音,磕磕巴巴地又说:
“要说呢,拔死人头发是不对,不过这些人生前也是干这些勾当的。就说我正拔的这位吧,她活着时就是把蛇剁成一段段,晒干了当成鱼干卖到东宫护卫营里去的。要不是害瘟疫病死了,估计她现在还卖呢。她卖的鱼干味道鲜美,东宫护卫们买来当菜吃,还求之不得呢。她干那营生也没错,不干就得饿死,反正是没有法子嘛。我干的这营生也没错。没有法子,不干就得饿死。我跟她一样,都是走投无路呀,我想她也会原谅我的。”
老妪大致讲了讲。
家将把刀插入鞘中,左手按着刀柄,冷冷地听着,右手摸了摸脸上红肿的痤疮,听着听着一股无名野火就生了起来。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正是老妪的话,激起他内心的邪恶。他再也不必为饿死还是当强盗而纠结了,刚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念头被他彻底从脑中驱逐出去。
“确实如此吗?”
老妪的话音刚落,他讥笑地问了句,然后忽地上前一步,用刚才摸痤疮的大手,抓住老妪的衣襟,恶狠狠地说道:“那么我扒了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怪我,不这样,我也得饿死。”
家将急急扒下老妪的衣服,一脚把缠在他腿上的老妪踢在死尸堆上,大步流星地走到楼梯口,腋下夹着抢来的棕色衣服,顺着楼梯一溜烟地消失在黑夜之中。
过了一会儿,死狗一样的老妪光着身子从死尸堆里爬起来,嘴里哼哼唧唧,借着松明子的光,爬到楼梯口,披散着短短的白发,漠然地看着门下。外面只剩下漆黑一片的夜。
家将早已逃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