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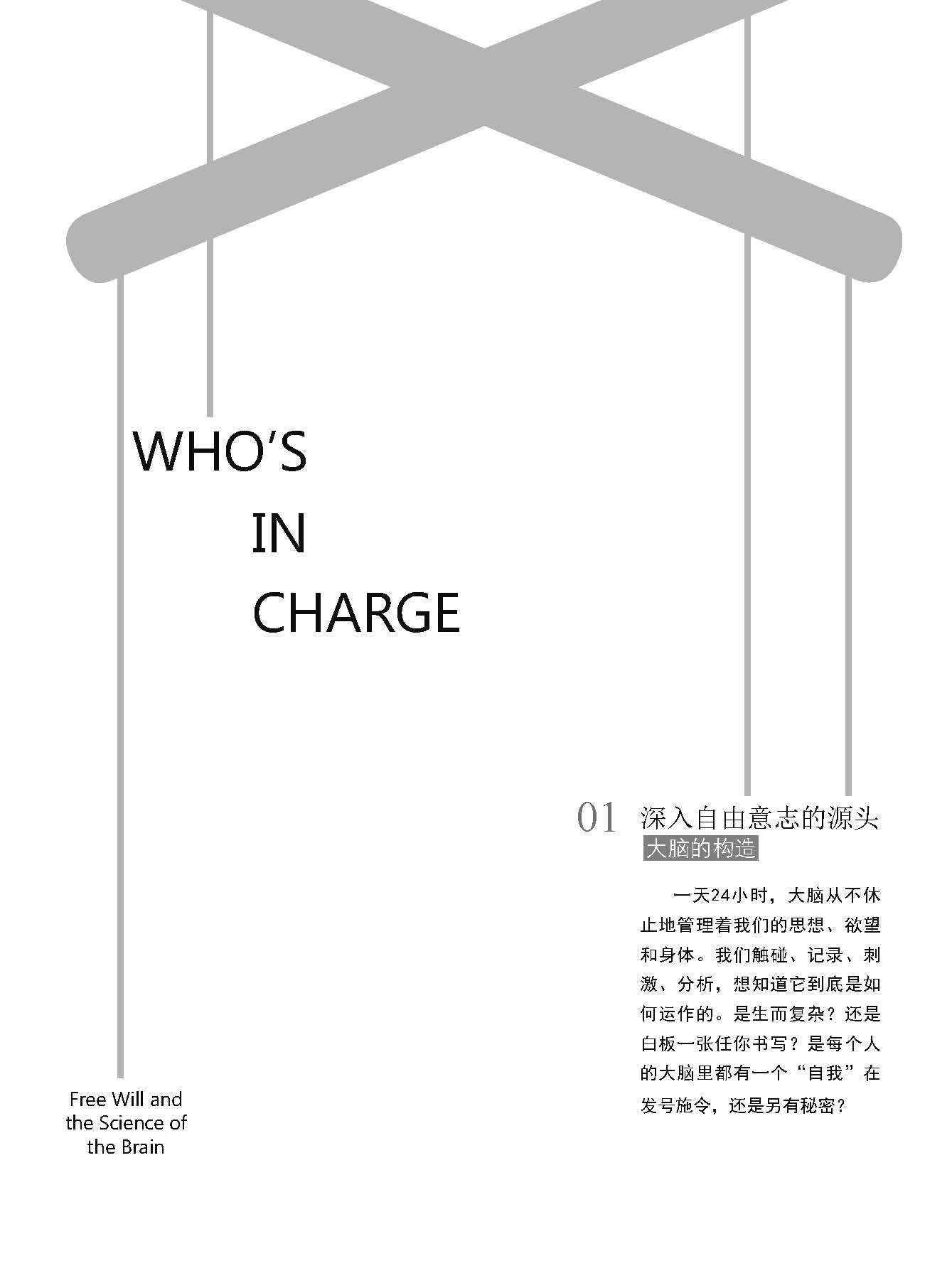
这就是那个日常生活中的难解之谜:所有人都感觉自己是意识统一的载体,行动时有着自我目的,能自由自主地做出几乎任何选择。与此同时,所有人都意识到自我是机器(虽然是生物性的机器),而宇宙的物理定律对两种机器——人工机器和人类机器都适用。这两种机器都完全像爱因斯坦(他不相信自由意志)说的那样确定吗?还是,我们能随心所欲地自由选择?
理查德 ·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代表了“人都是确定的机械设备”这一开明科学观,并直接地指出了它的含义。为什么要惩罚那些从事反社会行为的人呢?为什么不能单纯地将之视为需要修理的人呢?毕竟,他认为,要是车熄火了、坏了,不应该打它也不应该踢它。要修理它。
把汽车换成一匹马,它把你从背上颠了下来。现在怎么办?你脑子里冒出的念头,想必不是把它牵去马厩修理,而是拿出一根棍子教训它。有生命的物体唤起了一种充满勃勃生气的反应,它是我们人类的一部分,与此伴随而来的,还有大量的感受、价值观、目标、意图,以及所有的人类心智状态。总之,我们的构建方式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大概是大脑吧)控制着人的许多日常行为和认知。我们的构成似乎极其复杂,大脑这部机器要靠独特的蒸汽才能运转,哪怕我们认为一切归自己说了算。这就是个谜。
我们的大脑是一套庞大的并行分布式系统,有着许许多多的决策点和整合中心。一天24小时,大脑从不休止地管理着我们的思想、欲望和身体。数以百万计的网络汇成了像汪洋大海一样的部队,而不是单个的士兵等着指挥官发话。这同样是一套确定的系统,它不是独行的牛仔,超脱于充斥宇宙的物理、化学力量之外。可惜,这些现代科学发掘出来的事实,丝毫也不能说服我们——每个人内心,居然没有一个“你”,一个“自我”在发号施令。这同样是个谜。我们的任务,就是尝试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人类大脑取得的成就,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存在一个有目的、有中心的自我。人类掌握的现代技术和知识多么精彩啊!
北卡罗来纳一只植入了特殊神经的猴子竟然能直接连上互联网,受到刺激后,猴子被启动的神经还能控制日本一台机器人的运作。不仅如此,它的神经冲动传到日本的速度,竟然比传到猴子自己腿上的速度要快!
再来看看你的晚餐。要是你运气好,今晚,你兴许能吃上本地种的沙拉、智利的梨子、意大利的美味干酪、新西兰的羊排、爱达荷州的烤土豆,还有法国的红酒。要多少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人合作,才能把这么多不同的东西结合到一起?数之不尽。先是头一个想出自己种粮食的人,头一个想到陈年葡萄汁喝起来更有趣的人,接着是达 · 芬奇,他第一个画出了飞行器的图样,还有头一个咬了发霉奶酪、觉得这是好东西的人,更有众多的科学家、工程师、软件设计师、农夫、牧场主、葡萄酒商、运输员、零售商、厨师做了贡献。
动物王国里,不相干的个体之间可不存在如此的创意或协作。更令人惊讶的或许是,有人居然看不出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能力有着多么大的差异。事实上,他们信心满满:自家有着忧伤大眼睛的宠物狗,聪明得马上就能到杂志上发表文章——《如何趴在沙发上支使你的人类室友》。
人类已经遍布世界各地,生活在千差万别的环境中。可跟我们血缘最近的亲戚,黑猩猩,则处于濒危状态。你肯定要问,为什么人类这么成功,我们的近亲却只能勉强度日。我们有能力解决其他动物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我们拥有某种它们没有的东西。可我们又发现很难接受这一点。随着人类迈入21世纪初,我们掌握了更多有助于解答部分此类问题的信息,这些信息,过去时代好奇善问的人一无所知。好奇似乎是我们的天性:自从人类有了历史,我们就一直想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谁。公元前7世纪德尔斐圣地阿波罗神庙的墙上刻着箴言: 认识自己 ( KNOW THYSELF )。人总是好奇思想、自我和人之为人的本质。这种好奇心从何而来?这可不是你家狗狗蜷在沙发上会想的问题。
今天,神经科学家正在探索大脑:他们触碰它,记录它,刺激它,分析它,拿它和其他动物的大脑相比较。它的部分神秘业已曝光,理论比比皆是。在我们为现代人类的辉煌壮举感叹之前,我们需要控制好我们的“自我”(ego)。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写下了以下的话,好似当代神经科学家:“人应当知道,欢乐、愉悦、笑容、强健的体魄,还有悲伤、哀怨、失望和慨叹,无不出自大脑。通过大脑……我们获得了智慧和知识,我们能看,我们能听,我们知道什么是逾矩,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坏,什么是好,什么甜蜜,什么讨厌……通过同一器官,我们也可能变得疯狂,神志不清,任凭害怕和恐惧攻击我们……” 1 他对提出的作用机制分析得很粗略,但原理丝毫不错。
所以我想,尽管让科学去解释作用机制好了,在此过程中,我们最好是采纳歇洛克 · 福尔摩斯“科学方法”的建议:“困难在于,需要把那些确凿的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与那些理论家、记者的虚构粉饰之词区别开来。我们的责任是立足于可靠的根据,得出结论,并确定在当前这件案子里哪一些问题是主要的。”
2
这种除了事实什么也不要的冲动,是着手解决谜题的一种方法,早期的脑科学家们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开始探索的。这是什么东西?找一具尸体,打开颅骨看一看。让我们来在大脑上钻个孔。研究一下中了风的人。把大脑传出来的电信号记录下来。看看它在生长过程中是怎么连通的。如你所见,激励早期科学家、甚至现在不少科学家的,就是这种简单的问题。不过,随着我展开整个故事,你会发现,不实际研究生物体的行为,不知道我们进化而来的精神系统天生应该去做什么,就绝对不可能解决“自我”与机器的问题。诚如杰出的脑科学家戴维 · 玛尔(David Marr)所说,仅仅是观察鸟的羽毛,你是没办法弄懂鸟的翅膀怎样运作的。随着事实的积累,我们需要将之放到功能背景下,检验该背景对生成该功能的潜在要素做了什么样的限制。让我们开始吧。
照理说,像“大脑发育”这种说起来简短干脆的东西,应当很容易研究和理解,但就人类而言,这一发育涉及的范围极广。它不光是神经发育,更有分子发育,不光认知随着时间改变,外部世界的影响也随着时间改变。事实上,它根本不简单:通常情况下,光是从推理中剥离出事实框架就是一个漫长、艰巨而迂回的过程,而要想揭示大脑如何发育并运作,命中注定也会这样。
等位性原则——新生宝宝的大脑就像一张白纸
20世纪初,大脑研究就遭遇了一次绕弯路事件,它给科学界和世俗世界带来了深远影响,直至今日,由它衍生出来的“先天禀性还是后天培养”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1948年,在我的母校达特茅斯学院,加拿大的和美国的两位伟大心理学家,卡尔 · 拉什利(Karl Lashley)和唐纳德 · 赫布(Donald Hebb)聚在一起讨论以下问题:大脑到底是一块白板(基本上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可塑体”)呢,还是它本身就有限制,并由其结构所决定呢?
此前20年都是白板理论占主导,拉什利是它最初的支持者之一。他最先采用生理和分析方法研究动物的大脑机制和智力。他仔细地在实验用大鼠的大脑皮层上形成损伤,并加以量化,测量其损伤前后的行为变化。他发现,移除皮层组织的数量会影响学习和记忆,但在什么位置移除没有影响。这使他确信,技能的损失和切除皮层的体积有关,和位置无关。他没有想到特定的皮层损害会令得大鼠丧失特定的技能。他提出了整体活动原则(大脑整体的活动决定了其性能)和等位性原则(大脑的任一部分都可执行给定任务,没有专业分工)。
3
拉什利在做研究生毕业研究时受到了这种学说的影响,还成了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实验室主任约翰 · 华生(John Watson)的好朋友。华生是个坦率的行为主义者,坚定地支持“白板说”。1930年,他说了一句名言:“给我一打健康而又没有缺陷的婴儿,把他们放在我所设计的特殊环境里培养,我可以担保,我能够把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训练成我所选择的任何一类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界首领,甚至是乞丐或窃贼,而无论他的才能、爱好、倾向、能力,或他祖先的职业和种族是什么。” 4 拉什利的整体活动和等位性原则很好地与行为主义的框架相吻合。
第一批发育神经生物学家之一保罗 · 韦斯(Paul Weiss)为等位性概念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他也认为,大脑发育是没有专门分工的。根据他在实验中所得的结果(为两栖动物蝾螈嫁接了额外一条肢体),他创造了“功能先于形式” 5 这一说法。他要研究的问题是,神经是专门针对肢体生长出来的,还是先随机生长,并通过对肢体的使用而后适应为肢体神经元的呢?他发现,移植给蝾螈的肢体逐渐受神经的支配,并能够学习跟相邻肢体完全协调同步的动作。韦斯的学生罗杰 · 斯佩里(Roger Sperry,后来成了我的导师)将韦斯广为接受的共振原则总结为“认为突触联系在下游接触中是完全非选择性、分散化的和普遍存在的一种设想”。 6 所以,当时人们认为,神经系统(从神经元到神经元)“最确定的一点”就是,它不是结构化系统。它由拉什利首先提出,由行为主义者跟进,还得到了当时最杰出的动物学家的赞同。
神经总知道该往哪儿长
但唐纳德 · 赫布不为所动。虽然他师从拉什利,但他是个有独立见解的人,并着手构建自己的模型。他认为特定的神经连接怎样运作非常重要,于是有意识地回避了整体行动和等位性概念。他已经抛弃了俄罗斯伟大生物学家巴甫洛夫的想法,后者认为大脑就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反射弧。赫布相信,大脑的运作能解释行为,有机体的心理学和生物学密不可分,这是一个现在广为接受的想法,但与那时的主流认识格格不入。行为主义者认为大脑仅仅是对刺激做出反应,赫布则意识到,大脑时刻处于运作状态,哪怕不受刺激时也一样。他根据20世纪40年代对大脑功能掌握的有限数据,勉强构造了一套框架。
赫布开始根据自己的研究设想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1949年,赫布出版《行为的组织:神经心理学理论》(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A Neuro-psychological Theory )一书,为严格的行为主义敲响了丧钟,转回了较早以前认为神经连接非常重要的观点。
赫布写道:“若轴突细胞A与细胞B靠得足够近、A能够激发细胞B,并且反复或持续参与B的启动,AB细胞单个或两者之间就会出现某种生长过程或代谢变化,使得A细胞启动B细胞的效率得到加强。”
7
通俗地说,在神经科学中,这就是所谓的“神经元一同启动,就一同交织”,它构成了赫布“学习与记忆”主张的基础。
赫布提出,一组共同启动的神经元构成了“细胞集合”(cell assembly)。在触发事件出现后,集合里的神经元可以继续启动,他认为,这种兴奋留存就是记忆的一种形式,而思维就是细胞集合的顺序激活。总之,赫布的想法道出了神经连接重要性概念的核心。它至今仍是神经学研究的中心议题。
赫布的注意力集中在神经网络以及它们如何运作、学习信息上。尽管他并未关注神经网络如何形成,但他的理论提出了一点暗示,即思想会影响大脑的发育。事实上,早在1947年公布的早期大鼠实验中,赫布就表明,经验会影响学习。 8 赫布明白,等人们掌握更多有关大脑机制的情况,他的理论必定会得到修正。但他坚持生物学与心理学相结合,为10多年后确立神经科学新领域打通了道路。
人们从这时开始理解:一旦信息得到学习和存储,特定的大脑区域就会以特别的方式运用该信息。然而,老问题依然存在:这种网络是怎么形成的?简单地说,大脑是怎样发育的呢?
保罗 · 韦斯的学生,罗杰 · 斯佩里完成了这方面的基础工作,日后,它将成为现代神经科学的骨架。斯佩里还十分强调神经特异性的重要。神经连接(或布线)怎样发生的问题,让他十分着迷。他对韦斯的“神经生长”说(认为功能性活动在神经回路的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表示怀疑。1938年,他投身研究的那一年,约翰 · 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两名医生,弗兰克 · 福特(Frank R. Ford)和巴恩斯 · 伍德尔(Barnes Woodall)做了另外一些违背神经系统功能可塑性教条的研究。这两人详细回顾了自己的临床经历,有病人神经再生多年,但功能紊乱却丝毫没有改善。 9
斯佩里动手观察大鼠的功能可塑性,看看改变神经连接会给它的行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将老鼠后肢对立屈肌和伸肌肌群之间的神经连接互换,使踝关节运动颠倒。他想看看,动物能不能像韦斯功能主义观点所预言的那样,学会正确地动脚。他惊讶地发现,即便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大鼠也完全无法调整。 10 举例来说,爬梯子的时候,它们的脚该往下时往上,该往上时却往下。他以为新的回路能建立起来,恢复正常的功能,但事实证明,运动神经元不能互换。接着,他又尝试了感官系统,把大鼠一只脚的皮肤神经换到另一只脚上。大鼠再一次照着错误的感觉动弹:右脚受震,它们抬起左脚;右脚疼痛,它们舔舐左脚。 11 它们的运动和感官系统都缺乏可塑性。
韦斯在实验中选择蝾螈充当人类的代替品,只可惜这是个糟糕的选择。神经系统再生只表现在低等脊椎动物上,也就是指,鱼类、青蛙和蝾螈。斯佩里回到20世纪初杰出神经科学家圣地亚哥 · 拉蒙–卡哈尔(Santiago Ramó-ny Cajal)提出的观点上:有一种趋化作用控制着神经纤维的生长和终止。
斯佩里认为神经回路的生长是神经接触遵循特定基因编码带来的结果。他进行了几十个巧妙的实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曾将青蛙的眼睛用手术颠倒过来。之后,当青蛙眼前出现一只苍蝇,它的舌头却朝着相反的方向伸出。即便眼睛换位置好几个星期了,青蛙仍然继续朝着错误的方向搜索。这就是神经系统的特异性:它不可塑,不能适应。他又将金鱼切除了部分视网膜。神经再生后,他观察到神经从中脑接收眼睛传来信号的部位,也即视顶盖生长出来。事实证明,神经的生长非常具有针对性。如果它们从视网膜的背后生长,就会长到顶盖的前面,如果它们从视网膜的前方生长,就会长到顶盖的后面。换句话说,不管神经的起始位置如何,始终都要长到特定的地方去。斯佩里得出结论:“每当中央纤维系统断开再移植,甚或仅仅覆盖上大略相邻的部位,再生总能带来有序的功能恢复,无需进行再教育性调整。”
12
20世纪60年代稍晚些时候,人们可以实际观察并拍摄下神经生长了,发现神经的生长锥连续发送微丝或触须朝着各个方向试探,它们伸长、收缩,感觉该朝哪个方向进行神经生长。 13 斯佩里认为,化学因素决定由哪一种微丝占主导地位,并设定生长路线。在他的神经生长模型中,神经元发送细小的丝状伪足(细胞里探出的纤细细胞质突起)观察该走那条路(这么说吧,就像是试试水深水浅),找到自己在大脑中的连接。由于一种化学梯度的存在,它们能找到合适的道路,前往特定地方。
这一基本想法引出了至今仍常见于神经科学的神经特异性概念。斯佩里的原始模型已经有所改变,做了细微的调整,但他的神经元生长整体模型保存了下来。神经元受基因控制而生长、连接,这一神经元生长机制带来的结果是,在整个脊椎动物王国里,大脑的组织方案基本上是一致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进化神经生物学家莉亚 · 克鲁比泽(Leah Krubitzer)认为,对所有由相同基因决定的物种,皮质中可能存在一种共同的遗传模式。
克鲁比泽总结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检验过的每一种哺乳动物,都存在共同的发育组织方案或蓝图,而看似不使用某一种感官系统的哺乳动物,也都有着退化的感觉器官和皮质区。” 14 皮质的某些部位,会因为头骨和大脑的不同体积和形状而略有偏向,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仍保留同一种整体方案。
拉什利和韦斯的实验似乎表明,大脑不同区域是未分化的,可互换的;斯佩里却指出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大脑的大部分网络由化学或物理化学的通路、连接编码从遗传上决定。这是一种硬连线观:神经细胞的分化、迁徙和轴突导向受遗传控制。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先天论的问题,也即认为思想拥有的观念完全是天生的,并非得自外部来源。这个想法的局限性,赫布已有所预见。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大约就在20世纪60年代初斯佩里微调自己神经发展理论的同一时期,英国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彼得 · 马勒(Peter Marler)迷上了鸣禽。这些鸟是从鸟爸爸那里学习歌唱的。他在做植物实地考察时注意到,同一类型的鸣禽在不同地区会唱不同的歌(他称之为方言)。他发现,白冠麻雀的幼鸟在出生大约30天到100天的敏感时期,渴望而且能够学习特定范围内的声音。他想知道,限制幼鸟接触到的歌曲,是否能控制它们所学的内容。他把处于敏感期的幼鸟隔离出来,只给它们听本地方言或外来方言的歌曲。幼鸟接触到的是什么歌曲,就学会了什么歌曲。故此,鸣禽学习的方言是依赖于个体经验的。
接着,马勒又想,如果给幼鸟接触另一类型麻雀唱的略有不同的歌曲,它们是否能够学会。他尝试换用了本地常见的另一种麻雀的歌曲,但幼鸟只学得会自己这一类麻雀的歌曲。 15 故此,幼鸟学习的歌曲方言取决于它们所接触到的歌曲,而它们能学会的歌曲类型,则非常有限。它们的学习范围受先天的神经限制。这种内置限制为白板说提出了一个问题,但尼尔斯 · 杰尼(Niels Jerne)并不感到吃惊。
学习只是在先天能力中做选择
20世纪50年代,瑞士著名免疫学家尼尔斯 · 杰尼撼动了免疫学世界的核心。当时在免疫学家中存在一个共识:抗体形成等于是抗原扮演指导作用的学习过程。抗原多为构成细胞表面部分的蛋白质或多糖。这些细胞可以是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寄生虫),非微生物(如花粉、蛋清),或移植器官、组织、输血细胞等。杰尼认为事实与此完全不同。他说,不是抗原生长成专门设计好的抗体,而是身体出生之时就具备各种不同类型的抗体:抗原不过是这些先天抗体识别或选择的分子。没有指令,只有选择。免疫系统本身就极度复杂,并不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得复杂。
杰尼的设想成了现在抗体反应和克隆选择理论的基础(就是带有受体的白血细胞——又名淋巴细胞与侵入的抗原相结合后克隆或繁殖)。这些抗体大多从未遇到过匹配的外来抗原,可一旦碰到,抗体就激活,产生自身的克隆,与入侵的抗原结合、阻止后者活动。
杰尼不断提出颠覆前人的突破性观点。他后来提出,如果免疫系统真的是基于这种选择过程展开运作,那么包括大脑在内的其他系统很可能也是一样的。1967年,杰尼写了一篇名为《抗体与学习:选择还是指令》( Antibodies and Learning: Selection versus Instruction )的文章 16 ,论述将大脑视为对选择过程(而非指令)做出反应的重要性:大脑不是能够学习任何东西的无分化团块,正如免疫系统也不是能产生任何类型抗体的无差别系统。他提出一个惊人见解:学习可能是一种对先天能力的排序过程,这些能力我们本来就具备,只是在特定时刻为应对特别的挑战而挑选出最适合的一种或几种。换句话说,这些能力是由遗传决定的神经网络,专门用于进行特定类型的学习。
这里有一个常用的例子:人很容易就学会害怕蛇,但却很难学会害怕花。我们有内置的模板,一发现某种类型的运动(如草丛里有东西在爬行)时就引出恐惧反应,而对花却没有这种天生的反应。和免疫系统的情况一样,这个设想认为,大脑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特异性(如前文论述的白冠麻雀学习歌曲一例所示的)。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系统(或器官)是从已经存在的能力做出选择。但它也意味着限制。如果先天不具备某种能力,就无从选择,故此也就不存在。
研究人员在达尔文最初的“教室”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观察到了选择在种群生物学里运作的一个著名例子。
1977年发生了干旱,大部分能结出种子的灌木颗粒无收,成年地雀大量死亡。地雀的喙有大有小。地雀以吃种子为生,喙是它们生计的关键。喙小的地雀啄不开干旱期间仍较为常见的刺蒺藜的木质果实和坚果,但喙大的地雀却啄得开。柔软的种子供应有限,早就被鸟儿们一抢而空,只留下个头大的坚果,而它们,只有喙大的鸟才能吃到。喙小的地雀灭绝了,喙大的地雀存活下来:这就是从已有能力中做出选择。次年,幸存下来的地雀的后代,往往体格更大,也有着更大的喙。
17
目前的大脑观,并不如拉什利、沃森和韦斯所描述。他们的模型把大脑视为一种什么都可以学习的无分化团块:任何大脑能学习任何东西。对于这样的大脑,很容易教它像享受玫瑰清香一样享受腐烂鸡蛋的臭气,也很容易教它像害怕蛇那样害怕花朵。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但厨房里飘出臭鸡蛋的味道,是不会给我的客人们留下好印象的——不管他们来了多少次。斯佩里对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大脑是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构建的,它由遗传决定,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它的布线方式基本上就预设好了。这种解释可以说明大部分的事实,但尚不足以说明研究中涌出的所有数据。它并不能完全解释马勒在鸣禽身上观察到的现象。
后天培养也很重要
事实证明,神经科学领域的故事多着呢。温辛(Wun Sin,音译)、库尔特 · 卡斯(Kurt Kass)和同事们研究青蛙大脑视顶盖的神经元生长时发现,给予光刺激,能提高神经细胞末端分支突起(也即树突棘)的增长速度和数量。这些树突棘传导其他神经细胞的电刺激,统称为树突分支。故此,视觉活动增强实际上带动了神经生长。 18 斯佩里认为细胞生长只受一种遗传趋化作用(细胞朝着某种化学物质运动)所影响。和他所说的不同,神经元的实际活动和它的经验也推动着它的生长以及其后形成的神经连接。这叫做活性依赖过程(activity-dependent process)。
烦人的是,新近的研究表明妈妈的话没错:应该勤练钢琴。事实上,练习任何运动技能都能使之趋于完美。练习不仅改变了突触的功效, 19 新近的研究还表明,活鼠的突触连接会迅速响应运动技能训练,并永久重新布线。 20 训练一只一个月大的老鼠用前肢够取物体,能让树突棘迅速形成(一个小时之内)。训练结束后,一些原有的树突棘消失,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新树突棘得到稳固化,树突棘的整体密度会恢复先前水平。同一批研究人员还发现,不同的运动技能,是由不同组别的突触编码的。好消息是,现在听妈妈的话也不算迟(至少对老鼠来说是这样)。练习新任务同样能够促成成年后树突棘的形成。坏消息是,始终都需要练习。看起来,运动学习是突触重组的结果,稳定的神经连接是持久运动记忆的基础。
联想学习(associative learning)是经验改变神经连接的另一个例子。如果你看过《奔腾年代》这部电影,你大概还记得,人们训练赛马“海饼干”时,听到铃声就要它开始奔跑。铃声一响,驯马师用马鞭在它屁股上抽一下,诱发“逃跑”反应,它就开始跑了。经过多次尝试,只要听到铃声,无需马鞭它也会跑了,最终,“海饼干”跑赢了东海岸的赛马冠军“战将”。
因此,虽然整体连接模式受遗传控制,外部环境的刺激和训练也影响着神经细胞的生长和连接。目前的大脑观是这样:它的整体方案是遗传的,但局部层面上的具体连接是活性依赖的,外部因素和经验都要发挥作用:和任何爱观察的家长或宠物主人说的一样——先天禀性和后天培养同样重要。
我们生而复杂
人类发展心理学中有许多婴儿发自本能地了解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知识的例子。多年来,哈佛的伊丽莎白 · 史培基(Elizabeth Spelke)和伊利诺伊大学的瑞内 · 柏莱乔(Rene Baillargeon)多年来都在研究婴儿懂得多少物理学。这是成年人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知识,可惜很少有人想过它打从哪儿来。举例来说,你桌上的咖啡杯通常不会让你给予太大的视觉关注。但要是你突然看见咖啡杯飞到了天花板上,它必然会极大地吸引你的注意力,你一定会瞪着它看。这有违地心引力。你认为物体要遵循一整套的规律,如果它们不遵循,你就会瞪着它们看。就算你从来没在学校里学过地心引力,你也会死死地盯着那个杯子。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婴儿。如果他的瓶子突然飞到了天花板上,他会死盯着看。
从婴儿会更长时间地盯着不符合一定规律的物体这一观察现象入手,研究人员梳理出了婴儿知道哪些规律。
柏莱乔在3个半月大的婴儿面前放了一个球,接着用屏风把球挡住。而后,她悄悄取走了球。屏风撤走之后,球没了,婴儿们惊讶了。这是因为他们似乎早就领悟了物质无法穿过物质的物理知识。3个半月大的婴儿就懂得物体是恒定的,即便被其他东西遮挡住,也不会消失。
21
另一些实验还表明,婴儿以为物体是紧密结合的,拖拽不应该让它们自然分开。他们还认为物体穿过屏风之后再出现时,应该保持相同的形状:球不应该突然变成玩具熊。他们认为物体应该顺着连续的路径运动,不能跨越空间间隔;他们对部分遮挡起来的形状做出假设:遮挡之后露出半个球形,取消遮挡之后就应该是完整的球形,而不应该有腿。他们还以为物体靠自己无法移动,除非有东西碰触它;物体应该是实心的,不能穿越另一物体。 22 这就是遗传决定的知识,我们生来就有的知识。我们怎么知道这不是习得的知识呢?因为不管此前接触过什么样的内容,各地的同龄婴儿都知道这些事情。
人类的视觉系统,似乎也内置了先天复杂性。在人类的感知层面上,还有其他许多内置的自动流程。比如,在视觉领域,你所看到的东西,不一定符合事实。人们早就知道,把两个度量光强度相同的方块放在不同的背景下,亮度看起来就不一样了。黑色背景下的灰色方块显得比白色背景下的同色方块更亮,见图1—1。

物体的照度基本上由照在它上面的光、物体表面的反射、观察者与物体之间所隔的空间透射度(比如有没有雾,有没有滤光镜等)所决定。对物体照度的感知叫做亮度。然而,物体的照度及其感知亮度之间并不呈简单的对应关系。光到达眼睛的相对强度,取决于这3种变量的组合。举例来说,你坐在一间有4面墙壁的房间里。墙面刷的颜色相同,但若是照度不同,某一面墙可能显得比其他几面墙更亮。故此,视觉刺激源和组合生成刺激的元素之间并没有固定的关系;视觉系统无法判断这些元素是怎样结合起来,在到达视网膜的图像上产生照度值的。
为什么演化出的是这样一套系统呢?杜克大学的研究员戴尔 · 珀维斯(Dale Purves)、博尤 · 勒图(Beau Lotto)和同事们指出,成功的行为需要反应与刺激的根源相协调,并不需要与刺激的量度属性相协调;这一点,只能依靠过去的经验(包括个体的过去和进化层面的过去)来学习。 23 例如,了解挂在树梢枝头的成熟水果的照度,比了解它的具体光学特性更有利。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视觉回路和所得的感知是根据过去视觉引导行为带来的成功所选择的。
“倘若刺激与处于同一发光体下的类似反射性目标表面相一致,目标物体就将呈现类似的亮度。然而,要是刺激与视觉系统对不同发光体下不同反射性物体的过往经验相一致,目标物体就呈现不一样的亮度。”
24
关键在于,我们在认知上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视觉感知系统通过选择过程,进化出了这样一种内置的复杂自动机制。
古人类学家估计,现代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生活在距今500万至700万年前。出于某种原因(大多数说法是,天气变化造成了食物供给上的变化),我们的共同祖先分化了。有几次尝试一开始就弄错了,也有的分支进化到了一定程度后无以为继,但最终,一条分支演化成了黑猩猩,另一条分支则成了智人。尽管我们智人是这条演进路径上唯一存活下来的原始人类,但还有许多原始人类出现在我们之前。这些原始人类残留下来的少数化石,为我们提供了人类进化的线索。
最初的两足行走祖先
有一种原始人类的化石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74年,唐纳德 · 约翰森(Donald Johanson)发现了第一个约400万年前的非洲南方古猿残存化石,震动了整个人类学世界。人们找到了这只古猿近40%的骨架,它的盆骨部分说明它是雌性:也就是现在著名的“露西”。令人吃惊的不在于发现了露西,而在于“她”双足行走,却并不拥有体积庞大的大脑。在这之前,人们认为,我们的祖先是先进化出了庞大的大脑,有了复杂的想法,才带来了两足行走。
几年后,在1980年,玛丽 · 利基(Mary Leakey)发现了约350万年前的非洲南方古猿足迹化石,它和我们的足迹有着几乎相同的外观、形状和重量分布,为两足行走先于大脑进化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最近,蒂姆 · 怀特(Tim White)和同事又找到了若干化石,其中有一只约440万年前的始祖地猿的脚,它尚处于四足行走到两足行走的过渡状态。 25 现场科考小组每发现一块化石,理论学家们就被迫回到绘图板前重新绘制人类的进化路线图。现在,蒂姆 · 怀特和他的国际团队提出,我们与黑猩猩最后的共同祖先并不像先前普遍以为的那么类似黑猩猩。两者在进化之路上分道扬镳之后,黑猩猩本身也经历了很多的变化。
有一位从事相关工作的理论家、心理学家列昂 · 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对现代人类的起源甚感好奇,他想知道,我们的祖先到底在哪一代上可被视为最早的人类。他指出,两足行走“几乎是一种灾难性的不利条件” 26 ,因为它极大地降低了奔跑和攀登的行动速度。此外,四条腿的动物靠三条腿仍然能对付着跑动,两足动物要是有一条腿受伤就没法跑了。这一缺点显然让后者在天敌面前更为脆弱。
转为两足动物,还带来了另一个不利之处:产道变小了。从物理上看,若有较宽的盆骨,就无法两足行走。在胎儿时期,灵长类动物的头骨是几块夹着大脑的平板,要到出生之后才合并到一起。这既可以让头骨保持足够的柔韧度,以便顺利通过产道,同时也让大脑在出生后继续发育。人类婴儿出生时,大脑的个头与黑猩猩婴儿相近,但发育却要滞后一些。因此,与其他猿类相比,我们出生过早,造成了另一缺点:人类的婴儿更加无助,需要照顾的时间更长。然而,出生之后,人类孩子的大脑发育和黑猩猩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人类孩子的大脑在整个青春期持续扩大,个头增至最初的3倍,并伴随着各种改进和影响。最终,它的重量达到1 300克左右。相比之下,黑猩猩的大脑在出生时就几乎完全发育了,成年后仅重400克左右。
两足行走必然具备某种能让我们祖先存活并成功繁殖的优势。费斯廷格提出,这些原始人类所具备的优势,不在于他们拥有了两条能够自由使唤的前肢,可用于除了运动之外的其他事情;而在于他们拥有了创造力十足的大脑,能为前肢琢磨出新的用法:“胳膊和手不像腿,有着专门的用途。人为胳膊和手发明了多种用途——这里的关键词是‘发明’。”欧文 · 洛夫乔伊(Owen Lovejoy)对始祖地猿化石做了猜测,认为雄性通过“以物换性”的方式,用前肢替雌性搬运食物,引出了一整套的心理、生理、行为和社会变化。
27
费斯廷格提出,独创性和模仿性推动了大脑的进化:“生活在250万年前的人类,并不需要全都冒出制造带锋利边缘工具的想法……只要有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发明了一种新流程,其他人就能够模仿并学习。”我们人类所做的大多数事情,最初都是某一个人先大胆吃螃蟹,之后由其余的人竞相仿效。是谁用那些看起来平凡无奇的豆子里做出第一杯咖啡的呢?是一个跟我有着不同大脑的人。然而,幸运的是,我不必自己重新发明轮子。我可以利用另一个家伙的聪明点子。发明和模仿在人类世界里无处不在,可在我们的动物朋友身上却惊人地罕见。
运动速度减慢和天敌更多,表面上看是劣势,实际上却是许多认知变化的重要催化剂。早期擅长创造的大脑必须首先解决天敌问题,“需求是发明的动力”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智胜天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更大更快——这个选项已经不具备可行性了。另一种则是大规模群居,加强巡视,增加保护,同时让捕猎和采集变得更为有效。多年来,在寻找是哪些力量驱动了原始人类大脑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人们推敲了许多设想。现在看来,有两种因素推动了自然和性别选择的过程:由于大脑变大,新陈代谢也随之提高,人类需要饮食能提供额外的热量;为获得保护而大规模群居,带来了各种社会挑战。
我们拥有的这个大个头大脑,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原因所在吗?
人类的大脑不仅胜在个头大
查尔斯 · 达尔文最先提出了这个观点:人类的能力仅仅是体积较大的大脑的功能。他写道:“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的区别固然很大,但它无非是程度上的区别,而非性质上的区别。” 28 他的支持者和盟友,神经解剖学家赫胥黎(T. H. Huxley)更是认为,人类大脑除了体积之外,没有其他独特的地方。 29 直到20世纪60年代,此看法一直是主流:人类大脑和我们其他灵长目近亲的大脑只有体积上的区别。
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的拉尔夫 · 霍洛韦(Ralph Holloway)决定站上擂台跟前人过过招。他提出,认知能力的演进变化是大脑重组的结果,并不仅仅是体积变化的结果。
30
他写道,“我是1964年在一次研讨会上做陈述时得出这个结论的。当时,我举例说明,一些小脑症患者的大脑体积连某些大猩猩都比不过,可他们仍然能够说话。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他们的大脑组织和类人猿是不同的。”
31
最终,到1999年,托德 · 普罗伊斯(Todd Preuss)和同事们为霍洛韦提供了一些物证。他们最先找到了猿和人类大脑组织之间的微小差异。
32
进化生物学家威廉 · 德 · 温特(Willem de Winter)和查尔斯 · 奥克斯纳德(Charles Oxnard)提供了更多支持的证据。他们认为,大脑具体部位的体积,与该部位对大脑其他部位的功能关系有联系。他们将363种动物的大脑部位比例做了多变量分析(同时分析多个统计变量),发现大脑部位比例相似性较强的动物群,往往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运动、觅食和饮食),但系统发育(进化)上的关系并不太强。例如,新大陆食虫蝙蝠的大脑部位比例和旧大陆食肉蝙蝠联系更紧密,却跟血缘关系更近的新大陆食果蝙蝠不那么相似。
德
·
温特和奥克斯纳德的分析显示,同一生活方式分组内的物种有着相似的大脑组织:大脑关系的收敛性与相似性,跟生活方式的收敛性与相似性相关度更大。
33
在所研究的363种动物当中,人类是唯一有着两足生活方式的物种。他们发现,人类和黑猩猩的大脑组织的差异非常明显,达22标准差之多(标准差测量的是平均值附近的数据分布。如果标准差大,那么数据的变化性就大。如数据呈正态分布,那么它通常会落在平均值的3标准差上下范围内)。故此,研究人员总结说:“人脑组织的性质和黑猩猩非常不同,而黑猩猩的大脑跟其他类人猿并没有太多区别,甚至跟旧大陆的猴子没太大区别。”
34
达尔文认为大脑只存在程度上的变化不足为奇。尽管所有的物种各有其独特之处,但却都由相同的分子和细胞构成,也基于相同的自然选择原理演进而来。此前做出的各种假设,都基于如下先决条件:只考察了人类的独特性。然而,耶鲁大学的神经解剖学家帕斯科 · 拉吉克(Pasko Rakic)对我们提出了一点告诫:“我们免不了迷惑于各物种间皮层组织的惊人相似性,却忘了我们应该寻找差异之处,人类认知能力提升的演进进步来自这些差异。”
35
人的大脑跟其他动物的大脑有着怎样的不同,其他动物的大脑彼此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它到底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的区别——围绕这些问题,各方意见的分歧还会持续下去。但有一个支持性质差异的证据相当引人注目。杰出的心理学家大卫 · 普雷马克(David Premack)多年来尝试教黑猩猩使用语言,他的立场和拉吉克一样:“展示动物和人类能力之间的相似性,会自动触发下一个问题:两者的差异性是什么?这个问题能避免人们误将相似性视为等同性。”
36
普雷马克强调的一个主要差异是,其他动物的能力不能推而广之:每一物种都有着极为有限的能力范围,而这些能力都只是为单一目标而适应发展出来的:灌丛鸦只为了将来的食物这一个目标做计划,完全不考虑其他的事情,它们不教学,也不在野外制造工具。乌鸦会在野外制造工具,但它们只是为了获取食物,它们不做计划,也不教学。狐獴不做计划,也不在野外制造工具,但它们会教幼崽,虽然只教一件事:如何不挨蛰而吃掉毒蝎子。它们无法把自己的技能适应到多个领域去。狐獴教育幼崽如何安全地吃蝎子,人类则可以教育孩子一切事情,并且,教学的内容通常可以推广到其他的技能上。简而言之,教育和学习得到了推广。
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能力的核心构成也是从具体的适应演进来的,人类拥有大量以这种方式演进来的高度精练的能力。这些能力结合起来,引出了解决一般性问题的额外能力,最终形成了人类独有的各领域通用能力。于是,人类的能力获得爆炸性发展,人类的条件全面就绪。现代神经解剖学家很快就会指出,当你顺着灵长类动物的树枝爬上人类这一级,你就不再是一项项地增加额外技能(这是过去的假设),而是你的大脑得到了彻底重组。
三位一体大脑模型由保罗·麦克莱恩(Paul Maclean)提出。依照这个模型,大脑结构以进化发育为基础,由三层构成:最早的爬行动物层,上面覆盖着大脑边缘系统,而最新的一层“新皮层”包裹着前两者。基本上,他认为,随着人类的演进,我们不断增加大脑的层次,就类似你往火车后头挂车厢一样。我把它称为火车式进化论。
当然,还有一个棘手的小问题尚未解决: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人类具备了这种了不起的能力呢?它是怎么来的呢?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为了保住相关研究人员的饭碗,也为了如今的研究生有课题可做,这个谜题现在尚未完全解开。不过,有一部分奥妙已经得到了破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
所有这些对大个头大脑理论(big brain theory)的批评指摘,逼得研究人员使用技术更先进的显微镜,一个个地清点细胞,为细胞染色,确定其详细情况。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大个头大脑理论的基础裂开了一条无法弥合的缝隙。
早在1999年我们还没有接触到显微镜带来的差异之前,有几个问题就曾给大个头大脑理论蒙上了阴影。尼安德特人的大脑比人类更大,但在能力范围上从未展现出超过我们的迹象。放眼历史长河,智人的大脑体积有过缩小的阶段。我是在研究接受裂脑手术的癫痫症患者时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裂脑手术将连接大脑左右半球的大片神经(也即胼胝体)切断,防止电脉冲扩散。然而,孤立的左脑(无法从右半球获得任何信号输入,本质上也就是体积减半)仍然和完整的大脑同样聪明。如果大脑的体积非常重要,你会认为,少了一半一定会影响问题解决和推理能力,但事实并非如此。
主张神经元以数量取胜的观点,现在还面临另一个问题的挑战。马克 · 吐温说过,“有关我死亡的报道太过夸张”,说人类的大脑体积比同等体格的猿猴要大得多,过去也表达得太夸张了。
个头大并不能说明更聪明
2009年,弗雷德里科 · 阿泽维多(Frederico Azevedo)和同事们 37 使用了一种新技术来计算神经元。他们发现,从神经元和非神经元数量的角度而言,人类大脑是灵长类动物大脑的等比放大:也就是说,和我们同体格的灵长类动物理应有这么多神经元,我们并不拥有相对更多的神经元数量。他们判断,人类成年男性的大脑一般含有860亿个神经元和850亿个非神经元细胞;大脑皮质占大脑总量的82%,拥有的神经元却只占整个大脑的19%。绝大多数的神经元(72%)在小脑,它只占大脑总量的10%。他们还发现,人类大脑结构中的非神经元大脑细胞和神经元之比,跟其他灵长类动物相当,细胞数量也跟同等体格的灵长类动物预期数量相吻合。事实上,他们的结论是:人类并不拥有相对于身体更大的大脑,在灵长类动物里不是异数;猩猩和大猩猩则拥有相对于大脑更大的身体,反倒是真真正正的异数。
人类大脑平均拥有860亿个神经元,但有690亿都位于小脑,也即大脑后方帮助优化运动控制的小结构。我们认为负责人类思想和文化活动的整个皮层区域只有170亿个神经元,大脑其余部位的神经元还不到10亿个。额叶和前额叶皮层——涉及记忆和规划、认知灵活性、抽象思维、启动适当行为并抑制不当行为、学习规则、通过感官挑选相关信息的大脑部位——所拥有的神经元数量,比视觉区域、其他感官区域和皮层运动区域要少得多。然而,额叶比大脑其他部位更庞大的地方,在于神经元的树状分支,这可能使神经连接增加。
现在,大脑解剖学家有必要解答这些发现的含义。 如果人类神经元的数量只不过是按黑猩猩神经元的数量等比增加而已,那么,它们的连接模式或神经元本身必然有所不同。
人类神经元的连接模式不同
大脑的尺寸增加,也就意味着神经元的数量、神经连接以及神经元彼此之间的空间全都随之增加。人类大脑皮层的体积约为黑猩猩的2.75倍,但由于细胞体和细胞体所占据的空间加大,人类大脑神经元的数量仅比黑猩猩多1.25倍。
38
这种空间叫做“神经纤维网”,里面充满了由轴突、树突和突触所构成的连接物质。一般而言,这一区域越大,它连接得越好
39
,因为有更多的神经元跟更多更多的其他神经元相连接。然而,随着大脑的扩大,要是每一个神经元都与其他所有的神经元相连接,连接所增加的体积和长度就将遍布增大的部分,这会减缓神经信号的处理速度,整体收益极为有限。
40
实际出现的情况是,并不是每一个神经元都与其他所有的神经元相连接。连接的比例不增反降。到了某个点,大脑的绝对尺寸和神经元总数增加,连接的比例下降,随着连接模式发生变化,大脑内部结构也发生变化。为了增加新功能,连接比例的下降会迫使大脑进行专业分工。一组神经元经内部连接,构成小型局部回路,执行特定的处理工作,并转为无意识的自行化处理。它们把处理的结果传给大脑的另一部位,为得出结果进行的所有计算却并不传过去。所以,正如我们此前讨论的视觉感知问题,处理结果(灰色方块显得更亮或更暗的判断)传过去了,得出这一结论的处理步骤却省略了。
过去40多年的研究表明,人类大脑有数十亿神经元组织成了专门展开特定功能的局部专门回路,它们叫做“模块”。例如,马克 · 莱切尔(Mark Raichle)、史蒂夫 · 彼得森(Steve Petersen)和迈克 · 波斯纳(Mike Posner)做了一次神经影像研究,示范了人类大脑中不同回路并联处理不同输入的一个例子。大脑的一个部位对你听到的词汇做出反应,另一个部位对你看到的词汇做出反应,还有另一个部位对说出的词汇做出反应,它们全都可以同时运行。
41
詹姆斯 · 林戈(James Ringo)意识到,大脑尺寸增大而连接比例降低的需求带来了更多专业分工的网络。他还指出,这解释了卡尔 · 拉什利的大鼠及其大脑等位性的问题:大鼠的大脑太小,并未形成专业分工的回路,后者是较大的大脑的特点。托德 · 普罗伊斯则评论说:“皮层多样性的发现给研究人员带来了太多不便。对神经学家而言,多样性意味着,将基于若干‘模型’物种——比如大鼠,恒河猴等——研究所建立的皮层组织学说推而广之是站不住脚的。”
42
贯穿哺乳类动物的进化过程,随着大脑尺寸的增加,进化历程最年轻的大脑部位——新皮层——不成比例地大幅增加。
新皮层多达6层,由神经元细胞构成,像一张皱巴巴的硕大餐巾纸一样覆盖在大脑皮层顶部。新皮层负责感官知觉、运动指令的生成、空间推理、意识和抽象思维、语言以及想象力。
尺寸的增加受神经形成的时机所控制,而神经形成的时机则由DNA控制。较长的发育期带来了更多的细胞分裂,由此也带来了尺寸更大的大脑。新皮层的最外层叫上颗粒层(Ⅱ和Ⅲ),它最晚成熟
43
,主要是向皮层内的其他区域进行映射。
44
我们实验室的杰夫 · 哈特斯勒(Jeff Hutsler)对于这些层提出了重要的观察报告:灵长类动物的上颗粒层神经元在比例上比其他哺乳动物要增加得更多。它们占灵长类动物皮层厚度的46%,占食肉动物的36%,啮齿目动物的19%。 45 这一层更厚,是因为它在皮层各部位之间有着密集的连接网络。许多研究人员认为,由于这一层连接了运动、感觉和联合区,它大量参与了较高层次的认知功能。不同物种这些层次的不同厚度,或许暗示了连接性相应的不同程度, 46 而连接性,有可能影响了不同物种的认知和行为差异。 47 新皮层尺寸的增加,能够再造局部皮层回路,增加连接的数量。
然而,随着灵长类动物大脑尺寸的增大,在大脑左右半球之间传输信息的粗大神经纤维束——胼胝体在比例上缩小了。
48
故此,大脑尺寸的增大和大脑两半球之间沟通减弱有关系。随着我们演进为人类,两个半球联系得不如从前紧密了。与此同时,每个半球内部的连接量,也即局部回路的数量增加了,从而带来了更多的本地处理。尽管有许多回路在大脑左右两侧对称地存在(比如,右脑有主要控制身体左侧运动的回路,左脑有主要控制身体右侧的回路),也有许多回路是只存在于单个半球的。过去几年,我们了解到,许多动物都有着神经解剖上的不对称性,但人类大脑回路的单侧化程度似乎要大得多。
49
我们与黑猩猩最后的共同祖先身上,一定已经出现了单侧化的部分框架。我的同事查尔斯 · 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和贝蒂 · 弗梅尔(Betty Vermeire)在研究猕猴的面孔感知能力时,发现右脑在猴脸觉察上存在优势;
50
人类大脑在辨识人类面孔时,同样是右脑占优。其他研究人员则发现,人类和黑猩猩都有不对称的海马体(调节学习和巩固空间记忆、情绪、食欲、睡眠的结构),右边比左边大。
51
不过,原始人类分支经历了更进一步的不对称变化。在寻找其他灵长类动物和人类之间不对称性的过程中,人们研究最多的是涉及语言的大脑区域,而这一部分也确实发现了许多不对称的地方。比如,人类、黑猩猩和恒河猴的颞平面——韦尼克区的组成部分,与语言输入相关的皮层区域——的左侧都比右侧大,但人类左半球在微观层面上最为独特:皮层微柱(新皮层6层结构内的单个神经元和其上下层的神经元并排构成的细胞柱,垂直地穿过各层。)更宽,之间的空隙更大。由此带来的不同神经结构可能表明,左半脑会以更详细、冗余更少的方式处理信息。它或许还表明,这一空间内还存在另一未知的构成组件。后语言区和布罗卡区(涉及言语的理解与产生)的皮层结构不对称性同样表明:这一独特能力是由连接性上的变化负责的。
52
在裂脑研究的早期,我们就遇到了另一个惊人的解剖差异。在黑猩猩和恒河猴的大脑中,前连合(连接左右半球颞中回和颞上回的纤维束)参与了视觉信息的传输。 53 然而,我们从对裂脑患者的最新研究中了解到,人类的前连合并不传输视觉信息,而是传输嗅觉和和听觉信息:相同的结构,不同的功能。另一个显著差异是主要视觉通路,它将眼睛的视网膜投射到枕叶(大脑后部)的初级视觉皮层上,猴子和人类都是如此。视觉皮层受损的猴子仍能看到空间中的物体,辨别颜色、亮度和图案。 54 可要是人类患上相同的病变,就不能再执行这些任务,彻底失明了。这种对应大脑片区能力上的差异,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物种的类似结构在运作上存在差异,我们需要对跨物种比较持谨慎态度。
新的成像技术——弥散张量成像,可以映射神经纤维。故此,人类大脑在局部层次的组织方式,研究人员现在可以获取、观察、检测并量化了。通过这种技术,人们识别出了越来越多神经连接模式变化的证据。例如,人类大脑中参与语言活动的白质纤维束——弓状束,跟猴子和黑猩猩有着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
55
人类神经元的类型不同
几年前,我很好奇人们怎么想——是认为不同物种的神经元细胞存在差异,还是全都一样。我问了几位顶尖的神经学家:如果有人要你记录培养皿中海马体切片的电脉冲,事先你并不知道这切片是来自老鼠、猴子还是人,你能分辨它们的差异吗?当时,大多数人都告诉我:细胞就是细胞。它是一个通用的处理单元,人的细胞和蜜蜂的细胞只有尺寸上的差异。如果你适当改变小鼠、猴子或人类神经元细胞的大小,哪怕你有智慧女神的相助,也无法判断它们的差异。但最近10年,出现了一个异端观点:神经元细胞并不完全相像,某些类型的神经元只能在特定的物种身上找到。此外,特定类型的神经元可能会在特定的物种中表现出独特的性质。
1999年,神经解剖学家托德 · 普罗伊斯和同事们找到了神经排列微观差异的第一个证据,它位于枕叶的初级视觉皮层当中。他们发现,人类4A皮层的神经元在结构和生物化学上都跟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在4A皮层中,这些神经元构成了信息传递系统的一部分:将来自视网膜的物体辨识信息,通过枕叶的视觉皮层传到颞叶。它们在人类大脑中形成了网状的复杂模式,而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则是简单的垂直模式。这很出人意料,普罗伊斯指出:“在视觉神经学中,人们有一种近乎坚定的信仰:人类和短尾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56 普罗伊斯推测,这种神经元排列上的演进变化,有可能导致了人类从背景中辨识物体的卓越能力。
这一发现牵连出了其他的事情:要知道,我们对视觉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认识,主要都来自对猕猴的研究。而正如普罗伊斯所指出,上述发现和其他的一些近期研究说明,皮层的多样性给人们早前的假设带来了不便。神经科学家对神经元结构、皮层组织、连接和其相应功能的概括,无不是以对猕猴和大鼠的研究为基础。这一基础的谬误究竟有多大,还有待人们判断,而且,它并不仅限于视觉系统。
就连大脑的基本构建模块,锥体神经元(这么叫它是因为它的细胞体形如三角锥体),也受到了严格的审视。比较神经学研究一直赞美锥体神经元跨物种存在,但这首赞歌唱了几十年之后,2003年,澳大利亚人盖伊 · 埃尔斯顿(Guy Elston)重新肯定了圣地亚哥 · 拉蒙–卡哈尔的独到见解。正如大卫 · 普雷马克担心人们在比较不同物种的行为时把相似性阐释成等同性,埃尔斯顿也哀叹,比较神经学家在研究哺乳动物大脑皮层时,“不少人遗憾地把‘相似’阐释成‘相同’”。这令得人们普遍接受:皮层是同质均一的,由相同的基本重复单元构成,这一基本单元在不同的物种中是相同的。 57 埃尔斯顿认为这完全不合理,“如果大脑中与认知处理相关的区域,也即前额叶皮层的回路和其他皮质区域中相同,它怎么可能执行人类心理状态这样复杂的功能” ?100年前,卡哈尔也认为这不合理。他做了一辈子的研究,得出结论:大脑并不是由相同的重复回路构建的。
埃尔斯顿和其他人发现,在前额叶皮层锥体神经元中,基底树突的分支模式和数量比皮层其他区域更多。这些树突令得前额叶皮层中的每一个锥体神经元具备比大脑其他部位更强的连接性。潜在而言,这意味着,较之大脑其他部位的神经元,前额叶皮层的单个神经元在一个相当大的皮层区域获得了大量更为多样化的输入。事实上,锥体细胞的差异并不仅限于部位差异。他和同事们发现,在灵长类动物中,锥体细胞存在显著的结构差异。 58
还有证据表明,神经细胞并不是在所有物种中都做出相同的反应。神经外科手术取出肿瘤的时候,部分正常的神经细胞也遭到切除。耶鲁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戈登 · 谢泼德(Gordon Shepherd)发现,把这些人类细胞放进培养皿中进行记录,对豚鼠神经细胞也做相同处理,两个物种的树突反应并不一样。
59
人类其他类型的神经元
20世纪90年代初,西奈山医学院的伊斯特 · 尼姆金斯基(Esther Nimch-insky)和同事们决定重新研究一种相当罕见的神经元。这种神经元最初在1925年由神经学家康斯坦丁 · 冯 · 艾克诺默(Constantin von Economo)做过描述 60 ,早已遭人遗忘。
这种细长苗条的艾克诺默神经元和较为矮胖的锥体神经元不同,前者有后者的4倍大,两者在顶部都只有一个尖端树突,但前者只有一个基底树突,后者则有着众多的分支。它们只存在于大脑与认知相关的特定部位——前扣带皮层和额岛皮层。
最近在人类 61 和大象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也确认了它的存在。在灵长类动物中,只有人类和类人猿 62 大脑里找到了艾克诺默神经元,人类最多(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均如此)。研究人员发现,类人猿拥有这种细胞的平均数量是6 950个,成年人类有193 000个,4岁的孩子有184 000个,新生的婴儿有28 200个。根据它们的位置、结构、生物化学,以及它们涉及的神经系统疾病,加州理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约翰 · 奥尔曼(John Allman)和同事们 63 提出,它们是参与社会意识的神经回路的一部分,并可能会参与快速、直观的社会性决策。
在原始人这条演进路线上,艾克诺默神经元似乎出现在1500万年前人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身上。有趣的是,存在此种神经元的其他哺乳动物,均为同样具备大个头大脑的社会性动物:大象 64 、某些种类的鲸鱼 65 ,还有最新确认的海豚。 66 这些神经元是独立出现的,是驱动进化的例子,也即相同的生物性状出现在进化上不相关的世系。尽管艾克诺默神经元并非人类独有,但它们在人类大脑中的发育程度,却是独一无二的。
2006年,伊琳娜 · 拜斯特隆(Irina Bystron)和同事在31天到51天大的人类胚胎中发现了一种前身细胞,但目前尚未确定它是否为人类所独有。 67 正如前身细胞这个名字所暗示,这些神经元是大脑皮层中第一批形成的神经元。这些细胞没有在其他任何物种中找到等同物。
这些物理解剖学上的差异、连接性上的差异、细胞类型的差异,皆有如山的铁证支持。我认为,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大脑和其他动物的大脑在组织方式上是不同的,等我们真正理解了它,便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何以有别于众生。
我们有着在大量遗传控制下生来就高度复杂的大脑,又靠着基因外因素(导致有机体的基因展现出不同行为的非遗传因素)和活性依赖学习把大脑进一步改良。这是一个结构化的、非随机的、十分复杂的、带自动处理的大脑,具备一套附加了限制的技能集合,还有着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通用能力。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看到,在大脑的不同部位,分散着无数的认知能力。每一种能力,都有着不同的神经网络和系统。我们也有着同时并行运行、分布在整个大脑的系统。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有多个而非一个控制系统。我们的个人叙事,来自这个大脑,而不来自某种外部的精神力量。
然而,前面还摆着许多未解之谜。我们将试着去理解,为什么我们人类能毫无障碍地接受人体的看家机制(如呼吸等)是我们大脑活动的结果,却如此抗拒意识包含在大脑之中的想法。我们还要考察另一个难题: “我们生而具有复杂的大脑,而不是一个能够轻易改变的空白大脑”这个观点为什么是这么难以下咽。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大脑行使职责的方式,以及我们对它如何行使职能的信念和感觉,不光影响了下游的因果关系、观念和自由意志,还影响了我们的行为。
但这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鲍勃 · 迪伦(Bob Dylan)可能会问,理解了我们如何来到这一步,会是什么感觉?好奇我们到底是不是自由选择的道德载体,好奇它到底如何运作,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一个人相信人类的意识、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都是确定的,他的实际感觉和其他任何人有什么不同吗?此外,看过两三章之后,理解了哪怕实情不一定如此,我们为什么仍觉得心理上统一且受控制,这又会是什么感觉?啊……其实没太大不同。
如果你担心的是,了解真相会叫人产生生存危机的话——我想说,没那么严重。毫无疑问,你仍然会觉得控制着自己的大脑,一切归你说了算,归你拍板定夺。你依然会觉得某个人,也就是你,坐在中间做出决定,拉动杠杆。这是一个我们似乎怎么也撼动不了的“超级小人”想象:我们总觉得有一个人,一个小人,一个灵魂,掌控一切。哪怕我们知道所有的数据,知道它是以其他某种方式运作的,我们仍然有着这种大权在握的压倒性感觉。
别走开哦。继续往下看吧。